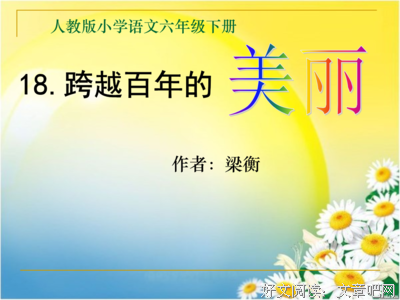
《跨越门闾》是一本由[美] 许曼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页数:43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有句老话形容封建社会中的女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将女性的活动空间限制在家的内部。但中国女性的活动空间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并非自古如此,唐代诗人张的名句就形容虢国夫人,“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可见彼时的女性出门骑马。唐代的女性还喜欢女扮男装走“男友风”路线,唐代末期马缟著的《中华古今注》记载:“至天宝年中,士人之妻,著丈夫靴衫鞭帽,内外一体也。”
及至宋代程朱理学发达,儒家复兴,女性的活动空间较唐代缩小,并出现了裹小脚、虐杀女婴、女子无才便是德等社会现象和思想形态。大多人对宋代女性有着比较刻板的印象,认为她们严格恪守着“男主外,女主内”的规则。华盛顿大学历史系的伊沛霞教授(Patricia Buckley Ebrey)曾于1993年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内闱:宋代的婚姻与妇女生活》,该书被誉为海外研究中国女性史的开山之作。
如同伊沛霞教授一样,美国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历史学系副教授许曼对于宋代妇女的研究不仅仅限于“家的内部”,根据其博士论文所翻译修订的《跨越门闾: 宋代福建女性的日常生活》试图将不仅将目光局限于“內闱”,而是将其扩展至门闾之外。
许曼教授毕业于北大,曾经师从著名的唐宋女性史专家邓小南教授,获得硕士学位后赴美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攻读博士,并于2010年获得博士学位。几千年来女性没有书写历史的权力,留存下来可供研究的女性相关资料较少,往往支零破碎不成系统。《跨越门闾》通过正史、政府文献汇编、法典、地方风俗志、笔记小说、诗词、绘画、传记、家谱、墓志等可获得的现存史料,试图超越传统框架,重构宋代女性在家庭内外的日常生活场景。之所以选择福建的女性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宋时福建经济发达,留存史料较为丰富和集中。
门,是家通往外部空间的隔离;闾,本意为宋代城市基本结构“坊”的门,至今福州仍保留着“三坊七巷”。宋代福建女性的日常生活在许曼教授的史料勾陈中渐渐被还原,宋代的精英阶层女性主持家中财政、为身为官吏的男性亲属提供行政或技术建议、和丈夫及亲戚出名旅行,投身于地方公益事业、积极参与宗教活动。与此同时,宋代的贫民女性们则因为生计而必须抛头露面。总之,宋代的女性生活丰富多彩,并未严格遵循“男主外,女主内”的规则。
通过史料的分析对比,相较明清时期的女性,宋朝各个阶层的女性享有相对的自由。宋代更依靠社会地方的自制,朝廷并未直接参与许多规章的制定;而明清的政府则更加集权化,将诸多儒家理学思想作为国家制度而推行。
许曼教授认为,在现实中,在当时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占主导地位的隔离女性或者束缚女性的意识形态。可以看到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认知上,许曼教授受到伊沛霞教授的极大影响,她们虽然承认“宋代存在着权力结构的不平等,同时却不会认为存在一种女性必然受到迫害的单线叙事,相反宋代女性具有让自己在现有框架下尽可能获利的能动性”;她们也同样强调宋代理学的理论理想和实际聚体施行不一致。
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韩明士教授(Robert Hymes)曾于1997年在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HJAS) 上发表对《内闱》的书评,指出“不应该把文化、体制当成是一种无所不包的统一体系,相反,它是变化多样、多条线索交织在一起的、不可能通过单线叙事就能阐明的复杂的社会现象的表象。”私以为,这一评论同样可以适用于《跨越门闾》。在有限的史料以若干个体推导出社会的意识形态和规则,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幸存者偏差,也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跨越门闾》读后感(二):挖掘宋代福建女性的生活日常
提到古代富贵人家的女子,传统戏文故事里总给人一种刻板的印象,说这些夫人小姐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平素只能蜗居在各自的内宅里,倚个楼台、逛个后花园、有才学的还可以弹琴论诗聊表慰藉,这些大概就是她们生活的主要内容了。
一道深宅大门真的就圈定了古代女子的全部生活空间么?还真不是。
从各类古装剧里可以看到,女子不仅要持家,包括打理家族的产业、维持家庭秩序,更要走出家门去维护自家与不同家族的友好关系,甚至在必要时助力丈夫的仕途或者事业。可以说,女性在家庭中扮演着与男性互补的重要角色,共同支撑起了家庭的重担。
这不仅仅是影视剧的构想,也是有历史依据的。师从邓小南教授、现任职于美国塔夫茨大学历史学系的许曼教授,在《跨越门闾》这本书中,收集并研究了考古学和古代文献资料,从中整理出宋代福建女性的日常生活片段以及精英士人阶层对女性日常活动所持的态度。从许曼的论述可以见得,宋代女生的日常生活早已跨越出门闾的界限向外扩展,被广泛认为明清时代女性才拥有的自主性和机动性,在宋代女性身上同样有所体现。
门闾之内,勤善持家
门是一座宅院与外界之间的关卡,开门则能与外界顺畅联通,关门则与外界隔绝,承担了隔离和联系的双重功能。一定意义上说,古代的门把“家”性别化了,或者说把家庭责任从性别角度作了区分:男性自由出入外界,负责对外事宜;女性则被约束在大门之内,承担内部职责。门限定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这正符合了《礼记》中所提倡的理想状态,“男不言内,女不言外”。
其实,“主内”绝不是轻松的事,日常要服侍公婆、烹饪、纺织、协调家庭关系和纠纷,更要打理好家族产业、管理财务收支平衡,责任重大。尤其是在大家族,女主人是否善于持家,对这个家族的兴衰异常重要。从墓志铭来看,北宋男性墓志铭中关于理财的信息比较多,到了南宋,理财事宜更多地归到女性身上。治家理财能力强的女性,能够赢得丈夫以及整个家族的认可和尊重。比如翁福清的妻子刘氏,在翁福清去世后一直掌家,把家族管理得井井有条,一家八十人,保持四代同居。这是相当厉害的成就。
有些事情是难免需要跟外界联系的,比如女性把做好的纺织品卖出去,这同时又给家庭带来了额外的收入。有时候,外界也会主动把信息传递到门闾之内,比如官方赠与的表扬孝女、节妇等道德模范女性的匾额,就会挂到门闾之上。闾是坊门的意思,坊是宋代城市布局里的基本居住单位,类似现在的居民社区。把匾额挂在门闾之上,以示表彰并鼓励他人效仿,把门闾变得更加公开化了。这也意味着门闾所代表的“公与私”“内与外”的界线有着一定的弹性,并不是那么固定死的。
出入门闾,有限隔绝
宋代的女性当然也会出门,除了探亲访友等必要的事务之外,还可能有短途的游玩等娱乐活动。但她们不能像男性那样完全自由地进出,光明正大地抛头露面,而是采取了有限的隔绝方式,包括坐轿、坐车或者戴面纱,以此来保护隐私。
宋代虽然颁布了禁奢令规定上层女性乘坐轿子的装饰,但是也很难明确地把官宦家和平民家的轿子区分开来。福州和泉州地区女性轿子独有的金漆装饰倒是特点鲜明。另外,这两个地区女性轿子的抬轿夫,大多是女轿夫或者僧侣,这也是独特的地方风俗。女轿夫和僧侣,为轿中女性形成了一个相对安全的人际关系界线,避免了轿中女性与“外男”的不必要接触。这也算是既允许女性走出家门同时又保持对外界隔绝的变通方式。
讽刺的是,这种方式,让坐在轿子里的上层女性得以保持了与外界的有限隔绝,而处于底层的女轿夫则直接置身于大众面前,毫无隐私性可言。所以,平民阶层的女性所受到的内外隔绝的约束规则,看来比上层女性要宽松。
门闾之外,造福一方
门闾完全没有困住有能力、有想法的宋代女性。她们的个人价值,不仅体现在治家能力上,在社会福利方面,同样有所作为。有经济能力的女性,往往拥有经济自主权,会主动参与地方性质的水利、教育、赈灾慈善等关乎地方福祉的公共事务。
据说在北宋时期,来自福州长乐县的钱四娘,带了大约十万缗的黄金去莆田濑溪试图修筑一座水坝用于灌溉农田。虽然水坝修筑失败,但钱四娘的投身公共事务的做法确实赢得了精英士人和当地人的尊敬和称许。
跟钱四娘类似,还有不少宋代女性都积极参与社区和地方的公共事务,勇于承担起社会责任,在地方上拥有很大的影响力。虽然不能排除这里面有追逐地方名声的因素,但她们所做的事实实在在地造福了族人和当地百姓,对地方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宋代女性的社会责任感也得到了精英士人的肯定,对她们采取了开放的态度。只要她们的想法或者建议“听起来合情合理且富有成效”,男性会很支持和欢迎女性亲属关注和参与地方政务。
门闾内外,思想娱乐
古代大家闺秀多受过良好的教育,琴棋书画以及诗文方面都有一定的功底。虽然这方面留存的记录很少,但女性在自己的私人生活空间有一些私人爱好和文雅的娱乐生活也是不难猜测的。
南宋姚勉的妻子邹妙庄就是一个喜欢读诗和旅行的女性,跟丈夫兴趣相投。姚勉亲自给妻子撰写了墓志铭,记录了妻子曾经在旅行中即兴创作的一首诗,可见他对妻子的才华很是欣赏和肯定。
宋代福建地区佛教盛行,很多女信徒都潜心理佛,甚至把宗教活动当作日常事务。关于这一点,其男性亲属的态度就各有不同了。有些坚决反对,并力劝妻子改变信仰,有的则持相对开明的态度。不论如何,宋代女信徒始终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她们在家静思、念咒、抄经,在外还会去寺庙参观、学习经课、观看仪式、捐赠造像,或者制作佛教刺绣图等手工艺品,活动形式多种多样。总之,她们保留了个人信仰的自主权,积极地发展个人的思想爱好,私人生活也是丰富多彩。
总之,许曼教授尽可能地在《跨越门闾》中展现了宋代福建女性的日常生活。她们不仅勤善持家,尽到家庭职责,还在能力范围内积极参与地方公共事务,为地方谋福祉,更保留了思想信仰和兴趣爱好方面的自主性,拥有独立的私生活空间。她们的所作所为,拿到今天,依然值得肯定。她们并不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死板形象,而是有血有肉、精彩生活、实现个人价值的鲜活个体。
2019.08.20雾凇
图片来自网络
说起传统社会的女性生活,一般人想像中大抵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景象。不过,正如英国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早就质疑过的,一个阶序严明的均衡体系只是一种幻象,而现实社会永远不可能符合那种完美的模型,会出现千差万别的情形,并且不断在相反相成的力量推动下动态调整。照这样看,严格意义上的“内外有别”也可能从未达成过,就像“男女平等”虽然是现代人所公认并追求的理想,但谁也不知道它哪天才能一丝不差地完全落实。
历史学界早已开始质疑原先那种儒家伦理主宰的历史叙事了。在妇女史领域,挖掘女性的声音、重新理解她们的社会角色和自我认识,一直都是主基调。前些年就有一部北美学者的论集《跨越闺门》,揭示明清时期的女性活跃在闺门之外的公共生活中,许曼这部《跨越门闾》虽然乍看书名和主题类似,但论述则更为严密,因为她并不仅仅是把“闺门”作为某种象征,而意在探讨女性生活的空间意义。最终她发现,虽然儒家伦理规定家里的“中门”是女性不能逾越的,但对宋代福建大户人家的女性来说,那其实是个有弹性、可渗透的边界,在现实中她们仍然能有一定的自主空间。不仅如此,儒家礼仪也并不只是铁板一块的教条,很多精英士绅在现实中对女性其实灵活而务实,就算是朱熹这样的大儒,也很清楚“礼顺人情”,需要对具体情形有所因应调整。
在传统社会中,“家”是对中国人最为重要的生活空间,而家“门”(“闾”是几户人家的坊门)则在这个空间中标出家族与社会的分界;不过,虽然礼法总是提醒人们:一个恪守礼法的女性尤其应当注重“内外之别”,“中门”还为女性划定了一个不受干扰的安全地带,但事实上,它并不是不可跨越的。要从零散的史料中拼贴、复原这样被湮没的图景需要深厚的功力和敏锐的问题意识,许曼从诸多方面看出宋代社会女性所享有的社会地位和自由度:士绅对母亲的尽孝、对女性乘轿外出的普遍接受、妇女在地方社会生活的能动性、对女德和“贤内助”的赞赏,墓葬形态和墓志也表明她们在家里的地位得到了更多承认而非一味压抑。这些看起来都不符合以往那种单纯将女性看作被隔离在家庭内部的单调设想。
女性“跨越门闾”,乍看只是空间上的渗透、流动,但在社会观念中,则意味着重大的变化:女性并未只被闭锁在属于“私领域”的家内生活中,而被鼓励和男性一起承担家庭、国家和社会的各种责任。这些事实超出了道德说教的范畴,但其实并未危害到社会秩序,相反,宋代所有阶层的女性在比明清时代的女性享有更多相对自由的同时,看来也帮助构造了一个更好的社会秩序和家庭氛围。
毫无疑问,这些论证都相当扎实,要有所补充都难,遑论质疑,它充分证明:宋代社会的“性别隔离”在事实上是不成立的,内外之间的界限模糊、流动、可渗透,“传统”远不是像我们设想的那么僵化。作为一个例证,它可说也很好地证实了法国民俗学之父阿诺德·范热内普的观点:一个社会中虽然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区隔和分界,有时两个存在根本差异的范畴之间有着鲜明界定(例如“神圣”与“世俗”),但现实中在这两者之间总是有些模糊的接触地带,并通过履行一定的“过渡礼仪”帮助人们完成身份的转化、状态的变换,或是空间的移动。一切坚固的东西,其实早在它们烟消云散之前,就从未停止过流动。
这也显示出,本书并不像它的副标题所谦逊表示的那样,仅仅旨在描写“宋代福建女性的日常生活”而已,而是以此来讨论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命题: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女性,是否真的生活在严格的性别隔离状况中?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这势必动摇以往对中国社会特性的认知。这就是伊佩霞曾说过的:“最好的妇女史并不仅仅告诉我们历史上的女人;妇女史挑动我们重新审视我们对历史和历史进程的理解。”换言之,这是“作为方法的妇女史”,可以由此让我们审视一系列传统的命题是否成立。
那么阻碍女性跨越门闾的那个界限,是否并不存在?答案恐怕也是否定的。在这方面,许曼的结论是谨慎的,她并没有认为宋代女性已经像现代人这么自由,也意识到乘轿出行尽管扩大了女性的传统空间,“但同时也允许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外部空间继续实行性别区隔”。不过,她看起来仍然乐观地强调宋代“福建发达地区的地方社区已经成熟和先进”,因而“为女性提供了各种各样的领域,在这里,她们超越传统的‘家’,并行使她们自己的能动性来扩大和改造其所能得到的社会空间”。在此,她突出了当地的发达,却低估了福建社会长久以来的特殊性:这个滨海角落的省份的文化底层既保留了对女性的崇拜(如妈祖和陈靖姑崇拜),甚至不乏对女性功德的推崇(建瓯有练夫人纪念馆,突出“大德保全州城”、“大德大爱”),但与此同时,它在价值观上却也相当保守。
更重要的是,在传统时代决定女性权利和行动自由的,并不是性别本身,而是其社会地位。这一点伊佩霞在其名著《内闱》中已经点明:虽然女性可以在规定的限度内,灵活地运用法律和社会规范,使之对自己有利,并由此创建自己的生活,然而一个基本事实是“在宋代,把人们视为一个角色经常超过他们的性别”,换言之,“宋代法律不太注意社会性别,在家族中担任何种角色才是基本的、重要的因素”。
瞿同祖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也以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尽管男女权利确实有别,但对古代中国人来说,限制其权利的,主要并非这一点,而是其权力地位。在《中国封建社会》一书中,他进一步指出:“女子是否庶出,毫无关系,而她在夫家或贵为妻,或贱为妾,那时才能决定她的命运。”因为儒家伦理其实是社会角色本位,性别只是其中一端,但更重要的是身份地位——简单地说,一个女性是女儿、婢女、妻子还是母亲,所要遵循的社会规范和受到的对待将截然不同,尽管她们都同样是女人,否则就没有“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这个说法了。
许曼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肯定了宋代女性的自主性,但她搜罗史料殆尽,却没怎么引用法律文献。相比起来,伊佩霞的《内闱》立论则大量依赖从法律视角来确定宋代女性的真实社会地位,并结合复杂的社会趋势变动,得出了不那么乐观的结论:宋代社会观念所体现出来的对女性本质的认识表明,人们认为女性“完全克制欲望才算是伟大”,其结果是,赞赏女性本身就强化了父权制,“抬高有胆量、顽强、自我牺牲的寡妇就像在赞扬有勇气的女人,但是潜台词是女人确实需要男人”。据此她认为,宋代女性的社会参与所形成的总体冲击不应高估,因为最关键的一点是:“在很多领域里她们的行动几乎都完全凭着周围的男人的判断,考虑什么可以容忍,什么应该反对,什么将成功或失败,令人愉快或不令人愉快,招人喜欢或令人厌恶。”
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精英女性在公共生活中的活跃,并不能证明女性作为一个群体已普遍享有权利与自由。比照一下当代的例子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韩国、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都曾出现女性领导人,但这并不妨碍这些国家仍是根深蒂固的男权社会,因为“女性”的身份对于这些精英女性赢得社会声望,远不如她们出身名门这一点重要。或许可以这样问:古代有性别政治吗?恐怕只有女性从社会结构中脱嵌出来的现代社会才有。讨论宋代女性的处境,对现代人有意义,但对她们自己却可能并无多大意义。
虽然本书强调宋代女性享有权利与自由和当时士绅对待女性的灵活务实,但在我看来,正是这一点,确保了一个弹性的传统伦理结构。在中国社会的政治实践中,向来就清楚这一点,因为再好的理念要落实,也要“看情况”。也就是说,规范是指导性和支配性的,但又是实践性和流动性的,俗称“因地制宜”、“理论结合实际”,切忌“一刀切”。正如沈洁在《民国的“失传”》中所发现的,虽然国家批判和禁止民间迎神赛会,但这只是作为言说姿态,是一种话语的策略性表示,“‘示禁’而实际‘未禁’的实践表明,在无碍于公共治安及社会安宁的情况下,信仰空间是可以在新的统治秩序内保留和继续的”。然而,不难想见,这既不意味着这些“迷信活动”可以不受打压地自我正名,也不意味着它们可以在官方划定的“尺度”之外自由地存在。
吊诡的一点是:宋代女性看似获得了一定的权利与自由,但却因此更难“跨越门闾”了——就像“透明天花板”一样,那道“透明的门槛”看上去不存在,其实却又是存在的。许曼只注意到“门闾”作为一个边界是有弹性的,容许一定的逾越,但没看到另一面:一个富有弹性的控制体系也更为强大。如果反过来解读,这就意味着,女性的权利和自由只有获得社会承认的前提下才能正当化,只有她的所作所为符合妇女规范,才能赢得尊重。在这个尺度内,女性不能完全发挥主体性来为自己争取,而只有在规范允许的框架内,其权利诉求才能得到承认——当然,公平地说,即便是对男性、即便在现代社会,也是如此。
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框架之下,女性最好的策略,不是激烈反抗社会规范,恰恰相反,她要表现出对社会规范无可挑剔的遵守,才能赢得社会同情和一致称赞——要获得和利用权利,就必须反过来显得更捍卫原则。虽然每一种性别意识形态的内部都会存在罅隙与矛盾,但对女性而言,通往自主权利的道路本身却要求她不去挑战父权制的秩序本身。人类学者Margery Wolf曾说成功的中国妇女“学会了主要依靠自己,但同时表现得依靠父亲、丈夫和儿子”,也就是说,她们不是从中脱嵌出来充分追求自己的主体性,而是在社会规范允许的框架内尽量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其结果,女性的角色规范和自我意识深嵌在结构中,被结构所容许,褒扬与奖励最终服务于驯化与控制。实际上,往往正是弱者更觉得有必要去遵守社会规范,因而男性精英的“灵活务实”与其说是对女性的善意,不如说是他们的特权。在《群氓之族》中,一个婆罗门孩子招呼老贱民进家门,老人眼神严肃地看着他说:“小主人,你可以放弃你的宗教,但我们还没有放弃我们的。”这也解释了那么多古代才女的轶事中,为何她们比其男性亲属更坚守女德规范:因为如果她们真的突破了那道边界,那就很可能不再能得到社会承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那道门槛其实远比表面看上去的更难跨越。
*已刊2019-10-21《三联生活周刊》,有修订 ---------------------------------------------------------------------------
勘误:
.42:安乐哲(Angela Zito)这样解释:按,“安乐哲”是汉学家Roger T. Ames的中文名,而Angela Zito的中文名为“司徒安”,p.323/414同改 p.354:毕阮《续资治通鉴》:p.384作“毕沅”,是 p.357:在李纲过世60年后,朱熹在邵武军撰文歌颂了官方对李纲的祭祀:按,李纲去世于1140年,而朱熹去世于1200年春,似无可能在临终之际还特地撰文。查李纲祠堂建于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朱熹所撰建祠碑记也在这一年,此处之误可能是因朱熹《邵武军学丞相李公祠堂记》原文中有一句“淳熙丙午距公去相适六十年”,而作者误以为是距李纲去世六十年。北宋末年,钦宗擢李纲为尚书右丞,但次年(1126)开封保卫战之后即被强令出京另就,此“去相”事件到1186年确实刚好一甲子。
《跨越门闾》读后感(四):【转】刘云军:走出“内闱”——海外宋代女性史研究视角的转变
伊佩霞《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1993年,时任教于伊利诺斯大学历史系的伊沛霞(Patricia Ebrey)所著《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一书出版。该书被誉为海外中国女性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于1995年获得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此后,海外汉学界涌现了一系列关于宋代女性史的优秀研究著作,如柏清韵(Bettine Birge)的Women, Property, and Confucian Reaction in Sung and Yüan China(《宋元时期女性、财产与儒家应对》,2002),李慧漱的Empresses, Art, and Agency in Song Dynasty China(《宋代后妃、艺术与能动性》,2010),柏文莉(Beverly Bossler)的Courtesans, Concubines, and the Cult of Female Fidelity——Gender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1000-1400(《妓、妾与女性贞节观——十一至十五世纪中国的性别与社会变迁》,2013)等。这些著作,无论是考察宋代女性的财产问题,还是后妃、妓妾等群体,都立足于宋代乃至宋元时期的宏观背景,讨论整个时代女性的生活情况。这种写法的优点在于,可以让人们从整体上了解宋代女性的情况,其不足之处,则是模糊了不同区域的差异,使我们看不到宋代各地女性丰富多彩的生活情况。当然,这种写作模式的长期盛行,考其原因,是受限于现存有关宋代女性史料匮乏与零散的情况。
柏清韵(Bettine Birge)的 Women, Property, and Confucian Reaction in Sung and Yüan China(《宋元时期女性、财产与儒家应对》,2002)Empresses, Art, and Agency in Song Dynasty China(《宋代后妃、艺术与能动性》,2010)Courtesans, Concubines, and the Cult of Female Fidelity——Gender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1000-1400 (《妓、妾与女性贞节观——十一至十五世纪中国的性别与社会变迁》,2013)那么,宋史能否像明清史那样,展开细致的区域史研究?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有成功的先例。早在1986年,哥伦比亚大学的韩明士(Robert Hymes)所著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官僚与士绅:两宋江西抚州精英》)一书出版,便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宋代区域史研究的成功范例(该书获得1988年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受其启发,海外汉学界又出现了一批宋代区域史研究的论著,逐步深化了人们对宋代社会史、经济史的认识。
韩明士(Robert Hymes)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官僚与士绅:两宋江西抚州精英》)2016年12月,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许曼副教授的专著Crossing the Gate: Everyday Lives of Women in Song Fujian (960-1279)出版(中译本《跨越门闾:宋代福建女性的日常生活》2019年6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发行)。该书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吸收并借鉴了海外女性史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丰富成果,展现了一幅宋代区域女性史的生动画面。
许曼 Crossing the Gate: Everyday Lives of Women in Song Fujian (960-1279) (《跨越门闾:宋代福建女性的日常生活》)许曼的本科、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师从知名宋史专家邓小南先生。邓先生对宋代女性史研究颇有建树,在邓小南先生的指导下,她开始宋代女性史研究。博士期间,许曼前往哥伦比亚大学,师从高彦颐(Dorothy Ko)、韩明士教授,继续宋代女性史的研究。正是在这种浓郁的海内外学术的长期浸淫下,许曼敏锐地抓住宋代女性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利用考古资料、地方志等丰富资料,成功地构建出福建宋代女性在家庭内外的生活状态,并进行了生动细致的论述,完成了近年来一部优秀的区域女性史研究著作。
与之前的宋代女性史研究著作相比,《跨越门闾:宋代福建女性的日常生活》(以下简称《跨越门闾》)一书的写作有几个比较大的改变。
首先,研究视角由家庭之内转向家庭之外。从伊沛霞的《内闱》开始,研究宋代女性婚姻、生活、财产、情感等方面的论著层出不穷,这些成果深化了我们对宋代女性家庭生活的了解。但另一方面,关于女性在家庭之外的活动情况则几乎无人着墨。事实上,众所周知,极少女性一生完全封闭于家中,不与外界接触,因此,仅仅研究女性在家内的生活不能勾画出女性的完整人生。《跨越门闾》一书注意到宋代女性研究的这一薄弱之处,便将研究重点放置于宋代女性的户外活动上,探讨了女性进出家门、旅途中的女性、女性与地方社会、女性与宗教、女性与丧葬等内容,基本涵盖了一位女性在户外活动的方方面面,包括她们生前以及身后的户外世界,全面展现了一幅宋代女性在家庭外活动的生动画面。待在家庭中的宋代女性可能“不窥中门”,但女性一旦来到户外,便非常积极地涉足地方福祉、宗教信仰、旅行等,与宋代男性的活动几乎一般无二。这些发现,极大程度上丰富了我们对于宋代女性的认识。
其次,区域女性史研究的成功尝试。之前的海外宋代女性史研究通常采取整体研究,往往由一个主题出发,如财产、家庭生活等,研究整个宋代,甚至更长时间段(如宋元时期)的女性史。这种研究方式的优点是,可以体现“长时段”的视野,容易看出某个问题的历时性变化过程。然而,缺点同样明显,因为两宋跨越近三百年,境内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不同,很难说各地区的女性生活都是相同的。《跨越门闾》精心地选择了宋代福建地区,利用丰富的文献与考古资料,构建出一个丰富的地方女性空间。通过这样一个区域个案研究,可以比对我们之前从宏观上对于宋代女性史研究的一些结论,深化我们对宋代女性的认识。
除此之外,纵观本书,还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史料丰富。众所周知,中古女性史研究的一个难点是史料不足,这也限制了很多问题的深入展开。作为一部福建区域女性史研究著作,《跨越门闾》对于宋代福建女性史料几乎竭泽而渔。首先是大量使用福建地方志文献。由于关于福建的宋代方志只有一部《淳熙三山志》完整保存下来,在本书中,作者利用了多部明清福建方志,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宋代方志不足的缺陷。此外,“为了考察宋代女性的日常生活,对提供来自各个身份群体女性运动和活动的蛛丝马迹的所有史料”(英文版第6页,以下页码均为英文版页码,不另出注),作者都加以留意。因此,本书使用了笔记、碑刻、诗文集、图画、考古报告等各式资料,使得立论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之上。
其次,论述细腻,结论审慎。可能因为作者是女性的缘故,本书文笔细腻,语言流畅优美,可读性很强。另一方面,作者在写作中用笔一直很克制审慎,对于一些史料的分析,并没有做过多的引申和敷衍,相反,一再指出史料的欠缺导致对一些问题的研究难以深入(262页)。比如第一章《进出之门》,作者在论述家庭中“中门”的意义时,一方面强调“中门”在家庭中执行性别区隔的重要性,同时又指出,在穷人家中恐怕(很可能)根本没有“中门”(99页)。“中门”的重要性更多体现在精英家庭中,而且不一定所有精英家庭都严格执行这一规定(30页)。作者还指出,“白天,中门内外男女之间的接触是不可避免的,也许是令人翘首以盼的”,“严格的性别区隔,不一定是正常的宋人家庭的典型做法”(41页)。这些论述无疑会让我们对书中所讨论的问题产生进一步的思考。同时,作者并没有因为研究区域史而过分强调福建宋代女性的特殊性,反而经常提醒读者,福建宋代女性的一些情况适用于宋代其他地区(261页)。
第三,以小见大、多学科交叉研究。《跨越门闾》虽然是对宋代一个地区女性史的研究,但作者的写作目的并不局限于此。本书试图通过对宋代福建女性户外活动的具体研究,进而探讨整个宋代女性史,并更进一步地,与明清时期女性的活动相比较。如作者认为,“与那些明清时期的女性相比,所有阶层的宋代女性都享有相对自由。宋代国家和精英在处理女性事务时,通常采取不干涉的策略”(265页)。相比之下,明清两朝的人则更积极地干涉女性事务。本书虽然是断代区域史的研究,但宏观的视野,呼应了“宋元明转型”的理论,丰富了人们对此主题的认识。
另外,在写作中,作者有意将福建女性置于地方史、儒学思想史、家庭内外、生死问题等大背景中进行考察,使得关于宋代女性的一些问题,得出新的不一样的结论。比如理学家(思想)与女性的问题,本书通过对宋代女性能动性的丰富展示,刷新了我们在传统观念下对理学家刻板形象的认识。从大儒朱熹到一般的理学追随者,其中很多人在处理女性问题上并没有如我们后世想象中那般恪守僵化的教条、压制女性,相反,他们中很多人体谅女性、尊重女性,采取务实而灵活的做法。如此,从女性史角度,对我们重新理解宋代理学思想的理论发展与实际推行之间的差距,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总之,《跨越门闾》一书通过对宋代福建女性诸多方面的描述,向我们展现了宋代女性复杂能动性的一面,对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宋代女性以及宋代社会,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正如邓小南教授所言,“《跨越门闾》力图超越传统框架,重构宋代女性在家庭内外的日常生活场景。作者以福建为重点区域,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深入辨析和细致解读,对物质与图像资料的广泛搜集和切当运用,将女性还原到广阔的活动空间和社会网络之中。在宋代政治、经济及社会变迁的背景氛围下,厘清了儒学理念与地方实践的关联、差异甚至脱节,再现了性别建构中各阶层女性的能动性和灵活性”。
《跨越门闾》读后感(五):【搬运+翻译】跨越门闾:一场关于宋代女性日常生活的访谈丨Crossing the Gate: An Interview with Man Xu about the Lives of Song Dyna
搬运地址:http://thebedrockblog.blogspot.com/2017/09/crossing-gate-interview-with-man-xu.html
对谈人:许曼、布伦丹·戴维斯(Brendan Davis)
编者按:布伦丹·戴维斯先生是一位游戏设计师,擅长做武侠风游戏的设计,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历史专业,因而对历史学研究前沿也十分关心。Crossing the Gate 出版后,戴维斯先生十分喜欢,曾在podcast(相当于中国的喜马拉雅)上对该书做过一个口头介绍和评论,他说,这个书能够给他带来“街景和即视感”。许曼老师说,她有时也会为戴维斯先生和他的同事设计游戏时提供一些建议,帮助他们尽可能地去还原真实的历史图景。
本文由许曼老师提供,刘云军老师翻译。
2017年9月6日 星期三
布伦丹·戴维斯(以下简称戴维斯):
我最近在播客上发表了一篇关于 Crossing the Gate:Everyday Lives of Women in Song Fujian (960-1279) (《跨越门闾:宋代福建女性的日常生活》)一书的评论。并且很幸运地,采访了该书的作者许曼。许曼是塔夫茨大学历史学的教授,专门研究中古与晚期帝制时期的中国,关注地方史、物质文化和社会性别。除了写作《跨越门闾》外,她还以英文、日文和中文发表过许多文章。《跨越门闾》一书由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你可以在这里了解更多相关信息。目前,该书正在被翻译成中文,并将于2019年出版。
戴维斯:
许曼您好,是什么原因让您决定写这本书,为何您把重点放在福建?
许曼:
您好。我的研究兴趣是中古中国的女性与性别。任何关于女性史和性别史的研究都应该是针对特定阶层、地区和年龄的。宋代地域之间,尤其是南北地域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得对地方社会女性史的深入研究成为必要。本书以宋朝东南边陲的福建路为研究重点,该地区在宋朝异军突起。其经济、文化飞速发展,在宋朝成为一个发达地区。它产生了包括朱熹在内的一大批新儒家,而朱熹的思想在晚期帝制中国逐渐成为正统思想。新儒家士大夫在福建的集中,为我们研究新儒家思想与当地女性日常生活的差异与一致性提供了有价值的背景。福建在教育、科举、文化等方面的繁荣,不仅造就了一个拥有大量精英家庭的地方社会,为女性活动营造了良好的生活氛围,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字资料和物质资料,用以复原女性的生活经历。虽然本书是基于特定地区的深入研究,但我相信它的许多结论适用于整个宋朝。
戴维斯:
您如何描述您的历史研究路径?
许曼:
对于研究中国女性史的学者们而言,史料不足被认为是一个严重问题。《跨越门闾》一书详尽搜集了尽可能广泛的现存史料,包括正史、政书、宋朝律令、风俗志、墓志、笔记、类书、诗歌和绘画。此外,它赋予了被社会史学者所忽视的物质资料以应有的价值。本书采用艺术史和考古学的方法,利用了以前未曾被人开发的各种史料,包括考古报告、博物馆藏品以及女性墓葬的发掘来复原从儿童期的社会化到死亡时女性的生命历程,以及女性生产、传播和消费的物品,包括化妆品、服装、刺绣、珠宝、炊具、书法和抄录的经文。对新史料前所未有的使用以及涵盖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女性研究、文学史、艺术史、考古学等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形成了本书在所有中古和晚期帝制中国女性史研究的学术著作中突出的包容性与独特性。
《清明上河图》中骑驴、带着面纱的女子戴维斯:
宋代女性的生活与以后的朝代比如明清时期女性的生活有何不同?
许曼:
在这一长时段框架下,本书一个引人注意的发现是,与明清时期相比,宋朝各个阶层的女性享有相对的自由。宋朝的国家和精英阶层在处理女性事务时通常采取不干涉的策略。国家从未颁布过规范女性日常行为的法令,并将女性民众的管理权交给地方官员。与放任自流的前朝相比,明清两朝在干预女性日常生活方面显得更为积极主动。宋朝与明清时期之间的巨大差异并不意味着在晚期帝制中国女性流动性的下降。在整个中国帝制史上,女性对家庭权威的操纵和对“家”外生活空间的扩张从未停止过。明清性别研究学者在许多方面揭示了女性在“闺闱内外”的能动性。相比之下,如果考虑到宋代政府和学者们对女性更为宽容的态度和正面的观感,明清女性在宋代的女性祖先们可以说生活在一个对女性更加友好的社会。
戴维斯:
您为何选择宋朝作为本书的研究时间段?
许曼:
大多数学者将宋朝描述为中国女性的黑暗时代,他们说,作为新儒家社会秩序基石的性别隔离的一部分,中国女性被限制在家里。在本书中,我认为女性的日常生活与这种意识形态的愿景大相径庭。宋代新儒家恢复并提倡“男主外,女主内”,这一古老观念表明在身体和功能上存在严格的性别隔离。因此,女性被期望限制在闺闱内,只处理家庭事务并与家庭成员互动。本书试图通过考察女性在性别建构中的角色,以及考察新儒家意识形态与女性现实生活之间的差异,将这一简单化的图景复杂化。本书对中古中国关于女性和性别角色的共识提出了强烈的挑战。这是第一部追踪女性在家庭内外跨越阶层的生活经历之多样性的英文著作。
戴维斯:
当时女性的财产权是什么情况?在商业和财产所有权方面对女性有何限制?
许曼:
宋朝女性拥有优渥的继承权,能够控制自己的嫁妆,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政府对女性财产权的立法。她们的个人财产主要包括婚前和婚后从娘家得到的东西。除了嫁妆和遗产,宋朝女性的纺织收入虽然可能有限,却是其能动性的重要来源。此外,一些职业女性积极参与高度商业化的经济。这些人包括稳婆、媒婆、店主、游方的宗教人士、挨家挨户做买卖的织工,以及离开“家”到外面谋生的小贩等等。
戴维斯:
新儒家所表达的性别理想在多大程度上是人们日常生活的现实?
许曼:
新儒家道德人士看到女性在广泛的领域扮演着非正统的角色,他们焦虑地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并在规范性文学中对上古思想进行了重申和重新解读。但我的研究发现,这些学者妥协并接受了不完美的社会现实。与新儒家顽固、教条的刻板印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本书展现了这些男性精英日常生活中更为灵活和实用的一面。他们尊重女性的家庭生活,不直接干涉女性事务,并采取道德说教和经济手段鼓励女性追求“正确”的生活方式。他们或多或少承认女性的价值,甚至支持她们在公共领域的贡献。
戴维斯:
您能谈谈在这个时期缠足的做法吗?它有多普遍?对它是否存在常见的误解?
许曼:
根据一些宋史研究者的说法,缠足对宋代许多男性有着不可抗拒的性吸引力。它最初是娱乐场所专业团体的时尚,随着一些上层社会女性的接受,它变成了中国女性气质的一个重要象征,并一直延续到晚期帝制中国。然而,这种时尚的做法并没有阻止女性走出家门。宋朝女性偶尔会外出旅游,像男性一样使用各种出行工具。她们与外界交流,融入当地社群,与当地政府互动,并光顾当地的宗教市场。虽然男性主导了公共领域,但女性获得并利用了各种进入公共领域的机会。
宋代女子日常服饰 提花对襟上衣戴维斯:
母亲、妻子和女儿在以士大夫为主的精英男性生活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许曼:
精英女性被认为是“内助”。“内助”的角色并没有将女性局限于闺闱内。她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中,不仅要孝敬公婆,协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还要支持丈夫的亲戚,与邻居交朋友,以及帮助当地社群中的人们。与其管理才能一样,她们对当地福祉的贡献有时与其男性亲属在帮助他们“家”建立当地声誉和维持社会地位方面一样重要。
戴维斯:
您的书中最引人入胜的人物之一是刘氏(八七嫂);可以谈谈她以及她是如何获得权力的吗?
许曼:
关于刘氏的记载来自宋朝一部重要的法律判例汇编。她被认定为罪魁祸首和主犯。作为寡妇,她从三四十岁开始犯罪,在被当地法官拘押之前,她一直是当地的恶霸。她的两个儿子生活在其权威的阴影下,听从她的指示,如何建立他们对当地社群的统治。她要么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一大笔嫁妆,要么就是从已故的丈夫那里得到了很多财产。这些财富成为她发展核心家庭在当地影响力的主要资源。她还关注儿子们的教育,并给其中一个儿子购买了官职,这增加了家庭的政治和文化资本。刘氏母子熟悉地方政府的标准职能,努力在现有的地方政府之外建立一个地方行政权威机构。他们的运作方式与地方政府一般无二——建造监狱,裁决当地人民的冲突,雇佣私人保镖,贩卖私盐,征收商业税……实际上,他们通过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建立了一个影子地方政府。
戴维斯:
“家”的概念是本书的核心。您能解释一下什么是“家”吗?为何第一章要着墨于它?
许曼:
本书展现了女性在不同地点的活动。宋代女性合法的生活空间是她们的“家”,这是一种不固定的概念,意味着家宅以及家人。社会规范被家内房屋结构实体化,塑造了女性的空间感和认同感。新儒家提倡物理上严格的性别隔离,并将中门从住宅院落中的一个建筑转变为一种带有明确象征性和物理性的结构,将男性和女性的身体分隔开来。然而,女性在“家”中的主导地位和多样化的家庭经历模糊了内外边界,并修正了可能划分男性和女性领域的建筑物的性别含义。
宋金墓葬中的妇人启门戴维斯:
在最后一章中,您对墓葬进行了广泛的介绍,并使用了已发表和未发表的报告中的所有可用数据对其进行了分析。您是如何进行这项分析的?它揭示了什么?
许曼:
女性的坟墓为我们提供了特别有价值的见解,让我们了解到有关地上和地下生活之间联系的性别规范和信仰。埋葬实践的三个方面——墓室本身的结构、尸体的相对位置以及内部的埋葬物品——提供了线索,让我们探究墓主人的亲戚以及仪式专家对女性所处位置的态度,因为正是这些同时代人决定了坟墓的位置、修建、内部结构、装饰和随葬品。像衣服等随葬品,往往是墓主人生前亲自挑选的;因此,它们构成了一个特别富有成果的场景,用以探讨女性向后代作出的自我呈现。书中对福建宋墓的研究表明,现世的性别差异和隔离并没有被带到来世,在来世,夫妻之间平等、和谐和沟通的观念占主导地位。对福建墓葬结构以及这些建筑内部的随葬器物的分析,展现出了宋代性别化实践的图像,比起单独文本研究所能看到的更加全面。
(本文由《跨越门闾》一书译者刘云军老师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