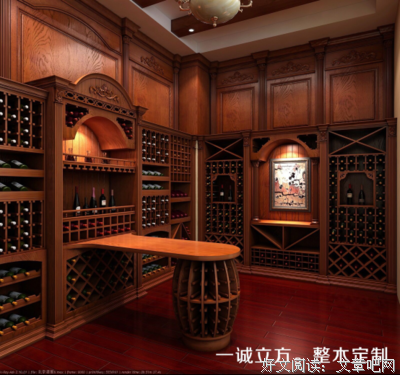几乎在作出职业选择时不怎么考虑世俗定义的成功,而以探索自我为最高追求,这样的人,能在这个世上活下去、活得好吗?
她是一个“向内”的人。
她喜欢独自一人读书、写作、摄影、旅行,诸多热爱背后皆是向内探索自身的强烈欲求。
但她也渴望与外界沟通,她乐于将目光转向他人,想分享自己的热爱之事、与他人交往。
她还渐渐发现,身为女性,自己多年所做的事原来都围绕着一条主线——女性的成长。
“就是特别想弄清楚,一个女性成长、变化的过程,想要知道她遇到了什么,又是为了什么。”
这十年间,她一直都在尝试——能不能以一种自己喜欢且擅长的方式,把自己的所有面向都“有趣地结合起来”?
文|安妮兔
▲主播/夏萌 配乐/first love
1
“做好一件事没什么窍门。无非是,选择做自己喜欢的事,并且尽可能利他。”
这些年来,菲朵自己摸索着,做成了好些事。
它“有趣地”将她摄影师、旅行者、写作者的多个面向结合了起来。
一同旅行的成员都是女性,她们跟随菲朵出行。菲朵不仅是领队,还是旅拍摄影师和记录者。
此前,菲朵曾在《新周刊》《华夏地理》《三联生活周刊》等媒体任职,享受着都市生活的光怪陆离。但她也总能感受到远方的召唤,于是一遍遍出走。
过去的很多年,菲朵只能接受一个人的旅行。她独自一人走过了许多地方。
在旅途中,她曾看过诗意的栖居地,触摸过山脉和胡泊。也见过心怀善意者、智者、可怜人......她与芸芸众生相遇,其中有安慰,也有险情。
说到旅行的意义,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答案。对菲朵来说,“旅行就是寻找回家的路途”。
她相信,如果我们价值的评判标准或者慰藉的来源还是在外在,需要依靠衣食住行,那会是一个死循环。
而旅途是个好的工具,它会让你不停有新鲜感,同时一遍遍回到自身。
“我明白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独自旅行,这其中的累积已经到了可以拿出来分享的时候。我可以给她们带来什么?没有技巧,没有形式,没有捷径……
我所有的,仅仅是出于自然而然的观察方式,以及自我疗愈的分享。”
旅行像面镜子,照出每个人。
有人会跟菲朵说,你说的一定是假的。你拍的那个地方是假的,我看到的那个地方不是这样的。
菲朵一开始对这种个体之间的巨大差异感到惊诧,后来坦然接纳,“你看到了什么,你选择相信什么,都是属于自己的,也都是真的。”
随菲朵一起旅行的女性,大部分是心智和事业都已经相对成熟的个体。旅行对于她们来说是一种出口、一个载体、一种休息。
在这里,他们平时社会型的那个“外壳”可以被卸掉,独立人格可以安然显露。
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立的世界,但她们又可以享受到集体出行的益处,如更安全,可以共享服务、饮食、交通等便利。
菲朵在旅途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拍照,她很沉默,她们也喜欢沉默,彼此都不会觉得奇怪。
“提供服务给他人,原来其实并不需要改变自己的个性。如果你能使得他人得到真正的收获,你是可以被接纳的。”
2
前段时间,有一位年长的姐姐跟随菲朵去了北极。她的父亲刚刚过世,很想去个很冷的地方。
整个旅行是她回忆和父亲的过往时光,坦然进行悲伤和哀悼的过程。
最后一天,她们看到了极光。她告诉菲朵,她此刻觉得很幸福,觉得可以送父亲走了。
拎着相机,菲朵这些年走过了大理街头的青石板,走过拉萨、香格里拉、北京、上海、杭州、成都、厦门;走过尼泊尔、印度、不丹、摩洛哥、丹麦、冰岛、斯里兰卡……
作为一个特殊的旁观者,杨菲朵目睹了她所拍摄的女性的变化,也见证了很多生命的过程,其中一部分人在进行长达十年甚至更久的影像记录。
菲朵拍摄过的女性已经有好几百个。在她的镜头下,每个女性都有自己独特的存在感。或温暖,或柔美,或独立,或坚韧,散发着属于自己的光。
有人问她怎么能够拍得这样好,她的答案是:“我在看她们的时候,其实就是在看自己。我拍的既是她们,也是自己。”
——同为女性,菲朵的镜头就像她的目光,充满接纳、共情。
这个过程是一种双向的滋养。在拍摄的时候,也有很多女性带给了菲朵力量。
▲菲朵拍摄的女性
那一年菲朵在拍摄一个长期专题——“一个人”。她专程来大理找菲朵,成为了那个专题里的女主角。
“我记得那天清晨她远远地向我招手,笑得非常灿烂,然后蹦蹦跳跳地向我走来。好像我们是认识很久的朋友,没有丝毫生分。”
等小倩走到菲朵面前,她才发现,小倩只有一只手臂。因为年幼时的一次意外事故,小倩失去了一只手臂,但这丝毫不影响她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菲朵和她开玩笑,说她是“断臂维纳斯”。
她们在一个早晨进行拍摄。太阳刚从洱海上面升起来。
小倩问,我可以唱歌吗?菲朵说,可以啊。小倩说,我可以脱衣服吗?菲朵说,可以啊。
菲朵被眼前所见震撼到:“她是我拍过所有女孩子里面,对自己身体最坦然的一个,最有自信的一个。”
菲朵也总会想起一个50多岁的姐姐。她来找菲朵拍照的时候是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她拍照是要送给她的孩子。
后来菲朵拍过她两三次,还没有拍完,她就走了。
这让菲朵意识到:“一个女性在这个家庭里面的份量其实非常重,意义非常大。因为一个女性可以影响整个家庭的运作,无论是她的伴侣,还是她的孩子。”
菲朵对女性的成长也形成了自己的感悟——就是她能容纳更多、接受更多。
“比如小倩,她必须去接受她自己身体的现实,知道她是一个这样的女孩。”
▲菲朵拍摄的女性
3
除了摄影,几乎每天菲朵都会拿出一个时间段用于写作。在家人入睡后,她会独自坐在灯下写上两个小时。
“这个部分给我营养很多,它一直滋养着我。至少我不需要通过别的方式,比如酗酒、抽烟、购物解决自己的内在问题,而是通过文字。”
“书写是低成本的,不分年龄、性别,任何人随时随地都可以写,它可以帮助很多人处理好自己的内在。”
就这样,菲朵开始着手尝试另一个项目——“女性的意识”疗愈书写营。
围绕女性的生命历程,菲朵梳理了100多个书写的课题,不同年龄段的女性都有相对应的课题。
这些课题直接跟生命有关,比如“青春期被孤立、被边缘化”,“给未出生的孩子的一封信”,“母女关系”、“一封遗书”等等。
每天一个课题,菲朵会先写一个导语,再由参与者自己写。书写营结束时,每个人都会得到一个完整的探索自我的档案。
长达60天里,一群陌生人自不同的城市前来,他们从最初的互不相识,到一起书写、分享,都不同程度地打破了局限,并且看到了彼此。
书写营禁语,这鼓励每个人充分将注意转向自己的生命体验和内在感受。但通过看到他人书写的内容,真正的支持和疗愈却可以发生。
“你会看到共性,因此发觉自己并不孤单。你也会发现,原来很多人和我不同,也有很多人的生活比我难多了。”
参与者从60后到90后到都有,她们的身份也各异,财务、律师、家庭主妇.....很多人从来没有真正书写过,甚至有很多人对自己和自己身处的世界都是没有敏锐觉知的。
“所以书写这些课题对很多人来说很艰难的,很多人坚持不下来。但这件事至少可以开始让他们开始观察自己、观察世界。”
她真诚地鼓励更多人开始书写。
因为,整理自己,面对自己,写出自己,慢慢就会弄明白你的真实是什么。
书写表达了你的意识,你的价值观,你的一切赞美和批判。你可以从文字里读到自己的痛苦和快乐来自何方。
“最终,写得多了,到最后也许能够站在对岸,如同隔岸观火般地观察自己。”
4
花了十年时间,菲朵终于还是把自己的喜欢变成了人生。
周围人觉得,她总给人一种笃定的感觉。
那种笃定来自于她凭借自己走出来的一条路,来自于她亲自经历的被世界接纳的体验。
如果你问菲朵——在作出职业选择时不怎么考虑世俗定义的成功,而以探索自我为最高追求,这样的人,能在这个世上活下去、活得好吗?
她的回答是:“我觉得自己活得挺尽兴的,没有任何遗憾,未来会一直这样生活下去。”
而让这一切发生,她只不过做到了既看到自己,同时又看到别人。
“每个生命都很美,也都很不容易。都要走自己的路,要爬自己的山,我能做的也不过是努力爬上自己的山头,在暗夜里点亮自己的火焰。即便这火焰只能照亮眼前的一小段路程。”
本期作者:安妮兔-好好虚度时光签约作者,对人类无比好奇的人类,探险者,写作者,印度爱好者。
图片:杨菲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