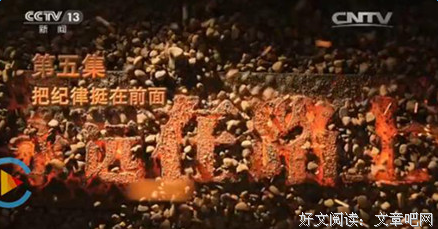《和凤鸣》是一部由王兵执导,和凤鸣主演的一部纪录片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和凤鸣》观后感(一):此影片谨献给生活在革命时期里的革命者和被革命者。
观影有感:
影片开始,冬天,一位老人在无人的小巷里走着,镜头就一直跟在她的后面,然后随着老人来到一处破旧的小区,走进黑黑的楼栋,开门、进屋、坐下,就这样,这位叫和凤鸣的老人开始讲述她的故事了……
片尾字幕是这样写的:此影片谨献给生活在革命时期里的革命者和被革命者。
导演王兵说——
我等到下午四五点的时候去她家。把光锁定后,随着谈话时间的推进,内容、感情越来越激烈,而光越来越暗。她谈到她在极端艰难的时期想自杀。她买到了自杀的毒药,她的小儿子站在门口,叫她妈妈,妈妈,她并没有理会;她讲到她丈夫死了之后,她晚上躺在丈夫住的地方睡觉,她喃喃讲到她内心的冲动,那种特别激烈的冲动,对自我的询问;她讲到30年后又回到她丈夫死的地方去祭奠,看到的残留的坟堆,都让人动容。而光线在叙述中逐渐消失。等天全黑了,我们才全部打开灯。大家才看清楚叙述的老人的样子。仿佛我们都从一个漫长的噩梦里回到有光的现实。
我的影片,不是为了证实一个事件,而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一个人的内心。如果人对人完全失去信任,那我们谈论一切问题就会变得没有意义。世界唯一能够变好,那是人不断地要获得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文化总是在它的进程中不断地,重新地,让人获得信任感。人的意识和文明的进程,总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得到矫正,知识也好,感受也好,情感也好,都是 在这样的变化中调整和矫正。我们不能总是用文本的方式去衡量的世界,如果连常识都不能相信,基本的经验和常识都不能去相信的时候,我们会活在虚无之中。
作为少数几名劳教的女“右派”,和凤鸣在三年劳教生涯中遭遇丈夫离世、家庭破碎后,历经三十年也拒绝遗忘,秉笔直书,用一本耗费十年心神与眼泪写就的四十万言自叙——《经历——我的1957年》,为沉重的时代记忆去魅。
凤凰鸣矣,于彼高岗。
和凤鸣生于1932年,原籍甘肃会宁。因受到丈夫牵连,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8年4月下旬,和凤鸣与丈夫王景超分别被下放到酒泉安西县十工农场与夹边沟农场劳教改造。
根据1980年中央有关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处理反右斗争遗留问题的工作总结报告》,经历过上世纪50年代末的“反右”运动后,全国得到改正的“右派分子”数量为五十五万两千八百七十七人。
女“右派”数字或无法可考,仅以夹边沟农场为例,3000多人中只有19名女“右派”。而和凤鸣所在的安西十工农场,几百名“右派”中也仅有两三名女性。
恰恰是身为女性的和凤鸣,在三年劳教生涯中遭遇丈夫离世、家庭破碎后,历经三十年也拒绝遗忘,秉笔直书,用一本耗费十年心神与眼泪写就的四十万言自叙—《经历—我的1957年》,为沉重的时代记忆去魅。
和凤鸣书写女“右派”的生活,早于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记录夹边沟的苦难,又早于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
《经历》出版十年后,和凤鸣由一个亲历者化作一个记录者,俨然已成为全国夹边沟难友、受难者亲属的联系枢纽。这些年来,好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大龄读者相继去世。和凤鸣一一报出他们的姓名,间或补充几句某人的事迹,表情竟也平静如烟。
当时代悄然变迁,终将翻去这并不明亮的一页时,幸好还有一些记忆固执地镌刻着自己,如和凤鸣。
因言获罪
和凤鸣的家庭出身并不好,父亲1949年前参加过国民党中统组织,判过刑遭下放,失去工作权利。但她正当青春岁月被下放到农场劳教,却是因受丈夫牵连之故。
在进步书籍的影响下,中学时的和凤鸣已被革命洪流深深吸引。她认同孙中山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适逢《甘肃日报》创刊,和凤鸣放弃了到兰州大学外语系就读的机会,向报社递交了两页自传并被顺利录取。这是她纵身跃入革命潮流的起点,也是命运被裹挟的开始。
报社工作开启了和凤鸣作为新闻人的职业生涯,也令她结识了未来的丈夫王景超。王景超是参与《甘肃日报》创刊的元老,报社内公认的一支健笔。热恋时的和凤鸣,曾收到他长达16页的情信,令焦灼的思念融于字里行间。然而败也萧何,当这支健笔迎上“大鸣大放”浪潮,写出几篇批判党员“官本位”思想和滥用“行政手段”的杂文后,竟被戴上“大右派”帽子,被迫了结了自己的新闻生命,还令妻子和凤鸣受到牵连。
革命年代的爱情,往往没有什么浪漫的开始,却要面临“风刀霜剑严相逼”的考验。“反右运动”开展近一年后,1958年4月下旬,和凤鸣与王景超分别被下放到酒泉安西县十工农场与夹边沟农场。
传汉武帝曾赐给击败匈奴的骠骑将军霍去病一壶酒,犒赏军中将士。霍将酒倒入当地泉水中,与诸人共饮,共蒙皇恩,由此有“酒泉”之名,后更传有“葡萄美酒夜光杯”佳句。但与古诗幽情迥异的是,酒泉实际上土地贫瘠,多为戈壁荒漠,时有大风沙,饮水尚且困难,无论美酒,生存条件十分艰难。
尽管如此,和凤鸣与王景超均未想到,此地一别,竟成永诀。王景超在酒泉下车,带着和凤鸣为他购置的新脸盆、一块五一柄的牙刷、结实耐用的帆布箱、八成新皮大衣,奔赴夹边沟,奔赴翻手云覆手雨的政治苦难对人命运的捉弄。
一个在“值得全国的‘右派’分子们羡慕”的十工农场养鸡饲兔,一个在令人闻之色变的夹边沟农场挖排碱沟。当王景超们光脚泡在碱水沟里劳动,任凭皮肉被蚀破时,和凤鸣们还有机会吃大包子吃到撑。与丈夫迥异的遭遇,令和凤鸣的牵挂与痛苦加倍。
此外,夹边沟农场对“右派”们的态度也十分严苛。从夹边沟发出的信,每人每月限制两封。需经管教人员检查,确认无有害言论,方能投递。起先和凤鸣还试图反抗,挑衅般在信里暗示道:“上次的来信为什么没有封口?望下次注意封口。”但什么也没有改变,丈夫的信依旧简短、平淡。“小娇娇”与“吻你”之类的字眼,再也不可能出现。
和凤鸣曾在信中与丈夫谈及“右派”应有“高度的自尊心”,不偷吃农场食物。此时她追悔莫及,担心丈夫受此影响,死要面子,但自知救援无力,又逼迫自己“冷酷地不去想他”。
她时刻不忘自己的“右派”身份,多年后才明白,这帽子恰如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在艰苦的环境中,能清除个体残存的独立思想。如钱理群所说的“精神隔离”,它剥夺人自由思考、言说的权利,束缚人交流的欲望,在空洞中使得“革命的绝对权威”乘虚而入。
自下放后,和凤鸣的工资被降级,由102元减到58.24元。但她每月寄35元给父母,以照顾两个儿子,又寄10元给王景超,改善生活。然而,到改造后期,王景超所在的夹边沟农场,已根本买不到任何食物。
1960年11月,劳教“右派”的口粮定量骤减为每月15斤。夹边沟农场将尚未饿死的人集体迁往高台县明水分场后,大批人没能把命熬下去。1961年元月,中共中央召开了西北局兰州会议,“抢救人命”,粮食定量才有所回升。然而,当和凤鸣终于鼓起勇气请假,前往夹边沟解救丈夫时,一切都太迟了—王景超已于一个月前死在夹边沟。出于“高度的自尊心”和为家人避祸的考虑,他甚至没有发出一通求救电报。
阅后即焚
有甘肃民谣道:“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夹边沟一行后,和凤鸣成了寡妇,亡夫也尸骨无着。三年时光倏忽逝去,分别那日谁也料想不到的天人永隔,空降和凤鸣的人生。她劳教时为他准备的干辣椒,他还小心收在遗物箱内,没舍得吃完。他三年来积攒的两本日记,却令和凤鸣如获至宝。“他再也想不到,这两本日记对我是多么贵重的一笔财富啊!”
忍着悲痛回到兰州后,和凤鸣总算与两名幼子团聚,她未对王景超作任何祭奠,还带两个孩子去看电影。“习惯成自然,我认为不祭奠,不作任何悼念,忘却一切,倒是正常的。”然而终究长歌当哭,在先后遭遇外祖父母、父亲三位亲人的离世后,守着孤独的和凤鸣,唯有继续书写日记,与心灵进行对话。
“文革”期间,所有这些曾寄托着思念、告慰与情感的字纸,均在担忧、疑虑与恐惧之下,被和凤鸣付之一炬。包括王景超的日记、小说底稿,他写给和凤鸣的信,和凤鸣的养鸡兔日记等,灰飞烟灭,无一留存。被搜查、被抄家的和凤鸣,再度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公职,遣送原籍监督劳动至1978年改正。
直到今天,这沿袭自“革命年代”的谨慎,仍着痕于和凤鸣的言行中。当被请求阅读她的日记时,和凤鸣羞涩一笑,婉拒道:“有些内容我也不愿意……”不愿意分享,还是害怕心事曝光,再遭罪一场?
直到改革开放后,和凤鸣才重新开始记日记。“不写,有些事情就忘了嘛。”
2010年9月,王兵新作《夹边沟》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映。和凤鸣的读者亦是难友,打来电话告知她这一喜讯。“我那个片子实际上是搞《夹边沟》的副产品。”和凤鸣说起自己的口述史纪录片时,尽管自谦,也难掩自豪之色—“这片子在美国、巴西等地都上演了。”
她的日记里还记录着与王兵初次见面的情形:2005年8月某天的大早,杨显惠带着王兵这个“很年轻”的小伙子,还有几名将参演电影的年轻演员,到家中拜访她。当时凤凰卫视制作的《社会能见度》节目正在播出夹边沟专题节目,而兰州市普通家庭收不到这个台,他们便专门到街上找了家宾馆,包一个房间看节目。
这才催生了长达三小时的纪录片《和凤鸣》。王兵带着助手与摄像机到和凤鸣家中,连着去了三天,只取了七八个小时的素材。摄影机背对阳台,有时聊到黄昏,室内光线暗淡到已看不清人物轮廓,也无人开灯。这部摒弃了所有戏剧性叙事可能的纪录片,后来拿下了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大奖。
拒绝遗忘
自1961年探访丈夫却连尸骨都未见着后,和凤鸣再也没有去过夹边沟。直到1991年,有难友与她通信,提起夹边沟分场高台明水的大片坟地—丈夫王景超的遗骨正是葬在那里。于是,8月30日,和凤鸣在大儿子陪伴下,于三十年后重返夹边沟。
这三十年来,夹边沟的雪化了三十次。祁连山脉的雪水融化后,或汇入巴丹吉林沙漠里的湖泊,或渗入夹边沟盐碱与沙粒覆盖的地表。总也有雪花随西北风而至,轻轻落于夹边沟茫茫白沙堆里的暴尸之上。
当年的坟头基本已被风沙抹平,曾记录每位死难者姓名的碑石、砖块上的字迹,也已经无法辨识。尽管如此,和凤鸣还是拍下了当年“右派”们挖下的水井,缺了顶的地窝子,大张着嘴的骷髅骨,甚至红白相间小格衬衣的残片。
谁料回到家后,她发觉相机里的胶卷并未挂上,所有影像失踪,似乎预示着三十年前在此劳教改造的“右派”们的一切生命痕迹,也终将在此荒漠中悄然湮灭,如同从未发生。
每念及此,和凤鸣坐立难安,终于在整一个月后的9月30日,二度重返荒冢。这一次,她掩埋了前月所遇见的曝露于空气中的尸骨,又在每幅照片背后,悉心留下说明文字:“这位死难者在临终前,还在大声呼喊,他在呼喊什么?他的双眼会是闭住的吗?死不瞑目的他,在30年后,将他临终前的惨状昭示世人。大概是要我们思考些什么吧。”
那时她已经从西北民族学院退休两年,与小儿子分开,独自生活,开始《经历》一书的创作。和凤鸣想,哪怕不能发表,这段历史都应该留存下来。
起初写得断断续续,眼看着近十年过去,1998年,戴煌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和从维熙的《走向混沌》出版,和凤鸣突然受到了激励。戴煌曾是新华社总社记者,早在1957年便辨别出“神化毛泽东”的倾向;从维熙则是著名作家。“他们都是名人,我不是名人,但我的经历跟他们又不太一样。”
和凤鸣开始加紧写,除了每天看一眼《新闻联播》外,取消了一切活动。从1998年秋后急赶到1999年,原本高度近视的她,引发了眼底病变,视网膜甚至出现裂孔。可她边治疗边写作,并未放弃书稿。
王景超在临死之前,曾对难友陈群说,“你是生活的强者,你一定能出去。你出去后,一定要写本书,把这里的一切都统统写出来。为了吸引读者,你不仅要写我们的苦难,还要穿插写上爱情。”
王景超去世后,和凤鸣建立过新的家庭。孩子们的继父陪她度过了“反右”后的六十年代与整个“文革”时期,于1983年去世。然而王景超的作家梦,他的要她坚持记日记的叮嘱,并未随“文革”中那把焚烧的火而灰飞烟灭。
四十年后的2001年,死者的遗愿终于付诸实现。但不是借助别人的笔,而恰恰是靠妻子和凤鸣的独自努力,受难者的私人记忆与时代烙印紧紧融合在了一起。如钱理群所评价,“不是所有的幸存者都能听见并记住牺牲者和他们的亲人的‘地狱里的哭声’的,他们在自以为的‘天堂’里活得如此的自在,已经觉得如果现在还要哭泣,就会破坏了他们的好心情,成为新的罪孽了。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健忘者,强迫遗忘者,和凤鸣这样的不肯,也不敢忘却的幸存者,就更感到了一种生命的重压。”
长歌当哭
《经历——我的1957年》首版只印了3000册,还是靠和凤鸣的老领导刘爱芝及时寄给她三万块,才能自费出版。和凤鸣把通信地址和电话留在了书的尾页上。五年后书籍再版时,又把学者钱理群的评论放了进去。迄今为止,循迹而来的读者、难友,或写信或通电话,已有一两百人。
因一本《夹边沟记事》,凡有媒体到甘肃采访,牵线之事必找杨显惠。又因这本《经历—我的1957年》,凡有难友欲寻亲人故旧,也脱不开和凤鸣的人际圈。
和凤鸣有一个棕皮小本子,按区号分隔,记满了全国各地各界难友的联系方式,详细到包含座机、手机、地址与邮编。杨显惠本来也有一个通讯录,去年装口袋里在街上走,被小偷摸去了。于是,和凤鸣的这本簿子,就成了唯一的“诺亚方舟”。有当年在夹边沟劳教过的幸存者,有读了书后认出亲人影子的死难者子女,也不乏铁流、章诒和等同样亲身见证过历史的老“右派”们。
尽管有些人不愿意重提旧事,但,“愿意说的‘右派’,还是多数”。这些年来,好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大龄读者相继去世。和凤鸣一一报出他们的姓名,间或补充几句某人的事迹,表情竟也平静如烟。就像她在纪录片《和凤鸣》中的讲述,偶尔有哽咽,但大体平静、通顺,用的是略显文学化的语言,多来自她亲笔写下的句子。
为了出版《经历》第三版,和凤鸣曾写信托付某出版社总编。因为敦煌文艺出版社在责编被迫检讨八次后,已无力承担出书任务。尽管还在等待新闻出版局的审批结果,但自今年4月开始,耗时半年后,和凤鸣已将书籍修订完毕。客厅桌上放的那本二版中,布满了她用红笔修改、增删的痕迹。
如今,和凤鸣依然坚持每天收看《新闻联播》,关心国家大事,关心选举权、政治改革、言论出版与民主自由。高血压与骨质增生限制了这位耄耋老者的出行范围和次数,却没有限制她的思想。她的信息源,除了那台老式电视,还有全国各地的读者,不定期寄来其可能感兴趣的报道、书籍等。在光线最好的书房里,堆着许多关于毛的境外书籍。若抚开上面的尘土,或许可瞥见这位老人的思路历程。
二战后,法国纪录片导演克劳德·郎兹曼倾注11年时间拍成《浩劫》,与曾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波兰人对话,试图重建那荒谬年代的历史。而对于和凤鸣来说,她的“经历”如苍茫海上一朵浪花,既是对晦暗历史与人性的见证,又首先是深入骨髓的记忆的延续。
王景超是河北人,京戏唱得不错。和凤鸣在改造时,也一度是唱眉户剧的台柱子。然而两人相守八年,从未有过配戏的机会。
“这段苦难升华了我们之间的感情。”一如几十年前,她曾在戈壁上唱过近百次的那支俄罗斯民歌——
“草原大无边,路途遥又远,有个马车夫,将死在路边。爱情我带走,请她莫伤怀,找个知心人,结婚永相爱。”
《和凤鸣》观后感(三):看过
和凤鸣就是兰州人,所以对她的口音很熟悉,她的母校也是二十七中。当时的工作单位是甘报社,都是非常熟悉的地方。对她的诉说特别容易投入进去,在看似平淡的诉说中,感受她情绪的起起伏伏,慢慢的最后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情绪,对那个时代苦难形成非常具象的体会。
她诉说那个时代的苦难,冤屈,饥饿,分离,奔波,死别。她说,在那个痛苦的时候,我们的爱情特别的甜蜜,是别人无法理解的。又痛苦,又甜蜜。她请假去看他,下雪的夜晚就她一个人,那时她没有想过别的,一心就想去救她的爱人,哪怕他此刻奄奄一息,但只要她在身边,就可以活过来。根本没想过还有可能会遇到狼和其他的风险。结果去了夹边沟,她的爱人已经在一个月之前就故去了。在这样的遭遇面前,我们遇到的都不值一提。
《和凤鸣》观后感(四):那段历史
因为没有看完,实在不该我来评论
但是似乎还没有真正看过的人讲话
我就来说说吧
在香港电影节上看的
honestly
影片本身有些沉闷
三个小时
镜头对着端坐家中沙发上的和凤鸣老人
一动不动
听她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那段历史
包括中间老人去洗手间/接电话/开灯
全部一一记录
很像我们熟悉的去探望老人的场景
听老人在对面絮絮叨叨的讲古
静静的听着
也许在心里感叹
也许对那些遥远的年代有些隔阂甚至厌烦
也许还在打哈欠
但是还是要听着
因为他们就是历史本身
错过了就真的是没有了
关于内容就不多说了
反右/夹边沟/右派/文革
印象深刻的一处
老人在讲述中唯一一次能感觉到眼光在闪耀
是讲到那夜丈夫告诉她自己被打成右派两人相依而眠
“那一夜我们的爱情开出了最绚烂的花朵”
在整个讲述中这句话似乎有些格格不入
但也许这一夜就是女人对早逝的丈夫的最绚烂的回忆了
只能说
人
在历史洪潮中
是如此无力
唯一能做的
就是
活着
努力的活着
《和凤鸣》观后感(五):《和凤鸣》超140字影评
距前面因《铁西区》而记住王兵,已经过去快三年。这一部的资源很罕见,找到后也躺在云上几个月。
敏感的、少有人谈的话题,会有很大吸引力,这是王兵的切入角度与投入方向。其实不需要技术。呈现原汁原味的初始化素材,也是王兵的优势。《和凤鸣》没有太大缺陷,几乎一个构图讲下来,观影十分疲惫。老太太逻辑清晰,是应该成为人上人的,然而……在记录时代的荒诞无稽中,影片免不了一面之辞的嫌腥,制作空间也过于狭窄——要在一个维度里做出维度,闪转腾挪,费尽力气,给观看者大脑的空间也极狭。我现在很怀疑导演是否具有构建复杂、完整电影结构的能力。
你问我伤心吗? 伤心。
你问我要翻吗? 无力。
你问我要overthrow吗? 不能。
无论是劳改营还是农场,翻译都是camp,多么讽刺多么尴尬。最广大人民是国家的土壤,politics是更加复杂的事物——框架、骨骼、影响土壤酸碱性、捏塑土壤,无论用什么比喻,都令人心痛,也催人奋进。想去研究一下任何能量实体形成初期的特征。
《和凤鸣》观后感(六):几句闲扯
一 片长
片长超180分钟,分两次才看完,中断的原因很惭愧:睡着了。
二 镜头
超长时间固定机位镜头,据说是王兵导演的特点,可是我恍惚觉得这就是把拍摄素材原封不动搬到银幕上来。
全片没有任何讲述人以外的素材镜头,貌似干净,实则削弱了后世存在代沟的观众对片子的理解和认识。导演或许成功炫出了他的个性或曰思想,但对于片子本身的主题表达有害无益,是为以辞害意、胶柱鼓瑟。
三 所谓客观
所谓客观冷静的记录,是否排斥拍摄双方的互动?
无论原教旨记录主义的朋友们怎么说,拍摄者对被拍摄者的介入和干扰都是无法消除的。片子开头和凤鸣老人明显表现出对镜头压力的不适应,表达的顺畅受到影响显而易见。
既然无法消除影响,何不耐心做些功课,编导和老人有些互动,帮助她把线索捋得更清晰一些呢?
四 细节
中文字幕极差,考虑到碟片版本龙蛇混杂,或许是版本的问题。
画面噪点多,只能是设备和手艺的问题,这个实在不应该。
五 其他
一部电影,包括纪录片,要说什么、给谁看,这才是核心,套句烂俗的话说,内容决定形式。
这个片子给三星评价,有一颗是因为选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