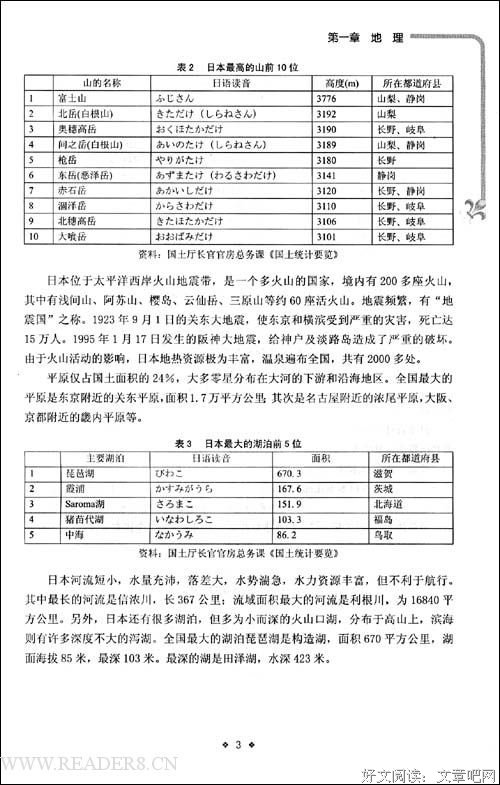
《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是一本由(日) 石川祯浩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2,页数:40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180-182
183-184
184
《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读后感(二):20世纪初年中国留日学生“黄帝”之再造 ——排满、肖像、西方起源论
20世纪初年中国留日学生“黄帝”之再造
——排满、肖像、西方起源论
28
20世纪初叶,在排满主义的洪流之中,“汉族”作为一个拥有想象上共同祖先的假想的血缘集团迅速诞生,继而刺激和鼓舞汉族民族主义的诸多工具相继出台,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30
二、黄帝像的出现及其发展
如前所述,中国近代黄帝崇拜的出现及其画像——在此统称为“黄帝热”——始兴于1903年的东京。具体来说,“黄帝热”的兴起表现在如下个方面:1. 采用黄帝纪年刊物的出现;2. 黄帝肖像画的制作及流传;3.有关黄帝事迹论说的出版等。关于第一点,已有诸多研究积累明确论述,兹不赘论。在此只需指出,当时采用黄帝纪年蕴含不奉清王朝正朔之意,是排满革命的明确表示。
41
一本著作未经正式翻译、介绍,而其学说却经过曲解、加工和复制,成为该时代的通论,并开始规范人们的意识和行动,此类事例,特别是在明治时期的日本及受其影响的清末中国屡见不鲜,而拉库伯里的“汉族(黄帝)西来说”正是其典型之一。
49
然而,看似引自拉库伯里著作的该楔形文字图,实为原著所无,而是《支那文明史》作者采自与汉族西方起源说完全无关的有关古代东方学的英语论文,且未做只字说明。不用说,除少数古代东方学者外,无人会去翻阅拉库伯里浩繁的原著,或者试图确认楔形文字图的出处,因此,对于日本及中国读者而言,《支那文学史》的转述即非全为拉库伯里学说,也全部是史实。此类对西方学说即非概括、亦非编述的加工,是明治日本接受西方思想时的常见现象,而决非仅有《支那文明史》的年轻作者为之。但远在伦敦的一位东方学者的新奇学说,经过介绍者追加“旁证”后,却不仅为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而且也被日本的部分信从者奉为“几乎不可动摇之定论”。
50
“…… ……中国者,汉族之中国也”。(刘师培《论中国对外思想之变迁》,警钟日报,1904.6.20)
上述引文表明,对他们而言,汉族西方起源说完全证明汉族是伟大的征服者,因此是优秀种族,统治中国实属当之无愧,更是优秀种族之标志。而如果了解了清末知识分子如何观察和理解近代世界,则他们如何以持有此种逻辑,也就不言自明。亦即,在他们看来,所谓近代世界史无非是雅利安、盎格鲁-撒克逊等所谓优秀人种不断征服劣等人种的历史,而在此过程中,身为土著民族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可言。在贯穿着优胜劣败“公理”的人类历史上,征服者即优胜者,成为征服者就拥有了取得统治者资格的根据。换言之,清末知识分子接受汉族西方起源说,由于其逻辑与承认西方人种在近代世界的优秀和霸权相同,从而通过比拟而得到了作为汉族理应拥有的类似的自尊心和优越感。
51
这种比拟思考方式,实为清末人种论及历史人物论所共有。在接受了社会进化论规定的人种优劣顺序的清末知识分子们看来,汉族作为种族,其文明程度尽管较之西方各民族大为逊色,但较之非洲黑人及中国国内尚未开化之少数民族,却显然远在其上,属于文明之列。此外,众所周知,出自清末知识分子之手的史传所颂扬的历史人物,除对外族入侵的抵抗者如岳飞、文天祥、郑成功等之外,还有不少远征异域者(或被视作远征异域者)如郑和、张骞、班超等。这表明,对本民族抱有的自尊,并非先天自然形成,而是通过寻求、确定哪个民族逊于本民族,并明确其差异、排定优劣来确立的;而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决然抗拒外族征服者的同时,却也难免被其本身试图成为征服者这一“强者的逻辑”所纠缠。假如把清末出现的黄帝称为民族主义高度凝聚的象征,则它是把有关民族主义的比拟思考方式凝聚后,才成为象征的。
从汉族始祖“黄帝”在1903年诞生于东京后,至今已逾百年,其间,“黄帝”从汉族的始祖,逐渐转化为“中华民族”的祖先,其立场已发生微妙变化,但对黄帝的颂扬却未曾中断。寓意黄帝子孙繁荣的汉族自我称谓“炎黄子孙”现在仍在使用,而黄帝陵祭祀念念举行,且规模不断扩大。如果黄帝是民族主义高度凝缩的象征,则这些现象或许是中国民族主义课题虽历经百年努力而仍未实现其目的的反映。
《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读后感(三):学者史者心
做学问,研究历史,客观、严谨非常重要。然而,历史研究与当政者的需求又难以割裂,特别是强权者和高压环境下尤是如此。一个学者史者的心,能始终保持是不容易的。好在,世界文明在发展,特别是域外学者更可以免受很多打扰。而能够查阅到不为人知的原始史料是相当不容易的,过程之波折艰苦,时限之长,可以想象。能够做到这些,除了学者史者本心之外,大概也和日本民族的极度认真细致有关。
本书作为历史学者的论文集合,每一篇都有严密考证,其中很多内容读者从未了解过。一方面披露了很多信息,另一方面也提示了很多新颖的观点。其中也有很多心照不宣的原因,作者客观点出,读者看来真是感慨赞叹。
作者讨论了晚清中国被称为睡狮醒狮的来源,可断定不是拿破仑提出的,而是梁启超根据读到的译著将中国作为沉睡着的佛兰金仙,即理解不够准确的雪莱夫人小说中的怪物弗兰肯斯坦,又将其想象为沉睡中的狮子,提出中国是睡狮。此一说在晚清被知识分子广泛传播,影响广泛。
皇帝作为始祖形象被大肆宣传始于20世纪初,进步人士将其作为反清统治的象征,慢慢经历从汉族祖先到中华民族祖先的微妙演变。当时也流行了汉族是西方入侵者的观点,体现得只是先进民族打败落后民族掌握统治权的认定。
上海租界花园在记载规则告示牌有狗和中国人不得入内的各项条文,与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对阅者、听者而言,其所产生的冲击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仅写“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非正式小型告示牌,或许只是其实物或者照片没有流传下来,而实际上却曾存在。但是,在尚未发现确凿证据的现在,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正式向中国开放之前,外滩公园门口有过限制中国人和狗入园的告示牌;但是,一般所想象的那种将两者写在一起的所谓“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似乎并不存在。而不管把狗和中国人相提并论的告示牌是否曾真实存在,帝国主义践踏中国主权的事实都摆在每个中国人的面前。较之列举列强几千条罪状,“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传闻更能一针见血地点破列强野蛮统治的本质。而且,正因其一针见血,才能不断为中国革命提供能量。
梁启超给予清末中国社会思潮的影响是巨大的,20世纪中国的巨人,如胡适、毛泽东等,都感慨地回顾他们在青年时代阅读《新民丛报》时感受到的强烈震动。清末青年所走的道路,是从利用梁启超的语言和其所提供的模式来思考和分析世界而开始的。
福泽强调“自身之自由”是一国自由之前提,而梁启超则认为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中华向来是极权统治,不强调个人,不鼓励个性。东亚甚至都如此。因此后来连日本的福泽也认识到“百卷万国公法不如几门大炮”。
中共一大没有留下出处明确的正式文件,人们是因其创立、诞生、开端等象征意义才关注。而二大不同,有关的正式文件如党章、决议案等都有完整保存。蔡和森说一大时的中国共产党只能说是宣传机关,而说不上政党,二大时才成为一个有政策的决议的政党。一大代表等有关史料的研究甄别,体现了作者作为历史学者的严谨。史料学考证非常必要,要尽量剔除层积性因素。
中国党史研究者的弊病,即依据数种文件中最具权威的资料拟制定论,其后的研究则对其来龙去脉不予深究,攀附定论而继续炮制论文,这样的过程不断重复,资料的出处也被不断省略和隐匿。以中共二大研究为例,说明一些所谓的最新学说的论文,并没有在史料发掘和分析上有新的突破,二是继承了部分党史研究者的如下弊病,即盲从权威资料,导致学者最基本的素质——分析思考能力——停止和瘫痪。
孙中山弥留之际,国民党内部左右派纷争激烈。汪精卫等代拟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孙同意并签字。苏联遗嘱没有同一时间提前征求孙意见,是签字时为避免党内分裂派基金和继承正统而形成的。孙亦一同签字。因此成为后来国共争论的焦点。
《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读后感(四):实证主义史学的问题
在有关历史的争论中,常可以看到两种互相矛盾的说法:一种从“大历史”(Macro-history)视角出发,认为过往的那些鸡毛蒜皮实在无关宏旨,“我为什么要知道”;另一种则认为历史的趣味正在于那些丰富的细节之中,不仅如此,推敲、发现、证实某些细节有时能带来新的认知。在历史爱好者中,后一种方法的流行并不亚于前者,他们推崇通过各种细节像刑侦术一样地追索、甚至“复原”历史“事实”,并认为这样得来的是更为坚实可信的东西。
石川祯浩在这本《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中所呈现的正是这种实证主义史学的方法。这与他以往几本著作的风格一以贯之,日本学者似乎也特别善于不放过细节所在,通过对档案材料的反复推敲(甚至是抠字眼),以加深对某些历史的更深认识。打个比方,这就好像在一个幽暗的隧道深处,人们各自盯住自己眼前一小块岩壁,想尽各种办法,试图把这里向前钻进几厘米。公平地说,这些做法自然有其价值,好过国内学界早先空洞繁琐地在意识形态上辩论一些不着边际的历史问题或粗放地重复谈“大问题”,因为“刑侦术”的确带来了某些新的“知识点”。大部分书都只有少量新东西,而石川祯浩此书的每一篇都是在扎实考证之后,有“道前人所未及”之处的。如果人人都能以狮子搏兔之力扎实地解决“小问题”,则累积起来将颇为可观,必能丰富和深化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学术的挺进也有赖于新的进展,无论其大小。
只不过,我对这种实证主义的路径也有一些本能的怀疑——这也得感谢石川祯浩,因为这种质疑也是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被激发出来的,这么说不是讽刺,因为能激发人思考本来就是一本书很重要的价值。我的怀疑在于:这种相当依赖于实证的做法,固然能推动新材料的发现、带来新的知识点,但有时会止步于那个新细节的发现上(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唯一坚实可信的,也不愿说过头话),在思辨问题时,在认知框架、对话语环境的辨析上可能会出现不小的问题。
这种实证主义的方法背后,隐藏着一个基本信念,即存在某个唯一的历史真相,它是可以通过更细致的“刑侦手段”触及或还原的。这无疑与后现代史学的观念相反,而属于某种更早的信念——这么说并无高下之分,因为国内学界有时虽然急于拥抱“后现代史学”,但其实连“现代”都还没认认真真做好。但在遇到那种真相已被掩埋在层累交叠的陈述、记忆(所谓“编织”)之中的历史时,这种方法就可能显露出某种局限性,而需要更新认知框架。
书中一篇关于外滩公园门前“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告示牌是否存在的文章,可说便存在这样的问题。当然,这个争议的存在,本身就与实证主义视角有关,因为它的症结在于:眼下没有任何实物或影像的资料能证明这一告示牌确确实实存在过,而当时人留下的文献记载则矛盾不一。虽然许多人都曾记载说见过这块告示,但具体怎么写,却有细节上的差异。例如周作人的记载是“犬与华人不准入”(周作人1903年9月11日日记);蔡和森称是“华人与犬不得入内”(1923年11月16日《向导周报》文);1924年孙中山则说是“狗同中国人不许入”(《中国内乱之原因》);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说自己在法国公园亲眼看到的是“华人与狗不准进园”八字。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杨昌济在1913年的记述最为具体:“上海西洋人公园门首榜云:‘华人不许入’;又云‘犬不许入’。”有材料证明,“华人不许入”和“狗不许入”是公园规定中分开的两条,但并未记载在一起;因此,如石川祯浩所言,“告示牌的问题,与其说事关告示牌存在与否,或字句有无,不如说是被理解为列强制造了‘国中之国’、歧视中国人、统治中国的野蛮象征,并流传开的。”实际上,关于张献忠“七杀碑”的具体字句也存在类似争议,现在并无材料能确信存在“杀杀杀杀杀杀杀”七字的碑文,但在世人心目中,这却更符合张献忠嗜杀的形象。
在这种历史问题上,实证主义往往以探求唯一真相的面目出现,并对人们惯有的历史认知具有某种解构的力量,但它其实只是争论中的一个声音。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这件事的争论中,从上海史学者薛理勇、熊月之,国外学者毕可思、华志健以及石川祯浩等,几乎所有人都聚焦于一种实证主义的思路,即究竟有没有实物或影像资料能证明存在“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一告示。但这个证据,就像许多历史资料一样,我们很有可能永远也不会找到。
在当时,姚公鹤等人的观点则虽然肯定这一辱华的告示牌存在,却又认为西方人这样做也有情可原,原因是华人入园时有随意采摘花草、践踏草坪之类的不文明行为。也就是说,在这一话语中,虽然承认告示牌的存在,但强调的不是殖民统治的中外矛盾,甚至也不是“上流社会”与“底层华人”的阶级矛盾,而被转化成“文明/野蛮”的分野。但石川祯浩并未再去分析这一话语背后的意味,他的兴趣好像仅在于告示牌是否存在、以及征引史料举证当时另一种声音认为不对华人开放是因为中国人举止不文明。
但这是问题的重点吗?我很怀疑。因为当时这些租界的公园并不是在出现了“华人在公园里的不文明行为”之后才禁止华人进入的,相反,这种禁止本身是他们特权的体现;而“华人的不文明行为”则是后起的、为他们的特权予以合理化的辩护,或是为了试图激发中国人尽速“文明化”而说的反话。这种话语,在西方的殖民统治中是屡见不鲜的——通过与西方普世的文明价值观进行对比,把东方各国锁定在低等级的位置上。这正是印度学者查特吉所说的,亚洲妇女所受的虐待,是“从根本上建构殖民主义话语的整座大厦”的基础之一。阿西莫夫在科幻小说《我,机器人》中,机器人的逻辑其实也是如此:因为人类自身存在缺陷,所以我有权接管秩序来统治你们。
近代西方列强并不只是在中国如此保留自己的特权。在埃及,人们认为“英国人冷酷无情,具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多年来,惟有埃及仆佣才能进入开罗豪华的吉兹拉体育俱乐部,这一点令人心酸)”(戈尔德史密斯《中东史》中译本页261),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翻版,而那并不是由于埃及人在这个体育俱乐部做了什么不文明的事。在19世纪后期,美国南方各州的“一些公园的入口处都挂有一块招牌:‘狗和黑人禁止入内’”(Domenico Losurdo《自|由主义批判史》中译本页359),这大概只能解释为种族隔离制度吧?而据Stephen M. Hart的《马尔克斯评传》,马尔克斯等拉美作家1961年在亚特兰大“他们亲身经历了美国南部种族主义的粗暴。餐馆不让他们进去,因为他们被当成是墨西哥人,迎接他们的是‘狗与墨西哥人勿进’的招牌。”(中译本页63-64)难道这是因为墨西哥人在餐馆里不文明?
在历史的研究中,“事实”往往充当着解构与祛魅的力量,因此实证性的史料往往具有重要价值。也是因为这样,当人们发现并无材料证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时,便倾向于认为这是虚构的、甚至是“流传了一个世纪的谎言”。但这不如说是一种受辱的象征、一种凝结着国族情感记忆的概括。科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中曾谈到,有些人群怕鬼,“毫无疑问,这纯粹是迷信;但是这种迷信却是一件事实,而且是我们所考虑这一局势中的关键事实。”这也就是说,历史学家仅仅去“厘清真相”而不顾“不实”的观念是不够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一话语背后的情结,至少与“事实”或“真相”同样重要,放弃对它的分析,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历史学家的失职。
勘误:
.42:古巴比伦加尔迪亚部落(Chaldea):迦勒底
《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读后感(五):不以史实为基础的推论都是空中楼阁
买此书之前,还只是对其目录中的题目有些兴趣。看了豆瓣上的评论后,觉得买对了。“实证主义”的历史学研究,正是我喜欢的,尤其看完高华的几本书之后,更觉得中国缺少“实证主义”的氛围。
1. 晚清“睡狮”形象探源
此文的结论是,“睡狮”形象的演化路径是:英国人吴士礼称中国是“弗兰肯斯坦”,中国外交官曾纪泽称中国“先睡后醒”,梁启超说中国是“睡狮”。文章结尾还引用了鲁迅在1933年文中所说“现在的所谓‘黄祸’,我们自己是在指黄河决口了,但三十年之前,并不如此。那时是解作黄色人种将要席卷欧洲的意思的,有些英雄听到了这句话,恰如听得被白人恭维为‘睡狮’一样,得意了好几年,准备着去做欧洲的主子”。
如果再深入了解一下吴士礼、曾纪泽的身份,以及梁启超的期愿,这个传闻之所以能广为流传出来就更容易理解了:吴士礼曾领兵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并支持镇压太平天国,他有条件有意愿“夸大”中国的重要性;曾纪泽表达的是外交官的立场;梁启超则将其化为中国人更容易理解的睡狮形象,以鼓励变法。在那个环境下,这种有利自信的传闻,被很多老百姓接受。而鲁迅作为国人的“扇耳光者”,敏锐而一贯地以扇醒中国人为己任。
2. 20世纪初年中国留日学生“黄帝”之再造
此文的结论是,“黄帝”作为汉族的祖先的形象,是20世纪初在日本留学的中国人创造出来的,所创造的内容包括黄帝纪年、黄帝肖像以及黄帝传说。作者暗示这三种创造都受到了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再造“天皇”形象的影响。
清末革命洪流既推动了“汉族”概念的形成,也被这一概念所推动。这段时间也正是“人种理论”风靡全球的时候。关于“黄帝起源”,还曾经流行过“自古巴比伦迁徙而来”的说法,这种有着“先进的西方人血统”的汉族起源说,进一步强化了“推翻满清腐朽政权”的正当性和必胜信心。
3.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告示牌问题考
此文的结论是,上海外滩公园“仅限外国人入内”和“狗和自行车不得入内”的告示内容最终被演绎为更具冲击力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文章也指明了这种演绎的背景,就是租界设施逐渐对华人开放。
中国人对于西方,一直并存着对其“秩序性”的追求,和对其“歧视性”的反感,这种矛盾其实一直到现在都还存在,比如WTO。
4. 辛亥革命时期的种族主义与中国人类学的兴起
此文的结论是,清末革命受到了其时传入中国的西方人类学成果的影响,区分汉藏人种和满族所属的通古斯人种的结论,为革命派找到了排满革命的理论依据,也让改良派很尴尬。
近代人种学就像当年的达尔文主义一样,是静态地看待自然世界、将人比作机械的时代的产物。现在持这种前现代观点的人,也不在少数。
5. 梁启超与文明的观点
6. 近代东亚“文明圈”的成立及其共同语言
7. 梁启超与明治时期日本的地理学研究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他既很快地接受了当时西方流行的人种论、地理决定论等近代科学观点,同时也敏感地意识到这类静态观念的局限性,相比之下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客观条件的影响,更接近现代科学观点一些。
8. 李大钊早期思想中的日本因素
此文引出了一个二十世纪初日本媒体界的一个风云人物——茅原华山。茅原是一个敏锐的政论家而不是政治家,他的观点是新潮而易变的。在某一段时期,他的观点吸引并影响了李大钊。
此文所研究的内容似乎还有一些敏感,因为似乎让李大钊这位伟光正的人物受到一个日本“瘪三”影响,有些高级黑。但事实就是如此,也没有必要因此嘲笑甚至贬低李大钊的形象。
9. 走进“信仰”的年代
10.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终结与苏联和共产国际
这段历史基本已经被沈志华、杨奎松等人研究透了。本文查证的是,当时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易所谓“私自将斯大林给中共的‘五月指示’给了汪精卫”的背景和可能的真相。作者认为,基于汪精卫的艰难处境,以及斯大林反托洛茨基的需要,即使是斯大林授意罗易给汪精卫看“五月指示”的内容,也有可能因形势的变化而让双方都不承认这个过程。
11. 走向农村革命
中国革命的胜利最终依托的是“土地革命”,这一点从后往前看虽然无疑是正确的,但认识到这一点,以及如何实践这一点的过程,却是曲折的。本文通过查阅一手资料证明,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正是来自苏联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和执委会第7次扩大全会推动了中共逐渐重视农民问题。斯大林认识到中国不能模仿苏联的工人革命模式,也认识到在中国维持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但由于意识形态以及权力斗争还有信息传播延迟方面的种种原因,他的中国农民政策介于激进与渐进之间,往往该渐进的时候,他的激进的指示传来了,需要激进的时候,他又在犹豫,最终导致中共进退失据。
当然,站在今人的视角去判断当年究竟该采取何种策略是没有意义的,但实证主义史学的价值就是,还原了当年的历史过程,让这一更为真实的过程看起来比后人通过回忆构建的过程更加符合逻辑。
瞿秋白是一个很值得深入研究的关键历史人物,在革命心理学上应该也是个非常不错的案例。
12. 早期共产国际大会上的中国代表(1919-1922)
共产党是一个生来就具有国际主义理想的政党,苏俄也很快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利用手中的国家资源实践其混杂着国际主义与国家主义目的的理想。同时共产党也是一个非常重视“会议”的组织。所以,自1919年内战还没结束就召开的共产国际一大到1922年的共产国际四大,都邀请了中国代表参加。但这一段时间也是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发展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时间,按照共产国际的定义,只有被它所承认的各地共产主义组织才能被叫做“共产党”,所以,究竟谁代表后来的中共参加了前几届共产国际大会,就成了一个政治问题。
俄国共产党形成并传播了两种行事风格:1. 按预订计划实施革命,2. 凡事重视组织程序(开会)。经过几十年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两个风格几乎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也可能正好暗合了中国文化特性)而不感知,现在仍然影响着中国政治。这两个特点区别于其他的政党及团体,天然具有计划性和民主性(一定范围内的)特点,或许这是共产主义能够影响世界百年历史(现在还在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
13. 由考证学走向史料学
中共一大作为革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中共党史中花在其上的研究投入也很多,成果也很多。不过,经过作者的考证,党史中这一重要环节却仍然存在着大量的疑点,无论是开会时间、地点、人数,都并不那么确定。因为缺少第一手的资料(这次会议是在秘密状态下开的,而且中途还因被租界巡捕搜查而换地方),目前所有的史料实际上都是二手的。作者着重分析的是陈潭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议》、葛萨廖夫的《中国共产党初期革命活动》和《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1929年12月31日),发现每一个都有很多疑点,要么是前后不一致,要么是相互不一致,连“葛萨廖夫”这个人都只不过是“校订者”。
然后,作者写本文的目的并不是在指出史料考证上的疑点,而是想指出,存在诸多疑点的现实为中共党史编撰者所无视,谬误被写进了权威就成为了权威。
14. 中共二大与中共党史研究史
此文承袭上文,仍然指出的是中共党史研究者“盲从权威资料”的问题。“实际上,远比那些似是而非的所谓代表名单更能反映出当时党的实际状况的,是二大时的中国共产党没有留下类似大会代表名单的文件,或者说没有名单也根本不会影响党开展工作这一事实。”
15. 孙中山致苏联政府遗书
孙中山遗书到底是两份还是三份,一般说法是三份:《国事遗书》、《家事遗书》和《致苏联政府遗书》,但作者考证发现,《致苏联政府遗书》的形成过程和前两份遗书很不一样,而且孙中山逝世后马上就存在着关于这份遗书真伪的争议。作者通过查阅资料和分析史料认为,该份遗书是在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弥留之际,在签署另两份提前准备好的遗嘱的同时,当场拿出来由孙中山签署的。但签署并非虚构,因为在场的国民党左中右元老也都在其上签了字见证其真实性。
基于这个起点,作者进而分析了为什么会出现围绕此份遗书的巨大争议:孙中山是联俄联共政策的最大支撑,他的逝世几乎必然会导致这一政策推行受阻,于是,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主流派对发布这一明显左倾的、信函形式的、形成过程具有某种阴谋性质的遗书采取的是隐瞒的态度。
“史实”究竟对于“史识”有多重要,其实在此文中就能看出来:不花精力考证史实,一切推论都是空中楼阁。相比而言,高华等中国当代史研究者的成果,多数都仍然是在用其所反对的方法来做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