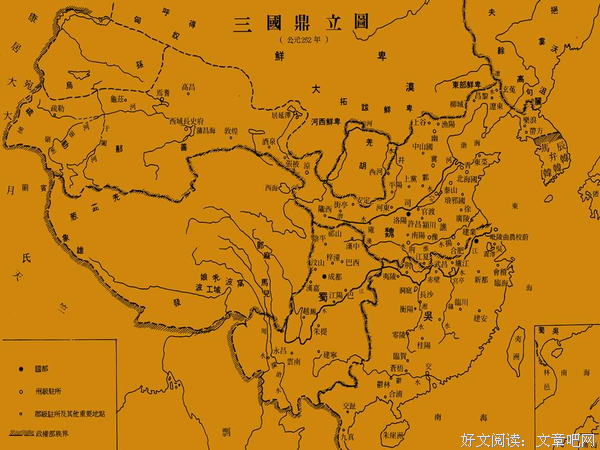《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是一本由仇鹿鸣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6.00元,页数:33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读后感(一):太难了,读不下去了
如题,理科生表示这个硕士论文真心好难理解,太多东西都不了解,而且写得很抽象,很难理解,靠。为毛和理工科学术论文完全不同的体裁,表述完全没法理解。。。。。。。。。。。。。。。。。。。。。。。。。。。。。。。。。。。。。。。。。。。。。。。。。。。。。。。。。。。。。。。。。。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读后感(二):很精彩
写得很精彩,把司马氏从崛起到八王之乱前期代表事件做了一次梳理,尤其是在一些对于事件的分析方面,给人很大启发(如对于高平陵之变的性质方面)。但个人觉得在家族网络的分析上似乎还有提升空间。作者一方面说陈寅恪的分析法抽象化了历史,忽略了一些东西。而在家族网络的描述上仍旧沿袭了这一路数。总感觉按照这样的办法多了一些理所当然。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读后感(三):政治史就应该做成这样
这本书是这几年不多见的很显示作者功力的政治史的研究著作,作者首先揭示了司马氏在河内的家族网络以及上升至首都的过程,接下来关于高平陵之变中曹魏元老政治态度的诠释,以及司马氏集团中两种势力之间的裂缝,并以此贯穿之后一章的研究,最后关于武帝的政治转变分析也很恰当。总之,此书新见颇多,值得一读。但是关于其中石苞等寒族武将能否构成一股政治势力我是存有疑问的。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读后感(四):收获良多
魏晋嬗代,政局中的关系网络却是被承继下来,所谓晋承魏制,不仅是制度也有人事,晋臣乃魏臣。很多魏臣支持司马懿推翻曹爽执政,与支持司马氏代魏并不相同,当然发展却未必如人所愿。 司马氏一族和诸多大族在曹魏时期就有相互盘根错节的关系,而晋朝成立后,宗族和功臣,一内一外,成为整个政治中枢的支撑。
司马昭——司马炎一房成为帝系,有立晋之功的司马师——司马攸、司马孚——司马望两支则成为朝臣,原本家族权臣走向皇权,帝系独大,由族到家。 因此晋武帝通过不断地出继与回嗣,来削弱司马孚一支的大宗力量。 强干弱枝。 晋武帝在咸宁二年病重,齐王攸有被拥立之嫌,导致晋武帝做出了引入外戚,制衡宗族力量,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而晚年令齐王攸出镇之国,一干朝臣因反对而遭迁,朝中外戚独大。杨骏矫诏,赶走司马亮,把持政局;而后贾后寻找宗室,共诛杨骏;后逼害储君,遭到司马宗室的反抗,八王之乱由此而起。西晋一朝也短暂而亡。 外戚、宗族、功臣,背后都是一张张关系网。这些关系网成了东晋门阀政治的萌芽。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读后感(五):乱谈一二
读到魏晋史,常有一疑问,何以三国时期汉人武功如此强盛,而转眼不过数十年,即有五胡乱华之祸?
欲答此疑问,不可不从西晋一朝探源。
仇先生的论文我早就拜读过,终于他有了此书问世,我当然迫不及待要大快朵颐。
本书基本上是根据先生以往研究的成果改编而来,选择以司马氏为中心作考察可谓再适当不过。
司马炎出身名门,精通权谋之术,此乃家教。然而他虽是嫡长子,能嗣承司马氏基业却并不容易,其弟司马攸几乎夺嫡成功。故对司马炎而言,司马攸可谓一生最大政敌。明乎此,则方可了解晋武帝一朝政局之根本。
司马炎精通权谋,玩弄政治手法娴熟,对于帝王而言,只要明白平衡臣下,自可垂拱而治。个中巧妙,后来的历朝君主,无论昏聩还是贤明,无不深知。特别是宋徽宗、明世宗这两位,一个失国,一个乱国,对这套手法也是炉火纯青。
司马炎为子孙谋不可不谓殚精竭虑,设计的接班格局也不可不谓平衡。然而政治毕竟不止是平衡游戏这么简单,扶一派打一派,只能是见效于短期。政治权力的运行好比开车,始终是动态的,最高的驾驭者只有始终把握方向盘才能一直安稳的走下去。倘若皇帝连起码的政治认知都不能做到,最后的结局必然是车毁人亡。
然而人,岂能无私心?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读后感(六):看完评论,有一点都没有谈及,补充一下
读完仇鹿鸣的《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上海古籍2012年6月1版1印平装本,印量1800。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古中国历史.信仰.制度研究书系》专刊第一种第三本。此系列购入多本感兴趣的作品,此书一出就购入了,但一直未读,实在是有太多的阅读选择的缘故。作者仇鹿鸣也是中青年中古史研究者中的翘楚。对于魏晋之际的政治史,除了大师陈寅恪,唐长孺等,以及田余庆,柳春新,卫广来等有过专题研究外,挖掘史料有限,大师在前,题无剩义,故而不易深入。仇著结合政治史与家族史的研究视角,却又另辟蹊径,在略显贫瘠的魏晋政治史中又挖掘出了新的东西。其中,尤以第二章《魏晋嬗代史事考辩》与第四章《武帝与西晋政治的转折》最为精彩。魏晋政治中淮南三叛其中的因果,高平陵之变发微以及伐蜀之役体现出的司马氏的内部矛盾,读来都令人酣畅淋漓。武帝羊车通常被视为统一后骄奢淫逸的见证。通过阅读仇书分析,其实也不妨看做武帝通过与大家功臣的联姻,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造成的问题,通过羊车的方式,避免后宫矛盾的做法。可以说,每个中国人心里都有一段三国情结,这也是我关注汉魏晋南北朝史的重要原因。不过,此书也有疏漏之处。第三章司马氏集团的形成、特质与矛盾衍生之第一节 从魏臣到晋臣:司马氏集团的凝聚,全书第167页中引文是“文帝”也即司马昭,引文谈的是向雄哭钟会,文帝责之之事,但下文解读却为司马炎(武帝)。且出现3次之多,故应为作者之失。不过,瑕不掩瑜,爱好魏晋史的同好们,此书还是挺值得推荐的。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读后感(七):随手一拈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推动我把这种书看完了。
我早就听说,历史专业的毕业论文,就是一本书。大抵是如此。我找到的是论文,不是书。但是就结构上看来,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不同之处。我想,作者对整个思路的改变,可能在论文到书之间也不多吧。
作者的解读,我也不是完全接受。本来,读史,就是一个极度两可的东西:记载的时候就不一定是真的假的,现在以现在人的视角重新看,那更难以分辨其中微妙的东西了。
但是作为一个毕业论文我觉得这个质量还是很高的...很值得一读。但是的的确确是过于枯燥,以至于读的过程中走了那么好几次的神。想来作者写的时候估计也没想到会对外给别的人来多读的缘故吧。
————————————————————————————
家族的兴衰大抵如此:几代终于通过培养和联姻出来几个有出息的人。有出息的人往往就会被当时的政治家所盯着,没有多少人在高官厚禄/改变世界的条件下能够拒绝于是纷纷走上了仕途,进去之后在层层叠叠的漩涡斗争中时起时落;有出息的人也往往会被各种因素所左右,接触的资源越多诱惑也就越多,不免和一些相貌俊朗的人杂交降低自己后代的质量。最终,在大的浪潮中,整个家族就被倾覆了。
再有,有脑子的人多动脑子想一想。现在和未来,实际都写在历史里。人类文明五千年,有良好记录的三千年,到现在的事儿,一遍一遍的,只是以五彩斑斓的外套,发生着一样一样一样的故事。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读后感(八):对待史料的批判性态度
历史学科,从某种角度上而言,就是对史料的梳理而已,所以史料也就是史学的基础,无论何种理论,都必须建立在史料基础之上,否则就是无本之木,整个无法成立。《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就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对本时段的魏晋交替进行了详细的考察。
本书明确与陈寅恪的儒法升降说进行对立考察,认为陈寅恪的司马家族代表儒家势力上升在证据力上有缺,因为司马家族本身并非儒学大家,反而是军功家族。这种对待前人的勇气,至少就值得赞赏,没有质疑也就没有推动。
而更值得关注的,则是作者本身对待史料的态度,明确提出了史料批评的方法,这种方法在文中处处可见,典型如晋书对晋武帝的看法,就详细剖析,认为晋书本身也受到李世民的影响,在选立太子的问题上,李世民本身有政治利益,也就是本身不是嫡子,反而通过政变获得天子位,因而对于晋武帝持批评态度。而即便是史料本身,齐王攸因为士大夫极为推崇,因而也确实在当时史料也没有问题。但是作者通过考察史料,对于清高的齐王攸进行了真实的展开。
这就是对于史料的处理方式,在对人性共通的基础之上,对于史料保持基本的批评态度,主要问题在于所有文字都是人所记载,也必然带有人本身的情感,无论是当时的记载(诗歌、日记等),还是后世编修的史书(二十四史等),本身也就不免带有个人情感意志,既然带有个人主观意志,就不是决然的客观事实。不仅是历史事,当下事也应当如是观。
所以对史料的批评,首先就是对史料作者的考察,史料作者的立场、态度是首要考察对象,任何史料都是人所做,所以要鉴别人的态度,这些作者必然有立场,立场之下,与文字表述的关联度如何,这些是否会影响史实判断?以此方式梳理、考订,才能得出更加接近历史真实的结论。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读后感(九):司马氏政治资源消长
嵇康、阮籍这些魏晋名士的诗中,常常使用“神鸟”与“罗网”的意象,流露出对于毁灭自由阴影的焦虑和恐惧。“焦鹏振六翮,罗者安所羁”(《述志》)、“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奋迅势不便,六翮无所施”(《赠秀才》)、“坎凛趣世教、常恐婴网罗”(《答二郭》)……随处可见的“罗网”,足见当时名士的精神重负,景蜀慧教授在《魏晋诗人与政治》中指出,嵇阮诗中“罗网”有二重含义:政治刑杀之“法网”和世俗礼教之“世网”,前者是外在的压力,后者则为内心压力。身处这些有形无形的“罗网”,魏晋士人个体的遭际也大不相同,徐高阮的《山涛论》开篇便指出,竹林七贤才性各异,“嵇康激烈而蒙祸,阮籍至慎以全身”,而山涛则是“深沉坚韧”角色,肩负重要的政治使命。几乎每个人都演绎了一段传奇,有的抑郁苦闷,倍感压抑,最终“鱼死网破”;有的人却能屈能伸,长袖善舞,将外在的“罗网”编织成自身的政治资源。司马氏家族无疑是魏晋之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如果说是他们对魏晋名士部下了“天罗地网”,导致了一次次危机四伏的政争,但司马氏家族政治网络究竟是如何形成?网络政治资本是如何集聚、增强和削弱?各方势力和士人个体在政治网络的微观运作中,又是如何相互纵横联合、牵扯角逐?仇著在诸多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将个案分析与魏晋之际整体政治格局结合,借助政治资源和权力网络的动态分析方法,发赜阐幽,引人入胜,反思“非曹即马”的“政治集团”、“党争”等传统研究路向,揭橥了士人群体的复杂面相。
一、前传:卷起与积累
让我们跟随作者的叙事脉络,先来看一看司马氏家族的“前传”。河内司马氏作为东汉新兴地方大族,其在魏晋之际中乱世的崛起之初,实是受惠于以“郡”为单位的乡里人际网络。同乡士人群体之间的血亲、婚姻、交往等要素方式,编织起了守望相助、缓急相应的乡里社会网络。司马懿最初正是得到了同乡名士杨俊的赏识,借助汉末品评人物的风气,从“乡邑之士”一跃而成“天下士”,从而有机会跻身中央政治的舞台。司马懿入仕曹魏,主要是出于荀彧的举荐,从此,河内司马氏与汉末最负盛名的大族之一——颖川荀氏之间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这也成为司马懿拓展政治网络、跨出河内区域的关键一步。曹丕受禅即位之后,司马懿被擢升为丞相长史,每与大谋,屡有奇策,成为魏明帝所倚重的核心幕僚,除了司马懿本身超群的个人能力和时政机缘外,通过与颖川陈氏的核心人物陈群等大族名士的交往、促其子与夏侯氏、泰山羊氏、东海王氏联姻等运作手段,突破了乡里地域局限,不断拓展网络圈层,积累了广泛的政治网络资源,逐步成长为魏晋之际举足轻重的政治家族。正如唐长孺先生所指出的,“东汉时期的地方政权一般控制在当地大姓、冠族之手,而大姓、冠族又累世通过察举和辟举跨出地方,为朝廷登用”(见《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司马氏家族的“前传”,只是地方豪族在易代之际兴起的一个缩影,其实在汉末的高门大族中,却也稍显平常。直到正始十年,司马懿以垂暮之年,成功发动了惊心动魄的高平陵之变,才是决定司马氏家族命运最惊险的一跃。
二、正传:豪赌与扩张
司马家族的“正传”,当以高平陵之变为起点。但直到十六年后的咸熙二年司马炎受魏禅,司马氏代魏历经祖孙三代四人才得以完成。赵瓯北公《廿二史札记》已指出“魏晋禅让不同”,“废一帝、弑一帝而夺其位”,可见司马氏夺权之艰。高平陵之变举事时,身为太傅的司马懿已经被排挤出权力中枢数年,本以三朝元老的身份,当可保全富贵、颐养天年,却借曹爽轻率出城谒陵之机,突然发动政变,冒险反扑而一击得胜,宋人叶适论之以为“异事”(《习学记言序目》)。司马懿之所以敢冒族灭之险,实是有过人的决断和手腕,充分了利用了朝中元老对曹爽的不满——曹爽本与司马懿同受顾命,协辅幼主,实是魏明帝平衡功臣、宗室的政治安排,但曹爽当政,却架空司马懿,斥退老臣,触动曹魏功臣群体利益,打破了政治权力的平衡。而曹爽身为宗室,功业不足,其举动自然引发了功臣元勋的不满,司马懿得以抓住时机,取得太尉蒋济、司空高柔等曹魏功臣集团中的重臣支持,果断成功反击。实际上,这群曹魏元老功臣只是希望维系原有的利益格局,仍“心存曹氏”,并非愿意司马氏一家独大。司马氏欲代魏,仍面对一系列严峻的政治形势。特别是政变后一年,司马懿病卒,司马家族权力的合法性又数度陷入了深重的危机。
司马师与其父相比,与威望、功业均显不足,吸取了曹爽败亡的教训,一方面,对内维护曹魏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继承司马家族上一代所构建权力网络,引进贾充、钟会等曹魏功臣弟子转投其门下,又吸纳名士山涛等和一些出身不高、又确有才能的下士为其所用,通过一系列恩威并施的行动,剪除异己,“挟天子以令诸侯”,仿曹魏故事,以霸府政治取代朝廷日常运作;另一方面,对外则迅速剿灭“淮南三叛”,至司马师因目疾早世之时,司马家族对曹魏权力中枢的控制已相对稳固。
陈寅恪先生最先指出,“魏晋兴亡递嬗,不是司马、曹两姓的胜败问题,而是儒家豪族与非儒家的寒族的胜败问题”(见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本书的研究,则突破寒族、豪族斗争的两分法,借助“权力人际网络”的分析工具,从微观层面动态地揭示了魏晋之际微妙的政治平衡。
作者指出,经过三代二十余年经营凝聚形成的司马氏集团,其核心成员人物的组成并非单一,最常用的手段,往往是试图通过将“魏臣”转化为“晋臣”,分化司马氏的政敌和对手,完成政治权力的转移。因为,司马氏家族的反对者,其人际网络同样根植于曹魏政治结构,也通过相互联姻、交往等方式连结,建立起千丝万缕的关系,凝聚成为密切相关的利益共同体。特别是曹丕接受了陈群的建议,制定九品官人之法,在制度上保证了大族的政治世袭特权(见唐长孺《士族的形成和升降》)。司马氏政权又借此极力而巧妙的维持了士族网络中微妙的动态平衡,“魏晋所杀,子皆仕宦”(郭象语),在不得以时果断将反对者单独剔除出网络的同时,又尽可能避免株连其家族和姻亲,最大限度保全曹魏旧臣对司马氏的向心力。
本书社会网络分析工具的运用,极大丰富了我们对魏晋政治细节的把握,政治资源网络的视角比政治集团更为动态和开放,也暗含了现代社会网络理论的命题:第一,“世界是由网络组成的,而不由群体构成的”,第二,“竞争不仅是资源的竞争,更是关系的竞争,而不是参与者的属性比较”;第三,“网络是开放性的,网络联系超越了群体,就会增加群体及其成员的价值”。
三、后传:固化与撕裂
西晋开国不过数年,政争便愈演愈烈,旋即将司马王朝拖入了崩溃的边缘。叶适指出“晋武帝大议论有四”,第一便是惠帝定嗣,而后三条关于贾后、贾充和齐王攸的进退去留,均因此而起。晋武帝为了保证皇位在本房支内的延续,以太孙聪慧而心存侥幸,做出了不愿意放弃弱智的司马衷为太子的决断,埋下了巨大的隐患,武帝先是不得以通过外戚杨氏集团势力,来对抗支持齐王攸的宗室和功臣集团,毫无根基且缺乏丰富政治经验的杨氏一族,迅速地败于贾充之女——惠帝皇后贾南风,终于重蹈了汉代外戚专权的覆辙,彻底撕裂了西晋政治格局,是为司马氏家族的“后传”。
累世仕宦为倾向的士族化进程,是汉魏以来形成的重要政治遗产,皇权与大族共天下的政治格局,成为南北朝政治史中一个长时段的特征,在文化上也逐步形成了清谈的共同趣味。随着九品官人法的“贵族化”倾向(宫崎市定《九品官人研究:科举前史》),早在西晋泰始之初,尚书左仆射刘毅就曾上疏武帝,认为曹魏的九品中正制不过是权宜之计,“未见得人,而有八损”,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疏虽有识,难收实效,司马氏本欲借此加强网络控制,故决不会轻易改弦更张,正如陈寅恪先生于《崔浩与寇谦之》中所论,“东汉儒家大族之潜势极大,虽一时暂屈服于法家寒族之曹魏政权,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故必伺隙而动,以恢复其旧有之地位”。一旦儒家大族地位恢复,其网络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必将日趋减弱,寒族个体的上升渠道也必将逐渐闭锁和固化,直至到南北朝“五胡乱华”外力所激,士族政治才又进入新一轮血雨腥风的网络重构。
再读寅恪先生的学生——徐高阮的名文《山涛论》,则为我们讲述了司马家族政争的精彩“外传”。与坚毅隐忍、肩负重托的山涛相比,与他一见如故的友人阮籍,则以其特有的清醒和精神超越,处处流露出了一种辞世远遁、逃脱藩篱之网的祈盼。阮氏的八十多首《咏怀诗》,在隐晦地记述了魏晋易代十余年步步惊心的政海风涛之后,于第七十首写道:“有悲则有情,无悲亦无思。苟非婴网罟,何必万里畿。翔风拂重霄,庆云招所晞。灰心寄枯宅,喝顾人间姿。始得忘我难,焉知嘿自遗”。遗世而独立,委质而全身,也许是渺小的个体超越尘网的唯一精神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