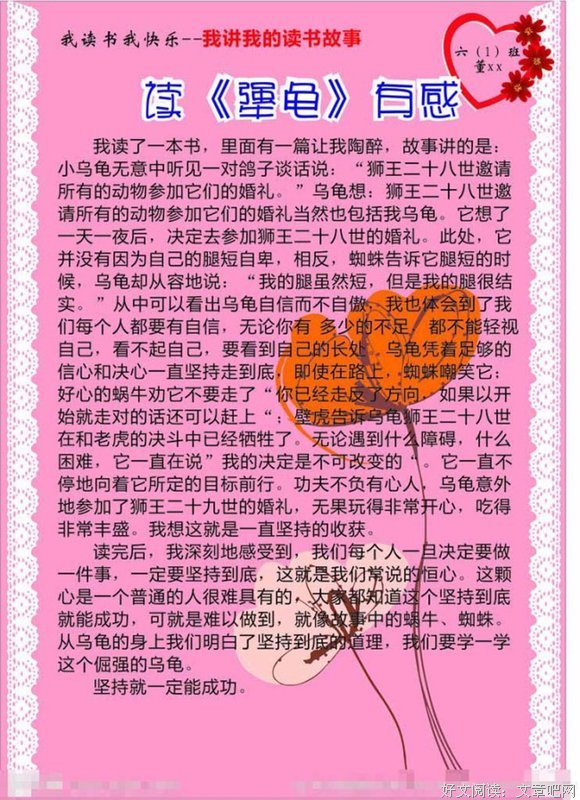
《张光宇现代设计》是一本由张光宇著作,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90.00元,页数:15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张光宇现代设计》读后感(一):考古:观千剑(与中国考古关系之简目,1934年-1965年)
张光宇将中国考古发现中的东方元素施以西方手法,移植、化合出符合时代审美需求,又不脱离传统根基的多个艺术门类的新的表现形式。这同样也是自己以往对文字的可能的兴趣所在,欣喜之余以了解张光宇在创作中的思考方式,分析、介入问题的角度,表达艺术的技术手法为趣,也正好旁观、丰富对东西方艺术造型异同的认识和理解。虽然其中新的思想或启迪可能性不大,更多还是以欣赏、品味为主。资料渐累,简理次序留备后用:
一、明清家具结构趣味
1934年,张光宇设计、制作的朱砂红洒金 “Modern Chinese” 家具,以1933年营造学社在北京通州发现的中国传统家具巅峰之作——多宝阁(匡几)为创作来源。
lt;图片12>普通办公家具,1934年,张光宇设计稿。来源于营造学社发现的多宝阁(匡几)。
lt;图片11>朱砂红漆几,1934年,设计、制作家具实物。1948年,张光宇绘制《金瓶梅人物》的主要角色西门大官人时曾以此几线描造型映射小说中的人物。此几面轮廓设计源自佛教符号——盘长,几足源于清代郎世宁绘制的《平安春信图》中的草地小几同类器物。
lt;图片9>附:
易物换形 “Modern Chinese”,朱砂红洒金家具,1934年
大巧若拙,朱砂红漆几,1934年
……
二、道教建筑装饰符号
1937年,张光宇绘制《林冲》插图,表现葫芦庙时,使用了中国传统道教建筑的装饰符号。
lt;图片3>附录:(暂未整理文字)
……
三、汉代画像砖抽象符号
1950年,张光宇设计中央美术学院院徽,使用了汉代画像砖中已高度抽象的树的符号,与汉字结合,再提炼、组合、抽象化,以表现美树、美术之古今融汇趣味。
lt;图片21>附录:(暂未整理文字)
……
四、藏传佛教密宗饰纹
50年代,张光宇绘制《刘三姐》(广西民间故事)插图,在表现“刘三姐攀登到悬崖边的葡萄藤上,一摇一摆地唱起歌来。恰巧被狠心的地主看见,用柴刀砍断了葡萄藤。可是三姐摇荡一下,藤子又链接起来了。”这段情节中,使用了藏传佛教的传统纹饰及构图,将宗教造型的神秘性与民歌中的传奇性结合。
lt;图片14>附录:(暂未整理文字)
……
五、汉代壁画造型寓意
1957年,张光宇绘《孔雀姑娘》的工作照中,手边有一展台灯。此台灯形象应来自汉代壁画中常使用的“月中之兽……兔”的形象及概念。月光入灯,奔兔动静,夜之所思,人月微光。
lt;图片1>附录:(暂未整理文字)
……
六、草原-农耕青铜器
草原-农耕文化链上的曲刃、直刃青铜剑的分布示意图
lt;图片18>草原曲刃青铜剑与农耕直刃青铜剑对比图
lt;图片17>1951年,张光宇绘制的《杜甫传》中,一舞剑器动四方的公孙大娘使用的正是直刃青铜剑,为农耕文明的青铜器典型式样。
lt;图片16>1960年,中国第一部彩色动画长片《大闹天宫》美术设计中的人物设定,张光宇让骑着青牛的太上老君手持曲刃青铜剑,为草原青铜器典型式样。
lt;图片2>附录:(暂未整理文字)
……
七、商代青铜鼎
1961年-1964年制作《大闹天宫》表现天宫上的建筑群时,使用了1958-1959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材镇炭河里乡新屋湾的商代礼器——大禾人面纹方鼎,此鼎四周饰半浮雕的人面,海内外独一无二之青铜重器。
lt;图片4>附录:(暂未整理文字)
……
八、人面纹
1960年,《大闹天宫》人物设定的巨灵神,张光宇着重突出使用了中国古代的人面纹。
lt;图片15>附录:(暂未整理文字)
……
九、元代佛教石雕
1960年,动画片《大闹天宫》中的天王人物设定,张光宇以北京元代居庸关大型汉传佛教密宗石雕天王为蓝本设计。
lt;图片13><图片6><图片5>从张光宇的作品来看,他是随时第一时间掌握考古发现的第一手资料的。这种时效性从1933年营造学社发现多宝阁,1934年张光宇就设计、制作出 “Modern Chinese” 朱砂红洒金家具之间的间隔时间来看,非常明显。如果他的一个两个作品靠近考古发现的时间,其使用文物进行设计也可能是一种巧合。但如此大量的作品留世,就不会是偶然而为之的了,必是他真的对中国考古学感兴趣。这背后一定有他时时关注考古发现的职业素养,想必也与他的时代中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借助各古文明以创造新的艺术形式有关,或者说也可能与他的本性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喜爱有关。
lt;图片19>张光宇对文物历史信息的阅读也很深。在1951年绘制的《杜甫传》中,公孙大娘一舞剑器动四方,用的是直刃青铜剑;在1960动画片《大闹天宫》美术设计的人物设定中,张光宇却让太上老君手持曲刃青铜剑。如果不懂青铜剑直刃曲刃的文化背景,是不可能用的都如此贴切、精妙的。张光宇是真正的在近现代历史中重新把握了东方数千年传统中的“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这种精神的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有这样横跨多个艺术门类,又留下了大量传世经典,甚至巅峰之作的现代主义巨匠,应该值得骄傲。但这或许更应催发后辈需理清头脑,坚决立意“急起直追的图谋”,不要忘了这是“落后者所应负的责任”!
……
记:阅读张光宇作品之考古因素的阶段性整理只是管中窥豹,应还有未知的实例等待对其继续深入。
……
……
读张光宇
《张光宇现代设计》读后感(二):一本特别的好书
张光宇集共3集 已出版《西游漫记》、《现代设计》、第3种《文学插图》尚未出版。《瞻望张光宇——回忆与研究》不是这一套书里的。未来还要出版《张光宇集》(全集)出版,分漫画卷、插图卷、绘画卷、设计卷、还有一卷动画和连环画。
张光宇集 现代设计 里面有很多人们从来不知道的重要第一手资料。比如《三日画报》版面、《蔷薇》封面、徽章、瓷器设计、剧装、西游漫记展览广告……以前从来没有发表过;一些漫画封面图像质量前所未有的好,研究、喜欢张光宇漫画的朋友,相信你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资料图像。都是从原版书、报扫描或翻拍的!
书的纸张好,印刷也很好,和《西游漫记》是一个系列。由著名书籍艺术家,三联书店的宁成春老师设计,特别要一提的,书的封面用了一大套令人惊奇不已的图像,那才是真正的张光宇(藏在深绿色护封里面)。
《张光宇现代设计》读后感(三):情歌:船行江流中的歌者(民间情歌,1934年)
如果可以,我想邀你与我同乘此舟沿江流而下,一阅时光峡谷中的水岸山色。此地此时人皆相传有一歌者,善唱山歌而自称这些古老的民歌皆为前人所留,不避年月,毕竟也只是抒发了他人胸襟,至于自己是否留情在内,世人闲谈有说绝不可无,有说也许歌者已将自己抽离在歌声之外,才有那些山峡回响中的阴影、日光,甚至水面映照在崖岸上的树丛、山花。人间的传言终归就象这江水一样,分不清那些混淆的是来自哪个自以为水滴的水滴,又与哪个或哪个水滴并不相同,唯取一瓢吟而忘却时代,唯有民歌者的歌声依然质朴如在,若有兴致,不妨与我同试。
歌中船行,时光变幻,歌声唱了又唱虽总有曲尽终绝处,而唱歌的人总要和着那些光影中的交错、疏离,顺流而下。岸虽然已经不同,水还是那条水,只是时而混浊时而清澈,这不妨碍水声如昨,山色依然还是山色,客官还是客官,民歌也还是民歌,从古至今从未变改。愿再听一曲者可顺流而下,另有它途者亦无妨离舟游闲于岸。这些不打紧的事体,来日或许又再相逢,亦未可见。
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
春,八九第六天
2013-02-27 22:31:01
……
小记:民歌者,有以本地域本部族风格强烈为界,亦有从不停留于任何山野高原平地丛林,在任何情感中交融,而不拒时光顺流而下,归入大海或娴静于低洼处寂静为湖。情歌《脚踏板凳手爬墙》另有非汉家版本,如《布依情歌 · 生要连来死要连》(似齐豫曾唱同类题材《藤缠树》)。
清早拉牛去犁田
犁田犁到田中间
见妹打伞田边过
黄牛挨打几多鞭
脚蹬板凳手扒墙
两眼睁睁望情郎
黄牛挨打因为妹
妹我挨打因为哥
为了情妹得自由
挨打挨骂泪没流
钢刀剖开哥肚子
情妹还在哥心头
打死打活妹不愁
前门打来后门溜
打断骨头皮还在
生死不愿把哥丢
......
生要连来死要连
恋歌越唱心越甜
妹变山中藤缠树
哥变青藤要来牵
藤缠树要缠到尖
生死缠到死那天
哥死妹埋不改嫁
妹死哥埋没团圆
双双死了都不算
黄泥盖背心才圆 布依族情歌,引自布依崽儿的 布依情歌搜罗(一)
……
读张光宇
《张光宇现代设计》读后感(四):家具:大巧若拙(朱砂红漆几,1934年)
在中国,实际上不但物质改进落后,思想文化也没有相当的发展,旧有的遗留为一些骸骨式的残砾的工艺,实不足以夸耀国家永久的光荣。历史上已早有评定过他的价值,近代人不宜再劳智虑去加以研究,倘然你已信过世界的进步是属于正途,那么,急起直追的图谋,也是落后者所应负的责任了。
——张光宇,1932年
传统从来不曾离我们远去。它要么雨化无形,浸润大地山野;要么安静地站在我们的视线之外,微笑并相信总有一天会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得到后世每个时代的理解和应有的尊重。就像在曾经的历史中新的传统没有被创造出来之前的传统一样。
这不是东方的“弱势文明”出于民族主义的、看似美好而空洞的抒情。当中国在外部意识形态斗争、内部社会发展的各种矛盾中的经济实力羽翼渐丰之时,当中国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崛起的代表之一、重新获得世界尊重之时,中国人有一种普遍的错觉:中国经济的崛起,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甚至,人们公开地探讨一个并不现实、也不存在的概念——“中国模式”。这种缺乏对世界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工业文明史)基本认识的错觉,普遍存在于所有的经济飞速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自冷战铁幕落下,第三世界国家纷纷从被殖民的泥沼中挣脱,找到属于自己国家前进发展的道路。经济的相对改善,使第三世界在历史中积累的屈辱开始反弹,反映在每个国家的社会的各个层面。世界近代史的工业文明铁律将再次发生作用:只要第三世界国家坚定的走现代化国家之路,那么自工业文明诞生以来,在欧美历史上发生的所有与社会发展有关的经济、文化事件都将以第三世界各国各自特有的形态重新演绎。如,寻找自我传统文化根源,加以现代化改造,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摆脱历史屈辱感,寻找面向未来历史的现实自我定位。
工业文明自摄影术发明与考古学结合以来,出于审美和社会生产的需求,曾锐意汲取自身及各个大陆上的古文明及文化,并根据社会生产、消费的喜好,择取有益于自己的养分,创造出折衷主义(以及不断前进、衍生出各种近现代美术思潮)。第三世界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无论是否能够实现工业文明强国之路,都不可避免的要从外部世界的各种强势、弱势文明的文化中吸收养分。每个国家自己的传统也都被各自重新认识,并由此创造出新的文化,以适应社会及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追寻传统的文化血脉,创造新的文化根基在于寻找传统文化中的本文明的自信,在任何一个第三世界国家都是必然的群体需求。这不会以人的意志改变,也不是仅仅中国所独有的现实。
中国在近现代历史中,也有基于工业文明审美取向的社会美学思潮,并留下实物。其中,最难得的是张光宇在上个世纪早期的一系列横跨各种艺术门类的作品,大部分经其家人精心收藏,保留了下来。这样得以使中国现代艺术的历史增添了除延安以外的另一条同样精彩的美学道路,互相辉映。由于有张光宇这个最新的、最近的与西方工业文明社会主流的思潮同步的现代主义传统的存在,可以为当下的中国艺术提供很多有意义的现实思考和预示。
这是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中与延安美学呼应的另一个最新的、最近的现代主义传统,张光宇的作品因其创作者对社会、文化、艺术的敏锐洞察力,超越了时间和空间,成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难得的是,张光宇不只以作品在时代中写下了中国人跻身于世界美术之林的那种与时俱进美术能力的自信;更重要的是,他对于现代艺术的认识是清晰、明确的,而且其对于中国文化在新的历史中的理解,也有冷静、深刻之处。如,在1932年出版的《近代工艺美术》的序言中,张光宇非常鲜明地以弱势文明的文化自我认定为前提,面对历史、现实赋予中国艺术家的责任和使命,他说:“……在中国,实际上不但物质改进落后,思想文化也没有相当的发展,旧有的遗留为一些骸骨式的残砾的工艺,实不足以夸耀国家永久的光荣……”
这是一种与梁思成、林徽因针对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完全不同的态度和方向;看似矛盾,却是中国文化如何自立于工业文明为主导的、新的人类历史进程中的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张光宇和梁思成、林徽因,在不同的文化领域介入东方文化的方式和态度,恰恰在看似矛盾的对立统一中,有效的构成了解决“中国文化如何在工业文明时代创造出新的文化形式”的这个问题的一个完整的、有机的、带有能动性的最佳解决方案。而曾经历史中的故事也正是如此地写下了这样的华章: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集体设计竞赛中,张与梁林两方分别代表中央美术学院设计组和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组参与其中。最后他们充分地将各自在一生对中国文化的探索、追求中形成的不同的思考、思想、经验融合在了一起,共同设计出了今日中国最有标志性的、最经典的现代艺术作品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张光宇一生的艺术实践,正如他在《近代工艺美术》中阐述的,以“落后者”的自我认定身份,“图谋” “急起直追”,肩负起时代赋予的“落后者”的“责任”!这绝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的艺术追求,更是一个思想者面对历史给予其艺术信念拷问时的正式回答,一种信念的坚持,一种艺术实践的勇往直前,一种带有东方色彩的哲学理念的知行合一。从近现代美术史的角度来看,张光宇在摄影、电影、连环画、家具等等各个艺术领域中的开拓和试验,基本与当时的世界美术潮流同步。不只他的理念,还有他的作品,也映射着这种“落后者”的“图谋”奋进中的巨大精神能量和睿智,以及硕果。
1948年,张光宇曾绘制过《金瓶梅人物》,其中一幅主要的人物——西门大官人的图稿中,除了人物以外,在西门庆的左手下有一小几,样子古拙、质朴,有趣、可爱。最初看到此幅线稿时,并没有对这个小几过多注意。但是,这张已经在1934年制作出来的“朱砂红漆几”,却含有了超越张光宇所在时代美学理论的、敏锐的、带有前瞻性的设计理念。这件看似微小的家具小品,其中的设计思想不低于西方后来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在反对现代主义的潮流中,体现出的那种价值取向和艺术表现手法及理念。
随着逐渐对张光宇的深入发现,尤其是对他在1934年设计的 “Modern Chinese”朱砂红洒金组合家具与中国营造学社在北京通州发现的一件传统多宝阁(匡几)的对比中的发现,以及对张光宇各个时期的不同作品与中国考古学上的文物发现对比可知:张光宇横跨各个领域的艺术作品和实验,尤其是家具设计中体现出的后现代主义审美特点,和他的西方同行们,在理解现当代美术的发展趋势和表现手法的出发点是一致的。
西方各种美术潮流是随工业文明的社会发展进程而动的,而张光宇依靠的或许就是对艺术本身内在规律的敏锐把握,有预见性的在当时中国还是农耕社会、并不具备社会发展与艺术同步的情况下,设计出符合近现代艺术发展规律的作品,以超越社会和时代局限。其最主要的特征是张光宇深刻地理解了在工业文明发展趋势中,艺术思潮必将与工业社会之机械强力结合,以消解过往人类所有的传统(不论艺术家自身所属东西方哪个国度);不拘泥于传统,甚至摒弃传统的理论和造型规则,只从传统中抽取创作者个体、自我、自身可以感知的、需要的元素,与大机械时代呼应,通过各种手法组合这些元素,进行无限的、多层面介入的艺术探索,并以作品表现出这种审美趋势的可能与必要性。如,1934年设计制作的一套朱砂红洒金组合家具。
这套被称作 “ Modern Chinese”风格的朱砂红洒金组合家具,从中国传统组合家具燕几、蝶几、七巧桌、多宝阁(匡几)中,抽离出自由组合的理论特性,使朱砂红洒金书桌、书架等家具,可以根据建筑的空间差异,摆放成不同组合形式,满足不同的审美需求;既有设计者对设计理念的整体把握,又充分地给予了使用者以自由组合的能动,这是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品往往独有的激发受众参与完成艺术品的最后阐述的互动性,以及提供多重解读可能的基本特征之一。在单体家具的设计上,张光宇从多宝阁(匡几)的多个构件造型中抽取结构的线条,融入到新式家具的装饰趣味和构成家具组合的整体变化风格之中,展现了这套朱砂红洒金家具可整合又各自相对独立的特性。并且,这种特性完全符合张光宇对其家具可以进行工业化量产通盘设计考虑。张光宇对这套“Modern Chinese”风格家具的设计,不应单单从设计理念上考虑其追求从传统中提取表现元素,他还使此套家具在生产、展示、使用、互动环节都有了充分的理论和技术准备,符合工业社会的艺术品的美学特征。
在1934年,张光宇不但设计了朱砂红洒金 “Modern Chinese”组合家具,也制作了“朱砂红漆几”等几个家具小品。设计原则同样是抽取传统文化中的表现元素,但表现手法反传统理念而行。由于“朱砂红漆几”的式样使用的传统元素因历史的隔绝,人们已经忘记了,甚至很多对传统中国家具或者器物不了解的人,对张光宇设计的这件看似笨拙的“朱砂红漆几”多有嘲讽、挖苦,故以清代皇家绘画为参照,制作对比图以见其形制在传统上的不凡来源:
郎世宁在300年前画下《平安春信图》,画面中间的雍正和年轻的乾隆身后草地上有一件典雅、质朴的小几。此类器物即为张光宇设计“朱砂红漆几”的传统来源。数十年来,世人少见深藏高阁的古代皇家绘画,也少见此几的形制,但不等于此物就平凡无奇。清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乾隆皇帝72岁再次打开此图时,曾题诗感慨时光以记:“写真世宁擅,缋我少年时,入室皤然者,不知此是谁?” 同样的,皇家绘画中的小几经过张光宇的笔端化合在西门庆的身边,亦应和了《金瓶梅》小说设定的明代背景中人物的社会地位。张光宇从小说中理解人物背景,以绘画返身来映射、烘托、再解读文字中的人物。从清代皇家绘画中择取家具小品,呼应明代小说中的权贵人物,此中深意是否也是张光宇妙手之下,通过美术让读者产生 “入画皤然者,不知此是谁?”的艺术疏离感的一种风趣、幽默的用意呢。
郎世宁从西方来到东方,折衷了西方绘画理论,创造出新的融合了东西方精髓的绘画表现手法,才最终得到了东方国度的认可(开清代一时中国画之新风尚),在《平安春信图》中画下清代两朝帝王在世俗生活中的拟样容貌。张光宇从西方表现技法中寻找融合东方线条意韵的可能,创造、绘制出了新的现代家具式样。在历史上,明代权贵使用过的小几形制,是否曾经渗透进了清代帝王的生活?而张光宇,一个现代主义艺术巨匠,是否就是从清代皇家绘画中,找到了小几的传统源流可以向上反溯历史至明代的可能,以这件“朱砂红漆几”直追明代小说,以绘画与小说人物互相辉映,实践着中国现代主义融合东西方传统现代手法之理念,“急起直追”。若郎世宁知道后世东方艺术家的这些努力,是否也将感慨历史如镜,映射着他从西方来到东方同样融汇东西方手法以创新的不易和艰辛。郎世宁是否也将如他笔下的乾隆一般的对时空以感慨——入室皤然者,不知此是谁?
顾城曾经说过:“我有些相信艾略特的说法:传统不是一个单向的流程,一个研究对象,而是一种关系,一种能动的结构;不仅古人使今人存在,而且今人也使古人存在——他们相互吸引、排斥、印证,如同化学反应中的可逆式反应,如同天宇间旋转的双星。”
“朱砂红漆几”的几面设计,其意味取向应与《金瓶梅》故事本身蕴含的宗教性有关,源于佛教的法器——“盘长”,民间世俗也称吉祥结。盘长,在佛教八宝法轮、海螺、宝伞、宝幢、莲花、宝瓶、双鱼、盘长之末,造型源于印度,寓意亦涵盖八宝。盘长无始无终,回环贯彻,佛法通明,不灭。同时,在佛教中,盘长为“长”,与“八识智”的眼、耳、鼻、音、心、身、意、藏中的“藏”相对应。
张光宇并没有使用太多“盘长”的具象符号信息。他在漆几的设计中,非常巧妙的只取了盘长的轮廓线条介入,对应小说贯彻始终的宗教指向;以抽象符号的宗教内涵,暗喻映射小说人物西门大官人的命运和小说的主题,是为带有后现代主义风格特征的手法。这不仅仅是器物造型上的技法,还着意于线条与文字的对应,为后现代主义的思维特点:提供多层面、多角度解读的可能,不计较是否存在歧义;提供器物造型的艺术形式,但不追求对形式的过度刻意表达;有宗教内涵,但不追求浮于表面阐述内涵;有呼应,但不以追求阅者响应为目的。闻者自知,不知亦无妨,设计者只需关注美学理论和艺术情怀存于线条之内。
如果写到这里,仅仅是对张光宇作品的设计来源的追溯、设计思想的追溯,或许只是末端之法。作者已离世,对其作品解读,后人总有各种因个体见闻边界产生的桎梏,这些不应影响艺术品真实价值的表达。但不妨让我们继续从其设计思想的特征继续深入下去。对张光宇在三十年代设计和制作的带有后现代主义风格特征的中国家具溯源之尝试的目的,自然是不为了去过多理会误读这种预设障碍的悖论前提。重要的是,中国眼下的当代艺术及文化是否应从传统中汲取营养,增加见闻,这是第一紧要的问题。消解传统,创造新的文化形式,这种当代艺术必须拥有的特性,一定要以改造传统的理论和手法为基础和前提,但是,这不等于不需要去了解传统。这也是梁林和张光宇互相辉映,构成一枚硬币完全不同的两面的意义所在。
不懂传统,不学习传统,如何消解传统?如何超越传统?如何创造新的面向未来的传统?当张光宇在上个世纪30年代已经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各种经典造型,完成了带有后现代主义风格特征的作品,今天的我们却还无法从中完全读取出他使用的传统器物的来源、手法之时,这是否是“落后者”真正落后了的明证?这才是今天中国文化及当代艺术应思考的第一个问题:想超越西方的当下,却没有自己的东方根基;想超越自己的东方传统,又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传统在何处。今日多数中国当代艺术家的思考,往往最终流于没有根基的个体的凭空体验、欲念的凭空意淫,理论的凭空臆造,凭空以虚无去反对、对抗、消解虚无,以至多数人最后走向彻底虚无。
只有充分了解西方产生各种思潮的社会背景、艺术思想和表现手法,才能急起直追;只有充分的理解了东方的哲学传统、思想、表现手法,才能破己桎梏,浴火重生。无以有为无,法以无为法。无无自然无有,无有自然虚无。东方的哲学和宗教以及道路,甚至艺术表现手法所向往的空无之境,从来不是追求空洞的虚无,而是通过更复杂和博大的人间试验和尝试,或者说人间体验,将天地自然万世万物作为体验的参照和对象,来归于东方哲学的天道自然。可惜的是,多数中国的当代艺术及工作者理解的虚无谈不上是真正的虚无,部分人也有追求东方境界空无的欲望,但对承载传统文化的古代实物缺乏了解和深入理解,甚至对离当代最近的、已创造出的可以参考的、借鉴的、学习的、使用的,如张光宇等等近现代美术大家的思想及其作品的新的现代主义传统,也一无所知——这是大脑的空无,不是东方哲学境界的空无。两码事。
张光宇在1932年曾写下:“……倘然你已信过世界的进步是属于正途,那么,急起直追的图谋,也是落后者所应负的责任。”他用他的作品完成了其所在时代赋予他的历史使命,中国近现代美术史有张光宇这样的现代主义巨匠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但今天的人们在面对中国文化的未来时,在回首自己的传统时,是否曾在自己的心中自问过:入室皤然者,不知此是谁?
……
读张光宇
《张光宇现代设计》读后感(五):家具:易物换形 Modern Chinese(朱砂红洒金家具,1934年)
当西方工业文明的艺术潮流风起云涌之时,中国近现代艺术大家们也没有停止与时代同行,他们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值得后世不断反复深入的作品。今日中国的当代艺术陷于数字时代的蒙昧时期和资本窥视的泥沼中分不清前路之时,认清自我的艺术传统与近现代历史的脉络,是整个时代向前发展的内在要求。然而也正是由于时代或命运的机缘,湮没在历史和潮流尘烟中的不止沈尹默这样为中国新诗开山的巨匠,另有很多重要的人物没有进入人们的视野被遗忘。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渐崛起,社会工业化的近现代国家自强之路的初步目标渐渐达成,以工业文明社会发展历史对照,今天的中国已经逐渐接近了如西方折衷主义诞生之初的那个时代:公路逐渐发达、伸展向中国的每个乡村;数码相机广泛的普及对应着折衷主义之前摄影术的发明;普通人从对物质需求转向对传统的关注(表现其一为收藏热潮的兴起)对应着折衷主义诞生之初与摄影术结合的考古学对于埃及希腊玛雅古代文明装饰元素的探索。如何在传统中寻求自我认定的潮流已经汹涌而至,而这种来自群体觉醒时代的需求又转化为对近现代历史认知的渴望。于是,近年逐渐被关注,并重新审视历史价值的中国传统古代建筑研究奠基人和开拓者的林徽因,既是如此潮流中的显露出的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林徽因被关注除了文化需求,还折射着政治、经济、文化等等一切关于传统和创新中的矛盾现实。当下中国曾以房地产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转型中如何保护古迹,如何发展新城,如何继承传统,如何创新经济发展模式。当政府开始控制住宅地产,资本流向的商业地产开始急速膨胀,外国建筑师迅速进入中国,没有自我理论与技术甚至美学体系的中国建筑渐有重新沦落为新形式的建筑殖民地之势。当商业地产日渐饱和,资本不停止的流向文化地产。全国各地一派兴建体育场馆、大剧院、各种博物馆、美术馆、电影院。华西村的村博物馆在中国建筑体系理论丧失的情形下,如西方折衷主义一样从传统中提取表现元素,又因人们的嘲笑而仿佛变成了一个热闹的笑柄,却也正在证明着传统理论的继承、创新、发展的缺失。眼下中国地产的变异是资本已和各级地方政府结合,新闻中不断出现从新疆到乌镇,从上海到北京各地都在筹备建设大型主题公园,新的一轮毫无历史根基和发展模式逆东西方艺术发展规律的资本地产狂潮正在兴起)。不仅仅新诗的沈尹默、建筑的林徽因,在近现代中国美术领域,张光宇也是一个被遗忘了的中国现代主义最重要的存在,甚至可以说这个人独自即可撑起中国式的现代主义。这不仅仅在于他的履历与历史同步,更在于他留下的各种作品,足以证明有这样一代真正的现代主义巨匠,中国美术面对世界美术史的时候是有底气的,“值得我们在全世界面前引为自豪(胡考)” 。甚至用最纯粹的西方的标准,他一个人就完成了贯穿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作品。虽然因时代潮流之变以及个人过早离世,没有让他太快的进入人们的视野,但天才的意义不在于世人如何等历史写定之后的觉悟,而反思其对历史以及时代的价值和对人类历史未来道路的预言,重要的是,他以独特的作品,吸收西方技法又超越西方模式,融汇东方审美又超越东方传统,完成了其他人都没有做过的事。他即不脱离时代,又不喧嚣于潮头,但他始终是每次时代潮流汹涌而起之前就已经敏锐察觉并提前出发的人。当回溯近现代美术史之时,无论深入多少,总会发现已有人留下了脚印,甚至那脚印不是独行先锋者的自我昂扬的姿态,它仅仅是一些通向远方的脚印,它明确而清晰的提示着后来者,这里虽有荆棘或迷雾重重,然而,可以通过!越对西方近现代美术史深入,张光宇的意义对东方的意义就越显重要,这也是落后的中国在近现代走向工业文明强国之路中必然的视角和反思,或者觉醒,我们并不缺少有分量的作品,只是应该更深入的了解西方,更深刻的理解东方,超越东西方的表面界限,才有为未来的未来创造出新的传统的可能,而这种可能,张光宇已经在不远之前的历史中留下了无数作品,标记了无数指向未来的具有中国气度的路标。
若今人仿古之意在崇古而非见今,则失了很多乐趣,只能踯躅于泥古。历史的意义从来就不仅仅是与过去有关,它从来都是相对于未来的存在而预示现实的可能。任何看见可能并将其转化为实物的探索者,即为每个时代的先驱,如张光宇。
接下来果然在张光宇的一张图稿中发现了和匡几的关系,于是重翻出营造学社出版的图纸对比可见,毫无疑问的,张光宇就在40-50年代(注:写此文时,书还没有看到,家具设计时间应为1934年)中间设计了这些基于中国传统家具多宝阁(匡几)之上的作品。西方列强随着公路的逐渐发达,摄影术的发明与新兴的考古学的结合,使还未深入到大机械工业时代的工业文明中诞生了以借鉴古埃及、希腊、罗马、玛雅等各种古文明元素的折衷主义潮流。张光宇用自己对传统的敏锐洞察力与营造学社的发现相结合设计出了具有中国自己的东方文化气质的现代家具,并且其抽离传统元素引入设计的手法,完全符合狭义的后现代主义利用历史装饰动机进行折衷主义装饰的设计风格。只不过不同的是张光宇的 “Modern Chinese” 家具保留了东方的气质,无须表露出西方价值观中那种必须黑白对立的所谓反传统姿态。“Modern Chinese” 的造型的确与传统有关,但跟中国传统家具又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它的趣味取舍是对多宝阁的 “结构线条” 的取舍。
与在绘画等美术作品中展现出的现代主义不同,张光宇设计的具有中国气派的 “Modern Chinese” 家具的设计思路也是20年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使用的。“Modern Chinese” 并没有将构思建立在 “匡几” 这个家具在中国传统家具最重要的特点,组合或者结构巧思上,而是从 “匡几” 的分解结构中,抽取出抽象表现线条,这是完全超越当时东西方时代的思路和手法。正如张光宇在30年代玩的连拍自拍,同类的技术手法后来1976年安迪·沃霍尔使用其成为美国波普的代表,在技术的使用和创造上,张光宇注重的绝不是单纯的简单的所谓传统理论中的理性、逻辑、合理性,而是完全与工业文明时代的所有美学的交叠、更替内部规律表现除的同样思路——那就是放弃对所谓出自理性的合理性的表达和内在理论追求,而仅仅以人的感官本身对于时代的存在和趋势发生的可能进行试验、总结,并大量广泛的应用到各类与造型有关的艺术创造之中。或者说,张光宇的这种放到今天依然不失先锋姿态的思路,也并非完全没有来由,中国传统白描于文字及笔墨造型中也多有其渊源,但张光宇的理解绝对不是简单的泥古,否则他设计的 “Modern Chinese” 家具一定会受限于匡几的优点,而不能从精神层面提取 “结构线条” 来表现 “装饰趣味” 的精彩,也就不能完成超越时代,整整超越了东方和西方当时的审美倾向,提前的使用了几十年后才出现的后现代主义的手法。那么,到底是什么能够使他完成这些创造,或许答案只有一个就是随时代而动。西方折衷主义诞生之初,人们不能从大机械诞生中发现它的无穷创造力之前,自然要寻找表现元素来以机械制造替代手工艺制造(虽然此时机械美学还没有质变),这就无法不要求折衷主义的诞生必然寻求各种传统表现元素,并且满足机械生产的丰富性,而摄影术和考古学的结合正为西方工业提供了大量的全球各种古人类文明的传统文化以从中提取现代表现素材。这与张光宇的思路是完全一样的,他并没有寻求机械加工的可能,但是他已经从现代主义的线条中找到了下一步变化的可能,出于对西方的深入了解,再结合东方的悟性,提前玩了一次精彩的后现代主义游戏——自己给自己设计家具,并使用它。所以,张光宇的 “Modern Chinese” 家具放在今天,如果解决一些技术问题,完全可以移植到家具设计中, 并且不失鲜明个性。因为他提取的线条,是中国传统家具经过无数年代无数的试验反复锤炼而出的。当然,如果非要寻求合理性,那么也许张光宇没有界限的横跨各种艺术形式,他的线条经过西方手法的出入,已可以随意用到任何造型艺术之中,无论是家具还是漫画,或者动画片,或者一切的造型艺术都可以随意运用。这种能力只能是一种建立在理性之上的感性可以抵达的,超越一切形式和界限的障碍,并不是单纯的没有来由的感性,也不是仅仅机械的循规蹈矩的理性。若不从感性积累蜕变为理性之上,再彻悟为空空妙手,他也就不是一个真的好玩的、会玩的人了——一个以人类的视觉所能触及的一切存在或者不存为观察乐趣的大玩家。
张光宇并没有在意摄影应该面向镜头,而是站在右侧如同出离了照相机关注的中心,却回头看向自己的几个小弟:特伟(“中国学派”动画、水墨动画片的创造者之一,《骄傲的将军》、《小蝌蚪找妈妈》、《牧笛》导演)、张仃(20世纪中国美术的“立交桥”,设计动画片《哪吒闹海》,首都机场巨幅壁画《哪吒闹海》)、丁聪(小丁,《鲁迅小说插图》、《四世同堂》、《骆驼祥子》插图)、胡考(小说家、文艺理论家、著名漫画家),仿佛画内人之间发生着什么故事,某种情节在推动;又仿佛某个画外人偶然的介入,趣味性之上的故事性,故事性又使观者产生空间中的时间感。当今天无数人在讨论摆拍或者不摆拍这种低级的问题的时候,70年前有人已经超越了这种无所谓的没意义的思考,而用人体的形态和空间构成,在这张照片中提示观者:这个人是谁?他为何回头看向另一边的人?从画面的情节必然中想走出来,还是偶然走到了画面里去?他是画中人,还是和我们一样的观众?他从哪儿来的?如此趣味,却似乎也是同时使用了艺术电影或者现代戏剧中经常使用的布莱西特的那种手法,艺术品应该具有出离艺术本身与观众进行交流的功能,甚至互相激发,在时间的延续性上允许存在偶然性、突发性以推动情节的发展,并不预设艺术作品的最终结局,并给观者也提供了无数选择的可能,留给每个人去完成这个作品,或者观者无动于衷也好,画中人还是非常俏皮的自顾自的玩着他的回头趣味游戏。此时,与同照片中其他几位日后成为中国美术史上各个领域中的大师们相比,张光宇这位当年这些还是毛头小伙子的大师们的大哥,至今埋没无闻真正跨越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现代主义巨匠,其对艺术的理解和执行力高低可见。(当然,其实这种看似高妙的艺术手法同样在张光宇热爱的中国传统民间艺术中比比皆是,在不知名的山间、村头,每天也许都有热爱曲艺的民间艺人们在打趣、嬉闹,延续着中国传统的另一条道路,那永不停息的下里巴的欢乐悲愁,然而能超越艺术表现形式的,随意如何玩都能超越传统、穿越东西方界限的如张光宇者,不多。)或者我们再换一种形式,以早期白话诗中的另一经典代表作来重新构建这种创作的思路,玩一次这些先行者们喜欢玩的那种超越物形障碍的游戏吧。并,以此证明,张光宇利用平面造型构建立体空间中对时间延续性的拓展并不是什么高妙的,或者不合逻辑的技术(如果非要如此机械的理解的话)。它仅仅是任何现代当代艺术表现形式都应该具备的素质,平面、空间、时间,甚至超越时间的技术手法,以及精神上的超越任何形式或既定规则,以及任何极限障碍,而追寻无限存在的可能。比线条更纯粹的文字同样可以构成对立体空间的时间性的描绘。
断章 · 卞之琳
你 站 在 桥 上 看 风 景 ,
看 风 景 的 人 在 楼 上 看 你 。
…… ……
彼岸即见,彼岸即现,彼岸不见不现又何妨。当道路消失,传统是什么,彼岸本不存在又何妨,如同张光宇在民间情歌中那铁线描绘的柔美与阴影回荡在中国数千年来田野山巅村寨河畔怒涛上的民歌声声声不歇,汇入每片这土地上的每个东方魂魄的血液,从不停止涌动着世间万世万物随手摘取的那东方传统中千年不败的花朵。当张光宇将汉代神话中的玉兔幻化做自己 “Modern Chinese” 桌头的一展月中奔兔小灯,又有多少传统如暗夜中的明暗光影在每个东方的预言中遥遥迩来。而这传统是否也将进入你的血液,或呼唤那曾经被遗忘了的却必将走向的关于东方的所有传说中未来的未来的春天。
空间 · 北岛
孩 子 们 围 坐 在
环 行 山 谷 上
不 知 道 下 面 是 什 么
纪 念 碑
在 一 座 城 市 的 广 场
黑 雨
街 道 空 荡 荡
下 水 道 通 向 另 一 座
城 市
我 们 围 坐 在
熄 灭 的 火 炉 旁
不 知 道 上 面 是 什 么
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
春,八九第九天
2013-03-01 20:00:56
注:文字早于见到书,当时不知道的信息为张光宇设计《金瓶梅人物画像》中西门庆的小桌,为 ” 朱红(朱砂红)漆几 “ ,制作于1934年。
“ Modern Chinese ” 朱砂红洒金组合家具制作于1934年,为 " 朱红(朱砂红)洒金靠背椅 ”、“ 朱红(朱砂红)洒金书架 ” 及 “ 朱红(朱砂红)洒金桌 ”
……
读张光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