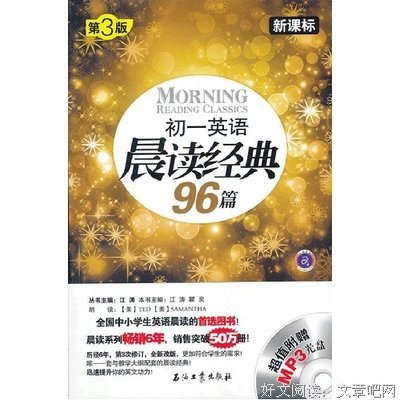《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是一本由Francis Fukuyama著作,Farrar, Straus and Giroux出版的Hardcover图书,本书定价:USD 35.00,页数:67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读后感(一):The end of harmony
http://www.economist.com/news/books-and-arts/21620053-how-benefits-political-order-are-slowly-eroding-end-harmony
The end of harmony
How the benefits of political order are slowly eroding
A BASIC rule of intellectual life is that celebrity destroys quality: the more famous an author becomes the more likely he is to produce hot air. Superstar academics abandon libraries for the lecture circuit. Brand-name journalists get their information from dinners with the great and the good rather than hard digging. Too many speeches must be given and backs slapped to leave time for serious thought.
Francis Fukuyama is a glorious exception to this rule. Mr Fukuyama earned global applause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in 1992. He won more plaudits in the early 2000s with his broadsides against the neoconservative movement that had nurtured him. But rather than milking his fame he has devoted the past decade to producing a monumental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what he calls “political order”. In its first volume,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he took the story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late 18th century. This second and last volume brings the story up to date. The two books rest on an astonishing body of learning.
This burst of intellectual energy was inspired by the half-failure of the liberal revolution that Mr Fukuyama once celebrated. “The End of History” proposed that markets and democracy were part-and-parcel of a single triumphant formula. But the past two decades have produced a more depressing picture. China has adopted a mixture of state capitalism and authoritarianism. Democratisation has failed in Russia and a host of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Mr Fukuyama suggests that a major reason why history has proved to be more complicated than he imagined lies in the quality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Neither democracy nor markets can flourish properly in the absence of a competent state. But such a state can produce many of the virtues of modernity without the benefits of either democracy or free markets.
tate-building is difficult. Mr Fukuyama argues that Europe and America have long led the world in doing the hard lifting. They inherited strong medieval legal codes. They introduced merit-based civil services in the 19th century. For the most part they introduced mass franchises after creating efficient state machines. The man who once talked about “the end of history” now talks about “getting to Denmark”.
Mr Fukuyama contrasts the accomplishment of Denmark et al in creating successful states with two types of failure. The first is a failure of institutions to keep up with social change, as in much of Latin America. After a spate of reforms in the 1980s Brazil’s government is a hotch-potch of first-rate departments and patronage dumps. The second is wholesale institutional failure. The failure of the Arab spring was essentially a failure of governmental capacity. In Egypt the Muslim Brotherhood failed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inning an election and winning total power, so the country’s middle class reluctantly re-embraced authoritarianism.
Yet this is not a simple story of the West versus the rest, or the developed world versus the underdeveloped world. Mr Fukuyama notes that southern Europe lags a long way behind northern Europe: Greece and Italy continue to distribute jobs on the basis of patronage. But he is at his most interesting on East Asia. China produced a highly competent state, staffed by first-rate civil servants chosen by written examinations and capable of monitoring the affairs of a vast empire. Mr Fukuyama argues that what we are seeing in China now is the revival of this tradition after a century-long collaps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reaching back into history to prove that you can create a competent state without the benefit of the Western traditions of democracy or the rule of law.
The book is sometimes frustrating. Mr Fukuyama frequently overloads the reader with his learning, and the first two parts of this book, on the state and foreign institutions, are too lengthy and the second two parts, on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decay, too short. But two things more than make up for Mr Fukuyama’s occasional failures.
The first is the quality of his intellect. He litters the book with insights that make you stop and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preserved the main features of Henry VIII’s England long after England had abandoned them, he says, including an emphasis on the authority of the common law, a tradition of local self-rule, sovereignty split among several bodies and the use of popular militias. Africa’s botched state-building can partly be explained by the fact that it is the most lightly populated continent in the world: it was only in 1975 that its population density reached the level that Europe enjoyed in 1500.
The second is his despair about the current state of American politics. Mr Fukuyama argues that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that allowed the United States to become a successful modern democracy are beginning to decay. The division of powers has always created a potential for gridlock. But two big changes have turned potential into reality: political parties are polarised along ideological lines and powerful interest groups exercise a veto over policies they dislike. America has degenerated into a “vetocracy”. It is almost incapable of addressing many of its serious problems, from illegal immigration to stagnating living standards; it may even be degenerating into what Mr Fukuyama calls a “neopatrimonial” society in which dynasties control blocks of votes and political insiders trade power for favours.
Mr Fukuyama’s central message in this long book is as depressing as the central message in “The End of History” was inspiring. Slowly at first but then with gathering momentum political decay can take away the great advantages that political order has delivered: a stable, prosperous and harmonious society.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读后感(二):他依旧相信历史终结
他依然相信历史终结
@RU李华芳
2011年,福山(Francis Fukuyama)出版了其关于政治秩序的巨著第一卷《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史前到法国大革命》。时隔三年,第二卷《政治秩序与政治衰退:从产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问世。作为亨廷顿的弟子,福山一直在深化亨廷顿的理论。这两卷本比亨廷顿关于政治秩序和政治衰退的理论更为深入,不管是从历史角度来看,还是从比较政治的角度来看,福山的两卷本不仅多了更多的细节,也多了更多的“内部差异”。这是大气磅礴的野心之作。
不少观点认为福山背弃了自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结论,因为在“历史终结论”中福山认为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最终各国都会选择民主制度,历史就此终结。而现在福山似乎更强调民主制度的不同模式及其限制,尤其是第二卷关于美国政治的衰退部分,直言不讳美式民主制度的发展限制了国家的行政能力,所以是福山背弃了历史终结论。
但真的如此吗?不妨先从福山对美国行政衰退的相关论述开始说起。福山说的政治衰退,借的是老师亨廷顿的概念。福山是将国家能力与法治和民主问责并列在一个层面上进行讨论的,这是福山在第一卷《政治秩序的起源》中的主要贡献。福山认为现代国家的去血缘化和官僚体系的非人格化,是国家能力增强必不可少的。福山在第一卷中给了中国历史诸多赞誉,主要也是说中国在增强国家能力方面确有可取之处。
但在第二卷关于政治衰退的论述中,更确切来讲,福山讨论的是一个国家行政能力的式微。福山举了个例子来说明美国政治的衰退。美国林业局(Forest Service)一开始的行政能力非常强,主要是因为一开始林业局是选贤任能,大量雇佣专家并且依赖他们的知识,同时林业局也具有很大的自主性,所以行政能力很强。整个林业局也非常高效,尤其是在木材开发上,卓有成效,表明了有效的行政能力。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林业局的目标越来越多,甚至目标与目标之间相互冲突。例如在防火这件事情上,林业局对野火的认识也经历了从有害到有利的转变,因此在对策上也出现了从灭火到不阻止的大反转。但这个还可以通过专家知识来有效解决。而其他的事情,例如森林保护和木材开发之间的冲突就没那么简单了。利益集团为保护居住在森林中的人的利益游说国会,往往要为几十万美元的房子花费数百万美元的成本,而这个成本往往要由政府来承担。
多重目标、限制日多,结果导致林业局的效率日趋低下。与此同时,林业局的自主性也逐步丧失。林业局的人现在更加关心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饭碗,增加自己的部门预算,而不是提高效率,因此他们也没有很强的动力去降低成本,导致行政效率进一步降低。福山认为管窥一斑,这林业局能力的下降就是美国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下降的一个缩影。
那么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了行政能力下降的困境呢?福山将政治能力(我这里认为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行政能力)和法治以及民主制度并列,并认为政治衰退是法治和民主制度内生的。也就是说,民主制度天生的局限会导致政治衰退。但从福山对美国民主的论述来看,实际上说的是美式民主里的“三权分立”导致的司法和立法分支对行政能力的制约。
(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退:从产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先看司法分支对行政的制约。福山特别指出法官造法对行政能力造成的限制。例如奥克兰(Okland)港口开发就因为各方利益摆不平,陷入旷日持久的诉讼中。长达数年的官司在事实上使得港口开发陷入停滞,即便最后重启,效率也已经极大降低。这是美式制度中司法对行政限制的典型例子。
在罗慎博(David Rosenbloom)之前,公共行政学里没有人系统地从法律视角审视公共行政。罗慎博认为除了传统上从政治和管理的角度来讨论行政之外,必须将法律视角也纳入进来。因为实在有太多美国行政上的问题不仅与美国宪法相关,也与美国的法庭判例相关。从美国历史来看,这实际上无可厚非,不管是妇女投票权还是民权运动,都是借着美国宪法的精神而逐渐展开的。美国宪法天然对行政就有所限制,尽管建立一个合众国也是宪法设立之初的目标,但这个目标并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乃是要使这个联邦政府为人的基本权利而服务。
政府是公仆,这当然是很理想的状态。实际上要面对的却往往是顾着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有效性,但往往不能兼顾公平性。反过来,也是如此。福山的论述着重在司法分支对公平性的要求限制了行政效率这一点上。且不说结果的公平性,程序上对公平性的要求,就足以拖垮一个项目。类似奥克兰港口开发这样的案例在美国并不鲜见,各方利益团体在无法协调一致的情况下进入法庭诉讼,项目开发长时间的推迟,效率低下对经济发展殊为不利。
福山也因此担心美国1964年的“民权法案”以及平权运动造成的不良结后果。平权当然是奔着公平性而去的,但一开始主要是为了修正历史上由于对肤色、宗教信仰、性别或者民族出生等对就业者的歧视。相对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十分“强”的法案,主要想防止的也是制度性的歧视。但平权运动不断发展,导致这个民权法案实际上成了一个特别“强”的法案,过去的歧视不仅要修正,也需要实质性的“补偿”。
如此一来就可能造成“反向歧视”。这导致政府部门招聘行政人员时,假如面临一个白人和一个少数族裔拥有同样的资质,白人很可能无法得到工作。甚至不少公立大学的反向歧视导致少数族裔获得了分数之外的“青睐”,形成了事实上的“降分录取”,这不仅是低效率的,也是不公平的。
福山进一步阐释立法分支如何限制了行政能力。除了“立法-上升为法律-通过司法”对行政分支进行限制之外,如果从源头上来看立法分支本身存在严重的问题,就可能对行政能力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那么到底什么影响立法分支的效率和公平呢?福山提出两点:党派化和利益集团。美国政治的党派化趋势被诟病久矣,而其极端表现就是两党分歧过大无法在预算上达成一致最终导致“政府关门”,影响行政效率。而在政府关门期间,大量公共服务不能有效提供,对社会公平也是极大的损害。
福山对比了英国的威斯敏斯特体系和美国体系,认为英式民主更能保证行政效率。因为英国只有一个议会,而不是像美式民主一样有可能造成分裂的政府。在美式民主中,不仅众议院和参议院有可能会控制在不同的党派手里,总统和议会之间也会出现分属不同党派的情况。这时候就容易出现分裂的政府,例如像奥巴马政府,总统是民主党人,但国会控制在共和党手里。分裂的政府造成形成行政窘境,总统要想做点事,往往通不过国会投票;而国会通过的也往往会遭到总统的否决,行政分支寸步难行。以预算为例,英国的预算制定比较有效,通过专职人员制定而后在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投票表决,往往一周两周就能搞定。但在美国长期的扯皮则有可能造成联邦政府关门。
利益集团的负面影响当然不是福山的创见,而是已经被反复讨论过了。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风起云涌,最后发展到占领华盛顿DC。哈佛大学的莱西格(Lawrence Lessig)在K街演讲,痛心疾首,认为华尔街问题的根源在K街,这些食利集团游说组织才是造成美国政治经济问题的罪魁祸首。但从美式民主的本源来看,正是因为利益集团能部分集结分散的利益,变成团体之后大家才边打边谈,最终发展出一个宪政来。所以利益集团也被看作是多元民主的一个重要基石。
但问题是从利益集团到多元民主有一个隐含的前提,那就是利益集团所集结代表的利益是长期不变的,这背后就意味着要将人们的利益固定住且长期不变。显然这个假设不现实。现实中的情况往往是多重利益主体之间有潜在的利益冲突,导致行政机构往往有相互冲突的目标,以林业局为例就是森林开发和保护之间的潜在冲突,背后是不同的利益集团的呼声。但这样一来往往会使行政机构无所适从,行政效率变差,能力由此衰退。
所以福山追根溯源指出国家能力的衰弱是美式民主“三权分立”逐渐发展的一个结果,而且似乎也看不到出路。美式民主制度也无法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福山把这种以行政效率低下为表现的政治衰退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制度惯性”和“思维僵化”。
不过以为制度惯性是思维僵化的一个表现。所以背后真正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思维会僵化。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Think, Fast and Slow)》一书中提到两种不同的心智模式,称之为系统1和系统2,大体上系统1依靠直觉做决策,而系统2依靠理性思考做决策。制度惯性归根结底还是思想僵化导致的,系统2不肯花心思,导致一部分人固守现行制度带给他们的利益,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抵制了可能的变革。因为变革会带来不确定性,利益集团要抵制变革以减少制度不确定性带给他们的风险。这可能是全世界都普遍的现象,不仅仅是美国独有。例如在中国这种思维僵化导致制度惯性的例子也很多,最典型的例子是贫困县和计划生育。这就导致改革总是很困难的,有时候甚至要激进革命去冲破旧制度的藩篱。
回到福山关于政治衰退的论述,小结起来大体是说美国政治衰退的表现是行政效率降低,而导致行政效率降低的原因是因为民主制度内生的因素决定的,例如司法和立法对行政的限制。利益集团和党派政治不仅影响司法和立法,也直接对行政效率产生影响。并且利益集团现在已经助长了制度惯性,使得制度不能灵活的调整,进而加剧了政治衰退的过程。
但福山对美式民主的检讨是对的么?他有没有忽视什么?在我看来,福山至少忽视了美式民主中两个重要的进展。一是代表性行政,即在行政机构中增强公务员的代表性。例如利古琦(Norma Riccucci)等人关于代表性行政的研究表明增强行政机构人员的代表性能显著提高行政效率和公平性,尤其是在那些需要公民合作的领域,例如公共安全和垃圾回收等。
另一个是公民参与和协商民主的发展。如同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的研究表明的,尽管参与和协商等可能只在小范围内管用,但小范围内的治理以及社区公共品的供给,才是民主的根基,这接的是从托克维尔到普特南关于结社和社区自治的研究传统。
因此,从代表性行政和公民参与这两个方面的进展来看,福山对美国政治衰退的论述就要大打折扣。尽管我不能否认福山提到的许多现象,例如党派化和利益集团的负面影响等,但美式民主依旧在发展,并不必然导致行政能力衰退。
在福山的笔下,中国的政治能力卓尔不群。在众多政治衰退的案例中,中国是一个例外。行政能力(国家或者政治能力)对于现代国家而言,举足轻重。因为如果行政效率低下到无法有效供给公共产品和服务,那么即便保证了表面上的公平,实际上问责性也是不足的。历史上去血缘化的政治和非人格化的官僚以及选贤任能的人事制度,造就了中国值得称赞的高效行政,也因此吸引了福山的目光。
当然,福山依旧相信历史终结,所以并不认为中国真的例外。因为尽管中国的行政能力比较强,但是法治不彰和民主羸弱,使得中国当前的模式注定是不可持续的。比如说中国的高铁发展,就得益于表面上极强的行政能力。对比之下,高铁在美国加州长达数载毫无进展的遭遇更进一步凸显了中国的行政效率。但由于法治和民主的缺失,导致中国高铁的社会成本极高,征地及环境问题造成了大量群体性事件。中国高效的行政缺乏有效的问责,例如无法通过法律甚至通过立法层面的努力,对因为以高铁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的受损人群进行法律救济。
中国模式无法持续的根本原因在于如果没有法治和民主对政治进行制衡,那么就只能进入到“期待明君”的模式。但期待明君模式往往遇到的是“坏皇帝”问题,如何防止坏皇帝?至少在中国历史未能探索出一条有益的途径,王朝更迭更多说明的是坏皇帝无法阻止,只能通过改朝换代这种代价极大的革命方式来替换坏皇帝。但起义者即便成功,等尝到权力的滋味,就又会陷入到坏皇帝的陷阱里。即便1949之后,“坏皇帝”的问题依旧存在。只不过“坏皇帝”变成了“政治狂人”,一系列运动,从大跃进到文革,没有稳定的政治秩序可言。行政能力也未见得有多高,而法治和民主当然是没有的。
所以如果法治不彰民主羸弱,即便拥有很强的行政能力,这种中国模式也不可持续。2011年福山就已经讨论中国历史对未来的影响,他当时提到儒家文化和红色文化会对中国未来有很大影响。我当时去信和他讨论中国的自由传统也会影响中国未来。福山回复称:“基于普世价值,我依旧相信中国未来唯一的可能就是民主化改革。(I still believe that this type of reform (democratization), based on universal values, is the only one possible for China in the long run.)”
是的,他依旧相信历史必然终结。
【推荐书目】
Fukuyama, F. (2011).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Fukuyama, F. (2014).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http://dajia.qq.com/blog/468353093172117
本文系腾讯《大家》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关注《大家》微信ipress,每日阅读精选文章。
(责任编辑:陈小远)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读后感(三):福山的终结,一本无思想无趣味的机场畅销书
读《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这卷时,我突然冒出一个邪恶的想法:这书其实根本就不是福山写的,他只是列出一个提纲,然后让手下的博士生去按照提纲找找材料填进去,最后,像无数中国的博导一样,福山给这本断烂朝报署上自己的名字。剩余的时间呢,福山就可以全世界到处飞,参加高端论坛,高校讲座,与政坛学界媒体圈的名流们把酒言欢了。
有这样的想法当然首先因为这本书奇烂无比,它是如此之烂以至于铁定会成为《纽约时报》的畅销书。因为它完全就是按照那种经常在机场书店见到的畅销书的写法来写的,像商业畅销书《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企业长青的八大关系》一样,本套书其实也应该改名为《成功国家的三个要素》,或像政治畅销书《Why Nations Fail》一样改名为《How Nations Succeed》。本卷把第一卷中提到的三个要素(国家、法治、可问责政府)再拿出来翻来覆去地说说说,然后找一些无聊的历史材料充数。其实许多商业畅销书都是这个路数,发明一个概念(像“黑天鹅”“引爆点”“长尾”“蓝海”这种),然后找一些材料说明,但人家这些商业畅销书里举的例子最起码有些还挺有意思,而福山的博士生找的这些历史例证真是又臭又长。
如果说在《历史的终结》时期,福山还曾试图做一种“哲学的政治学”,用柏拉图的“理性、激情、欲望”,用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用科耶夫的“历史终结”,用尼采的“末人”,甚至用“消费社会”来作为思考的框架,那么在《政治秩序》时期,福山则完全转向了“畅销书的政治学”。
福山的这种转向给读者留下了一些重要问题:是继续沿着科耶夫以降的法国思想往下走(或与科耶夫对话的列奥·施特劳斯往下走),还是开始用《经济学人》的方法思考政治(像刘瑜说她所做的那样)?重要的政治问题究竟是“虚无主义的战争”(《历史的终结》最后一章提到的那样),还是按照“强国、法治、民主”的顺序来把“失败国家”改造为“成功国家”?或者更具体一点,ISIS的崛起实际有两方面的原因:1. 伊拉克在战后没有建立起一个“强国家”,而ISIS在某些地方填补了政府职能的空缺;2. ISIS号召了那些厌倦自由民主制下虚无享乐的“末人”,比如ISIS中有不少人是来自英法的中产阶级,他们招募那些自由民主国家的新成员时是这么说的:“难道每周吃 Nando's 烤鸡就能让我们满意吗?快来加入圣战吧!”这两方面孰轻孰重?
福山的转向真正是福山的终结,表示他不再动脑子了,成了智识上的末人,凡事拿出三件套,眨一眨眼睛,找到了幸福。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读后感(四):福山的局限
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最大的遗憾不是在于它的内容,而是在于它对于福山本人的意义。本书发行后,许多评论认为它代表了自《历史的终结》之后,福山对于当代政治新的思考,象征他思想的转变。不得不说,这种看法实在过高估计了这本书的定位。
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本质上是一本命题作文类的书。在这里看不到《历史的终结》中那种积极系统的理论构建,而是以福山的三元素:政权,法治,问责制为框架,去解释世界各国的一些政治经验。并提出了一个对西方读者来说可能还算新颖,但对中国读者完全是常识的一种看法,那就是“盛衰论”。既然理想的政治是由三元素构成的,而三元素又是相互联系与制衡的,那么三元素的此消彼长自然会导致“盛”(order),“衰"(decay)的相对变化。其中order大概就是这种演变中的一种平衡的理想状态(equilibrium),而decay自然就是一种失衡,或者“不全面发展”了。
对于西方读者,这本书带来的震动不仅仅是这种盛衰论的提出,更重要的是福山第一次把盛衰论应用到西方自由民主体制上。长期以来西方有一种看法,那就是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对“衰退”免疫,或者说根本不存在衰退的问题。这里面牵扯到德国理想主义哲学和黑格尔,本文不再详述。基本思想是人类历史的进程是“人类精神”的觉醒的反应,人类精神最终觉醒就会出现达到一种“至善”的状态,而自由民主制就是这种至善,这也就是“历史的终结”的含义。
而福山在本书中的思想,是含蓄的承认西方自由民主制也是由要素制约的一种机会性的状态,也会因为因素的变化而产生“好民主”与“坏民主”。这跟福山之前认为自由民主制是人类终极形态,将“传之万万年”的态度比起来,自然是一种转变。但是对于从小受到阴阳辩证思维熏陶的中国读者,尤其是目睹近来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种种问题和西方国家本身的政治衰退,这很难说有多震撼。最重要的是,福山的转变仅仅是态度上的,他在思想理论上其实并没有太多新的见解。
中华文明在政治上是非常早熟的,丰富的政治经验以及史学传统,使中国人注重实际历史经验和案列的分析总结,很早就有了对于盛衰变化的反思。相对的,西方学术传统从苏格拉底开始就更喜欢理论概括。我们今天熟知的很多西方政治术语,五花八门的各种主义,本质上都是一些理论模型而已。实际上世界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完全对应某一种主义。拿这些模型往实际情况上套,尤其是中国这样复杂的国家,肯定是盲人摸象了。
福山能够抛开一些繁复无用的理论模型,从要素变化的角度分析政治的演进,也是一种突破。但是方法论上仍然免不了生搬硬套的习惯,以及西方政治学者史学基础差和不看第一手资料的毛病。如果说福山对于西方国家尤其美国的叙述还有一些自己的创见,那么他讲中国的那几章简直就是找几篇中国研究的论文填进去的。他对于儒家和法家的理解可能还不如国内书店里的国学科普,对于中国历史的误解就不用说了。
福山本行还是研究当代政治的智库人士,而不是搞政治哲学或者政治史。他以《历史的终结》成名,我觉得还是在冷战结束的特殊时间点所造成的,可能属于“风口上飞起来的猪”那一类吧。相对的,福山对于当代政治的观察还是有比较独到精确的见解,至少能反映西方的第一流水平。虽然福山写这本书没太上心,原创并不多,但是还是集成了一些高质量的观点,尤其在当代政治方面,比较值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