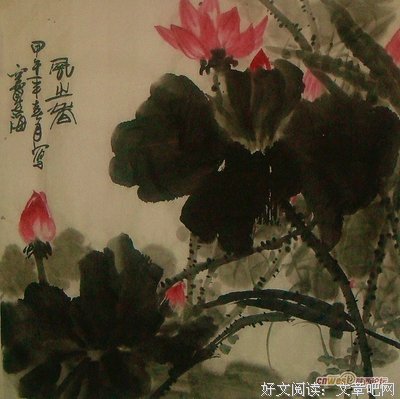《出家》是一本由张忌著作,中信出版集团 / 中信·大方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页数:26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出家》读后感(一):都是为了一个家
男人,携带一家到城里生活,租在一个小房子里,投靠自己的亲戚,后来亲戚无法依靠,男人为了一个家庭,同时打三份工。
男人为管事的人送鳖,送早餐,送牛奶……早上四点起床,晚上还得照顾娃,有时候一晚上只能睡俩小时。
很难说男人是个骗子,也很难说男人不是个骗子,是不是个骗子很难定论。
有市场的需要,男人就为他们解决疑惑。还真是运气,他解决的那几个疑惑,真的解决了。
按理说,如果他当了和尚,他或许会有一番前程;但是同时,他也得放弃自己的妻儿。可是,孩子们跟他并不亲,所以,放弃了,大概也就放弃了吧。
因果。
《出家》读后感(二):你的“出家”,“我”的回归
近来脑子乱,手捧着《出家》,心里想的,却是汪曾祺的《受戒》。
汪老的《受戒》的确美。想想也是,与少年有关的,怎能不美呢?恐怕连他们的梦,也是香甜甘美的吧?与《受戒》一样,《出家》讲述的,也是关于佛门的故事,但它所带给我的,却是一种沉甸甸的感觉。那么,这种沉重从哪而来呢?张忌的《出家》,又向我们敞开了怎样的世界呢?
翻开书页,主人公方泉,带着焦灼与困惑步步走来:作为一个携妻带女初进城市的“乡下人”,他一无背景,二无学历,只有一身的力气,还有“要让一家人过上好日子”的愿望。
怀揣着这个愿望,方泉身兼数职,努力养活家里人:送牛奶、送报纸、蹬三轮……精打细算,步步为营。他总以为,自己每一步都走得很稳当,他还盘算起未来的幸福日子:有儿子,有房子,一家人,快快乐乐——要求不高,可对他来说,已经够了。
但命运已在前方为他准备各种坎坷,这坎坷,简直是层出不穷,应有尽有:牛奶公司倒闭;三轮车被扣押、被罚款;被恶棍敲诈……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爬起,他咬着牙,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总算,添了丁,攒了钱,仿佛幸福已向他招手了。谁知道,老婆又得了囊肿……
一声叹息!
生活跟游戏多么相像,过了这一关,马上就有下一关等着你,而且下一关总是比这一关难,一关又一关,永远打不完——当更大的挫折迎头砸来时,方泉终于控制不住自己,放声大哭。
幸亏还有梦想。
如果说,方泉还有最后一点梦想的话,这梦想应该是寺庙屋顶上的那道光泽吧?或者,是阿宏叔送给他的《楞严经》吧?偶尔的机缘巧合,使得另一扇门向他打开,门里,有一个全新的世界,方泉摸索着踩了进去,开始了着另一种生活——做空班、当乐众、当方丈……
《出家》的书腰上,刻着一行字:劳碌牵波的生活,是否有一刻让你想要逃离?逃离?确实如此,对每个人来说,为自己量身定做的生活再怎么妆容精致,总有卸妆的时候,甚至一不小心,还会面露狰狞。使人畏惧,令人想要逃离,逃得越远越好。更何况是方泉,那个挣扎在社会底层,“闯关”闯得精疲力尽的方泉。
方泉也想逃离,但一开始,他未能跑远,始终在家庭与寺庙之间跳来跳去——他跳离压力重重的现实世界,走进破旧但宁静的山前庵,但那一刻,自己真的“身体澄明”了吗?他逃离与俗世并无两样的方外之地,回到家中,却发现自己这个顶梁柱,遭到了孩子的忽视,爱人的质疑。
应该说,方泉还算是个老实人,虽有小聪明,懂得利用“潜规则”,但还能守得住底线。这些底线,在那个慧明口中的“末法时代”中,显得又是如此可贵。这也使他得到慧明、周郁等人的好感,误打误撞之下,有了寺庙,有了护法,也有了尚算可观的收入。理想总是建立现实之上的,当现实中的压力不再咄咄逼人后,我们的主人公,总算可以构筑心中的理想了。他的理想,已不再是原先的“衣足饭饱”,而是一张绚丽无比的精神蓝图。山前庵,那个曾经的避难所,在他脑海中也已脱胎换骨,成为实现宏伟蓝图的实验田。
小说最后,方泉站在城市的马路上,看见了“人潮汹涌,旗帜招展,一个人坐在法台上,双手合十,仁慈地俯视着众生。”也许那一刻,他才找到了最真实的自我。
或许,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我”。这个“我”,不是别人眼里的“我”,这个“我”,始终潜伏在自己的灵魂最深处。有些“我”,一直在蠢蠢欲动,呼之欲出,有些“我”,却藏得太深太深,深得揪也揪不出来。那么,现在的你,找到那个“我”了吗?
《出家》读后感(三):对“家”与“出”的理解
“家”——是主人公向往的生活方式,是老婆温柔、有儿有女、20年后可以存100万;“家”是主人信奉的道德体系,举头三尺有神明、不取没道理的钱财、诚信厚道;“家”是主人公信奉的“不贪念超出自己福报的利益”。 而“出”又是什么呢?作者以做“陆水”、“佛事”的形式,描述了一夜暴富、巧取豪夺的故事。这些经历,不仅解决了贫苦家庭的燃眉之急,更促使主人公迅速瓦解了一直以来对于怎样构建“家”的想象。更重要的是,在建立新的价值体系的同时,主人公所追寻的,并非只有金钱,他想要从给人做漆工到给人摸摸头的转变,他想要从社会最底层到受人匍匐的转变,他想要的是——尊重! 而这,恰恰是他当初认为的虚妄。 书中结尾,那个坐在冰冷的庙宇门槛上,彼时与此时的“我”对望的场景,既是主人公对过去与现在的反思,又是未来看的预兆。因为人一旦登上了山巅,就不可能永远满足院子上的那方天空了。YJC于成都
《出家》读后感(四):去写“做官”吧,不要在一窍不通的领域盗听途说。
出家为僧,在这片土地上已经延续了近两千年,就如同做官一样,每个人的出发因由都不一样,其心路历程、信仰目的也各不相同。无非崇高,无非卑劣。但是出家与做官有本质上的区别。
古德有言:出家者,大丈夫之事,非将相之所能为也。夫将以武功定祸乱,相以文学兴太平。天下大事皆出将相之手,而曰出家非其所能,然则出家岂细故哉?今剃发染衣,便谓出家。噫!是不过出两片大门之家也,非出三界火宅之家也。出三界家而后名为大丈夫也;犹未也,与三界众生同出三界,而后名为大丈夫也。古尊宿歌云:最胜儿,出家好,出家两字人知少。最胜儿者,大丈夫也。大丈夫不易得,何怪乎知出家两字者少也。
《出家》读后感(五):《活着》《出家》
《活着》,讲述的是在那样的大环境下,所有不幸集中到了一个人身上, 生命如此脆弱,当最亲的人接连离开,是隐忍地活着,还是结束,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脆弱的生命对命运大喊:要么你一下撞碎老子,否则,即使伤痕累累,老子也要活着。
所以相比《活着》,《出家》应该是《活该》,就是你要‘活’得更好,你就‘该’付出更多,这就到了心理的另一个需求层次,当方泉偶然得到了一座寺庙,又偶然遇到护法周郁,在心底的强烈的自我实现的需求被唤醒,他改变了“要让自己的老婆孩子生活得更好的”初心,那“终”会是什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假如方泉的宏伟目标全部如愿,到了自己人生巅峰的他是否会顿悟,成为真正的大师。
近日读张忌的长篇小说《出家》,篇幅不长,流畅好读。故事并不复杂,讲得是一个方泉的人,带着妻子秀珍,离开乡村,来到城市里讨生活。两人生儿育女,辛苦生活。方泉、秀珍读书不多,从事的是底层工作。方泉送牛奶、蹬三轮车、装修工,偶尔去寺庙里兼职。秀珍的工作体面一点,在超市里当售货员。一家子生活虽苦,倒也其乐融融。在因缘巧合之下,他得到一间自己的寺庙。经营寺庙是桩大生意,赚钱多。但像所有发财的人一样,家人与他愈发疏离。佛事成为生意,他成为“末法时代”的一员。
底层老百姓把当和尚当作是一门谋生的手段,自古有之。高僧圣德皓首穷经,跋山涉水追求佛理的精神,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僧侣,如平常老百姓一般,品尝着生活里的喜怒哀乐。宋朝时期,佛教已经完成了世俗化,随着商业的发展,便出现职业性的僧侣。他们通过为老百姓祈福、做佛事等方式来增添收入。和尚收入颇丰,他们游冶狎妓、偷情私通、娶妻纳妾,亦是常见。在岭南一带,僧侣娶妻蔚然成风,与普通老百姓无异。一时之间,朝廷也无法禁止。明清僧侣的生活状态,与宋朝其实无多大区别,从《水浒传》《金瓶梅》可以得知。
从历史的维度去理解方泉行为,只不过是“惯性”,走了前辈的路子。方泉对佛法的理解,是粗浅的——哪里知道佛法啊,只会念《楞严经》——所有的思考,皆是出自于朴素的道德观和世界观。在巨大的机遇面前,他会彷徨、迷茫,大概是出自于对自己以往的经验与知识的不信任,但当护法到位之后(周郁),自然会是选择更广阔的前景。
当一个人完成“选择”这个行为时,意味着他有所取舍。在小说中,张忌把家庭与资本对立起来。他获得山前寺之时,便是与家人关系疏离的开始,仿佛是资本在吞噬着爱情。但张忌的好处是不批判,他从容又明净地叙述着——这很了不起。
资本自有他的逻辑,信仰是一宗生意。路内讲过一个故事,说是有人投资寺庙,把信仰当作一桩生意,不用三年就能赚得满盆满钵。这个细节,被他写进长篇小说《慈悲》 。《出家》里的寺庙,与路内提到的状况差不多,阿宏叔的寺庙由一间破庙,发展成金碧辉煌的大寺,也有资本的介入。可以想象,方泉在周郁的介入之下,会是一个新的阿宏叔——中国人的信仰,几乎都是功利主义的。
有个细节,很值得玩味,即是方泉改名为广净。广净,洁净也。在所有的宗教文化里,洁净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佛教的洁净,由外及内,发展成一种仪式和文化。小说前半部,方泉深处底层,东奔西走,但却是“洁净”,因为欲念不多。而获得山前寺之后,他改名广净,但却内里肮脏的,因为生命里充满躁动与欲念。
《出家》读后感(七):关于位置
人生来各有千秋,有富可敌国的,有才华横溢的,有劳苦贫穷的,有迂腐守旧的...
人的一生,是要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的。
对方泉来说,枕边的秀珍,膝下的三个来之不易的子女,本该是他生活的一切追求。
他能吃苦,这也许证明了他能三百六十五天如一日的早起做工。
但不同的是,他会念经。能装的像一个得道高僧。这绝对证明了他能在这个‘末法’的年代混得一口佛家饭吃。同时他又好心肠正直,能给香客们留下极光辉的印象。
一开始的出家,是机缘巧合,是为了养家而出家。是为了‘还愿‘,是怕佛祖的惩戒。
到后来,方泉发现了,或许碌碌无为的人生道路偏僻山林里,才真正存在着他的位置。
这个位置不一定是光明正大的,它是被山下的人,甚至自己的女儿瞧不起的。
这位置也不一定是干净透明的,当代的寺庙在作者的揭露下,鲜有古时的佛性,能说会道的护法、临时找来的兼职和尚、甚至寺庙里抽烟等等场景(这个场景倒是真真切切现实存在的),都是和普通人心中的佛寺相差甚远的。
但是它是一个,对方泉来说,天造地设的位置。这就够了。
这可能也是个叛逆的故事。想起路边野餐的一首诗-‘世界依靠衰老维持平凡’。
方泉为了儿女妻子,日复一日地操劳。大女儿懂事,却可以在必要时将父亲的身份抹去;二女儿三儿子只认得零食和礼物;老婆虽然贤惠,却总是把心思全部藏在心底。诚实质朴,却被城里的老板、条条框框、官僚主义、腐败的教育等等逼得时时入不敷出。如此生活,儿女全部长大后,又对儿女的儿女做同样的事。日复一日,无限轮回,多么平凡又多么万劫不复。
而方泉的出家,则像是象征了对这一轮回的破除。佛门也许不是唯一的出路,但它是方泉斩断羁绊的最好选择。留下一笔财产给家人,两手空空。不负众生,众生也不必负我。
《出家》读后感(八):绝对的出世与入世,根本不存在
《出家》这本书听着名字或许会让人联想到宗萨钦哲仁波切的《人间世剧场》、《八万四千问》和索甲仁波切的《西藏生死书》这类书,恰恰相反,小说内容抛开了佛家所谓的修行和证悟,完全从故事角度呈现一个被残酷现实逼迫得不得不靠假扮僧人赚钱养家的故事。从主人公开始假出家到真出家最后又回家的过程中,让读者与他一起经历跌宕起伏的思想变迁,对出世和入世的概念进行了重新演绎。
《出家》的腰封上写着“劳碌奔波的生活,是否有一刻让你想要逃离?”提出一个常人所面临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但读完小说,你会得到属于自己的答案,甚至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答,但无论哪一种解答与领悟,都会对你产生正向引导,这就是张忌这本小说的精彩所在。你是怎样的人,最后主人公方泉就会是你想要成为的样子。
一、小人物生活中的挣扎
作家戈舟把《出家》与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作了类比,甚至给予了更高的评价,他说“它的难度似乎要比那两部杰作更高一些。”因为《活着》有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垫底儿,相对来说,容易实现人物命运的起伏;《许三观卖血记》里有一个极端贫困的现实,戏剧性于是容易达成。而《出家》中的方泉,他的现实逼迫没有那么严峻和尖锐,在他身上,丧失了小说家容易摆弄的“传奇性”。张忌对这种“惯性”做出抵抗,用“适可而止”去书写悲伤。
第一次读余华的《活着》我不记得哭过多少次,我深深地无情的命运撞击得支离破碎,那种活下去的精神似乎也不能称之为一种勇气,因为人在多次激烈的生活冲突下,已变得麻木不堪。
张忌的《出家》有两处让我让我鼻子发酸,原文如下:
(1) 我忽然对以后的生活有些绝望,因为我几乎已经看到了自己所能做到的极致很少有人像我起得这么早,我也想多睡会儿,也想偷懒,可我总是像牛一样的用鞭子抽着自己往前走。可这样的辛苦,又怎么样呢?到头来,我不还是将日子过得跟狗一样?
(2) 方长,怎么了?
爸爸身上有味道。
我一愣,是不是香烟味儿啊?
不是。
我闻了闻自己身上,没有啊。
方长说有的,他顿了一顿,又说,是和尚烧香的问道。
我一愣,你怎么知道和尚烧香的味道?
放长说,是姐姐告诉我的。爸爸,你是不是个和尚啊?
我没说话,我觉得尴尬
晚上,躺在床上。我突然对秀珍说,秀珍,我不当和尚了。
秀真似乎一时没听见我的话,扭头看我,于是我又重复了一遍。
我不当和尚了,我想回家,再找份工作。
(1) 故事背景:方权为了维持家庭生存已经身兼三分工作,但命运总在和他开玩笑,在辛苦为大女儿筹攒学费过程中,不料与别人碰车,最终赔车又赔钱。兜里好不容易积攒下的几千块钱没了,只为一个简单的愿望辛苦付出,结果却付之东流,这种情感爆发使方泉再被多年生活摧残下产生一种深深的绝望。
(2) 故事背景:方泉由假出家最后成为真出家,但其出家的最终目的是为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他实现了。方泉有着小人物的生存智慧,也不乏大场面的机智聪敏,在经历了多次违背内心的事件后,方泉深感痛苦,同时孩子对自己做和尚这一身份的不认同,也深深地刺伤他的内心。他决定放弃做和尚,选择回家。这种放弃意味着将告别伸手即可来钱,而要重回到起点的生活。方泉体会过那种没钱的滋味儿,是那样的无奈和心酸,他依然做了这个决定。
二、出世与入世
出世与入世的概念,在小说中以超越常规思维进行全新解读。方泉这个人物让入世和出世这两种行为水乳交融,不可割裂。他在入世时体验着出世,在出世中裹挟着入世。
方泉被生活折磨得精疲力竭,在入世的状态下,内心常抽离出世。比如他会感觉自己像漂在水中一样,完全失去了重量,但他却拼命地想要抓住水中的那道光。还比如他会经常路过村口的东门庵,他觉得与寺庙有种难以表达的情感。这时候的出世,才是我们常规意义讨论下的出世。而在小说中,方泉的出世即以出家为营生赚钱养家,在这种出世状态下却为实现极为入世的想法,并且此时的出世必须借由入世的手段作为支撑,才能满足方泉出世的外衣。出世与入世这两个概念在小说中完全打破常规定义的界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出世与入世。我想或许这一点是作者写作的初衷。
《出家》读后感(九):一个男人的精神出轨史
有些人把《出家》和《活着》、《受戒》相比较,在我看来,这是部男人的精神出轨史。当方泉尚未完全将做佛事当作敛财手段时,他有些佛缘,但当他接手山前寺后便成了一个投机倒把的CEO。讽刺的是,方泉从前是个大男子主义者,认为让妻子外出赚钱是自己无能,觉得可耻,然后,后来的他为了完成宏图伟业,不惜接受周郁做其护法。
这是方泉的两次精神出轨,第一次是对信仰,第二次是对家庭。
《出家》不是活着,方泉所面临的命运比福贵慈眉善目。《出家》也不是《受戒》,汪老笔下的明海本就无太多佛心。《出家》更不是腰封上那一句“一桩养家糊口的营生,让他发现了另一个自我”的噱头。与其说他发现了自我,不如说是在钱财面前丧失了自我。方泉充其量是一步步发现自己竟能成为阿宏叔口中那个“被钱找上门”的人。他要逃离的是那个刷一天油漆挣150的自己,更是那个在《楞严咒》中找到安宁的自己,他要凭借能诵《楞严咒》的本领,换取金饭碗和高高在上的尊严。
这世间,多的是没有门路不得不自甘贫苦并能苦中作乐的人,却鲜有见过繁盛香火却能孤守青灯的和尚。
《出家》读后感(十):糟点:腐朽顽劣的重男轻女思想和和尚膨胀的“捞金”欲望
一个差不多是80后(1979年)的作家写了一本60年代风格的小说,评论界将《出家》类比于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
看书首先入眼的是题目,而《出家》这个题目,很容易让人想到厌世、遁入空门的佛教内容,这里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本书无关宗教信仰,写的是实实在在的生活。
“劳碌奔波的生活,是否有一刻让你想要逃离?”这是本书腰封上最亮眼的一句话,也是对“出家”原因的暗示。
读完整本书,感动的地方很多,但也有个人认为的两大糟点,不吐不快。
糟点一:书中主人公方泉腐朽顽劣的重男轻女思想
方泉,初中文化,老婆秀珍,文化程度不详可能更低。从农村进城务工,方泉一人身兼三份工,送牛奶、送报纸、踩人力三轮车载客,秀珍无业在家养娃(曾做过短暂的超市营业员)。这样的家庭经济能力,却养了三个孩子。不是说家庭条件不好就不能养三个孩子,如果出发点是喜欢孩子,那没问题,但方泉的动机仅仅只想要一个儿子而已。
“说实话,迎来第二个女儿,让我有些失望。原本笃定这会是个男孩儿。秀珍怀孕时和此前是多么的不同。可结果,却依旧是个女儿,就像老天跟我开了个玩笑一般。我很后悔,早知道,我应该带着秀珍去照一下B超。”
为了防止第三个孩子又是女儿,方泉花了600块钱在另一个城市做私人B超检查。
来看看书中其他部分对生儿子的描述:
1.我是喜欢儿子的,没办法。女儿嘛,养大了终归要嫁人。嫁了人,就是别人家的了。儿子呢,是当种的,一辈子都是自己的姓。我是独子,自然希望生个儿子,将姓氏传下去的。
2.这可是我的儿子,是天底下最宝贝的东西。
3.我儿子可是什么都换不来的宝贝疙瘩。
4.看着她的神情,我觉得自己有些羞愧,为了那个还没出生的儿子,我竟然可以忍心将两个幼小的孩子扔在家里。
5.当我确定秀珍是真心想为我再生个儿子后,我兴奋不已。的确,这是我心里最渴望的事,可我不敢说,我怕会伤害秀珍。
6.算算,拢共也就不到一年的时间,如果满整年,存下五万肯定没什么问题。一年五万,十年五十万,二十年就是一百万。方长现在刚一岁,等方长到了二十岁的时候,我就可以交给他一百万了。
确实书中多处不乏方泉爱女护女的情节,但对儿子的渴求能看出他打从心底对儿子有一种与女儿不同的特殊感情,这是对女儿的偏见和歧视。
殊不知,这种传统的偏见不知在无形中酿成了多少家庭的悲剧,误了多少子女。
在某村,有一户典型农家,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为了要儿子,丈夫逼着妻子一胎又一胎地生,直到第四胎生了儿子,才作罢。在丈夫眼中儿子就是天底下最宝贝的东西。平时家中,儿子吃稠女儿们喝稀,儿子吃肉女儿们靠边站。
这不算重要,顶重要的还是读书,毫无疑问读书的机会留给了儿子。从小娇纵的儿子却并没有好好珍惜这宝贵的机会,初中学业未完成就开始四处浪荡。
而女儿们,却个个大字不识,这让她们在今后的人生过得异常艰难,也错失了很多改变命运的机会。
他们家小女儿做事胆大心细,十分聪明,有时候胆量和魄力还能震慑住一群男子。尽管表面上很强悍,但内心深处却总怀有一种深深的自卑感。因为她没机会念书、不识字,这是永远也填不平的鸿沟。
年轻时,她一个人凭着自己满肚子的主意和聪明劲儿领着一群人奔波讨生计,可时代变化太快,新生事物催生着下一批新生事物,旧的东西不停地被淘汰。跟在她后面的人很快抓住新机遇,有了新的发展。而她独自落寞地站在原地,再也没了从前充满热血的干劲儿。
纵然她有一千个想法、计划,但没有一个她真正敢做,不识字没文化永远是她的拦路鬼,她能做的事只有在小饭馆洗洗碗,建筑工地上打杂,服装厂当女工。随着年龄的增大,这些体力活儿让她逐渐有些力不从心。
丈夫不在家时,她不敢一个人坐车出远门。不会去银行取钱,不会发短信不会念短信,也不会寄快递,正如她所说,自己就像困于笼中的困兽。
而前面那个从小娇纵到大的儿子,性格极端自私,脾气古怪暴躁,敢于与父母大打出手,终于父母被他的各种作,各种花式折磨气得驾鹤西去。
这是农村重男轻女的一个典型例子,也绝不是唯一的例子。
糟点二:与其说当和尚被职业化,不如说是“捞钱”
回顾方泉几次入寺庙做和尚的经过,可以发现前面4次是为生活所迫,想要改变家庭经济状况,把“假和尚”作为一项谋生的饭碗。逐渐方泉的野心变大,做和尚的原因不再纯粹,竟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欲望”成分。
第一次做和尚,因为二囡即将出世,生活拮据,赚些钱贴补家用。
第二次做和尚,刚生下的二囡嗷嗷待哺,送牛奶的工作又出了问题,还是为了挣钱。
第三次做和尚,为大囡交了入学赞助费,又被人讹了钱,还交了三轮车罚款和停车费,再次经济困难,难以养家糊口。
第四次做和尚,秀珍生病做手术杂七杂八花掉了5万的积蓄,就算大人不吃不喝三个孩子总不能挨饿,所以还是因为钱。
前四次为养家糊口,不得不做和尚,完全可以理解,毕竟不是违法乱纪,伤害他人的事情,更何况彼时的目的仅仅是尽到一个身为丈夫、父亲的责任。
直到接受了一座寺庙,成为住持,认识一个叫周郁的女人,方泉萌生了要扩大寺庙的野心,起了真正出家的念头。
经周郁介绍来庙的陈阿姨,她儿子的模具厂生意不好,便想问菩萨儿子换个什么行业好?若不换行业,模具生意什么时候能好起来?
这样的问题菩萨有答案吗?我不知道,方泉更不知道,为了让菩萨保佑,陈阿姨向寺庙捐了两千元的香火钱,还答应生意好起来之后会再来做一场佛事,所谓做佛事,重点还是在于掏钱。
后来周郁又给方泉介绍了一个象山船老大,还吹嘘方泉这里的佛事没有不灵验的。船老大因为每次出海总打不上鱼,一下出手十万来寺庙做佛事。也不知是不是菩萨保佑,船老大真的发达了,还特意送来了五万的谢礼。
说实话,这真像一场越做越大的捞钱骗局。咱不说方泉仅主持一场佛事是否就值得几万大洋,难道做佛事真的能让人的愿望(欲望)实现吗?
书中一位长了师傅说,一个好的寺庙,必然有好的护法。护法就相当于公司的业务员,四处拉人来寺庙做佛事,而这些做佛事的人个个都希望菩萨保佑,说白了就是利用斋主相信菩萨的心理来捞金,不然护法周郁哪来一辆红色宝马呢!
方泉说自己对出家动心,我十分怀疑。我不相信他是对吃斋念佛,身心俱静的空门日子有兴趣。不然为何在周郁找他之后,原本坚持早起、早睡、念经、打坐的日子再也坚持不下去了呢?
在周郁带他到上海参加斋主宴会时,他享受着众人带着诉求的崇拜目光,耳边充满赞美,不停有人叫他活菩萨。他觉得这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刻。
方泉真的把自己想象成了活菩萨。事实上,他除了会背《楞严咒》,会敲木鱼,佛家真正的智慧又知道多少?又真正用佛家智慧为人解答过什么?被盲目地崇拜,自己还特享受,这不是很可笑吗?
方泉出家,难道也打算请护法拉香客,然后开始捞金,那这又算哪门子出家呢!
“我现在过得一团糟,我有老婆,我还有两个孩子,我每天都想着让他们过得好一些。每天四点钟我就起来了,天还黑着,别人都在睡觉的时候,我就起来了。我每天都很辛苦地干活儿,我从来没让自己偷过一天懒,真的,我真的觉得自己尽力了。可是我还是赚不到钱,我还是养不起它们。我说不清那种感觉,就像有一个大勺子,每次我有了一点钱,那个大勺子就会伸过手来,像舀水一样,将我的一切全部舀走。”
除了上面两点很糟糕外,书中呈现出的对卑微生活的无力感十分打动人心。
方泉就像余华笔下的许三观,每每遇到困难总能靠卖血渡过难关,而每次方泉遇到困难,总能通过当和尚迎刃而解。
《出家》中展示的底层生活,现实不乏诙谐,悲伤适可而止,还总流露出脉脉温情,也没有把人逼到透不过气来的尖锐。
尽管有吃拿卡要的马站长、总让员工干私活的亲戚老板、敲竹杠的坏人等反面人物,但也有坚决不收红包的医生和耿直讲义气的朋友阿良。
总之,这不是一个让人厌世的故事。人世兜转,来往匆匆,无常才是万物有序,我们甚至还能从方泉的夹缝求生中看到自己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