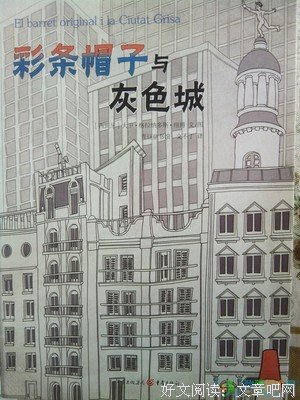《错把妻子当帽子》是一本由[美] 奥利弗·萨克斯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6.00元,页数:26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有次在我外婆家,拿她的按摩枕头放在脑袋后面,一边震动按摩一边看快乐大本营。
奇怪的是,电视画面像水波一样晃动,而电视机以及周围景物却没有任何变化。开始以为是数字信号出了问题,可画面仍旧在晃,晃的很柔和,速度还不慢。
我一惊,把按摩枕头拿掉,眼前恢复正常,有点不可思议,继续把枕头放脑后,画面又晃,周围平静的让我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所以,所有你以为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种病,统统有可能发生。你瞧着你眼前发生的一切,咬住手指觉得不,都没有用。是我们太狭隘。
比如这本书《错把妻子当帽子》。
皮博士去拿帽子,抓的却是他妻子的脑袋
吉米永远十九岁,下一秒就忘记
克里斯蒂娜灵肉分离
艾斯太太的左边不见了,她化妆只花半边脸,因为只看得到半边
等等……
精神病永远不可以被统一归类治疗,他们在自己的世界跋山涉水。我说不出书里面生动的案例的万分之一。只有看几遍。
《错把妻子当帽子》读后感(二):人类到底起源自哪里?
起初拿起这本书,很容易想起中文的《天才在左,疯子在右》。不过读完后发觉差别还是很大的,本书的注意力主要放在人类的大脑上,研究各种脑部“病变”引起的行为失常,而且对于这些案例作者都进行了相当有深度的思考和极具人文关怀的发问。而《天》则更像是一系列的猎奇,案例也主要是一些有心理“疾病”的人,多为受到刺激后的心理变异,在文笔和思考上都欠缺力度。
这本书的翻译真的太棒了,一度让我觉得在原著就是中文。本书的作者本来就以文笔著称,被称为“医学桂冠诗人”;而译者则将这种文学性很好地转达了出来,书中有些部分的表达相当曲折和微妙,翻译出来的句子让人赞叹。
人类大脑的潜能到底有多大?
读完此书后对此十分好奇。作者介绍的这些案例,有些是大脑中的有些潜能被释放,有些是某些功能被增强,比如嗅觉极度灵敏,想象力极度丰富,精确的记忆,对数字的直觉,等等。
这些潜藏的可能性是否来自于久远的过去?也就是说,人类曾经能做到很多现代人不可想象的事情,只是都被遗忘了,作为潜能藏在大脑的深处?
那远古的人类到底经历过什么?人类到底起源自哪里?因为在大脑不断让我们目瞪口呆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质疑,生命真的是从单细胞生物开始演变过来的吗?造物主真的不存在吗?
什么是真实?
书中还有些案例是主人翁看到、听到了“不存在”的东西。也即是说,只要是大脑相信的东西,就是我们自以为“看到”、“听到”的东西。那真实和幻觉的界限在哪里?有
没有可能,我们现在深信不疑的东西,只不过是人类共同的幻觉而已?
归根结底,我们还是会回到相同的质疑,那就是,人类到底来自何处?生命的起源在哪里?
很值得一读。
在线阅读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atalog.php?book=135210
作者奥利弗·萨克斯不但以亲身的医患经历,写作了一系列的“医疗轶事”,如:《觉醒》、《单腿站立》、《错把妻子当帽子》,还将病患案例文学化,将虚构与真实融为一体,饱含同情,着力描写患者的各种身心体验,给读者打开一道通往奇异世界之门。
萨克斯将神经病学的理论和案例深入浅出地写进书里,既轻盈又沉厚。本来,神经病患,在普通人看来是一类与自己很少发生关联的遥远而陌生的群体。萨克斯以客观平等的态度看待他们,与他们交流,在书中展现了他们的心灵世界。
今天的儿童治疗工作坊第一天,Barbara老师讲了一句令我非常震动的话,她说:父母都是不完美的,为人父母的过程充满挣扎和困顿。但有时候我们的这种不完美,反而帮助我们的孩子变得更强壮。
这两年醉心于对精神健康、情绪和感受领域的学习,很多朋友都会问“异常的东西接触多了,自己会不会也变得异常?”“总是被人倾倒情绪垃圾,压力很大吧?”我觉得情绪受到感染因而需要督导、自我体验这固然是事实的一部分,但更为重要的部分是这些接触让生命变得更加丰盈。
接触异常最大的收获是,深深地体会到生命是如此地脆弱,同时又是如此地强韧。脆弱到一个小小的损伤、变异就能让人彻底失去很多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功能,在这个世界变得困难重重,饱受打击。但是,人类能够忍受巨大的创伤、挫折、病残,一旦接受无可改变的现实,就能够获得新生,以自己的方式去适应,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就像被切成两段的蚯蚓重新生长一样。脆弱让人谦卑,尊重每一个人存在的方式,尊重每个人的命运。而强韧让人永不放弃信任和希望,不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
“神经病”在中文语境里是一句侮辱人的话,可是萨克斯收录的这些“神经病人”的故事却让人非常感动。特别喜欢最后一个部分《心智简单者的世界》,就像作者说的,他们让我感觉非常温暖。生活在精神孤岛中的自闭症患者其实也有交流和表达的愿望,只是因为他们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太独特,难以被理解。同时因为这种独特,使得这个世界对他们来说充满危险。当有一个愿意理解他们的人出现,他们也会非常努力地去表达。
当一个人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能够维护和发展自己的独特性,同时又能被人接受,对这个世界有所贡献,实现自己的价值,获得爱、关心和尊重,那么不论他是怎样的残疾、弱智,他都是一个美好的人、幸福的人、自我实现的人。而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要以牺牲自我来获得在这个社会上的成功和被他人接受,那么这个人以社会的标准来衡量再优秀再成功,也是空虚的,悲伤的。如果一个人不得不将自己和他人隔开以维护脆弱的自我,那也同样可悲,这无疑是很多病人的困境。
从病人推演到普通人,每个人本来都是独特的。但因为社会的要求,我们总是不得不牺牲或隐藏一部分自我,这是一件普遍而又非常痛苦的事。这种牺牲是否真的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必要呢?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一个更为人性更为人道的社会,能够去倾听和尊重每个人的独特性,那么个人自然就会打开自己,在和他人的互动中发展自己。
但为什么这个社会不能变得更人道呢?因为构成这个社会的每个人都有恐惧,我们担心世界会失序,我们不愿面对和自己非常不同的他人,这种不同不仅让交流变得困难,还会唤起很多不愉快的感受。这种恐惧,这种不愉快是自己内心感受的向外投射。如果我们能够对自己更宽容,更尊重,就有机会看到自己的潜力,发展真实的自己。而这种经验反过来又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尊重他人。
所以,让我们首先更人道更尊重地对待自己吧。我是独特的,让我努力活出真实独特的自己,找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而不是委曲求全或者愤世嫉俗。
《错把妻子当帽子》读后感(五):错把璞玉当顽石
这大半年,断断续续的,终于将这本书读完了。当初看到时候是把它当做像《天才在做,疯子在右》的一类书来读的,心里抱着全是猎奇的心态。可是开读后,却发现这是本有关精神病研究的科学论著。
既然是科学论著,趣味性自然就少了那么一点,但是却更有严谨性以及真实性。感觉作者确实是一份非常非常有心的精神病理专家,在拥有强大专业知识背景的情况下,还保留着一种作为自然人的感性。对于这些被大众所摈弃的精神病患者,作者就像剥玉米一样总能除去他们外在不正常的因素,最终看到他们内心的‘果实’。
虽然对于这个领域的知识我是十分匮乏的,但是我能感受到作者的这份心,这种相信科学但又同时尊重自然的心。真心希望我们国家在医学领域也能出现这样的大师,我期待着。
《错把妻子当帽子》读后感(六):Let it be
和《天才在左,疯子在右》不同,作者OLIVER SACKS本身是个神经学科的医生,这本书里的这些人,他们并不是单纯因为心理原因从所谓的“正常人”变成了天才或者疯子,而是因为实实在在的神经上的缺陷、损坏或者破裂而导致的。
这更令人惋惜,因为没有谁可以预测生理疾病的来临,脑子那么复杂,想要修复更是困难重重,这就更让这件事情平添了一些无可奈何的悲伤。
我是一个太正常普通的人,身体健康,也几乎没有住院的经历,所以很难理解生理上的病痛给一个人带来的伤害和折磨,对生命能量的消耗有多严重,也很难理解因此而引发的对“正常地活着”的毁灭性的变化。
但幸好也不全是坏消息。
在书中的这些病例身上,比如错把妻子认成帽子的音乐教授,他自己并不觉得有什么异常,那么很好啊。
我们不能替任何一个他人决定,他的内心感受,愉快不愉快、痛苦不痛苦、要不要改变、能不能维持原状,等等。最主要的,还是自我这个主体,和自我意识、身体控制,是都能被自己掌控的。不管这种掌控是借助了他力还是自己可以完成,但有掌控,能决定,就可以了啊。这也是尊重任何一个生命的体现之一。
比如书中的双胞胎数字神童,最终被外力的判断而被迫分离,是最令人难以忍受的。他们会继续因为脑部的损伤和缺陷而痛苦,同时又被剥夺了仅存的幸福沟通与依靠。对他们而言,这可能就是灭顶之灾。
所以,对我们自身,生命价值应该尽量做到be myself;我们对待这些有缺陷的人,则是可以一定程度上let it be.
《错把妻子当帽子》读后感(七):我希望我不是我这个神经病
刚开始做咨询和演讲的时候,前辈告诉我,这个行业不如我想象的好玩。我说这是我的兼职,纯粹兴趣爱好,可以保持那种世外的淡定。
前辈还说,你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我说阅人无数是我的目标之一。
随着对这个行业的深入,总会有一种莫名的责任与压力越来越重,曾经自己略带悲悯不成熟的理想主义,只会在现实里感受更多的愤怒和抑郁。
最近半年也看了不少心理学专著,发现一个问题,那些科学的心理学理论,都是有科学的案例也就是有行为论证的(岂不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
还有一些我觉得不科学的理论,例如早教,都有很多创造“理念”的科学性欠缺的瞎扯。
原以为随着科学发展,科学无所不能。但是面临理念瞎扯,也理解了很多科学家会迷失其中。
牵扯理念是无法直接被改变的,需要引导和感触。也明白了,教育果然不是容易的事情。
还好通过一年的哲学学习,已经可以坚定的调控自己的理念和心理。但是和各种咨询者接触的过程中,面临他们一些深层次的“理念”性的东西,真是哭笑不得。教育资源的不平衡,也造成了一些地区理念的差异巨大。
当然,有的人会说“子非鱼焉知鱼之乐”,正如中医一直在抨击方舟子一样,很多知识分子也会用未知世界偷换概念的理论来支持伪科学。封建是不是愚昧?皇权是不是政权?是否这些思想的广泛存在,社会文明进步缓慢,甚至还有落后的趋势。
百家争鸣理论性的交流也是好事。想想“科学”的定义我们都还没有搞清楚。当然如果有人争论,他也会用哲学的观点或者告诉你他的不是伪科学的行为。就如方舟子说这药没科学根据,那边偏偏就有人说治好了他的病。
好吧,不研究什么科学的理论了,了解点还在探索阶段的神经学。大不了,要么是我神经病,要么是你神经病。
《错把妻子当帽子》读后感(八):在凌晨四点钟,评价一本关于神经失序者的书,是因为我想成为第二十五位。
三年来,身边的人都觉得我疯了。
因为我发疯地读心理学的书。
是么?我不觉得。
疯子从来不觉得自己是疯子。
被大家再次评头论足,
真是我的小小悲哀。
可是这一个小本子。着实读到我肝儿颤。
爱这一个字,已经成为红尘大俗。俗到你不忍提及。
我宁愿承认,这个小本子,只需要一两个个案,
就足以更改我的某些世界观。
豆瓣上,我向来言语耸动,夸张变形。
其实我内心在哀求各位,各位,其实我表达的是我的真实感觉。
你信么?你一定不信。
比如那位优雅浪漫,自尊且顽固的,可怜的皮博士,
他眼中的世界,失去了辨认的线索,或者说,
他无法把所有线索连接起来,
形成“印象”。他可以描述你的鼻子,眼睛,却无法辨认老妻的面孔。
他依然是大学音乐教授,他热爱音乐,他几乎所有时间都在歌唱,
他却错把妻子的脑袋当成帽子,试图优雅地放在自己的脑袋。
再比如,对自己大腿失去认知的可怜人,
他把自己的大腿,当成夜半醒来被别人恶作剧放在床上的大腿扔下床,
结果是,他把自己扔下了床,他痛苦且恐惧地哀号……
再比如,那个永远19岁的水手,永远以为自己活在1945年,
他对所有数学物理机械的精通,他优雅且宁静的思考状态,
都几乎让我沉迷且自卑。他的博学与礼貌,
活生生就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2战前的美国青年,
他却活在80年代里 ,念着他的1945,
和“比自己苍老到可怕的哥哥”一起创造温馨的重逢场面,
我想起,刚刚看到的抗美援朝60年纪录片里,
类似的障碍者(他们是患者?不!)我也看到过。
这些看似神奇,细想就在你我身边,从未缺席的孤独的人们,
让我想为他们唱一首LOOK AT ON THE LONELY PEOPLE,
然后深情拥抱他们。彷佛我完全可以共情到他们。
为什么呢?
因为作者奥利佛先生在他们生命里扮演的那个角色,
令人感到心碎的温暖。
他为戳穿了水手的幻想而自责;
他端详所谓弱智的少女舞蹈,且在春光里吟诗,
他相信少女告诉他的“真心疯话”——的确是被忽视的真理!
反思我们所谓的正常社会在用自以为是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我给的标签)方法来测试调教他们。
他独家读到的人性之真善美,我们从来置若罔闻,孰视无睹。
我几乎不忍把它读完。
他的同行把自己的这项事业称为“浪漫的科学”!
这几乎拯救了我对科学的伟大偏见。
因为科学可以如此浪漫,让我一七尺男儿向往如是。
我把我广告领域里节余的所有用以赞美的形容词,都献给亲爱的奥利佛先生。
你值得我们一读再读。
《错把妻子当帽子》读后感(九):聪明者会生存,残障者懂生命,而我们学一心平等
“宇宙和个人意识相交的地方,是人的心灵。整个世界的复杂与宏大,都只能在我们的心智之中被反应和理解。从《火星上的人类学家》到《错把妻子当帽子》,再到《脑袋里装了2000出歌剧的人》,最具有慈悲心和同理心的医生奥利弗·萨克斯,用一种别致的方式告诉我们,什么叫做‘重要的东西,只有用心,才能看得到’”
—— 题记
小王子说,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到的,得用心看。
如果是这样,我们还要眼睛干嘛?
庄子同学说,从前有个人叫混沌,被凿开了七窍之后,混沌就流血而死了。
如果是这样,我们还要七窍开,耳聪目明干嘛?
卡夫卡说,他变成了一个甲虫,用甲虫的方式感知世界,却还有人的思考。
如果是这样,那只能用“甲虫大脑”时,他还能算做一个人吗?
存在本身是种悖论,人是一种和外界交换信息、能量的生命体。
脑科学告诉我们,发达的大脑有90%的贡献来自于视觉的进化。
借由视觉,我们的大脑开始能够感知到一个三维的世界,动态、立体的世界。
我们从单细胞生物的点国、平国终于进化到了3D世界。
借由敏锐感官而进化出的发达大脑,终于让我们这个物种站上了食物链的顶端。
统治地球还不够,这个物种里叫做Elon Musk的人还想让我们成为多星球生物。
只是,当人的数量越来越多的时候,似乎,有那么一些人就显得“不太正常”了。
有的人开始没办法辨认物体,他把妻子当做帽子,拿过来,试图扣在头上
有些人开始没办法看到自己的左脸,很奇怪的,她无论如何只能在半边脸上化妆,自己的右脸就像完全消失了一样,她无法看到、或感知到右脸仍然存在
有的人开始只有7秒记忆,像是《海底总动员》里的多莉,刚刚知道的事情又马上忘记,倒是有些像开悟的智者,心无挂碍地活在当下
有的人开始莫名其妙地过度性兴奋,人老之后又忽然被丘比特之箭猛烈射中,根本停不下来的荷尔蒙与兴奋
还有人左右脑功能完全失调,在逻辑、数字和框架场景下她是个完全的白痴,可是一旦到了戏剧、情感和即兴场景,她就变成一个数一数二的天才
当我们面对千奇百怪的大脑和神经疾病,萨克斯几乎不聊病理和疗法
却只是把一个个活生生的故事讲给你听,不是医生的医案,不为了治疗的成效
只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以“人之为人”的方式,去观察,去理解,去呈现
在所有“疾病和不正常”的表象下,他发现了一片“隐秘而广阔”的超越之美
当你的眼睛没办法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必须用“心”去看了呢?
几千年来,东方的智者都在追寻让人“关掉感官”,从而打开“用心看”的存在模式
无论是《心经》,“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身香味触法,照见五蕴皆空”
还是庄子说的“坐忘”“斋心”,把看到的听到的,道德的伦理的规范,全都抛诸脑后,斋心斋到最后,我把我自己给丢了。
或是老子说,“閉其兌,塞其門 … 是谓玄同”。将打开的七窍重新收摄返回,把自己的那点耳聪目明、小小心机全都关掉,人,就能重新回到“混沌”,回到“道”。
智者告诉我们,别做一个在“生存模式”下费尽心机的小人,别被外在世界的声色犬马太多诱惑拖着走,要做一个像小王子一样的人,纯粹、良善、才能开启心,用心去看到真正重要的东西,在那时候,才能打开你的“生命模式”
“生命模式” 是什么? 是你的感官可能有问题,你的动作可能有问题,你的大脑和一切都极不正常时,你开始突然跳脱出这些框架和设定,并深刻地意识到,作为生命本身的你,仍然是完整无缺,那个生命本体,了了分明,如如不动。
萨克斯医生的病人,都像是被上帝咬过一口的苹果,而不得不打开自己的生命模式
狂躁无常的病人,站在教堂的祷告声中,完全地安静下来,融进一片巨大的神圣中
被认为是智障的女孩,在表演的舞台中,进入了一个完满无缺的生命体验
智力低下的男孩,却能完整理解复杂的巴赫音乐,他似乎完全活在巴赫之中
他们或许无法理解一个“正常”的,作为表象的物质的世界,无法理解我们眼中那么正常的物体、形状、作用、符号,这个被我们认为是“真实而唯一”的世界,在他们的心智和头脑中,恰恰是难以理解,甚至是不存在的
然而他们的心智中,却有一个我们更加难以触及的世界。那是一个融会贯通、心领神会、诗一般完整的世界,他们能看到、想到、并且活出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世界。在他们自己的那个心智世界中,他们不再是残缺不全的病人,相反,他们想破茧蝴蝶一样振臂高飞,常有巨大的喜悦和圆满
萨克斯说,他瞥见了一种巨大的生命力,作为生命本身的圆满和可能性。他瞥见了一种令人震撼的、超越语言的智慧,那些“白痴大师们”所展现出的创造性聪明——他们能听到一般人听不到的旋律和乐曲,看到一般人看不见的数字游戏的密码,创作出一般人无法想象的奇异画作。
而作为人类整体所需要的,恰恰是认识、接纳并学会欣赏培育,这些另类的美与智慧。
有一天,庄子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振翅而飞,它在蝴蝶的身体里、心智里,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盈快意。醒来之后,才发现自己仍然被困在这沉重的肉身里, 他一半黯然,却又瞬间喜悦:也许,沉重肉身为人,或轻盈飘飞为蝴蝶,所拥有的本质,仍然是一模一样的生命力吧。
于是,有人说,当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他还把窗也关上了。别着急,上帝是打算开空调了。你是急着把门窗凿开,还是该坐下来,享受这清凉呢?
《错把妻子当帽子》读后感(十):大概人人都有神经缺陷吧~
好像是高中生物课听说过胼胝体受损的人会无法将左右眼看到的事物联系起来。
后来生理心理学课说到过目测距离感缺失这种情况。
还有很多电影描述过记忆储存能力缺失,以及神经对肌肉的控制能力消失的事。
虽然个案让人心情沉重,但看书的时候还是难免趣味盎然,因为这些缺失,才让人发现大脑无穷的神秘能力。
其实有些案例虽然难以想象,但我们似乎也体会过,只是没当一回事儿罢了。比如长时间写同一个字,就会突然不认识这个字。这不就跟错把妻子当帽子的、只能看到细节的失认症类似了吗?
而我总是健忘,总是记不住陌生人的脸,常常叫不出同学同事的名字,五音不全而浑然不知,其实也是某种大脑缺陷吧^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