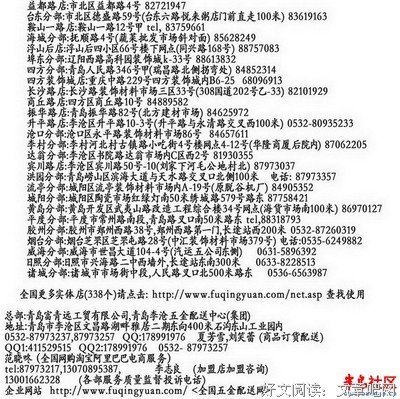
《八百万零一种死法》是一本由唐诺著作,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元,页数:42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八百万零一种死法》读后感(一):全能的唐诺
唐诺抽丝剥茧般把劳伦斯·布若克的小说分崩离析,各种隐喻跃然纸上,主人公斯卡德像在显微镜下般被我们观察。
惊觉我看的所有那些侦探推理小说的作者都已作古,布若克竟然还健在,而我自以为熟知推理小说各种形成各种流派,可是却不知道布若克,也不知道他是“冷硬派”的开山鼻祖,好吧,我又自大了。
当我看到220页时,我发现原来唐诺不单单在讲述布洛克的小说世界,从另一面实实在在地又讲述一个小说的发展史,故事的构造学,人类世界的形成及发展史。唐诺博闻强记的本领在此一览无余。
布洛克笔下的人物,私家侦探也好,雅贼也好,他们属于社会的边缘人物,他们有着自己行为准则,他们有着自己的一套善恶理念,而他们也往往会用自己的方式去达到自己伸张的正义,这种正义可能是法律所不耻的。
相较半路出家的钱德勒,他们也许互相拜读过对方的小说,也许相互鄙视过,更可能相互仰慕过,不管是哪种可能,他们笔下的人物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为冷硬派的主角一定要是个受过创伤的的私家侦探,他们在伸张正义的时候往往有着一副悲天悯人的侠义豪情。对于读者来说,故事的发展必须按照一定的模式发展,而正义也必须以某种方式得到伸张,所以,很多冷硬派侦探小说背后会透出一种悲哀的无奈。
《八百万零一种死法》读后感(二):侦探小说的“入时”与“过时”
文/李小丢
在谈论这本堪称劳伦斯•布洛克的侦探小说引文大全的《八百万零一种死法》之前,我们首先要问一个有些奇怪的问题:我们现在还需要读侦探小说吗?这个问题显然不是杞人忧天,早前有文学评论家感慨,近二十年西方主流文学创作力的萎缩,主要是在于这个社会再没有秘密了。不太挑剔的看,这样的感慨多少是对的。
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人类如今每时每刻都在增加着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和对神秘现象的祛魅过程。在并不久远的过去,绝大部分知识的获取途径和代价都是高昂的,教育和书本需要付出金钱和时间,实践更非易事,需要金钱、时间、勇气,或许还需要一些上帝赐予的好运气。坐在电脑前往搜索引擎里键入几个关键词,在几秒钟内就能无偿获得海量信息?在过去的人看来这不啻于某种神话或魔法。
知识不再神秘,更多的人可以用更理性的态度来看待这个世界,从社会发展的总体角度上来说是好事,但是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却是个噩耗。二十世纪后五十年的文学成就,大多集中在南美洲、东欧甚至是非洲这些人类社会的边缘区域,因为只有这些地方还容得下瑰丽的想象,作家们还可以在文中搭建自己的梦幻国度。唐诺认为,曾经风靡一时的罗宾汉和亚森•罗平的故事之所以现在已沦为童书、漫画和卡通,这绝非偶然,而是因为它们的文学想象在成人世界中过时了。
“类型小说的世界,可以假,可以梦幻,可以大言不惭吹牛,但读者心中仍有一把尺,现实的尺。这是堆叠了他们对生活世界的所有或完整或破碎的知识、信息、印象乃至于气息所铸成,并内化成为一种阅读时的自然感受。”无懈可击的价值观、完美无瑕的人格品质、战无不胜的人生经历……这些传统侦探小说中正面主人公的必备条件如今只能拿来骗骗小孩子了,就算阅读文学作品是另一种形式的做梦,但是弗洛伊德也说了,哪有什么梦境不残留现实成分呢?
这个世界已经容不下完美的英雄了,就算是有些微瑕疵的,例如吸食可卡因,曾败于艾琳•艾德勒手下的那个原著中的福尔摩斯也过于完美了。人们需要的是贴近真实的虚构,需要的是有血有肉和我们普通人一样的“反英雄”人物。他之所以成为英雄,不是因为他天赋异禀、能力超凡,而是他决定去承担起那些看起来超出他能力范围的事。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精神,这才是生活的真相。
“向现实靠拢,为的是保有童话。”所以老牌超级英雄、完美侦探们也在人们的这种期望之下纷纷转型,超人、蝙蝠侠、新福尔摩斯都带着一种暗黑而凛冽的气质重新登场。而劳伦斯•布洛克近五十年的创作生涯中,都在致力于创作这种更加贴合时代精神的侦探小说。这,也是唐诺对他推崇备至的最重要的原因。
无牌私家侦探、酒鬼马修•史卡德是优雅的绅士侦探福尔摩斯的反面,中年二手书店老板、谨小慎微的雅贼伯尼•罗登巴尔是风度翩翩、来去自如的怪盗罗平的反面。对劳伦斯•布洛克来说,侦探、偷盗、凶杀仅仅是他表达现实的一种手段。跟其他的侦探小说家不同,他并不热衷于诡计,他最早只是想成为一个作家,再看看他想写的东西用什么样的方式能最好的表达出来。结果,他写出了至今尚未过时的侦探小说。
刊于《周末画报》,转载请注明。
====================================================
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做了个读书类的微信公众平台:
读书有疑(微信号doubtsinreading)
每日推送一些有看头的书评(当然不只是我写的)、作品作家、精彩短篇等。编选的宗旨就是有趣、有品、有疑。欢迎喜爱读书的朋友们推荐、订阅。
快!关注起来!关注一下不会怀孕的啦!(●'ω'●)丿♡
《八百万零一种死法》读后感(三):侦探小说与现实世界的诗意联通
长久以来,本人一直有一个读书的癖好就是一开始不读前言,因为有的时候书目的前言总是写的非常详尽,有导读者灌输给你的一套概念后,在看到的著作就有了先入为主的概念,而非本真的体会。有的时候对书失望了也就不会在返回去了看前言,只有当大呼过瘾或者一篇迷惘之时,才会回顾前言对比阅读发现自己的缺憾,故而也因此造成了一些缺憾。
曾几何时,就听说唐诺的著作算是才子书的典范,后来在学校图书馆偶然翻到台版的《唐诺推理小说导读选》两册,才发现原来那么多读过的侦探小说,都是唐诺作的导读,而当这一篇篇散落各地的导读整理成册之后,才发现唐诺的语言真是那种读起来叫人停不下来的美感,尤其是这两本书还是竖排繁体这种最难阅读的排版格式,就更能发现才子唐笔法之高超精湛。
今年下半年世纪文景终于在大陆引进了这两本著作,上册改名为《八百万零一种死法》下册改名为《那时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前者主要是对硬汉派推理小说的解说,后者是对古典主义推理小说的点评。在读唐诺著作时,想起了这学期在批改学生书评作业时的思考。诚然,经典的推理小说就那么几部,但至少在唐诺笔下精彩的书评却不是仅仅几篇。宽广的视野对细节的细致把握,是成就优秀书评的根本。亦如我们在批改学生作业时多次强调,书评主要是给未读及此书的读者做的导读,那么文章的笔触时时都应为读者着想,但也不能脱离著作本身。唐诺本人是作家,他懂得变换不同的角度去叙述个人的作品。而本书最精湛处在于这些新颖的角度是在评论中给人以焕然一新的体验。
一般的书评人在评讲作者生平与著作写作的关系时,会引经据典的要么讲述某种类型小说的理论意义,学术意义上的掉书袋或者所谓的深度的文化背景诠释等等,看上去很是高深,却离读者所处的现实社会太远。而唐诺的评论作品最为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当他简述了一段书中的精彩段落后,就写道一些生活的道理,而且在布局谋篇中他善于写作一些看似没有关系的事情,最终将它们串成一体,这种写作手法也宛如一部短篇推理小说的创制过程。
比如在评论劳伦斯·布洛克的推理小说《刀锋之先》的序文《献祭的花》一文中,先探讨了本书女主角薇拉,作为一个前“进步共产党”(虚构的团体)的一员,在革命之后隐逸于纽约51街当房东的故事。第一节作者简述了六十年代世界性解放运动中关于花与性的隐喻关系,之后一节引述孔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大致能够描绘那一代人的心境,真是太妙!第三节,又引用中国成语的“屠龙之技”讲述时代成就两面性的挫败感,最后上升到理论层面探讨恋爱、革命与宗教的三位一体。这三者与哲学家、政治家眼中的三位一体区别太远,却是日程生活中最为让每一个青年身体发肤间最容易感知到的三位一体。之后本文的最终一节,作者在本书第56页中写的最让人动容:
最终的献祭
在这个三位—体的世界中,死亡便有了极特别的意义,它是选民对至高者应许的一个报称系统,一个坚信不疑的戳记。
什么样的人最爱谈死呢?
答案是:恋爱中人、宗教中人和革命中人。恋爱时,它叫生死相许;宗教时,它叫殉道燔祭;革命时,它叫慷慨献身。
不这样你如何能回报至高者对你千万中挑一的青睐呢?如果你不把你一切所有、包括最终的生命给献祭出来,你如何侈言你的纯净呢?
如此,我们还需要追问,那些燔祭的花儿,都哪里去了吗?
由此可以看出在唐诺的笔下,他并不把侦探小说局限于推理、诡秘的精心购置,而是向读者更加剖析作者在写作之中的多方位的关怀,在我们阅读侦探小说的同时不应该仅仅把它们当做类型小说去阅读,而是应该把他们作为这个时代文学的一部分,经典的著作是值得时代洪波洗刷的。
《八百万零一种死法》读后感(四):违天择:不自觉的人
文 / 违天择
究竟存不存在各种文学体裁?博尔赫斯曾在他的《侦探小说》 里发问。他的看法是:文学体裁与其说取决于作品自身,不如说取决于读者的看法。审美观需要读者与作品二者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文学体裁。倘若一个读者事先认定 《唐吉坷德》是一部侦探小说,他也必然会从《唐吉坷德》中获得阅读侦探小说的阅读体验。博尔赫斯认为应当捍卫被冷落的侦探小说,因为侦探小说在混乱不堪的年代默默保持着经典著作的美德,正在一个杂乱无章的时代里拯救秩序。
把文学体裁问题看成是作品和读者两者之间的事,博尔赫斯或许低估了作家的创作自觉性。格雷厄姆·格林就主动将自己的小说分成“严肃小说”和“消遣小说”。更有约翰·班维尔这样的小说家,写侦探小说时索性换一个笔名,并直言写侦探小说的自己是匠人,写严肃小说的那个自己才是艺术家。从作家层面,小说在创作手法和心态上便已有了先天的分别。
而读者中也很少会有人像博尔赫斯一样在整个文学图景中判定推理小说的价值,至少不会笃定地宣称出来。赏析侦探小说时,谈诡计、情节和文笔是没问题的,可一旦希望谈论更多,总会有读者善意提醒:“别忘了,我们是在读推理小说。”大陆作家王安忆、台湾地区出版人詹宏志都写过专门赏析推理小说的著作,但他们的赏析从来都是安全的、不会越界的。作为类型小说的推理小说,在审美上与纯文学小说存在天然界限,这几乎是作者与读者共同的审美自觉。
那么,是否可以将博尔赫斯的例子反转过来———用阅读纯文学的心态阅读一本推理小说,然后获得阅读纯文学的阅读体验?先锋作家马原曾在他的《阅读大师》中将阿加莎·克里斯蒂同海明威、加缪一同归入文学大师行列,但他赏析克里斯蒂的文字又在此后的增订版中被除去。其实很好理解,无论马原怎样推崇,这位推理小说女王看上去都太过“类型”了。如果真的会出现一本打破这种审美自觉的书,那一定是比马原更“不自觉”的读者去写比阿加莎·克里斯蒂更“不自觉”的小说家,比如唐诺和劳伦斯·布洛克这一对。
《八百万零一种死法》的书名取自布洛克最知名的马修·斯卡德系列小说《八百万种死法》。纽约有八百万人口,有八百万种死法。多出一种死法,意味着多出一个不在小说现场的人,读者的视距被拉远,获得局外人的视角。这是看《八百万零一种死法》的视角,也是马修·斯卡德看纽约的视角。当经纪人建议布洛克将马修的职业设定为警察或私人侦探时,布洛克说:“私人侦探更适合我,我更喜欢局外人。”
马修并非布洛克唯一的主角。“谭纳系列”颇具詹姆斯·邦德色彩,但他不过是个领救济金的写作枪手,谭纳女郎也不像007女郎一样处于陪衬地位,而是总能重构谭纳对爱情和两性的期待。“雅贼伯尼系列”充满古典推理风情,但布洛克却又亲自戳破这个假象:“它既无情又冷酷,不会像简·马普尔小姐或彼得·温西爵爷那样轻巧地四处走走就能够解决。”是继承还是戏仿?布洛克与推理小说的关系让人难以说清。
作为布洛克小说的推介者,唐诺最先辨识出布洛克游走在类型文学边缘的写作特色。阅读唐诺为布洛克作品写的导读,会发现唐诺总是不务正业,时而去讲经济学、人类学,时而又转换到卡尔维诺或者本雅明,难怪有人批评唐诺“博而罕约,游谈无根”。“游谈无根”值得商榷,因为这些顾左右而言他的文字确有交汇点,找到交汇点便抵达了小说深处。而换个角度,唐诺式的“博而罕约”或许正是布洛克与推理小说貌合神离关系的绝佳注脚。
为一个作家的作品勤勤恳恳献上近四十篇导读,唐诺对布洛克的喜爱不言自明。但唐诺始终保持清醒,他从不讳言,即使布洛克的小说好到这样的地步,还是离伟大的小说差了不止一两个档次。写推理小说导读是希望借由最优秀的推理小说将读者引入另一个层次,因为推理小说到了某个地步就碰到屋顶,再想往前走就必须离开。
因此,《八百万零一种死法》就有了”抵达”与”离开”的双重属性,既是对布洛克作品的深度解读,也可以看成唐诺引领读者叩开更广阔文学殿堂大门的敲门砖。无论是单纯的推理小说迷还是对小说有更多期待的读者,都不妨跟紧唐诺,试试看。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http://whdszb.news365.com.cn/whdszb/html/2014-10/17/content_194313.htm
《八百万零一种死法》读后感(五):八百万零一种读法
#一
最近有朋友问,硬汉派的推理小说有什么好看的。我想,唐诺的这本《八百万零一种死法》是最好的答案。
#二
从名字可以看出,这本书是有关《八百万种死法》的,是有关马修·斯卡德的,是有关劳伦斯·布洛克的。的确,这本书是有关劳伦斯布洛克的评论集。
按照劳伦斯·布洛克作品的分类,本书同样按照书评针对的不同系列,分成五部分。分别是:马修·斯卡德系列、雅贼系列、伊凡·谭纳系列、杀手系列以及其他三本不成系列的“非系列”。
在唐诺评价的三十九本书之中,很遗憾的,自己也就仅仅看过马修·斯卡德的那一套。新星出版社、红色封面、硬壳装帧。从图书馆借回来的时候,足足装了一书包。那个时候,《烈酒一滴》还没有出版,《繁花将尽》就像是它的名字一样,暗示了这个系列的完结。不过,后来我们知道,马修也许不再破案了,但是关于他的故事并没有结束。
关于马修·斯卡德的17本书,摞起来厚厚的一叠。在这些密密麻麻的文字里面,就能知道马修一生的故事。在《斯卡德死亡曲线》之中,唐诺回顾了有关马修的所有书目,为他盖棺定论的总结了一生的发展,也总结了系列小说的发展轨迹。唐诺认为,斯卡德曲线(包括有关斯卡德的小说)是两条曲线的叠加:
一条轨迹,是强调小说与纽约市现实的发展相吻合,记录了纽约的死亡史实:
gt;那个行过死荫的残酷峰顶,正是纽约最危险最罪恶(也是所谓最华丽的)索多玛娥摩拉时代;而《恶魔预知死亡》之后的缓坡,则同步于朱利安尼市长大治后的纽约改头换面新死亡景观。
有关马修斯卡的与纽约的关系,《行走的城市》与《不自由·毋宁逃》两文中还有更详细的解读。
一条是作者劳伦斯·布洛克自己人生轨迹的投影:
gt;小说的时间和现实时间是一致的、同步的,现实人生的时间对小说中的斯卡德是发生作用的,从年纪、体态体能,到他的情感和心思变化,以及最重要的,是他对死亡这个永恒之谜的感知——对一个小说书写者而言是某种挑战,正面向着现实人生、包括自己的人生,以及社会诸多他者的人生。
这条曲线很明显叠合于斯卡德个人年龄和身体的那道私密曲线,叠合于布洛克本人的私密曲线。
这两条曲线,
gt;叠合于大纽约市真实时间曲线,让斯卡德小说取得普遍的、联系与广大他者的坚实基础,而不是顾影自怜的喃喃自语,叠合于斯卡德自身、乃至于布洛克自身的真实时间曲线,则赋予了斯卡德小说质地真实的感受细节,死亡不再是身外物,是不相干的纯粹吓人用的东西,他者之死一个个融入镶嵌到“我”的身体内部里来。
从以上的几段引文中,我想,关于最初的问题已经有了答案。对于硬汉派的推理小说,我们看得不是一个个的案件,而是参与到主人公的成长之中。看得不是故事,看得是人。起码,在马修·斯卡德系列中确实如此。
#三
如果我们一直在讨论马修·斯卡德的人生经历,一直谈劳伦斯·布洛克创作历程,一直说硬汉派小说如何如何,那就似乎离着《八百万零一种死法》这本书相去甚远。那些东西,是上面那本书要说的,如果我继续写有关劳伦斯布洛克的文字,那就成了要与唐诺打擂台,那就没有什么必要了。起码没有必要把题目起成这样。
所以,言归正传,还是回到正题,谈谈唐诺的这本《八百万零一种死法》。不过,在正文开始前,还是要再说一个故事。
gt;有一次,一个猎人送给他一只兔子,阿凡提把兔子作成了一锅兔子汤,邀请猎人来吃晚饭。
一个星期后,有人来敲他的门,阿凡提问:“谁?”“我是你朋友的朋友,也就是送你兔子的哪个猎人的朋友。”阿凡提请他进了屋,给他喝了一碗兔子汤。
过了几天,又有五六个人来敲他的门,他们说:“我们是哪个送你兔子的猎人的朋友。”阿凡提热情地招待了他们,也请他们喝了兔子汤。阿凡提的好客的名声传遍了四乡。
一天,他家又来了十几个人,一进门就自我介绍说:“我们是哪个送你兔子的猎人的朋友。”
阿凡提看了看这伙人,笑着说:“真没想到,大家请坐,请里面坐。”
客人坐下后,阿凡提提来了一桶脏水。
“这是什么东西?”大家捂着鼻子问。
“这是你们朋友送给我的兔子做的汤的汤。”
从那次以后,再也没有人登阿凡提的门要兔子汤喝了。
所以,“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下文不是想象中关于劳伦斯·布洛克的文字,起码做好心理准备。
#四
在写书评的时候,最怕的是没有东西写,尤其是关于同一个作家的不同的作品。如果每一本都要写出新花样,新内容,实在是一个技术活。这不仅仅是要求作者有笔力充劲,还要求评论者必须有一双慧眼,能够从作者相类似的作品中,把握到不同的风貌。前者,或者是可以通过大量的写作,形成自己的评论模式,成为一个模板;而后者,则需要的是评论家作为读者的天赋,在每一本书里,都品味出相当不同的滋味。这个需要的,恐怕的就不仅仅是勤奋与练习可以做到的了。
当然,要想写书评也不是难事。书评最好写的有两种,一种是介绍作者复述内容。当然也不是没有创见,但更多的就还是泛泛一般的的告诉读者,本书大治的形状,至于其精要在什么地方,应该注意什么地方,哪些地方有创见,则是含混其辞。要说是社科类的,还是好说,毕竟其观点清楚,容易提炼,也就容易勾起读者的兴趣。但像是劳伦斯·布洛克的这种小说怎么介绍呢?要还是介绍作者复述剧情,那还有什么意义呢?纯属是浪费时间。
另一种呢,则是恰恰相反。借着原作的酒杯,一杯杯的浇着自己的块垒。自己想说的话,就打着原作的旗号,肆意的发挥。下笔千言离题万里。这种文章,如果质量高自然也会看得心潮澎湃茅塞顿开,但是大多数如此写书评的,还是自己肚子里的东西太少。要想评论一本书,必须得把这书和自己知道的那点东西子丑寅卯凑上关系,才能挤得出来。
话已至此,可以猜到,唐诺的书评是达到了相当的高度,甚至有个别的篇幅,已经超过了单纯的书评,甚至是文学评论也说得通。
#五
唐诺书评的写法自有其精妙之处。非要总结出特点——虽说有点削足适履——就是以点带面。他将自己当成一个读者,寻找书中让他思考让他感慨的一个小点,写的时候将其放大、丰富,引起读者的兴趣和共鸣。听上去容易,但是读起来确实觉得魅力无限,想要这么模仿,却也不是能够简单的效仿。
在《父之罪》的《上床·作为一种志业》里面,唐诺简单的介绍了案件的特点,是最接近古典推理的一部小说。随之没有在类型上过多的讨论,直接将他认为书中最重要的一点提出,就是斯卡德在书中提出的问题:
gt;目标正确手段错误和目标错误手段正确,哪个比较糟?
唐诺不是大专辩论手,他没有想去回答这个问题,而是结合书中的内容,细化这个大问题,最终落在一个地方,**职业**,或者说**是否职业**。
斯卡德是一个侦探,这个毫无疑问,但是他在办案时候却客串了抢匪。而受害者温迪,她结交一些年长的男友,究竟是满足恋父情结,还是为**妓女**这个身份掩护呢?唐诺试着去分析,但是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在这种不确定的状态下,读者的兴趣被勾了起来,想知道书中是如何描述这个问题,又是如何解答解决这个问题的。
比较最初说的两种写法,唐诺的功力在这就见了出来。明明是一本推理小说,但是他却偏偏不去分析案件本身,不去讨论推理是不是无懈可击,不去思考犯案动机是不是成立。他却像是一个社会学家,在一本推理小说中,试图去讨论人类身份何以成立的问题。就这种本事,恐怕够我是学上一阵子了。
当然,唐诺之所以能够这么写。是因为在动笔写书评的时候,他已经看过不止一本马修·斯卡德系列的书籍,最起码这本书里就出现了《八百万种死法》的名字。《八百万种死法》已经是马修·斯卡德系列的第五本书,所以对于该系列,唐诺必然胸中有沟壑,也就难怪下笔如有神。
#六
这本书也并非没有缺点,不是作者的笔力造成的,而是编辑的遗漏造成的。书中的篇目的排列,上面提到的是说按照不同系列分为五编,这个没有问题。可在各个系列的内部,排列的顺序是按照劳伦斯·布洛克创作的顺序来排列,而并非按照唐诺写作的顺序。这种方式就有了问题了。这样一来,就很难看出唐诺本身的成长,看出他的阅读关注点的变迁。这本书的价值就屈服于劳伦斯·布洛克的作品,成为其书的导读,变成了附庸。而无法凸显出这本书评集自身的价值,这点让我极为不满意。
在《从斯卡德的十月之旅讲起》一文中,唐诺开头就说到,《在死亡之中》这本书距离《八百万种死法》的出版已经有十个月的时间。这部马修·斯卡德系列的第二作,竟然是台湾出版的第十本书。其可以想到唐诺自己在这十个月中”发生了些有意思的事”。
在这篇书评里面,作为推理小说迷的唐诺,就是认认真真的讨论“推理小说“尤其是”硬汉派“(唐诺称其为”冷硬派“)小说的接受过程。引发唐诺讨论的,是当布洛克的书出版之后,
gt;招徕的读者并不是传统的侦探小说迷(他们往往不知道拿它如何是好),而是一些奇奇怪怪的读者.
为什么会这样,唐诺就在这篇文章里面给我们做出了解释。
唐诺先是追根溯源,达许·汉密特和雷蒙德·钱德勒二人的大名是不得不提的。随之冷硬私探派的总体特点予以介绍:
gt;这个类型小说的新约定,采用的是其中私家侦探的身份和造型以及这名私探和周遭世界的**关系**这部分,而不是**写实**本身,毕竟,显示世界太复杂、太流动,像流沙,在上头不好建构如此线条简单的类型小说华厦。
对于达许·汉密特和雷蒙德·钱德勒两人而言,他们写作的时候,更愿意将自己的小说成为**侦探写实小说**,但是随着这种模式的类型化,逐渐的人们就抛弃了他们作为先锋者的要求,而寻求更加稳妥与保险的方式。新推理类小说类型——硬汉派小说——随之诞生。
但是,达许·汉密特与雷蒙德·钱德勒两人在最初时“对抗类型的写实记忆,成为了冷硬小说的天生反骨”。也就使得冷硬派小说成为**最暧昧**、**最难以安心归类**的一种类型小说。这类小说的阅读趣味,则是集中在**某个人的处境**。
具体到斯卡德的小说,
gt;他里面的处境,即使我们人不同在纽约,但同样活在城市、走过岁月、看过想过但有过死生契阔,我们蓄积着难以言说的层层心事,很偶人的,被这个踽踽独行的无牌私探给叫了出来。
唐诺——炫妻狂魔——引用朱天心的话评价马修斯卡德的作品:
gt;这组小说的正确位置,根本就应该摆入马尔克斯、格林、卡波特、纳博科夫这些了不起的作家群中。
上面引用的篇幅,同样是书评中的内容。和前文有很大的类似之处,就是唐诺找到了关于《在死亡之中》这本书有趣的阅读点。这个点并非是来自书中的内容,而是书的社会影响与历史地位。从读者的角度来说,这些内容原本是都不会知道的。但是通过唐诺的介绍,就会将这本书放在一个更加精确的位置,最起码的功用,是可以调整自己的阅读期待。不会是因为想要读一本黄金时代推理而看到这本书,就破口大骂。当然,这种写法有没有问题呢?当然有,因为所讨论的这些点,放在马修斯·卡德任何作品里面都成立。但是,就像是新闻作品一样,这篇书评的出现恰逢其时,恰恰是马修·斯卡德系列作品在台湾出版的第十本。在那个时间介绍,承前启后,就别有意义了。
#七
我的这篇书评,应该如何定位呢?我用了两个部分详细的复述唐诺书评写作的特色,划分到第一类似乎是有根有据。要说划分到第二类,那肯定说不过去,毕竟我都没有什么自己的生搬硬套的理论升华。但是还是有小小的期待,就是将自己的这篇书评能够拔上一个台阶,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复述也不是泛泛的说感想。也就在复述之后,试着提炼唐诺书评的写作的手法。
落实到我自己的这篇文章里面,我写的也并非是唐诺解读劳伦斯布洛克之后,对我在推理小说这个观念上的冲击。我反而关注的并非是唐诺写作的内容,起码在文章里表现的不明显,我关注的是他如何写作。将这本书评集,视为一本写作技巧的参考书。这要算是我对这本书的较为独特的一个兴趣点。
而有关写作方面的文章,书中也有两篇涉及。分别是《一长串的死者》的书评《小说,像一只小鸟》和评论《布洛克的小说课堂》的《书写的技艺之路》。相较前者,后者更多的更像是布洛克自己的独白,他在写作时候的所思所想。不过有一点唐诺总结的非常关键:
gt;很多书写者都告诉我们,每一个好作家都是好读者。
书写者的成立,是从其他书写者处继承过来,成为一种“技艺”。
他又引用卡尔维诺的一段话,作为总结:
gt;目前正流行的另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是:将领敢、潜意识的探讨与解放三者划上等号,将机会、自动作用与自由视为等值。这一类的灵感,建立在盲从每一个冲动,实际上是一种怒从。古典作家遵守一些已知的规则写悲剧,比那些写下进入他脑海中的一切、都受束缚与别的他一无所知之规则的诗人,还更自由。
书写的技艺是需要学习的,也是可以学习的,最佳的方式莫过于阅读阅读再阅读。在如何提高阅读的鉴赏力上,书中同样有一篇漂亮的文章《鉴赏布洛克》,在此就不赘述。
在《小说,像一只小鸟》里面,唐诺通过分析“作者意图”与文本意图“,帮我们分析了斯卡德这个人物是如何一点一点的建立起来的,就是通过一个个人物的塑造,让斯卡德逐渐走出了小说,成为了生活里面的一个人。当作者从雪坡高处丢下第一粒石子的时候,雪球就会自己慢慢变大。当雪球滚到了《八百万种死法》的时候,斯卡德“重生”了,离开了作者意图的窠臼。随着,唐诺说道**写作者的天职在于把作品写得更好,而不是展示权力**。作者并非是上帝,因为作品没有在作者面前完全展开,所以作者也就无法超越时间。他如果一意孤行的试图掌握笔下人物的命运,有时则会适得其反。要知道,即便是上帝,也容忍了亚当与夏娃偷吃了禁果。
但是,在写作的时候是不是由着笔下的人物随心所欲呢?唐诺同样不认同这样的观点。他只是大而化之的提出,有经验的作家会掌握到这种**松紧之际的张力和艺术**。
#八
对于唐诺的这本书,不同的人肯定有不同的读法。即便是我自己,刚开始也仅仅是将其视为书评集而已,试图借着唐诺的眼睛去欣赏劳伦斯·布洛克作品中未曾被我发现的魅力。而随着阅读的深入,与之前的阅读期待不同的感受油然而起。
至于唐诺的这本书会给你什么样的感觉,这个问题就只有你亲自去解决了。
《八百万零一种死法》读后感(六):蔡康永的推荐
虽然这个书里面看起来,唐诺是一个颇为被动的写作者,他就是不得已扮演了出版的角色,然后在出版社的要求之下,必须要为这些他推出的推理小说做一个导读的工作,可是你可以看到唐诺在做这个写作的时候,他自己非常地自得其乐,其中写了很多他身边发生的事情、他的价值观的推演过程,那这些都是我认为好作家必须要具备的特质---就是他得乐在其中,他得在写的时候觉得很得意,有迫切感要告诉你这一些事。我常常在帮人家导读的人的书里面,看到一些过度冷静或者过度理性的写法,相对来讲,唐诺的写法是充满了乐趣,让人即使对于推理小说毫无兴趣,纯粹看一个人怎么样表演他在阅读推理小说这件事情,唐诺的书都可以满足地看到这种表演。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唐诺作为一个作者,他能够用我们很少看到的有趣活泼的或者带一点辛辣讽刺的轻蔑态度,来解释一些在台湾常常被忽略的一些概念,这些都是在一些高傲的知识分子写书的时候,常常没有办法得到的一种优待。我觉得在看唐诺写推理小说的时候,能够因此吸收到非常多……老实说跟推理未必那么有关的想法,一些历史上的演化过程当中所产生出来的支线的知识,这些都是阅读的乐趣。如果你是希望很有效率地吸收推理小说的简介,我觉得唐诺的书未必是首选,可是如果你要读一本有趣,然后可以遍及地去培养出非常精确而且标准比较高的对文学的鉴赏能力,我觉得唐诺做了一次非常好的示范。我们作读书节目的人,当然对于其他爱读书的人,也都会有一份亲切感,尤其是看到一个爱读书、会读书,而且能够把那个感觉传递的特别的准确而清楚的人也会很兴奋,这就是特别为你推荐唐诺的书,尤其这两本他对推理小说的导读。
——蔡康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