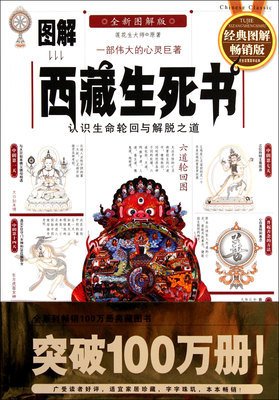《西藏生死书》是一本由索甲仁波切著作,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9.80元,页数:419,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西藏生死书》读后感(一):精神的修炼
姑姑是位佛教虔诚的信奉者,从读高中开始就受其耳濡目染被灌溉了一些佛教文化和保存善念的知识。但那个时候正是青春叛逆期,虽然表面上总是迎合姑姑,但心里早已不耐烦的想要赶快逃离。各种轮回报应,各种孝敬礼仪, 姑姑每次都能讲的口若悬河,我却嗯嗯呀呀的敷衍表示已传达内心。
这些年的生活历练让我变的越来越懂得和喜欢去思考,思考人生甚至人性。虽然仍不知其解,却也不求甚解。因为一旦真看破了,就没了继续追寻的意义了。
接触这本书的时候,我已经基本可以体会到人性了,也明白人性就潜藏在我们身体各处。人性的各种缺点被我们偷偷掩藏却暴露无遗。我试图说服自己用行动将这些缺点埋葬的更深更彻底,或者用更阿Q的方式告诫自己这是人性使然,你没有错。
这本书一开篇就讲到死亡,讲到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是因为人们毫无准备和对生命的理所当然。所以一旦死亡来临,同时带来的就是巨大的毫无防备的痛苦。谈到对于死亡的态度和痛苦的解脱之道,就是接受它,不要排斥它,与死亡同在,因为每个人都正在死。或快或慢,或近或远…无一例外。
其实,这何尝不是你对待任何人和任何事的一种方法呢?接受它,面对它,对,还有与它同在。
“心是什么?”上师蒋杨钦哲仁波切在传授心性给还是年幼的作者时提出了这个问题。读到这我一下就想到了心其实什么都不是,心不是胸腔里面跳动的心脏,也不是你我执着的引以为傲的大脑或由荷尔蒙产生的感觉。
如果硬要比喻心,或许心就是一种念,一直潜藏的本真的自我,一种对美好事物和包含着伟大爱的念。它残留在人类的身体随着基因传播,驱动着人们追寻美好生活的向往。
如果说人是有灵魂的,把心性比喻成魂魄,那么人就是由肉体和魂魄构成,佛教所强调的禅修就是让魂魄镇定然后摆脱对肉体的束缚。凝聚然后脱离。
不是无欲无求,而是不为所动。因要摆脱人世间的无知,执着和恶欲,所以念才要变的如此镇定自若。
想起来以前读书的时候,老师总让我们上课要“聚精会神”。 为什么要聚精会神?因为只有“念”定了,才能“专心”,才能有所为。
人的生命是伟大而神奇的,是神奇的大脑,灵魂,智慧完美的结合。是区别于动植物的高级动物,正是因为人有了心性才变的与众不同,变得智慧非凡。
如果要人类为了远离生活中的痛苦,去剥离心性和灵气而努力修行去达到自我的圆满,不也是一种执念吗?
但证悟了佛的大智慧就在于当禅修获得圆满的同时,起初的念也便随之消失,不复存在。
念一旦起了,无论是善念还是恶念,是善报还是恶报,它都会被为此追逐而来的人类的执着所迷惑。
对于佛的理解,我总是觉得是要慧根才行的通的。所以愚昧的思维只能带我到达这里,心存善念仍是我彼时的态度。
《西藏生死书》读后感(二):上善若水
生是一种偶然,死是一种必然。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也必须接受自己的死亡。我几乎时刻都会想到死亡,但并不是以消极厌世的方式,一方面我对死亡害怕恐惧,不知道何时死、怎样死,因此更加珍惜自己鲜活的生命,感恩知足;另一方面我对死亡疑惑敬畏,不知道什么是死、死后如何,因此需要学习死亡、学习面对死亡。
这样的情况下,翻开读完了《西藏生死书》。这应该是一本写给西方国家读者的书,但不影响阅读。
坦率地说,并不完全理解,不能完全读懂,也并不能做到百分百地认同,还是有很多困惑甚至怀疑的地方,但总体来看,绝对是对心性非常好的净化体验。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抛弃很多杂念,以平和安宁的心态来了解和学习。我是谁?现在的我,是由姓名、年龄、家庭、工作、社会身份所标注的一个客体,如果去除所有外在的符号,此刻坐在这里思考的我,到底是谁?这应该是个哲学命题了。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如果全部向上追溯,归根结底都会统一到哲学上来。“接触哲学的皮毛会让人成为无神论者,但深入了解哲学,会把人导向宗教。”我不讳言,我是个唯心主义者。一方面,我是客观唯心的。我相信世间是有神秘而伟大的力量存在的,也许是主宰一切,也许是裁断一切。人类总是愚昧得可笑,遇到自己所掌握的知识解决不了的事情时,就用迷信来搪塞,这只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即使解释不了那也是真实存在的,而人类解释不了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太多了。科学和迷信其实只是一步之遥,人总是以为世界就是自己所能看到听到感觉到的样子,对还未证实的事总是本能地加以排斥。怎么能认为没看见的就是不存在的呢?证明不了存在就说明不存在吗?这不是很荒谬?就像以前坚持认为地是方的一样,坐井观天的青蛙永远不知道天到底有多大,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我相信超自然的力量,而对于宗教的门类,我并不了解,也许像我们隶属于不同的国家一样吧。书中给了很好的答案,信仰什么都没关系,哪怕没有任何明确的宗教信仰,因为任何宗教都只是真理的不同化身而已。书中也提到中阴闻教得度的理论和现代物理学的观点越来越趋于一致,对此我深信不疑,科学向前发展,才赫然发现原来曾经的迷信是更高层次的科学。另一方面,我是主观唯心的。我相信人的意念是具有无比强大的力量的,可以影响改变身体、生活,可以创造奇迹。当然,不是点石成金那种物欲上的心想事成。任何宗教都是导人向善的,书中极力阐述了这样的观点,让人的心善良而温暖。我觉得自己已经算是个比较宽容、善良的人,但是和上师提倡的境界相比实在是相差太远。不知不觉中,自己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接近颇瓦法的修炼的,但却非常简单地只是祈祷家人平安健康,自己可以为他们承担一切痛苦,远远没有达到为普通众生承受不幸的程度。因为自己以为为太多人祁福都是私念奢望,更无论钱财名利了。我不同意盲目的信,无论是什么,怀疑是必要必须的,允许怀疑接受怀疑的才是真理。自己的疑惑一是宿命到底存在与否,按上师的说法,命运是取决与业的,做什么得什么,虽然果皆有因,但是当下的行却时刻影响着未来的命。二是爱自己和爱别人的关系。其实一向认为自己还算是宽容善良的人,但是要做到对人全部宽容还远不够,特别是以德报怨地对待自己着实不喜的人。禅修的境界是需要完全不考虑自己而全心为人的,而我实在还是很爱自己的,爱自己的身体、爱自己的思想,如果是自己深爱的人纵然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但一般情形下,邋遢的自己是连本人都不能允许的。不过这也大概很少会产生尖锐矛盾吧,进一步修养心性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放弃自己。我想热爱生命关爱自己同时也善待别人宽容包含是自己最理想的状态。
《西藏生死书》读后感(三):放下,生也自在,死也自在
一本让人“放下”的书,等了许多年,许多年。 这是个正经版本,内外纸张装帧都很好,精装。
对密宗几乎一无所知,对藏传佛教更是一无所知。
都生生充满浮华。
“默然,悲伤,又心有所悟,又释然,然后安然睡去…… ”
见人这么一条评论,也似心有所悟。
读到《人生五章》,更是心静如水。
1.我走上街,人行道上有一个深洞,我掉了进去。我迷失了……我绝望了。这不是我的错,费了好大的劲才爬出来。
2.我走上同一条街。人行道上有一个深洞,我假装没看到,还是掉了进去。我不能相信我居然会掉在同样的地方。但这不是我的错。我还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才爬出来。
3.我走上同一条街。人行道上有一个深洞,我看到它在那儿,但还是掉了进去……这是一种习气。我的眼睛张开着,我知道我在哪儿。这是我的错。我立刻爬了出来。
4.我走上同一条街,人行道上有一个深洞,我绕道而过。
5.我走上另一条街。
不知当我即将告别人世的一刻,我是否能够真正放下。
松开手,放下心头的牵挂。
慢慢地阖然而逝……
《西藏生死书》读后感(四):法门之内的死亡宗教
这本书持续看了两个来月.有两个晚上都各自翻看了整本书百分之十的页数,其他很多时候,都是在某些小店吃饭间隙,还有蹲厕所或者临睡前,草草带过几页.生活,索然无味,所以谈这本书,也是如此.我想什么时候会有一个新的宗教起来,而我们平时思考和识略过的小事件,虽然像落地即消遁的人生果,却和这新宗教有万缕相连.
各人心想不同,对我而言这本书讲有三个方面的事:一是生活回忆,二是藏传佛教法门,三是对信佛的辩证,而贯穿三者的是对死亡的关怀.书作者意欲是向大众阐述<中阴教法得度>这本佛教僧徒间流传的深奥古书的广袤内涵,所以这本书绝大部分是我所说的第二条:藏传佛教法门.
我根本不知道我所指"法门"这个词的意思,用佛教话语阐述是用怎样的词句,幸亏我不在乎这点,否则,看完这本书,我会无从谈起.一个不在乎的人如果对这件事太过内行,极为审慎,那才叫虚妄呢.
所谓法门,我想应该是对应<中阴教法得度>中的教法,而中阴,我想对不信佛的人而言,可以对应为"佛态",是信佛之人的姿态.如此解释,可以类比:一个人会游泳,对游泳技能,诸如蛙泳,潜水头头是道,他人即认为此人水性好,弄潮儿.对旱鸭子而言,他不会游泳,他也没有水性,所谓游泳技能,那是天外飞仙的事了,所以旱鸭子眼里,说蛙泳即是说水性,内含各种羡慕嫉妒恨.而说一个人处于信佛的状态,可知他接受佛教对人事的定语,对中阴这个极重要的词,以及相关"名词解释",更会有长长短短的说法和实践,即所谓门道,也就是<西藏生死书>的主要内容.
我想我有很强烈的诋毁这本书中所说佛教,以及生活中形色不一的佛教的某些内涵与形式的意愿.当我用某些词,或者某种解说,并且自圆其说,我会以为我达成了这个意愿.譬如我上一段提及旱鸭子与弄潮儿的区别,便是想讲清楚:中阴,到底只是佛业之内的人的中阴,跟不信佛的人的生死并无太多关系,即使不信佛的人再羡慕嫉妒恨,而僧侣再光明.对于全然讲道状态下的佛教,仅仅是种"迷信",也一直会是种"迷信",能看到的一点是:它对于未来和未知是如此拘泥.
当然,有这种意愿,只是说我处于这种角度,我对一种宗教的讨论,并不会因为处于某个角度而失去颜色.生活中没有真理,但我们是为了求得真理的这类人,比起意愿,我更信服和依托认知,或者说有无限未知的认知及寻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索甲仁波切对生活回忆,主要是对他的上师,都娓娓而来,也好似天外飞仙.圆寂三天不去扰动的死身,那道加持在法国乡村的彩虹,电话相连的桃乐丝和仁波切,第一次经历的亲近的人的死亡经验,睡狮的或禅定的去世修行,在尼泊尔还是印度的一次重大传法和去世,不平凡的修佛的师母和师母的妹妹,在蒋扬钦哲仁波切养育下的儿时等等等等.索甲仁波切对这些记叙,都没有过分修饰,像一个和蔼之人的交谈时的谈吐,只是带有种佛教师傅的独特味道,一种因为沉浸,反而放开的感恩和满足.
2.<西藏生死书>中,索甲仁波切时有对信佛和不信佛去辩证,这更多的是他的无心之举,对佛教大师而言,信不信佛和人的受业都因缘而定,,这显然不会是他内心会强调和认证的问题,假若索甲仁波切致力于梳理此事而成书,我想那一定会是一本精彩的书,更适合人世间的我们.对我们而言,不是信佛会怎么样,信佛会遇到什么的关切,而是佛业在不在那里,我们在哪里,我们怎么样的关切.之所以相信那本不存在的书会精彩,是因为索甲仁波切在<西藏生死书>中零星提到,便打动了我.
3.对死亡的关怀,从听闻到佛教故事开始,到遇到实体的僧人,到阅读实体僧人和僧院的新闻等等,一直以来我都不知道佛教对死亡的关怀如此深,深到可以理解为它就是一门关于死亡的宗教.至于我之前的听闻,我想是俗世对佛教的误读,以及俗世和佛教本身的缺漏和恶业所致,譬如香火,譬如报应.
对死亡的关怀,无非是临终关怀,对佛教(藏传佛教)的信仰,无非是西藏人的生活姿态,这两者都是博大精深的事情.距我们遥远.前者终会来到,后者是些永远神秘的杂糅神话.
4.而那些法门和概念,最基本的是禅定,除了禅定,其余部分我丝毫都不能理解,无从去理解,我想不提也罢.因此,我这篇文字的题目开头的词"法门之内"便无从认证了,佛教,到底是不是执念在法门内的宗教?而对上师的执念,是否是我对这本书的误读?
5.对于个人而言,关于信佛,关于禅定,关于怀疑.全部是引用,并且因为记忆力的原因,不能很好的找回当时阅读的心态和感染,以及相应段落.
quot;心灵深处的改变,死亡的心跳,战士的精神,不变者,心性",这是<西藏生死书>在讲心性和禅定前的几章,我是看这几章时心动的."因为无常让我们感到痛苦,即使一切都会改变,我们还是死命地执着,我们害怕放下,事实上是害怕生活,因为学习生活就是学习放下""我们因为执着不可能执着的东西,而经验都一切痛苦""我们时刻都要快乐,但追求快乐的方式却那么笨拙,以至于带来更多的忧愁.我们往往认为必须抓住,才能获得快乐的保证.我们问自己:如果我们不拥有,怎能享受呢?我们总是把执着误以为是爱啊!即使拥有良好的关系,由于不安全感/占有欲和骄傲,爱也被执着所破坏了;一旦失去了爱,你所面对的,就只剩下爱的纪念品和执着的伤疤""虽然我们一直认为如果放下的话,就会一无所有""如果一切皆会死亡和改变,那么什么才是确切真实的?表象之后,还隐藏着什么无限宽广的事物,来包容这些无常而改变的东西呢?"
quot;我们的生命都消耗在紧张焦虑的奋斗上,消耗在讲求速度和打拼的漩涡中,消耗在竞争、执取、拥有和成就上,永远以身外的活动和先入为主的偏见让自己喘不过气来。禅坐刚好相反,它完全改变我们「正常的」运作模式,因为禅坐就是无牵无挂的境界,没有竞争,没有想要去拥有或执取的欲望,没有紧张焦虑的奋斗,没有成就的渴望:这是一种没有野心的境界,既不接受也不拒绝,既不希望也不害怕;在这种境界中,我们可以慢慢纾解束缚的气氛,把一切情绪和观念,化为自然素朴的虚空。"
quot;为了取代当前虚无主义的怀疑,我请求你们要有我所谓的「神圣的怀疑」,这是觉悟之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承袭自先人的修行法门,绝不是目前饱受威胁的世界所能忽视的。与其怀疑「它们」,何不怀疑自己的无知、自以为是、执著和逃避。我们对于解释实相的热衷追求?其实,终极实相的信差——历代上师们,早已经用他们那惊人而无限的智慧告诉我们,实相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怀疑需要有真正的善巧方便才能对治,我发现很少有人知道如何研究或利用怀疑。现代文明如此崇拜贬损和怀疑的力量,但几乎没有人有勇气贬损怀疑本身,或者像一位印度教上师所说的:把怀疑的狗转向怀疑本身,揭开嘲讽的面具,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恐惧、失望、无助感和烦人的状况引发了这些怀疑"
6.终上所不述,这是本有深厚内蕴的书.其中精妙之处,我讲述到的极少,故称为终上所不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对我们这些反抗心过于强烈的人,所谓韩寒反智,公知传播常识,但愿我们不会得来一个对人世之上的所有,悉数反对的宗教.当然,之所以说这句,跟我的反抗心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因为我的悲观主义.
各种窘迫,各种疾病顽盛,还有悲观,斗胆说,我们这群人需要一个新的宗教.
《西藏生死书》读后感(五):《伊尔的神话》柏拉图
如果死后确实有生命的存在,你也许会问:为什么这么难记得呢?在《伊尔的神话》中,柏拉图“说明”了为什么人转世后没有记忆,伊尔是一名士兵,“战死沙场”,他经验了死而复生。当他“死去”时,看到许多景象,同时接受训令复苏过来,以便吧死后的情况告诉他人。就在他要回来之前,他看到那些正准备出生的生命,在恐怖、烟雾弥漫的热气中移动,通过“遗忘的平原”,那是寸草不生的荒凉沙漠。“当夜幕低垂时”,柏拉图告诉我们,“他们就扎营在‘失念河’边,失念河的河水无法用任何器皿来装。他们每个人都被要求喝这种水,有些人还糊里糊涂地喝了很多。每一个人在喝水的时候,就忘掉了一切。”伊尔被禁止喝水,醒过来时,他发现自己就在火葬场的柴堆上,还记得他所听所见的一切。
吉美林巴说,想象一只老鹰吧!它飞在高空上,并没有投下影子,没有任何征象显示它就在天空。突然间,它发现了猎物,俯冲而下,猝然扑倒地面。当它降落时,恐怖的影子就出现了。
诚如佛陀所说:“现在的你,是过去的你所造;未来的你,是现在的你所造。”莲花生大士进一步说:“如果你想知道你的过去世,看一看你现在的情况;如果你想知道你的未来世,看看你目前的行为。”
善心
在佛陀的时代,有一位年老的乞妇,名叫倚赖喜悦。她常常看国王、王子和其他人供养佛陀和他的弟子,她最希望的莫过于也能像他们一样供养佛陀。所以,她就外出行乞,但一天下来仅要到一枚小铜板。她拿着这枚铜板,向油商购油。油商告诉她,这么少的钱,什么也买不到,但当油商听说她要以油来供佛时,不禁对她产生了怜悯心,给了她想要的油。她拿着这些油到僧院,点了灯。她把灯放在佛前,许愿说:“除了这盏灯,我没有什么好供养的。但希望通过这种供养,我将来能获得智慧之灯。愿我能解除一切众生的黑暗,愿我能净化他们的一切业障,引导他们证悟。”
当天晚上,佛陀的弟子目犍连前来搜集所有的灯时,其他灯的油都烧光了,那位乞妇的灯却一直烧着。破晓时分,目犍连看到那盏灯还燃着,油满满的,并且有新灯芯时,心想:“这盏灯为什么白天还燃着?实在没有道理。”于是想要吹熄,但灯仍然燃着。他试着以手指掐灭烛花,没有成功,又试着以袈裟将其闷熄,依旧没有办到。一直在看的佛陀说:“目犍连,你要熄灭那盏灯吗?你是办不到的。你甚至无法移动它,何况熄灭!即使你把大海的水都浇到这盏灯上,它还是不会熄灭。世界上所有河流和湖泊的水都熄灭不了它。为什么呢?因为这盏灯是以诚心、清净心供养得来的,那种动机使得它拥有巨大的功德。”当佛陀说完这句话,那位乞妇走向他,佛陀为她授记将来必定成佛,名曰“燃灯佛”。
《西藏生死书》读后感(六):苦海逃离指南摘要
G:在拉萨茶铺里偶然翻到过一本介绍人死亡前后的一些程式和细节,印象深刻,但那时苦于在线售书不流行,终究是没有找到这样一本书买来认真读。后来《西藏生死书》忽然流行起来——第一反应是,作为一本畅销书,这肯定不是当初我匆匆翻过的老书。因为如此,我很多年都没有看过这本书。
因为2017年遭遇痛苦的契机,加上经历了一次临终治愈,身边又有人提到这本书——“千金难买回头望”,如果能在爱人离世前后抓住任何可能的契机与他再有一次联络,那为什么不去争取呢?不管是假的也好,心理疗伤而已也罢,总归是想在医学之外再做点什么让自己好受。
1. 当我们死亡的时候,万般带不去,尤其是我们如此钟爱,如此盲目依赖、如此努力想活下去的肉身。而我们的心也不见得能比我们的身更可靠。
2. 我们每一秒钟都被混乱席卷,沦为善变心的牺牲品。如果这就是我们唯一熟悉的心识,那么在死亡的那一刻还要依靠它,就是一场荒谬的赌博了。
3. 我们唯一的人生目标,(p21这时落下一只小虫子,身长大概五毫米,用铅笔画出它的运动轨迹,后来它也开始研究铅痕一样地爬行,特别好玩。它可能是飞不动了,不知道只是要休息一下,还是死亡前兆。昨天姥姥十周年,我用这本书其中一页写了东西烧给她,还祈祷昨晚可以梦到她,但是始终无梦。今天下午做了一场梦之黄粱,梦见了目前困扰于我心的根源,梦见了我的无线的纠结往复....不知道现实和姥姥那里的沟通桥梁究竟是什么,可能用错了方式,可能错过了会意,也可能真的只是“花也没有,绿草也没有,只余小沙丘”.....)就变成要确保每一件事情安全可靠。一有变化,我们就寻找最快速的解药——一些表面功夫或一时之计,生命就被如此虚度,除非有重病或灾难,否则我们不会从恍惚中惊醒过来。
不管如何,先等小虫子飞走我再翻页吧。20170430
《西藏生死书》读后感(七):正确面对死亡就能更好地把握现在
很早就听说过这本书,可是一直没有见到正式版本,前面买过一本《图解西藏生死书》感觉没有大家评论的好,无非是介绍一些藏传佛教的仪式和教义。上周在新华书店闲逛,一回头忽然发现了这本书。买回家后原来打算先翻一翻,等我把手上另一本书看完再说。可是才看了两页就不自觉被吸引住了。开头好像在叙述一个故事一般描述了他的童年生活,介绍了他的上师,还有他在童年时面对亲人死亡的故事。然后慢慢展开介绍了藏传佛教的精髓教义,关于轮回,关于禅修等。主要的是告诉人们如何正确地面对死亡。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亚龙说:“人最大的恐惧是死亡。当一个人能够正确地面对死亡时他就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
看这本书的时候心里会有一种很平静的感觉,觉得原来自己每日在担心害怕的原来都是自己的小我不停制造的幻影,而且看完后感觉心里很有力量,原来在各种情绪来的时候整个身心感觉都被它左右了,完全无力挣脱,现在终于可以用平常心来观察它,知道它会来也会走。
可能跟作者在西方求学的经历有关,本书虽然是一本介绍藏传佛教的经典著作,可是完全用了让现代人都能接受的口气来叙述,一点都不深奥晦涩。虽然索甲仁波切是藏传佛教的上师但书中不只是宣传佛教,还引用了很多其他教派的教义像苏菲神秘主义,基督教等。让我不禁崇拜作者的学术的渊博和包容性。让我们理解其实不管是什么教派,精髓的教义是一样的,都是追求人的本性,达到证悟。
《西藏生死书》读后感(八):最终审判我们的将是我们自己
“对于死亡的恐惧和对来生的无知……没有谁教导人们死亡是什么,该如何死去,也没有人给予任何死后的希望,揭开生命的真相。”
并不把这本书当作佛教理论的普及介绍,更愿意看的是对生死的探讨。
有时候我想,宗教诞生的终极作用,也许只在于教会我们如何面对死亡。生的全部意义,也许也在于死亡。如果没有死亡这个原点,就无法赋予生一切价值。以死之眼观察生,寻得生的意义,这是一切宗教要传达给我们的。
阿多尼斯有一句话说得好,我们不应该随意否定他人的宗教,但归根结底,宗教是一种投诚,人应当成为创造者,而不是奴隶或者仆人。因为宗教只是提供了一条捷径,但真正属于自己的路,必须每个人自己去探索,是绝不能走捷径的。对于宗教中最优秀的人来说,宗教也只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远方目标的参考点,他们把自己的终极探索借助宗教的图景投射到那个目标,事实上,那目标背后隐藏着的是他们自身,而不是他们的神。而且归根到底,他们通往他们的“神”的路也是他们自己探索出的,所以他们敢用内心的认识取代教义——这样的人往往会成为宗教改革者。也同样,在更成熟的强者那里,甚至连这个参照目标的面具都不需要,他看得到自己的神,他定义自己一个人的宗教,让自己和生死的终点对话,为自己寻找出生的意义,为死亡赋予安详,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今天的人们被教育要否定死亡,认为死亡没有任何意义,不过是毁灭和失去一切。换句话说,大多数人不是否定死亡,就是活在死亡的恐惧中,连提到死亡都是一种禁忌,甚至相信一谈死亡就会招来不幸。
有些人则以天真、轻率的欢愉心情看待死亡。他们因某种不知名的理由,认为自己的死亡不会有问题,对于死亡无可担忧。……一位西藏上师所说的话:‘人们常常犯了轻视死亡的错误,他们总是这么想:嗯,每个人都会死。死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死再自然不过了。我不会有什么问题。这种想法很美,但到了临终那一刻就不太妙了。’”
人如果没有学会如何死亡,将永远无法学会如何生存。可是现代人还有多少会追究生的意义呢?无暇思考,亦或,无从思考。生就是生,只是现象。我的一位朋友说,她认为人生只是一场观光旅游,尽可能快乐,尽可能体验一切可以体验的东西,所有经验都不要错过,体验就是目的,不为任何意义存在。她笑问,这种是不是所谓的虚无主义。我说,你这只是彻底现世至上的现实主义者。能够享受现世的一切,并充实地为之欢喜和忧愁的人,绝对不会因为生存的无意义而绝望。死亡带来的空无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个科学常识,既不构成对生的威胁,更不会变成对生存意义的拷问。就算在许多知识分子、所谓的文化人之中,所谓生存意义的追问,也更像一种矫情的粉饰和故作深沉。用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识别:生存的无意义会让他们痛苦吗?会让他们失去生活的实感吗?答案显然是,不会。他们只会为追求不到手的东西而痛苦——现世的福乐:物质、金钱、名誉、成功……他们不会有虚无主义者那种彻底撒手的洒脱——他们不甘,也不会有从虚无中产生的极端的行动动力、彻底无畏的疯狂和勇气——他们不敢。他们的死亡之眼不曾打开,在这场观光之旅结束时,会喟叹空来世间一场吗?又或者,在死亡的那一刹那清明中,忽然明白,想起一切,原来孜孜倦倦追求的一切都是都没意义的,却一切都来不及,又一世虚度,无尽的悔恨、恐惧,但一个人站在死亡的当口,没有任何一个他人能来帮你。宗教信仰也许就是在这个时候起的作用。如果你能相信,无论信的是什么,都能拉你一把,可是如果你没有信仰,或者你的信仰最终动摇了呢?你所能倚靠的只是无尽的虚无和绝望。那时才会发现,原来你一生逃避的就是面对它,这本是你唯一该做的事,你本有一生的时间用来准备,去面对,可是你又浑浑噩噩地让它过去,在最后的时光中追悔莫及。这是最大的恐惧——地狱的实相。你可以逃脱世间的一切,却逃脱不了自己。
也许这个无法逃脱的“自我”,能从另一个角度让我们窥得生的意义。谁都明白,人除了自己,什么也不拥有。甚至自身,都是向神秘的深渊借来的。世界是幻象,是梦幻,所以人就用各种各样的标签定义自己、粉饰自己。可是这自己是什么?当你质问,我来到这世上一趟,做了什么、得到了什么?得到这所得的“我”是什么?在质问的“我”又是什么?现实主义者回答,我得到了体验。但生命这盏明灯点亮时照见的一切,在光线消失后是否依然存在?亦或不存在?如果没有任何存在,何必要追问,何必要恐惧?逻辑上彻底的虚无者不会恐惧,但事实上却不存在这样的人。我们在恐惧,这个恐惧产生的起点,必然蕴含着一个说“是”的准则。我们都带着某种使命诞生,但是直到死亡的瞬间,也许才会记起它是什么。一切的悔恨都因此而生。又或许,我们冥冥中已经走上那条路,不知不觉完成了它,那么死亡时,会因欣慰而安详。这种寻得,也许是来自原生态的自然,也许是来自二次生的觉悟。前者倚赖机缘的不确定性,后者需要高度的精神认识。能认识死亡却不恐惧的,只有真正的智者与勇者。很多“不怕死”的人,只是因为他们并不晓得“死”是什么——他们轻视了死亡。真正的活法应该是:认识死亡,珍惜它馈赠给我们的机会,为此找寻一生,给出自己的答案。所有人都知道的答案,所有人都忘记了的答案。
一些人浑浑噩噩地活,浑浑噩噩地死去,他们死的时候恐惧,却不明白自己恐惧什么。
一些人看清了终点,却背过脸,装作没看到。他们欺骗自己而活,却不能欺骗自己而死。于是他们同样在痛苦和恐惧中死去。区别只在于,他们清楚自己恐惧什么,却没有去面对它,因而失去了战胜它的机会,或者说失去了它给自己的馈赠、机遇和教诲。他们同样也浪费了一生。
一些人面对着终点,不断追寻着意义,也许会寻得,也许会错失,也许找寻本身就是一种意义——最后找到什么,或者没找到什么,无论哪种,都是一个回答。在面对死亡时,这个答案多少能给他们一些慰藉。
传说也存在这样的人,真正的觉醒者,生死已被他们征服,一切都不再构成限制。
对于只是凡人的我们,也许只有在死亡的那一刻,才会知道自己找到的是什么。借鉴那些有过濒死体验的人的经验,也许是个参考。不少有不少据称是明白了生死的意义,并要转述给世人才回到人间的人,他们共同说出的是:俗世追求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唯一该做的事就是给他人带来幸福,让他人的心灵得到抚慰——这正是世上那些疯子和先知们说出的事实:天国近了,你们改悔吧。地狱并不存在,除了在我们心中。最终审判我们的将是我们自己,一切都逃不过。因此,在生时补偿一切,不要留下遗憾。
《西藏生死书》读后感(九):《西藏生死书》没有那么好
曾经在我迷乱的时候,对于这本书难以阅读下去。这次我带着虔诚的心再次打开,并认真的做着笔记与导图,然而前面因为内观过的感同身受的支持外,后半部分令我厌烦不已。一直想做文学评论但是不知不觉的难以逃开批评,或许,这又一次提醒我去走进内在,看看那里在发生着什么,为何如此。
对于灵修类书籍,我通常难以看下去,无论是书中难以印证的存在还是作者那一副“爱信不信,不信是你太过凡人”的态度。我们的学习过程,就是带有偏见和选择的,这种思维定式决定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然而,就因为这样,这类丛书才应该认真的有体系的梳理清来龙去脉,让人明白可以至此,而不是仅仅只会重复:如果你想从本书得到益处,就必须毫不怀疑的相信所说的一切。另外,修行本身就是需要修慧,通过自身的体悟获得智慧,著书的形式虽可以普及佛法或者真理,然而加入作者的阐释通常会有离题千里的效果。
《西藏生死书》或许应该叫做《中阴闻教得度》注释更为贴切,书中体系凌乱,大部分是对《中阴闻教得度》的引用和解释,本来对于第二部分临终关怀很感兴趣,但书中连过度都没有只是是简单谈过,直接导向是对禅坐以及各种修行方法的教授,然而遗憾的是,作者给你讲过之后,通常还不忘一句,如果修行必须有上师的指导。本书秉承了通常意义上的佛教教义,就是对死后的重点阐述和教导,仿佛这一世都是为了来世的安宁,而对此生并没有进行较好的指导。知道死才知道怎么活不假,但以死后为目的的修行却是有点本末倒置了。
我不否认,书中有很多句子和语言都可以打动或者震撼心灵,但是对于整部书以及作者的思想来说,却是细枝末节。有如,于丹的心得,孔子本不是这个意思,被作者加以自己的阐释,在意思上正确无比,抚慰心灵。
《圣经》的解释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加入不同的注解,妄图通过《西藏生死书》了然佛法的真理或者生命的意义是非常狭隘的。尤其是对某一宗教的教义的了解,一定要去看最初的经书,否则后世的解释只能是越发的偏离和可笑。
心灵存在向往永远都不会错,但是盲目和不求真却是产生迷失的可能。我告诉自己顺应内心,这类的书籍看不下去就不要看了,佛教的发展太过庞杂和有政治色彩,中途的几经异化难以见其面目,如若追寻就找到最根本的内容拜读。信仰不是宗教,是对内心的皈依和追寻,更不需要外在形式的装扮。
《西藏生死书》读后感(十):我为什么执迷不悟
书中在慈悲心一章说了一个故事:某僧人日夜修行精进,以求见某个佛,然而,在山上苦修六年却没见到,丧气地下了山。下山后(这个阶段的故事和李白的故事有点像)看到一个人操着一根巨大的铁棒在磨,想把它磨成铁针。僧人感到很惊讶:这世间竟然有人坚持着做这种愚不可及的事,而我连修行都坚持不下去!于是他带着羞愧的心,又上山修炼。
苦练三年后,僧人还是没有见到佛,心淡地下了山。这一次,他看到一个巨大到突破天际的岩石,有一个农夫,拿着一根羽毛不时地蘸水,然后往岩石一顿狠刷。这个农夫做这一切的原因,是因为这块石头遮住他家的太阳了。(就不能搬家吗?!)僧人和我一样愤怒,并且惊讶,和上一次一样,带着羞愧之心上山修炼。
僧人再苦练三年后,佛还是没有出现。僧人狠狠地瞪了练功房,痛下决心:我这一次再也不会回来了!(这一段重口味)下山后,看到一条下身腐烂的狗,并且有蛆虫在腐烂的部位蠕动,然而它身残志坚,拖着残败的身躯去咬僧人。僧人一看,顿时觉得这条狗无比可怜,想用手帮它把蛆虫去掉,但又怕弄伤那些蠕动的娇弱的蛆虫,于是他,他!用!舌!头!去!撩!走!蛆虫!舌头快触到蛆虫的瞬间,金光四射,佛出现了。画面太美。
看到这里,觉得实在自己实在没慧根,不仅不感动,反而一阵恶心。不想效仿僧人,是没大爱吧?
当书谈到修行法门以及上师时,其中出现了很多次类似于“上师是绝对真理的化身,要全身心相信上师。”此时脑中的弹幕是:希特勒?邪教?要找到一个佛法高深,德才兼备的大师来指导修行,几率太低,也就是说,看缘。若怀着这种念头去寻找修行去寻找上师,会不会有被心术不正的家伙利用的危险?盲目崇拜的历史,在我国,在德国也有,后果在现在也是显而易见的。至于与佛教接触甚少的平凡人,还是老老实实地去人间炼狱感受天堂。
在书中对于生与死的界分,也可以用村上春树的一句名言来定义:死并非是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如果在脑海树立这种观念,那么对死的恐惧会少一些,也理解得深一点。
书中对于临终者的照顾方式,简而言之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上想问题,让对方释放情感,让对方试着修炼法门等等。和人际交往也有共同之处。
曾经听说这样一种观点:人要死三次。第一次死,是肉体之死。第二次死,是社会地位的寂灭。在葬礼时,大家怀念你,然而社会上再也没你的位置。第三次死,是真正的虚无。当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人记得你的时候,你才算是真正地归入了虚无的死境。名垂千古和遗臭万年,在某种程度上都算是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