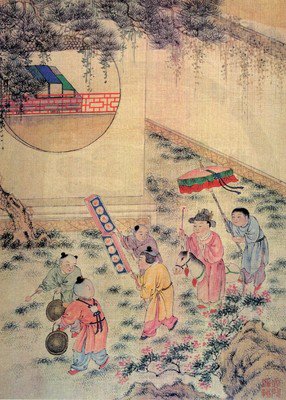编者按
在胡玮莳的主持下,两位“治愈系”青年作家辜妤洁与浅草千叶子就创作进行了对话。访谈主要围绕治愈系文学的特点、日本文学的语言和风格、和风元素的应用等话题开展。两位不仅分享了自己的创作心得与趣味取向,还深入剖析了和风之美。
辜妤洁&浅草千叶子
辜妤洁:
青春文学作家,日本明治大学硕士。曾获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主要作品有《致樱花树先生》《就算海水淹没岛屿》《一瞬的光和永远》《若你转身牵我的手》《风筝有风,海豚有海》等,曾在《萌芽》发表《我已离开太远》《就像拥抱一只小狗》《一点一点发亮》《我们的拼图》《界线》《花火》《直到永远》《寂静爱》等。
浅草千叶子:
原名郑宇龙,西南政法刑侦学院本科,日本神户大学中国文学硕士。当过警察、空服员、广告文案,会日韩意越数国外语。著有长篇《前世今生的樱花》《倾城之泪》等,曾在《萌芽》发表《渣男物语》《温泉旅馆一番街》《Hi,鱼丸店少年》《大学失恋形状录》等。幼时有三大梦想:出国,出书,赚大钱。现在就剩最后一个没有实现了。
胡玮莳:妤洁,在日本求学生活多年,你自身感到所处环境给你的写作带来了哪些变化?比如经历的事件、常用的意象、写作语言以及行文风格是否有受到日本文学环境的影响?你怎样看待和处理这种变化?
辜妤洁:在日本,自由与自我紧紧相关,它让我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也带来相对封闭的生活。到日本后我大部分时间一个人待着,会自我审视,对写作也有了更多思考,比如为什么写,想写什么,怎么去写。当然,这可能也和年龄有关,成长到一定阶段都会思考,而环境会引导我们将思考的重点落在哪里。影响会有一些。以前听过一个说法,西方文学是开放性的,读到的是想象力和情节,日本文学是闭合性的,读到的是细节和变化。我现在的创作也很注重细节,为了强化情节,我会尽力先列出故事大纲。其实影响更大的是日常生活,日本人的思维和表达方式与我们有差别,纤细、含蓄、克制,注重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举个例子,我回国后,国内的朋友常常说“你敬语用太多了”“需要什么时就直接吆喝,千万别太礼貌,我可怕那一套”,但在日本,很多认识几年的人也要讲敬语啊鞠躬道别啊之类的,很有仪式感。在日本生活和学习需要适应他们的方式,言行习惯的变化落实到写作中就是行文风格的变化。不过这种变化是可以调整的,毕竟一棵树长了二十多年,树干定型了,新长出来的只会是枝丫,枝丫按需修剪就可以了。虽然考虑过意象过于日式会造成隔阂的问题,但“四月我从电车上跳下来的瞬间,被迎面飘来的樱花打动”,刻意修改成桃花就很奇怪了。我不想自以为是地去考虑读者想看什么,能做的只是尽力写出我能写到的最好状态。无论变好变坏,首先需要改变。
胡玮莳:这句“四月我从电车上跳下来的瞬间,被迎面飘来的樱花打动”是不是很有治愈系的特点?有人说你的文字柔软可亲,能够给人触动。你笔下时常出现的“樱花”“微风“”海滨“”明媚”等颇具清新感的词语在你看来是不是形塑你语言风格的一个重要元素?
辜妤洁:谢谢。我不是一个情绪激烈的人,语言风格接近性格。之前朋友来东京旅游时和我住了一段时间,很忙的时候被日本老爷爷拉着聊两个小时,出门吃饭也几次主动帮隔壁桌不会日语的游客点餐(有时对方并不礼貌),朋友说我这样的性格不够尖锐,写不了评论性质的文章。我反思了好一阵呢,后来想如果能在柔软之中挖掘出细腻深刻的东西,也会变得有力量。做人和作文都想是这样。
我没有刻意去写某种意象,我在东京住过的地方叫台场,属于填海造陆起来的区域,在阳台上能看到海。晚饭后我常常去海滨散步,一个人坐在沙滩上发呆或者想问题。创作中实地取景既生动又简单,在那段时期里我被它们围绕着,就用得多。词语的使用频率是语言风格的一部分,我修过一点日式花道,这里有相通之处。在花道里,除三个主枝外,花往往并不担任重要角色,花道的精髓在于体现花的美态的“形”,更在于兼备品味的“神”。在指导、原材、工具、步骤相同的情况下,所有人插出来的花的感觉是不同的,这就是风格吧。
胡玮莳:浅草,你也在日本生活多年,这对你的写作有怎样的影响呢?日本文学的语言、行文风格以及典型的和风元素对你来说是怎样的存在?有人评价你的小说有种日语“直接被翻译过来”的感觉,那么你自认为受日语句式的影响很深吗?日语翻译腔在你看来有什么独特的修辞效果?
浅草千叶子:很奇妙,我对日本的印象,似乎不随我在日本工作、学 习的经历有所改变,日本好像一直就在那里,仍旧是那个让我无法捉摸的国度——而且才回国小半年,就似乎离那里异常邈远了……日本人不爱说话,尤其不爱说废话,讲求“距离感”,这让我写的东西越来越宅化。我至今还记得2012年冬天,东京下了好大的一场雪,JR电车全线停运,我跟好几个韩国同学一起从千代田区生生走回靠近千叶的新小岩。那一路,无人言语。我仿佛体会到了《津轻海峡冬景色》里“北归 的人群中无人言语(北へ帰る人の群 れは誰も無口だ)”的感觉……也因为这样,我写的东西里越来越多出一些“留白”,一些想象的空间——就好 像山水画那样。
到日本后,因为专业的关系,我开始阅读日本原版的小说,而且读了很多莫名其妙、乏人问津的冷门作家的作品。说起来,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还是推理小说,尤其喜欢坐在山手线上一边读一边看窗外的景。那些曾经在书中出现的场景,都变成了身边的现实,这让我陶醉。这些和风元素对我而言,已经不再是臆想的所在,而成了实实在在触手可及的物件。现在想来,在日本留学的四五年,真如镜花水月一般。
至于说我的写作受日语影响深,倒是无力反驳。其实仔细看鲁迅写的文章,也受了很多日语的影响。用我导师的话来说,喜欢写日式中文的人,往往都喜欢那种“异化”的感觉——既是中文,却又同一般人的行文架构有所不同,试图在腔调上辗转出新意。有时同一个意思,用日式中文写出来,感觉就完全不同。我举一例:“他死的时候,是昭和6年4月8日的那个早晨。”如果用一般的中文写出来,应该是:“昭和6年4月8日早上,他死了。”或者:“他在昭和6年4月8日早上死了。”一般而言,翻译腔的最大特点就是动词的名词化,以及逻辑的清晰和简明。这样的效果就是——容易创造异国风情?
胡玮莳:“我仿佛体会到了《津轻海峡冬景色》里‘北归的人群中无人言语(北へ帰る人の群れは誰も無口だ)’的感觉……”这段文字让我的心充分地感知到了情与景的合一,可以说是日式美学的典范了。
本文为节选,刊于2017年第十二期《萌芽》。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者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