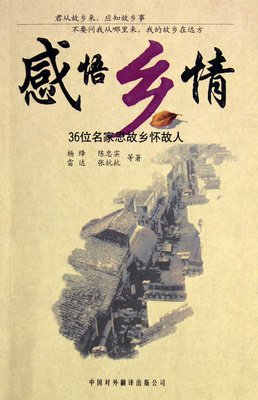“果园村”隔壁的村庄叫“刘庄”。
那个时候的我,活泼好动,很是得到一帮男孩子的喜欢,其中就有居荣法。他喜欢我的方式是,每天早上来我家等我上学,什么话都不说,等我吃完早饭,要上学了,那就拿起我的书包,背在自己身上,到了学校,他先用衣袖擦干净我位置上的灰尘,再轻轻将我的书包放下。
整个一年级我的书包大都是居荣法替我背的。
这样背啊背的,有一天母亲在家说起,居荣法的父亲找到她,想和我们家认个“干亲”,让我做他的“干女儿”。
那时候认个“干爹”,和现在认个“干爹”的意思完全不一样,那时候认个干亲,有“相中你们家女儿做我们家儿媳妇”的意味,虽然没有明说,但那个意思母亲是明白的,所以迟迟不同意。
可是居荣法的父亲很执着,三番五次地找到母亲,母亲实在是不好意思拒绝,就同意了。
这样我就有了一个干爹,我的干爹叫“温兆财”,干妈叫“居鲜红”,我还有了两个干姐:居荣珍、居荣红。
我对有了个干爹还是挺高兴的,因为我们那个地方的风俗,每到过年过节,尤其是端午节,干爹都要“带”干女儿来家吃饭,还得给干女儿买新衣服,我喜欢吃和新衣服。
每次去干爹家,都会看到我的两个干姐,她们确实长得不好看,身材粗壮、脸蛋黝黑,穿着红色的衣服。
我对两个干姐没什么印象。只记得有一次,我去他们家吃饭,饭桌上有一盘糖饼,啊,太好吃了,那个时候我虽然才6、7岁的年纪,但也懂得去人家做客,吃相不能太难看,所以吃了两块糖饼,就装模作样说“不吃了”。饭后我在干爹家四处溜达,溜达到厨房,一眼就看到灶台上有一盘吃剩下的糖饼,眼看着四下无人,我迅速地拿起一块糖饼放进嘴里,正狼吞虎咽着,荣珍进来了,我被碰了个“现行”,尴尬极了,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没想到荣珍像没看到我的“窘相”似的,很自然的说:“荣法呢?不在这块啊?”然后就转身走了。她的自然,缓解了我的尴尬,我松了一口气。
就是那一次吧?我要回家了,荣珍送我,在她家屋后头,她对我说:“我这两天出不去,你去上学,帮我找一下胜权,让他晚上十点在大队部等我。”胜权我是认识的,长得很帅气,在村里的柳编厂上班,和荣珍是同事。我们学校离柳编厂不远,我满口答应:“好嘞!”
正是黄昏时分,晚霞布满天边,给荣珍的脸上抹上了一层亮红的光彩,她的眼神里,有一种深深的忧伤和忧虑,她嘱咐我:“别忘了啊。”她的神情,让她那张平庸的脸,也变得有感染力起来,我说:“我不会忘的!”
可是,我还是忘了,而且忘得一干二净。直到过了很久之后,我听母亲和人闲聊,说起荣珍:“听说大丫头不听话,在厂里不知道和谁搞对象,兆财不同意,不让她上班了!”我心里一惊:荣珍托付我的事情我忘了呀!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理,我没有告诉母亲:和荣珍搞对象的那个人,是胜权。
随着母亲的工作改动(母亲是乡村教师),我在二年级的时候转学了,记忆里,那之后我就再也没去过干爹家,是不好意思面对荣珍吗?想不起来了,反正再也没去过,也没见过胜权。
再一次见到荣珍,也是我最后一次去干爹家,是我三年级的时候。干爹要死了,临死之前,指名要见我。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说不出话,但还是努力望向我笑着……荣珍站在父亲的床边,默默地流泪。
荣珍在父亲死后不久,由家里做主嫁给了我们村的一个木匠,两个月之后,因为和丈夫吵架,喝下农药,死在了棉花田里。
记得母亲好像是在晚饭桌上说起这个消息:“你那个干姐,喝药水死了,两口子吵架,这丫头,心眼怎么这么小啊……”,我心里大大的一震,但面无表情。晚饭后家人都在院子里纳凉、聊天,我早早就上了床,放下蚊帐,8月份天气非常闷热,我在蒸笼一样的蚊帐里,身体像泡在汗水里却浑然不觉……
离开故乡已经二十多年,那些人那些事,并没有因为时光久远而模糊,相反却愈加清晰。我时常想起荣珍——
那次她碰见我偷吃,一定是知道我不好意思,所以她赶紧借口找荣法,转身走了……她真是一个善良又善解人意的人;
那次她让我给胜权带信,两个人相约见面,是想商议他们的爱情怎么能够得到父母的同意,亦或想私奔?如果那天我把信带到了,她的命运会不会改写?
那次荣珍知道我没有将信带给胜权吗?她会不会以为是胜权不愿意去赴约?所以死心嫁给了那个她不爱的木匠?
……
想起这些,我就心下难安,自责愧疚,而这一份自责和愧疚,再也没有办法传递和化解,因为那个善良的干姐已经不在了……
也好,就让我背着它们一辈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