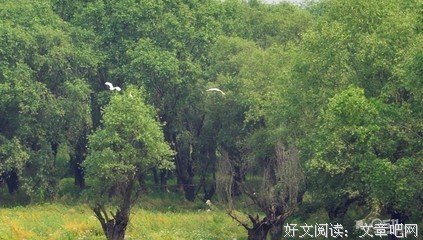在豆瓣上看到过一个帖子:不考虑薪水尊严面子,你最想做什么工作?
有一个回复打动过我:
“认真想了想,我从小到现在最想做的工作就是扫大街,而且只在秋天工作,不考虑天气不考虑阳光,每天清晨出门慢悠悠的扫一条街,耳朵里塞满音乐,把所有的落叶都堆成你的形状。”
后来我问过自己,那么我呢?
不需要有太多的客户,也不必应付同行间无聊的应酬,无所谓这个月能不能赚到北京郊区一平方米的房价,甚至偷个懒也没关系。只需要在洱海边有一座两层半的房子,和一张铺满阳光的藤椅。
做得过且过的生意,赚能养活自己的钱。白天招猫逗狗,打包一辆顺丰小车就能运走的快件,日落前关闭电脑和手机。晚上数星星看月亮,爬上屋顶喝冒着冰茬的风花雪月,趁着夜色写情诗。
然后把我收藏的每一双球鞋,写下的每一句文字,都冠上你的名字。
“你看吧,你不好好念书,就只能像XXX一样,低声下气的当微商,说不准卖的都是三无产品”
后来,我解释了我并不需要低声下气,因为买卖买卖,是自由且平等的交易。至于是不是微商这个永恒的论题我已经不想解释了,完全属于白费口舌。
“孩子,你听妈说,千万别跟XXX学,卖鞋能有什么出息,还不如多考几个证书傍身”
再后来,她们仍不死心的挣扎,自说自话的认定了我每个月的额外收入大概最多不超过四位数,于是。
“咱家不缺你累死累活赚的那点钱,来,这1000块拿去花吧”
“呸!一双鞋卖好几千!无良商贩!赚的都是黑心钱!”
仿佛自力更生变成了一件令人不齿的事,温室里的花朵就应该永远享受庇护,他们不需要面对世界,也不需要正视自我。
这是大部分中国式家长的通病。他们在孩子身上寄予了太多的希望,甚至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也正是因为这种病态的执着,让这些花骨朵常常一出恒温篷就被冻死。
事实上这是另一种摧毁天性的暴行。所有的灵光一闪都被按上无理取闹的帽子,探索世界的梦想也到不了远方,那些被禁锢在一方沃土的孩子看似享受着最优厚的照顾,实际却是懦弱的逃避。
我倒不认为提前认识真实的世界是一件坏事,一点一点深入,感受光明和丑恶,磨练出波澜不惊的态度,总好过猛然当头一棒。
我从不认为学生时代依赖自己是一件羞愧的做法。发传单,端盘子,当导购,收银员,或者卖球鞋。其实这些工作远比不上陆家嘴写字楼的光鲜也无法比拟长安街侧政府机关的权势,但能用廉价去定论吗?很显然不行。
付出劳动,获得合理报酬,天经地义。而独自面对社会,这也是一道迟早都要跨越的坎儿,拖得越晚,沟就越深。更无法否认的是,这些懂得掌握分寸的人,才能轻松避开一路上的沟沟壑壑。
明确目标,列出计划,然后为之奋斗。错了就错了,大不了从头再来。
要我说,只要你愿意,在时间经历和心气儿都足够的前提下,想卖鞋就行动,想旅游就订票,想喝酒也不用克制,想恋爱便大胆亲吻。
根本没有所谓的“你不好好读书,长大就只能XXX”。
要知道,理想不分贵贱,那些挑着手指甲一脸不屑说出这种话的人,不是生活里的幻想者,就是心理上的LOSER。
<END>
往期精选
“老鞋已死”
“我的名牌鞋是偷的,爱马仕是骗的,保时捷是租的,但想炫富的心是真的”
那个因为调包正品球鞋被判入狱的少年。
“你的鞋子就是你的底气”
致球鞋婊:货自己调,别找我男朋友
“卖鞋以后,我从花100块都小心翼翼到花一万块毫不犹豫,但好像越来越迷失了自己”
“通过你的鞋子,我看到了野心”
“你仍是我心里背着阳光投篮的少年”
“我是鞋贩子,不是慈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