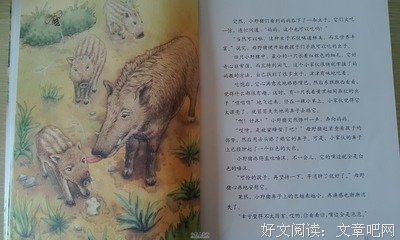《吃动物》是一本由[美]乔纳森·萨弗兰·弗尔著作,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80元,页数:23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吃动物》读后感(一):你还敢吃肉吗
看了这本书,你对肉食的兴趣绝对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相信我,这本书传到的信息,会让你今后的生活更加健康。
关于动物养殖的很多真相是你现在急需获知的,但在传统的媒体里,绝对不会报道宣传的,看这本书,你能知道这一切。
《吃动物》读后感(二):吃动物的我触动了
亲自调查工厂化农场的饲养环境,动物的生存环境,让现实展现眼前,作者并非简单的纯理论化的告诫我们吃素的弊端,而是让我们了解现代农场动物饲养的整条产业链,给我们的判断提供论据,可信度高,尤其让我惊讶的是现在温室效应的加剧中,动物饲养居然占如此重的分量。
对于动物的生存环境及从出生到死亡过程中通过农场工作人员的现身说法让平时只图口爽的我增添些许罪恶感,如果说生命平等,那我们如何身临其境的体会它们的心境,如果换做是我们人类,又会如何呢?这也许是困惑之一吧!
《吃动物》读后感(三):几点疑问
1,作者把肉食仅仅视作一种传统和习见,却始终没有论证植物在营养上可以完全取代肉蛋奶,是一个逻辑上的大问题。如果茹素将导致人类在营养摄取上的严重不足,人类还是否应该坚决弃食肉类?哪位有这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请不吝赐教。
2,在“杀”这一点上,要求人类对被杀动物死亡过程的“无痛苦”负责,将“人道”推及动物,那从逻辑上是否也应要求猎杀人类的猛兽对所猎杀人类的“无痛苦”负责?这个问题其实还是那个老问题,是不是应该将动物与人平等同视?还是说人应该把动物视作“人道”对象,但动物可以将人视作“动物道”对象?
3,即使茹素,我们现在所食用的植物大都也是工厂化管理,密密麻麻,使用化肥、农药,转基因作物,反季作物等等,是不是因为植物没有知觉这些加诸动物身上就是“罪孽”的做法在植物身上就漂白了?我觉得未必。首先,这些“罪孽”,不管加诸植物还是动物身上,最后作用到人身上,作用在环境中,产生的恶果都差不多。其次,植物真的没有知觉,没有情感么?没有所谓的植物伦理么?再次,就算植物没有知觉,如果没有知觉就可以为所欲为,那么“无感人”、植物人岂不是……
4,如果把众生平等和众生都应享有“人道”的伦理观推至极致,那么人类只能吃观音土了……或者人吃人。
5,作者在书中似乎提到,即使要食肉,也应该拒吃工厂化农场生产的肉类食品,这一点我非常同意。但作者提出的解决方案似乎是回归传统养殖方式,家家户户自己畜养动物。那我想问,这样做,养殖过程的“非人道”行为是可以阻止了,但屠宰过程中的那些残虐行为呢?满足单户家庭需求的养殖只会加剧屠宰过程中的非人道行为吧?因为谁家也没有能力为了杀一只鸡还要先将它电晕,然后用自动化的利刃,快准狠地一刀下去……
《吃动物》读后感(四):人能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作者描述了工业化农场给动物带来的痛苦,如果一个人并不care动物的痛苦,对她/他来说,动物的痛苦不能构成放弃肉食的理由。一个人可以在自己的满足与动物的痛苦之间作出选择——“爱心不能当饭吃!”“别人家的孩子死不完,何况动物?”“感谢动物的牺牲,感谢上帝的恩赐……”
作者还提出一个理由,工业化农场对生态和环境的破坏,据说美国的河流和土地已经被污染了,工业化农场附近的居民健康也受到了影响,作为一个中国人,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美国人民表示同情……作者说,美国的模式已经传播到中国,中国的环境、生态和人民的健康也要受到威胁了……只要污染不到我身上,先吃起来,谁知道世界末日是哪天?
作者最后的理由,工厂化农场会不仅让食品安全成问题,动物们畸形、有病且被喂食了太多抗生素,还会造成禽流感等疾病传播,一个普通的不是特别爱吃的中国人能做的,也就是自己尽量不吃,连劝阻家人都没有信心做到,何况改变世界?
书中有句话发人深省:问题在于我们想吃太多肉,又不愿意为此付钱。一个不能完全吃素的人的理性的选择,应该是少吃肉,吃好肉,而不是顿顿无(劣质)肉不欢。
我可以不管鸡的痛苦,可以不管屠杀鸡的工人的心理问题,但是我不想让自己的儿子吃那种方式养出来的鸡肉。
植物的食品安全比动物更好么,作者没说。 奶牛的饲养方式安全么,我不知道。奶粉对于婴幼儿营养的必要性似乎已经不容置疑。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已经被相关企业所垄断了,就像作者所说的肉品行业在美国所做的那样。
公众或者消费者有没有权利知道食物的饲养过程和饲养方式,鸡或猪是否健康,喂了多少抗生素,死亡率多少,死鸡死猪如何处理?
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君子存之。人可以选择做符合道德的事,也可以选择为了健康吃什么不吃什么。我们可以选择吃猴脑,吃兔头,吃狗肉,也可以选择不吃肯德基,不吃火腿肠,不吃方便面。
《吃动物》读后感(五):选择吃什么,是个问题
读完这本书,我迫不及待给哥们描述书中所说的工业化养殖的残酷与无情,也许潜意识在向他贩卖素食主义,也许是出于在乎身边人的健康的缘由。没想到,他一句“呵呵”像一盆冷水把我从头浇到脚,我都来不及颤抖就失去了继续‘布道’的欲望。
弗尔在书中说,‘当然,大多数人在享用肉制品(包括奶制品与鸡蛋)时,都不用去面对关系到宰杀动物这样令人不快的事实。消费者可以远离这些现实,在餐厅享用或者在超市购买鱼、肉和奶酪,这些产品或者是做好的,或者被切成了一块一块,好让消费者不会轻易联想到这些食物的来源。问题正处于此。这样一来,养殖业便能悄无声息地转而用不符合健康标准的,非人道的方式饲养牲畜,大众也不会有所觉察。。。我确定多数人若知道实情,肯定会为之丧胆。’
作者在文中抨击的是工业化养殖而非家庭式农场,文中罗列了大量的工业化养殖的冷酷和无情的一面,追求利润最大化是这种粗暴对待动物的根源,而粗暴对待以及非人道的屠杀和恶劣的养殖环境则是细菌和疾病的温床。同时,广大消费者对肉食的选择是对工业化养殖的变相补贴和支持。
吃什么?也许你说,别人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有选择的权利而你不去做出选择,结果是,你的不选择其实已经做出了选择。
不用纠结于吃肉还是吃素,肉食主义还是素食主义,你无须为自己贴上某一个标签,需要做出选择的是吃健康还是吃不健康,你看,这样就简单多了。每个人都不会选择吃不健康,然而工业化养殖所生产的肉类是不健康的,你还会选择吗?当然,素食也有不健康的,诸如农药残留等等。这并不是说我们最好的选择是啥也不吃,我从来没有增加死亡这个选项。我们要练就的其实是鉴别力,从诸多的市场化食物中鉴别出健康又美味的食物,无论肉类,无论素食。
《吃动物》读后感(六):工业化肉食生产
记录911的小说《特别响,非常近》的作者乔纳森·萨弗兰·弗尔,第一次撰写这本非小说的社科类的书籍。当然他自己并不这么看。乔纳森说,“人们总是期望把书分门别类——小说、非小说等等,可是生活却不能依此划分。生活可以同时是幽默的、悲痛的、严肃的和浪漫的,因此一本想要映射出生活本来面目的书,至少是这本书,融合了生活中本身就存在的这些元素。 ”
《吃动物》这本书暗含了两个前提。
第一个前提是:吃动物并不会推翻人类的食物伦理关系。什么是食物伦理关系?我理解为:人类作为目前地球上最具智能的生物,是有能力也有权利去食用其他的生物,包括植物和动物,以保证自身的延续。也就是说,无论吃植物还是动物,都是不违反道德的。
第二个前提是:动物是食物链的一部分。人类作为杂食生物,既食用植物也食用动物。但人类能食用的植物类别远低于动物能食用的职务类别。因此,草食类动物食用植物、肉食类动物食用草食类动物,无论草食还是肉食,都将植物转化为人类能够食用并得到的更多的营养。
当农作物实现了工业化大规模生产后,肉食动物也逐步进入了工业化生产阶段。例如鸡、牛、猪等。不过这也是本书的一个局限,即对肉食动物在饲养和宰杀过程中不人道的调查与描写,更准确地说,完全漠视这些动物对生存条件的感受、对死亡时痛觉的感受,这在其他的类似书籍上,是可以了解到的。因此阅读过其他类似书籍的读者,在读这些书的时候,难免会有点兴味缺缺。
说回工业化生产肉食。作者乔纳森想集中表明的态度就是这是一种“不健康”的食物生产方式。乔纳森没有标榜素食主义和杂食主义孰优孰劣,而是告诉读者,农作物可以工业化大规模生产(可是现在也出现了转基因),但肉食采用同样的方式则并不可取。研究表明,快速成熟、长肉的鸡、牛、猪等,不禁受到生存环境的影响,也受到宰杀方式的影响,多种因素的累加,其结果就是肉食的味道依旧可口诱人,但是其成分就是不够健康。
不过,人类的饮食文化的确需要思考和审视。比如一日三餐,这是由于人类以体力劳动为主的时候,至少需要三次补充能量,而现在真的还需要吗?比如食肉,以前肉类包含的营养元素是无法替代的,人类需要食用肉类来获取,而现在依旧如此吗?
------------------------------------------------分割线-----------------------------------------------------
(书叔有话说)
《吃动物》读后感(七):读《吃动物》
最近对吃特别有兴趣,加之很喜欢《厨房里的人类学家》作者庄祖宜,在网上搜寻她的博客,发现她参加了一期TED演说:“吃出更好的未来”。她的演说中谈到了禽类的养殖现状,海产捕捞,其中“拖网”这种形式对自然环境造成的伤害等。中间推荐了几本书,其中之一就是《吃动物》,也是目前有简体中文出版的一本。
这本书的全名叫做《吃动物——一个杂食者的困惑》,作者做了父亲后开始思索:我们为什么要吃肉?如果我们知道肉是被如何送上餐桌的,我们还会吃吗?并开始研究大部分肉食的源头,做了大量调查与暗访,集结成册。展示了当前(以美国为主的)工业化养殖业现状,也走访了坚持天然养殖的农户。于我,这本书加深了我的既有观念,也引发一些记忆。
去年在厨房曾经和C有过一段关于素食的对话,当时的我想着,既然不吃动物,也不要吃植物好了,你怎么知道植物不会痛,没有受到强烈的伤害呢?和C聊到这些,她告诉我她是“选择肉食者”,坦诚的说因为喜欢肉的味道,难以做到素食,但是她自己养马,对马的喜爱让她推及所有动物。了解到当前工业化农场是如何饲养动物后,决定减少肉食,并只购买/选择以天然方式饲养和妥善屠宰的肉类。落实到具体生活上,因为这样的“有机”肉不易获得,价格也很高,她选择每周只有1-2天吃肉。当作是一个treat,也是她本人尊重这些生命的方式。
听完后我好一阵思索,这也是我对“选择肉食”播下的种子。后来和农场主J熟悉了,花大把时间泡在农场工作,看着小鸡小鸭破壳而出,感受到和它们的亲密,看着小牛出生,喂食他们,这一切给我的震撼难以言喻。J是我认识最棒的人!她大半生都是素食者,但如果偶尔吃肉,只会吃她亲手饲养的动物。乍听之下难以理解,这些动物可都是她一手养大的,而对她来说这是一种更深的联结。一方面痛恨工业化养殖对动物的残忍,另一方面却明白正是因为人类对食肉的需求,最终也让她可以有这样一片地方,以最小的干涉,天然饲养和亲近她的动物们。big bill是农场的一头牛,当他“时机已到”,屠宰回来后填满了整整一大个冰柜。有人表示伤感,或说不会吃它的时候,J只说,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心的迎接bill将带给我们的力量。
前几天看书时说到日本人吃饭前常说的那句“我开动了”,日文原意是“我从您那里领受(生命)了”。这一解读顿时make sense。同样的,我想到去年在社区吃饭前念的最多的一句祷词,虽说这种形式和宗教脱不开关系,但内容咂吧咂吧却也怀着一股朴素的感恩之情:
Earth who gave to us this food,
un who made it ripe and good,
Dear earth,
Dear sun,
y you we live,
To you our loving thanks we give.
— by Christian Morgenstern
《吃动物》读后感(八):人是动物,而非动物
最初是因为喜欢弗尔的《特别响,非常近》,所以来看了这本《吃动物》。
为了完成这个故事,弗尔拜访了许多农场,结识了许多农人和工厂主。而令他想要去解开自己多年关于肉食和素食的困惑的初衷,来自于他孩子的降生。
“ 此刻家人全都真真切切地呆在我身边,我的研究已告一段落,往后将很少有机会再见到农场动物的眼睛,但一天当中许多食客一生当中数不清的日子,我将凝视着儿子的眼睛。”
这个第六章或者第七章结尾语是一个父亲的担当,尤其使人感动。
这本书里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个细节:
“作为开天辟地第一个人,你在沙漠、泥地或者是洞穴里描绘动物,混合着人与动物的形象,动物既是你,也不是你。”
狮身人面的达芬克斯,双翼蛇发的美杜莎,或者是先秦时期的山海经里的部分形象,挥舞着双臂又或瞪着炯炯双目,身着古典服饰又或赤身裸体,他们被称作怪物,但现今看来,他们只不过是混合了人与动物特征的综合体。
史前时期,人对于本族的观念尚且模糊不清。作为开天辟地的第一个人,他握着手中的器物,沾染着矿物颜料,在自己的穴居的洞壁上第一次试图描绘一个“人”的形象,在一头奔驰的鹿旁边,这个戴着面具的“人”长着八叉鹿角,腿肚轻盈如同羚羊。这个人,是神,是怪物,也是动物。
尽管知晓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种景象,仍然触动了我内心的某个角落。在历史开始之前,人类和动物本来就是从大海而来的单细胞生物共同进化而成的亲兄弟。
《吃动物》通过叙述科学报告结果、工厂写实、不同利益者的不同看法以及弗尔自己的感想,最终立场还是倾向于号召人们杜绝食肉。
我是个杂食者,饭量较少,吃肉不多,但并非能够戒掉肉类,在写这篇读后感之前刚刚喝了两碗肉汤。我能吃下的肉,早已面目全非没有了动物的模样,如果哺乳类或禽类动物未被切块,我是万万吃不下去的。但全鱼,我却可以忍受筷子在其尸体上戳戳挑挑,这倒也印证了书中那个“人类对鱼类天生残酷无情”的观点。
人类的进化得力于第一个摄取动物蛋白质的祖先,百万年来,食肉的基因早已烙入我们的血液。吃肉是本能。我觉得本书中的观点都很在理,但因为素肉少见,我仍会选择吃肉。
如果食肉对地球已造成了如此的负担,与其号召人们素食达到全民茹素的幻想,倒不如努力去发展实验室肉品,我相信,在未来世界,肉类产自培养基,工业化农场这个名字也将成为过去时。
《吃动物》读后感(九):专访弗尔:工业化养殖时代别无选择
1977年出生于华盛顿的乔纳森·萨弗兰·弗尔曾以小说《了了》和《特别响,非常近》中独特的叙事为文坛瞩目。《Granta》杂志将其选为美国最佳青年小说家之一。《吃动物》虽然是一本非小说类作品,却一样有着充满活力的风格和创造性。美国著名女影星娜塔莉·波特曼透露,弗尔的新书《吃动物》使她成为了一名严格的素食主义者。“弗尔的书最大胆之处,在于描述吃动物不但污染了我们的后院,而且污染了我们的信仰。他提醒我们,我们的食物象征着我们所相信的东西。”
在青少年时期,弗尔有时吃肉,有时是素食主义者。成为丈夫和父亲之后,他一直在思考两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吃肉?如果我们知道肉是被如何送上餐桌的,我们还会吃吗?《吃动物》巧妙地结合了哲学、文学、科学和作者的经历,探究了形成我们饮食习惯的一些约定俗成的传说,展现了为了让肉能更便捷地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自然界付出的惨痛代价。《吃动物》展示出了作者强烈的道德感,文笔活泼而富有创新精神,是一部令人赞叹的通俗社科类作品。
你从一位小说作家转而写社科作品,能谈谈写作不同题材的感受吗?
弗尔:写小说和社科作品是两种不同的体验。当你写小说时,你想去感动其他人,无法确定采用什么方式,但写法却更为自由。而在写作社科作品时,你却始终都清楚要遵循什么样的路径。
《吃动物》延续了你一贯的风格,语言幽默且富有创造性,并充满严肃哲理思考。你是如何把这种混搭的风格结合得如此浑然天成的?
弗尔:我想这样的风格并不是我的一个想法、一种技巧,这就是生活,我只是表现了生活本身。人们总是期望把书分门别类——小说、非小说等等,可是生活却不能依此划分。生活可以同时是幽默的、悲痛的、严肃的和浪漫的,因此一本想要映射出生活本来面目的书,至少是这本书,融合了生活中本身就存在的这些元素。
你花了三年时间准备、写作此书,请问在这个过程中,你从中得到了什么呢?
弗尔:这个过程中最触动我的,应该是工业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之广阔,它已经覆盖到了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事实上,在当今的社会,工业化养殖已经渗透到了每一个角落,我们已不可能再做出其他好的选择。
关于吃动物和吃植物的问题,有许多的争议。动物和植物都是有生命的,如果不吃动物了,那么植物呢?
弗尔:其实我在书中并没有提出任何人必须要做某事或不做某事的观点。我只是提出,在我们面前存在着一个非常深刻且重要的问题,而且由于我们本身都已接受并具有自己的价值观和传统,因此几乎每个人都会发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面对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人们会表现出许多不同的反应。我的反应是,停止吃肉;但对其他人不同的反应,我同样尊重。我并不是非常担心吃植物会给植物带来痛苦,因为没有论据证明它们能感受到痛楚,而对于动物,科学已有详细可靠的证明,告诉我们它们具有痛感。
吃肉是一种传统、一种习惯,因此放弃不是一件简单易行的事情。你觉得大多数人有可能会放弃吗?
弗尔:对于一些人来说,放弃吃肉轻而易举,而对于另一些人,却极为困难。这取决于许多因素,比如:你过去习惯于吃什么食物,你的家庭生活是怎样的,你的工作生活是怎样,等等。因此,虽然对我来说,这种放弃相对比较简单,可我也承认,这并非对任何人都是可行的,而且对于一些人,可能还是一种挑战。
考虑到工业化养殖的种种弊端,你认为有什么好的方式可以解决吗?
弗尔:反对工业化养殖的论据是多方面的。工业化养殖危害环境、罔顾动物福利、侵害养殖业者群体,对于全球经济也产生了负面影响。由于弊端涉及范围广泛,因此解决也需要多方考虑,不是一蹴而就的。我认为,小规模的养殖会是一个消除这些弊端,解决问题的较好答案。
你现在是一名素食主义者,而且也影响了一些人。你认为成为素食主义者是一个改变人生的选择吗?
弗尔:毋庸置疑,改变饮食习惯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但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巨大、彻底的改变。相反,我认为,做出这样的选择真正的关键在于——下一餐摆在我面前的是什么?没有人会在任何时候都能做正确的事情,我也一样。但我认为,至少,每个人都想用自己的方式尝试。
□文/利 珠
刊于《时代报》2011年12月19日 总第1925期
《吃动物》读后感(十):肉食的代价
作者 曹东勃
民以食为天。吃,几乎是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的本能,并在漫长的人类进化过程中承载了更多的意蕴,发展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饮食文化。对吃什么、怎么吃、何时吃、在哪吃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不过,《吃动物》一书并不讨论这些问题,而是对两个问题作出思考:我们为什么要吃肉?如果我们知道肉是被如何送上餐桌的,我们还会吃吗?
作为通俗社科类作品,《吃动物》并不试图更为精微细致地阐述理论,而是巧妙结合哲学、文学、科学和作者的卧底经历,突出展示现代工业社会中,为了让肉更便捷地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环境、政府和第三世界付出的代价。作者并不讳言自己是一个素食主义者,但这本书的不同之处恰在于对肉食者的“同情之理解”。
人为什么要吃肉?以色列的演化经济学家奥菲克曾给出一个解释。距今一百八十万年前到两百万年前,人类进入了狩猎和根块采集的时代,实现了由完全的食草动物向杂食动物的转变。即是说,人开始“吃动物”了。这种转变需要有一定的生产技术、社会组织和生理结构支撑。首先,人学会了使用火,降低了消化难度,建立了中心-四周的辐射状采集和狩猎生产方式,告别了逐水草而居、边走边吃的起居习惯,逐渐形成复杂的分工合作模式。其次,食草动物以植物为食,在获取过程中消耗的能源较少,但在消化过程中消耗能量较大——因植物富含毒素,所以食草动物需要相对强大的肠胃来反刍;食肉动物以食草动物为食,并不需要很大的消化器官来分解有毒物质,却需要相对强大的脑来设计追捕猎物。考古学家的发现表明,原始人类大脑容量的骤增与肠胃容量的骤减也大致发生在这一时期。几百万年来,人作为杂食动物,其食谱结构并没有显著的改变。
近二三十年来,一些新生代的人类学家倾向于从性别视角解释这一变化。他们认为,人类的祖先最初是素食者,后来为适应新的环境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发展出杂食的习性。因为狩猎收成不可靠,史前人类更仰赖于采集活动,而女性是早期社会中采集食物的主角。直到后来,关于人性的男性主义假设渐成主流,对“人作为狩猎者”这一形象的描摹遂成标准刻板。男性气质代言了人类这一种别的全部,好战者、侵略者、掠食者成为狩猎时代人类的一张名片。肉类以及肉食行为,具有这种男性主导的意识形态所需要的象征意义——肉是阳性而有力的食物,“真正的男人”就要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相形之下,素食则是女性的食物。肉食还被贴上丰裕与成功的标签,是社会地位的象征,更是好客的标志。
然而,站在今天回望,尽管多数人已欣然接受食用动物是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但根据记载,人类确曾对此所造成的暴力和死亡感到深深的矛盾,并留下各种古老传说。不同的文化架构下,“怎么吃”的伦理规约表现出不同的风貌:印度禁止食用牛肉;犹太教讲究屠宰过程干脆利落;俄罗斯的苔原上,雅库特人声称是动物来一心求死。文明起源于伪装,人们常用谎言遮蔽戾气以自我确证善意的存在。古希腊神谕指示人们,在宰杀动物之前,要在其头上洒水,当待宰动物上下点头以甩掉头上的水时,意味着它点头同意自我牺牲。以色列的传统仪式中,红色母牛为替以色列人赎罪,必须自己步行到祭坛前,否则仪式无法生效。诸多神话的背后,隐含着一种交易逻辑:动物“选择”了逃避自然和自由,投向人类的怀抱并接受驯化,人类向它们提供食物和庇护,而动物向人们提供蛋、奶、皮毛乃至肉体和生命。这种对吃动物行为的慢条斯理的包装和逻辑链条冗长的伦理辩护,早已在诸多文化中沉淀为不可抹去的传统与习俗。
本书作者弗尔并没有满足于从一般的伦理学视角做出素食主义的应然判断,而是通过对若干养殖场的亲身探访和对相关人员的深度访谈,呈现出一些数据和事实。他认为问题的恶化来自于农场的工业化或养殖业的工厂化。从历史上看,这一趋势首先出现在农产品加工环节。早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从美国的辛辛那提到芝加哥,屠宰场、肉联厂就大规模出现了。在这些加工厂中,从宰杀、放血到分解处理各个环节都由专门人员替代了原来经验丰富的屠夫。亨利·福特后来也证实,屠宰业流水线生产的高效率给他以极大启发,他将之逆向运用(从“分解”到“组装”)到汽车工业,引领了一场制造业革命。不过,这种集约化趋势,主要停留在农产品加工领域。直到1923年,美国一位家庭主妇史迪尔开创了现代畜禽产业。史迪尔原本只负责照料家中饲养的一小群放养鸡,而当接到一张五百只鸡的订单时,她并没有回绝。为度过严冬,她将这些鸡关在室内饲养,并在饲料中加进营养补充品,这些鸡在新的喂养方式下存活下来了。十多年后,她饲养的鸡数目就达到了二十五万只。
工厂化养殖业的勃兴,得益于两方面的技术进步:一类是以机械化、电器化、自动化为代表的物理技术进步,自动化喂饲、供水、温控、灯控和风控,使禽类养殖更为密集,生长周期也大为缩短;另一类是以基因工程为代表的生物技术进步,通过在饲料中掺杂药剂和抗生素刺激生长、抑制疾病特别是控制变异。1946年,在美国农业部支持下,举办了“明日之鸡”竞赛,目的是选拔那些以少量饲料培育出拥有肥厚胸脯的鸡。1950年代,蛋鸡与肉鸡在功能上开始分化并被分类“培养”。
政府的角色也悄然发生着改变。1928年,美国总统候选人胡佛喊出了“丰衣足食”的竞选口号。随后的罗斯福新政更是在世界范围内引领了一轮政府干预、支持和补贴农业的新风尚。大量生产、大量消费,这被认为是通往丰裕社会的幸福快车的两个轮子。诉诸价格扭曲的方式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和生产热情,以科学技术的进步支撑产能的扩大,成功地创造了半个世纪以来食品帝国的奇迹。一方面,食品价格相对于其他产品价格的变化速率是缓慢的,肉价亦是如此;另一方面,一场以农民进城为核心特征的全球性人口流动和城市化浪潮大幅减少了全球范围内的农业劳动力,在一些国家,农用土地的数量也在减少。
城市消费需求的增长、养殖成本的增加与肉价的平稳,这三者合力将传统的家庭式农场引向工厂化经营的新路,规模化成为迫不得已的选择。只有不断扩大养殖规模、增加动物产能、降低成本,才可能获利,这是最明显的经济理性。一个从前只需饲养五十头牛的养牛场,如今至少要饲养一千多头牛才能生存。小规模的家庭式养殖为求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不致倾覆,也多相互合并组成专业的畜产合作社。以工厂化养殖方式出产的食用肉占据消费市场的主流。在这种激烈的现代竞争中,工厂化养殖业最关心的是:如何让牲畜在短时间内更快地生长、如何节省畜养空间、如何最富有效率地喂食牲畜——使之多食一分则浪费、少食一分则不足。
工业化武装了农业,一切看起来很美,全球肉食者数量飙升至空前高度,越来越多的人却开始追求返璞归真。养殖方式的急功近利甚至已引起行业内部的巨大不满。弗尔采访的一位传统鸡农告诉人们:“你在超市购买的火鸡没有一只能够正常行走,遑论跳跃或高飞了。它们甚至无法自行交配……火鸡腿是否应该再短一些,膝盖骨应再缩小点?人类偶尔产下畸形儿,我们不希望下一代重演悲剧,却对火鸡这么做。”饲养肉鸡的第一个星期要二十四小时施以照明,促使其多吃饲料。随后再减少照明,一天熄灯四个钟头,借以调教出鸡的最短睡眠时间。这些工厂化养殖的速生肉鸡,在人为控制的环境中,长期处于非正常的作息状态。长久的照明、狭小而污秽的空间和病菌感染的高风险足以令其身心大乱。
由于畜禽养殖效益比较低,管理不严,绝大多数养殖场没有污染处理设施,将畜禽粪水直接排出,其所含的病原微生物和有机氮等,常常会造成土壤和水质的污染。一个本土的案例是,广东东莞市以行政手段从2009年1月1日起,全市禁止养猪。应当指出,“禁猪令”的出发点是治理养猪造成的环境污染,这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城市对大规模的现代养殖业的挤压和傲慢,但也的确戳到了命门。这之后不久,网易公司的丁磊就宣布进军养殖业,希望探索一种新的无污染养殖模式。这个事件多少反映出中国消费者试图挣脱这既不安全、又同质化得有些乏味的现代食品体系,另觅新路的渴望。
工厂化养殖的间接后果是全球谷物消费结构的重大变化。深度卷入现代市场体系的养殖业成了推动现代农业——特别是种植业结构调整——的一大动力。在美国,大多数的牛奶是工厂生产的。农民为奶牛而种植庄稼,收获庄稼,将它们切割成可入口的碎片,然后饲喂奶牛。悉心关照动物、在意食物生产来源的传统农民形象已成为田园诗般怀旧情绪的一部分,如同以往打电话时负责传声的接线员一样。以机器代人力的“看不见农人”的农场,是工业逻辑下农业发展的归宿。
农业服务于工业、种植业服务于养殖业、低附加值服务于高附加值,这似乎是一条市场铁律。美国有近百分之七十的谷物,是被用来饲养牲畜的。不独美国,一些刚刚解决了“人的口粮”问题的发展中国家,面对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提高带来的消费结构升级,也不得不立即又投身于满足“猪的口粮”、“鸡的口粮”等饲料用粮的新战役之中。当地球上有近十亿人口处于饥饿状态,人们还将近一亿吨的谷物和玉米制成生物燃料时,联合国特使就声称这种行为是“违反人性的罪行”。而养殖业每年耗去七亿五千六百万吨谷物,又该当何罪?素食主义者就此将矛头尖锐地指向工厂化养殖业与肉食者。他们指出,食肉是获取能量效率较低的一种方式,用来喂养牲畜的所有谷物可以喂饱五倍数目的人。大规模的肉类制造业吸收了庞大数量的各种形态的原料和能量,却只生产相当少量的成果给人类,就生态、营养以及热量而言,是得不偿失的。而在享受这种相对“奢侈”食品的同时,对全球性的饥饿坐视不管,这种食品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上的严重失衡也是一种不能容忍的现代性病症。
这种现状应当如何改变?《吃动物》的作者显然非常矛盾,这大概也是一切素食主义者会普遍面临的困境。弗尔多次提及他的外婆在二战期间躲避德军的故事。在那种恶劣的生存条件下,一个俄国农夫从屋子里拿了一块肉给她吃。但她拒绝了。“为什么?”“不为什么。”“因为不符合犹太教规?”“当然啦。”“就算能靠它活命都不吃?”“如果什么都不在乎,何以值得挽救?”弗尔将很大的希望寄托在这种宗教的规约或道德的自觉,希望在“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主体性的现代社会,改善农场动物的遭遇。很多素食主义者也采取求诸己的方式,认为只要个人茹素,总能点滴改善、星火燎原。他们热衷于从抽象的比较人性与动物性的哲学论辩中,发掘人对动物的怜悯之心,进而伸张动物权利、保障动物福利。这些缺乏历史维度的主张,在高度物化和商业化了的消费社会、在“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现代经济系统的铜墙铁壁面前,显得软弱无力。
《吃动物》并没有描绘一个大圆满的结局。在人口膨胀、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当下,有机农业、生态农业、家庭式养殖,只能是规模化、集约化、工业化改造传统农业过程中偶尔泛起的几朵浪花,表达了消费者对现代农业系统的不满。其改弦更张,却非一朝一夕之事。后现代的都市人将自己对现代性苦痛的纠结和抱怨移情于乡村。城市中的动物福利组织成员,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实际上都在某种程度上宣扬和代表了某种传统的农村价值:敦亲睦邻、天人合一、爱恋土地、尊重生命。但世界已然改变,在新世界中,一句“何不食素”的反诘恐怕并不比昔年的“何不食肉糜”高明多少。
这种几乎是在两个“平行空间”进行的“鸡同鸭讲”的“穿越”,有时是无心之过,有时则是有意为之。北大的姚洋教授曾有这样的亲身经历,当他在威斯康星读书的时候,与一位美国同学讨论环保问题。该同学建议中国人不要学美国,不要用冰箱,那样会毁坏大气层。姚洋就问她,如何储藏东西呢?该同学的建议是可以用地窖之类的前现代手段替代。姚洋又追问,那你们美国人呢?该同学的回答是,我们美国人已经养成习惯了,没法改了!这类双重标准、富贵病和伪道学,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着。而对素食主义这个话题,所能做的,恐怕还是经济的归经济、文化的归文化。生产方式中的现代弊病,很难以生活方式或个人偏好的简单转变来救治,它更有赖于制度的建设性改良和经济的可持续成长。从这个意义上说,《吃动物》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预先思考的好问题。■
(刊于《东方早报》2012-0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