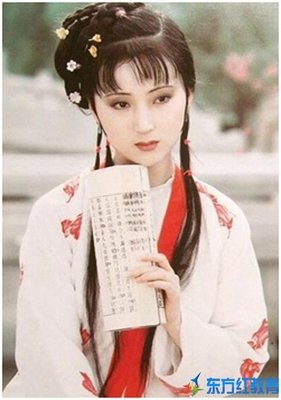《門外漢的京都》是一本由舒國治著作,遠流出版出版的平裝图书,本书定价:NT240,页数:19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門外漢的京都》读后感(一):浮华清欢皆在此城
如果一生只能去日本一次,如果一次只能去日本一个地方,那无可置疑必定是京都。舒国治也是悠悠地把京都当做他人生的第二居所,小住小憩,酣睡暴走,万事浮华不如清欢的样子。这本《门外汉的京都》与其说是京都游记,其实更像是讲述与京都的机缘和晃荡京都的禅理。
面对书中耳听为虚的京都,也许自己眼见为实的东京倒像是一种自我心理安慰。现代化的大都市总有着相似的面容,东京也毫不例外,也许在东京看着吉野家和无印良品,能找到与在上海同质化的安心熟悉感,却无法怀有那种异国他乡所独具的微醺略醉的风情。然而只有书中描述的京都那样的地方,可以随便挑一个角落,一片景出来,即便是一堵长长矮矮的围墙,岚山上的一个院落,古寺庙门外的匆匆一瞥,颇具江户川风情的街头小咖啡馆,便像是包含着和风清韵的整个宇宙一般。
有时甚至很不怀好意的觉得,对于《门外汉的京都》所有的喜好,或许全源自于对于京都的热爱,这种热爱极具恹恹的挥发性,只要从京都的一景缘起,便可以铺陈到整一本书的字字句句和自己心中,京都的旅馆、京都的手袋、京都的长墙、京都之吃、京都的黎明与晚上、京都的气,皆是融华丽同简朴于一体的丝丝入扣。
“事实上,京都根本便是一座电影的大场景,它一直扮演着古代这部电影,这部纪录片。整个城市的人皆为了这部片子在动。”这也许是我看到过于对京都最好的描述了,整个日本,原本散发的就是一种气氛,京都尤甚。它是一个像你在看电影的城市,种种光影弥漫和移步换景,一个像舒国治那样的旅人,便不自禁地做了京都不登堂入室的门外汉,望着那些数不清的世代和过着深刻日子的人家,自知容不得打破和入侵,便自觉保持着一份矜持的距离。
此前看《水城台北》时,便感叹舒国治那一种对细节的孜孜不倦的个性,甚至愿陈列一切枯燥的细枝末节,以换得对记忆和怀想的一份殷勤不变。人心中怀有太急切的热爱和热情时,做事情往往易走极端和偏锋,可却并不想用此来形容一次次反复前往京都晃荡的舒先生,生而为人,又有几个可以为着自己一份执念而亲历亲为的呢?不过是都在迷失现实和虚构远方罢了,更不用说游历之后厚厚一本赞歌,与其说是充满滥美之情,或许更是自己对京都的一种不解情缘妄图阐释吧。
这世上有很多种游记,攻略型的、散文型的、广告型的,又或是体验描述型的,可是无论哪一种,都比不上若隐若现的那一种撩拨人心,像是京都寺庙一扇半开半合的门,满园春色只得半数入眼,怎能叫人心不瘙痒,脚步不犹疑呢?
也是为着此,怎么甘心一生只去一次日本,去日本只去一次京都呢?
原文BLOG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6f39a41c0100rpzr.html.html
《門外漢的京都》读后感(二):梦里的京都
如今我对于京都,就像幼时对于苏州,充满了绮丽的幻想,想象着那种充满东方韵味的意境和生活氛围。
是看《源氏物语》的时候喜欢上了京都,然后又看川端康成的《古都》,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京都寺庙的枯山水,秋天的红叶,再看林文月的《京都一年》,但终究没有亲眼见到京都,不知道京都到底长怎么样,透过舒国治的《门外汉的京都》,就好像打开了一条门缝,又把京都偷窥了一番。偷窥得越多,就越想到京都去亲眼看一看。
这是我看的第四本舒国治的书,对于舒国治那种闲适的生活情调和语言风格自然是极喜爱的,多少次也想着像舒国治那样生活,希望将来不至于成为憾事。
舒国治写到的京都,确实都是我想象中京都的样子。“有時我站在華燈初上的某處京都屋簷下,看著簷外的小雨,突然間,這種向晚不晚、最難將息的青灰色調,聞得到一種既親切卻又遙遠的愁腸。這種愁腸,彷彿來自三十年前或五百年前曾在這裡住過之人的心底深處。”这份愁肠,我想如今也正郁结在我的心里。
舒国治说他去京都,为了那一份唐宋韵味,为了竹篱茅舍,为了村家稻田,为了小桥流水,也为了大桥流水,为了氧气,尤其是为了睡觉写得最精到:“每天南征北討,有時你坐上一班火車,例如自京都車站欲往宇治,明明幾站,二十多分鐘的短程,但只坐了一、兩站,人已前搖後晃,打起瞌睡來,坐著坐著,愈發睡熟了,幾乎醒不過來,實在太舒服了,突然睜開眼睛,只見已到六地藏了,急急警惕自己馬上要下車了,但仍然不怎麼醒得過來,唉,索性橫下心,就睡吧。便這麼一睡睡到底站奈良,不出月台,登上一輛回程之火車,再慢慢往回坐。”这一种遵从造化,无期无为,随遇而安的境界古往今来又有几人能达到?
还有,舒国治写到的京都,寥寥数笔就好像让读者亲见了一般:“一入夜,大夥把燈光打了起來,故意打得很昏黃,接著,提著食盒在送菜的,在院子前灑著水的,穿著和服手搖扇子閒閒的走在橋上的,掀開簾子欠身低頭向客人問候的,在在是畫面,自古以來的畫面。”这不正是我脑海中想象的画面!
总之,我觉得这样的京都,越来越不真实了,除非是在梦里,不知何时能亲见梦里的景象。
《門外漢的京都》读后感(三):舒国治: 晃荡见真淳的行者
台湾一本新创刊的杂志《小日子》的发刊词是:“走进尺度亲切的巷弄,寻找远离大街的迷人小店,这是我们喜爱的城市生活”,我一看,不由叫出了声:多么舒国治的生活!是的,很多时候,舒国治在我心目中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晃荡游走于寻常巷陌看街景、找吃食,甚至只是在河边望天打野眼、呆坐或负喧的闲散野逸的生活。
前不久在孔网上淘到《纵横天下》,喜不自胜,里面收录了舒国治获长荣旅行奖首奖的作品《遥远的公路》。可以说,正是这篇作品开启了舒国治旅游文学的滥觞,有了它,才会有后来的《台湾重游》,才会有后来让他暴得大名的《理想的下午》和《流浪集》,才会有掀起台湾京都旅行热的《门外汉的京都》,才有后来我称之为“舒氏乡愁三部曲”的《台湾小吃札记》、《穷中谈吃》和《水城台湾》。
我初次接触舒国治,其实是从网上先读到他发在《联合报》和《中国时报》副刊上的千字旅行小短文,惊艳不已,他所写的不外是喝茶、吃饭、睡觉、走路四事而已,在读多了文化大散文式的空洞旅行文字以后,读到这等亲切扎实的文字,悠然兴起旅行之思,哪怕就是钻进所在城市的巷弄看看此前未留意的东西,也大有趣味。喜欢舒氏散文,首先与其别具一格的文字风格有关,他的行文遣词文白夹杂,有一种盎然的古韵古意。“英国的全境,只得萧简一字。而古往今来英国人无不以之为美,以之为德;安于其中,乐在其中”,“青莲院……几乎有中国武侠小说中的邈远意象”,“有时想想,人的一生,便在这一杯茶与一泡尿之间度过了”……顺着这些字句的藤蔓,就进入了舒氏充满逸趣的世界。事实上,他在《遇上便吃》中风流快意的笔墨,读来令我神往,宛如六朝人物的潇洒举止:
“路边见有现榨甘蔗汁,喝一杯。碰上北方小馆,有小米粥,喝一碗。偶见老式冰果店,倘洁净,吃一盘木瓜,看到老头子卖烤红薯,买一个,或即吃,或携家吃,甚少见推车售茯苓糕矣,偶逢,买两三块,自吃,也送人,乍然发现一硕果仅存烧饼店(黄桥烧饼),购二十个,自留数个,余送人,按铃不在,置信箱内……”
自从读了《理想的下午》和《流浪集》,我就成了铁杆的舒粉,逢人就推荐他的文章,甚至和朋友在某网上建立了“门外汉的舒国治”小组。不过从网友的反馈来看,对“舒氏散文”极爱和极厌的都大有人在,爱之者如我赏其文字,迷其字里行间体现的一种浪游的生活态度,而厌之者认为他的文字读多了,总觉得流于轻逸,感觉软腻浮滑。他所谓悠游晃荡的人生,太易被人看作是对自己品味的自矜自夸自诩,又在出版商的炒作下,无意中成为小资品味的代言人。我认为另一个原因是讨厌的人往往只读过舒氏的这两本书,还没有读到他此后所写的几本书的缘故。将他看作是一波文化炒作的产物,反而是错过了舒氏散文的好处。
事实上,我最喜欢的舒氏文章,正是这后面的几本。它们没有了《理想的下午》和《流浪集》中自己旅行和人生品味的稍微过度的标榜和炫夸,而体现出他更为本真质朴的一面。而且,我觉得像《台湾小吃札记》、《穷中谈吃》和《水城台北》虽然仍然谈的是他的经历或他的回忆,但是这种经历和回忆,由于体现出一种时代氛围,因而超脱了个人品味的炫示,而形成了一种对“宜居城市”、“宜居生活”的看法。表面上看,《台北小吃札记》无非是对台湾各地(最主要是台北)的美味小吃的罗列,事实上,舒国治的野心在于以小吃带出一个城市和城市中人的风貌。《台北小吃札记》之所以写得好,不仅写出了六十七家台湾各地小吃店的味之美,也写出了经营者的风貌,一种对饮食不敢马虎,对人生不敢马虎的态度,此外透过小吃写出了城市的底蕴和气质。饮食之美,说到底是人情之美,所以他说:“小吃的佳美,透露出城市里人的佳良。事实上台北之好,主要是人与人的关系密切,人情最温热,最喜被照拂也最喜照拂别人的体贴。”这人情之美,见于“鼎泰丰”给客人找钱总是找新钞,见于南机场推车烧饼全露天的手工制作,见于刘妈妈担担面的老板娘对吃饭的白领女孩说“小姑娘,今天想吃什么”的殷殷问候中,见于永康街Truffe One手克巧克力“九蒸九晒”的熬糖工序中,见于秦家饼店的干烙式葱油饼恪守旧制、细揉慢火烙的慢功夫中……对小吃的热爱,背后体现出一种追求清简、鲜美、洁净、不尚奢侈的平民旨趣,而舒国治的晃荡游走在大街小巷,追寻一家家佳美的小吃店,无疑正是对这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的实践,实在与人们所说的小资代言人沾不上边。
《台北小吃札记》、《穷中谈吃》和《水城台北》可以说是舒国治的“乡愁三书”,前两书是“吃的乡愁”,《水城台北》是对一个阡陌纵横、河道密集的田园台北的乡愁。这三本是回忆之书,回忆台北城市五十年发生的巨大变化,他最大的一个感慨是并不是好的东西一定会流传下来,大到一个城市的田园风光,小到一个优质小吃店,都很容易在时光中湮灭星散。而在这背后,反映出的是人们饮食观念的变化,而这些变化通常是往陋劣的方向发展,表明人们对“吃得好睡得好”等基本的人生大事不再有起劲的追求,也就是对活着这件事苟且了事。《台北小吃札记》、《穷中谈吃》、《水城台北》等诸书已经对此有深切的提醒,因此,于我而言,它们是当代版本的《东京梦华录》、《梦梁录》或《扬州画舫录》,美好的回忆底下总有一股惘惘的忧伤,因为太过于美好的、清简的生活品味,总是在社会的大发展大进步中丧失无遗。
舒国治所谓的理想的城市和理想的生活都带着点农业社会的传统古意,而寿岳章子笔下的京都,大概是他心目中最宜于生活、最适于晃荡的理想城市,所以他为此写了一本《门外汉的京都》,引发一股京都热。他在《理想的下午》一文中提出的构成理想城市几个要素:理想的河岸、理想的街树、理想的街头点心等等,在京都皆有着完美的体现。
在舒国治笔下,京都有说不尽的迷人,比如它的木造旅馆,带给人一种丰润的感受,比如它的走来走去走不尽的长墙,它清幽的黎明、曼妙的夜晚,像时代剧背景的街巷和干活手艺人,构成了宜居宜行宜住的悠闲城市。对中国人来说,京都更迷人的是它无处不在的唐宋氛韵,“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日暮掩柴扉”等中国古诗的意境,唯在京都才能透彻体验到。京都迷人的还在它的田园特色,“都市中竟还能见到稻田,也就是田园的风光能与都市设施并存,表明城市之清洁和良质,也透露出城市的不势利”。
舒国治记录下了一个城市最本真最质朴的生活,这种生活清简、恬淡、闲逸,在当下营营役役的都市生活中显得何其奢侈、珍罕,又多么值得追求。所以我每次读到舒国治谈他心目中的理想行业,除了无条件认同之外,真的有照着做的冲动:“若有一个年轻人,不想再忍受上班,决心每日烘三百个葱花面包,下午三点出炉,六点便全数卖完,再如主妇每日中午将精心调制的五十个便当拿到公园卖,半小时卖完回家”!
多么潇洒,又多么的不切实际。但是,这段话就算不能让我付诸行动,大概也会提醒我,想一想自己的生活,真的是自己想过的吗,真的没有改变的可能?李安说:“舒国治的文字与情怀不时地提醒我,在岁月飞逝中,我们生活得有多粗心!”舒国治的书,至少为我提供了营营役役的现实之外想像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能让我不时去反观省思自己的生活和人生,我想这大概就是舒氏文章最大的功德。
《門外漢的京都》读后感(四):京都的门外客
“怀此颇有年,不敢问来人。”
第一次读这本《门外汉的京都》是2006年。读完之后最记得三件事:第一,舒国治先生真是游荡的高人,玩得妙、写得雅;第二,京都好似一派清冷之色,虽然是妙,估计得安安静静地去玩;还有一件,就是他在书扉页上自己用两句诗拼出来的这一个对子。上句是陶渊明先生的句子,下句却从是从唐诗里截出来。两下接在一起,写在素色的扉页上,仿佛能在唇齿之间念出无限情怀。
再然后,再然后这书里写的京都风物就约莫剩下朦朦胧胧、灰色的影子,像秋季清晨树林上的那一抹水雾,在读书的年月里头慢慢飘散。偶尔这影子在心头荡漾一下,挑拨起去京都游历的念想。
几番周折,终于等到了真的要去京都的这一回。我把这本书从书架上取下来,仔细放在行囊里。带着它,也不翻看,施施然从京都走了一圈回来。唯有远离了京都之后,才重新翻开细读。这样一来肯定要错过一些在书里面写过的茶屋、庭院,还有那些藏在巷子里面的旅舍——可是又别有期待,看看自己能不能和舒先生喜欢的美景和心情在京都偶遇。
最先遇到的是京都的雨。“雨天,属于寂人。”旁人都在匆匆躲雨,他却在那寥落大雨中觉得天地静好,何处也皆去得。回想起旅途中我在知恩院山顶佛堂的山门处的一场淋漓大雨,还有龙安寺枯山水前的密雨飞丝,彼时彼地的清静之意从指尖悠悠流过。
看他写京都的竹篱茅舍之美,“竹径有时风为扫,柴门无事日常关。”——唐人的句子被舒先生用在京都的民舍和小店真是十分贴切。白墙乌木,这在高台寺附近宁宁之道上的清凉色调,正是他眼尖从小津安二郎在《彼岸花》里面的一两个貌似漫不经心的风景。还有京都的渍物、豆腐、京果子、抹茶和加了麦芽糖的冰镇姜茶,哪怕是平常食物,京都的美食一样细密精致。还有他写二年坂、三年坂的坡道,两旁是帘招洒然的店家,古风盎然,一不留神就错过的青龙苑是树、石、泉、茶室错落有致的上佳美景,恰恰围在几家店家之内,偏巧也让我们遇上了——在京都游荡时的清淡心情,在到千里之外的书房又找到了应和,甚至是更有雅韵的短歌。这份快乐只有看舒先生写古都名城才有。
理所当然,没有来得及“偶遇”的京都美色远在这四日行色匆匆的光阴之外。好比岚山的竹林,黎明在大泽池边的古琴,宇治川边菊家万碧楼上看寒风碧水的旅居心情,嵯峨野村家的白色长墙......舒先生在京都摸索了十几二十次的感受总不能妄想在四天就能尽得其中妙笔吧。可他还是自称为京都的门外汉。
“门外汉者,只在门外,不登堂入室。事实上太多地方,亦不得进入。如诸多你一次又一次经过的人家,那些数不尽的世代过着深刻日子的人家。你只能在门外张望,观其门窗造型、格子线条,赏其墙泥斑驳及墙头松枝斜倚、柿果低垂之迎人可喜,轻踩再他们洒了水的门前石板,甚至窥一眼那最引你无尽向往却永远只得一瞥的门缝后那日本建筑中最叫人讚赏、最幽微迷人的玄关。” 等到我也把京都都踏遍的时候,我大概才能真正体会舒先生写这段话的心情。到底京都虽美,可都不是我们的。无论是唐人的风流蕴藉,还是后人的隽永细腻,如今我们竟要特地到这异乡来体会了。“人生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舒先生在曼殊院里面看到良尚亲王留下的笔墨中抄了一句刘禹锡的诗。如此心情,正是古今相同。
《門外漢的京都》读后感(五):在京都,緬懷一個消逝了的中國
舒國治說,京都,他已反覆游覽過許多次,可多年來,「每興起出游之念,最先想到的,常是京都」。日本,對華人,總有莫名的吸引力。
華人訪日,於路所見,不論市井巷弄,或是山野古剎,入目的第一眼,常是驚鴻一暼的驚艷:除了為眼前景之精致優雅而驚訝外,更有一分似曾相識的親切感。這分親切感,為東亞人所獨有;西人游日,雖亦識貨,如斯嘉麗約翰遜在《迷失東京》中,賞看櫻花爛漫的園林,醉心僧人虔誠的唱誦,他們畢竟很天真,他們的感受,少了這一層厚度。
按舒國治自己的話,他去京都,「為了沾染一襲其他地方久已消失的唐宋氛韻」。唐詩中古代風景的形像化,往往在京都得到印證。如杜牧: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
京都的寺廟,三步一間,五步一座,為數不下數百,「南朝四百八十寺」,恰可作京都的寫照。又如書中所述,王維詩中常出現的「柴扉」(如「日暮掩柴扉」),他處早已不存,京都亦多見。甚至所到的許多寺廟中,直接題有漢字的詩句,詩中所寫,又常與寺內或周邊的景致相映襯:「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或是「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風雅之余,亦似在提示游者,兩個東亞近鄰間千絲萬縷的聯系。
什麼,閣下以愛國的中國人自居,是反日的?殊不知日本,其實就是中國 —— 是凝結在唐開元年間的,一個仍還很優雅,在國際上仍還備受尊崇的中國。一如《大長今》裏的服飾官名總讓人聯想到鄭和與張居正的時代,日本的一切,從寺廟建築到盆景插花,保留了太多的盛唐風韻。而那麼多,在中國的土地上,都煙消雲散了,如春夢般,了無痕跡。身為中國人,在早已異化的故鄉生長,唐詩裏的落梅與柴扉,在意識中沉睡。直到有一天,你第一次踏足京都。
當你終於明白,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傳統,已庶幾摧折殆盡,而所剩下的一點,竟爾殘存在一片異國的土地上,你會作何感受?一個華人,佇足京都古樸典麗的唐式寺廟門外,迷醉於其樓閣之美輪美奐,其氣質之幽清素雅;更咬牙切齒地想,此風本屬漢唐,而今竟非為己有,殘陽斜照,斷鴻聲裏,無限春風恨;曰不如歸去,卻又諸般流連不舍。對日本,這一份既慕且恨、欲去還迎的復雜情感,那些高呼保釣、四處打砸的憤青,又有幾人能體會?
揭開《門外漢的京都》,你看到了插圖中,京都的尋常巷陌。那斑駁的青色磚瓦,隱隱地是那麼熟悉。它讓你想起了你的家鄉蘇州,那河道兩旁長滿青苔的舊屋,和公安在那百年的老牆上,用亮得扎眼的白色,漆上的那個大大的「拆」字。那一晚,你獨自坐在天台頂上,望向一座又一座的高樓,和一處又一處鋼筋混凝土的建築工地,想了很久很久。水村山郭酒旗風,水村山郭酒旗風,淚眼朦朧中,你一遍又一遍地默念着,不知為什麼,怎麼也停不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