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春的猫
高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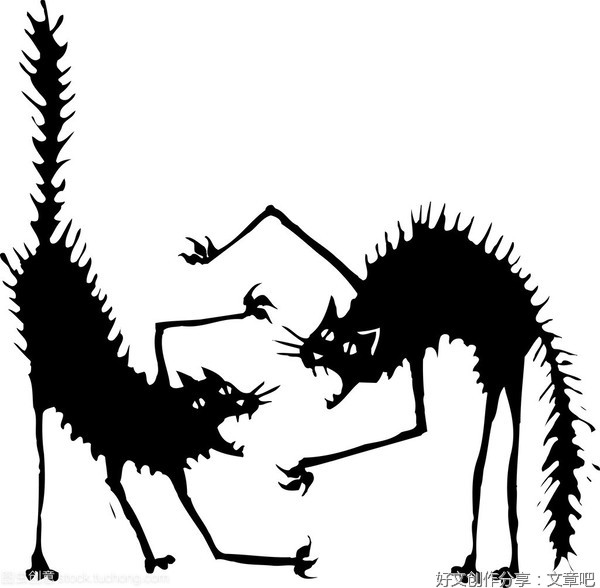
春意如潮,漾漾千里。然而东风无力,刚探出暖融融的头,就被朔风逼退了回去。春便如猫咪般不甘地伸挠爪子或腾挪身子,贴着人们的身子蹭来蹭去,人身便沾了一抹暖意。随后的天气便接二连三冷一阵暖一阵。
我很喜欢猫,但我却无法包容叫春的猫。它们怀春时也要闻令而动,恰在立春过后,集约而来。那时天地之间,万猫齐喑,似哭似叫。有的如撒泼的孩子边在地上打滚,边鼓噪出一股不得不引人注目的声势;有的则如悍妇骂街般相互对骂,声如裂帛,刺立而虐心,给四周造成一股强大的威慑力。而这些正值雄性激素迸溅期的男猫,为了一只女猫或是双雄对决,或是三雄鼎力,彼此脊骨耸立,尾巴爆炸,歪头侧目,一步步逼近对方,另一方也正步步为营,跷勇迎战。双方时常是对峙如山,时刻有压倒对方的势头。在一决夺胜负时,它们或许没想到竟遇到了与它同样彪悍的对手;有时多只猫相互厮杀,那场面则如打群架的敌我两伙。
一连多日一群猫不约而至,为爱情上演一场场争风吃醋的大战,在院子的平房上或是墙头上,不分日夜,你追我跑,叫嚣不止。这样一来本寂寥素常的生活因这些叫春的猫的闹扰,像速开的热水,沸反盈天后又顷刻归于一种情去缘灭的死寂。
每次听到外面猫声鼎沸,伊娃就从自己的小窝窝里爬出来,懒洋洋地跳到窗台上,两双棕色的大眼左顾右盼,那情境像资本家小姐站在洋楼上观看贩夫走卒在花街陋巷里投机专营,你吆我喝,明争暗斗。观后伊娃一脸不屑:这世界的纷纷扰扰与我有何干?她却不知,当她站在窗台上看热闹时,有别的猫就站在对面的房顶上观看着她。或许那些猫对伊娃正心怀恻隐,因对它们来说这世上没有什么比剥夺了生育能力更要生无可恋的了。
我却从没觉得绝育后的伊娃与之前有什么不同,傲娇故我。曾经那些怀春的日子与她不过是恍若隔日。如今一身寡欲的她反倒要可怜起这些情感泛滥的雌猫,在它们浑然不觉沦为一群雄猫泄欲的工具,成为一妻多夫后还要稀里糊涂担起一母多子的生育机器,为了子息不孤而繁衍众生,年年不息演绎着一轮轮尘世孽情。伊娃冷傲的眼神说明她不屑这泱泱猫界的所谓凤友鸾交,已与猫类分别为圣,或已超然物外。正如人类社会崇尚着从一而终的单夫只妇,和合双全的两情模式,若非如此就是掺杂了交易和利用的情感,如当今社会各种的骗婚和买卖婚姻。
伊娃从窗台跳下来时,抖擞了一下身子,瞬间白黄黑三色花像一团盛开的锦簇,柔软而亮丽,让我仿佛看到了开在春天里的一朵风信子。
或许是长期的养尊处优慢慢软化了伊娃的一身芒刺,她学会了与身边人保持远者不怨,近者不逊的距离。并与自己曾经不堪回首的过去和解,那个因不断地生育导致她丧失了所有的乳头,还一度营养不良的过往。她当然不知道自己的过去与人界这几天热议又义愤的丰县小花梅的许多处境竟如此雷同。除了啼饥号寒备受屈辱地活着,非猫却胜似野猫的小花梅还要无限可能的机械地重复着繁衍生命。这点伊娃要比她幸运很多。
但愿伊娃能以豁然之态祭奠曾经不堪的自己。还好有我,及时止损她的猫格,护她度过余生的安暖。然而小花梅呢?即便有人帮她验明正身,追根溯源还她一个真正的家,但她又怎能摆脱八孩之母的职责和重负呢?伤痕累累的她所得到的心灵慰藉都不及伊娃一次绝育后的涅槃重生来得实在。
人世间的春天从来都没迟到过,疆土下春潮在涌动,天地间万物在复苏。并不是因为有猫在叫春。只是那些如冬虫还蛰伏在地下暗无天日的小花梅们的春天,需要具有灵性良知的人来唤醒。届时这世间的春天便“欣欣然张开了眼”,
我一直喜欢猫,可是唯独不喜欢叫春的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