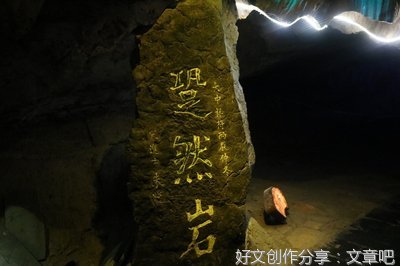
关于生活我是这么看的:它实在的部分人们知之甚少,大家更多是有许多观感。不同的观感决定了不同的理解,这些理解之间彼此可能并不兼容。小时候对生活的观感要好一些,那是因为把目光聚焦在了生活的某一边,人又带着无限好奇心。在好奇心之下,无所谓善恶高低,只考虑是否新鲜。带着这样的心态去观察,生活的这一边看到的都是鲜花似锦,绿草如茵。
等人成长起来,目光转向生活的另一边,自己也走在路上,双肩承受越来越重的分量,观感就会完全不同。想来那些风景区的挑夫,并不会在工作间隙感受到什么风景。长途汽车司机在远途,也并不会觉得长路迢迢,无尽奔行中有什么浪漫或者寂寥。倒是能看到许多苦和累,于是就看到了生活的另一边,近处是燃烧的火焰,远处是没有颜色的黑。
生活本身没有说话,也不曾装扮自己。但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生命时期,看到的生活完全不一样。如果仅只是停留在观感的变化也就罢了,可惜是个人就会心随境转,感受和心态也会随之改变,有时候觉得阳光明媚,有时候又觉得凄风苦雨。而且,很容易坚信当下的感受就是真实,就是全部,就是永久,生活就会这样无尽地延续下去。
所以总有人说,建立内心的平衡很重要。怎么理解这个平衡?要我说的话,那就是两边都看看,看完两边走中间。不曾发现地火岩浆,这样的人怕是过于天真,等偶然接触到生活的真实会难于承受,觉得都是幻觉,都是破灭;不曾发现鲜花绿草,这样的人怕是无法快乐起来,靠着否定行走人世。否定并不是因为理性判断,只不过赢面比较高,人就喜欢上自己是正确的这种感觉。
大多数人应该在这两边之间来回晃荡,心境也就在正面和负面之间来回切换。在这晃荡和切换之间,有天可能幡然醒悟哪一边都不对。无论自己喜欢还是厌恶,生活自顾自地运行,全然不会理会人们是什么想法,什么观感,什么判断。生活对正确和错误没兴趣,对真理和谬误也没有兴趣,它只安排日出日落,架设好舞台,然后就退隐到观众席上。等着我们在舞台上找寻剧本和线索,扮演自己认定的角色,猜测生活的意图,在狂喜和失望之间来来去去。最后,等我们终于精疲力竭,才意识到生活对每一个人都无动于衷,这时候反而感觉会好一点,因为自己并不特殊,所以生活也就不曾特殊对待,那么一切起伏变化之中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针对和特别的安排。
人们总觉得生活要比命运柔软一些,因为在生活中自己可以做许多选择,可以采取许多行动,因此自己对生活比命运有更多掌控。要我说这两件事其实相差不大,行动的区别无非是扛着一把躺椅走进生活,还是穿上隔热服戴上面罩走入生活。如果生活并不是鲜花绿草,也不是烈焰岩浆,所有这些行动也就失去了意义,并不比和不可知的命运抗衡高明到哪里去。所谓在行动中找寻生活的意义,我猜测意思大概是说通过行动去发现生活的真实。在获得真实之后,才可能谈得上意义。
所以讨好生活没有用,它并不分亲疏。猜度生活也没有用,它自己也没有答案。和生活讨价还价也没有用,它根本就不打算和你做生意。赞美和诅咒也没有用,因为它也不曾一定要你看到怎样的景象,随你怎么想都无所谓。心怀期待或者拒绝同样没有任何用处,你几时见过它做出响应?如何判断是心灵福至还是随机波动?
走在中间的意思是放弃期待,放弃拒绝,放弃讨价还价,放弃猜度讨好,甚至放弃自己一厢情愿的想象,认为生活应该如何如何。接受真实的意思是承认生活总是不会按照我们的期待行事,它有自己的安排。合在一起就是假装自己的确有所选择,即便内心并不确信也依然如此,然后可以接受所有的后果,装作是自己建立起来的因果关系,即便内心有强烈的愿望把一切归结为命运也依然承受。这样一来,生活两边的风景就不再那么重要,当你有一颗安定的心,那么随时都走在中道。
讲这些道理其实也没有什么用处。谁不曾经历过生活中的温暖和严寒呢?谁不曾因为这种感受就有所推断呢?谁不曾因此激发起贪婪或者是抗拒,谁不曾觉得自己应该值得生活的特别对待?到得头来,无非也就是发现一件事:“我觉得”这三个字是世界上最不重要的,“其实是”三个字最重要但是又不知道答案,却也因此有了个追寻的方向。路都得靠自己的一双脚去走,那些来回折腾也需要自己去经历,最终的开悟时分更完全取决于自己。我也希望尽早有那么一天,无论自己看到什么样的景色,都只觉得是风景而已。希望你也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