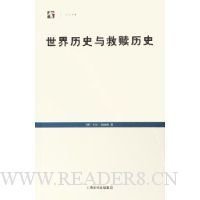
《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是一本由[德] 卡尔·洛维特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0,页数:28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精选点评:
●没读懂……
●补一个,每部世界史最终都通向神学的救赎层面
●逻辑清晰,发人深思。 在前现代,西方对历史哲学有两种基本的看法,一种是古典式的,认为历史是基于不变的人性的周期性循环运动;一种是基督教式的,认为世界历史是向一个既定目标的行进。现代历史哲学以一个原则为线索,系统地解释世界历史,将历史事件及其序列与一种终极意义联系起来。这只能来源于基督教神学,依赖于“救赎历史”的神学解释,完成于对“末世论”典范的世俗化,建立起进步的必然性。当理性排除了神学信仰之后,只能依赖于现世的先知引领历史的方向,于是出现了拿破仑、列宁、希特勒。20世纪的史学既同时用理性和信仰两种不同的眼光看历史,不能向古代的希腊或犹太人那样看到清晰的图景。作者认为应该接受这一点,像布克哈特那样更多地理解古典的立场,放弃对历史终极意义的追索,而回到历史本身的连续性中进行有限的解释。
●本书的目标是想历史地证明历史哲学起源自救赎史末世论,核心指向是洛维特对现代性的思考:究竟是以基督神学还是以异教思维来看待这个世界,近代精神是犹豫且模糊的。《圣经》和保罗的历史神学是源头;奥古斯丁认为神圣的历史与世俗的历史有时相遇但本质上是分离的;波舒埃革新了奥古斯丁,更为强调世俗历史的相对独立性;伏尔泰和维科把宗教的历史纳入并隶属于文明的历史,从而把世俗的历史从天国的历史中解放出来。黑格尔将历史神学改造为一种思辨体系,摧毁了对天意的信仰。孔德、普鲁东和马克思用进步的观念取代了天意,提出试图世俗历史的可预言法则。最后,布克哈特抛弃了神学的、哲学的和社会主义的历史解释,并由此把历史的意义还原为纯粹的连续性——没有开端、进步和终结。本书没有很多哲学上的建构,很像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倒叙的手法很精巧。
●绝巘翻回日月车,就是错字比较多。
●搞笑的是上面有个评论说,对照英文版发现翻译糟糕。然而扉页分明写着是根据1949年德文版译出的……莫非他认为独立翻译过《康德全集》的李秋零竟然不会德文?
●*
●贵哭我了,我可真是俗学典范
●就是校对差了点
●差强人意吧,慢慢发现洛维特的思路比较简单
《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读后感(一):【转】章可: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引介
【作者简介】章可,浙江杭州人,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文科基地班,2009年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获博士学位,曾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为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史学理论等。著有《中国“人文主义”的概念史(1901-1932)》(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读后感(二):内容太好,不忍因翻译不佳而减分
【问题】
Ø 摆脱了神义论的辩证法,将给偶然性、意外性提供怎样的位置?
Ø 如何把握巴特菲尔德的“潮流”或“情势”与“隐秘计划”的差别?
Ø 辩证法对东方人为何陌生?“理性的狡计”是否存在于东方的古代思维中?
Ø 除了由“众人”再度“下降”为“个人”,成为学院派“游牧人”外,我们是否还有其他选择?
《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读后感(三):《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读书札记
从古至今不乏对理解历史行为和历史承受之意义的尝试,但历史解释能获得其合理性吗?西方世界在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神话中和在对基督耶稣的信仰中,给予苦难以不同的回答。但无论是异教,还是基督教,都不相信人类意志及其理性的筹划能够作为历史的指导原则—这无疑是一种现代式幻想。无论人是感到自己听任上帝那无法探究的意志摆布,还是如古老的格言:“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Ducunt volentem fata,nolentem trahunt)那样,听任命运和偶然性的摆布,都是无关紧要的。它们根植于人类对朦胧前景恐惧的思维深处,以至于现代人类近乎狂想式地将自己设定为世界的主人,从而将终极意义的追问搁浅。但人类已回不到原初的“对大地的忠诚”的朴素信仰,又失去了天空的庇佑,这个宇宙小孩如同苇叶般漂泊无依。只有在对历史程序的末世论限制范围之内,历史才是普世主义的,只有在救赎史末世论的引导下,历史解释才是可能的 。
历史仅仅是“一系列人类进程的事件”吗?如果历史处于希腊精神所理解的世界之中:世界在永恒地循环复归,事物生生灭灭。这种自然方式的理解、不变的秩序或许给了异教“宇宙是可靠”的保证,但这种毫无意义的重复对人的生存又有何益处?在此,历史由于不断地复归而失去它之所以成为历史的有效性。 奥古斯丁毫不留情地反驳了这一学说,但由于他是以道德—神学的方式回应古代世界观,因此无论对于浸淫理性精神的希腊人或是经验主义的现代历史学家,他多少显得有些不可理喻。在奥古斯丁的经典叙述中,对上帝无条件的信赖和对适然世界的贬低显露了他作为基督徒的虔信。基督教的信仰应许了信徒拯救和永恒的天福,相比起来,古典的永恒复归论是无望的和令人憎恶的。然而,即便奥古斯丁以世俗历史和神圣历史论说基督教学说的真理性,世俗历史在他看来本身就是无意义的。
与约阿希姆(Joachim,1131—1202)以预言—历史的寓意式方法阐释救恩史不同,身处前几个世纪的奥古斯丁是以《旧约》—《新约》的传统图式解释救恩史。只有在末世论未来的拯救和审判里,在救赎历史最初的启示和未来的完成之间的一段时间,世俗历史才会进入奥古斯丁的视域。也正如圣经对历史的诠释那样,基督之前和基督之后的历史事件的价值是根据它们对审判和拯救的可能意义来衡量的。生活在尘世之国里的人的全部意义在于向着超世俗目标朝圣,而唯一真正的救赎历史和上帝的国的历史进程也就在于这种“异乡之旅、朝圣”。在奥古斯丁这里,历史真理是启示在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之中的,它在可能在基督之后历史进程的任何一点上一劳永逸地显明。奥古斯丁的主题和旨趣仍是末世论的信仰史—这依赖于不可见的信仰之眼,以至于他忽略了历史程序的“本真”,也并没有在神明天意和历史程序之间建立自明的联系。 一切到约阿希姆这里终于发生了改变。在约阿希姆看来,只有在各种秩序的前后相继中,历史真理才可能得到启示。他立足于三位一体说创造了理解救恩史的普遍图式,救赎历史的基本法则是从《旧约》和《新约》的“字句”时代向“精意”的时代的不断进步。这种先知性预言意味着尘世秩序是服从转变的。相反,奥古斯丁却从未涉足过这点。如同十六世纪陷入狂热末世论信仰的路德,约阿希姆并未意料到他推动了对新的历史实现的追求,并在之后的莱辛、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进步思维形式中得到体现。 越接近现代,历史解释就愈趋近于进步论的思维方式,这显然撷取自犹太教弥赛亚主义和基督教末世论。即便孔德试图以人类认识发展三阶段论为他的实证哲学提上日程提供正当性,设定科学阶段为人类历史的终极形态,也改变不了他思想的神学属性。 同时,现代性的祛魅似乎在表面上造成了与传统的断裂,人或者世界都化归为偶然性的存在,人类好像诺斯替主义中漂泊无依的“异乡客”。永恒之丧失导致当下之丧失,一切都将成为过去,暂时存在的事物无不有限,无不是非存在。尼采适时的提出永恒复归的意志来解答对历史意义的追问,他复归的并不是古典世界观中的自然历史,而是伦理上的命令,从而摒弃了古典世界观的“圆周”。他如此地强调权力意志,肯定超人的创造性,以此作为对堕落的道德基督教的反叛。但这何尝不是虔信的宣称? 洛维特在绪论里写到,“古代和基督教这两大思想体系,即循环的运动和末世论的实现,似乎穷尽了理解历史的各种原则上的可能性。就连阐明历史的各种最新尝试,也不过是这两种原则的各种变体,或者是它们的各种混合罢了。”于此观之,岂非良有以也?
为错别字扣星。
《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读后感(四):《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总结摘要
最后两篇附录没有总结,但是写的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