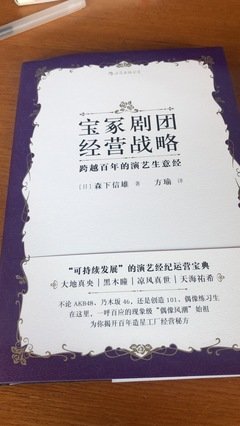
《从苏联归来》是一本由(法)安德烈·纪德著作,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8.50元,页数:16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从苏联归来》精选点评:
●GCZY就是坨屎,苏式GCZY就是专制的另一体现。人们应当生活在开放社会中!
●黑资料
●说实话:“说实话,真的很难。”但纪德做到了!
●1936年,68岁的高尔基逝世。为了纪念演讲,比他小一岁的纪德前往苏联,他的见闻录受到比他大两岁的罗曼罗兰的大骂。32岁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也在同年去世。纪德看望并亲吻了瘫痪在床的他。同年去世的还有55岁的鲁迅。 其实更有趣的是纪德,作为一个诚实的作家,失望过后依然欣赏(或寄希望于)苏联并且相信革命之处——毕竟他所指出的苏联之弊病已为今人熟识。不过仍有一二有趣之处,比如纪德三次提及堕胎政策变更之后的影响,“苏联是世界上手淫最流行的国家”,以及一条脚注里同性恋自由是不是马克思主义。
●译笔佶屈聱牙,不忍卒读,毁了此书
●对被蒙蔽的群众的心态的记录和当今中国的小粪红真是出奇相似。
●虑
●就深度而言比《俄国人》差很多,毕竟只是游记而非长期观察,但也看到了苏联某些阴暗面,如果要想全面了解还是推荐《俄国人》。与当下应景的一句话是《真理报》上面什么都有,我们都了解。
●三十年代的翻译读起来还是有点别扭~
●纪德有《访问苏联归来》,罗曼罗兰有《莫斯科日记》,茅盾有《苏联见闻录》,对比着看很有意思
《从苏联归来》读后感(一):书评
纪德的嘴是不会说谎。因为对苏联的深沉的爱,他勇于揭露苏联社会中的黑暗。从纪德的书中,看不出他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失望,更多是对于革命的得利者(篡夺了革命领导权的官僚)的一种谴责,从纪德的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苏联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一幅怎样的景象。纪德所看到的事实为五十多年后的苏联解体埋下了定时炸弹,如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中指出的,苏联的命运,取决于工人阶级和官僚之间斗争,要么是工人阶级的政治革命挽救这个堕落的工人国家,使之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要么是官僚亲自导演一场资本主义复辟。很不幸,工人没有能起来变革这个制度,于是乎苏联解体了,资本复辟了,莫斯科红场上列宁的遗体如同木乃伊般仍躺在棺材里,而他九十多年缔造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已改变了她的颜色。
《从苏联归来》读后感(二):从苏联归来
此书主要由两篇文章构成《从苏联归来》《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安难》。前篇可以说是游记,而后篇则是反驳文章。
纪德曾经左倾,于是夸赞苏联,可是去苏联参加高尔基葬礼并游历后写出前文,其实现在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但当时在欧洲全面左倾的情况下。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之举,于是批判四起,而纪德也不是善与之辈,于是又索性写出后篇,此文就是直接的揭露性作品了。从这点看,他还算是个斗士。
问题在于他写的确实是事实,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苏联为了从农业国飞速成为工业国而对下层人们进行了“超剥削”。但显然苏联特权阶级的存在以及扩大也是事实。此作品可以看成了解《古拉格群岛》外的苏联的一个窗口。
说实话,现在看来,苏联和美国两个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完全把“社会主义”和“民主”给弄臭了。其实也许这两个名词所代表的内容是美好的。可惜的是苏联式社会主义和美国式民主已经弄毁了这种美好。真是令人遗撼至极。
很不错的作品,小而短但精彩。
《从苏联归来》读后感(三):那个苏联很中国
对11月22日出生的人而言,生命最大的意义就是追求自由与解放。
纪德,生于1869年11月22日。他始终保持自由的灵魂,不为任何权利服务。这大概也是导致他的书无论在哪个制度的社会都曾被列入禁书的原因。他只忠于自己,当下的自己。
他游历了非洲,目睹法国对殖民地资源的盘剥,使他极度渴望改革。于是,他成为了共产主义者,但在访问了苏联后对共产主义的幻想破灭。
他在苏联看到了什么导致他要同共产主义决裂?
看看这本书吧!那些场景你一定不会觉得陌生。
为了买东西可以用一整天的时间来排队等待还习以为常的人们。(最近刚见过这样的长队吧?)
质量低劣价格高昂却还是供不应求的商品。(比如每年2月份的什么票。)
对正在发生的一切唱赞歌。一点点异议一丝丝批评都将导致严厉的惩罚,并且批评也会被扼杀。(我们经历多少灾难,还是有人会说:大难兴邦~~~)
巨幅画面里,领导正在讲话,大小官员分列两边,鼓掌。(你有没有在报纸上看到过这样的照片?)
外国友人处处受到热烈欢迎,盛宴款待,奉若上宾。(今年我们深刻的体验了一次吧?)
“这里前不久还是一片荒芜,忽然间就有了这道楼梯。”(标榜自己的建设做的多快,做得多好。。。。)
如果他们还关心国外正在发生什么的话,他们更在意的是外国人如何看待他们。他们希望从我们这儿得到的不是信息,而是恭维。(哈哈哈哈哈哈哈,这个心理。。。。)
每天上午,《真理报》交给他们适宜知道思考相信的东西,可不能另有他想。(我们的媒体啊!)
纪德说:他们的幸福是由希望、信任和无知构成的。
而要他们继续无知的幸福,还是让他们不再无知而变得不幸,他不知道哪个好一点。
《从苏联归来》读后感(四):【读品•细读】杨荷:纪德的困惑
我一直试图把纪德在苏联的笔记与我零零星星听到的毛时代的特色两相比较。而今早,我回忆起一件事情:一个多月前曾给Patrick发过一本《上海摄影艺术集》,那是1980年左右的版本,所有的照片均为文革刚结束时所摄,其中还有几张华国锋的相片。我匆匆看完之后,留下如此印象:画面上每个人都面带纯真的笑容,都在热火朝天地建设“四个现代化”。儿童们快乐地学习文化知识、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工人们在生产岗位上干劲十足;科学家鞠躬尽瘁,为了社会主义科学事业废寝忘食;文艺工作者则奉献文艺节目讴歌这一切和平美好的景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用一句话归纳:社会秩序井然,民众真诚朴素,各司其职,为着一个宏大的目标而欢呼雀跃。
当时,我怀着暗暗的嘲讽心态来评价这些照片,心想——他们的笑容大概是摄影家为了歌颂祖国而刻意抓拍的瞬间,我不相信在那样匮乏的年代人们会真如照片中一样快乐。然而,在看到纪德这本《从苏联归来》的相关记述时,我意识到自己的判断有误。引用一段纪德的原话:
“(在莫斯科文化公园)我时常到那里去。人们一进园门,仿佛到另一个世界。在这群青年人、成年人和妇女中间,到处都是认真的,端谨的;没有一点愚蠢的庸俗的行为痕迹,没有狎昵,没有放浪,甚至没有戏谑。人们到处感到一种欢乐的热情……一种非常的一致性支配了人们的服装;无疑地各人精神上也是这样。正为如此,每个人才觉得快乐并表现快乐。(人们缺乏一切的东西太久,所以有了一点东西也觉得满足。当邻居没有更多的东西时,自己所有,自己就满意了。)”
纪德在去苏联的前几年曾深深地迷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法共交往密切,因此,他以参加高尔基葬礼为名义,受苏维埃作家协会的邀请去苏联访问。纪德的政治理想是消除剥削、消灭不平等,让生活愁惨的人都过上幸福的日子,他一直憧憬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会是这样一个美好的国度。然而,直到他在苏联亲自呆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对于那里的专制制度与民众生活应该重新作评价。他不顾各方阻挠,回国后即出版了这本游记。可以想象,这本书遭到苏联各大媒体怎样的谩骂,以及法共怎样的批评。
归根到底,这位法国文豪背负的人文传统,使得他不能忍受为了某个宏伟的目标而消解一切个性的制度。他半是无奈,半是愤慨地写道:“人们还能期望什么更好的呢?全体的幸福只有解消各人个性才能得到。全体的幸福只有牺牲个人才能得到。为要获得幸福,那么随声附和吧!”在这种体制下,普通民众不需要为生计问题过多操劳,只要调低自己的物质需要,在庞大的体系里找个容身之处,那么生存便能得到基本的保障;由于周遭每个同等阶层的人都同样的不富足,攀比也不成其为问题,所以人们甚至感到很快乐。的的确确是很快乐。难道卑下低劣的生活就不可以快乐吗?这又让我想起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中提出的一个尖锐问题:让个人获得解放、承担起自由,而需要自己做出抉择时,这到底是一件喜事,还是一次灾祸?当每个人不得不依靠已有的资源解决自己的需求,为了一些决策而大伤脑筋之时,他们是愿意继续拥有这种权利还是放弃这种权利?
我不知道答案,因为我猜测,有许多人是宁可回到不用费力思考这类问题的状态中去的,他们并未对自由的到来做好准备。《告别有情天》这部电影不就是类似的一个主题吗?当一个家仆习惯了受主人差遣的生活时,他是坚决不愿意自己去过一种自由生活的。或许我们还可以举出《肖申克的救赎》为例,那个在监中活过大半辈子的老人,一旦刑满释放,反倒无所适从,不知怎样应付监狱外的世界,只好自杀了之。习惯了束缚的人们,一旦这束缚突然掉落,他们会作何反应?诺齐克也讨论过相关的问题,假如一个人,因为某种原因,要求牺牲自己的自由而换取一些利益,这是道德还是非道德的?
话题似乎离纪德的书越来越远了。纪德的思想冲突在于,他秉信的个人自由与对专制国家对个性的压制冰火难容,他以为这样牺牲了自由而达到的“和谐”是不道德的。他对苏联的平民充满了同情,又禁不住抱怨斯大林的制度泯灭了他们的个人意志。几年前,我曾阅读过纪德的文论,其中有三篇是解读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讲座文稿。纪德对俄罗斯民族的好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那位俄国大文豪的影响。没准儿,他在心里把自己当作陀氏的小学生哩。
纪德算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的“蒙”一直持续到读研时期),另有几位启蒙老师已经被我“抛弃”,他们的书我不会再读,然而纪德却是永远值得尊重的。我愈是细读,愈是发现他那闪光才华之下的质朴和正直。
[法]安德烈•纪德著:《从苏联归来》,郑超麟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8.5元。
《从苏联归来》读后感(五):从苏联归来,他反戈一击
从苏联归来,他反戈一击
邀请他访问苏联,给他好吃好喝好招待,但他随即成为斯大林政府眼中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因为他忠实于真相,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发表了一本记录苏联见闻的薄薄的小册子。
因为这本书,苏联收回了曾给予他的全部赞誉,并组织一批人对该书进行了批驳。
因为这本书,他遭到了友人和同道的围攻和谩骂,一向受他尊敬的罗曼·罗兰甚至称他为“丧尽了良心”
因为这本书,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不少热血青年对延安怀了犹疑,停下了奔往革命圣地的脚步,后来,该书成了中文译者一贯反动的罪证。
这本书是《从苏联归来》,作者是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纪德,中文译者是郑超麟,被打为托派的早期中共党员。该书还附录了《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这一部分回应了各方对《从苏联归来》的攻击。
1936年六七月间,纪德应邀访问苏联,因为此前他怀着世界大同梦表达了对苏联的拥护。在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与敌视之中,孤独的苏联收获了一位国际著名作家从法国伸出的友谊之手,那份感动自不待言。
访问是短暂的,大约二十多天,而且全程由苏方陪同,参观路线对方自然也是有着精心的安排。即便如此,纪德透过预设的重重包围,在惊鸿一瞥中,即洞察了这个国家体制弊端中的内核,以及国民令人极为不安的精神状态。尤为难得的是,他愿意将自己观察到的苏联实况即刻公之于众,哪怕这些文字令自己的尊严受损,使自己像个出尔反尔的小人——要知道,他刚刚发表了宣言拥护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
译者序言中说,“书中所反对的,主要是当时苏联流行的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我以为,书中有两大主题,一个是在计划经济下的人们的生活和工作状态,一个是强大的无处不在的专制政权对民众精神上的控制。人们或者已经被洗脑(如那些天真可爱的孩子,沉浸在赞美其建设成就的迷梦中),或者虽无法洗脑但已在精神上完成了控制(如那位被迫在公众场合驳斥纪德的文艺观,私下却又向纪德认错道歉的画家)。
计划经济的全面施行,其结果往往是造成商品的极端短缺。到21世纪的今天,这一结论似乎无须理论的论证了,刚刚摆脱“计划”掌控的中国人绝不会陌生。在这本书中,我们重温了买东西排长队的场景。苏联建国仅仅18年,经济政策的恶果已经显露无遗。商店没开门,人们就排起了长龙,因为椅垫只有四五百件,而要买的人有八百,一千,甚至一千五百。他们在做听天由命的等待,只要有一丝希望,都要排下去。不用说,商品多是粗糙的,丑陋的。对于工作效率,作者有一个妙趣横生的记录:“人家对我说:他(劳动竞赛中涌现出的一个先进人物——笔者注)五个钟头之内做了八天工作。我冒昧问他们说:这话不含有当初他用八天来做五个钟头工作的意思么?但我这话问得不太好,他们宁愿不回答我。”
不过,对苏维埃制度极为推崇的纪德并不认为效率低下、商品匮乏是缺乏市场竞争所致。显然,作者有自己的盲点,他并没有能力为精确观察到的现象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经济学分析,只给了一个模糊的令人不知所云的解释。
仅仅是物质上的贫困,尚不足以令人灰心,而精神的控制,言论的压制,舆论的一统,让这位来自法国的深具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的作家倍感压抑和愤怒。“我参观过这个很繁荣的集体农场的好多幢住宅。……我要说出每幢住宅给我的使人不快的奇怪印象:一种完全消灭个性的印象。每幢住宅都有同样的丑陋家具,同样的斯大林肖像,此外绝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一件个人物品,没有一点个人纪念。各个住宅都可以互相交换的。那些集体农场人员本身似乎就是可以互相交换的。”消除差异,消除隐私,消除个性,获得统一,获得平等,获得幸福——但抹平了差别、消泯了个性的人们还有幸福可言吗?
虽然时间短暂,纪德已屡屡感受到在苏联发表异见、提出批评的艰难。虽然注意到入乡随俗而小心翼翼,但他自由主义的灵魂事实上还是有意无意地触碰了苏联民众业已养成的禁忌:他本想在斯大林的故乡给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发封电报,以表谢忱。拟稿时,电文中对斯大林以“你”相称,身旁的翻译及其他工作人员习惯性地建议他要冠以“人民导师”、“劳动者领袖”等称呼,争执不下,盛怒而无奈的纪德决定不发电报了!
他还注意到,这里虽然鼓励自我批评,但“这种批评除了一些告发和谏劝(食堂里汤煮的不好或俱乐部讲演厅内地扫不干净等等)以外,只在考究:这个或那个是合乎“路线”,还是不合乎“路线”?人们所讨论的并不是路线本身。人们所讨论者,乃是要知道这件工作,这个行为,这种理论,是否符合于这个神圣路线。想将这批评推远一点的人,有祸了!”这种现象,中国的读者再熟悉不过了。即便在今天的中国,人们似乎在言论上仍有颇多禁忌。比如,一旦上头定下了中国教育要产业化的政策,中国的经济学者所能论证的就是,教育产业化如何如何好,如何执行才能更好。对这个产业化方向本身是否有问题,是否荒谬,往往是难置一辞,因为那是不合宜的,发表不出来的。
我一直在惊叹,到一个陌生的国度访问,在很短的时间里,即便是一个职业记者,能有这么多发现吗?——他的观察曾被攻击为“皮相”的,但近70年的时间并没有淘洗掉这本书,历史还证明了他的精准和深刻。这一点,唤起了我极大的阅读兴趣。
喜欢这本小书的另一重原因在于,虽然蕴含了丰富的思考,但《从苏联归来》的语言却是感性的,细腻的,平易的语调缓缓地叙述,一些温暖的镜头和沉郁的场景时而透出纸面。写书著文的时候,他仍残存着温情和希望,相信“苏联终归要克服我所指出的重大错误”,世界大同的梦终归要实现。但到了后来出版的《答客难》,面对苏联的和友人的舆论围攻,他愤怒了,他毫不留情了,他剪灭了曾怀的同情心,来回击那些射来的明枪与暗箭。这时,他以理性的论证为主,文中的同情与抒情意味比《从苏联归来》淡了许多。
《从苏联归来——附:答客难》(法)安德烈·纪德,郑超麟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110千字,定价8.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