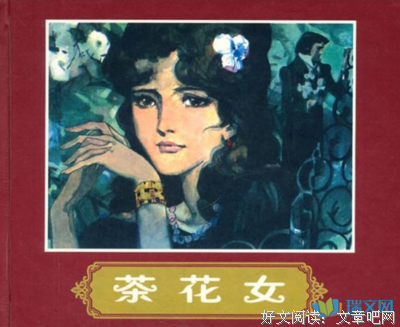
《米佳的爱情》是一本由(俄)蒲宁著作,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5.00,页数:23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米佳的爱情》精选点评:
●什么是爱情,得不到的东西往往被神化,得到了也不过尔尔。别赋予感情过多的东西,慢慢感受,真爱没那么容易寻到,如果那么简单, 你我早已得到爱情
●记得是很早之前看的,蒲宁把初恋时两个青年人的无知和因此产生的危险描写得入木三分。当初海誓山盟地牵了手,后来倒也信誓旦旦地扣动了扳机,子弹射穿胸膛而落在地上,但中弹倒地的人早已没有力气把它捡起来,难过的是,扣动扳机的那个人永远还是他自己。恋爱需谨慎啊
●戴驄翻译的也太好了233诗一样 “我难以想象爱情可以缺少妒忌,依我看,没有嫉妒就是没有爱。”
●卡佳成了白月光
●写的真好
●越读越觉得蒲宁很“可怕” 。特别是米佳这篇。
●自私是爱情悲剧的开始
●啊,还是不错的小说 特别那篇俄国老板娘
●非常喜歡《從舊金山來的先生》,《輕盈的氣息》和《騎兵少尉葉拉金案件》,其實後面幾篇較短的文章也寫得極其好,結構緊湊節奏完美,結侷都設定的很好很好,非常符合我對短篇的審美。蒲寧簡直是寫短篇小說的托爾斯泰。
●这是一个关于爱与死的童话,初恋很危险,但更危险的是沉迷于痛苦不能自拔。
《米佳的爱情》读后感(一):平淡却实在可以想象的结局
米佳,他的爱情,从一开始我便猜到:以悲剧收场。米佳,有着拜占庭式的双眼,单纯而腼腆的笑容,小孩子一般的心智,这些吸引着卡佳,卡佳在我看来有着独立的兴趣追求,但是迷恋于米佳童话般的感觉,成熟,睿智,富有主见,他们之间的爱情,如一团火焰般,炽热的升起,缓缓的幻灭,从开始到结尾我认为米佳神经质过重,米佳希望卡佳只属于他一个人,不想和世界分享,米佳不喜欢卡佳对他小儿科幼稚的评价,他希望自己在卡佳的心理是一个高大,负责,值得依靠的 存在,而不是仅仅是只有一双拜占庭式的双眼,他不习惯卡佳对艺术的执着,社交的迷恋,甚至对于考试中没有看他一眼都感到不自然,认为她忽略疏远了自己,其实或许卡佳一直在一如既往的改变,只是米佳没变,这好比,他们俩是两条相交的直线,米佳相交以后变成一个点,不在运动,但是卡佳继续依着自己的速度和方向前行,在这个意义上米佳是个悲剧的存在,他忘却了自己,因为爱情,不变卡佳是一切,现实的发展让他失望,他回到了乡下,本想是调整一下,但是已无可挽回,最后的自杀算是给了一个童话般的结局,让人欣慰,有很多这样的爱情,束缚的爱情,如果可以称之为爱情的话,一方静止,一方运动,一方单纯的像块镜子,一块喜欢社交,若没有很好的沟通和润滑,很可能是悲剧的发展,如果你是属于这个,改变方向吧。
《米佳的爱情》读后感(二):无声的哀怨
刚刚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把蒲宁的小说《米佳的爱情》看完。
蒲宁是举世公认的语言大师,也是和我最有共鸣之处的一位俄罗斯作家。他身上有着典型的俄罗斯作家身上那种纯洁自然的清新感,仿佛静静的顿河在春日里破冰时发出的那种蹦蹦的声音,自然而又意义非凡。他的文章就是这样美不可言。
《米佳的爱情》开始时主人公米佳和卡嘉相爱,然而两人因对平凡生活的不理解而决定暂时分开,而这分开竟成了恋爱的终结并为米佳的生命画上了终止符。米佳最后在忧郁中开枪自杀,和歌德笔下的维特有着惊人的相似,但是米佳毕竟不是维特,米佳的自杀是因为情人的背叛,而维特的自杀是因为在社会现实面前找不到出路。可以说两个作家的作品分别从两个方面解读了青年人失败的爱情。。
米佳是个举止略显粗鲁而心灵 无比细腻的青年,他爱上的卡嘉则是一个一直处在聚光灯下的魅力四射的艺术系女孩。卡嘉的外向的魅力是米佳无法承受的可以说双方的恋情最开始就并不是真正的爱情。米佳对卡嘉的是对美丽和活泼的喜爱,而卡嘉对米佳则是可爱与鲁莽的喜爱,双方的恋情从一开始就背上了包袱。
从米佳离开卡嘉到乡下的老家开始,在过了几天农村瘾后,米佳的精神就出现了隐隐约约的变化,他开始不断的给卡嘉写信并且对卡嘉越来越憧憬,让自己的生活处处都幻化成卡嘉的样子。这样的情况初看起来是对卡嘉的恋爱的坚定执着,实际上却是恋爱死亡的一个前兆。这时的米佳生活的情感已经越来越孤立,生活面已经越来越狭窄。除了卡嘉就什么也没有了。到后来这样不正常的感情与生活开始反噬米佳。米佳在村长的鼓动下半推半就的和农妇阿莲卡发生了偷情。这不仅是因为阿莲卡长得像卡嘉这一简单的原因。其中不乏因卡嘉对自己冷淡而采取的报复心理和对卡嘉病态了的爱情——因为自己的生活早已处处是卡嘉,那么和长得那么像卡嘉的阿莲卡偷情也许是冥冥之中的老天和卡嘉的默许的呢?米佳这样想。
这种病态的爱情最后有卡嘉寄来的一份分手信给出答案。卡嘉的背叛与自己如此付出而得不到相应回报的绝望,对自己偷情的罪恶感,所有的情绪纠结在一起,最终结束了米佳的性命。这是米佳病态的爱情态度所导致的结果。和歌德笔下的维特的死有着不同。维特是因为爱情找不到出路而自杀,米佳是因为得不到接纳而自杀,两者对爱的执着都达到了相同的高度,然而米佳的爱情里又多了一分普希金式的悲情。
短短几万字的小说,足以为正在摩拳擦掌准备为爱情献身的八零九零后的入世戒!
《米佳的爱情》读后感(三):温柔的爱 温柔的死
温柔的爱 温柔的死
一般认为蒲宁写得最好的小说是《从旧金山来的先生》。这个小说写的是大自然的力量与人类虚荣心之间的较量,故事的大部分场景集中在前往意大利的旅途中的一条船上和一个旅馆里。一个一生不停地追逐金钱的美国富翁,到了晚年还要通过享受恢复身体的活力,拯救麻木的灵魂,死亡的降临使他不得不屈服了。蒲宁在叙述这个富翁的旅行的同时又好像非常仇恨这个人物,因此这个小说的叙事调子是愤怒的(像小说中写到黑暗中的海洋和风雪),又略带讥诮的。
《米佳的爱》则要温柔得多,因为它的温柔,我说它贴紧了蒲宁的天性。虽然我们读完这个小说的最后一句会发现,小说行进的终点是一个暴烈的动作—米佳开枪自杀,但我们还是愿意沉浸在小说温柔的光芒照耀之下。《从旧金山来的先生》写到死亡,是一副公正的命运之神的面孔,《米佳的爱》里死亡的降临则是温柔的,带着抚慰心灵的力量,它让人“不再害怕那个骇人的世界”。小说中,米佳从欲望和焦灼交织的梦境中醒来,摸索着打开了床头柜的抽屉,抓到了冰凉而沉甸甸的手枪—蒲宁在这时这样描写:他深深地、愉快地舒了口气,张开了嘴,欣慰地使劲开了一枪。
这是一个俄罗斯式的“少年维特的故事”:恋爱中的米佳为嫉妒而痛苦,决定离开情人卡嘉,去乡下好好梳理一下他们的关系。在故乡的庄园,风景的更迭没有让他淡忘卡嘉,反而让他更深地陷身在情与欲的折磨中,他孤独地等待着来信。在庄园管家的诱引下,他和庄园的女工阿莲卡发生了肉体关系,卡嘉终于在一封迟来的信中拒绝了米佳的爱,米佳在绝望中开枪自杀。蒲宁在这个小说中主要是在叙事格式上(而不是在复杂的人物关系纠缠中)制造紧张,展示他细致的感受和对恋爱中人内心图景的描绘,同时小说还流露了他对女性的柔情和对传统的某种态度。因此我倾向于把蒲宁看作一个本质上的抒情诗人,而不是以分析见长的小说家。
在小说第五节,米佳准备动身去乡下了,和情人分手在即,他以一种别样的心情感受着周围的一切:房舍,街道,街上行走或坐车的人,春天那种总是阴沉的天气,灰尘和雨水的气味,栅栏和胡同内开花的白杨树散发出的一种教堂般的温馨……随着叙事的推进,我们会发现,这种风景和心情共同激发的感受出现在了米佳睡在故乡庄园的第一个晚上:那一个夜晚,卡嘉、村姑、他接触过的所有女性、夜晚、春天、雨水的清香、新翻耕的泥土味、马的汗气等等在他的意念中交织成一片。蒲宁在写到人物的敏感的时候,也暴露了他自己的天性和抒情诗人式的思维方式。由乡村风景引发的安宁过去后,米佳陷入了对情人的思念之中。小说中写他第一次想起卡嘉是由深夜花园的一声鸟鸣引起的,他当时的情状是“浑身哆嗦”,“竖着耳朵凝视深邃的黑暗处”。随着时间的流逝,卡嘉的形象越来越强烈地出现,小说的9到11节,叙事上的回旋和重复像一支乐曲一样把这种紧张推至了最高点,然后是一封来信缓解了这种紧张(“默默地、幸福地期待着下一封来信”)。在这一部分,小说出现了另一个主题的声音,死亡的声音, 主人公由父亲的死领悟到这世界死亡的存在的这一场景出现在小说的第10节中。
小说行进到此,还没有出现丝毫肉欲的成分。夏天的爱情越来越变得像一场热病,我们主人公的痛苦一次又一次地接近顶点,他一次又一次地走到死亡的边界。小说中这样写他去邮局等信回来后的心情—“他途经的树林和田野仿佛都以自己的美和幸福向他倾压,使他感到内心乃至肉体隐隐作痛。”其实风景一直是小说中潜在的一个角色。这时的小说出现了另外一股力量,世俗和肉欲的力量,代表这股力量的则是庄园总管和女工阿莲卡。米佳默许了这种诱引,这时小说对夕阳下的钟楼十字架的一段描绘可以看作他微弱的道德自责。接下来是女工们在庄园里干脏活的一个场景,充满了各种气味和声音的描写,这个场景透露出的世俗生活的气息为即将出现的堕落(如果这算道德上的堕落的话)作了最好的铺垫。
一个恋爱中的少年,一个情与欲折磨下的生命,结束这种冲突和无望的等待的是他自行选择的死亡……在此我看到对人性的真正抒写,看到一种伟大的叙事艺术的余绪。蒲宁推到我们眼前的这个虚构世界是那么有力,又是那么真实,连风景他也赋予了生命,这或许与他对乡村、对女性乃至对整个世界的赤子之心有关,但从职业的角度看,是他对小说艺术的忠诚—出色的描写与叙述、暗示、气氛渲染、叙事的结构与节奏—赋予了这种感受以优美的形式,我倾向于把这看作是艺术家最高意义上的道德。
《米佳的爱情》读后感(四):初恋是危险的
通读一遍,我们不难发现蒲宁小说中一以贯之的主题:爱情和死亡。将这两个词连接在一起并不奇怪,但很少有人能像蒲宁一样,将初恋者内心的挣扎、幸福和苦闷,刻画得如此传神,色彩斑斓,甚至让人绝望。
《苏霍多尔》中的娜达莉娅不顾一切地爱上了少当家,得到的回报却只是被驱逐、被遗弃的命运。《在巴黎》的男主人公在获得了渴望已久的救赎后,却不得不撇下另一个寂寞的灵魂而与死神作伴了。同时,初恋的滋味,也使米佳不堪忍受,最后选择了开枪自杀;使骑兵叶拉金和他的情人一步步地驱于灭亡。
蒲宁笔下的恋爱是饱含着诗意的,色彩斑斓的。
“在这段美妙的日子里,米佳快乐地、专心致志地欣赏者春天给周围带来的变化。但是卡佳不但没有因此而退居一旁,没有因此而消失在周围的景物之中,相反,在它们之中无处没有她的存在,而且正是她的美使它们生色。她的美同日益欣欣向荣的春天一起,同日益繁茂的银白的果园一起,同日益湛蓝的苍穹一起,如蓓蕾般怒放吐艳。”
——《米佳的爱情》
蒲宁笔下的恋爱也是危险的。他对初恋期这样描述到:
“这是个危险的年龄,是决定人的未来的可怕年龄。在这个年龄,人通常正处于医学上所谓的性成熟期,而在现实生活中,则是处于所谓的初恋期。人们几乎总是抱着诗意的、极其轻率的态度来看待初恋。殊不知这个“初恋期”却经常伴随着形形色色的悲剧。从来没有一个人想到过,恰恰是在这个年龄,人会产生较之激动,较之情欲,即所谓的对异性的渴慕远要深刻、远要复杂得多的感情。人在这个年龄不知不觉地经受着惊心动魄的青春的煎熬,做着痛苦不堪的剖析,接受性的最初的洗礼。”
——《骑兵少尉叶拉金案件》
我觉得蒲宁对女性的刻画总是怀着一种敬畏之心。《轻盈的气息》中的麦谢尔斯卡娅有着“压倒所有同学的超群出众之处——娴雅、时髦、玲珑、顾盼生姿的眼波……”,她带着轻盈的气息来到这个世界上,直到被嫉妒的情人杀死时,一直是那般欢快地散步着、欣赏着、呼吸着,仿佛一团空气,令人耳目一新却又无法触及。这样的女性对于理想的爱慕永远超过了对于现实生活的满足。她们的性格、态度也往往使爱慕她们的男性置于被动的、顺从的、危险的境地,其结果,不是男性维特式的死亡便是女性被非理性之火发配去见了上帝。
那么跟这类女性恋爱的男同胞们又是怎样的呢?
“往往有些男人属于一种极其复杂而又深为有趣的类型,这是一种返祖类型,不仅仅对女性,而且对其本身的处世态度都是异乎寻常的敏感的,他们的心灵和肉体全力以赴地追求的正是这样的女人,于是他们就成了层出不穷的爱情悲剧的主人公……这种男人非常清楚地感觉到,与这种女人相好和亲近总是痛苦的,有时的确是可怖的,甚至会送掉性命……可偏偏心心念念地去找这种女人,正是去找这种女人——明知痛苦,明知要死,却飞蛾扑火似的去找苦,找死。为什么?”
——《骑兵少尉叶拉金案件》
从中我们可以感到一股无法阻挡的对生的渴求以及对死的崇拜,恋爱者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没有平衡点。
归根结底,他们是拒绝平庸的人。他们不满足于眼前的美景。他们一边追求,一边逃避,经历过心灵的狂欢,又立刻坠入苦难的谷底。他们一直生活在为自身编织的梦境中。直到米佳扣动扳机的那一刻,他才从沉沉的睡梦中被唤醒,而此时他却已获得了解脱。
帕乌斯托夫斯基谈到蒲宁的创作时曾说:“蒲宁的作品只可研读,切不可不自量力,试图用寻常的而不是蒲宁的语言来转述他以经典作家的笔力和精确性所描绘的一切。”我在写这篇评论的时候,也注意尽量去引用他的语句。然而时常会感到,像对待一件无瑕的艺术品,语言消失在喑哑的深处。
《米佳的爱情》读后感(五):爱杀
蒲宁,193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俄罗斯作家。1870年,他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里,曾当过校对员、统计员、图书管理员、报社记者等。丰富的人生经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养料。从1887年发表文学作品起,到1953年去世,六十多年间,佳作不断。其中《米佳的爱情》是最为大家所熟知的蒲宁作品。
1933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中这样写道:“在《米佳的爱情》中,蒲宁以对心理的全面的娴熟把握,来剖析年轻人的情感。在这种心理把握中,感官印象和心理状态得到了出色处理,这是特别不可或缺的。”
可以说,要想深入了解爱情,这一篇是绕不过去的文学经典。
(一)
主人公米佳在莫斯科的幸福日子,小说中写到“当时他俩邂逅,相识没几天就觉得世上最大的乐事莫过于同对方交谈(哪怕从早谈到晚),米佳怎么也没料到竟会这么快就进入他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起便偷偷企盼着的那种神话般的爱情世界。
爱情很奇妙的一点就是:越是爱到深处,就越想要把对方据为己有,就越敏感多疑,担心对方不够爱自己。但是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对爱情都有自己的理解和追求。所以一旦深入到对方的生活中,慢慢地摩擦就会出现。这在恋人之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米佳和卡佳也不例外。
小说就是从一次小小的不愉快开始的,而且它预示着人物后来的命运走向。
爱情的表现方式,正面是甜蜜,反面是妒忌。爱人只能为我所有,任何事情或者人分散了爱人的注意力,都会让人“妒火中烧,恨得牙痒痒的”。
爱情很奇妙的另一点,你越想抓紧它,它就像是手中的沙,漏得越快。米佳对卡佳的爱,是独占式的。这种爱,最开始会让对方感觉分外的甜蜜,但是到了后面逐渐会觉得窒息和想要逃离。卡佳这样独立的女孩,当然希望有自己的空间,可以去自由地徜徉。两个人最根本的矛盾就浮现出来了:米佳越想占有卡佳,卡佳就越想逃离;卡佳越要逃离,米佳就越想占有。这样的恶性循环,最终会导致悲剧。
两人越行越远。卡佳变得越来越忙,越来越像是出入交际场的名媛,米佳再也无法忍受这种耻辱和痛苦了,他要离开莫斯科,回到自己的老家去。只有那样,米佳才能松一口气。短暂的离开,虽然不能解决问题,可是会给双方一个沉淀和反思的时间。毕竟,太过在乎,双方都无法呼吸。临分别前,双方的感情仿佛又回到了最初的幸福状态,卡佳过来帮米佳收拾行李,“甚至陪他去买捆绑行李用的皮捆带”,有一回卡佳甚至哭了——卡佳是从来不哭的——这泪水甚至使米佳觉得卡佳是他最亲的亲人,一股强烈的怜悯之情油然而生。米佳觉得对不起卡佳。”
短暂的告别像是挽救了这段爱情,昔日那些矛盾和冲突都掩盖在甜蜜的面纱之下。离别的车站,挥洒的泪水,米佳觉得卡佳身上的一切都是如此美好,无论是卡佳可爱的脸蛋,还是卡佳娇小的身材;无论是卡佳还带着少女稚气的妇人艳丽风姿和青春活力,还是卡佳向上抬起的晶莹的双眸,都如此美丽,如此动人,如此让人心生爱意。可是啊,他们就这样分离了。火车开动了,不可预知的未来开始了。米佳想着他们未来还可以重逢,他不知道命运等待他的将是黑暗的深渊。
(二)
就这样,米佳怀着对卡佳的思念,回到了家。
而那个让米佳又爱又恼的女朋友,因为分离,此时在米佳的脑海中,也不再是那个矫揉造作的女演员了,卡佳像天使一样美丽,像白雪一般纯洁。米佳如此爱这个精神上完美无瑕的卡佳,每每回忆,脑海中浮现的都是美好的片段。
卡佳的来信让米佳觉得自己对于爱情的等待是得到认可的,自己所遭受的一切都有了价值。
人的欲望就是如此,有了第一封信,就企盼着第二封信。几天来,米佳一直很有把握地等待第二封信来,并为此感到幸福,甚至自豪。可是盼星星盼月亮,盼到肝肠寸断,都没见信来,现在的米佳越来越苦恼,越来越不安了。
米佳像是疯了似的,不断找借口去邮局,看有没有卡佳来信。可是等待米佳的只有无穷无尽的伤心而已。
我们再来看开头,“米佳在莫斯科的幸福日子到三月九日就戛然而止了。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可以说米佳的直觉是对了,就像是一件美丽的瓷器,一开始只是一个极其细小的裂缝,到后面越裂越大,最后碎成一地,无法收拾。而米佳也付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真是让人叹息。他们爱情悲剧的症结是在于性格的不同,米佳占有欲太强,而卡佳有一颗独立自由的灵魂,这个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著名评论家斯捷布恩认为,蒲宁成功“挖掘了位于两个世界之间的作为实体的、源于人的自然状态的爱情悲剧”,可谓是一语中的。
这篇小说除开对爱情有着出色的描写之外,对于自然景物的描写也让人叹为观止。蒲宁把那份炽热浓烈的爱渗透到随处可见的自然风景之中,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春天特有的那种苍茫的暮色笼罩着大地,从洞开的车窗里飘进雨水的气息,似乎还夹着蘑菇的清香。树木尚未披绿绽青,仍是光秃秃,可是列车的隆隆声在树林里听起来毕竟比在旷野上要清晰悦耳的多。前方已闪烁着车站的点点灯火,那灯火蕴含着春日特有的哀愁。”这样细致优美的描写,在小说里比比皆是。自然界在蒲宁笔下美得让人叹息,那散发着清新气息的白色桦树、漂浮的朵朵白云,田野里绽放的小花,温暖和煦的阳光、叮当作响的马铃声等,如此生动,如此迷人。
(三)
书里的爱情跟作家本人的爱情何其的相似。1927年,蒲宁认识了一个年轻的女作家加丽娜·库兹涅佐娃,从而开启了一段火热浪漫,同时也是痛苦难熬的黄昏之恋。爱情有神奇的作用,让作家重新焕发了青春,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但是,蒲宁那时候已经有了妻子维拉·穆罗姆采娃,他这场疯狂的爱恋,给妻子带来了巨大的伤害。蒲宁跟米佳一样,专制独断,充满了极强的控制欲,加丽娜·库兹涅佐娃实在是忍受不了,离开了他。这对年迈的蒲宁来说,是沉痛地打击。他无法理解,也无法原谅库兹涅佐娃的背叛。他也像米佳一样,陷入了快要发疯的境地,脾气变得暴躁易怒。还好他的妻子维拉·穆罗姆采娃,对他不离不弃,一直无微不至地照料他,直到他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