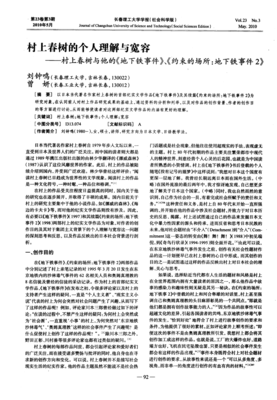
《約束的場所-地下鐵事件Ⅱ》是一本由村上春樹著作,時報文化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00.00元,页数:26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約束的場所-地下鐵事件Ⅱ》精选点评:
●村上关于善恶,黑暗与光明的思考在这本里进一步加深了,囫囵吞枣地读完,迷雾的地方还很多,需要再读几遍的书
●他的書,我最愛這本
●最后两个访谈尤其好
●还是要读小说啊。
●第一本接触村上春树的作品,文字平实,但内容细读感觉震撼,能观照自我,像在和自己对话一样~ 非常推荐
●95年日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后,村上对奥姆真理教教徒的访谈录。掩藏在妖魔化形象之下,这群教徒其实既不愚昧更不凶残,只是多了些对世界和人生的质问,却没人尝试去理解他们。事实上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现实活得地道,但求社会能让这群人有一个出口而不至于投入奥姆怀抱。”如果要成为一个乐观的人,单单喜欢美好是不够的。像喜欢光明一样厌恶黑暗,也许整个思考的回路就变成‘如果可以把黑暗完全消灭掉就好了’,那样必然会变得愤怒起来。” 当时读完《约束的场所》后写的一段话。纯粹即极端,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必须学会怀着恶活下去。
●從加害者的角度看真理教沙林毒氣地下鐵事件. 不能少看邪教在日本的力量.
●非常值得推荐!有许多引起思考的地方。PS看完这本书,就更明白《1Q84》尝试传递的信息了。
●發覺喜歡看村上的報導文學多於其小說
●奥姆真理教
《約束的場所-地下鐵事件Ⅱ》读后感(一):读书记录
里头的信徒说到:“就是对自己现在的生活有怀疑,难道这一辈子就这样下去吗?总觉得有所欠缺,因为这样才接触了奥姆教,在组织里,一切已经安排完毕,就不用烦恼人生到底怎么安排。”说起来,人无法把握自己的心,过于自由也是一件很困扰的事情。我觉得我自己最近一年的生活都是如此。
同时我也很惊讶的发现所谓教会,其实跟一个组织严明分工明确的大企业一样,并且还有昂贵的入会费一说,里头就是一个小社会。不同的是,那些信徒已经或多或少的失去了自主思想的习惯。
2007-8-13
《約束的場所-地下鐵事件Ⅱ》读后感(二):约束的场所
一本关于奥姆真理教中八位信徒(原新图)与村上春树的访谈录。
书中的主人公们都算年轻,他们在入信之前有着各种各样的人生,其中不乏社会精英。对现世生活的不满,以及对教团内宁静祥和生活的向往,可以说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共同点。
他们对生活所怀抱的不满不是鸡毛蒜皮的不满。可以说在思考生活本质,追求真我这一点上,他们要比很多人负责的多。这八个人无一例外的不能认同充斥现世的成功理念,从学校教育到就业工作。自己所接受的学校教育未能引领自己接触到真正的睿智,只是重复枯燥地向人灌输知识,走出学校之后浮于表面的人际交往与乏善可陈的工作令他们感到自己的人生在不断磨损,到头来两手空空一无所有。无论如何,这样的人生不是他们所向往的,这种根本性的苦恼一直束缚着他们的心灵。
就在彷徨踌躇之际,麻原彰晃和他的奥姆教义进入了他们的生活,以救世主的姿态张开双臂欢迎他们。承诺入信之后通过修行就可以达到不朽,永离苦恼。这样的诺言对那些精神游离于现世之外寻求慰藉与解脱的孤独心灵来说,几乎就是无法抗拒的甜美果实。
入信成为信徒之后还面临着是否出家的选择。若是要彻底摆脱现世的苦恼就必须出家。这八个人最终都出家了,抛弃了现世的工作,财产,割断了与朋友、家人的羁绊。出家之后他们在乡间或道场过着与世隔离的集体修行生活。出家之后他们的确获得了自己所向往的“纯粹性”。一心只是追求修行,早离苦海。并且根据教主的指示,将教团布置的任务视为修行的方式。工作之余就是休息,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虽然肉体疲惫不堪,但灵魂却是安宁。然而,这安宁却是将“自己”这一存在完完全全地交给了麻原和他的教义,剩下的“无”里面自然就不存在烦恼的空间。
这样的“无”是不可能将纯粹性保持下去的。没有烦恼也就没有独立判断,没有独立判断也就没有责任,没有责任也就无从抵挡恶的诱惑。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五个变过装的男人用磨尖的伞件戳破了装有自制沙林毒液德塑料袋,12人死亡,5,510人以上受伤。当然,村上所采访的8个人跟毒气都没有直接关系。
面对这样的人间惨剧,我们都能想到什么?
同情被害者,谴责加害者,呼吁法律惩罚事件相关者,议会立法来规制教团集体活动。是的,这些都很重要。
不过我想关键一点是去接触信徒们的心灵,理解他们的想法,而不是像主流媒体一样狂热地给他们贴上雷同的标签,像政府一样逼迫他们强制退教,这种方法不可能从根本上治愈他们的伤口。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普通人。“既不是落伍者,也不是奇怪的人。他们是生活在你我周围的普通人……那可能是我,也可能是你。”村上如是说。
惨案发生以后,他们起初都不相信这会是教团所为,虽然公开审判之后都或多或少接受了现实。但关键问题在于,不管这些人退教也好留教也好,他们对自己选择加入教团从来没有后悔过。从来没有后悔过,这样的事实非常震撼。我想这应该就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对此,村上给出的回答是:“因为在那里确实存在现世所得不到的纯粹价值存在,就算结果转变成恶梦般的东西,那光所反射的辉煌温暖的初期记忆,现在还鲜明地留在他们心中,那不是别的东西能够轻易取代的。”
“如果有类似这个有光的什么再一次咻地在他们眼前出现的话(那或许是宗教,或许是宗教以外的东西),他们心中的某种东西,不管愿不愿意也许又会被吸引过去。在这意义上,对我们的社会现在最危险向,或许与其说是奥姆真理教本身,不如说是‘奥姆式的东西’”。
这样的东西的确有如太阳一般令人向往,阳光普照之下任何疑惑都将不复存在,只要自己向它献出自我,就可以穿过窄门到达那至高的境界。这捷径有着无限诱惑。活着的人们难免会对生活产生不满,不满的情绪越是深刻,越是与生活的本质混淆起来,我们越是容易被这光芒所吸引。
尽管这光芒本身并不是邪恶之物,不过,如河合隼雄先生在书后的访谈里所谈到的那样:“教团本身其实是好的容器,不过,光是好的容器还不行。如果变成采取那么纯粹、极端形式的教团的话,一定还会发生问题。那么纯粹的东西紧紧地聚集在内部时,外侧如果没有不惜杀人的极恶家伙时,就无法取得平衡。这样一来,如果不向外诉求的话,也许里面也会发生严重的争吵,组织从内部开始崩溃。”善与恶总是要达成一个微妙的平衡。
在人世,至善万能的组织过去不曾存在,现在未有存在,将来亦不会存在。那阳光虽然出于善意,但却不是我们所应坦然接受之物。
坚守自我,即使在追寻真我的同时也不能抛弃自我,也许这就是我们抵挡那光芒的唯一方法。
《約束的場所-地下鐵事件Ⅱ》读后感(三):讀書筆記《地下鐵事件》、《約束的場所》/村上春樹
《地下鐵事件》
我一向對宗教有點興趣。得知《約束的場所》是關於奧姆真理教的信徒/前信徒的報告文學,便找來看了。
因為《約》是《地下鐵事件》的「續集」,順理成章,也應該拿《地》來一讀。不過我從圖書館拿到這兩本書之後兩天,就率先讀完《約》了,《地》只是看了八十多頁。當然,這有客觀的原因:《地》記錄的受訪者有61人,近六百頁;《約》記錄受訪者8人,頁數不到《地》的一半。
《地》 主要是1995年東京沙林毒氣事件受害者的訪談記錄,《約》是奧姆真理教信徒的訪談記錄。在1995年3月20日,奧姆真理教的信徒,分別在東京地鐵的5 列列車上,故意釋放沙林毒氣,導致13人死亡,約6300人受傷。作者自述他開始訪談計劃的原因之一,是感到傳媒上報導的並不是他想知道的事情。在傳媒的 敍述中,毒氣事件是個正邪對立的事件,受害者是無辜的,加害者有罪、走火入魔。故勿論事實是否如此,作者卻想知道當時人的感受——他們那天感受到甚麼,事 後有甚麼感受,這件事對他們的生活有啥影響。也許他覺得去做這些訪談,能令他會更「貼近」當天發生的事,而不是由那個正邪分明的角度來看該事件。於是,作 者就寫了《地》(1997年出版)。決定寫《約》,是《地》出版後的事情:作者寫《地》的時候,故意盡少接觸關於真理教的資料,也許是害怕形成某種刻板的 印象吧!《地》完成之後,作者心中有個感覺,覺得需要了解真理教信徒的想法,便開展第二輪的訪談。
《地》,我總是斷斷續續的讀。我覺得這本書是挺悶的。我想作者做訪問的時候,應該不覺得沉悶,因為他可以用不同的觸覺去認識受訪者。可是當印象化成文 字,好些受訪者的敍述都大同小異,來來去去都是這樣的格局:被訪者的職業是甚麼,家庭怎樣,日常做些甚麼事;那天出門時的情形,遇到氣體時的感覺(大多數 都說沒甚麼特別,只是覺得空氣有點怪怪的),之後的反應(有好多人還是撐着上班去,回到公司,聽到新聞說沙林毒氣,想自己也可能中了毒氣,才到醫院去), 事後的身體狀況(例如記性、視力或體能差了)(發怪怪或可怕的夢),以及對真理教的感受(有些人沒甚麼感覺,有些帶着恨意,有些則主張要用重懲這些人)。 這些人多數主要是輕傷者。毒氣事件,對某些人來說,好像跟在街上踩到狗屎之類的事情差不多。
不知怎的,寫着寫着,我覺得自己有種偷窺的心理,好像很期待毒氣事件改變了受害者的生命,這也許是受害者生命裏面起承轉合中「起」或「轉」的部分……醒來吧,這是報告文學,不是小說。
至於受影響較大的人呢?例如,那13個死者身邊的人或地鐵車站的職員呢?我也不太想說些甚麼。或者這類故事,在電影、小說或者報章已經聽得太多,例如甚麼創傷後遺症等。暫時也是沒甚麼「特別」想一寫。
如果不去追求甚麼,《地》的題材和角度對我來說還算少見,可算是一次特別的閱讀經驗。特別在哪裏?我現在努力地去寫一篇讀後感,結果擠出了那種有點虛無、方向不明顯的感覺……倒真的有點像作者的小說了。作者在書中提過,現實本來就是有點模糊、混亂和矛盾的。
《約束的場所》
讀着那些曾經進過奧姆真理教的人的自白,很有共鳴。(呵呵,我大有入邪教的潛質呢……)
他們的共同點是:
和家人關係疏離
對社會(成人世界、社交法則)有所懷疑、不滿
可能接觸過不同宗教或超自然的事物,有些本身的生活亦充滿難以用常理解釋的事情(如很真實的夢境)
喜歡很理論化的事物
喜歡抽象事物,如藝術
有覺得世界/社會就快走向末日的感覺
=========================================================
書摘:
成績還不錯噢。可是起伏很大相當不安定,尤其進了中學之後,"""自己想做的事和不想做的事,分得非常清楚。雖然並不覺得讀書本身有多苦,可是卻很抗拒用功讀書這回事。也就是說自己想學的東西,跟學校所教的東西實在太不相同了。"""
對我來說我覺得所謂學習應該是可以變聰明的。可是學校裡所教的卻是「澳洲有幾頭羊」之類東西的死背而已。我覺得這唸得再多也沒辦法變聰明。所謂聰明,以我小時候的印象來說,也就是在童話故事「姆米家族」中出現的史納夫欽所擁有的那樣的東西。"""對我來說,長大應該是這個樣子。應該學會那種沉著冷靜或富於知性或智慧之類的東西。"""
……
……看到那個我真的很失望。"""原來人在長大成人之後,也沒甚麼成長嘛。"""
——你是說看到電視劇,裏面的角色實在太差了,就讓你決定性地失望了嗎?
是啊。在我心目中所謂大人的形象,因而完全崩潰。"""他們年齡漸長,知識或經驗也許增加了,可是內容卻完全沒有成長。我想這樣的話如果把外觀拿掉,把表面的知識拿掉,剩下來的豈不還跟小孩子一樣。"""
……
是啊。我一直在想這種事。從十二歲左右開始就對哲學性的結論之類的東西做過各種整理。甚麼事情一開始思考起來,就可以一個人一連六個鐘頭都落入沉思。對我來說所謂「學習」,說起來就是這麼回事。相對的在學校所教的,說起來卻只是像為了拿分數的賽跑一樣而已。
我偶爾也跟朋友談起這個,可是卻沒有結果。對會讀書的朋友提起這種事,人家也只會佩服地說「哦,你好會想這種事噢。真厲害。」而已,話題並不會繼續發展下去。我最關心的事情,卻找不到可以暢談個夠的對象。
……
不過我跟身邊的朋友都相處得很好。談話內容也會適度配合對方。我非常懂得「這時候這樣說的話人家應該會接受」,這樣子朋友也相當多。能讓朋友高興,自己看了也覺得高興,這種生活大約維持了十年左右。可是回到家剩下自己一個人的時候,又會常常想「這樣做著活下去,到底又會怎麼樣呢?」畢竟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卻沒有一個人可以一起做。
我 大學時代加入美術社團,很活躍地參加過各種活動。不過我想在自己內心裏,卻相當乖離。換句話說對外裝成很外向地活動的自己,和內向的自己之間的乖離。確實 我一方面是很明朗熱心地活動著,也交了很多朋友。可是一旦回到自己房間後,就會一頭埋進非常孤獨的世界裏去。而且周圍沒有一個能跟我共享這種世界的朋友。
我從小就有這種傾向。還記得小時候,我常常躲進壁櫥裏去。我不喜歡跟父母親面對面,就算在房間裏也沒辦法擁有屬於自己的空間。小時候,父母親不是會干涉我們很多事情嗎?能逃出這些,獲得安靜的空間,說起來只有壁櫥裏。這或許是個有點奇怪的興趣,"""在黑漆漆裏一個人獨自封閉起來時,會有一種自己的意識悚速敏捷地尖銳化似的感覺。可以說在黑暗中和自己面對面。所以像奧姆的靜修retreat(隱遁性),在某種意義上是我從以前就喜歡的。
我 也喜歡鑽進棉被裏把頭整個蒙起來睡覺。把棉被蒙住頭後,就可以進入自己喜歡的另一個世界。雖然意識還清楚,但一面醒著,卻一面進入和夢的世界相交的中間地 帶去。在那裏,我可以自由地到任何地方去旅行。在那棉被裏,建築起像是只屬於自己的精神世界。這種習性變得有點停不下來。"""
……
——你所說的小時候感覺到壁櫥式「黑暗世界」,跟你的奧姆真理教體驗有沒有關聯?
有 白天的世界和晚上的世界。我想不開到要出家的地步,是因為我認清了在白天的世界,隱藏在我心中的類似願望的東西怎麼都無法消解掉。所以只能把白天的世界抹 殺,或去加入某種活動,自己把白天的世界拋棄掉。所以我才會去打開奧姆真理教的這扇門。也就是,像跟自己心中的黑暗相遇一樣。……
河合:
quot;""為了不要再出現這種人,我想今後每個人都必須更堅強起來才行。"""因此教育要好好做好。現在的教育已經完全不行了。"""我們不能不思考讓每一個人變堅強的教育。"""可是,沒去上的孩子居然有十萬人,這倒是相當進步了。文部省能夠容許這個,表示文部省也改變了很多。
村上:
這是一件好事。因為我討厭學校。不過,以前某個地方做過調查,我讀了那調查報告,讓日本人選自己最喜歡的詞語時,「自由」大概是第四或第五名左右。要是我的話不管怎麼樣都會把「自由」放在第一,日本人最喜歡的詞語卻是「忍耐」或「努力」喲。
……
河合:
雖然不是說因此才有佛洛姆(Erich Fromm)的。不過你看他寫的《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所以從小就要教育,"""自由是多麼美好的""",多麼可怕的,這是教育的根本。因為我喜歡這位老師,於是我就常跟這位老師對談,高明的老師會讓小孩自由發展。讓小孩自己去做。於是小孩會做得很不錯。雖然也會做出一點奇怪的小東西,不過奇怪的東西也要讓他們去做。
quot;""現在的教育都灌輸他們各種知識對嗎?所以人生智慧部分的學習反而疏忽了。日本的情況特別嚴重,從小學開始就已經要他們「用功讀書」。用功讀書跟人生根本沒有關係。""" 上次我跟Donald Keene先生談話,金先生年輕時候為了拿獎學金而非常用功地讀過數學。因為數學容易拿到好分數,對領獎學金非常有幫助。因此數學上他不知道有多麼用功,可是他說,那樣讀的數學對我的人生一點幫助也沒有(笑)。我說那倒也是。
《約束的場所-地下鐵事件Ⅱ》读后感(四):姓名:C
一个外国人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要不要自杀?
1980年左右,在村上刚刚写完《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球游戏》时,他决心当一个真正的作家,但是这有一个问题,作家有两种:追求故事的,和追求语言的。他想了很久,决定自己要做一个主要追求故事的作家。所以在18年之后,与心理师河合对话时,他自称“小说家”(fiction,非写实创作者)。我认为,与在小说里四处埋伏笔,照顾到每个角色的出场比例相比,创造故事的人,更应该有的素质是要把握故事发生的原因:这个人为什么做这件事,那个人为什么做那件。
会亲自去做纪录片式的沙林事件双方采访,也是因为他感觉,这件事情可以解答一些原因。就此他做了个有趣的比喻:一个160的男人手拿小小的锥子从对面走来,在擦身而过的时候,有可能你的感觉是一位180的大汉,拿着棒球棒。哪一个是真实呢?“所谓世界难道不是每个人眼中的世界吗?”所以他要记录两边的真实,就写了采访受害者的《地下铁事件》以及采访奥姆信徒(都不是实际去投了沙林的人,都是信徒)的这本《约定的场所》。关于世间事的原因。他得到了答案,在每5天采访一人的工作里,就好像粘在一起的肥皂泡,一个一个破开,并入邻居,最终指向最大的“一个”泡,在破灭之前被人眼捕捉到。感谢这本书,我也找到了一点答案。连带着与人有关的书籍,也可以心同此理,在读的时候同时翻关于《金枝》(虽然没看完)、《史记》(虽然没看完)和《玉君》都可以有更多层的读后感。
这答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我要不要去死。
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人生的意义是虚空。人不接受自己的意义是虚空。
访谈里的一个人A说:我小学六年级时候看到一把剪刀,忽然想,这把剪刀虽然是大人努力做出来的,可是总有一天会坏掉。有形的东西总有一天会坏掉。一切都会毁灭,毁灭是宇宙的法则,以后他就以消极的眼光看世界了。
C高中毕业的时候想,要不要出家?或者去死?实在讨厌去公司上班,讨厌就业。一面这样想,一面在汽车零件公司工作。
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星期天自己在家里,在阳台溜达,觉得活着真无聊。我想死,想了很多次。我讨厌和害怕那么多作业,觉得人真可怜,必须要学会那么多字,真可怕。结果我没死,但是小学四年级清楚地想死现在还是记得很清楚。我活下去的动力,只是每个月可以看到新的《童话大王》。
“一存一存,你又错了,为了这几张纸,你做了个雇佣式的教员,野鸡式的兼教!”这是《玉君》中男主角在北京教书,领到薪水时对自己的咆哮。上班领工资的你,也这样质问过自己吧,有没有?
这是对存在价值的疑惑,对目下无谓地被剥削的困惑。可是又能怎么办呢?别人不都是这样过的吗?
很对,很好,很高兴还有别人。
《史记》开头,颛顼的权力又下传了几位,到舜,“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贤人政治,使得漂泊的民心有所归,这是民有福。这不是贬损民愚昧,如果大多数人都思考过人生意义,并且不得不放弃追寻意义,那么大多数的人都是愚昧的。这推论中间的一步是:放弃对意义的追寻,就需要承担虚无的痛苦,这痛苦如此之苦,以至于人忘记自己是自己在活,而渴望沟通,渴望见到别人和自己一样,渴望温暖与引导,交出自己,谁又没有在向外交出呢?
信徒里有几位都认识到,现在的公司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宗教,拿不定的事情,直接按照上司怎么说就怎么做好了。“实际被害的,得了后遗症的乘客,也有几位回答村上,说如果上司命令去投沙林,自己真的就去投了。”
说到公司,你真的以为你的公司就没有在杀人吗?你在哪一步上做了什么的推手,既然拿了钱,绝对脱不干净,只是大多数没有直接到会做噩梦的地步吧。
后记里提到一位被现实社会推去做凶手的“体贴的林医生”。林郁夫本是热心的医生,对医疗制度医院体系失望,(看过《白色巨塔》的人可以了解那失望是怎样接近绝望)后来入了奥姆,成为精英。会对社会失望的人,都是有纯洁心愿的人。他亲手投放沙林这是不可原谅,但是他本来是个得到好评的好医生的。
A怎么进入奥姆的呢。因为他自己买了小册子练功,身体有感觉,又去奥姆的道场,就被劝诱出家了。采访的这些人基本是这个路数出家的。
所谓出家,就是将家人、私人物品、朋友、工作,全部都在一天放弃。这在我们看来不可思议,其实也好理解。人生虚空,除了修炼再无意义。死有何妨?出家就好像死一样,死的时候还可以带家人和工作走吗?想到这里,他们就什么都抛弃了。有没有意义先另说,起码可以少苦一点。
前几天与两位日本通的老师聊天,提出我的疑问,他们几乎以为我是在为奥姆辩解而攻击我。现实的人想到地铁沙林事件,第一谴责的就是:你凭什么、有什么权力去剥夺别人的生命?
我试图体会,奥姆的人以为:杀了你是替你圆满,你的人生不值一提。
但是在对话中,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有不公平的地方,在于奥姆的人鄙夷世人,不给他们说话的机会。这也是疯子的逻辑。我认为怎怎,你闭嘴,我觉得怎怎,所以怎怎,你闭嘴,怎是怎。
正确的态度应该是:
你好,请问你的真理是什么?
xxxxxxxxxxx
好的,但是我的真理是认为你应该死,不管你是谁,我是不是认识你。
xxxxxxxxxxxx
你说的不对,xxxxxxxx
你神经病,xxxxxx
接下来俩人可以论道。其中任何一方也有回避不理的权力。这样就比直接扔沙林公平。
但是奥姆的人不会给世人辩解的机会。访谈里的B这样说:在奥姆的公社里,他们做活也不像社会上那么有效率,什么事情说“啊,我忘记了。”都不会有人追究,慢吞吞的。什么问题和故障发生就说:“啊,业障除掉了,真庆幸。”因为他们自觉认为,俗务不值得紧张。所以教团的人轻视外面的人:你是苍蝇吗?你是蚂蚁吗?都为这种事情而烦恼。可是我们却心平气和。
F入信以后,渐渐看不惯教团,因为发现团里的人有这样逻辑。好像我在开快车撞到别人的车子,教内的人会觉得:撞了你也没关系,因为我在做更重要的事,是为了救济才赶路的。这样把别人当傻瓜以及憎恨别人,在F看来很过分,F本来对世人的鄙夷由此减少了很多,他开始反省自己这样瞧不起人不对。F真是个可爱的人。
而世人对于这些迷途孤儿,态度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日本通说,现在的民众对奥姆的人是有歧视,房东不会租房子给他们。D说,有人要求他们放弃教义,那样就考虑接受他们。但是他认为教义没有错,怎么可以放弃呢。
事实上是庸碌的众人将“不同者”推入不同者的角落。
A说,学“七跌八起”这成语,反感大人,为什么跌下去七次,起来八次呢,那多的一次在哪里呢?都没有人认真告诉他。
我也是。初中化学几乎得满分。以为自己学到的是真理。高中时候,课本都不同,以前当水是纯粹的,不会参与化学式的,高中老师告诉我,那是因为怕初中学生理解不了,所以权且那样讲,其实那是错的。真是不可相信的东西,玩弄我们的信任。
敏感的人,将成长历程里的件件挫折积累起来,变成对正常人间不信任的态度。没有调整到这一点是他们生存技能的欠缺。不同者应该自生自灭,想死就去死好了。为了人类筛为更乐观易活的种族,大家不是都在这样做的吗?
E对于目前的生活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不满,只是对自己在这个社会上,这样活下去,经常感到类似“不足”、“不满”的感觉。
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这样想,或者觉得“能活着已经很幸运”,不再追究其他。对我现在来说,大家都知道我们要结婚,不结婚是神经病是失约。有一次不高兴,老许劝我说:你现在有工作做,有婚结,是多少人羡慕的,你还好意思不高兴吗?他说的有道理。也许我就这么结婚,过下去,也许有了孩子就会有意义,那如果到他们青春期,背叛父母的时候,会是什么心情呢?或者那时候已经衰老,不再计较,以能吃到明天早晨的包子为目的,自私地活下去。
可是我还会想,如果像泽木耕太郎一样,离开这个国家,去哪里流浪几年,该多好。这是一个离我越来越远的梦想。自己也慢慢变成为背叛梦想找很多借口的普通人。
10年前,我在课外认真地学日语,没有想到会有什么用处,就是想学。那时候川大东区操场的看台底下,倾斜的小房间里,住着一个老疯子,他穿的邋遢,念叨着俄语,在校园里走来走去。听说他是俄语系的硕士,或者博士,好像大家都叫他张博士。他没有工作,俄语学得很好,是痴迷俄语的人,但是没有工作。因为别人不喜欢他。也许他有自己的问题,也许只是际遇不好。看看这人间又美好到什么程度?
村上会问每个人:如果你接到命令去投沙林,你会不会去?
在回答时说自己不会去。有的人回答自己会去。B的理由是:我害怕,我对于别人的转生还没有看透,我没有权力要别人死。但是B认为,教主已经可以看透了,教主命令这件事是一点问题没有的。也许,由高级干部去做这件事,是因为他们已经修炼到可以看透了,一般的信众也许可以就此理由接受大师兄们去做的这件事。
C与父亲相处很不好,父亲弥留的时候说“我们来把话谈清楚吧。”C回答“拜托,你干脆死掉算了。”事后回想,觉得是自己杀了父亲。
后来C在琉球遇到高明的巫师,又读了Lyall Watson《非洲的白色咒术师》,那里说跟平常人一样,普普通通地结婚,普普通通地生儿育女是最苦难的修行。由此他就安心上班,一度想要好好孝敬父母了。
比较起来,C还是更喜欢教团里的人,比能在世间很适应地过一般生活的人更容易感到亲近。他认为坏人只有麻原一个。麻原是很有力量的人。
这就说到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教团有能量?为什么大家纯洁的修炼,最终会导致杀人的事件?
这与226事变后的军国主义,与中国的60年代甚至斯大林时候的集权都有相似(村上在后记里比之于1932年的满洲国):越是带着纯洁的方针目的的集团,其中心越容易扭曲。在漩涡的最里面是失控的“动物”。麻原装作咳嗽,说:“我们受到攻击,咳咳,我还只有一个月可活。”信徒就痛哭。这个团体卓越并且纯洁,它会引导大家走向和平的乐园吗?不,它必须与外界敌对。和平的乐园并不卓越,也与纯洁南辕北辙,没有反省,没有修正地一路走去,只能使事态膨胀,如果不会自觉修正自己,那只能膨胀到自己消灭自己的地步。每一位信众的纯洁的信仰都应该对此负责。
H认为,投放沙林不是宗教性的冲动发疯,而是有深思熟虑的宗教目的的,但这面纱背后的东西,只有麻原和心腹村井俩知道,其他人只是棋子。H是在沙林事件之后脱会,并且写书批判奥姆。与可爱的C比较起来,我鄙视H。
H提到“终末观”,就是末世理论,这与麻原表演自己要死了,假装被外界攻击一样,是一种畸形膨胀的需要。不过他有点辩证地看沙林事件,将之视为很多年来日本社会积累的怨恨、扭曲的一种释放,释放之后日本社会会得到净化。但是真正的问题是细菌一样滋生着的“终末观”(我认为是人生虚无),这不可能被消化和消失。
麻原是什么人,从别人的描述看来,类似国内的大师,某种程度的超人之处恐怕还是有的。
人有这么多,手长脚短,肤色理解力各不同,其中会有手特别长的,自然也会有特异功能者,这样的人如果认识到自己的能力,有尝过控制别人的快感,既然大家心里都有忐忑,为什么不借此请你们跟我走,去试试看可以走到哪里呢?总好过立刻死。
《史记》开头一个家族故事,说颛顼是个好领导:“动静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连神都听他号令,可见他是个巫师。
那么纯洁的信仰,为什么变成对一个人的盲信了呢?只是因为见过几次神灵般的特异功能表演吗?
D说,这好像解数学题一样,在到达一定程度之前,只能相信老师所说的,照着做下去,没有别的办法。这条定理啊,这个公式,不相信这些,就没办法解答问题。
昨天我男人说,有一个走到一半自觉说了停止的例子,是二战时候的西班牙佛朗哥政权。二战中他宣布中立,背叛了之前支持他独裁的希特勒,战后又迅速亲美,种种“中间自觉停止”的行为,使得他统治西班牙几十年。所以说,没脸没皮的人才适应俗世,这也是C这样单纯的青年会投向奥姆的原因。
别人攻击奥姆的理由,之一是,麻原怎么可以让自己的孩子就那么继承教主的位置呢?这好理解,因为没有办法心无芥蒂地接受其他人,真正能够容忍的,只有自己的孩子。
D出家的时候,父母气得不得了。因为他们不认为奥姆是佛教。我问两位日本通老师,一般日本人也不认为奥姆是佛教。
D:觉悟到过去认为是自己的东西其实不是自己,近似苏格拉底的“无知之知”,所以说佛教是离“心灵控制”最远的宗教。这是字面游戏,奥姆里的人被劝导说,因为觉得自己不是自己,所以舍弃自己。其实每一个听信了这说教的人,都是惧怕做人的责任,将之全部推卸给教主,所谓离“心灵控制”最远的理由,也就是没有了自己,没有自己的心灵,谈何控制。但这种舍弃,本身就是一种控制,是教主的收集。
每一个人都将自己奉献给教主,由此导致的任何后果,都是教主的功业或者罪孽,借此达到自己的安稳平和。其实这样的信徒,本身就是狡猾和自私的。虽然也许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
E认为,奥姆的手段是把“自己”和“烦恼”同一化,为了消除自私,必须把自己一起舍弃。E认为这扭曲了佛教的教义,真正的解脱应该先把自己找出来,而不是简单抛弃。正因为交出了自我,才会对杀人这样的事情失去感觉。
E说教团里有残酷的修炼,也会有体罚,会听到人大声求饶,死去活来,而最后有人温柔地对你说“你熬过来了,真好。”你就会想:“啊,我已经通过考验了,尊师,谢谢你。”
这种伎俩的名称我忘记了,在野蛮人的成人礼,在高校接受新生的考验仪式上都可以见到。人在受折磨的时候,也就雌伏,并且从心底认可了折磨自己的这方。
G被吸引的理由正是“自己可以不用想事情,自己可以不用做决定。”在已经解脱了的麻原大师引导下,一切已经为大家安排好了。多么美好的天堂。
以前的G觉得自己,没有专长,没有什么地方特别优秀,就这样活着很疑惑。入会又脱会后她说:没有就没有地活下去又有何妨呢?
有一点我与村上一致,这不是偶然的事件,这是关于个人与社会,这是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的事情。不过推得太泛,话也就没了建设性,也许建设性应该是:记得自己有罪,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题外说一件有趣的事情。
对C来说,出家最大的困难还不是这些,而是费用太贵了。看到道场里大家都二十万、三十万地交钱,觉得非常可怕。C自觉是个穷人,所以特别吝啬。
后来因为会费打折又打折,C就加入了。其实在刚加入没多久,C就发现麻原有问题,那些狂热他觉得可笑。但是沙林之后警察找C,“最近奥姆有没有联系你啊?”C想,哎,不知道有什么状况,要不要去看一下?
他就跑去奥姆的道场附近张望,又想,这些书以后就买不到了呀,就到处收集奥姆的书。结果警察一直在跟踪他,他就又被带去警察局被盘问好久。
另外,宗教与写小说也相似,这相似在《1Q84》体现为天河的才能。
我写的都是我私人笔记,不是宣扬人可以无差别杀人。我只试图理解这些人,因为他们身上有我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