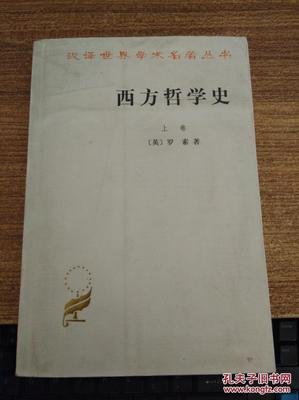
《中国哲学史》是一本由冯友兰著作,后浪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68.00,页数:76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哲学史》读后感(一):用西洋之法研究中国哲学史
以往的阅读范围几乎没有涵盖哲学领域,这次读新版的《中国哲学史》,确实有点力不从心,断断续续花了很长时间。书中大段大段地引用古代典籍的原文,细读实在费劲,只能勉强跳着读。在这里,写一点琐碎的感受。这本书是冯友兰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准。后来这本书的英译本在西方问世,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哲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大目的是“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到实质的系统”,因此他主张学习西方哲学的原则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比较中西哲学,从而建设中国哲学。
在这本书中,冯友兰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两次社会巨变,第一次是从春秋战国到“大一统”局面,第二次是晚清闭关锁国到被迫开放,由此他将中国哲学史划分为古代和近代两阶段,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范围局限在中国古代先哲的思想。借鉴西方哲学的方法论,冯友兰将中国古代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
“子学时代”百花齐放,思想自由。各家学说言论层出不穷,平等辩论。冯友兰对孔子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中国哲学的开山之人,也奠定了儒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从春秋到汉初,贵族政治没落,旧的社会制度崩溃,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子学时代”结束。
“经学时代”的原则就是将古代的东西当作经典,后人只能做字面的解释,其他都不能动。儒家典籍被历代统治者选为“经”,“六经”成为儒学思想的标准和基础,人们只能不断对“经”进行阐释,极大压制了新的见解。这一时代延续千年,直到晚清,冯友兰认为“经学时代”总体上是保守的,哲学理论虽然更清晰丰富,但创新的成分有限,多是“旧瓶装新酒”。
相比胡适的“疑古派”,冯友兰自称为“释古派”,既不会迷信教条,也不会全盘否定,他主张“同情之了解”,在做哲学研究时应该换位思考,从被研究的各家各派出发,尽可能客观全面地阐释古代先哲的思想理论,因此他很注重探索时代背景,以追溯各家各派的来龙去脉。这种治学态度贯穿在全书之中,也是这本书的调性颇为温和的原因之一。
此次后浪的再版,以1947年的版本作为参考底本,尽量保留了冯友兰的原文,也对正文和引文做出校勘,足以看出编辑的用心和辛苦程度。装帧很舒服,纸质的手感也不错。七百多页,捧在手上很有质感。我不太喜欢这款封面设计,其实可以更简洁一些。
《中国哲学史》读后感(二):试以严刻理智之态度读哲学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的绪论部分就提到,他试着兼顾“叙述式”与“选录式”两种方法来写中国的哲学史,所以整本书最终呈现出非常完整的一个“中国哲学”体系。细读下来,常有“原来如此”或是“需要再仔细想想”的感受。就如金岳霖所说:“他没有以一种哲学的成见来写中国哲学史。”并且能将诸家思想的相互交融及彼此影响都涵盖其中。
无论是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在哲学的分类上经常采用时间段进行分类。胡适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将其分为三个时代:古代哲学、中世哲学、近世哲学。而冯先生采用的是另一个观点,即将整个哲学史分为两部,“自孔子至淮南五为子学时代,自董仲舒至康有为则经学时代也。”他认为西方哲学引入中国后,整个中国哲学将会是另一派走向。只是“尚无卓然能自成一系统者。”所以本书关于哲学史的介绍也到此阶段为止。
冯先生提到中国哲学家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多注重于人之是什么,而不注重于人之有什么。”从而也导致了“中国仅有科学萌芽,而无正式科学”以及整体逻辑的欠缺。这与大家谈论起中国文化始终是重道德忽视正义,有异曲同工之感。所以在这本书中,冯先生是比较克制的没有过多表达自己的个人喜好,而是将所有观点一一客观呈现。而关于哲学的书写,冯生生强调的是“皆必以严刻的理智态度表出之。”似乎为了呼应他自己所说的“严刻态度”,在讲述任何观点之时,全都附上之所以得出此观点的原文作为“论据”供读者一并思考。
《中国哲学史》体量非常宏大,从孔子开始,至廖平的经学五变,将整个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思想文论都通通编进此书之中。有时候冯先生也会对各位思想家以简短有趣的评价,使能人更好的去理解他们的言论。比如说孔子“平生以好学自负”,而“孟子乃软心的哲学家”,“荀子为硬心的哲学家”。诸子百家,各有千秋,又互为影响。随着时代的不同,又衍生出不同的思想言论。在子学时代,提到“天”时,冯先生时常将其解说为“上帝”,可见当时西方基督教之思想也亦影响很深。而本书印象最深刻的在于经学时代佛学之介绍,从哲学的角度将佛学的思想倾向与其支脉介绍的非常详细。从南北朝时期佛教思想引入至宋初,“中国之第一流思想家,皆为佛学家。”而佛学思想中加入了诸多中国思想之倾向,中国佛学与印度佛学又完全不同。从南北朝时“多有以庄学讲佛学者”,至佛家学说一变而为儒家之说,其中再加入道教中一部分思想,从而融合为“新儒学”。至此也就能清楚的理解为何近来我们常说的“儒学是中国几千年来政治、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基石”。
由于整本书成稿于20世纪30年代,书中所使用语言习惯与今日的我们已有很大差别,再加上占据了很大比例的古文引用,使书读起来并不轻松。需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并顺便温习下并不怎么熟练的古文阅读知识。但是读着古时思想原汁原味的文章,内心所受到的感触与启发还是完全不同。若真心想厘清中国哲学思想之发展与脉络,本书是不错的选择。
《中国哲学史》读后感(三):《中国哲学史》: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奠基之作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写于20世纪30年代,其时中国尚无完整的哲学史研究著作问世,作为严谨的学术著作,《中国哲学史》填补了此项研究的空白,至今仍是现代中国影响最大的哲学史著作。
此次后浪出版公司再版的《中国哲学史》是史上最全、用力最勤的一个版本, 逐字核查引文,对于一部70万字的著作来说,其背后付出的工作量自不待言。而新增校勘表、人名译名对照表 ,方便了我们理解内容,毕竟冯先生写作此书时所采用的语言和习惯与我们有较大的隔膜。此外,书中注释部分对于理解书中内容也有所助益。
我们为什么要读这本书?用韩国前总统朴槿惠的话来说就是:让自己找回内心的平静。在今天这个浮躁忙碌的社会,内心的平静无疑是最值得珍视的。读《中国哲学史》,能有这样的收获,可见虽是学术书籍,亦可在普通人的生活中起到意想不到的影响。
我们要怎样来读这本书?读此书最大的一个障碍无疑是其文字是半文半白的,对于远离文言文传统的我们,无疑是一个挑战。参照冯友兰先生著的《中国哲学简史》,是一个好的办法。《中国哲学简史》是用英文写的,同为后浪出版,赵复三用纯白话文翻译,是书内容精简,并且易于理解。两书参照,对于理解《中国哲学史》这部学术著作有很大的帮助。
《中国哲学史》一书虽然厚重,全书却极有条理,逻辑清晰,表述简洁,思想深刻,多有创见。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子学时代,从孔子至西汉淮南王,下篇经学时代,从西汉董仲舒到清末康有为。对于各时代主要哲学家及虽非以哲学家名世但有较突出哲学思想的人物,均有介绍,能抓住其思想精髓,给予一针见血地阐发,如古文经学家扬雄和王充,指出其贡献是使儒家学说和阴阳家学说分离,有开魏晋时代思想的先锋作用。
冯友兰先生对于不同流派的哲学家注重其相互之间的影响,同时又注重本流派不同时代的发展趋势和同中之异。如指出儒墨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儒家重义,墨家重利。儒家奉行实用主义哲学,墨家奉行功利主义哲学。而同为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孟,孔子讲仁及忠恕,多限于个人的修养方面,孟子则应用于政治及社会哲学,孔子着眼于内圣,孟子注力于外王。
哲学的本质是爱智慧,而智慧要应用于我们的人生。冯友兰先生在讲解庄子时,一语道破幸福的真谛:“幸福不是求来的,只须‘顺其自然’之性。”冯友兰指出庄子的幸福之道正是这样:凡物皆由道,而各得其德,凡物各有其自然之性。苟顺其自然之性,则幸福当下即是,不须外求。
细读《中国哲学史》,才会对古人多一点理解。儒家因为注重实用主义,其观点均必须有用。如关于婚姻只注重其生殖目的,所以孟子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儒家是不考虑爱情的。因为不重视爱情,在独尊儒家的封建社会,才会发生陆游、唐婉这样令人痛心的爱情悲剧。
《中国哲学史》讲述了一部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思想史,通过这部哲学史,我们也更加容易进入古代社会,对于古人思想生成的文字典籍,才会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儒家、道家、佛家共同缔造了一个思想复杂的中国古代社会,处于各个时代的人身上,多杂有各家思想,如我们熟悉的大诗人杜甫,身上就兼有儒家、佛家和道家的思想成分在,这其中儒家思想占据主要部分, 影响他的立身行事和诗歌创作。
《中国哲学史》让我们了解各个哲学流派及其思想,对于中国古代哲学的发生、发展脉胳有了一个清晰的认知。从中我们也会悟出哲学绝不是阳春白雪,每个人的生命中都应有哲学的身影在。
《中国哲学史》读后感(四):《中国哲学史》:中国人喜欢怎样的哲学
我系统地阅读哲学史,是从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开始的。黑格尔认为哲学史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因为哲学的目的是真理,真理是“不变的、永恒的、自在自为的”,而历史却是一度存在,但到另一个时代却又消亡的事物,“如果我们以‘真理是永恒的‘为出发点,则真理就不会落到变化无常的范围,也就不会有历史。但是如果哲学有一个历史,而且这历史只是一系列过去了的知识形态的陈述,那末这历史里就不能够发现真理,因为真理并不是消逝了的东西。”(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
哲学史存有这样的矛盾,而“中国哲学史”,矛盾就更大了。“中国哲学史”该作何解?是“中国哲学的史”,还是“中国的哲学史”?若是仔细考量,后者要率先出局,因为哲学到底是个舶来的概念。中国自古并无哲学,有的只是百家争鸣时的“子学”,以及不许百家争鸣后的“经学”。故而这部《中国哲学史》,其实是“中国哲学的史”,冯友兰先生是比于西方哲学之概念,令“子学”与“经学”纳入到“哲学”的范畴之中,才有了这本书的讨论。故而本书亦是以“子学”与“经学”做分期,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两编:子学时代以孔子为始,止于《淮南鸿烈》;经学时代起于董仲舒“独尊儒术”,终于廖平“经学五变”。同时冯友兰先生认为,比于西哲“上古、中古、近古”三时期,中国哲学“无近古”,盖因西洋哲学之近古,与中古哲学“其精神面目,实有卓绝显著的差异”,而中国哲学直至康有为、廖平时,“皆装于古代哲学——大部分为经学——之旧瓶内。”(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可以说,从不过二三百余年“子学时代”止,到历经千年的“经学时代”,中国哲学并无突破之见。
缘何?西哲自中古至近古的剧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科学革命之驱动。钻研“针尖上究竟能站多少天使”的经院哲学,终究要让位给更贴近现实世界、贴近“人之本质”的康德、尼采之流。但中国之现实旧瓶并未打破。纵然被“地球绕着太阳转”“马车不如火车快”的现实吓得一激灵、再激灵,中国哲学依旧可以安于治理与驯化的旧瓶。了解了地球并非绕着太阳转,也没法让人们放弃传统的伦理纲常,真正关注现实损益和人之本身。
因而这里便体现出又一个对照,即纵然人们不愿相信、不喜欢“地球绕着太阳转”,但总要服从于科学实证,要发展更真切、更“真理”的哲学理论,要思考“头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准则”。但中国哲学却存在一种偏好特权:那煊赫一时的、占了上风的“显学”,多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而中国哲学的脉络,也正是以这样的方式被推动。这一点,在《中国哲学史》中多有体现。依笔者愚见,中国人对哲学的偏好,盖有以下三点:
其一,重伦理而轻逻辑。实际上,伦理学与哲学的界限问题,始终是要严肃讨论的。英国当代哲学家伯纳德·威廉斯的著作《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便指出伦理学的对象应该只能使人的伦理生活,而不应该是人的伦理反思。如果把伦理学定位为后者,并且一味地要在一定的理论起点上为人的伦理活动寻找解释,就会实际地破坏了我们的真实伦理生活面貌。但在中国哲学的范畴里,我们并不会区分伦理学与哲学的界限,大多哲学家,都在传授生活的应然之规。既然是规矩,就不必有逻辑,于是讲“天下为公”的,亦可信“一毛不拔而利天下”——关于世界的真理,一切全在如何解释。再进一步,“我”的解释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我”有没有掌握“解释的权利”——法、术、势原本层层递进,但实践起来却混为一谈,仅剩强权之道、胜王败寇;
其二,重“一统”而轻“分立”,观中国哲学的发展脉络,每一时期都有非常清晰的“合流”趋势,无论是战国末“道术统一”、经学时代初的“百家合流”,还是宋明以降的“三教合一”,人们似乎乐见“天下大势分久必合”,而视“合久必分”为“艰难时代”。但实际上,百家如何合流,三教又怎能统一?无非是放弃差异,承袭旧制以合乎时宜,选一“核心价值”而取消所有差异。因而论医者亦称“手足瘘痹为不仁”,奏乐者亦有或靡靡或“进步”之分,偶尔活泼,却终要“严肃”;
其三,避虚而就实。这一点就佛学的传入而论最为典型。佛学本为虚空之学,“如露亦如电,如梦幻泡影”,但进入我国,便需摒弃虚之愿景,传授“极乐净土”“立地成佛”之实道。相应地,如唯识宗之吾人之识皆“依他起”等提法,则与中国人之思想倾向并不相合,凡事皆应有实,怎可“ 外无内有,事皆唯识。 ”。但需注意的是,这里“避虚就实”,“实”又需以“虚”来达成,譬如理学与心学之争,到底是“吾心即是真理”“个个都是圣人”占了上风,而至于信仰,更是无人惦记着苦修,一心只想着“放下屠刀”——哪怕自己不过是鱼肉。
《中国哲学史》写到最后,冯友兰先生倒是有几分希望的,毕竟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冲击之下,“旧瓶”早已碎裂,是时候“贞下起元”,期待新的开端了。但“贞下起元”这个词本身偏重的便是“元亨利贞”之如环无端,盖因创造的时刻在人类历史上少之又少,循环往复才是常态。旧瓶已碎,新瓶却也可以是“新的旧瓶”——反正,是我们喜欢的那一个。
西人赫胥黎有云“我们终将死于我们喜欢的事物”,然中国文化绵延五千年亦未断绝。故中西有别,诚不我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