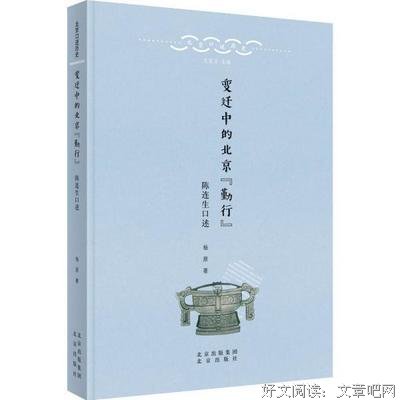
《变迁中的北京“勤行”》是一本由杨原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432图书,本书定价:平装,页数:2020-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变迁中的北京“勤行”》读后感(一):另一视角下的史料
看到这本书的名字时候,容易有种误解,以为会讲很多1949年之前勤行人的历史。口述人陈连生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末,1948年当“六合顺”饭馆学徒的时候才12岁,并未有太多民国时期的行业经验。据其讲述,自己刚进城没几个月,北京就围城了。1948年是内战最激烈的时候,物价高涨,很多饭馆也没有客人办不下去了。“六合顺”的老板掌柜的跑路,只留下他一个小孩看铺面。
1950年开始,对私人资本进行限制。所谓限制,就是控制原材料。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比方说一个饭馆,每天需要60斤面,结果只提供30斤,那自然是不能好好做生意的。既然没有足够的原材料,很多勤行就只能歇业或者是勉强维持。
1952年开始“三反”运动,针对勤行主要是“反五毒”(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斗争。工会把勤行里的工人组织起来,让勤行的老板们站在台上,开展“说理会”,痛斥他们如何虐待和压榨工人,揭发举报他们如何往酒里兑水等弄虚作假。
有些人只好关闭饭馆,但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很多人因此失业,经济也不能发展。所以一方面对资本家又采取了“限制、利用、改造”的方针,给予他们经营权、用人权和管理权。另一方面,勤行中的工人也被说服主动要求降低工资。陈连生自己的工资就从9万降到了6万。
这样的日子也没有维持太久,1955年开始了清产核资,对所有企业进行清算。把饭馆里的桌子椅子等固定资产和生产工具核算一遍,按照这个核算出来的总数,给饭馆所有者每年0.5%的利息,保持7年不变。7年后成为公私合营企业,该饭馆成为国家财产,饭馆曾经的所有者不再有任何补偿和经营收入。这些所谓“资本家”是家财万贯、财大气粗吗?好像也不是。据陈连生回忆,六合斋的老掌柜早上吃饭也只是一碗茶就俩焦圈儿,儿子小掌柜就没的吃,只能看着。
1956年以后全面公私合营,饭馆们大洗牌,往往是几个饭馆合并在一起,保留原来的招牌或者换个新名字。因为翻身当家做了主人,不再受资本家剥削,工人们的积极性非常高,每天工作都在12小时以上毫无怨言,简直让现在的996相形见绌。
陈连生后来去的“南来顺”,也不是旧时的“南来顺”。老“南来顺”是石昆1937年在天桥开的店,最早是靠卖爆肚起家,后来添了涮肉,渐渐出名。新“南来顺”是1961年原“南来顺”和菜市口小吃店合营而成,地点也迁到了菜市口。当时的目的是把这些有名但是规格不高的小饭馆改成高级饭庄,以达到“货币回笼”的目的。
过去买东西都凭票,没票有钱也买不到。货币回笼就是可以不需要票,高价买东西。例如本来这东西凭票是1块钱,不凭票是3块钱。票都是限量供应,但有的人工资高,有能力多花钱买点好吃的。不过1961年,大饥荒刚过去,就算是好吃的也未必有多高级。
陈连生的视角不同于以往“吃客”的视角,但也不是一个勤行普通人的视角,而是一个经营管理者的视角。由于长期在公私合营后的南来顺工作,谈话内容更多涉及的是个人经营经验、人员管理,并未涉及更深的行业信息。整本书的叙事线索比较混乱,民国史料较少,因而难以做出更多更深的对比。另外陈连生主要是在南城清真饭馆从业,其他地方的大教饭馆了解不多,所以感觉这书的名字起得有点大于内容。
另:p5. 关于民国时期的“斤”,括弧内写“1斤为0.5千克”,太草率了。民国时期是十六两秤,1斤并非0.5千克。如果陈连生此处确实说为后来的市斤,编辑应该注出。
《变迁中的北京“勤行”》读后感(二):“北京小吃第一人”陈连生回顾“勤行”变迁
《变迁中的北京“勤行”》是陈连生讲述北京餐饮业变迁的口述历史。在这本书中,在“勤行”奋斗一生的陈连生回顾了他在餐饮业几十年的从业经历,讲述了他在经营南来顺、吐鲁番餐厅过程中的个人经历、从业经验、行业变迁以及相关的菜品、北京小吃等知识,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关于“勤行”的传统和北京小吃的内容。
“勤行”是老北京话,指的是餐饮业等需要手勤眼勤的行业,饭店、茶馆跑堂小二这些直接招待客人的职业,正是“勤行”。
陈连生是老北京餐饮业中的泰斗级人物,解放前就已经进入勤行在饭馆当学徒,解放后他又花费几十年精力经营南来顺、吐鲁番等餐厅,业绩非常出色。他既懂餐馆的管理经营,也懂菜品小吃,被誉为“北京小吃第一人”。
传统“勤行”里主要分堂、灶、柜三部分,“堂”管跑堂,直接服务来吃饭的客官,“灶”自然是厨师组,管炒菜做饭,“柜”管理财物,进货、验收、库存、经营记录相关。
在经营过程中,陈连生也非常注重堂、灶、柜三方面的管理,发挥各部分的优势,聘请有独特技能的名厨、打造特色菜品,食材质量也严格把控,他还尤其注意发挥堂头的作用。
在“勤行”里,堂头担负着拉客人、营销菜品和拴住客人的重大任务。优秀的堂头往往能凭借卓越的服务,吸引客人们追堂头。假如这样的堂头换了一家餐馆工作,他的铁杆客人们会随着他光顾他所在的新餐馆。
这主要是因为堂头熟悉客人的饮食偏好,不需要客人费口舌,就能够根据餐厅现有的食材储备,自动为客人安排合胃口的饮食搭配。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样的堂头就是一种VIP服务了,客人自然满意,能把“头回客变成回头客”。
陈连生在经营过程中,就非常注重发挥堂头的作用。当他了解到客人遇到了难事的时候,即使事情与吃饭无关,只要能帮忙,他都尽量帮忙。因为多次帮客人解决了非常棘手的问题,他赢得了很多忠实客人的支持和赞扬。
陈连生非常熟悉北京小吃的各种类别。很多小吃都是贫苦百姓填饱肚子的方便吃食,比如边走边吃的“手拿食”,包括烧饼馃子、火烧、锅饼、烤白薯、糖油饼等。
他还提到,以前那些生活困难又没赚钱方法的人,被称作“没落儿”的,会去抢别人的“手拿食”,咬一口、舔一下甚至吐两口唾沫,就算能要回来,被抢的人也不能吃了,只好放弃。在1985版的《四世同堂》电视剧中,就有八个孩子的父亲陈野求在街上抢祁瑞宣手上油饼的桥段。
另外,庙会上还有很多种“碰头食”,大人带着孩子逛庙会的时候,碰到了就顺便给孩子买着吃,比如豌豆黄、芸豆卷等。
说到底,不管是“手拿食”还是“碰头食”,都是给普通劳苦大众方便果腹的,只要能节省时间、填饱肚子或者尝个鲜儿就行。但是,百姓们还是尽量在有限的条件下创造出了不同的花样,为生活添点趣味。小吃记录的正是普通百姓生活和民间文化的一角。
无论是菜品还是小吃,必然随着时代不断变化着。在“勤行”经历了几十年,陈连生始终抓住了“变”这个字。从《变迁中的北京“勤行”》中就可以看出,他能敏锐地抓住时代的新需求、新变化,在变化中继承传统,在变中求生。这是每一个成功的企业管理者都必须掌握的准则。
有些传统小吃的制作方法中,可能存在不卫生、不健康的步骤,这种做法必然要进行改良。传统手工现做小吃,产出量有限,保质期短,不满足现代人的大量需求,于是很多小吃换成现代的流水线批量生产、卫生小包装,方便购买和携带。
人们的饮食喜好也在不断改变。比如“四做鱼”的传统做法中包含一项内脏,但是现在吃鱼内脏的人越来越少了, 新式的“四做鱼”就变换出各种鱼肉菜替换掉内脏菜。
饮食文化原本就是不断变化的。在变化之中继承传统的内核,通过创新使之不断改良适应新时代、新需求,不断更新换代,这样饮食文化才能保持活力,源远流长。
2020.09.17雾凇
《变迁中的北京“勤行”》读后感(三):从口述史中寻找老北京的风貌
在这些年“怀旧热”的潮流中,有关老北京的事物重又激起人们谈论的兴趣,比如胡同、遛鸟、茶馆、庙会、斗蝈蝈、琉璃厂、四合院、冰糖葫芦等等,可是大多数谈论往往停留在相对表层的符号层面,缺乏对老北京历史内核的阐发与论述。当代人谈论老北京,总会不自觉地带有现实意识和情感,以致或多或少偏离真实境况,而要想讲清楚老北京的历史内核,某种程度上非真正的“老北京人”莫属。
北京出版社从2014年开始出版的“北京口述历史”就是一套由“老北京人”讲述北京历史文化的丛书,到2017年已经出版两批共十部,今年又新近出版了《变迁中的北京“勤行”:陈连生口述》《“文物人”与“人文物”:常人春、常寿春兄弟口述》两部。这套丛书的主编是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定宜庄,她是国内著名的满清史学者以及最早的口述历史研究者和实践者之一。对于想深入了解老北京人真实生活的读者来说,无论本地“土著”还是外地“北漂”,从这套丛书入手,都是一份可靠的保障。
北京小吃溯源
卤煮、爆肚、焦圈、豆汁儿、炒肝儿……这些都是北京声名远播的代表性小吃,好这口儿的食客百吃不厌,抗拒的人则闻之色变。那么,相对于“大餐”的“北京小吃”到底怎样界定?如何分类?是否存在一定的标准?
《变迁中的北京“勤行”》一书的主人公、“南来顺”老经理陈连生生于1936年,12岁进入餐饮行业学徒,在行业内经历了1949年后的对私改造和公私合营、困难时期、计划经济时期、改革开放等重大变迁,是回答这些问题的不二人选。
北京老字号的清真饭庄有“老三顺”,分别是“东来顺”“西来顺”和“南来顺”,东来顺以涮羊肉闻名,西来顺以炒菜、烤鸭著称,南来顺则主要是用小吃吸引食客。陈连生从1961年到1989年在南来顺担任餐厅经理,堪称北京餐饮界“活化石”级的人物,素有“北京小吃第一人”的美称,由他来追溯小吃源流,再合适不过。从书中看,陈连生谈起北京小吃,也是滔滔不绝、如数家珍。
在陈连生看来,“北京小吃”这个概念是1956年餐饮业公私合营后成立各小吃店开始的,当时各区相继新成立了国营小吃店,北京城里最有名的是四大小吃店:西四、隆福寺、大通、南来顺。“这些小吃店里的品种,就渐渐地被叫做北京小吃。在这以前,没有这么叫的,等于是约定俗成。”
那么什么样的食物可以算是“小吃”?陈连生说小吃过去被叫做“手拿食”,顾名思义,就是可以手里拿着吃的食物,比如油饼、烧饼、火烧、芸豆饼、烤白薯等等,是劳动人民用来充饥果腹的食物,过去甚至还有一部分穷困百姓直接抢别人手里的东西吃。后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准提高,小吃的范畴也在不断扩展,可以分为早点、夜宵、零嘴儿、炸货、消暑、甜品等不同种类,包括馄饨、鸡汤面、炸酱面、豌豆黄、爱窝窝、杏仁豆腐、凉粉等今日大众熟悉的美味。
针对现在越来越多人感叹北京小吃毫无标准可言,陈连生提出,北京小吃其实有据可循,那就是计划经济时代下由饮食服务公司内部出版的“成本核算卡”。所谓成本核算卡,是上世纪70年代末时为了统一小吃的制作标准而核定的用料成本单。陈连生掌舵的南来顺因为是当时北京最大的小吃店,小吃品类多、质量高,宣武区(后合并入西城区)饮食公司就决定在南来顺搞品种试验,将每种小吃的用料标准确定记录下来,进而推广到全区、全市。
成本核算卡在当年的用途主要有两个,一是可供餐馆在计算成本时使用,二是可供饮食服务公司在检查工作中使用。例如,做100个糖油饼,需要面粉10斤,每个重1两,质量标准要求是“圆形鼓腔,直径16.5厘米,金黄色,糖面均匀,不糊”。陈连生保存的这些核算卡在当今市场经济环境下更显珍贵。
当然,书中不仅谈论小吃,还有关于南来顺饭庄的历史、经营“老字号”的感悟等内容,足以从食道风味见出人生况味。
诚如这部口述历史的访谈者、北京社科院满学所博士后杨原指出的那样,从以往北京饮食文化的文献看,大多是文人以食客的角度进行讲述,即便有的书是行内人所著,也都是一些菜谱类的工具书,陈连生的这部口述有很大一部分讲的是饮食行业本身和行业历史掌故,故而具备相当大的史料价值。
常氏家族的“人文物”
如果说陈连生是北京餐饮界的“活化石”,那么常人春则堪称北京民俗界的“泰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的主编定宜庄其实早在2006年就为常人春做了口述,可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书稿拖到2015年常人春去世时也没能出版。直到今年,常人春的口述才最终与弟弟常寿春的口述合为一册出版,被命名为《“文物人”与“人文物”》。
“文物人”或“人文物”,是常人春自创的词,用来描述像他自己这样的人,意思是有些人本身就是“活的文物”,他们的一生承载着城市的历史文化变迁,如果不重视这些老人,那么很多珍贵的历史记忆将随着他们的去世而湮没无存。在此意义上,定宜庄带领学生们做的口述工作,就是在打捞记忆、保存历史。
常氏兄弟的家世非同一般,他们的祖父常晓茹是满洲旗人,而且在民国年间曾任京兆全区侦缉处处长,类似于现在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根据常氏兄弟零敲碎打的回忆,常晓茹的传奇生平才慢慢浮现出来。访谈者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和时代背景,对常晓茹有如此评价:
20世纪初正值辛亥鼎革之际,在北京城已经维持了数百年的八旗制度及其带来的“超稳定”状态面临崩溃解体,旧有的社会阶层也被打破……在旧日的一切规则都被破坏,科举中第的出路也被堵死的情况下,知识分子阶层地位下降,但那些原在官方体系以外的人扩展权力、提升地位的可能性却大大提升。这是个催生了大量乱世英雄的时代,常晓茹应当就是其中一位。
作为一位乱世英雄,常晓茹如何得到京兆全区侦缉处处长一职,常氏兄弟已经无法说清,不过访谈者根据他们提供的信息可以推断,常晓茹在京城经营着一张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与北洋军阀、清朝遗老,以及各种宗教、会道门等都有来往和利益纠葛。
访谈中最重要的发现是常晓茹参加过“在理教”的经历。“在理教”据传创立于清康熙年间,以劝戒烟酒为名发展教众,规模遂逐渐壮大,到上世纪30年代,北京、上海、南京三地都形成了“理教会”。不过民国政府并没有将“在理教”看成是宗教,而是将其看作一个社会公益团体,认为它的目的还是“劝人为善”。由此也就可以解释常晓茹何以一生乐善好施、出手阔绰,甚至愿意收养一位与他素不相识却冒认是他儿子的陌生人为义子。
常人春后来之所以走上民俗研究之路,也跟祖父有关。常人春幼时体弱多病,于是常晓茹就带他到地安门外正一派道观火神庙看中医,并让他成为火神庙住持田子久的“记名弟子”(非正式出家修行,只是在庙里挂名)。虽然不算正式出家,但常人春每逢重要的节庆诞辰,都要到庙里去“随喜”,长期耳濡目染,就记下了很多仪式仪轨。
早年间,常人春学习各种民俗传统纯粹是兴趣使然,并没有做记录研究的打算。1955年,常人春给《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栏目写了一篇替胡风辩护的稿子,后来受到“胡风案”的牵连,去往东北农场劳动改造,结果一待就是24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落实政策”后,常人春才终于回到故乡北京,先是在上世纪80年代盛极一时的中国文化书院秘书处当秘书,中国文化书院解散后又通过政协成为“社联人士”,开始撰写、发表民俗文章,也出版了多部著作,在社会上赢得了一些名望。
常人春一生未婚,晚年略显落寞,甚至家宅拆迁后,只能寄居于北京民俗学会会长高巍家中,直到去世。访谈中,弟弟常寿春坦言他与哥哥的关系不睦,也指出哥哥在为人处世方面的许多缺点,这些都有助于读者加深对常人春这位民俗泰斗的理解。
从“小吴历险记”到《旗人风华》
在《“文物人”与“人文物”》中,常人寿透露了一点家族秘密:他们虽然都是满洲旗人出身,但1949年后填报户口时,报的都是汉族。这是因为民国初年时,由于满清统治的终结,满人在社会上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备受歧视,当时很多人无奈之下都改了汉姓、报汉族。常氏家族就是这股时代浪潮下的一例个案。
旗人是源于满清八旗制度下的贵族群体,他们曾经荣耀,世居内城(清代实行“旗民分居”政策,内城住旗人,外城住汉人),却又一夜之间跌下高坛,或主动或被迫地融入普通市民阶层,乃至渐渐被大众遗忘。但今人热衷于提及的老北京文化其实很多都属于旗人传统,因此谈及老北京文化,旗人一定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北京满族翻译家、作家罗信耀曾在民国年间写过一本给外国人看的、关于北京生活习俗的著作。这本书最初是用英文写成,1939年至1940年间在北京的一份英文报纸《北平时事日报》(Peking Chronicle)上连载,原名《小吴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Wu),通过虚构主人公小吴的经历,生动地描述了北平市民的生活习俗。《小吴历险记》由北平时事日报社出版单行本后,很快就被式场隆三郎翻译为日文出版,书名变为《北京的市民》(春秋文艺社,1941年)。1987年,日本平凡社甚至又出版了该书的第二个日译本,书名被改成《北京风俗大全》。
作为一本介绍北京民俗风情的读物,《小吴历险记》长期“墙内开花墙外香”,一直没有中译本,直到最近北京出版社推出了由罗信耀的儿子罗进德“译写”的首个中译本,并更名为《旗人风华:一个老北京人的生命周期》。
这个中译本有两个特点,首先是从书名上突出了此前在书中被隐藏的旗人元素,罗信耀毕竟是旗人出身,介绍民俗时不可避免地带有旗人色彩,所以定宜庄在本书序言里也说:“正如老舍、穆儒丐那些满族作家一样,那种旗人特有的风格却无法遮蔽,而从他描述的各种京城百姓的生活习俗、行为方式和性格观念中透露出来,那是北京文化中深厚的底蕴,是清兵入关后数百年在京城积郁的结晶。”
其次,罗进德没有按常规方式忠实于原文翻译,而是进行了大量增删和改写,目的是“为了把一本写给外国人看的书,改造成一本给中国人看的、有‘京味儿’的大众读物”。如此作为两代人之间的延续和对话,自然无可厚非,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则似乎有损这本民国著作的史料价值。除了对照英文原著之外,读者根本无法分辨哪些是罗信耀的原话,哪些是出自罗进德之手。
不过无论如何,罗信耀的这部“海外名著”总算有了一版中译本,那些老北京的绝版风貌终于时隔在80年后,得以接受故土迟到的回望。
(刊2020-9-11北京晚报,https://ie.bjd.com.cn/5b165687a010550e5ddc0e6a/contentApp/5b1a1310e4b03aa54d764016/AP5f5b2c01e4b0d90351f8b5d2?isshare=1&app=5efd94cae4b0a59cede7b847&contentType=0&isBjh=0 )
《变迁中的北京“勤行”》读后感(四):陈连生:我亲历的新中国对餐饮业的改造
【访谈者按】 解放以后,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前,有过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在这六、七年中,对于资本家的“限制、利用、改造”,在现代人的认知当中其实是很模糊的,即便是史学工作者,不专门研究这一领域,可能知之甚少,都是一些宏观上的了解。在这一阶段当中,陈先生是以一个青年工人代表的角度,讲述了当年前门一带勤行的状况。1956年,社会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宣告完成,陈先生也由一个普通工人成为了劳方副经理,开始了新的职业生涯。他对这一历史阶段的讲述,也启发我思考了一个问题,这就是从1949年到1956年,这短短的几年中,公私合营是如何顺利完成的,也就是说,自家的买卖,怎么痛痛快快地交给国家了呢?通过对陈先生的采访,我似有所悟,应该说解放初前几年的对私改造,对资本家的“限制、利用、改造”,是后来公私合营的前奏,是公私合营必不可少的前奏。勤行是一面小镜子,但从中也可以管窥到北京这一时期其它行业的大致状况。那么公私合营之后,对于陈先生自己来说,我想20岁就初任经理,是他人生中的重大转折,从职工到经营者的角色转变,这种当家作主的翻身,按他的话说“从一个小伙计,成了副经理,那时心理感觉很自豪,工作积极性就更高了”,为他开启了新的一页,开始从经营者的心态来看待和思考行业,他之后的所思所想都是以此为起点的,我想这部口述也是由此开始进入了我们的正题。 北京口述历史《变迁中的北京“勤行”——陈连生口述》 杨原 北京出版社
本文摘录自《变迁中的北京“勤行”:陈连生口述》 杨原 著,北京出版社 2020年8月 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有删节。
从限制到公私合营 陈:解放后,也就是1950年,开始对私人资本进行限制,1952年开始对私人资本家进行改造。什么是限制呢?就是原料控制,对私营企业核定,给你一定的原料来加工生产。比如,我们经营的会芳春,一天只供应30斤面粉,够维持6个人的基本开支,并略有盈余。到1952年开始“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主要开展了“反五毒”(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斗争。前门区工会把工人组织起来,共同跟资本家做斗争。(北京的形势基本相同)那时大街上安装了宣传喇叭,主要讲:“是谁养活了谁,资本家如何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是谁创造了人类财富”通过这样的宣传讲解,使工人提高了阶级觉悟,主动地参与到对资本家的斗争中来。 我所在的会芳春饭馆属于珠市口这一片,也就是从珠市口的“天佑行”到煤市街口这一段,形成一个小组,我那时才十六岁,思想比较活跃,主动加入到了工会中来,成为了工会的积极分子。在对资本家开展斗争的运动中主动站出来揭发检举资本家的违法行为,组织开展对资本家的“说理会。”在工会的带领下,把几个资本家叫到一起,站在台上,我们工会积极分子、工人坐在台下,对他们进行批斗,揭发资本家如何偷工减料,如何掺水使假,如何打骂工人。 杨:这都是那里的资本家? 陈:这些都是前门这一片几个饭馆的资本家,他们都是开饭馆的。这些资本家站在台上,工人围坐在台下。工会主席就组织开说理会。事先,工会主席做好了工作,谁是积极分子,谁先说,谁打头炮、说什么,都是有准备的。当跟我做工作时,工会主席问我,你敢说吗?我说:这有什么不敢,这些资本家确实是压榨工人,坑骗群众吗。在说理会上,大家高呼口号。 杨:刚才说您的掌柜李俊也在台上吗? 陈:也在。我揭发他们呀。比如往酒里兑水,打骂工人,这些在旧社会都存在,解放初期也存在。解放以后成立了烟酒专卖公司,我每天都要上专卖公司去买5斤酒,倒在店里的酒坛里,老板当着客人是不敢兑水的,客人不在的时候,兑上半舀子凉水,这是常有的事情。再比如:师傅和老板怄气,就拿徒弟当出气筒,找茬儿打骂徒弟。 杨:您学徒的时候是不是很苦啊? 陈:是的,太苦了。 杨:您开始学的那些手艺? 陈:小饭馆,要求样样都要学,样样都得会。切菜洗菜、刷家伙洗碗、送外卖、卖东西、生火、添煤,上板、下板,老板是不会让你闲下来的。过去学徒讲“三年零一节”这个时候没有工资,老板只给点零用钱。学徒只是个名号,都是自己偷偷学,小饭馆经营品种也少,看着看着就会了,主要是个熟练程度。 杨:老板们除了打骂工人、掺假使水,还有哪些问题? 陈:大问题几乎没有。过去开买卖赚钱,或多或少都有些使假,包括现在也不少见。只是抓住一些资本家的小错误,多他们进行教育改造,解决问题并不是目的,目的是教育工人,提高阶级觉悟,使资本家成为改造对象。 这之后,一些小资本家觉得经营不下去,自己的买卖自己做不了主,就关张不干了。不利于经济发展,更不利于解决就业。于是政府对资本家采取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给与资本家“三权”(经营权、用人权、管理权),利用他们的经营资本经营经验,限制他们的不法行为,改造他们的世界观,把资本家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样做对社会确实有好处,既保证了工人就业,又能使社会经济有效的流通。 经营就要赚钱,赔钱不行,所以也说服职工自动的把工资降下来。比如那时我挣9万元,就自动降到6万元。(1948年12月1日,新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制发行第一套人民币,至1951年底,人民币成为中国唯一合法货币。但是第一套人民币的面额较大,而且单位价值较低,在流通中计算时,以万元为单位,不利于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给人民生活带来很大不方便。1955年3月1日公布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第二套人民币和第一套人民币折合比率为:1元等于1万元。) 杨:这钱能合多少小米儿呀? 陈:那时人民币还没有流通,使用的是法币。后来折合人民币,1万元法币,相当于1元人民币。 从1952年到1956年,这期间发挥了资本家“三权”的作用,有了“三权”资本家可以照常经营,但是工人有了监督权,资本家的不法行为逐渐减少了。 到1955年开始了清产核资,对资本家实行了赎买政策,准备公私合营,国家接管。当时成立了一批清产核资工作组,这批工作组成员的组成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二是零售公司、银行抽调的人员、三是政府机关抽调的干部。工作组组成之后,对所有企业进行了清算。不过,工作组来到会芳春清点资产,桌子值多少钱、椅子值多少钱、生产工具值多少钱,合在一起有个总数,按照这个总数,给资本家5厘定息,7年不变。从此公司私合营了。买卖就是国家的了。 1956年全面公私合营,全面公私合营这一块就是大洗牌了。 杨:怎么个大洗牌法儿呢? 陈:哎,你听着啊,当时就出现两个名词,一个是大食堂、一个是小吃店,1956年以后公私合营并店,过去的小企业,二三十人、四五十人的小企业一下变成一个大食堂,一二百人了。 杨: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陈:公私合营以后由小变大,就是综合起来了。比如我在菜市口这一片,当时卖小吃的挺多,就集中起来一个大店,变成小吃店了,所有小吃都集中起来了,原来你那一个小摊儿、他那一个门脸儿,这样集中起来便于管理。使这些人既有生意,又有营生之道,统一实行工资制。这样这个企业本身,各种风味虽然都在一起,但是实行工资制度,不是你自己经营了,就是合营了。那么一些大的饭馆呢?也是几家合在一起,就变成一个大食堂。 杨:就是您说的那个会芳春? 陈:这个是西珠市口食堂,会芳春、中顺号、广义轩三家合在一起,共48个人,广义轩规模大一点,把这两户搁进去,把街坊动员动员、拆迁扩大一点,拆迁那时就是一句话的事,不像现在搬迁什么的。 杨:行政命令? 陈:对,不但是行政命令,接受命令的人还高兴,哎呦,我这儿被国家用了。 杨:他住哪儿去? 陈:当然得给安排,所以当时你提的这个问题大洗牌,就是这样洗的。这样变成大食堂,过去有风味的东西就比较少了,虽然还有这个东西,但是未必突出这个品种和风味了。因为大食堂本身就是大众化的东西多,所以你说的洗牌是纯纯粹粹的大洗牌,特殊风味除了单独留下哪个风味之外,比如像丰泽园、同和居这些大的(饭店)之外,其余都并在食堂了,没有什么特色的东西了,风味特色基本上消失了。 杨:您那会芳春呢? 陈:会芳春、中顺号、广义轩,广义轩在珠市口路南把角,挨着永安茶庄的地方,现在的铺陈市北口路南。我们那两家在老清华池西侧,这三家合在一起,叫西珠市口食堂,大概48个职工。 那时候在我们前门区成立饮食管理处,饮食公司的前身是前门区饮食管理处。这个规模多大呢?从虎坊桥到花市西口,就是马路西。从磁器口往北到哈德门,哈德门往西到宣武门、菜市口,这一块是前门区,这儿成立一个管理处,是饮食管理处。那时是100多家饭馆,有几百个青年工人。 杨:我现在感觉有很多大饭庄也是老字号,但是公私合营以后是中心店,当时像您这样的经理把那里经营得好,逐渐变成中心店,抽掉了很多其他店的骨干? 陈:中心店是一种形式,我们是直属店。 杨:就跟直辖市似的? 陈:中心店是多少家饭馆,每一个饭馆有一个负责人,是店经理。中心店是中心店经理,就管下面各饭馆,上面是公司。南来顺不是,南来顺上面直接是公司,跟中心店是一个级别。中心店是十几个或者几十个饭馆,作为一个中心店,这里也有一个办公的地方,有经理、副经理、书记、副书记,这是一个机构,没有实体,管着下面的实体。像南来顺下面这些兴升馆直接的实体,是直属公司的,就是这样。 杨:您的老掌柜李俊后来怎么着了? 陈:李掌柜岁数大了,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看门、值班儿、搞卫生这类的,那时候还没有退休制度。 公私合营后,基本上是大锅饭的形式,在当时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职工成为了企业的主人,职工积极性高了,你挣40元,他也是40元,人人平等,再不会受气挨打了。我所在的西珠市口食堂有48个人,一个经理,两个副经理。经理是上边派下来的公产代表,一个副经理代表资方,一个副经理代表劳方。我是劳方选出来的副经理,那时候我是这一片的团支部书记,我们工人选举自己的劳方经理来代表劳动者一方,副经理金德山是资方代表,因为是三家企业合并后组成的西珠市口食堂,所以,三个资本家之中,选出一个资方代表出任副经理。 杨:原来他是最大的吧? 陈:不是。在对私改造过程中,金德山比较积极,态度好,所以选了他。而最大的买卖铺是广义轩的杨德仁,原来广义轩有十八、九个人,这是1956年的时候,我那时候20岁。我们的经理叫李博交,他以前在银行工作,地址就在施家胡同,就是大栅栏往南路东一个胡同里。李经理算账是一把好手,算盘打得噼啪响,就是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对干餐饮又是外行,平常只上半天班,所以,企业的事他基本不管。金德山是资方副经理,胆小怕事,遇着事情也不敢做主,所以,西珠市口食堂的大事小情儿,都由我负责,实际上经营工作都是我主导的。 做生意就要与客户打交道,当时场上我们这儿吃饭的有乐松生、常子久、孙孚凌等人,这些人因为挨着我们饭馆进,所以常来吃饭。 杨:您说的乐松生是同仁堂的。 陈:乐松生是同仁堂的东家。他当时在工商联合会的时候,经常来我们这里叫外卖。一般是早餐在家吃过了,午餐在联合会吃,就叫些外卖,我们做好了给送过去。一般都是点个炒饼、鸡蛋汤或是打卤面之类。1958年,我到兴升馆举办28面红旗先进事迹展览的时候还专门接待过他一次。他是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的副市长。他们这些人对吃饭很讲究。孙孚凌是福星面粉厂的厂长,也在商联会兼职,现在已经90多岁了,我们俩关系还挺好。常子久是回民中的一个大资本家,他的哥哥常柱久,解放前去了台湾,大概是玉器行的。合营以后,他到我这里来吃饭,总是客气的打招呼“陈副理,忙呢?”从此,大家都叫我“陈副理”。从一个小伙计,成了副经理,那时心理感觉很自豪,工作积极性就更高了。 解放了,工人真正成为了企业的主人,打心眼里感谢共产党,所以,我也积极要求入党,本来我的入党申请应该是1955年10月批下来,正赶上清产核资,事儿多工作忙,拖了下来。到1956年2月24日正式加入了共产党。那时还没有召开八大,我学习的是“七大”党章,所以说,是七大时期的党员。
年轻时候的陈连生
杨:七大是1945年开的吗?发表的《论联合政府》? 陈:是啊,那时,一听说我入党了,职工、熟人老远的跑过来和我握手祝贺,很光荣的,和现在人不一样了,现在人们都觉得无所谓了。那时,前门区成立了饮食管理处,就是我所在的饮食公司前身,前门饮食管理处管辖的范围是:从虎坊桥到花市西口儿,从瓷器口往北到哈德门(崇文门),哈德门往西到宣武门,宣武门到菜市口,这一片。那时有100多家饭馆,有几百个青年工人,我是中支团支部书记,西珠市口食堂的副经理。 公私合营以后,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职工工作热情很高。到1958年,大跃进开始了,商业企业掀起了“学先进、赶先进”的高潮,那时候,兴升馆被评为28面红旗。 旧社会的北京与新中国的北京 杨:您是什么时候到兴升馆的? 陈: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新升馆被评为“28面红旗之一”,计划单列,调整为科级独立单位,调我去任团支部书记,副经理。兴升馆也是一家老字号,当时规模比较大,有三层小楼,大概1200平米左右,三层是职工宿舍,一层经营散座,二层有十几套雅间,雅间都用活隔扇分开,根据客人需要,比如安排三桌饭,就把雅间的活隔扇打开,就是一个能摆放三桌的一个大厅,安排两桌,就拆成两桌的大厅。而且有女招待,和现在所说的“三陪”差不多。解放后,他那里“三陪”没有了,但是基础设施好,环境好,服务好,饭菜质量好,在评比中劳效高,收入高,利润高,因此被评为“红旗单位之一”。当时,评比出的红旗单位有28家,比如:天桥商场、北京饭店、东四副食店等等,兴升馆是其中之一。 杨:您说说这个。 陈:大跃进期间,北京市长彭真对商业系统提出了“三少、两好、一便利”的要求”。“三少”就是人员少、费用少、损耗少,“两好”就是服务好,质量好,“一便利”就是方便顾客。1958年夏季,召开了评比大会,在大会上区委书记张旭上台发言,并把红旗分发给了这28家单位。大家敲锣打鼓,并绕着北京主干道游行一圈,以示庆贺。在这之后,北京商业战线,掀起了“学天桥、赶兴升”活动。 这时,兴升馆划归“宣武区饮食管理处”为充实兴升馆的力量,对兴升馆人员做了一定的调整和补充,于是我被调进了兴升馆,按照副科级待遇,那时我22岁。 到兴升馆以后,我主要做的是宣传和接待工作,当时来兴升馆学习参观的团体很多,全国各商业战线的人士都来的不少。对这些参观考察团体,我主要给他们讲解了兴升馆历史和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兴升馆合营后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取得的成绩和一些做法。 杨:您说过,一直在一线。 陈:当时我们单位的经理是老兴升馆的徒弟,平时好喝点酒,主要精力是抓经营,书记不太喜欢热闹,主要做企业的党建工作,我的分工除副经理职责以外,主要是宣传和接待工作。 那时到兴升馆参观的有曾山,就是老商业部长,我都接待过。商业部还有个张副部长,长期蹲点在兴升馆。经常来的有曹保真,他是商业部的司长,杨东起,他是商业部的一个科长。还有北京市服务局党组书记丁铁锋,宣武区委书记张旭、区长蔡平、区委常委郭华等,在这期间,我即是讲解员又是接待员,和这些人打交道多了,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和友谊,为我以后的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杨:介绍什么情况? 陈:接待工作要避开饭口时间,通常上午在10点以前,下午在2点到4点之间。基本上都是业余时间。主要带领客人参观,介绍企业的经营情况,收入水平,利润完成情况,人均劳效,企业是如何管理的,怎么样调动积极性的,职工是怎么样焕发工作热情,努力为顾客服务的,以及工作中的经验。比如,当时兴升馆的职工搞卫生,都是在下班以后,大家拿着大板刷,刷洗桌椅,把桌子上的油漆都刷掉了,全都漏出了白茬儿,现在看有些愚昧,但当时刚解放不久,北京气象一新,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工作景象。 杨:生意怎么办? 陈:生意还是照做,各有分工。国家政策是赶英超美,职工工作积极性很高,人人学先进,争模范。到处都是大跃进的劲头,每天工作都在12小时以上。有个叫张友会的女服务员,和我年龄相仿,人也敞亮,说话声音也大,服务热情,待顾客相亲人,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那时候她马上要临产了,挺这个大肚子,还端托盘呢,干着干着就不行了,马上要生,这时就赶紧送医院,走到半路上,孩子就生下来了。那时,这种事情很多,工作都有一种忘我的精神。 后来跟我一起搭档的俞博印,他媳妇叫阎桂芳,在大中旅馆工作,半夜十二点,眼看着孩子就要生了,只能自己一个人去大栅栏医院,刚走到半路孩子就生在马路上了。附近有个浴池,爬着去敲浴池的门,给爱人打电话,爱人来了,用自行车驮着,送到医院。那个年代条件很艰苦,但是人们却没什么怨言。 杨:为什么没有怨言? 陈:解放前比这还苦,解放后还好了很多呢。人们当然没有怨言了。 其实,旧社会的北京是另一番景象。一说北京的四合院,现在人们都说老北京“四合院”怎么好,其实,旧社会的北京,除了围着皇宫这一片,有些王府,有些大户人家的四合院,相当不错,其他的地方根本不行。到了南城都是用“核桃砖”(碎砖头儿)垒的房子,外表看着还行,却没什么真材实料。比如大栅栏这一片儿,你到那些四合院看看就知道了。过去在北京做买卖的人,都在城里置办个外室,养个小老婆之类的,所以,大栅栏周围,除了一些商号是正经建筑,其他的都是拼凑的房子。就这个,穷人也是根本住不起的。一出城,都是板打墙,上边支上几根棍子,铺上芦席,这就是房子。天桥一带全是这种贫民窟。进入60年代,才有所改善。我说的,就是天桥自然博物馆附近。那里的房子都是用荆条支起来,外边糊上泥的建筑。 杨:就是金鱼池? 陈:在金鱼池南边路东一带。现在人们进北京打工,租房子住,过去不是这样,几个人搭个窝棚就算是家了。丰泽园的了事掌柜进京打工的时候,就在永定门外城墙根儿底下,搭个窝棚,和几个要饭的一起住。 二说北京的饮食。现在人们到饭馆就餐,几个人叫上一大桌子菜,吃不了剩下一大堆。过去是没有的,来饭馆吃饭的人既节省又讲究,比如要个“炮羊肉”还要嘱咐一下,“宽汤儿”。为什么呢,主要是用这点儿菜下酒,剩下点菜汤儿,拌面用。能天天吃饭馆的人几乎没有。比如,现在老北京炸酱面,你去吃的时候,给你八个菜码,当时也不是这样,而是按照季节给您上个一、二个菜码。那时候没有反季节蔬菜,冬天只能是黄豆芽、白菜码,您要吃黄瓜码,就得等到夏季。这还说得是北京的饭馆。北京的穷人基本上能吃上“杂合面”就已经不错了,偶然吃一回面条,还得是两样面的,吃白面的,很少有人能吃的起。就说炸酱面,穷人吃,没菜码,就着几块萝卜皮就已经很好了。有的家儿人口多,买不起足够的黄酱,怎么办呢,炸酱的时候,兑上点儿水,抓把干面放在里边一块炸,多加一点咸盐,这就是炸酱面了。 三说北京的冬季。更不好过,大街上到处都是“倒卧”。什么是“倒卧”呢?旧时穷人,夜里没地方去,找个破庙的门洞就睡一宿,也许到了早晨就冻死了。 四说北京人吃早点。在北京花天酒地的人是有的,但是大多数消费不起。比如我的老掌柜。早晨就买一碗豆汁,俩焦圈儿,这就是早点了,而这还只能是老掌柜的待遇,少掌柜只有看的份儿,吃是不可能的。穷人没有早点,大多数人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解放以后,吃的饱了,穿的暖了,人们自当感谢党,感谢毛主席,所以,在那时候的苦,根本不算苦,大家没什么怨言。 杨:听说您不吃猪肉,到了汉民馆怎么办呢? 陈:我12岁出来学徒,在回民馆工作,久而久之,养成了不吃猪肉的习惯。到了汉民馆以后,接受不了猪肉了。和我一起调到汉民馆的还有一个人,叫张久元,他也不能吃猪肉,吃饭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两个有时候就买两个馒头,再去隔壁的“六必居”买点酱菜,对付。我还有个便利条件,就是和西珠市口食堂比较近,我可以去西珠市口食堂吃饭,而张久元是菜市口出来的,他就更不方便了,没干多久,他就调回了回民食堂。 我在兴升馆两年多,一直不太适应那里的伙食。1958年调进去的,到1961年就调出来了。
2019年在南来顺饭庄
在兴升馆期间,我也得到了不少锻炼,我负责的团支部被评为“八好团支部”,成为了全国先进青年集体。那时候,领导机关不像现在这样,没有卫兵站岗,都是门口一个传达室,来找人办事,谈工作,很随便,推门就进。
2020年08月19日发表于《澎湃·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