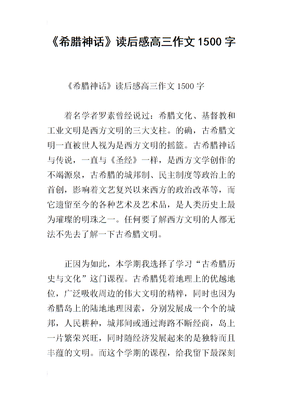
《神话修辞术/批评与真实》是一本由[法]罗兰·巴特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6.00元,页数:28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神话修辞术/批评与真实》精选点评:
●非常难读,几度看不下去。但让我意识到批评反诗性却又很诗性,第一部分很有启发性。
●符号学去死吧!
●神话修辞术非常赞,虽然前面的部分有点涩,但是仅仅是读完理解的部分就获益匪浅。“自由式摔角的境地”“茶花女”“占星术”几章,简直是思维风暴,闻所未闻的解读,而且如此精准到位尖刻犀利,并且最重要的——不卖弄。他大约就是达到了君君老师所说的“以系统的眼光审视和解读生活吧”。崇敬之心。
●170325-26,花了两个早上细读了今日之神话,等空了把几本书放在一起读。
●前言竟然比正文还难懂,但是正文很好看。
●这本书我读了好多年。最主要的是《神话修辞术》的上半部一直拿拿放放。个人建议,《神话修辞术》应该反过来读,先读下半部(理论),再读上半部(基于理论运用的文化批评)。最后说一下,和往常读巴特的书一样,译者序建议跳过,感觉一般都和书的内容脱节。
●巴特的神话学充满了奇想色彩。这种感觉在卡塔萨尔那些充满神经质的短篇小说以及莎士比亚那部“豆花、蛛网、芥子”都陷入狂欢的喜剧《仲夏夜之梦》中也能找到。巴特也许并不想创立某种垂范于世的理论模型,毕竟“尔曹身与名俱灭”,他要的,更接近于在疯狂的智力游戏中,截获一点好玩、一点顽皮与讥诮。
●似懂非懂地看完,只觉得巴尔特吐槽法国人过渡保护法语那段很爽。
●第一部分很好看,第二部分看得懂的都好看。。。。
●“从语言角度看,嘉宝的独特之处在于观念范畴,A赫本则在于实体范畴。嘉宝的脸是型相,赫本的脸则是事件。”
《神话修辞术/批评与真实》读后感(一):mmmm,很符合这个硬朗的年轻人
还是喜欢他老年的恋人絮语,少了现代主义文学的无法弯曲的思维。神话修辞术,批判,批判,后现代的鲁迅。对社会上的偶像崇拜和扫盲工作做了很多的贡献。
“《写作的零度》(1953)、《神话》(1957)、《符号学基础》(1965)、《批评与真理》(1966)、《S/Z》(1970)、《文本的快乐》(1973)等等,影响了人们对文学和文化的看法,也可视为巴特对文学研究工程延伸而成的一套思想体系。生平参见《罗兰·巴特论罗兰·巴特》(1975)、《偶遇琐事》(1987)等,后一本书由友人编辑出版,应该是他唯一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的文字。”
“同性恋”有点搞笑了,老家伙始终忘不了带给这世界批判。最后的恋人絮语回归了托尔斯泰似的EROS,遗憾!
《神话修辞术/批评与真实》读后感(二):特别通告!
刚从当当网订购了《神话修辞术》,搜索到博客“Out of noise”的有趣评论,转载了,与大家共享。
版权声明:转载时请以超链接形式标明文章原始出处和作者信息及本声明http://positron.blogbus.com/logs/46085239.html
《神话修辞术》,即Mythologies,作为上海人民再版的“罗兰·巴特文丛”中的一本,已经出版了!这一次的Mythologies是屠友祥的新译本,原来错译,误译百出的那个台湾译本可以扔了。
题外:期待屠友祥氏能把中国人大出的那套罗兰·巴特也重译一遍(话说中国人大那帮人——李幼蒸,张祖建,绰号怀宇的张智庭等等——快赶上以陈永国为首的清华帮了!他们不仅大肆糟蹋了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他们甚至将翻译的魔爪伸向了德勒兹!大哥,你们就行行好吧!陈帮主,你就给我们留条活路吧!)
《神话修辞术/批评与真实》读后感(三):由此书想到那些“比火腿还薄的友情”
读巴特《神话修辞学》时想到的:在这个类型(充满各种主题的个体)的世界里,女性本身就类型来说时常会遭受到各种威胁。这威胁有时来自父母,有时来自男人的目光,有时也来自女性群体内部。就第三种情形而言,“女人之间的友情”是解救困境的途径,它暂时化解了精神上的危机。可一旦这种具有缓和作用的方式遭到失效。这时,某些空幻的弥补手段就自动出现了——如:沉默、想得开、自我欺骗、保持希望和距离——使得失败的行动变得高贵,其目的旨在将人际关系中失败的体味进行升华,使自身(尤其是具有忧郁气质的个体)对抛弃感、无用感具有一种免疫力,从而保护女性主体的完整感。正是出于对自身完整感的维护,为“女人的友情,比火腿还薄”这句台词,提供了一种奇特的解释。 (配图自日剧《我不能恋爱的理由》)
《神话修辞术/批评与真实》读后感(四):神话学的概念
罗兰巴特构造的神话学系统如图所示,是一个二级符号系统。
第一级的系统是一个语言学系统,由能指和所指组成符号。第二级的系统才是神话的部分,符号成为了第二级系统的能指,和第二级系统的所指组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的符号。而罗兰巴特为了区别于第一层的符号系统,把第二层的符号称为是形式,把神话的表意功能称为是意指作用。
罗兰巴特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应当还没有转向晚期的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倾向。比如他依然假定了有一个自然的语言系统,本身没有发生神话的意义扭曲。当然罗兰巴特在《神话学》中所表述的观点是存在问题的,他假定的“元语言”并非就不是另一种初级符号系统的次生系统。
为了通俗理解这个问题,下面举例:
首先需要了解的是,能指和所指是什么意思?
能指和所指来自于索绪尔的语言学的概念。能指是形象,所指是概念。
比如当我们认为玫瑰是代表激情的。在这里,玫瑰变成了一个符号。玫瑰的意义是被赋予的。也就是说,这里存在着两个东西,一个是玫瑰的形象,一个是激情的概念。而符号是两者的整体或者说两者的复合。
这是语言学层面的东西。
其次需要了解的是,神话是什么意思?
这是罗兰巴特的一个创生。
他认为渗透到社会当中的不单单是纯然的“自然”语言,更多地是存在着多样的神话修辞。神话不仅仅是人们在民俗学/考古学发现的种种泛灵论的古老传说,更是充斥在现代巴黎的种种景观。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形塑了今日的神话,这也是为什么他选取了许多碎片式的文化景观作分析的缘故。因为他想通过这种批判来解释小资产阶级生活的伪善。神话本身是派生于语言系统的次生符号系统。罗兰巴特正是意图揭示现代神话的真相。
最后,我们好好聊聊形式和概念(所指)。
符号在第一层次的系统当中是语言系统的末端。在这一层次当中,符号本身是具有意义的。它本身作为一个能指,按照索绪尔的理论来说,具有任意性,它包含的意义是丰富的。(最起码罗兰巴特假定是丰富的......)
罗兰巴特说,当说我名叫雄狮这句话。
当不与一个概念结合的时候,当没有具体语境的时候,这个句子能够包含丰富的意义:我是一头动物,我是一只雄狮,我生活在这样的森林里,我刚捕猎归来,大家要与我分享我的猎物,但我作为更强壮者,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将所有猎物归于我自己,其中最终的一个理由就完全是因为我名叫雄狮。
可是当这句话放在外国公立中学初二年级学生课本当中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意思,这是个例子,用来举例阐明法语的表语的配合规则。而在这样的使用当中,我名叫狮子这句话的意义就贫瘠了,和所指我是一个文法例证结合在一起说明了自身的用途。神话的根本特征在于适应性,它总是针对明确的群体灌输概念。(比如文法的例证性明确针对一年级的学生。)
为什么要揭示神话的真相呢?
罗兰巴特认为神话的本质是一种扭曲的关系————把神话的概念与神话的意义连接起来。符号在神话当中脱离了自身的历史,抽象为了一个高度形式化的能指。而潜在的概念又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掩盖自身的痕迹。这种神秘化/神话化掩盖了事实本身。
可参考神话学《葡萄酒和牛奶》的部分,或者黑人士兵朝法国国旗敬军礼的例子。
《神话修辞术/批评与真实》读后感(五):西西弗斯的巨石
我们发明了语言,有了文字,产生了文明,摆脱了茹毛饮血,摆脱了地心引力,却永远也摆脱不了语言和话语的控制。语言和话语,就像是西西弗斯每天所推得巨石一般,每当我们以为自己的智慧足以使我们摆脱结构的枷锁,却往往发现我们对于智慧的自尊就像巨石般从山顶滚落,却又是那么的无可奈何。
从语言诞生之日起,语言的目的性始终伴随着人们的生活,语言的产生是为了人们更好的协作,在原始社会里能够合作生存,但是这种通过语言和话语的合作从一开始就带有了目的性,无论是一起打猎,还是一起生产劳动工具,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语言的发出者的背后就是某种行为的完成。随着社会的发展,思想不断走向成熟,这种隐藏在语言背后的目的性悄然生根,并且在人们的思想里迸发出异常的活力。话语懂得了伪装,语言学会了修饰,话语和语言一旦披上了修辞的外衣,就使得谎言也带有了合理性。
最可怕的是人人往往对这种合理性并不自知,很多学者已经发出过警告,我们并不能够自觉地分析出日常生活中接受到的话语合理性背后隐藏的目的性,归根结底原因就在于我们本身就认为其是合理的,这种虚幻的真实来源于话语和语言的魔力:根据对《神话学》的理解,叙事就像是一种神话,各种各样原型故事赋予叙事话语以合理性,伴随着合目的性的修辞手段,使得媒体的受众与潜移默化中产生影响。在曾庆香老师的书中有一句话我印象深刻“在某个时候被奉为是对客观事实的叙述或真知灼见就是神话,只不过我们当时没有意识到它的神话性罢了,同样,在某个时候被斥之为神话的实际上就是一种对客观事实的叙述或真知灼见。”这种观点使我联想到了休谟的怀疑论,对规律的普遍性的质疑,合理性有一天也许会变成不合理,而不合理在某个时刻看来又是合理的,就像是人们对牛顿经典力学的崇拜,在量子力学出现以前,对三大定律的质疑是非常可笑的。同样对于信奉经验主义的人来说,通过归纳法获得的知识,也会因为其结论不能保证绝对正确,带有着出错的可能而被证伪,可观点被证伪的现象往往是极难出现的,就好像是有一天你告诉一个人,太阳不只会从东边出来,这只是人们观察到的一个特殊现象,太阳还会从西边,北边,南边出来,甚至干脆不出来,那个人一定会认为你是极为可笑的。神话的作用就是如此,其赋予了合理性,根深蒂固与人们的思维中,甚至直接参与形成了思维的形成,人们并无意识反抗,而是按照神话的内容去接受。
叙事就是一种神话,或者说当神话作用于话语时,叙事就变成一种人们难以反抗的工具。我们可以回顾以往的很多研究,无论是后结构主义提出的“文本之外,再无他物”还是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我们难以摆脱,我们引以为傲的理性就像是缸中的大脑一样,只对自身的存在自知,而不知道自己浸泡在什么环境之中。对叙事的研究打开了人类社会的结构性,将结构主义运用到人类学上,便可以分析出人类社会的结构性差异,无论是红色与绿色所对应的禁止与通行,还是男性与女性的性别差异在语言中的塑造,还是群体在媒介中的“象征性消灭”,都是语言和话语支配性的表现。划分了结构,设定了认知,语言和话语从此便具有了合理性。
当然,如果我们只把语言和话语比作西西弗的巨石,人们始终被滚落的巨石所支配而不能把握自己的理性,那么难免有一些宿命论和决定论的悲观思想。我们的现代理性尚未被解构,虽然福柯关于知识与权力的论述令人感到十分精妙,甚至感到对现在理性的失落,但是人的主体性始终存在,而伴随着主体性的理性也不会被语言和话语规训,就像是西西弗斯故事的结局一样,当巨石滚落之际,西西弗斯发现了一种别样的美感,并从这种美感中获得了满足,至此再不感觉这种日复一日的行为是那么的枯燥。语言和话语也是如此,语言和话语通过叙事具有了神话性,而我们的理性却仍然可以把神话变为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