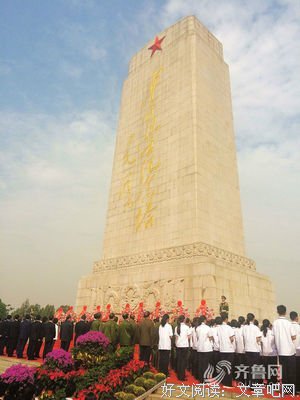
《英雄山·伏击》是一本由徐贵祥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页数:35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英雄山·伏击》读后感(一):力透纸背的书写
《英雄山·伏击》读后感(二):“互文”艺术手法的神奇效果
《英雄山·伏击》读后感(三):英雄之路:道是奇崛最平凡——读徐贵祥《伏击》
文丨廖德凯
1
徐贵祥善于写军旅英雄,比如《历史的天空》里的梁大牙,又如《八月桂花遍地开》中的沈轩辕,《穿插》中的凌云峰。
这些英雄都出身于普通的指战员群体,而哪怕是最普通的指战员,每一个人身上,其实都是一个传奇故事。
《伏击》也写英雄,但写了一个看似荒谬的英雄诞生的过程。易水寒原本是一名国民党军下层军官,在特殊训练后接受特殊任务,冒充我军“已牺牲”的指挥员找到组织,并伺机暗杀国共谈判中的我方重要人物,达到破坏联合抗战的目标。然而,在红军中的耳濡目染,让他对自己的使命产生了怀疑,最终在关键时刻枪口转向。最后,他成为一名优秀指挥员,与自己所冒充的人在抗日战场上配合战斗——离奇的是,他所冒充的红军指挥员,却用着另一个国军军官的名字,在抗日战场中浴血奋战,直至牺牲。
双重冒名、学习“敌人”过程中反被感化、关键时的反转,让这部小说有着传奇般的剧情。但正因为这些剧情的传奇性,有时不免让人猜测:作者脑洞大开,但不会全是瞎编的吧?
你别说,这些冒充、感化、反转的剧情,在那段历史中,还真有其事。徐贵祥的工作,只是进行了“杂取种种”,经过艺术化后,形成了性格鲜明、特点突出、形象生动的艺术群像。
2
《党史纵览》(2007年04期)刊载军史专家何立波文章,解密了抗战时期一桩离奇的冒充案:
1943年6月22日上午10时,毛泽东要接见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旅长田守光,被毛泽东称为“延安的福尔摩斯”的边区保安处侦察科科长陈泊经过了解,得知田守光3月上旬从华中出发进入边区,在抵达晋西北时有电报发给中央军委,称所持的中共华中局的介绍信在渡海战斗中丢失。新四军确有田守光其人,看似毫无问题。但事实上,真正的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旅长田守光、该旅参谋长彭雄等人,于3月初从山东赴延安参加党的会议,在连云港海面上与日军遭遇,所有人员遇难。军统特务查清楚死者中有新四军旅长田守光,在戴笠的亲自策划下,军统派出数批特务潜入延安,包括这个“田旅长”,欲寻机刺杀毛泽东。陈泊小心谨慎,最终还是在蛛丝马迹中查出了真相。
冒充牺牲的我军指挥员,执行暗杀重要人物的任务,这不就是易水寒冒充红军“穿山甲团”团长凌云锋的原型吗!
易水寒思想转变的来源,是一个叫陈兴林的热血青年。1938年,原本要去延安的陈兴林在半路被军统特务截住,经过“洗脑”和强化训练,伪装成进步青年被派往延安长期潜伏。经过多日的观察思考,陈兴林认为共产党的确是为国家为民族着想的,因而愿意为共产党办事。1941年底,保安部通过陈兴林的配合挖出了大量潜伏特务。
艺术来源于生活,能够打动读者的文学作品,都能从生活中寻找到源泉。再离奇的剧情,只要来源于生活,都会让读者感觉到合情合理,“就应该这样!”而那些脱离生活实际的“脑洞”,在热闹与喧嚣之后,读者回以的只是“神剧”二字。
《伏击》荒诞离奇的剧情,其实很合理。
3
我对小说最大的要求比较庸俗——必须好看,最好是看了一部分就放不下来的好看,看完了还心心念念里面的人物和情节的好看。《伏击》和《穿插》都基本满足了我这个庸俗的标准。
每个读者对于“好看”的标准不一样,但至少应当具备以下特征中的一个或一个以上,如果都具备的话,那就堪称完美了。
一是个性特点鲜明、有代入感的角色形象。代入感不仅仅是指读者自己代入其中的角色,也包括读者觉得角色熟悉,喜欢、讨厌、印象深刻,都属于读者的代入感。读者能够设身处地关注角色的命运和发展,是一个角色是否让读者有代入感的基本判断。《伏击》、《穿插》里的人物,易水寒、谢谷、楚大楚、凌云锋、安屏、蓝旗、蔺紫雨、张达理,甚至是出场不太多的胡琴、陈达、乔东山、王铁索,都会让我关心他们的命运。
二是有一个好看的故事。很多时候,好看的故事和代入感其实是一体的,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好看的情节可以独立于鲜明的人物形象而存在。当然,《伏击》有着好看的故事,即使脱离了那些鲜明的人物,故事剧情的曲折传奇,也足以吸引我的好奇心。前边已经说过,《伏击》的故事在实际生活中可以找到原型,但如何把原来相对平淡的情节安排得引人入胜,则需要深厚的笔力进行支撑。徐贵祥善于讲故事,把这段故事讲得很好看。为防剧透,就不多说了。
三是有打动人心的笔触。《伏击》与《穿插》所写的故事,发生在生死攸关的特殊时期,无论是国家、民族,或是政党、军队,都时时处于紧绷的状态之中。失落、迷茫、冤屈,大概每个人都会有出现那种状态的时候。一直记得安屏的一句话:“信仰没有如果。”一句话诠释了先烈们为什么能够顶住这些负面情绪,毫无保留地为这片土地和人民奉献自己的生命。
4
信仰是装在自己心中的天,理想不一定需要在我的手中实现,但我每一次的选择和牺牲,总会让民族距离那个最高理想更近一些。
这就是“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原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邹碧华说过一句话:“每个人都是历史,如果能让自己完美一点,历史也会完美一点。”这一句话,和安屏“信仰没有如果”形成了互相印证。所有坚韧向上的人,都会有坚定的信念。《伏击》和《穿插》里的那些共产党人,不用“结果”和“如果”影响自己的内心,读之令人动容。
徐贵祥并没有用说教的语言告诉读者这一点,事实上,书中主要人物基本没有绝对的“反派”。但是,通过情节的推动和人物合乎情理的性格与思想发展,却让读者自己深刻感受到了这一切。
说了这么多好话,并非《伏击》就没有暇疵,《伏击》中也有些小BUG,比如打篮球时出现了“三分”的表述,“赵禹”后面变成了“赵钰”。但这些技术上的小问题,自然无法掩盖这部作品的优秀。
《英雄山·伏击》读后感(四):战争过去的当下,我们谈的是和平
读完《伏击》,书里几个人物的身影,挥之不去。故事虽已画上句号,我却隐约有股剪不断的情绪。我问自己,换作是我,我是易水寒,是蔺紫雨,是蓝旗......会怎么做?每读一本好书,无不是精神的成长史。
《伏击》的故事结构并不复杂,国、共两党的主要人物,彼此交叉,又各自独立,在战争的背景下,个体的发展脉络,与国家息息相关。两者相互影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他们的所作所为,从所处立场来看,无对错之分。至于选择的成因,皆是听从内心召唤,由衷地做出决定,立誓此生无悔。掩卷而思,我的体会是:选择关乎命运,战争考验人性。
01、选择
一念之间,走一条怎样的路,从做出选择开始。易水寒,原名易晓岚,蔺紫雨的表弟,是蔺家账房先生的孩子,后来在国民党的“青干班”,是特务组织成员。教官陈达搞了个“借尸还魂”计划,决计让易水寒借红军干部凌云峰的尸体“还魂”,潜入红军执行任务。
起初,易水寒畏缩不前,茶饭不思。他平日滴酒不沾,不吃鸡爪,并非胆大之人。陈达教官却认定他有潜力,只是未被挖掘。在蔺紫雨的鼓动下,易水寒接下任务,从此以凌云峰的身份存在于世。
红军队伍不乏精明者,易水寒的自证之路,注定艰辛异常。他几度想将真相和盘托出,又因各种原因打消念头。如果此前他的身份一直被红军怀疑,那么直到枪口掉转,将原本击毙文中戈的打算作罢,这才收买到人心。
那一瞬间,潜意识里易水寒未曾发现某个转变,他的一半已成为凌云峰。是环境使他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由外自内,脱胎换骨的变化。
易水寒隐去自己,以凌云峰的身份示人,这一过程是变被动为主动。从被迫接受任务,努力扮演好新角色,到主动采取行动,逐渐淡忘真身份,由此获得成长。
他在与凌云峰融合的同时,后者也在适应另一个身份。尽管凌云峰实战经验丰富,相比易水寒,他更为成熟,但替代楚大楚,如一张白纸般重新开始,也是对他的挑战,是成熟基础上的成长。两人相遇时,一句“好样的,兄弟”,是对彼此的认可和认同。
战时无平坦道路可走,艰难险途中,总有更艰难。易水寒和凌云峰选择最险的路,从浅处看,实现了自我价值。往深处想,是为国家的安定。当个人利益与家国利益相冲突时,每个人各自的选择,将决定自我命运。而将个体选择叠加后的集体选择,则决定国家的命运。
02、人性
战争关乎生死,生死关头考验人性。陈达教官立功心切,为达目的,他可以舍弃曾同舟共济的战斗伙伴,可以不顾八路军的安危,亲自制造混乱,置对方于险境,甚至可以视自己的生命为草芥,只要能达到目的,便没有什么不可牺牲。
他自私又贪婪,明明整颗心已被欲望占满,时时刻刻都在蠢蠢欲动,却美其名曰国家至上。在得知蔺紫雨被捕后,陈达虽有担忧,但第一关心的是,“那几个汉奸是不是蔺紫雨她们亲手杀的,八路军有没有插一杠子贪天之功”。听完白迁的汇报,这才彻底放了心。
令人讽刺的是,八路军何时想过功劳归谁,都是中国人,本该一致对外。陈达格局太小,心胸狭隘,和蓝旗相比,像不懂事的孩童。蓝旗冒死救胡琴,负伤后胡琴精心护理,国共间的隔阂被抹平,一道鸿沟,因两人友善的互助关系而填满。
若换作陈达,危险时分,断不会向共军施以援手。为争头功,不择手段是他的本性。论仁慈,他不如蓝旗。论坚定,他不如蔺紫雨。蔺紫雨受尽折磨,酷刑不能教她屈服。死亡逼近,她誓死保护陈达。而陈达,早已将她作为牺牲品。
考验虽类似,个人做法不同。有人为一己,有人为大家。无事时,言行不具参考价值。一旦事出,品性高低,当即立下。人性深处,都埋藏有一颗利己的种子。若培育,它便生根发芽,可能会生出恶之花,也可能相安无事。
我敬佩那些说服自己,从私利中醒来,心知这颗种子尚在,却不为所动,久而久之,这片心田已干涸,而它旁边,另一颗利他之种被种下,每行一次善,人性便累积一分厚度,逐渐胸怀似碧海般深远,似青山般宽厚。
03、和平
战争终将结束,和平之光照耀人间。小说写到几个精彩的战争场面,我印象最深的是麻雀岭一战。“夜空被撕裂了,弹道飞舞如流萤,沉睡的山谷喧嚣起来,好像戏台上鼓乐齐名”。这场战斗,从拂晓一直打到上午十点多,奇迹般地坚持了两天。
尽管一场成功的战役,具有艺术审美价值,但不可避免的是,它以流血和牺牲为代价。而沾染血泪的艺术,悲壮和苍凉是底色。因此艺术化战争,是对罪恶的逃避或原谅。
如果敌对双方无一妥协,和平注定是海市蜃楼,美好愿景势必会破灭。国共两军从起初僵持不下,到共军先妥协,国军赢得面子了吗?并没有,实则妥协者,反而是胜者,胜在民族大义为先。
之所以国军精英,最后会心甘情愿选择共军,是被共军的言行感化。共军讲团结,弃分裂,有胆有识,宁愿马革裹尸,绝不做逃兵。但凡真心悔过,共军既往不咎,只要一心为善为诚便可。
基于此,即便得知易水寒的真实身份,文中戈等人仍选择接纳。共军善于用人,懂得容人,才华横溢者,英勇无畏者愈聚愈多,方可各司其职,战时不留死角。若想招来凤凰,首先要是棵茂盛巨树。再反观国军,人才凋敝,嫉妒心旺盛,只顾蝇头小利,缺乏人性的温度。
共军主张和平,国共合作,一致对敌,内斗只会加剧破碎,关键时刻不分国共,保国要紧。而保国,正是每个国人的希望。同人民想到一处,势必赢得民心。任何时刻,和平都至关重要,拥护和平,国内也好,国际也罢,始终是中国的主张。
小说结尾,战争结束,作者写道:“如今,以苍山南麓的隐贤村为中心,我们这些人的灵魂经常聚集在一起,当然,我们不打麻将,也不跳广场舞,我们在一起就做一件事情,数星星,天上的星星有多少,永远也数不清。”
这是一个忧伤又温情的尾声,死去的人再也无法欣赏星辰,活下来的人望着星空思念。而这一切,生的幸运与死的哀伤,仅是属于少数人的记忆。随着和平永驻,一代代人共享安宁,假如我们在凝视繁星时,除了感叹夜空璀璨,也能感恩前辈浴血奋战的精神,大约这星辰也会变得不同往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