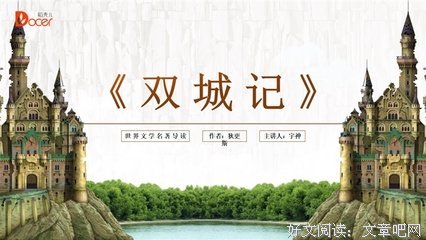
《我的双城记》是一本由贾葭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45.00,页数:43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的双城记》读后感(一):我的双城记
《我的双城记》,贾葭著,三联书店,2016年1月第1版。居然又是一本专栏文章合集,且大多数文章集中于2010年至2012年间,实在是芜杂的一本书。说是双城记,对最想看的香港部分却实在不多,且实在过浅。以我看来,更多是以香港发泄对北京之怨气,写不出这两个城市的格局来。除北京的份量最重和香港外、台湾、广州、南京、杭州都有涉及。这种蜻蜓点水式的专栏文章虽不能称之肤浅,但亦难免限于篇幅、时限与时效,流于表面。貌似俏皮的文字一篇篇看来还好,但合成集子便无深读必要了。
《我的双城记》读后感(二):我的双城记
对于人与事,看懂了讲出来是一种境界,看懂了不讲是一种境界,看懂了讲一个笑话给你听是一种境界。
贾葭就是第三种。他的《我的双城记》很欢乐。大多数时评杂文的淋漓至尽来自于用词的恶狠狠。贾葭并没有,他用一个又一个笑话讲了生活中的荒唐可笑。需要多么聪明,胸怀多么大才能做到这点。
发给朋友看贾葭,朋友很快发过来贾葭的生平与公众号。好喜欢。
我一直以为是生活中很少有人懂幽默,读了贾葭,我知道是很少有人象贾葭一样格局这么大,这么接地气的幽默。
从某种方面来说,生活非常美好。又多了一个偶像,多了一份欢乐。
贾葭很清秀,一双小眼睛很狡黠。他的理想生活跟我的几乎一摸一样:白天读书,晚上写字。
他笔下的万圣书园好喜欢,太原没有这样的地方,我尽力把自己家打造成这样子好了。
就象马家辉说:我爱读,你必,也爱读。
《我的双城记》读后感(三):帝都居不易 香江水长流
[在我写完这篇不知所云东西的时候,听说这个之前被迫搞行为艺术的贾老师终于现身了。]
前两天,一个叫许亿的白胖子兼吃货兼黑心房地产从业者突然在群里不平则鸣(我之前给这个中年胖子的随笔集《旧时光的味道》贴过电线杆小广告),说是又有一本刚面世不久的公开出版物被拿下了,一股吃到了过季阳澄湖大闸蟹似的不满。
他说的那本书叫《我的双城记》,是个叫贾葭的码字儿的人写的,我去京东上顺手搜了搜,果然在自营一栏中显示了“无货”俩字,只是一些入驻的书店拉拉杂杂还搁在架上。转道去了亚马逊和当当,这书稳妥妥地还放在售卖一栏里。
《我的双城记》读后感(四):贾葭笔下,写出新一代中国都市人的迷惘和纠结
贾葭做过宁漂、京漂和港漂,因为传媒工作的缘故,不免又要漂流更多的地方,甚至漂到了海峡彼岸。于是便有了这辑俏皮幽默、冷眼热肠的好文章,不妨视之为新中国漂流记。虽说漂流,但贾葭却能精准掌握一座城市的本色;因为漂流,他反而看见了我们本地人看不见的角落。这种潜伏在日常都市生活之中的游荡目光,正是上佳专栏作者的标记。
——梁文道
专栏作家不崇高也不低贱,不太累也不轻松,不难当也难当好,就像天下所有其他匠人的状态一样,凭自己本事吃饭,总是很光彩的。这本书的文字不煽情不造作,可当成一个专栏作家的成长史来看。
——连岳
贾葭神出鬼没于北京,香港,台北,以至华人世界的各大城市,不易捕捉。幸而,神龙不见首,文字却留尾。一篇又一篇的长短文章写出他的所感所思所析所论,无不直指城市核心,是上等城市书写。我爱读,你必,也爱。
马家辉
贾葭待人至诚,其文字也至诚。笔底波澜之下,可见其对城、对人的悲悯与爱。
——王小山
《我的双城记》读后感(五):城里城外
刚刚知道,机场分局说,贾葭确因一起案件,3月15号被带走的。这一天,两会也刚结束。什么案件,我其实并不关心,一来我们并不是那么熟,更重要的是,我想,没有人民公安做不出来的案子吧。
从三联出来时候,特意到三联自出版区找这本双城记,恰有一本,封面敞开着,有人刚翻过的样子。我拿到前台,收银员说,这个书最近卖的还挺多。我也希望他是炒作新书,不见了。
现在看来,玩笑开的有点苦。
后来我带着书,在北京北站,上了去延庆的末班车。车内咣当咣当,车窗车外拥堵的西直门、北四环、五道口,忽然静音了,夜色覆盖了北京城,把灯火留在了身后,我在仍然咣当咣当的穿行在延庆的山区。夜太黑了,我翻看贾葭的这些个豆腐块,偶尔会被机灵和玩笑逗的会心一笑,车过了南口站,感觉车厢里只剩我一个了。
不知道是否过了居庸关,过了水关,但我能想象一列有着光亮的火车正穿行在四顾漆黑的深山,有点孤单,也有一点被山神俯视的温暖。第一次出远门,是坐火车去武汉上大学,车在太行山南下的时候,我见过一样的山。
北京算熟悉的城市?看过这些个说租房中介、说海淀、说万圣、说出租司机,还有北京大妈的文章,有时还会被文章带回到一一对应的场景,不少觉得机灵转的过瘾,但大多时候,是一个外省来京务工人员自嘲的苦涩。
贾葭在南大学中文,遣词造句都不赖。相信,读过他离职腾讯《大家》主编的辞职信的人,会认同我说的不为过。
书,还剩香港的部分没有读。人,找到了。
对于记挂他的人,比起找不到,这算好消息吧。他的爱人也不用那么慌张了。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城市,一个人,说不见就不见了,没有人告诉你哪里去查消息,直到有了一个消息。
《我的双城记》读后感(六):#2020年翻阅100本书
《我的双城记》读后感(七):北京的精神分裂症
《我的双城记》的作者贾葭是京城的交际花,这从他书里所写的内容就能看出来,他在这本书写的,是居住在北京和香港的生活经历。无疑,他热爱饭局又热爱文艺,喜欢泡在著名的万圣书园消磨时间,也流连于各类饭局。不过让人奇怪的是,这种交际花,还有时间读书呢。
这些专栏时间跨度很长,最早的写于2003年,这似乎并不是多久远的时间,那场著名的”非典”还未从人的记忆里消退,但作者笔下的北京却已是大变了模样。最简单的例子,作者在专栏抱怨过北京动辄二三百万的房价,但现在可能还不够首付;作者抱怨过北京户口,虽然经济给人带来了自由,模糊了北京和非北京人的区别,但他当时不知道限购是个什么玩意;作者还煞有介事的抱怨了北京的沙尘暴,他只晓空气不好,不知雾霾将至。这些细微的改变让人茫然,是吗?以前的北京竟然是这样,似乎看起来还是个有点自由的地方呢。
我记得福克纳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人生像一辆急速向前的马车,看越远的地方越清楚,越近的地方越模糊。我们与时代的关系似乎也是如此,身处其中,除了焦虑,似乎感受不到大的变化,茫然接受,不知道该以何作为参照物。
贾葭的这些专栏,无疑就是今天北京的参照物。
他写的是好的,与爱掉书袋的作家不同,他总是喜欢写身边的小事,与南方来的朋友吃饭,朋友将茶壶盖斜扣在喝空的水壶上,服务员走过来,直接给扣正了。这种生动的、好笑的生活细节在书里很多,分寸也拿捏得很好。不过如此多的讽刺与抱怨,作者竟然没有被打,也是奇怪。
作者也是个讲究人,他不坐地铁,觉得地铁站里气味不佳,穿戴也得体,与传统的不拘小节的公共知识人不太一样。这背后的意思是,他保留了自己的生活空间,未将它全然开放给某种理念,人也是温和的,并不愤怒。这些专栏里的文字也是如此,精致、妥帖。
说起来,只有看了这本书我才知道,原先在北京打车竟然如此难,不仅看出租车司机脸色,还要看自己的姿色。在早期的专栏里,贾葭没少调侃这件事,但是现在,各类打车软件确实解决了这种困扰。打开手机,点开app,输入目的地,如果可以的话,稍为加点小费,来接你的司机就会殷勤有加。
我从来就不知道时代是不是向前的,在循环往复中,我看到倒退,又看到希望,那些带给人自由和禁锢的力量似乎在相互拉扯。但我还是不太明白,我有时悲观,有时乐观,言论举止像个精神分裂。这本书的作者似乎也是这样,在一种茫然里,记录着急速地、易变的时代。
注:本文首发于今日头条
《我的双城记》读后感(八):我的第五年
晚上不想写作业,于是读完了贾葭老师的《我的双城记》,他写南京,香港,台北,杭州,广州,皆收放自如,文采飞扬。然而最熟悉的,写得最多的还是北京,北京的交通,雾霾,书店,胡同,租房,大院儿...嬉笑怒骂,毫不费力的幽默和辛辣,在操场边读着不禁笑出声来,转头又是一阵叹息。
来北京第五年,对这个城市感情很是复杂。要说熟悉呢,即使是在五道口还是常常迷路,前几天终于去了神往许久的清华园火车站,一下车就找不到方向了,打开地图,还是因为说不清自己的位置被师傅愤然挂了电话,站在路边举着电话目瞪口呆。可是要说陌生,我那过度吸入雾霾的肺和常因为过敏迎风流泪的眼角,恐怕都要出来抗议。
高二的时候,同桌来T大参加暑期夏令营,回来告诉我,北京真好,地铁两块随便坐,你说,如果没啥事儿,出来做一天地铁也是很开心的。
后来我们俩一起来了T大,在地铁上找到位置的次数屈指可数,更不用说满车的汗臭味和喧哗声。再后来,地铁涨价,2块钱好像只能去一趟北大了。还回不来。
如果不赶时间,公交才是最好的出行方式,中学时候开始,没事儿的时候我喜欢一个人坐公交车在城市里面乱逛,随机上车,随机下车。可是我们家那个十八线城市,公交车绕着城市基本一个小时就可以逛完,很是不爽。北京很好,能够满足我这项生存需求,而且又因为我搭错车,坐过站,坐反方向的技能惊人,因此随机地去过许多奇怪的地方,比如公主坟,玉渊潭,某某沟,某某河。
当然也因为计算错时间,被堵在北大东门到清华北门的路上,长达一个小时。
北京的冬天真长,长到让人觉得好像永远都不会过去了似的。一下雪就变成的北平,如今已然是看不见了。雾霾天的北京俨然一个深不见底的噩梦,纯白洁净的雪只会出现在照片里面。高中的时候,冬天是最喜欢的季节,天冷气清,头脑最是清醒,有利于记忆和思考。可是来了北京,冬天变成了最sentimental的季节,需要时时握紧拳头打打气,常常往自己的头顶浇一碗热鸡汤,才能平安捱过漫长而寒冷的冬季。去年冬天为了躲避寒冷,甚至跑去了一次香港。
去年冬天,北京天气最差的几天,在风里冻得哆哆嗦嗦的时候也会狠狠地想,不如以后到南方去,可是转过头想想夕阳里金色的昆明湖,生长着古老的树木的老胡同,永远能让我平静下来的美术馆和三联书店,虽然天气很差但四季分明的气候,便也觉得十分舍不得。
于是,春天来的时候大家都格外兴奋,食堂外面开了小小的一树花,于是朋友圈立马开启了摄影大赛。风刚刚开始变温柔,我们就赶紧抓住一切周末出行,带着小帽子,到鼓楼去,到百望山去,到长城去,到春风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好像这辈子从来没见过春天一样。
我发现我很白痴啊,进入了一个我全然不懂的世界。这位作家还说,你有那么多大v朋友,此时不用,更待何时呢?还是不是朋友?王五四呢?让他带个京东链接发一篇书评啊。我说读书人面皮薄,不好求人。但事实上,昨天到今天晚上,我一直在求转发,好像过去积攒多年的人品要厚积薄发了。
昨天下午在田朴珺工作室喝下午茶,走的时候,我特别不好意思地说,你方便的话在微博上帮我发个照片吧。田老师说,你想怎么发?我又不好意思地说无所谓啦。后来我又觉得只发照片似乎对卖书无甚帮助,于是打算在微博上带上链接。谁料一打开微博,发现我的账户被封了——上一篇微博是批评胡锡进老师那篇香港书店的文章。
于是我又重新注册了一个微博,发了三张图,小心翼翼地说,“希望能多卖几本哈,谢谢大家。”然后打开朋友圈,刷到蒋方舟的一条,于是迅速私信她:方便的话帮我转条微博。她痛快地答应了,然后,我又特别不好意思地说,我能带条购买地址吗?她说好呀好呀。她早就卸载了微博,说要我等一下,她下载一个微博再转。我于是把那条微博分享给她。
后来王小山、张晓舟、朱学东几位都转了。还有(司马)南学泰斗、(周)带鱼学专家文三娃也转了。我看书一直到半夜,给在美国的闾丘露薇发微信求转。她很体贴地说,等北京时间白天再转。朋友们都挺给力,接下来就看王五四、张嘉佳的了。一路下来,就是一个感觉:很不好意思,很腼腆。王小山说我这个人实诚,我认。因为卖书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对出版商而言,我就是个新人,没法装。
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无非是想多卖几本书,我在朋友圈非常诚实地说,多一刷我有三万九的版税,这是税前。相比而言,实在算不上太多。只是我觉得中国写字的知识分子着实辛苦,版税没有港台高,印数没有西方多,一本书拿不到多少钱。中国虽然是人口大国,但人年均读书量只有日本的百分之一。看着那些长年占据榜单的心灵鸡汤致富秘诀创业机密和建设和谐社会中国梦的著作,实在让人扼腕。
扯了这么多,如果大家想随手帮我一下呢,就在豆瓣上点“想读”,阅读原文链接是京东的购书地址,想买的呢,非常感谢您的支持。不想买的呢,也不用点进去了。再次感谢大家,祝大家丙申年春节愉快,阖家幸福,猴腮雷!!
《我的双城记》读后感(十):zz:从京漂到港漂-空间与政治
从京漂到港漂:空间与政治
白信 HeForShe
记得08年刚回国,跟某教授谈起中国政治转型,blabla一通之后,我谈起政治的本义就在城市,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速,中国政治的重心越来越以城市特别是超大型城市为中心,早就不再是那些热衷“三农”情怀的人们的乡愿了。而且,这种城市中心的政治,不是简单的因为政权机关都在城市,那从来都是中国城市或者政治的传统,有别于欧洲的封建政治传统,连枫丹白露都与巴黎有着几十公里,而是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空间的不断扩展和改变所形成的政治。以著名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的话说,就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现实,部分是真实的,部分是虚构的。
这或许便是我们今天所经历、见证、生活其中的中国城市景观。其中,既有生长中的新公民社会,他们在以业主自治、教育平权、倡导LGBT和女性权利、抗议强制拆迁、文物和社区保育、兴办打工子弟学校、甚至跑马拉松的方式改造着城市景观;同时,还有其中的无数北漂青年,与农民工群体一样,感受着、碰撞着“进入城市的权利”,也就是列斐伏尔意义上重建时间与空间统一性的努力。而这一解释似乎也同样适用文学,多少伟大的文学作品,真实叠加虚构的创造,便构成人民长久以来对一个城市空间的记忆。
贾葭,2002年从南京大学毕业来到北京后,尤其是离开国有媒体机关开始真正的北漂生活后,便以自己的脚步,穿街过巷,探访北京的胡同和人群,记录也虚构着北京城市的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不过,就像城市的空间和政治并不只是胡同或中产,“进入城市的权利”也不限于北京的暂住证或者户口,还可延伸到上海、香港、台北、纽约等等,一条条空中航线的连接打破了传统的时空限制。作者向往着、实践着穿梭于香港和台北的不同空间,在这些地方的不同媒体任职,然后进入当地的景观之中,也在专栏作家的写作过程中,以专栏而非纯粹的文学形式,在今天的城市景观中,交织回溯着这些城市的历史记忆,生产出《我的双城记》一书。
在这本文集里,既有帝都风物、庙堂江湖、胡同大院等等,也有较帝都远为活跃的香港一地的公民社会,以及似乎更为古老、温文尔雅、被小确幸掩盖的台北生活。只是,这样的时空统一,竟然如此一贯地出现在作者的行迹漂流中,却没有消灭抵抗和冲突。作者的每篇文章虽然短小,却在在冲击着读者对规制、传统、文化和现实的感受。这似乎也是作者对自由的理解,一如他当初走出大院,步向胡同和市场化媒体然后香港,从主编到专栏作家,贾葭向往的是穿梭在不同的城市,也就是高频地去体验“进入城市的权利”,然后思考城市政治的具体意涵。
而最终,这种进入城市的权利作为时空的统一性,一旦被人们赋予了“哲学上的特权”(即形而上学),被城市政治自我意识然后加以强化,那么便如列斐伏尔所说,其主体性便消失了,“一般意义的阶级在其中既没有位置,也没有身份”,城市化制造了新兴中产阶级也同时消解着阶级,只有抽象的公民才可能继续集结在自治的城邦中,或者反之,被剥夺公民权利的逃逸者接受被统治。作者对“进入城市的权利”的渴望、对城市时间和空间统一性的探究,从北京到香港,从京漂到港漂,却终究免不了个人在新书付梓后的命运——消失在繁忙的京港空中航线上,仿佛马航370的消失。
是主体,还是系统?作者以亲身的命运,变换成列斐伏尔最后的问题,提醒我们,每一个刚刚开始品尝所谓新兴中产阶级主体性的个体,却要面对主体性的消失,仿佛都市社会的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