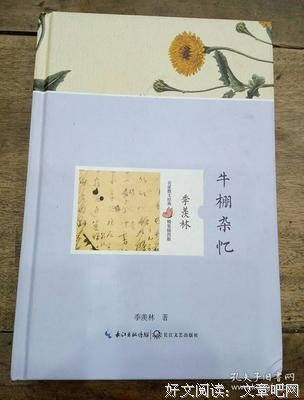
《杂忆与杂写》是一本由杨绛著作,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2.00,页数:27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杂忆与杂写》精选点评:
●杂忆部分很有趣
●<花花儿>推荐...
●杨绛的文字像清茶,淡淡的文字,陪着你回味她所经历的过往岁月。
●平淡有致温情的经典之作
●平淡动人
●温暖人心
●两口子都写散文,我偏爱老太太的。不是为了俏皮而开的带掌故的玩笑,而是看过一次两次之后,笑在心里。
●@北京。
●杨绛先生
●不矫情的女作家真好。怪不得人人喊她先生。
《杂忆与杂写》读后感(一):喜欢,如饮茶
是什么样的一本书呢?薄薄的,对,太厚的书,怎么也看不完呢。象这本书,里面都是几页的文章,如珠子一样连起来,可以随意从什么地方开始。。。
除了薄薄的,文字也是淡淡的,没有你不懂的文字,没有故意摆学问,没有什么地方让你觉得别扭的。
好像一个特别慈祥而又经历颇多的老太太,而我们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孩子,在那一个很阳光很阳光的下午,听她讲,有时就睡着了。
就是这么一本书。
《杂忆与杂写》读后感(二):流浪儿
杨绛的《杂忆与杂写》,大部分篇目在大学时读的杨绛文集里都有收录。在文集里,我最喜欢的是《我的父亲杨荫杭》,《我的姑姑杨荫榆》,《记杨必》,还有回忆自己从小读书经历的篇目。这些文章的格调就像她翻译的那首诗。
我和谁也不争,
和谁争我也不屑,
我以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
我也该走了。
可惜在杂忆与杂写里,没有收录她回忆父亲和姑姑的两篇。
昨晚读到一篇散文,特别喜欢。叫《流浪儿》,把自我阐释的通通透透。转贴在此。
我往往“魂不守舍”,嫌舍间昏暗逼仄,常悄悄溜出舍外游玩。
有时候,我凝敛成一颗石子,潜伏涧底。时光水一般在我身上淌泻而过,我只知身在水中,不觉水流。静止的自己,仿佛在时空之外、无涯无际的大自然里,仅由水面阳光闪烁,或明或暗地照见一个依附于无穷的我。
有时候,我放逸得像倾泻的流泉。数不清的时日是我冲洗下的石子。水沫蹴踏飞溅过颗颗石子,轻轻快快、滑滑溜溜地流。河岸束不住,淤泥拉不住,变云变雾,海阔天空,随着大气飘浮。
有时候,我来个“书遁”,一纳头钻入浩瀚无际的书籍世界,好比孙猴儿驾起跟头云,转瞬间到了十万八千里外。我远远地抛开了家,竟忘了自己何在。
但我毕竟是凡胎俗骨,离不开时空,离不开自己。我只能像个流浪儿,倦游归来,还得回家吃饭睡觉。
我钻入闭塞的舍间。经常没人打扫收拾,墙角已经结上蛛网,满地已蒙上尘埃,窗户在风里拍打,桌上床上什物凌乱。我觉得自己像一团湿泥,封住在此时此地,只有摔不开的自我,过不去的时日。这个逼仄凌乱的家,简直住不得。
我推门眺望,只见四邻家家户户都忙着把自己的屋字粉刷、油漆、装潢、扩建呢。一处处门面辉煌,里面回廊复室,一进又一进,引人入胜。我惊奇地远望着,有时也逼近窥看,有时竟挨进门去。大概因为自己只是个“棚户”,不免有“酸葡萄”感。一个人不论多么高大,也不过八尺九尺之躯。各自的房舍,料想也大小相应。即使凭弹性能膨胀扩大,出掉了气、原形还是相等。屋里曲折愈多,愈加狭隘;门面愈广,内室就愈浅。况且,屋宇虽然都建筑在结结实实的土地上,不是在水上,不是在流沙上,可是结实的土地也在流动,因为地球在不停地转啊!上午还在太阳的这一边,下午就流到那一边,然后就流人永恒的长夜了。
好在我也没有“八面光”的屋宇值得留恋。只不过一间破陋的斗室,经不起时光摧残,早晚会门窗倾欹,不蔽风雨。我等着它白天晒进阳光,夜晚透漏星月的光辉,有什么不好呢!反正我也懒得修葺,回舍吃个半饱,打个盹儿,又悄悄溜到外面去。
《杂忆与杂写》读后感(三):死鬼-杨绛的好事
杨绛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兔死狐悲,惜老怜贫,人可以做好事,但事后得沉得住气,哪怕旁敲侧击着,也得要人家老王张口说才行,哪能急三火四的,自己个满世界吆喝,菩萨下凡,做了天大的善事。想当年白雪公主她后娘还没那么猴急。
但无论如何,铁了心的杨绛从此耐心潜伏,冷眼看着八十年代的风波退去,内心就热锅上的蚂蚁一般,等着自己的伯乐“登堂入室”,再彼此心照不宣地签了份“卖心契”。也终于在近二十年后钓到了几只“肥王八”。君不见,『老王』被“合谐”的灵魂进了少年的书包,成了蒙心的猪油,杨就化身九零后们的历史“正能量”,紧接着就是『我们仨』畅销大卖,她终于实现自己做了一百年的梦,成为文坛盟主,天下第一正派大作家,可极讽刺的是,杨走在人生边上却登到了自己野心的顶峰,死也不打算下来了。
如果说世纪末死去的冰心还是所谓的“文坛祖母”,那自新世纪以来,她显然被杨绛整过气了。而杨就如愿以偿,成了名副其实的文教“西太后”。她“茅房里偷手纸”一般,洗稿了冰心的『小橘灯』,因为冰心的成功虽极偶然,却也极好复制,无非东风吹,战鼓擂,杨就自作聪明,依葫芦画瓢,也诹了一篇同样居高临下又“死道友不死贫道的”自恋文章,就是大名鼎鼎九零后们的“唐僧肉”可令学业仕途“长生不老”的『老王』,果然还写得龙颜大悦,雨顺风调,成了“拨乱反正”的时代里最“贴金”的声音。
『老王』也顺理成章的和『小橘灯』一样扣着时局的命门,进了普天下的教材,被“收编”为可以左右学子仕途命运的“敲门”文章,学“好”了,就是“社会栋梁”与“民族之光”。学“坏”了,就是“倒行逆施”和“不忠不孝”了。真是蛇精偷走了葫芦,小娃傻傻地认贼作父。
时代的换汤不换药里,雅俗共赏着,只不过把冰心用来照路的橘子灯,换成了老王送给杨绛的香油和鸡蛋,可这油和蛋放在一块儿送,老王一介草莽,他再憨厚又怎么可能没听说过,民间口耳相传的调皮话,说的是,“鸡蛋抹油—滚蛋啊 !” 这还真不是开玩笑,像老王一样穷苦,却还去乞讨办学的大教育家武训要得了杨绛那铁公鸡的施舍,恐怕会和老王一个下场,只消几个铜板,杨就敢自诩武训的恩主,再把他圣人的光环偷走,戴自己头上,扮个圣母接着偷。这个杨绛跟那个杨澜是一丘之貉。
老王这样的“人血馒头”,对一个灵魂阴暗行事如秃鹫一般的文人来说,真是“有便宜不占-王八蛋”。杨绛写信,写散文,写回忆录,欺负了一圈,都是死人来的,钱锺书 ,钱瑗,女婿王德一,老王,张爱玲,冰心,当然一众跟在她屁股后面数钱的拥趸,虽然还能喘气,也都是死心塌地的行尸走肉了。
其实撇开“羊粪”不谈,我建议各位去读一读,韦君怡的『思痛录』和章诒和的几部著作,而不是仅仅通过杨绛的『老王』去理解和关照那段历史,两头真的人是可信的,杨绛语焉不详的历史的另一面也是折磨人的。人活着,虽不用太较真,可总得起码对得起自己的智商,你们一个个都老大不小了,你们不进步,中国必然要倒退的,别再读那些鸡屎文了,杨绛随便看看,尝尝鲜,也就可以放下了,成年人该有更深的思想,更真的精神,这倒跟升官发财没啥关系,可人起码可以输个明白,死而瞑目吧。
时代在变,鲁迅被请出课本,张爱玲仍困冷宫,而杨绛这样民国文坛的三流女文人,八面玲珑之后,却被请进课本,成了时代乡愿者的头牌,亲们对她多留个心眼是明智的。输光了不丢人,可光屁股谢恩真丢人。
最后,我对老王实在无太多的话可说,他就是苦难本身,是一切时代的主角,任何时候都不能被违心亵渎的“民”,而利用这亘古不变的苦难为材料,仨核桃俩枣就给打发了,再加工成历史的“善莫大焉”,时代的“好大喜功”,如此扭曲的人做扭曲的事再扭曲着理解,扭曲着表达,这世界是万万简单不了了,人生和社会更是变得极其复杂而且残忍乖戾。 所以我想,真正为文之人必须把“老王”写实写真,不能赞美,因为实在无“美”可赞,亦不必怜悯,因为我们自己也“好”不到哪去。
这个世界里,所有人都可能是老王,却绝不会有圣母,即便有,也不是杨绛。
《杂忆与杂写》读后感(四):鸡蛋抹油-杨绛的算计
时代的换汤不换药里,雅俗共赏着,只不过把冰心用来照路的橘子灯,换成了老王送给杨绛的香油和鸡蛋,可这油和蛋放在一块儿送,老王一介草莽,他再憨厚又怎么可能没听说过,民间口耳相传的调皮话,说的是,“鸡蛋抹油—滚蛋啊 !”
就像张爱玲和冰心有过小小的交集那样,杨绛和苏青也有过一些业务上的来往,可苏青看不透杨绛的"鬼雅",杨绛看不真苏青的"浑俗",所以两人合作改剧本的事就没下文了。但一桌麻将,几圈下来,“屁和”输光的冰心就是个彻底的可怜虫了,张爱玲暗讽她层次太低,苏青更直接怼她长得难看,灵魂和身体分别被极聪明和极率真的两个“牌精”给“杠底开花截了和”。女文人的圈子是极戏剧化的牌桌,不见血的生杀活埋,有点“野路子”的残忍,像分娩时非人的疼痛。
不过带给冰心毁灭性打击的恐怕还要属杨绛了,这个首鼠两端的"左右手",“投机取巧”的“墙头草”,殊不知,贼船上更是尔虞我诈的步步惊心,杨绛驾轻就熟,葡萄架下宴客,大观园里设局,一对赫赫扬扬,女先生,男院长,两口子遮天盖日,百事周到。而冰心就捉襟见肘,疲于应付,三寸野心,一朝磨平,被迫去“寄小读者”,几次三番之后,彻底沦为文教“奶子”。可见善恶奸贤虽不共戴天,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即他们皆不待见无病呻吟又长相平凡的庸人,好比冰心这一流的。
但是把文化界的“下脚料”丢给儿童,如此的误人子弟,实在兹事体大,冰心一辈子尴尬,就是总出现在最不该自己出现的地方,如把最好的才华文笔丢在『太太的客厅』里,却把最矫情乡愿的话寄给了祖国的花朵们。也难怪林徽因送她一坛醋,啥也没说,正经人恋爱工作,两头忙不过来,才没时间对牛弹琴。可杨绛就是虎视耽耽的秃鹫,冰心的名声像曾经滋养过剩的肥羊肉,还是令那“禽兽”垂涎三尺的。冰心的平庸让杨绛看到了自己“选秀入宫”的唾手可得,正是“好风凭借力,送她上青云”。
冰心的鸡肋之感也要怪她自己德不配位又傻人没傻福,不幸生在民国那"水浒"一般弱肉强食的文人世界里,天破个窟窿,漏下一众风流冤家,谁叫她自己是面糊的,美不及李师师,恶不敌孙二娘,浪不齐潘金莲,作不过阎婆惜。她只是圣洁着肤浅地以为小妹杨绛是个"贤良"的蚊子,几滴血就够养她一辈子,可憋了一肚子狐疑,杨绛却还是杜鹃下的蛋,翅膀刚一硬就打发冰心卷铺盖腾出自己在"文渊阁"里的“牌坊”,她也要陪皇帝读书,作天子门生。此话怎讲? 亲们耐心往下看。
理解冰心的大不幸,还得从进一步看穿杨绛开始,她的虚伪亦表现在对苏青的态度上,杨自己承认苏曾找过她为把『结婚十年』改编成剧本,可苏青就很自然的在『结婚十年』里写到过自己迫于生计而打算学日语进日行做事,这样的汉奸小辫子对杨绛来说,那是现成的借题发挥,可是因为苏曾经“看得起”她,杨才有选择的忽视了,所以她气不过地鼓动愚众批判张爱玲,就是“酒家女造谣生事,不甘寂寞,所谓谁敢不多看老娘一眼,老娘就定让他过不去”,只因为张不只看不起她,更是连睬都不睬她,简直当她是吹灯拔蜡,墙上的一抹蚊子血,黑了干了就她自己知道。
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不论时代,文人比的就是谁文笔好,谁想得更妙,放的更开,“匍匐”得更低,显然杨比一般人聪明的多,但比之天才,她就明显脑子不够用了,别说独占鳌头,就是在当时,比她强的文人都太多了,连冰心都比她“强”,深居简出几乎不见人的张爱玲就更是众矢之的,骨灰宅女不出风头,反倒乘着流言出尽风头。魑魅魍魉,多少残花败柳,如潘柳黛之流,没缝的鸡蛋还要下蛆呢,更何况同样妒火中烧,却又心思极诡僻幽灵的杨先生。她的手段是划时代的,也好运得骇人,放长线钓王八,刀口上舔血两不耽误,杨绛对时局的触探堪比“毕马威”的精算师,人性堕落的数字模型,她了如指掌,又兼具阿里巴巴和马云的身段,长袖善舞,能屈能伸,虽心术不正,也好在足够的无耻淡定,是女文人的脂粉队里罕有的能够左右开弓,玩转权政,为我所用的凤毛麟角,活似夜叉变的蔡文姬,嘴淡心苦,明是一盆水,暗为一把刀,信口开河,除了真话,什么都说。
妒忌的种子可机缘巧合的开枝散叶,再假以时日,更是遮天蔽日的怨毒,甚至就像『古文观止』的开篇所说的,一个难产的女人会怨恨自己的孩子而产生极具变态后果的恐怖情愫。所以复杂人性里哪怕是看似单纯的母性,也要在具体事件中耐心观察校验,才能有所体证,不然就是一厢情愿的自愚愚人。又所以泛泛而谈之中,杨绛看似曹操一样的白面清高,就十二分的靠不住了。我们时常得有尤三丫头的犀利眼光,和晴雯姑娘的洞若观火,方才看得真王熙凤的“花花肠子”,防得住薛宝钗的“诡意幽思”,而不是作迎春姐尤二娘似的糊涂忠厚,白白的死,也无人待见,徒惹“虎狼屯于阶壁,尚谈因果”的讥诮。
还有一个几乎没人注意到的有趣轶事,亲们权当笑话听就行。当年林徽因送醋,人说是暗讽冰心嫉妒,反正都是些皆知的闲话,这是历史的大背景。而人心的小背景是,杨绛“茅房里偷手纸”一般,洗稿了冰心的『小橘灯』,因为冰心的成功虽极偶然,却也极好复制,无非东风吹,战鼓擂,杨就自作聪明,依葫芦画瓢,也诹了一篇同样居高临下又“死道友不死贫道的”自恋文章,就是大名鼎鼎九零后们的“唐僧肉”可令学业仕途“长生不老”的『老王』,果然还写得龙颜大悦,雨顺风调,成了“拨乱反正”的时代里最“贴金”的声音。也顺理成章的和『小橘灯』一样扣着时局的命门,进了普天下的教材,被“收编”为可以左右学子仕途命运的“敲门”文章,学“好”了,就是“社会栋梁”与“民族之光”。学“坏”了,就是“倒行逆施”和“不忠不孝”了。真是蛇精偷走了葫芦,小娃傻傻地认贼作父。
此一举还一石二鸟,杨绛踩他人头顶上位成功,差点要改名“杨紫”。同时也把冰心挤兑得过气了,事过境迁,“减租交租”的大团结一去不回,八零后的“小橘灯”也就彻底熄灭了,时代得炮制新的骗局。只不过冰心那盛名难副的庸人走进历史是极悲哀的惨状,因为既便“大奸大恶”都是反面教材里的永恒,被咒骂之余,还能获得一点知性的理解,好比秦桧也是“曲线救国”。俗话虽说“恶人总有恶人磨,邪党自有邪党害”,可是冰心被杨绛取代之后,将来还会不会有人为她扫墓都是未知数了。总之骂她“教子无方”的亲孙子是肯定不会再去祭奠她祖母了。更要命的是,冰心自己的文章不只乏善可陈,更没坏到令人产生骂的欲望,像用过的洗脚水,不很脏,但拿来洗手那是作践,可肥力又太不够,拿去浇田,就实在小题大作,浪费功夫。不过无论如何,冰心总是灭在杨绛的手里了。这是极耐人寻味的,想必“裹脚布”久了也得换成更时新的,更好使的,才能继续拴牢年轻人的头脑,令他们的精神继续跛下去,一如既往。
时代的换汤不换药里,雅俗共赏着,只不过把冰心用来照路的橘子灯,换成了老王送给杨绛的香油和鸡蛋,可这油和蛋放在一块儿送,老王一介草莽,他再憨厚又怎么可能没听说过,民间口耳相传的调皮话,说的是,“鸡蛋抹油—滚蛋啊 !”
杨绛的“不食人间烟火”,虽说是装的,却也是颇费周章的假戏真作,虽说登高必跌重,可冰心点着灯照着路还算下了台,十八辈子的脸,算是没有丢尽。可杨绛作贼心虚的习惯了,套路总往歪里想,结果“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