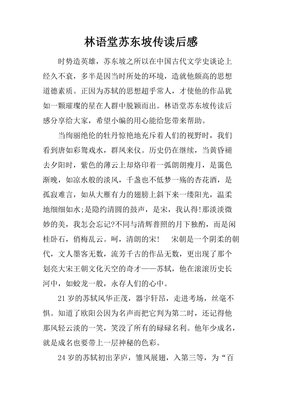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上下册)》是一本由郑振铎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18.00元,页数:119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上下册)》精选点评:
●我买的便宜,但是收获很大!非常好的书籍,我为我买了这本书感到一种骄傲! 历史观的改变,范围,新的发现
●断断续续读了半年,很棒的中国文学指南,小说变文戏文诸宫调民歌宝卷弹词,集大成之作,成一家之说.如果郑先生没有英年早逝,这本书的后续会如何呢?
●与众不同,流畅,才情,没有酸腐气。
●記得當初是衝著「插圖」去的,十年裏只是草草翻了幾遍為了看圖。目前書架還未立起,手邊能看的正經書不多,今天抽出來一翻開居然有微微的潮濕混合蠹魚的氣味了。讀了下冊的南宋部分,果然津津有味。
●很細膩的文學史。
●太深奥!
●每章后开书单,经典的文学史
●徐子东曾指郑振铎的《文学大纲》为其文学启蒙书籍,而这本《文学史》相信也不啻为相应读者的思想史佐料。抛开待考证的史料,又略嫌囿于追本溯源。很有见地!
●读完了上册。材料丰富,文笔优美;但似略嫌浅杂,于“文学”之义不能做更深刻的探讨。故作为一本史学著作,在释古今变化之迹上,显得有点无力,但这似乎是许多文学史的通病了。
●不错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上下册)》读后感(一):成一家之言
郑的白话文读起来很拗口.
书才刚开始看,已经很赞赏郑的独立观点.关于诗经中"风雅颂"的论述很详细,除却列举古今的两种评论外,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上下册)》读后感(二):与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比较
与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汉语言专业基础教材)来比较,这本更侧重史料的辨伪与分析(可能和作者性格有关,现在是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因此,可能含有个人的主观想法与评论),而袁的更侧重学术大众。 这可以从引用的书籍看出来,郑的参考书大部分是基于原典基础,基于作者态度的评论。而袁的是综合各家之言,面相广泛学生而编纂的普适类文学史。 如果作考研的主要参考书籍,不太建议。但是可以做考研辅助参考书籍。袁的《中国文学史》中关于文学活动的时期分段,比如就引用了他的观点。 相当于从个人独特的学者视角看待文学史的发展演变,而且对于理解袁的《中国文学史》有很多帮助。 史料辨伪分析部分,我一般都直接跳过,毕竟当前水平有限,入门级的越看辨析越晕,不如直接看重点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上下册)》读后感(三):有见地的一本书
要想研究中国文学史要那么一两本所谓的〈中国文学史〉教科书是很有必要的,但也是很危险的,现在的那些书在我眼里看来基本上就是垃圾,集体创作的东西,毫无个性可言,大量个人貌似客观主流的评价,对原作者详细的介绍个评价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许多学生根本就是只看教科书不看原文了,这跟写这个书的初衷相背。但这都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学那么丰富,但是文学史就那么几册,选哪些作家哪些作品是一个要认真考虑的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大家的文学史都写得很没有个性,反正写来写去就是那么几个作家,在古代还好些,在当代,意识形态是会把一部分作家给遮蔽了。
还好还有郑振铎,在建国之前他就写了这本书,没有受到当代精神文化污染的一本书,从这本书中,你可以看到中国俗文学的发展的一个源流,其实现在读古诗,就算那些诗歌伟大吧,但是有几首能抒发个人的感情呢,那种经过提练的感情总是让人感觉远远的,倒是那些民歌、散曲,真是有无穷的味道,都说当代纯文学不值钱了,其实纯文学从来就不值钱,只是一帮人清高的炫耀物,为了升官的一个手段。而对花间词,对宫体诗,现在的官方一直是持批判态度的,但是细读一下,里面还是有一些真情的流露,诗贵情,我是一直这么认为的。而对于诗歌浅白一路,从王梵志到寒山、拾得再到顾况、罗隐这一路代表的浅易的诗歌也是当代文学史被遮蔽起来了的。
不用细看,翻翻这本书,也许你就可以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一些个别人没有注意到的东西。
最遗憾的是中国古代没有记录歌曲的谱子,那些优秀的东西就没有了,西方文学的发展跟音乐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中国也是一样,可惜没有曲谱,很多有声韵的东西都失去了,虽然文字还留存着,但是少了那份直观的味道,真的是很大的遗憾。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上下册)》读后感(四):吴光兴 | “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 与郑振铎的文学史观 ——兼论“综合的中国文学史”的体制困境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18年第6期 第34-42页
内容提要在郑振铎的文学史研究之中,“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是他长期关注的主题。他的文学史分期实践,与他成长并奋斗在其中的“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环境、他的个人气质与趋向、他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之间,具有广泛复杂的联系。而相关的,他的代表作《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现代学术史上引起的风波,与“综合的中国文学史”的体制困境之间的联系,亦值得思考。
关键词 郑振铎;文学史写作;文学史分期;《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综合的中国文学史
在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上,郑振铎以多领域、高产量著称。尽管如此,他的学术领域仍有一个“重中之重”,以《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等为代表的特色鲜明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倾注热情高,持续时间长,成就也很突出。在文学史写作实践之中,郑振铎对于“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有过特别关切。本文试由这一事关文学史基本架构与史家文学史观的关键点切入,探讨他的文学史写作的历史经验,总结其风格与成就。而对于20世纪30年代前期《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问世之初所引起的那场纷议与风波,本文特提出“综合的中国文学史”体制困境的问题来讨论[1]。纪念郑振铎,也反思现代学术史。
一 郑振铎的文学研究生涯
与文学史写作
郑振铎青年时代上的是铁路学校,他投身文学事业,完全出于爱好。他的文学研究,一方面,主要通过自修习得,与接受过常规学院培养的学者有所区别,受制约相对少,自由度相对大;另一方面,他对于文学(包括“文学研究”)的兴趣与热情异乎寻常,开拓之勇猛,也异乎寻常。在观察他的文学研究生涯之前,先要对此有所认识,他日后成就之取得与学术“出身”之间也存在某些微妙关系。郑振铎的文学研究生涯大体上可以分为“进取”“一家之言”“成熟”“晚年”四个阶段来追踪。
1.踊跃进取阶段(1917年至1927年)。在参与发起并加入“文学研究会”之后,郑振铎进入自觉从事文学研究的阶段。1920年,他经手起草《文学研究会简章》,声称:“本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其中,“整理中国旧文学”即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谓“整理”表明不是对于传统文学的简单接受,而是有立场的研究。当时有“整理国故”思潮,“整理中国旧文学”为其中一部分。1922年,郑振铎发表《我的一个要求》,大声疾呼一本比较完备的“中国文学史”:
我要求一部“中国文学史”,但是那里有呢? “中国文学史!”唉!那里有一本完备的呢? 我要求,我现在向研究中国文学的人要求一本比较完备些的中国文学史![2]
据与郑振铎同为“文学研究会”发起人的郭绍虞自述,五四时期,他本人也屡次尝试写一部《中国文学史》,后来退而求其次,缩小范围,遂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之研究[3]。
郑振铎勇于实践,在20世纪20年代“文学研究会”的活跃期,对于世界文学之介绍、中国旧文学之整理、新文学之建设,都有出色贡献。文学研究方面,他编译、撰述的在《小说月报》连载三年的“文学大纲”系列论文,令其异军突起[4]。他的“文学史”写作,开始于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俄国文学史略》,正文13章。书中配插图、附录大事年表、参考书目等,都预示了郑氏文学史的特色。而“中国文学史”之写作,前述《文学大纲》之编撰可以视为“打头阵”的项目。《文学大纲》一书专论中国文学史的,有12章20多万字,已成一部初具规模的“中国文学史”。可以说,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起步,实“寄寓”或“嵌入”在“世界文学史”之中。这也预示了他的文学史写作的某种风格色彩。
郑振铎:《俄国文学史略》,商务印书馆1924年初版本2.著书立说,“自成一家之言”阶段(1927年至1935年)。1927年5月开始的欧洲访学、访书、访古迹之旅,是郑振铎学术生涯的新起点。他在巴黎、伦敦查阅到不少中国文学新资料,主要是小说、戏曲、变文等。1928年秋返国,郑振铎加紧撰述,于1930年“试验式”地推出《中国文学史》(中世卷第三篇上)。1931年秋,应“文学研究会”老友郭绍虞之邀,郑振铎远赴北平燕京大学等校任教三年多,其主要目的仍然是摆脱繁重的编辑事务而专心撰写“中国文学史”等著作。《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于1932年底开始,由北平朴社陆续出版。在毁誉交加的风雨之中屹然自立、驰名学坛。1934年,“十年工力,毕集于斯”的《中国文学论集》也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所撰《〈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亦可做极好的“新文学运动”简史来读。对于郑振铎的学术生涯乃至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学术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出版,标志着“文学史”领域的郑氏风格已臻完成。
3.成熟与开拓阶段(1935年至1949年)。1935年上半年自北平返沪,直至1949年,国内国际风云变幻之际,郑振铎参与领导左翼文艺运动,在鲁迅逝世之后,更成为上海乃至全国文坛的中心人物之一。文学研究方面,1938年,他为国家抢救购置了极为珍贵的《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同年,出版《中国俗文学史》,也发表、出版了许多论著。此时期,与他逐渐建立起来的藏书名家之地位相适应,他屡次编集小说戏曲资料书,在俗文学研究资料库建设方面的这类努力,也导向到将来的《古本戏曲丛刊》。
4.晚年(1949年至1958年)。新中国成立以后,郑振铎担任许多公职,发表了一些论文,最大的成绩是组织团队整理出版大型文学资料丛书《古本戏曲丛刊》。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论集》《中国俗文学史》等均有新版问世。然而,由于大体上因仍旧貌,他在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中受到较多批判。当时,他也自我批评,但还没有来得及学习运用更新的理论方法对旧作进行彻底修订,就在1958年10月因公殉难了。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作家出版社1957年修订版1957年,郑振铎的老友周予同应邀为古史专著《汤祷篇》作序,对于郑氏学术成就有一段近乎“盖棺论定”式的概括:
振铎兄治学的范围是辽广的,也是多变的。他从五四运动前后起,由接受社会主义思想而翻译东欧文学,而创作小说,抒写杂文,而整理中国古典文学,而探究中国古代文物。概括地说,他的学术范围包括着文学、史学和考古学,而以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为他毕生精力所在。[5]
综上,追踪郑振铎的学术生涯,文学史研究堪称中心线索。总结并继承他的学术遗产,对于他中国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成就,更要认真面对。
二 郑振铎的文学史分期实践
分期问题之于文学史写作,一般具有框架的地位。分期的权衡与确定,深层地看,导源于学者本人所秉持的文学史观,而学者之写作文学史,整个文学史叙述的展开、资料的采用,无疑又受到分期框架的基本制约。郑振铎从事文学史写作,就具有非常自觉与明确的文学史分期意识。1932年7月,北平朴社发行《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预约样本》,为不久将要问世的新书打预约广告。《例言》指出,《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取材”“分期”“论断”“插图”几大卖点之中,“分期为自己独创”是重要一项[6]。下面,以时为序,考察郑振铎文学史写作实践如何处理分期问题,并探讨分期背后的文学史观。
以1923年至1926年间的《文学大纲》这个“打头阵”的项目为例。有关中国文学史的部分包括12章(章节序号与最初连载时略有不同),似可整合为7个段落:(一)第七章《诗经与楚辞》、第八章《中国最初的历史家与哲学家》;(二)第十章《汉之赋家历史家与论文家》、第十一章《曹植与陶潜》;(三)第十三章《中世纪的中国诗人(上)》、第十四章《中世纪的中国诗人(下)》;(四)第十七章《中国戏曲的第一期》、第十八章《中国小说的第一期》;(五)第二十三章《中国小说的第二期》、第二十四章《中国戏曲的第二期》;(六)第二十九章《18世纪的中国文学》;(七)第四十四章《19世纪的中国文学》。如果暂不考虑(四)(五)有关小说戏曲的两个段落的插叙因素,即为5个时段;而(六)(七)所述18世纪与19世纪均属清代,再行合并,则“中国文学史”最终可分为4个时段,大致对应先秦、秦汉至刘宋、萧齐至15世纪明代中叶、清代。
观察并分析《文学大纲》有关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实践,可得如下结论:第一,本书以英国学者的同名著作为蓝本与基础,在操作层面,尊重原作的历史框架,“中国文学史”按时间顺序“嵌入式”地补充其中。比如,第七、八章先秦文学置于第二章《荷马》序列之末;第十、十一章秦汉至刘宋置于仅次于第九章《希腊与罗马》的位置;第十三、十四章仅次于第十二章《中世纪的欧洲文学》之下;18世纪、19世纪的情况更是如此。第二,专设四章(占总篇幅的1/3)来特别论述中国小说戏曲史,既有西方文学重视小说戏曲影响的因素、五四时代文学趣味的因素,也与郑振铎本人强烈的个人学术志向与兴趣有关。将小说戏曲实质上提升至中国文学最重要文体的地位,学术史上这一文学史观的重要创新,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的新文学阵营内部已成一时共识,然而,郑振铎本人对此问题的定见、坚持与热情,也不可漠视。第三,共计12章的章目名称当中,第十三、十四章“中世纪的中国”是个新概念,比较显目。一方面,这主要是对于欧洲历史流行的“中世纪”概念的比附,西罗马灭亡于公元476年,“中世纪的中国”则始于南齐建元元年(479);西方“中世纪”大致在1500年前后结束,“中世纪中国”遂以明朝中期为枢纽。另一方面,质诸中国文学史实际,律诗建制基础的新体诗恰恰导源于南齐的“永明体”,明中叶以后,小说戏曲的文学成就趋向高峰,所以,“中世纪的中国”起讫,确实也能在文学史上找到文学、文体方面的依据。郑振铎对于“中世纪的中国”文学成就的自豪感亦令人瞩目。中国文学史上的“中世纪”概念,重在时段称述,不含有西方“中世纪”历史概念固有的价值褒贬。第四,《文学大纲》首章《世界的古籍》对于中国文字的发明、书写以至印刷的历史均做了扼要介绍。末章第四十六章《新世纪的文学》末节论述20世纪前四分之一时期的中国文学成就,以“新文化运动”作结。
《文学大纲》于1926年、1927年分册出版面世之际,对于中国文学的全过程已经有过一次系统论述的尝试,郑振铎文学研究的注意力便往撰述比较完备的中国文学史方面集中。1927年、1928年访欧,回国之前写作论文《敦煌的俗文学》,以后一系列论文都是为未来“中国文学史”作积累的。1930年4月22日夜所拟的《中国文学史草目》,标志着包括“古代”“中世”“近代”三大卷的中国文学史分期新框架已经完全成形,如果按规划全面实现,这将是一部三卷十篇十八册一百章的皇皇巨著[7]。
郑振铎:《文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27年初版本对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充满自信的“分期为自己独创”,该书《例言》简明介绍道:“本书就文学史上的自然的进展的趋势,分为古代、中世及近代的三期,中世文学开始于东晋,即佛教文学的开始大量输入的时期;近代文学开始于明代嘉靖时期,即开始于昆剧的产生及长篇小说的发展之时。每期之中,又各分为若干章,每章也都是就一个文学运动,一种文体,或一个文学流派的兴衰起落而论述着的。”[8]
全书三大卷,从传世本的篇幅来看,“古代”“中世”“近代”分别占12章、43章、9章,分配严重不均衡。然而,作者属意在“指示读者们以中国文学的整个发展的过程和整个的真实的面目”[9],这里一再申明的所谓“整个的”过程、“整个的”面目,才是郑振铎写作中国文学史、进行分期的创新性所在。作者自述,西晋之前的中国文学具有两个特点:一则,纯然为未受外国文学影响的本土的文学,印度思想(佛教)虽然在这个时代之末开始灌输进来,但是,文学影响的痕迹还看不出来。二则,纯然为诗与散文的时代,小说、戏曲等重要文体都未见萌芽。因此,将从有文字记载起至西晋末年止(建兴四年,即公元316年之前)的文学史,断为上卷“古代文学”[10]。
中卷“中世文学”:始于东晋、终于明正德(317—1521)1200百多年的文学史,郑振铎称为中国“中世纪文学”。比《文学大纲》确定的“中国中世纪”概念,上限前移162年,由南齐上移至东晋。史家满怀热情讴歌“中印结婚”的“中世纪”中国文学史。
下卷“近代文学”:始于明世宗嘉靖元年、终于五四运动之前(1522—1918)。共历时380余年。郑振铎认为,明嘉靖以来的“近代文学”是“活的文学”,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休戚有关、声气相通。综观前述上、中、下三卷之分配,“古代”“近代”两卷均为本土文学,中间“中世文学”则以中印文学交流(“中印结婚”)为基本背景。因而可以说,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之分期,将文学方面的本土、域外交流与影响,放置在“最高标准”“最大视野”之处,中印文学交流隐然成为文学史分期的“一级标题”的依据。
观察《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分期实践,因为郑振铎自五四时期开始,持续关注、介绍印度文学,而历史上佛教传入中国,本就参与缔造了中国文化史的巨大变迁,且佛教文学重视通俗与草根,又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诉求颇为契合,再加上郑振铎深受写作《英国文学史》《艺术哲学》的19世纪法国学者泰纳(Taine,1828—1893)民族、环境、时代理论的影响,重视民族间的文学交流,所以,纵览整个中国文学史的大格局、大演变,他抓住中印文学交流为主要视角,可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风云际会的清末民初时期,复古与新兴、本土与舶来、高雅与通俗,各体文学济济一堂、角逐争胜,也为郑氏文学史高度关切文体演变,以之为研究、论述文学史的基本单位,营造了浓重的历史氛围。《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分期框架自成一家之言,总之,“分期为自己独创”,言之不虚。
泰纳(Taine,1828—1893)郑振铎的另一部文学史名著《中国俗文学史》(1938年出版)没有采用综合分期的框架,而是分类进行论述。为论述方便与篇幅合适,《中国俗文学史》未纳入俗文学最重要的小说、戏曲[11],全书十四章,第一章《何谓“俗文学”》之下,共计13章,主要按时序论述从远古至清代的民歌、散曲与讲唱文学,大体注重初期发展,一旦为文人学士注意并引入高雅文学,则不复置论。
未成书的小说史、戏曲史方面的单篇论文,郑振铎的目光亦专注于“演化”“演进”的观念,与关切“文学史分期”属于类似的思想习惯。
郑振铎还曾有撰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计划,惜未成。但是,他论新文学历史的名文《〈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被评价为一篇极好的现代新文学小史[12]。对于这段短短的“伟大的十年间”的新文学历史,郑振铎的叙述颇有分期与演进的观念,发难期的“白话文运动”、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起来之后的“纯粹的新文学运动”[13]、新文学“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14]等,尝鼎一脔,令人印象深刻。
“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也是郑振铎发表于《文学研究》1958年第1期的论文题目。正式发表之前,在外访与讲学期间,他多次以此为题,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多个友好国家的学术机构与大学发表讲演。《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对于他自己《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古代”“中世”“近代”的文学史分期体系也做了检讨与反思,指出:“虽然已经注意到‘时代’的影响,却过分强调每一种文体的兴衰,不曾更好地把文学的发展和历史的发展结合起来。这乃是卷没于资产阶级的进化论的波涛里而不能自拔的。又论述印度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时,也有过分夸大之病。”[15]在自我批判的基础之上,经过厘定原则,郑振铎提出了新的中国文学史“五期”说,如果剔除“近代期”(鸦片战争至1949年,相当于现在的近现代文学)、“现代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于现在的当代文学),则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传统文学史分为:
上古期,邃古到春秋(公元前2000年左右—前402年),奴隶社会文学的时期 古代期,战国到隋(公元前403年—617年),封建社会文学前期 中世期,唐帝国到鸦片战争(618年—1840年),封建社会文学后期[16]
这个新的文学史分期的方案,主要表现为接受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于中国社会形态的基本论断(即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前提,对于文学特殊性方面的兼顾,在章目上表现不明显。当然,这一唯物史观社会史背景上展开的文学史分期框架,郑振铎本人没有来得及在文学史写作之中实践,就因公殉难了。
综本节所述,郑振铎文学史写作当中的分期问题,以《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古代”“中世”“近代”三卷分期为典型形态,这是他的独创。这一创新之举,“摆脱政治史、社会史乃至经济史的套路,另辟蹊径地做出这样一个分期,应当说也有利于中国文学史的独立叙事系统的形成,有利于更加真实贴切地讲述中国文学演变的故事。在这个故事当中,文学的演变是由思想、题材、词语进而到文体的一整个连动变化的过程,变化起因于与文学关系最深的宗教、艺术和音乐等因素的介入,变化的结果则是旧文体的衰落和新文体的诞生”[17]。文学史分期应该“听命”于史家的文学史观,那么,郑振铎“独创的”文学史分期实践,究竟以什么样的文学史观为基础?
三 郑振铎的文学史观
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分期实践,源于他的文学史观。文学史观又是文学观的历史运用,而任何观念都有一个建构过程。下面构拟“郑振铎与他的世界”作为一个平台,综合历史语境、个人气质等因素,探讨他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
第一,文学史的“崛兴”与郑振铎的“预流”。五四时期,郑振铎与同时代许多人一样很快萌发了撰写“中国文学史”的念头。而1921年,胡适已经在教育部国语讲习所开讲“国语文学史”课程[18],讲义就是《白话文学史》初稿。大学开设“文学史”课程则构成另外一个助力因素[19]。返观中国传统史学,也有个兴朝必修史的原则,新兴王朝成功颠覆了旧王朝之后,要为旧王朝修撰断代史,通过修史建立新的政治正统。如果不拘于体裁形式,历史悠久的中国史书中也有“文学史”记载(见《文苑传》《艺文志》等),主要是文集状况、名作纪事、作家生平事迹的综合。文学观念、文学史观方面的自觉意识比较淡薄。“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史热望,与传统史学关系并不直接,而受西方启发较大。现代西方的“文学史”著作体裁,是在日益浓厚的历史“发展”与“进步”观念条件之下脱颖而出的[20]。所以,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涌现出的中国文学史热潮,应视为“新文化运动”建设的重要方面军。目的指向通过新的叙述方式建构新的历史秩序和价值认同,从而进一步论证“新文化运动”的合法性。
从“新文化运动”阵营的文学史序列看,1920年教育部颁令,国文教材改文言为白话国语,白话文运动告一段落。1921年,胡适开始讲“国语文学史”,1928年《白话文学史》正式出版,仍是开风气之先。1932年开始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以独具的特色、宏大的篇幅,在当时“文学史”热潮中独树一帜、脱颖而出。
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卷,新月书店1928年版第二,“活的文学”与当代文学本位。文学分为“死”“活”,是五四时期的流行话头,“活的文学”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诉求。所谓“活”,与口头语言联系则为白话,与社会民众联系则为通俗,与当下现实联系则为写实,分别以文言、高雅、雕琢为敌对方面。《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分期的主要架构之一明嘉靖“近代”说[21],体现了“活的文学”的观念:“近代文学的意义,便是指活的文学……近代文学的时代虽因新文学运动的出现而成为过去,但其中有一部分的文体,还不曾消灭了去。他们有的还活泼泼的在现代社会里发生着各种的影响,有的虽成了残蝉的尾声,却仍然有人在苦心孤诣的维护着。……真实的在现社会里还活动着的便是这近代文学。她们的呼声,我们现在还能听见,她们的歌唱,我们现在还能欣赏得到;她们的描写的社会生活,到现在还活泼泼的如在。”[22]
在郑氏文学史“近代文学”框架之中,昆腔的流行及其带动的地方戏热潮、长篇小说的发达、各类说唱文学的产生、民歌的流行,反映了时代精神,是文学殿堂的瑰宝;而当年志在复古的文坛盟主“后七子”等历代文学正宗,地位则被边缘化。某种意义上,嘉靖以降的晚明异端革新思潮,也构成激发新文学运动的一股“潜流”。这一处置方式,与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著名论断桴鼓相应。郑振铎写作文学史,以当代“活的文学”为权衡,因为五四时代的当代文学是“革命性”而非“继承性”的文学,所以,郑氏文学史有个“更换主人公”的大动作,“将被颠倒的再颠倒过来”。
第三,瞩目民间文学。重视民间文学,也是当时的时代潮流,民间故事、民谣等的搜集、整理,蔚为一时大观。郑振铎对民间文学(或“俗文学”)的热情,以名著《中国俗文学史》之存在,不遑多论。《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绪论”以外来文化、民间文学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两大原动力:“有一个重要的原动力,催促我们的文学向前发展不止的,那便是民间文学的发展……一方面,他们在空间方面渐渐的扩大了,常由地方性的而变为普遍性的;一方面他们在质的方面,又在精深的向前进步,由‘草野’的而渐渐的成为文人学士的。”在中国本土民族文学的范围内部,民间文学、文人文学之间的张力与互动,构成郑氏文学史叙事的重要维度。
第四,文学的“世界主义者”。郑振铎写作“‘中国’文学史”,但他不是一位文学的民族主义者,而是一位彻底的“世界文学主义者”。他的文学史写作的重要起点是“世界文学史”性质的《文学大纲》。文学没有国界,人类心灵相通。“人类的最崇高的精神与情绪的表现,原是无古今中外的隔膜的。其外型虽时时不同,其内在的情思却是永久的不朽的在感动着一切时代与一切地域与一切民族的人类的。”[23]从共时性角度看,郑振铎“世界主义”的视野,有利于他的文学史在中国传统的诗歌、散文两大文体之外,更将戏曲、小说与变文等长期不被重视的叙事、通俗类作品包罗进来。
第五,中印文化交流、比较文学。《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分期实践,以东晋“中世文学”说为关键,之前“古代”、之后“近代”,截断众流,一分为三。“古代”“近代”均以本土发展为主,“中世”是个关键的、决定性的例外。郑振铎认为,世界、人类文学的本质相同,然而,具有时代、环境、民族等外在因素的限制,民族为活跃的主体。所以,民族间文化交流,对于文学发展的推动至关重要。
郑振铎论中国文学发展的原动力,推崇外来文学(特别是印度文学)的巨大影响,分布在文体、思想、题材等各方面,他称之为“中国与印度文学结婚”。中国“中世文学”丰硕成果、辉煌成就之取得,深受印度文学的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许多中国学者研究佛教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巨大影响[24],关心中印文化交流,郑振铎是其中重要一员。
第六,以“美与情绪”为标准、以“时代”为单元、以“进化”为真理。“文学是艺术的一种,不美,当然不是文学;文学是产生于人类情绪之中的,无情绪当然更不是文学。”[25]以“美与情绪”作为进入中国文学史的标准。历史观方面,郑振铎明确指出英雄豪杰的历史观念已经陈旧,新的文学史不能仅写成文学巨人的合传,更要瞩目时代与民族精神,综合展示激动人心的民族精神历程。
总之,尽管《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最终并未完成,“近代卷”后半部分有十多章未写出,然而,从全书体现的文学观、文学史观的角度分析,作为叙述者的史家,立足点实在自己的时代,观察中国文学史的眼光从后往前投射。这部特色鲜明的“新文学运动”版文学史,以通俗的、叙事的戏曲小说高度发达的“近代”为重心;叙述“中世”文学的巨大成就,也重视表彰各种新文体的产生,指向“近代”;遥远的“古代”文学,再也不可能是辉煌神圣的“文学渊薮”。以“价值重估”为导向,全史涌动着“活的文学”的气息,佞古、拟古、复古等各种“以古为尚”的思想观念被破除殆尽。文学史呈现出一派以现代新文学为目标的“进化”景象。
四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引起的
风波与“综合的中国文学史”的
体制困境
“福兮,祸兮?”《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这本代表郑振铎文学史研究风格与成就的著作,甫一问世,却辗转给作者带来无妄之灾,导致他丢掉在燕京大学的教授职务。1933年至1935年的这一风波的事主,表面看首要者是当时燕京大学国文研究所学生吴世昌,而据鲁迅书信、顾颉刚日记等材料证明,实际上应与顾颉刚、胡适等人有关。顾颉刚《我怎样厌倦了教育界》一文,自述他与事件的关系:
“郑振铎解聘事件”,本来是吴雷川校长的意思,因为他作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错误太多,给国文系学生吴世昌揭发出来,登在报上,妨了校誉,所以要辞掉他。又因国文系教授马季明上课敷衍,闻宥与郑振铎积不相能,形势汹汹,工作停顿,要把三个人同时去掉,组织一个“国文系审议委员会”处理此事。我既非文学院长,又非国文系教授,关我甚事,乃偏偏要套在我的头上,使人疑心我排挤振铎。[26]
由此可知事件的环节:第一环节,《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书中错误为燕京大学学生吴世昌揭发并登到报上,妨碍到大学声誉;第二环节,校长决定解聘郑振铎,组织“国文系审议委员会”落实,顾颉刚参与此事;第三环节,郑振铎被令离开燕京大学,最终回到上海。
1933年夏燕京大学郑振铎宅前(左起,小朋友略):俞平伯、郭绍虞、浦江清、顾颉刚、赵万里、朱自清、朱自清夫人陈竹隐、郑振铎夫人高君箴、顾颉刚夫人殷履案、郑振铎研究这一风波,非本文主旨,学界已有一定成果[27],近出论文则将冲突的主要根源定位为郑振铎坚持的五四文化立场与燕京大学实行的学院派严格规范之间的深层次矛盾[28]。诚然,学术规范方面的矛盾是事件的根源之一,然而,初出茅庐的20余岁年轻学生的两篇书评,果真有力量赶走文坛劲将的大学教授吗?而且,焦点竟然是教授新出版的代表作?这些值得辩证与思考。
再行审视事件第一环节:《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年12月出版,吴世昌12月4日即撰《评郑振铎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二册》,次年3月在《新月》杂志四卷六期发表,从变文起源、词的起源、唐诗评论、论述文字等方面对“郑著”进行严厉批评,称“为中学生作参考书翻一下”的资格都不够[29]。6月,《新月》四卷七期有《郑振铎先生来函》作答。随着《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各册陆续出版,吴世昌又有《评郑振铎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一、三、四各册》发表于1934年3月《图书评论》第2卷第7期。附录吴氏《论变文发生时代与词的起源诸问题》同时发表,也是与郑振铎商榷的。两篇书评以批评性、否定性意见为主,用语直率,偶有轻蔑与冷嘲热讽。但是,具体意见仍能言之成理,这应该也是常规书评得以发表的底线[30]。可以说,尽管书评表达方式直率、偶尔有过激之处,但本身属于正常学术批评层次;关于文学史的基本学术观点,吴世昌先生晚年仍持类似立场[31]。
青年时期的吴世昌审视事件的第二环节:吴世昌书评固然锋芒毕露,但与燕京大学解聘郑振铎之间并无必然关联。对此,研究者引述较多的鲁迅致郑振铎的系列信件,间接保存了当事人郑振铎方面提供的原始资料,有助于澄清这一环节,具有很强的证据力。鲁迅与郑振铎当时往还合作,书信来往较多。据鲁迅的三封回信(分别回复郑振铎1934年7月2日、1935年1月4日夜、1935年1月6日来信),郑在燕京大学被“营植排挤”,“三根”(即顾颉刚)为主谋,“月光”(指《新月》派人士)与谋[32]。1935年1月11日,燕京大学通过“国文系审议委员会”决议,正式解聘郑振铎[33]。顾颉刚还在1935年1月20日的日记中洋洋自得[34]。
1930年,吴世昌以大学二年级生在《燕京学报》发表论文,得胡适著文揄扬而一举成名[35];1935年研究生毕业,所得工作即顾颉刚推荐[36]。数年间,门生与恩师往还非常密切[37]。书评之作,或非授意,然而,耳濡目染,其趣味、判断、立场,深受顾、胡之影响,可决其必[38]。而事实上,顾、胡对于郑振铎的文学史研究评价都很低[39]。所以,可以说北京学术界的某阵营,借《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之出版而掀起“逐郑”风潮,大约就是史实真相,所谓学术规范之矛盾,只是被利用的一种因素。文人学者们都非生活在“真空”中,他们的喜怒好恶,有时就这样构成对于学术发展的影响因素。
郑振铎比胡适年轻7岁,论辈分,两人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历史上略有先、后之别。胡适倡导白话文、新文学、整理国故等,郑振铎都有热烈响应。在现代文学史学史上,《白话文学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先后接力,郑著受到胡著的影响也很大[40]。胡适说:“这书名为‘白话文学史’,其实是中国文学史。”[41]客观上,二人以“接力”态势问世的文学史之间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胡适对于“半部《白话文学史》”的焦虑必然是存在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横空出世,在资料、插图、分期等方面都有特色,郑振铎富于文学气质的个性在文学史写作之中也得到较好发挥。
左起高梦旦、郑振铎、胡适、曹诚英与学术史核心观念相关的,更有“综合的中国文学史”的体制问题。现在大家习以为常的包罗小说、戏曲、诗歌、散文等为一体的“文学史”体制,是原生于西方文化环境的一种观念,以“格义”类比的方式借鉴过来。“中国文学史”应该写成刘师培《中古文学史》那种式样,以本土的文学理论观念为构架叙述本土经验。但是,这种本土类型的文学史体制,与引进西方式“文学史”观念的时代潮流之间很容易产生抵触。比如《中古文学史》以汉魏六朝文学观念为依据,对于六朝民歌、六朝小说视而不见,这显然不符合“五四”时代要求。作为一时文化前沿事业的“文学史”体制,以破除文学旧传统为目标,同时又“综合”地采用历代文学原料。既破且立,这一在全新的理论框架、价值标准之下“推倒”并“重建”的“综合的中国文学史”体制,堪称文学革命时代从事“价值重估”的学术典型。胡适、郑振铎奉献出的都是这一类型的“时代的成果”。胡适以白话的“活的文学”为文学史演进的主线索,郑振铎则综合欧洲文学史家泰纳(Taine,法国)、勃兰兑斯(G.Brandes,丹麦)等人的理论,以“情绪与美”为标准,通过文学演变史展示国家、民族的精神历程。此类文学史写作以“综合”为基本方式,打通各个时代,汇总各种文体,侧重挖掘文学史长期受压抑的低俗层面和“小传统”,开发历代文学对于新文学建设、发展的资源价值,并建构历史认同体制,其功劳不可谓不大。然而,若以客观的标准衡量,可能会引起一些疑问。“综合的中国文学史”如何可能?文学史写作之中,科学与价值观之间的张力该怎样处置?
钱锺书指出:“在传统的批评上,我们没有‘文学’这个综合的概念,我们所有的只是‘诗’,‘文’,‘词’,‘曲’这许多零碎的门类。……‘诗’是‘诗’,‘文’是‘文’,分茅设蕝,各有各的规律和使命。”[42]文体、门类之间的独立性、区别性强过综合性,这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面相,也是中国文学史的“特殊国情”。另一方面,研究者在文学各门类、历代文学大小传统之间穿梭综合,也容易陷入“《六经》注我”式的过度阐释,妨碍对于文学史的“同情之了解”。写作“综合的中国文学史”,挑战性极大。我们也看到,现代的文学史经典多是《宋元戏曲考》《中国小说史略》之类对文类做独立研究的著作。西方学者系统介绍中国文学的著作,有的采用各自“类编”、分别叙述的方式,避免了多端、无端揉和出“‘一个’文学”[43]。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论述各体俗文学,主要采用“类编”式,也令人眼睛一亮。
回头再审视引发《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风波的书评,吴世昌对文学史之类书,总体持消极态度,但是,他也明确表示:
我并不主张不要文学史,自然也并不以为凡是文学史都要不得。文学史是可以写的,是应当写的,假使(一)作者是这方面极精湛的学者,(二)作者是自有其文学批评之新见解或新理论,(三)作者在某一种文学作品的演变上或和社会别方面的关系上有新发现,(四)作者自己是一位受人爱好的文学作者,他的文学史本身即可成为一篇优美的文学。[44]
按照上述四个标准,符合(一)者,他举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符合(二)(三)者,举胡适《白话文学史》。而在接着转入的对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正式批评之始,他策略性地巧妙避开了以标准(二)(三)来衡量郑著:
郑先生的《文学史》,我最初在《北平晨报·学园》内读到他的序文,据他自己说是并不希望能成“一家言”的。……郑先生这么一说,我们就不好意思拿第二个条件——作者自有其文学批评的新见解或新理论——来绳准了。[45]
根据本文上述“综合的中国文学史”的体制特征,大文学史写到“精湛”“经典”的地步比较困难,所以,个人撰中国文学史,争胜途径只能在史观、理论批评的创新,与鉴赏细腻、文笔优长等方面。避开(二)(三)(四)等宏观标准,以郑著史料、史学等资料细节层面的不足为主来要求其“精湛”,对于它的评价就不免有偏颇。事实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与胡适《白话文学史》的类型相似,正是以“成一家之言”自立于学术史的,分期问题反映的就是一个史观创新,在理论批评方面、文学与社会联系方面、作者的文学感受力方面,郑著文学史也都有特色。
综本文所述,“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涉及综合的中国文学史的史观、论述结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分期实践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历史诉求关系密切,具有学术史里程碑的意义。郑振铎的文学史研究,体现了他不可取代的“少年”精神、“自由”热情,凝结了他“如泉的思想”与“活泼进取”的劳绩,足以激发一代代后来者,值得永远记取与怀念!
注释
∨
[1]关于郑振铎文学史的研究,可参见范宁:《郑振铎对中国文学研究的杰出贡献》,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第396—42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戴燕执笔:《〈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所显示的方向》,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中国文学史学史》第二卷,第59—70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董乃斌:《论郑振铎的文学史研究之路》,《文学遗产》2008年第4期;陈福康:《郑振铎论(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然而,以“文学史分期”为切点并与史家文学史观进行联系方面,尚有充实之余地。另外,置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于不顾,径直以“类西方”的大“文学”观念为架构,汇总各文体、串通各时代,写作“综合的中国文学史”,其实是具有先天性的体制困境的。本文因《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风波,亦讨论到此问题。
[2][15][16]郑振铎:《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第36—37页,第19页,第25—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3]参见董乃斌:《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成就与贡献》,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第312—31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参见陈福康:《重印〈文学大纲〉序》,郑振铎编:《文学大纲》(上),第4—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郑振铎全集》第3卷,第573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6][12]陈福康编著:《郑振铎年谱》,第183—184页,第239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7]陈福康:《郑振铎传》,第230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按:《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年12月开始出版,1957年重印时,补写了4章,传世本共64章,未完成全书计划。特别是“近代卷”远未完成。
[8][9][10][22]郑振铎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例言”第2页,“自序”第1页,第11页,第930—931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
[11]按:郑振铎本有另撰《中国戏曲史》《中国小说史》的打算。惜未成。
[13][14]郑振铎:《导言》,郑振铎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争集》,第8、17、19页,第1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17][19][24]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中国文学史学史》第2卷,第69页,第75—94页,第69页。
[18][41]胡适:《白话文学史》,“自序”第1页,“自序”第6页,岳麓书社2010年版。
[20]参见[美]雷纳·韦勒克著:《近代文学批评史》第1卷,杨岂深、杨自伍译,第35—3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21]按明嘉靖元年至五四之前(1522年—1918年)为中国文学史的“近代文学”阶段。
[23][25]《郑振铎全集》第8卷,第6页,第8页。
[26]顾颉刚:《顾颉刚自传》,第10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7]陈福康的系列著作,这方面资料引用比较全面。不赘。
[28]参见季剑青:《1935年郑振铎离开燕京大学史实考述》,《文艺争鸣》2015年第1期。
[29][31][44][45]吴世昌著、吴令华编:《吴世昌全集》第二卷,第52页,第91页,第46页,第4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30]参见董乃斌:《论郑振铎的文学史研究之路》,《文学遗产》2008年第4期。
[32]以上三封信分别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2卷,第477页;第13卷,第11页;第13卷,第13页。
[33][34]《顾颉刚日记》第3卷,第296页,第299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35][36]吴世昌著、吴令华编:《吴世昌全集》第1卷,第11—12页,第1页。
[37]《胡适日记》1933年12月30日记载,他应邀赴燕京大学国文系同学年终聚餐,吴世昌雇汽车来迎接,关系可见一斑。见《胡适全集》第32卷,第24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38]吴世昌第一篇书评作于1932年12月4日,刊于次年3月《新月》杂志(《吴世昌全集》第2卷,第55页)。《顾颉刚日记》1932年12月16日记载,当天,吴世昌与《新月》编者叶公超到访,一起用餐并长谈至九点。对郑氏文学史的评论,不排除就是当晚的一个话题。
[39]参见《顾颉刚日记》第3卷,第202页;《胡适全集》第32卷,第451页。
[40]徐雁平:《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中心》,第198—214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42]《钱锺书散文》,第81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43]例如James R. Hightower, Topics in Chi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