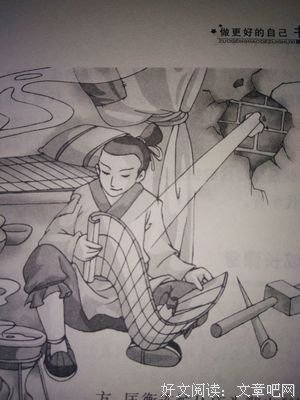
《黄宗羲全集(共12册)》是一本由黄宗羲 著 / 沈善洪编校 / 吴光编校著作,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简裝本图书,本书定价:700.0,页数:1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黄宗羲全集(共12册)》精选点评:
●补记
●额。
●第十、十一冊南雷詩文集閱畢
●只读了第一卷
●封面设计蠢炸&丑炸
●通读完宋元,但是明儒一直读不下去。与其买学案单行本,不如买这个。
●第一集读过
●我的毕业论文用到的书 看了些 感觉很好 语言有力
●第10、11、12册
●2017年,一定到梨洲老先生的墓前鞠上一躬。
《黄宗羲全集(共12册)》读后感(一):《明夷待访录》读书笔记
《明夷待访录》读书笔记
经世济民之书何在?读罢此书,良久叹息,振聋发聩,此书之谓也。
曰君臣,曰法律,曰用人,曰经济,此书之内容,可堪经世济民四字。
“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民者,本也,官吏者,末也,民之幸福,安乐,天下之系也,官吏者,服务人民之公仆也,未有公仆高高在上,而人民如草芥于下也,今日之官员,皆须有此为人民服务之精神,方有长治久安之长远也。书中之言语,可深深衍之,则近道也。
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原法》
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
大学祭酒,推择当世大儒,其重于宰相等,或宰相退处为之。——《学校》
眀夷者,“夷之初旦,明而未融。”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先生能于乱世出此书,以留后世经世济民之士子问道就学,治国安邦,真用心良苦,读此书,甚振奋,治国平天下,不读此类经世济民之鸿篇巨制,不可得也,他日历块过都,驰骋天下,此书即诸君之利器也。
此不得不读之经世之书也。
小舟
2014年12月2日星期二
《黄宗羲全集(共12册)》读后感(二):《子刘子行状》读后感
《子刘子行状》读后感
舍情而言义,非义也。
近日读黄宗羲全集,刘宗周先生行状,感慨颇多。
先生者,刘子宗周也,先生早年从外祖受学,后举进士入仕,前后历晚明诸帝,崇祯年间天下大乱,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内忧外患,先生告思陵以归本德化,不宜急急以兵食为先务。竭生灵之膏血,以奉军旅之费,如此则驱天下之民,而尽归于寇。然思陵竟以迂阔答之。先生罢而召,召而罢,终不能用,而天下事以去矣。
吾读其文,未尝不叹息,思陵,非昏君也,先生,亦忠臣也,然不能吁咈都俞,以成股肱之任,此明之哀也,先生殉国,何其悲壮惨烈,然有先生之行,之文,之死,吾辈方知有忠义,名节之可贵,此古大臣之风也。屈原,陆秀夫之类也。
读其行状,依稀置身其时,先生音容笑貌,如在眼前,先生自家庭以至宗族,朋友,乡党,施之无不各当其节,晚生叹服,亦当以先生之忠义,以天下为己任,为吾之榜样,为国为民,尽忠尽心。
史之先后,当一脉贯之,今日之事,亦是后世之史,可不慎哉,可不畏哉,可不慎哉?
小舟
2015年4月19日星期日
《黄宗羲全集(共12册)》读后感(三):黄宗羲全集(十二卷本) 目录一览
第一册 哲学·经学·政治学
黄宗羲全集序 沈善洪撰
明夷待访录 一卷
孟子师说 七卷
深衣考 一卷
葬制或问 一卷
梨洲末命 一篇
破邪论 一卷
子刘子行状 二卷
子刘子学言 二卷
汰存录 一卷
思旧录 一卷
黄氏家录 一卷
明夷待访录未刊文 二篇
附录 黄宗羲遗著考(一) 吴光撰
第二册 历史学·地理学
弘光宝录钞 四卷
行朝录 十二卷
海外恸哭记 一卷
西臺恸哭记注 一卷
冬青树引记 一卷
金石要例 附论文管见 一卷
历代甲子考 一卷
四明山志 九卷
匡庙游录 一卷
今水经 一卷
附录 黄宗羲遗著考(二) 吴光撰
第三册 宋元学案(一)
第四册 宋元学案(二)
第五册 宋元学案(三)
第六册 宋元学案(四)
第七册 明儒学案(上)
第八册 明儒学案(下)
第九册 易学·历学
第十册 南雷诗文集(上)
第十一册 南雷诗文集(下)
第十二册 附录 人名索引
《黄宗羲全集(共12册)》读后感(四):有趣的黄宗羲
黄宗羲年少时为其父黄尊素申诉、报仇,孝子之名的背后也同时继承了其父于东林党的一切特质。 崇祯朝加入复社,成为其中的活跃分子;弘光朝与其他复社成员上蹿下跳;鲁监国朝为对抗阉党余煌,附和赴日乞师之师,黄宗羲的前半生就这样在党争和抗清之中度过。 康熙朝之初,随着天下几近抵定,其人也转而隐居,做起了遗民。虽屡次拒绝出仕,但是在修史上却还是派出了他的儿子黄百家和弟子万斯同。 等到三藩之乱被满清镇压,随着庄氏明史案、鹿樵纪闻案、黄培道诗案、沈天甫案、朱方旦案、戴名世案等文字狱,以及扩大科举规模、尊崇程朱理学、宣扬满汉一体等拉拢汉族士大夫的政策,在这一系列软硬并施、拉打并用之后,转而为清廷高唱赞歌。 不比顾炎武、吕留良那等思想家,黄宗羲晚年吹捧满清,但其思想和著作中却强烈反对君主专制。如此言行不一所表现出的矛盾,尤其是透过其一生的经历,可以很鲜明看出其人作为明末士绅阶级的代表人物,东南士绅、手工业主、矿主及海商利益的维护者,东林党的身份和自我定位贯穿其一生。 而他的所作所为,甚至在著作中体现出的那些民主思想,其实际上也不过是为东南士绅和东林党张目而已。 所以,当满清开始邀请其效力,他就让儿子和弟子出面,在背后遥控,借修史的机会洗白东林党、污蔑政敌;所以,当满清开始软硬皆施的拉拢汉族士大夫,他就转而投向满清,全然不顾晚节不保;所以,
透过历史,能够很清楚的看到明末儒家士大夫阶级欺软怕硬的本性——在面对明王朝时,他们张牙舞爪的豁夺中枢和地方的权利,以最大化利益;但是当满洲贵族向他们举起屠刀之时,却也只能不情不愿的跪舔这些不讲道理的奴隶主。
《黄宗羲全集(共12册)》读后感(五):【读品•考辨】杜建华:乾初与梨洲
“呜呼!确之登师门最后,得事吾师之日浅,年已逾于强仕,学未及于童蒙,日用之间,举步滋疗,圣贤之道,窅乎未闻。方期与渊结庐云门,若邪之中,朝夕函丈,订数年游,究千秋之业,而时移事远,天崩地坼,挚友见背,明师云殂,宇宙茫茫,向谁吐语!”
乾初早年纵意诗酒,才情特殊,自师事宗周方弃俗学而向道学,由此而及其人生之正途,至若江河如海,其意义甚大。上文乃乾初祭师之作,语甚痛涕,其中至为重要者,乃其所云:“订数年游,穷千秋之业”。
乾初才高性殊,自闻世以来,所听者皆朱王末流疏空之言,所见者皆贪靡虚伪堕落之风。所谓“少读书卓莹,不喜理学家言”所言即此。蕺山授徒,首晓以“圣人可为”之旨,而乾初亦有《圣人可学而至论》信可为师承之作,可知乾初于蕺山之学甚是信笃。其与好友蔡养吾信中云:“若但择花晨月夕,乘兴往游,饮酒赋诗,自夸盛概而已,此则吾先师,先友之罪人,而岂不肖弟之所敢齿哉?”亦明归道之志。“千秋大业真吾事,临别叮咛不敢忘。”“江水汩汩,云山屼屼;仲秋而出,学何以不惑!江水回,云山崔巍:秋尽而归,学何以不颓!”则更明其拜师以后后矢志进学之宏愿。
然则,何为“千秋大业”?梨洲言曰:“先师之学在慎独,……先儒曰:‘意者心之所发。’师以为心之所存……自身之主宰而言谓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谓之意。……先儒曰,‘未发为性,已发为情……’师以为指情言性,非因情见性也;即心言性,非离心言善也。……又言性学不明,只为将此理另作一物者,……夫盈天地间,止有气质之性,更无义理之性,谓有义理之性不落于气质者,臧三耳之说也。”梨洲此说欲以呈宗周之学说,明先师思想之指归,恰可见乾初所云“千秋大业”之所在。即救心学于末流,正学风于颓靡,期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梨洲出于东林,自父蒙难,始从学宗周,当为蕺山门下最负盛名亦最有成就之高徒。然其于“千秋大业”,所发者似不甚多,心学之理论亦未有较先师明者,此盖因蕺山之学业已精圆,无甚可得而至更精纯。然梨洲日后所成蔚然为大,虽于义理与史学论而言,当以后者为大,然其理气之源当属刘学,若无此源即无史学之用。此即梨洲得于蕺山至紧要而极易疏忽之处。
梨洲言:
“先师蕺山曰‘予一生读书,不无种种疑团,至此终不释然。不觉信手拈出,大抵于先儒注疏,无不一一抵牾者,诚自知获戾斯文,亦始存此疑团,以俟后之君子。倘千载而下有谅余心者乎?不肖义蒙先师收之孤苦之中而未之有得,环视刘门,知其学者亦绝少。径以牵挽于口耳积羽,浅积所锢,血心充塞,大抵然矣。近读陈乾初所著,於先师之学十得之四五,恨交臂而失之也。’”(梨洲撰《陈乾初先生墓志铭》凡四稿,本文取其二稿)。
此言所及蕺山门人之中,尚乾初一人得宗周所传,可见乾初昔日负志为学之愿已付。然,其于当年所云“千秋大业”,得之者谓有多少?有史记云:“(确)问学宗周,乃刮磨旧习。宗周卒,确得其遗书尽读之,憬然而喻。著性解,禅障,大学辩。”其言性则曰:“人性无不善,于扩充尽才后见之”,反对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可分,以气、情、才即为性,不以“气质之性”为可信。以此观之,则其说确应尽承蕺山之要义。然乾初性素奋疾,于师承之发挥中,亦有激进之修正,甚而背离,无怪乎梨洲言其:“理学之别传”。由此可见梨洲、乾初师承于宗周者有二,谓哲学思想(心学)之基础,谓“千秋大业”之志。哲学思想之基础,恰如人之首脑,谓有指导之功,而蕺山心学,实已由救蔽而起异变,始脱自千年来印度文明虚空之影响。梨洲、乾初承此心学,加以一番开拓,日后所成,竟成另一天地。“千秋大业”之志素为儒家出世之内在要求,梨洲、乾初于师承处顿领此志愿,继而勉力一生而为之,此即二人融佛入儒建立清代实学之动力所在。
梨洲之哲学思想虽未成系统而大体可识。先儒论道,于程朱必言“格物致知”;于陆王必言“心外无物”,盖前者识“理本气末”,后者见“心为一元”,一外物一本心,而过分求之皆流于无束无傍之蔽,故蕺山有“慎独”“诚意”之说。而梨洲实有开辟之心,欲于朱王上求一完整之哲学思想,以救学术之弊,以融合儒佛之“千秋大业”。
“盈天地皆气也”,梨洲一反程朱理一元论,而倡“气本论”。道“夫太虚,纲緼相感,止有一气,无所谓天气也,无所谓地气也”又道:“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如此,则将气置于本体之上,归于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思想,避免了佛学的疏空。梨洲又在气理关系上发于师门而胜于师门,宗周持气为本,而未能明气理之辩,梨洲则曰:
抑知理气之名,由人而造,自其浮沉升降而言,则谓之气,自其浮沉升降不失其则而言,则谓之理。盖一物而两名,非两物而一体也。
又曰:
盖离气无所谓理,离心无所谓性,佛者之言,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寞,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此是他真脏实犯,奈何儒者亦曰,“理生气”,所谓毫厘之辩,竟亦安在?
以上两言皆欲明“气为事物之本原,理为事物之根本”之理,而不同于“世儒分理气为二”之辩。梨洲以为气理“盖一物而两名,非两物而一体也”,故其论气理之辨则为“理气是一”,“理气无先后”,即以气为本体而理气相依,无有轻重。如此,则既非本体二无论,又非朱程“理本论”与“理本气末”思想,则融儒佛思想于一,于当时观之,确有莫大之进步。
又,梨洲师承为陆王一系,心性之见实为重要,其言心性则曰:“盈天气皆心也”,《明儒学案序》中表达颇为完整:
盈天地皆心也,变化不测,不能不万殊。心无本体,工夫所至,既是本体。故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非穷万物之殊也。是以古之君子,宁凿五丁之间道,不假邯郸之野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使美厥灵根者,化为焦芽绝港。夫先儒之语录,人人不同,只是印我之心体,变动不居。若执定成局,终是受用不得,此无他,修德而后可讲学,今讲学也不修德,又何怪其举一而废百乎?
可见其于心性之上所持应为“心一元论”,而上文所述,梨洲以为“盈天地皆气也”,则不上下不一矛盾相克乎?其实不然,梨洲以为“心以思为体,思以知为体,知以虚灵为体。”承认心以虚灵为体。而蕺山以为“心无体,以意为体,意无体,以知为体,知无体,以物为体。”则以物为心之体,已于心、气之间有一连结。梨洲更以“心无本体,工夫所至,既其本体”为论,颇能发挥师说而更具实践之意义。其言心、气则曰:“夫在天为气者,在人为心,在天为理者,在人为性。理气如是,则心性亦如是,决无异也。”又其于《孟子师说》卷二中论此甚详:
天地间只有一气充周,生人生物,人禀是气以生,心即气之灵处,所谓知气在上也。心体流行,其流行而有条理者,即性也。犹四时之气,和则为春,和盛而温为夏,温衰而凉则秋,凉盛而寒则为冬,寒衰则重为春,万古如是,若有界限于间,流行而不失其序,是即理也,理不可见,见之于气,性不可见,见之于心,心即气也。
此即打通心、气,整合朱、王之语。故其语“盈天地皆心也”实未损其“盈天地皆气也”之本体论唯物性于一分,而其通心、气,合朱、王之探索实有救先儒于禅障,启后世于彷徨之功。
梨洲以心、气相通而理气是一,故而心性亦如一。其曰:“盈天地皆气也”“盈天地皆心也”。“盈天地皆道(理)也”,而其所通之处则曰:“功夫”。即探索真理之过程与方式,如此则有其重实践之举,则有其经世致用思想之产生,则有其“千秋大业”之立,则可尽去佛之疏空于儒之实用。又“盈天地皆理也”,此理为事物之规律,梨洲强调其客观性,由此,前则削先人儒佛合流后之神秘泛神色彩,后则启学人科学之精神。梨洲哲学自有其不严密之处,而其立心之巨,探索之艰,承前启后之功,不可不记。
至于乾初,则事事与人相辩,未曾立系统于思想,其言论多因事而立,为一事之便而前后言他,或有矛盾,不曾一贯。然较梨洲之复杂求索,乾初思想虽为零碎,大体之方向尚可明视,谓,其笃于蕺山异变之心学而有重大修正。
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刘述先先生曾作一文《理学殿军——黄宗羲》,其曰:“……不象陈确、戴震以欲为首出而开了另一思想的典范”,论其“以欲为首出”而归其东原,称其革命。乾初之思想是为激进,《大学》之辩惊骇同门,而有梨洲“理学别传”之言。融佛入儒之语论,是为偏激,然其反禅障而正孔孟之举诚为方法而已,而指归其意则不得不谓去佛之污而建立实学。乾初《无欲作圣辩》、《与刘伯绳书》《近言集》中言人欲即天理,亦可视其正人视听,救流蔽之激进之手段,且此种言论于乾初文集中实为少数,智者尚有一失,况夫乾初救禅障于心切之人哉?故如此之言,尽可笑而略之,所谓小失不干大节,乾初思想尚为蕺山心学之继承,此言无误。
虽为心学一系,乾初之学于陆王宗周亦无全盘接受。陆王以心为本体,而乾初似无心之本体超越性,其言:
孟子即言性体,必指切实可据者,而宋儒辄求之恍惚无何有之乡。如何云平旦之气,行道乞人之心,与夫孩少赤子之心,因端之心,是皆切实可据者,即欲求体,体莫著于斯矣。
无先天超越之本心,故乾初论学必独重“工夫”之实践,此与梨洲相同,应为二人共感时事,而变而通之道,而其收融合儒佛之效。其曰“孟子言性必言功夫,而宋儒必欲先求本体,不知非工夫则本体何由见?”又曰:“工夫即本体也,无工夫亦无本体矣。”至而有“未穷之理不可以为理,未尽之性不可以为性。《中庸》言至诚能尽性,可见诚有未至,即性有未尽。以未尽之性为性,是自诬也。”之论。而梨洲以气为本体,以心气相通而有实践,乾初因无先天本体之超越,又不以气为本体,故其论工夫不免有僭于本体之谦。然此一嫌疑较之去疏空于实用,融佛学于儒学,则尽可视而不见。
梨洲、乾初二人形而上思想比较,则梨洲之探索与所成甚巨,乾初亦有其特色。统而观之,二人俱承师说,而梨洲有一横向之整合,故而打通理气、心性,而开一豁大场面,而乾初则于心学上有一纵向修正,激烈之处蔚为大观。如此纵横之发展,豁然开阔之场面于大学术史角度观之,亦可谓二人尽识禅者虚空之蔽而勉力使之渐于朴实,此于明清时代诡异变幻之际,融佛入儒之时,更显其开辟之瑰丽。
上承师门,下开后世,而通纵横,此陈黄二人形而上思想之谓。而其于具体学术思想观点之上亦有精彩之激荡,亦于广阔层面上彰显二人融佛学于儒学的思想探索方式的碰撞。
老兄云:“人性无不善,于扩充尽才后见之,如五谷之性,不艺植,不耕耘,何以知其种之美?……夫性之为善,令下如是,到底如是,扩充尽才,而非有所增也,即不加扩充尽才,而非有所减也。……是老兄之言性善,反得半而失半矣。(梨洲《与陈乾初论学书》)
可见梨洲与乾初于人性之善恶,天理人欲之关系,宋儒所发是否禅障之上颇有异见。而此俱为中国学术争论之议点,二人以之论说,欲倡儒学融佛自成实学,当有非常之效。以人性之善恶观之,梨洲与乾初皆以为人性为善,而梨洲持人生而即善论,强调善为人之天性,而乾初持人成性全论,强调后天之扩充尽才。此问题自源头而论,则首始于人性考察之基准,先儒以孩提之童论人性,则尽生人性善恶诸说。宋儒为求一解,故而以为人之所生理气而已,人未生而理已在,人即生,其善恶则以其气禀论,气清则善,气浊则不善。使先前各家之争尽归于此。而乾初之所论当属突破,其以五谷喻人,谓“不艺植,不耕耘,何以知种之美?”实惊人之问,启不知者于茫茫矣。至于梨洲据宋儒之说而以性善为人之本质,亦有其理。梨洲言:“是老兄之言性善,仅得半而失半矣。”此语即从分析逻辑而来,若以“扩充”为论,假使一人怙恶不悛,是其孟子之性善也哉?一语即中乾初扩充尽才而有性善之蔽。而二人于此论,各言其理,亦自有其据,梨洲之性善为超然之本质,乾初之性善为倡后天努力之需要,前者以明“善”的重要,意于使儒者皆有“善”性,行儒家之“千秋大业”,而此时之 “千秋大业”恰为儒学融佛自成实学之努力。此点初看颇为牵强,置之于当时而论,却有其用意所在。至于后者,一目即明其欲以后天之努力尽去佛学之疏空。
老兄云:周子无欲之教,不禅而禅,吾儒只言寡欲耳。人心本无所谓天理,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向无人欲,则亦无天理之可言矣。……然以知言气质言人心则可,以之言人欲则不可。……必从人欲恰好处求天理,则终身忧忧,不出世情,所见为天理者,恐是人欲之改头换面耳。(梨洲《与陈乾初论学书》)
“人欲好处即天理”此即乾初之论天理人欲之辨,也即刘述先教授论乾初以“欲为道出”之据。而梨洲则直论其为“人欲之改头换面”,天下滔滔,皆为利来,皆为利往,其以为“必从人欲恰好处求天理,则终身忧忧,不出世情。”提出一个深刻问题:“使‘人欲恰好处即天理’,则何为‘恰好处’,则如何行之?”。料来乾初无法回答此一问题,因由便自梨洲而来。乾初作天理人欲之辨,而其竟有人欲何为之问,显为偷梁换柱,转换概念之计。然其问或有所蔽,其于天理人俗之理解则无所害。梨洲博学大气,自知宋儒之“存天理灭人欲”之天理乃一人性化之标准,其初立之时当无所害,于此融佛入儒之努力亦有柔性的借鉴,故其信之而非乾初之论。而乾初则以“存天理灭人欲”之末流为准,不以其先为则所视者皆疏空之举,所作此论亦为应该。
大抵老兄不喜言未发,故于宋儒所言近于未发者,一切抹去,以为禅障,独于居敬存义,不黜为非。夫即离却未发,而为居敬存义,则所以本事者当在发用处矣,于本源全体不加涵养之功也。……而老兄之一切以事为立脚者,反是佛家作用见性之旨也。(梨洲《与陈乾初论学书》)
至于“宋儒本体说为禅”之论,乾初之意为反对宋儒空悬“本体”之性,只求体认,而无视践习,故有“以为禅障”之说。其于《瞽言》中论:
至相传要诀,以半日静坐,半日读书为为学之法,然乎否与?孟子之‘必有事’,《中庸》之‘须臾勿离’,读书耶?静坐耶?禅和子受施主供养,终日无一事,尝半日打坐参禅,半日诵经看语录,便了却一生,使吾儒效之,则不成样矣。
梨洲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仅论乾初只讲作用,不讲本体,反而为禅,为禅家“作用见性”之说。“老兄之一切以事为立脚者,反是佛家作用见性之旨也。”其实,乾初重“为善”而轻本体,意为实践儒家之论理规范,救正疏空之学风。乾初似有以今事论前事之理,而梨洲气度博大,于融合中善求禅者精华,其融合的方法以渐进宏大为主。二者相较,概而括之,则可谓乃其志向与责任同一而其探索有一纵一横,其为学有广博与精进所致。
梨洲于其独特哲学之上衍生出其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而乾初亦由不重心之本体,独重工夫而有崇实尚志的实学思想。二人于实践上融儒佛,开风气,其实学思想又有不同,若以“破”“立”相较(即前文所述之“去污存精”),则梨洲之“立”远胜於乾初,而乾初亦占有一“破”字之功。
乾初之学向称素位,其近于生活而严于自律,况其激于时事,多为惊世骇俗之言,多作彻底非常之举,而其学问眼界非广博于梨洲,故唯占一“破”字。乾初之“实”乃“真实”之实,非“事功”之实,固于前儒之流弊,尽可破之;乾初之“质”乃其素位之学,不重理论之思辨,特重日用之体道,身体力行是也。
曰其崇实,则有《大学》之辩,乾初不入时风,不喜理学家言,唯恶一假字,曰“学者通病,大率一‘假’字,其驰骛不知止者,三分是名,七分是利;近乎此者,则七分是名,三分是利。”进而乾初推其源流,批判之眼光直指《大学》一书,意于推翻各家之所据,作一彻底之举,以复孔孟之实。“窃欲还《学》、《庸》于戴《记》,删性理之支言,琢磨程朱,光复孔孟,出学人于重围之内,收良心于久锢之余。”《大学辩》书成,同门皆骇责其“不能发明师说,而又忽为新论,以驾出其上。”惟梨洲之言甚宽,谓其“决无依傍,决无瞻顾,可谓理学中之别传矣。”乾初于此,亦未尝动摇,其言曰“君子之行止,论是非不论利害;论是非之关于世教者孰大孰小,而不论利害之切于身计者谁浅谁深。”“虽一家非之不顾,一国非之不顾,天下非之不顾,千秋万岁共非之不顾也。”乾初去禅障求崇实之心可谓坚矣。
曰其尚志,则有《葬书》之力行。乾初痛陈丧葬之陋俗,立族葬之法,倡深埋之理,作《葬经》以广之,为《六字葬法》以明之。如此,则于礼和,于情通,而于民易行。乾初倡深埋之理,以防蚁虫之害,以免坍塌之虞。又民家境各有不同,故其作《富葬图》、《贫葬图》以供民用。而最可称力行者,当为韵文《葬经》,其言:
土必择高,葬必穴深。
必狭而实,而平,而坟。
必近而合,毋远而分。
必求诸己,毋求诸人。
勿停,勿迁,勿越,勿禁。
穴城蓄水,杂木横根。
戒之戒之,奚取虚文!
量力而举,而何伤于贫乎!
乾初此救疏空、正风俗之举,苦心孤诣,高风大德,其尚质之行,非弥坚可为。
有乾初之破,更有梨洲之立,其经世致用之学,专事开创,而以史学为著,另有政治、经济、教育、科技之类亦有相当建树。梨洲之实学,可视为其融佛入儒自成实学之最大努力,亦为最大成果,开辟之学,流传甚广,如此,则后学者皆以实学为学,不复有疏空之蔽。论其史学成就,则著书立作,创学案体,开浙东学术,真乃大家也。梨洲著述丰盈,书分三类。一为制度史,以《留书》、《明夷待访录》、《破邪论》为最。《留书》似为《明夷待访录》之前身,二者所论颇近,而后者独以其“天下之大害,君而已矣”闻名,盛名之下已掩《留书》之功。《破邪论》凡七篇仅一《骂先贤》便可知梨洲作此书之用意乃针砭封建之弊,倡其崇实尚志思想。三部著作皆以批判为旨,而力求发教训与其上,尽彰梨洲经世致用思想之华彩。
其二为学术史,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未尽,后全祖望终其书)二部著作,其中学案体制之立,最可见梨洲用力精深。学案凡三部,一序,二评传,三文摘。序用语精当,专以概括学派源流,为学宗旨;评传则与后世所作相当,而独重以精言述要旨;至于文摘,梨洲则以“分别宗旨,如灯取影”为旨尽取传主文集中言,此一事者,诚如精卫填海非精诚而不能至也。盖明儒浩浩,而先生竟能竟之,其用力之坚,当为吾辈效之。
其三为历史记录与文献整理之类,当与后世方志学相当,其著有《行朝录》、《弘光实录钞》、《思旧录》、《海外痛哭记》、《姚江逸诗》、《四明山志》等。
梨洲授徒,经史科学并重,其门生往往博学多见,况师徒治学严谨,立论大气而耐精深故其史学成就终有浙东一系。元隐逸大儒刘因已言诗书春秋皆史,阳明先师更谓五经亦经亦史,而后乃有章实斋。其学派之彰应自修《明史》起,盖明史馆中,梨洲门徒之盛,所负之重,为天下共睹,况梨洲之建议每被采纳,梨洲所集之史料悉与贡献,巍巍一部《明史》,几如浙东之作。“四方声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梨洲此言,满负经纬之志。事功之学,千秋大业,儒者风范,一目尽览。
一破一立、一纵一横之间,二人形而上思想之探索尽归实用之学。思想上弃禅者虚空之流弊,实践上恢复孔孟实用之学,如此则尽儒者“千秋大业”之志,则融儒佛而复中华清朗之学。
(清)陈确著:《陈确集》,中华书局,1979年4月,2.75元。
(清)黄宗羲著:《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700元。
(清)黄炳著:《黄宗羲年谱》,中华书局,1993年12月,12元。
刘述先著:《黄宗羲心学的定位》,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1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