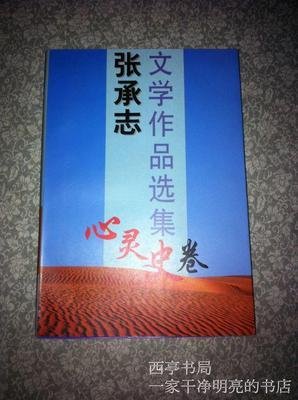
《张承志文学作品选集(心灵史卷)》是一本由张承志著作,海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8.00,页数:33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张承志文学作品选集(心灵史卷)》精选点评:
●对回民题材没有感觉
●坚定的信仰,催生心灵的伟大,呈现惊人的力量
●2010-09-27 购于孔夫子
●高中学过那篇汉家寨 自此就喜欢上了张承志老师的文章 对人性和心灵的一记有力的叩问
●这本书丢掉了
●一本让失言了许久的回回能够在夜间哭泣的书,一本让当代文学想回避却又不能的“杂种”。
●"刀只是架在古人脖子上,他们希望古人演一出合口味的戏以供他们喝彩。"感觉自己每天就是在干着这样的事情啊-_-# 至于命运的"前定",看历史越多越感觉命运是有定数的,不过牺牲流血的方式还需再考虑。 抛开人道的一切言论,哲合忍耶的无畏的精神,是我这样一个犬儒的平凡小老百姓所敬佩的。我为我唯唯诺诺的生命感到卑微。
●似乎有点原教旨主义的味道
●情节弱,又写得极像历史书,实在不是我的菜。
●四点五星,总让人想起《叫魂》。张承志太浪荡了,火气旺盛。
《张承志文学作品选集(心灵史卷)》读后感(一):值得长期阅读
1995年的那个冬天,懵懵懂懂的我,被这个书名吸引,被作者倔强的照片吸引,这会是本什么书呢?又会是个什么人呢?
带着这份好奇,买了回去........
时到今日,已过去13年了,四处辗转,书始终不丢不弃,是仍然值得一读的书,所以,是一本值得长期阅读的书。
《张承志文学作品选集(心灵史卷)》读后感(二):一把匕首式的文学丰碑
记得那年还是大三初冬,我正重感冒,浑身酸痛,无意中借了同学的《心灵史》,不厚,在感冒的迷糊状态下四个小时一气读完,然后不敢再回头阅读,因为阅读时,这本不厚的《心灵史》就像一把匕首一般直插心脏,浑身的寒意加重了病情,但是感冒所带来的迷糊一扫而空,因为我知道遇见了一个新的世界。
打小开始我阅读过的小说,小说最后总是谈到人的救赎,或者至少在描写人“生”的状态,就如基督山伯爵恩仇记最后写道的一般“所有人类的智慧都凝结在‘等待’与‘希望’之上。”而阅读完张承志的《心灵史》,我只是看到尖刃,和尖刃上流淌的鲜血,但是我这种感觉不是想贬低这本小说。因为偏执、屠杀就在那里,我们却要用文字伪造出来的爱化解一切,用所谓的终极真理虚幻出一个希望,那不是另一种虚伪和残忍吗? 而张承志因为自己无法改变的出生,记录了那段游离于我们汉民的历史,记录了那段在二十五史正史上只所作“蛮夷”的历史,把对于主流民族可以算是细枝末节,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历史如此完整的以自己的眼光记录下来,于是把这无法化解的硬疙瘩铸成了丰碑,这本史诗的成功就在于他自己创造了一套价值。
对于传统经典略有涉猎,读过部分《论语》,背过《老子》,略看过些《庄子》,精读了《资治通鉴》九十卷,而且还在读下去,觉得我们的汉文化其实是叫我们怎么活,《论语》和《老子》不过是活的两种方式,《资治通鉴》更是中国人生存方式的各种缩影,只有《庄子》有点跳出了生死之圈,甚至可以说汉文化的主流不过是现代所谓”成功学“的变种而已,为了所谓的活,我们的文化为生存设置了无数的规定。而张承志的《心灵史》说的是人怎么去死,诉说了活是偶然的,而只有死才是必然的,这是我在阅读完《心灵史》十二年后忽然看见的东西。
《张承志文学作品选集(心灵史卷)》读后感(三):张承志,向时代复仇的刺客
张承志,向时代复仇的刺客
作者: 祥子 来源:《mangazine/名牌》
臧否现当代作家的《齐人物论》里有个假设:张承志即使拥有韩少功的综合素质,仍是张承志;但韩少功一旦具备张承志的孤标胆气,顿会一飞冲天。
张承志只能是张承志,是因为他有个不变甚至宿命般的文化立场。这立场的选择,并不取决于张承志在知识上的判断力,而是一种种族认同。
张承志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黑骏马》和《黄泥小屋》依然是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文本。在文学语言上,他是拥有最高辨识度的一位,但他的重要性更取决于他独特的姿态。
张承志对自己的精神勾画在小说《错开的花》(1989)中已趋于完整,他想象的人生四个极致—山海的探险家(内陆亚洲史考察者)、叛匪之首领(红卫兵缔造者、回民叛乱史研究者)、牧羊人(插队内蒙知青)、迷醉的教徒(穆斯林信徒),都在他的精神游历之中。
1991 年,张承志出版了很难归类(文学?历史?宗教?)的文本《心灵史》,用自己的激情感受,重构了中国回民的哲合忍耶教派在18 世纪与官府抗争的历史。从此强化和清晰了其一系列的“血
性理想主义”、“种族中心主义”和“贫瘠土地情结”。这是从边缘处向汉文化中心发出挑战。这种挑战至少是“五四”后大范围公开表现的第一次。自近代中国面临民族和文化危机以来,先辈或引“西”,或改“旧”,基本都忽视了中华民族内部的异质文化资源,而张承志为知识人提供了一个极有意义的位置参照点。
《心灵史》之后的散文创作,张承志站在民族信仰和“贫瘠土地上的底层人民”的立场上,嘲笑文化精英,抨击知识分子的堕落;赞美“任何异端、任何理想主义、任何美、任何新鲜的希望”。但以信仰之美,不能替代时代批判。“袪魅”后的现代,的确在金钱化、快感化、污浊化,但倒退寻“魅”(迷狂)的方式却是唐吉诃德式的。记得章太炎曾认为康有为比袁世凯更不可原谅,因为袁氏的称帝野心多少还算人之常情,康有为居然想当教主,那是无论如何不可原谅的。
《聋子的耳朵》是张承志最新的散文随笔集。从以前的《荒芜英雄路》、《以笔为旗》到《谁是胜者》,书名已没有当年的悲壮和任性了。翻开书,发现这平静甚至有些禅意的书名,并不是因为批
评家们的围剿让张承志韬晦其志,而是将坚持的姿态内在化了—“或者是因为有一种认为大街上匪患滚滚的心理,所以本来是流水茶饭,我却敏感而警觉,好像随时准备拔出匕首,刺入无影之中的腹。在一个失聪的年代,一切判断的根据,只是‘内在的听力’。也就是说,拒绝强制灌输塞入耳朵的喧嚣声响,用人的另一种本能,去听取茫茫沉默中的哑语本音。”成为这个时代最激烈的批判者的同时,张承志却拒绝与这个时代对话。
假如一种宗教或团体并没有遭受严重迫害,并不必以激烈抗争的异端面貌出现。而张承志在书中对布什连任而愤怒,因阿拉法特病危而悲恸,他从不掩饰其对苦难和殉道的渴望—某种圣战情怀。
在我看来,唐吉诃德以骑士的方式在向非骑士时代挑战,而张承志以刺客的方式向眼前的大时代复仇。复仇的本质是一种私刑。“公刑”(或主流话语)愈强大,反而衬托出复仇“以义犯法”的悲剧审美意义。而民间对快意恩仇的赞美从来没有停止过,那是弱者对强权的一种震慑。
《张承志文学作品选集(心灵史卷)》读后感(四):只问是否人道
他在前言里说,希望那些从《黑骏马》,从《北方的河》以来一直追随着我的读者,可以继续追随我。然而我从《黑骏马》,从《北方的河》一路追随过来,却再不能追随他。大概张承志说的很对, 没有宗教体验和信仰的人很难理解这部书;我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我游荡在甘南,在青海附近,我看见神庙前匍匐的人,我希望我有信仰;我无数次直面死亡,我看到无底的深渊,我希望我有信仰;我希望这人世之后,还有灵魂,但是我没有信仰!
要我说的,这生命是仅此一次的生命,没有来世;不管是回民是汉民,或是别的民族;都不应该成为狂热和极端思想导致的无辜者和冤魂;人道主义,不是宗教;是孔孟;子路请问事鬼神,子曰“不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不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但是说“仁者爱人!”当其厩火,不问马先问人;中华文化的大智大贤在几千年来重复着这样的人道,人不应该忽视死,人不应该草率被杀,即使是自愿的,镇压的路是一条血腥的路,殉道的路也是一条血腥的路;所以这个在《圣经》还有《古兰经》中重复的亚伯拉罕以子献祭的故事都被认为残酷恐怖;所以鲁迅先生在散文“二十四孝图”讲“郭巨埋儿”觉得思之后怕!《心灵史》却又一次激情洋溢的赞美这个故事,那是马化龙自愿以八门三百口人殉教,被杀戮!难道这里面没有无辜者,没有不情愿者?妇女惨死,十二岁的孩子要被阉割,谁能确定被称为汴梁太爷的小男孩对营救者的拒绝不是对哲合忍耶的拒绝?他的冷漠不是对宗教的冷漠?
张承志是一个走火入魔的人,这历程从《黑骏马》到《北方的河》,到《黄泥小屋》再到《心灵史》,并不是没有轨迹可循!他对激情壮阔的美,对于神迹般的造化之美,对于忍受苦难的史诗般的美一如既往的痴迷,成就了这部书。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心灵史》写的很美,这美是“殉道”,是“束苔依斯”,是守密与隐忍,而这美是充满着痴邪的美;所有在文化史上成为大师的人他们是从这些私狭走向坦荡的那一部分,这些人包括拉伯雷,莎士比亚,歌德,雨果,托尔斯泰,泰戈尔,鲁迅,但不包括阿里奥斯托、左拉、席勒、普鲁斯特、拜伦、米兰·昆德拉,矛盾、沈从文。
《心灵史》不是人道主义的,不是心灵追求和完善的正道,它是宗教的;宗教不是现世的,因而没有对只此一次的生命应有的尊重和珍视,宗教没有死亡;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孔孟不是宗教,它没有解决生命最深层的危机,所以自古没人信仰孔孟,独尊儒术的汉武帝也不能信仰它,子曰“吾见蹈水火而死者,未见蹈仁义而死者”。文明时代宗教的余地很小,所以古希腊同样没有宗教,有神,和我们一样,但也有死,和我们一样!
就像维科在《新科学》中指出的:宗教的来源是恐惧,恐惧来源于无知,这无知的产生是因为文化的落后和生活的贫瘠;所有希伯来人的苦难催生了“基督教”,印度人的苦难产生了“佛教”和“印度教”,至于伊斯兰教,同样也不例外,《心灵史》的哲合忍耶教派是在被压抑中在颠沛流离中发展壮大的,张承志叙述的很清楚,所谓“不平则鸣”而已;直至今日,宗教的忌讳和礼拜不再那样严格,可能我们周围遇到的回族中严格遵守穆斯林教规的寥寥无几,这就是现状;消除恐惧的是文明,削弱宗教的也是文明;当今的宗教更多的沦为仪式,而它的教义转化成了文明时代的文化和传统;但是宗教不会消亡,它和文明此消彼长;近代以来,对信仰和宗教的呼声再次高涨是在现代主义以后,是在艾略特的《荒原》以后,是在《尤利西斯》以后,因为文明式微了,西方文明被机械化摧残着,一片荒原,因而他们需要溯源,所以宗教又一次被提及!
在这最后我得说,关于历史我对于作者是没有发言权的,二十四史我只读了一半,更多的秘史更不是我能了解的。新历史主义如果让我来说,我会认为它是伪科学;或许更多时候我们在追问历史真相的同时忽略了追问它的原因——不是为辩论谁是谁非,而是为了更好的活,更好的完善我们的群体道德和个人品行!
《张承志文学作品选集(心灵史卷)》读后感(五):关于哲合忍耶
2006年的某个星期五下午,我开始知道哲合忍耶。那是在李老师的课上。老师提到苦行僧式治学的张承志以及他的《心灵史》。"这是哲合忍耶教派的圣经"。从那一刻起,哲合忍耶,这个一向是穆斯林诸多教派中的苏菲主义的一支;这个隐忍、坚强经历了太多磨难,本意"高声颂扬"而后又不可思议般销声匿迹的教派,这个从一开始就"扛了红旗"的教派开始一点点的进入到我的视线,而且一发不可收拾。这偶尔的一瞥却带来了惊鸿般的震撼。我发现这一切太过神秘,一个个克拉麦提(奇迹)就在我的眼前发生。我本以为自己和这神秘的一支绝无任何联系,而实际上我和哲派的关联却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这种宗教的神奇之于心灵的震撼是我从未体验过的。我想,这或许就是冥冥中注定的,根本无法也无须解释。
我对穆斯林一向是崇敬、喜好、并乐于接近的,我很抱歉的这么说,但却肯定这里绝无半点猥琐之意。那些毕恭毕敬的净身仪式,那些千百张口中同诵出来的低吟浅唱般的阿语经文,再加上那些古老的、不容半点改变和质疑的教义本就令人肃然起敬了。而那些戴着小白帽子的孩童的明亮的眼睛和留着圣行的"利毫耶"(腮胡)的慈祥的老者更是让人不能不亲近。大学四年,我有幸居住在我们院的穆斯林宿舍。宿舍的四个舍友中有两个来自宁夏,而我经常和他们同住同吃也就适应了穆斯林的诸多习惯。穆斯林的生活是简单而寡欲的,这让人原本复杂的欲望变得简单。宗教多是教人向善的,这样的信仰给每个信徒的生活增添了几分平静和神圣。
洋是二人中的一个,家在青铜峡。他本就是哲和忍耶教派,这是我和哲派的一次关联。我曾去过他的家,那儿是宁夏平原上的一个宁静村落。去时正值秋收,到处是金灿的黄。洋家的小院儿干净、平和。妈妈和奶奶出来迎接我们,头上罩着白色头巾,正是穆斯林妇女的打扮。不远处即是清真寺,隐隐传来诵经之声,令人沉醉也让人心里产生一种火热的颤抖。那是一种类似于模糊的,神秘的某种东西在心里一点点清晰、凸显的颤抖。
在洋家的时候正赶上斋月,洋不封斋,但奶奶却以最虔诚的方式进行。每日太阳升起,早6点前,吃下一颗红枣,喝下一杯水就进入封斋状态,直到晚上6点后结束,此间不再饮水进食。但正常的劳作却不因此而暂停。信徒们以肉体的寡欲和苦行换取精神的清高与解脱。多少个夜晚,当他们齐聚诵经、思苦行之道时定能想起这宗教的种种辛酸和祖师爷的创道之艰。
关于哲合忍耶的历史,《心灵史》已经做了极其详尽的记载,而我显然对之理解的不够透彻。但请允许我照着我的理解对这段历史继续讲述。我努力把自己重新置于那样的年代,虽然我知道这其中的悲怯对于我这个"外人"来说,想要感同身受实在太难。毛拉马明心因为传新教而被捕,尽遭牢狱之灾。信徒苏四十三、麦力赛等人起义,围困兰州。后马明心于兰州城头遇害,苏四十三战死华林山、麦力赛战死金城关。当年那凄壮的一幕让人不忍再提及。而于我而言,心灵的震撼并非仅仅与信徒们对宗教的虔诚相关。这种心灵的共鸣来自于对追求自由的敬佩,来自于对追求信仰--这种最基本权利的崇敬。
马明心被清军杀害于城楼后,几经辗转最终葬在兰州,墓地被称为东川大拱北。而这也是我和哲合忍耶的再次关联。每年逢马太爷的祭日三月二十七,来自甘肃、宁夏、新疆、云南的哲合忍耶齐聚于此,共同祭奠这个解众生之痛的祖师。此景我未曾亲见,却从一亲历于此的摄影者的文字中用心感受过这样的画面。他写道,低沉的念经声不绝,一个诵经者抬头定见对面人的脸上同样满是泪水。只有熟知哲合忍耶教派历史的人才能体验为何他们有如此的苦难,也唯有他们才能理解今日哲合忍耶为何能有如此的坚忍。
我想,张承志是幸运的,正如他所说,他在偶然之间寻到了哲合忍耶,并把之作为一生的精神支柱。他把这一切记载下来,并把这一切与汉族朋友共享。我想,我亦是足够幸运的。我不能解释这一切巧合。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指引着我写下当时的志愿,是什么力量引着我来到兰州,来到毛拉马明心的拱北,来到穆斯林宿舍遇见洋和钊。我只能将这一切归结为宗教的神奇。不管怎样,对于我这样一个普通人来说这些就是主的克拉麦提,这已然是一番太过传奇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