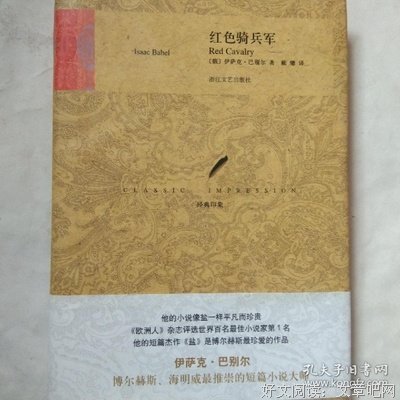
《骑兵军》是一本由[苏] 伊萨克·巴别尔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2019-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骑兵军》读后感(一):剥开了“人间喜剧”的糖衣
《骑兵军》读后感(二):战争下的诗性记叙
苏联作家伊萨克·巴别尔的《骑兵军》是一部质量参差不齐的短篇小说集。
篇目的长短不一并不造就这一现象,反而是从素材转化到一篇完整小说过程的神秘和不稳定。因此头几篇如《激流强渡兹布鲁齐》和《诺沃格拉德天主教堂》,最大的问题是小说结构保持了原素材的粗糙感和原始感。人物对话于推进、表现的无力,让《骑兵军》的部分篇目更像回忆录或日记,而不是小说。
《扎莫斯季耶市》可能是诗性语言同战争侧面记叙相融最接近完美的一篇。夜晚的大地散布着凄然的意象,麦地、筋疲力尽的马、雨水、烟囱、雾霭、信号弹。战争在另一面激烈进行,人性和兽性则在这安静的地带暴露无遗。“‘咱们输掉了这次战役。’沃尔科夫嘟囔道,接着就打起了呼噜。”战争的胜利并不是所有人都在意的。那个政治逐渐戒严的年代,沃尔科夫的行为无疑是一次解构,一次静默的讽刺。
“我”随部队进驻布季亚季奇,它从波兰人手中回来了。“我”借宿的家庭决定:一家移居莫斯科,老头子找著名教授看病,女儿伊丽莎白进培训班学习,小儿子上学校学习。此时“我”和伊丽莎白恋爱了。经过一场短暂的战役,市中心已成废墟,“我”为了赶上所属旅,将他们抛下在那片荒凉之地。所有的希望和期盼像枯萎的花,这就是《吻》,战争不会直接将人毁灭,却会通过一系列戏剧性的事情使人绝望。
《骑兵军》读后感(三):革命不是浪漫主义的诗
伊萨克·巴别尔是天才的苏联犹太裔作家。1920年6月,26岁的巴别尔志愿加入布琼尼统率的苏俄第一骑兵军。作为《红色骑兵报》的特约记者,巴别尔随第一骑兵军远征波兰,既要行军打仗,又要为《红色骑兵报》撰写鼓动文章,书写战事日记,颇有“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意味。一路上,巴别尔还坚持写战地日记。他以这些战地日记为素材,创作了一部名闻世界的短篇小说集《骑兵军》。
众所周知,苏联时期曾经产生过一批反映十月革命以后苏俄红军在内战中的战斗生活的作品,如《恰巴耶夫》、《铁流》、《毁灭》等。《骑兵军》之所以有别于它们,显得与众不同,独具一格,是因为巴别尔遵循这样的创作原则:“一个人应当了解一切真相,这好像显得没品位,但却很有趣。”换句话说,他看重的,是依据生活的本来面目,真实、多维地反映现实生活,并将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不露痕迹地贯穿在作品之中。《骑兵军》的开篇《激流强渡兹布鲁齐》,开始的一长段场景描写,“昨日战场厮杀和战马死伤发出的血腥味儿,点点滴滴,渗入向晚的凉意。黢黑的兹布鲁齐河咆哮着,激流险滩卷起千堆雪。桥梁都被破坏殆尽,我们不得不泅渡过河。一轮明月映在河面上,波光粼粼,水面上呈现出战马的马背,成千上万匹马,马蹄踏踏,溅起哗哗的水花”,作家用他那惯有的简洁而华丽的文笔,将骑兵渡河的浩大场面,战场的悲壮气氛,生动传神地勾勒出来。然而,到了小说的后半部分,作家写自己被分配到夜宿一犹太居民家,半夜醒来,发现自己居然与一具死尸相伴而眠,接着是死者女儿的讲述:父亲临死前还在恳求波兰人不要当着女儿的面杀害自己。老人至死都想着保护爱女,她不禁感慨地问作家:“我很想知道,整个大地上,您还能在哪儿找到我爹这样的父亲……”此时,我们才明白,这段描写呼应了小说开头的场景描写中隐约透出的血腥味,也凸现了战争给普通人所造成的巨大伤害,以及在杀戮中依然顽强闪耀的亲情的光芒。
《骑兵军》总共38篇短篇小说,每篇都在千字左右,但往往言简义丰,耐人寻味,结局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其写作手法颇得俄罗斯短篇小说大师契诃夫与法国作家莫泊桑的神髓。在《一匹战马的故事》中,骑兵六师师长萨维茨基将第一骑兵连连长赫列勃尼科夫心爱的坐骑占为己有,赫列勃尼科夫为此耿耿于怀,多次上诉告状,但都未能将心爱的战马要回来。他心灰意冷,最后竟然退党退役。小说到这里原本可以结束了,但巴别尔笔锋一转,表明自己与赫列勃尼科夫趣味相投,常常在一起喝茶,“我们受同样的激情的鼓舞。我们两人都把世界当作五月的牧场,是徜徉着女性和骏马的牧场”。这略含忧伤的抒情文笔中,有让人深思的意味深长。
巴别尔着力表现现实生活的复杂多样,他笔下的人物不是“扁平人物”,往往充满了矛盾,行为怪诞诡异,难以捉摸,因而使小说的内涵也变得丰富复杂,可以从不同的层次加以解读。《骑兵军》中的名篇《盐》,以一个“革命战士尼基塔·巴尔马绍夫”写信给“亲爱的编辑同志”的形式,讲述了他亲历的一件事。一个面容姣好的女人抱着孩子,恳求哥萨克们让她和孩子上火车。之前,有两位姑娘因为搭乘这趟满载哥萨克骑兵的火车,而被强奸了。但在巴尔马绍夫的劝说下,哥萨克们同意让她搭车。经过一夜的颠簸,巴尔马绍夫发现了破绽:这个女人怀里的孩子一晚上既不哭也不闹,安静地出奇。于是,他走到女人身边,突然打开包裹孩子的襁褓,原来里面是“足足一普特盐”。他义愤填膺,一脚把这个坏女人踹下了列车。接着,“我从车厢板壁上摘下我忠诚的步枪,从劳动者和共和国的土地上,抹掉了这个耻辱”。表面上看,小说是在谴责十月革命后出现的“布袋小贩”所从事的投机倒把买卖,立场十分鲜明,实则不然,作者通过这则悲剧性的故事,反映了战争所造成的民生的凋敝,对为谋生而丧命的小贩寄予了同情。
《骑兵军》的出版为巴别尔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但并未给他带来安宁。显然,巴别尔的创作理念与当时苏联主流的文艺思想格格不入,这部小说集甚至受到了布琼尼的愤怒声讨,被指控为是对第一骑兵军的诽谤。虽然有大文豪高尔基的竭力庇护,但巴别尔终究难逃厄运,于1940年1月被处决。时光流逝,《骑兵军》依然光芒闪耀,巴别尔在这部小说集中所展示的非凡的才华和人道主义理想,让我们赞叹,也让我们沉思。
《骑兵军》读后感(四):给你一面多棱镜,照现人性真实
《骑兵军》是一部奇异之作,整部作品(张冰译本)由38个短篇构成,与其说是短篇小说,毋宁说是叙事散文,各篇独立成章,并无前后一贯的人物和故事情节,但连缀起来,却能让阅读者勾勒出那场战争的场景、战事的残酷以及哥萨克兵凶蛮残忍英勇善战和战区人民蒙受的深重苦难。作者采用多视角的叙事风格,灵动地展示了战争中的众生相,不着痕迹地刻画了人性中包含的美丑善恶,作者的叙事风格简洁明快,冷峻且不动声色,在景物描摹上又充满了瑰丽的不同寻常的意象,常有出人意料震撼人心的效果。
第一篇《激流强渡兹布鲁齐》就能一下子抓住读者的心,前面的大段铺叙和梦境描写,让人以为这是通常意义上的战争序曲,结果,突然出现反转,直到那女人鼓起勇气说道,“我很想知道,整个大地上,您还能在哪儿找到我爹这样的父亲……”。这是这部作品的序曲,战争的残酷、人性的残忍、生命如同草芥般的卑微一笔带出,震撼人心。
《一封信》:通过代写家书的方式切换了叙事主体,更加生动地刻画了战争中父子相残的人伦惨剧。
《潘·阿波廖克》:有渎神的意味,那个故事、那些圣徒画像,但比之战争大规模杀戮,渎神又算得了什么,究竟是上帝以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亚当,还是亚当的子孙以自己的模样想象出了上帝?对于一个穷画匠,心中有上帝不如口袋中有银币,想象力的匮乏正如物质的匮乏。
《基大利》:“革命就是叫人满意。叫人满意就不能让家有遗孤。好人做好事。革命就是好人做的好事。而好人是不会杀人的。”“……那个什么国际我们也知道。我想要的是好人的国际,我希望每个人都能登记在册,并能领到一份最高标准的口粮。”——革命来袭,睿智的、有朴素革命观的、遵循教规的犹太人看上去也有些困惑。
《我的第一只鹅》:向蛮横粗鲁递交的投名状。任何想融入新环境新团体的人都不得不屈己悦人,倘能反思“被杀戮染红了的心”,就不失本真。
《马特维·罗季奥内奇·帕夫利琴科行传》:和地主有夺妻之恨的红军军官回乡报仇了,爱恨情仇快意恩仇有仇不报非君子。帕夫利琴科出乎我们意料,且看他,“开一枪是对他的恩赐,枪子儿打不到他的灵魂。通常我会脚踹敌人踢上一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我希望弄明白我们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我想起了我舅舅,建国前他随四野部队进了关,建国后当了军官,他很想回乡把虐待过他的那个算命先生揍一顿,被外公劝止了。
《一匹战马的故事》:哥萨克在战场上英勇无畏,漠视生命,没有人道情怀,嗜杀成性,但却把战马视为生命的一部分,这个被夺了战马的哥萨克孤愤难平,不惜退党退伍。显然,世界不是五月的牧场,或有女性和骏马徜徉其上,也有凛冽的风霜雨雪和莫名的不公不平降临其间。这个故事有续篇,夺马师长萨维茨基的回信似有一种大无畏的悲观。
《叛变》:这篇和《盐》构成姊妹篇,革命战士尼基塔·巴尔马绍夫再度出现,再度以其颠倒黑白颠覆众生的革命口吻把他们私刑杀人、施放黑枪的不法行为涂抹上革命的金辉和正义的缘由,读来令人绝倒。
《拉比之子》:革命如暴风骤雨,裹挟一切,“革命中的母亲,是小事一桩”。
《汗血马》:连长包林的骂娘最令人动容:“我把你都看穿了……你总想活在一个敌人也没有的世界上……你的所有努力都是在朝着这个方向——一个敌人也没有……你知道这会是什么结果吗?这样活得会很乏味……”。谁说不是,我等良善的知识分子都朝这个方向乏味地活着!
《吻》:温情犹在,希望在否?“我终于看到了发端于贡西奥罗夫斯基公爵城堡的深情一吻所带来的道路,这是一条无法避免的不归路……”
爱伦堡在回忆巴别尔时说:巴别尔是个讲故事的高手。他的前妻卡什琳娜说,巴别尔最高的智慧,就是他会说俏皮话。他的女友金斯伯格也说:巴别尔是一个讲神秘故事高手。他的女儿娜塔丽娅评价道:父亲也许不是最英俊的男人,但他身上有种活力,而且能使身边的事物也充满活力。这个英年早逝,临死前还天真地央求“让我完成我的作品”的男人善于从生活中汲取创作素材,然后以一种似有若无的幽默笔触讲故事给你听,没有歌颂没有控诉没有投枪与匕首,掩卷思之,似有一丝反讽,其下则是悲悯、人道情怀、希望和对生命的敬意,对生活快乐的渴望。…这就是他的作品魅力所在。
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杀戮的历史,争夺资源、残虐同类乃人之本性,作者在告知你这一人性的真相。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地是公平的,施恩施害,全在于人。
《骑兵军》读后感(五):苏波战争,哥萨克人和被秘密处决的巴贝尔
得到听书:
1.本书
《骑兵军》是一部短篇小说集,作者是伊萨克·巴别尔,他是苏联著名短篇小说家。这部作品在苏联文学史上,曾引起军界与文艺界的剧烈争论,甚至,两方的最高人物布琼尼和高尔基都给斯大林写信,指责对方的手伸得太长。斯大林亲自出面干涉,这才平息了两方的争执。虽然斯大林当时站在高尔基这方,但最终,巴别尔为这部作品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本书也一度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不过,好的作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1954年,苏联政府为巴别尔平反。三年后,《骑兵军》在苏联解禁重新出版,之后陆续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巴别尔的文学成就也得到了世界的肯定。1986年,《欧洲人》杂志选出了100位世界最佳小说家,巴别尔名列第一。文史学家都认定,巴别尔的艺术创作经验,对于苏联小说的发展有过决定性影响。
2.苏波战争
俄国和波兰的世仇可以追溯到17世纪初。当时,波兰是东欧的强国,历史远比俄罗斯悠久。波兰还趁着俄国内乱,在俄国扶持了一位伪沙皇,史称“伪迪米特里一世”,两国也为此爆发了多次战争,历时长达近二十年。这一期间的俄国,同时经历着天降灾难、外部入侵和内部政治斗争,毫不夸张地说,已有亡国灭种之危,俄罗斯民族遭受的苦难几乎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当。
但是,俄罗斯民族在绝境中,往往能爆发出不可思议的力量。最终,俄国打败了波兰,一举成为欧洲强国之一。波兰却逐渐走向衰落,沦为欧洲的二流国家,后来还有过很多次名为合并、其实是被吞并的惨痛经历。时间没有平复俄国的怒火,在波兰衰落之后,俄国先后三次主导瓜分波兰,18世纪末的最后一次直接导致了波兰的灭亡,于是,俄国获得了原波兰领土的62%,此后,波兰退出历史舞台长达123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俄罗斯帝国、普鲁士王国、奥地利大公国先后分崩离析,波兰的民族武装领导人毕苏斯基才乘势重新建立了波兰政权。
在波兰东部与俄国接壤的领土问题上,波兰与苏俄产生了纠纷。波兰的毕苏斯基认为,只有恢复过去的强盛,才能一雪前耻并保证自身的安全,因此,他渴望恢复波兰衰落之前的领土规模,其中就包括现在的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当时的苏俄刚刚经历了革命和内战,苏维埃政权尚未站稳脚跟,对于这次领土纠纷,苏俄不希望再起干戈,因而愿意承认波兰的独立,通过谈判解决纠纷。那个时候的国际形势普遍反对新兴的苏维埃政权,对苏俄很不利。波兰方面就利用这种形势,发动战争,迅速占领了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甚至在苏俄再次做出让步之后,还继续向苏俄进军。但是,历史再次重演,波兰想借苏维埃政权根基未稳将其一举击溃的算盘,最终落空了。虽然战争一开始波兰占据了上风,但是外敌的入侵在无形之中,加速了苏俄内部的整合,甚至连原本对革命并不是很热情的前沙皇军队也纷纷请战。很快,波兰军队被赶出了苏俄境内,英国也被迫出面调停,希望就此停战。
关于战争失利的原因有许多,过去苏联给出的官方结论是:由于领导人托洛茨基的错误判断,干扰了红军的作战计划,进而导致全盘皆输。不过,后来的历史学家根据资料复盘,形成了一种看法是:苏俄高层之间不和睦、相互掣肘,导致战略决策无法实施。那些进入波兰作战的部队,也没有得到当地人民的支持,反而逼得波兰全民皆兵。对于苏波战争中红军失败的原因,无法得出单一的结论,需要考虑多种因素的合力。这其中,进入波兰作战的部队不得人心,没有取得当地民众的支持,是公认的一个原因。这一点,我们在《骑兵军》里可以略窥一二。
3.哥萨克人
哥萨克是俄罗斯、乌克兰民族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游牧社群,他们以骁勇善战著称。哥萨克不以血缘关系为联系纽带,而是通过武力来认定一个人是否有资格成为内部的一员。由哥萨克组成的骑兵军,有个很明显的特点,他们擅长奔袭作战,基本不用带粮草等物资,完全靠就地取材获得补给。这样的特点,再加上内部松散的联系纽带,就导致骑兵军的战斗纪律非常涣散,战士往往自行其是,不听军官指挥。另外,许多骑兵军都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争中与波兰人结下深仇,也时常出现罔顾纪律、大肆抢掠、滥杀俘虏和犹太人的事情,部队的名声受到了严重影响。苏联高层本以为,骑兵军能得到波兰当地人的支持,结果事与愿违。巴别尔作为在战斗第一线的知识分子,清楚地看到了问题在哪里。他肯定了哥萨克们的骁勇善战,但也没有因此忽略他们的恶行,他把这些真实地记录在这本书里。
“十月革命”后,俄国经历了一场内战,一边是列宁领导的革命武装——苏联红军,另一边以邓尼金将军为首的保皇派,被称为白军。当时,两方都竭力拉拢具有极强战斗力的哥萨克。许多哥萨克家庭都因为父辈坚持信仰上帝,后代却向往革命,于是产生了分歧,甚至反目成仇。白军战败后,一部分白军哥萨克加入了红军,也有很大一部分流亡在乌克兰东部和波兰,这些地方过去都是亲沙皇势力的地区。那些曾经与红军作战的哥萨克,在苏波战争期间一旦被发现,可想而知会面临怎样令人唏嘘的命运。
生活在波兰当地的人,他们的风俗文化很多元,犹太人、波兰人、乌克兰人都想要保存自己稳定的生活习惯。这让哥萨克们异常恼火,他们见到当地的宗教场所就要进去胡闹。哥萨克们习惯跟死亡作伴,磨灭了对死亡的恐惧感,因此,他们对生命的态度极为冷漠。强奸妇女、虐杀俘虏,以及为了补充给养与当地居民发生流血冲突都时有发生。
4.被处决的巴贝尔
尽管这本书因此在苏联一时间洛阳纸贵,但是这场风波并没有结束。巴别尔敏锐地察觉到了危机,他一直竭力保持低调和沉默,再也没有写出有力的作品。但是他还是没能逃过劫难。1939年,巴别尔被秘密逮捕,罪名是参与阴谋恐怖活动。从记录来看,逮捕决定竟是在作家被捕了35天之后才做出的。1940年,巴别尔被秘密处决,一代天才就此陨落,但是这本书却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局限,在文学的天空中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