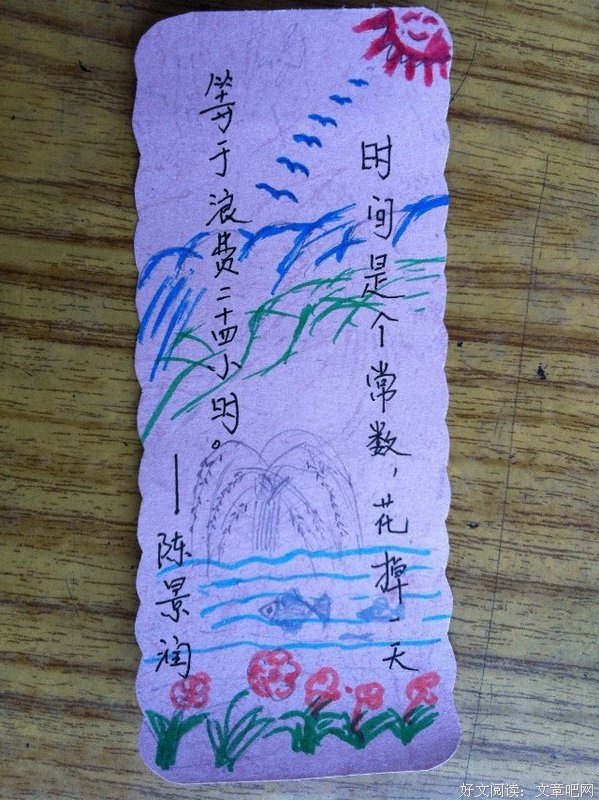●那些生活需要速度的陆生脊椎动物,至少已在三个独立的时期对鱼类古老的身体结构进行了改造。哺乳动物的祖先和恐龙的两个分支都分别做出调整,以便解决「陆生鱼类」(fish-on-land)在爬行上的不便。它们的四肢朝里移动,同时向下,使身体重量直接压在四肢上,这样更便于保持平衡,在向前跑动时也不至于一头栽倒。脊椎的左右摇摆,则被上下的弯曲行动所取代。……颇具讽刺性的是,这种构造新奇的脊椎,也重新回到海洋中去,试图与古老的鱼类脊椎一较高低:鲸鱼的尾巴上下移动,而不是左右摇摆,这表明它们是来自陆地祖先。美人鱼似乎也同样如此。 ----戴维·乔治·哈斯凯尔《看不见的森林》
●一段小路,我看到一个腿脚不便的中年人,好害怕那是以后的你。我看到一个穿印花围裙的女人,一下子想到一个月前的你。
眼睛湿湿的,心脏空空的,老爸老妈,知道我在想你吗?
●方便的东西,必定会有不便之处。 ----村上春树《爱吃沙拉的狮子》
●不要心痛太久
我一定会再来见你的
所以,要好好等我
不要下太多雨
因为会给市民造成不便的
我只离开一下子
我答应你
这一次,我来找你
我一定会去找你
来世,我一定会生命力满值
长长久久的在你身边 ----《孤单又灿烂的神-鬼怪》
●年轻时的我们也许会在成长中迷失了方向,时间是稀释单纯的毒药,成长让每个人心的距离有了星河般的遥远,城墙成为了你我不语的保护色。不得不说,如果当初本身就是个伪命题,成长终究会让人变得成熟。
望着爷爷哭泣的表情,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老人最后身体功能退化后也会像小孩一样需要我们照顾,他们知道自己许多的不便,但却无能为力。我们能做的是不忘责任跟孝顺。责任是种担当,而孝顺却是种觉悟。有种难于割舍的感情便是血浓于水的亲情,请惜之。更何况我们也有老的时候。
●我住在老家的时候,和同屋伙伴不在一处劳动,晚上不便和她们结队一起回村。我独往独来,倒也自由灵便。而且我喜欢走黑路。打了手电,只能照见四周一小圈地,不知身在何处;走黑路倒能把四周都分辨清楚。我顺着荒墩乱石间一条蜿蜒小径,独自回村;近村能看到树丛里闪出灯光。但有灯光处,只有我一个床位,只有帐子里狭小的一席地——一个孤寂的归宿,不是我的家。因此我常记起曾见一幅画里,一个老者背负行囊,拄着拐杖,由山坡下一条小路一步步走入自己的坟墓;自己仿佛也是如此。 ----杨绛《干校六记》
●修行有三不足,不足食,不足衣,不足睡。不足食,取止饥不宜过饱,更不能求美味;衣取御寒,宜服粪扫衣,更不能贪求美备;睡取调倦,不宜久睡。盖久眠长愚痴,多衣增挂虑,过饱不便用功。 ----《虚云》
●在绿色的丘陵间延伸着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上面并没有铺设水泥,只由黄土培实而成。虽然正处于欧洲的正中央,但这里还没有沾染现代文明的颜色,维持着原有的乡土气息。虽说住在这里想必多有不便,但也乐得远离都市的喧嚣。
●你们要走,我不便留。
●我没有胆挂念,你没有心见面,试问我可以去那边,只要我出现,只怕你不便。
●女人总是喜欢爱情中有着那些小小的悸动。让她们躯体上坚固的堡垒瓦解,铁石的心柔软,果断的理性丧失。然后才知道这只是一种生理悸动,并不是她们向往的安全臂膀,确实不安的爱情,等遍体鳞伤便又会从新修筑更坚固的堡垒。若当初没有那一点点不便方向向往喜欢与悸动变不会对自己如此折磨。
●有人说,《老张的哲学》并不幽默,而是讨厌。我不完全承认,也不完全否认,这个。有的人天生的不懂幽默;一个人一个脾气,无须再说什么。有的人急于救世救国救文学,痛恨幽默;这是师出有名,除了太专制一些,尚无大毛病。不过这两种人说我讨厌,我不便为自己辩护,可也不便马上抽自己几个嘴巴。有的人理会得幽默,而觉得我太过火,以至于讨厌。我承认这个。前面说过了,我初写小说,只为写着玩玩,并不懂何为技巧,哪叫控制。我信口开河,抓住一点,死不放手,夸大了还要夸大.而且津津自喜,以为自己的笔下跳脱畅肆。讨厌?当然的。 ----老舍《我怎样写小说》
●逝去的已逝,不变的不便...
●我认为中国人有时间的最好往自己的大脑里注入一点新文化,与中国文化做为一种对照也可以,用中文可读的书有限,还尽是被删节的,中国文化只是世界文化的一小小部分,以汉字来认识世界存在诸多不便,因汉字在世界上不流行,汉字之美犹如一朵深谷小花,但边儿上可能就是一堆狗屎,你读读环球报之 ----石康《石康微博》
●我的生活,你无需干涉
你的生活,我也不便打扰
就这样吧.
●天下有信数三:一曰智有所有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举,三曰强有所有不能胜。故虽有尧之智而无众人之助,大功不立;有乌获之劲而不得人助,不能自举;有贲、育之强而无法术,不得长胜。故势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乌获轻千钧而重其身,非其重于千钧也,势不便也。离硃易百步而难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远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穷乌获以其不能自举,不困离硃以其不能自见。因可势,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时有满虚,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人主为三者发喜怒之色,则金石之士离心焉。圣贤之朴深矣。古明主观人,不使人观己。明于尧不能独成,乌获之不能自举,贲育之不能自胜,以法术则观行之道毕矣。 ----韩非《韩非子》
●遇上不想被知道的事物便拿别件做伪装,这种手法确实不无可能,尤其是牵扯到性与死亡这些不便公诸于世的事,更容易遭人隐瞒。 ----伊坂幸太郎《一首朋克救地球》
●1915年 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相爱 那时的孙中山已经在家乡和卢氏结婚 孙中山又反对纳妾 于是在万不得已之下去征求卢夫人的意见 问询她是否同意离婚并说明离婚的理由 在那个一纸定姻缘一言定半生的年代里 裹着小脚的卢夫人在回信只写下一个“可”字 她同意离婚 不追究不问询 不埋怨也不抱恨 朋友问她“为什么这么轻轻松松就同意了你可知道离婚对于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 她对友人说“我常识不够 更不识英文 我又缠脚 行动不便 我怎么可以帮到先生呢”说罢泪下
●我这空空如也的人生,表面繁华却敌不过命运,看破看淡后,也不便在多追寻。 ----《一生最爱纳兰词》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二十三岁,母亲要我结了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二十七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极简的阅读系列》
●我应做的事只有一件:如何在我的肉体这个缺陷比什么都多的容器之中活过每一天。作为课题说单纯也单纯,说困难也困难。说到底,就算出色完成了,也不会被视为伟大的成就,谁都不会起身热烈鼓掌。老老实实说来,我一点儿也不中意自己这个现实容器,出生以来一次也没中意过,莫如说一直憎恨。我的脸、我的两手、我的血、我的遗传因子……反正我觉得自己从父母那里接受的一切都该受到诅咒,可能的话,恨不得从这些物件中利利索索地抽身而去,像离家出走那样。理所当然。无论怎么看都不能称为健全的物件。若以方便不方便的角度而言,明确说来是极其不便。尽管如此,我仍在内心这样认为——如果将外壳和本质颠倒过来考虑(即视外壳为本质,视本质为外壳),那么我们存在的意义说不定会变得容易理解一些。 ----村上春树《海边的卡夫卡》
●“这儿一点罗曼蒂克的气氛都没有!原本不适宜在这儿给你讲爱情故事,可惜时间有限。不能等到下回分解!你们这些跟了我多年的年轻人,不是一直想探听我为什么终身不娶?告诉你,宝山,我娶不到自己最爱的一个女人,因而终生不娶了!那是个很好的女孩子,心地好,相貌好,什么都好!”
“你也很好哇!”
“两个很好的人,不一定能结成夫妇。”
“那多么可惜,但是,为什么呢?”
“因为她遇到另外一位更值得她爱的好男人!”
“你定很伤心了!”
“这是必然的。当时,我简直伤心欲绝……我说的是50年前的事了!从来未曾在人前提起过,今天我给你道来,因为很希望让你明白,一个有情用情的男人,真是会为爱而伤心的。只是我们不张扬,不便为外人,甚至最亲密的人知道罢了!” ----梁凤仪《芳草无情》
●雨蝶
一簇雨的飘逸,映入眼帘的是一串朦胧,如果,朦胧是一种美感,哪么,雨水的降临、就是上天对苍生的恩赐。
尽管,下一场雨,或许对我们带来某些不便,不过,可以让我们在百忙中停下来偷个懒,甚至于,把工作或生活节奏放慢一些,好好去梳理不经意的遗失。
一只彩蝶的飞舞,就像一只精灵在牵引,彩羽翩翩蕴含着绚丽,一抹动人的斑斓、触动脑海的缤纷,瞬间戳开心灵。微小的生灵,勾起鲜艳夺目的色彩,萌动思绪。
听雨、赏蝶,是一份情怀,飘过来的是一种意境。
虽然,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但我不这样认为,自然界所有的事物都是讲求融汇,只是我们会否用心去捕捉而已。陌生搭配,产生互相映衬的韵味,这就是神奇,也是一种
●只是你转身与他谈笑的一个背影,都会让我心如刀绞,你终究还是逃离了我的世界,那我也不便打扰了
●为何家中杂物过多影响财运
关于家居太过杂乱会影响风水气场,这个问题白龙王许老师已多次提过。一个家里杂物太多,整个屋子很乱,不管是衣服、玩具、杂志几乎无处不在,生活在这样杂乱的气场中,怎能有好心情,又怎能有好运呢?屋子杂乱,空间自然减少,灰尘多不便清扫,影响风水。气场混乱,财运自然也好不起来。
--白龙王许少锋经典名言警句
●不便说,便不说……
●生命恰似一段旅程,这一程,我们都会路遇很多人,有些人成了你的命中注定,有些人则成了你灵魂的永恒。每个人的生命里或许都有一样东西,说不清是什么,只是固执地于某一处宁静和自己的心纠缠不清,于是,不便放手,不忍放手。
●一个人搭乘飞机,而又能够选择的时候,会有很多人都会选择靠窗的座位吧。尽管,出入会略有不便。但,有了这扇窗,我们就拥有了特别视角下的壮阔风景,它们,与我们的人生旅途一样,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有一些美景,一生只遇一次。
●甲骨金石镂刻不易,缣帛成本高昂,简牍则较为笨重,不便展阅和存藏。因此,古人开始探索制造一种更为简便的书写材料,这就是纸张。纸张发明的时间,尚难确考,根据考古发掘所获古纸,其出现时间至少可以上溯到西汉。纸张发明之后,并未直接替代缣帛简牍,而是经过了一个较长的并用时期,大概在汉末三国时期,纸张才正式成为通行的书写材料,中国书籍史从此迈入辉煌的纸本时代。纸张制作成本低廉,易于书写和修改,纸书也极便于流播和存藏,因此,极大地刺激了知识传播和著述编撰,尤其是文学作品的创作 。 ----潘建国《物质技术视阈中的文学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