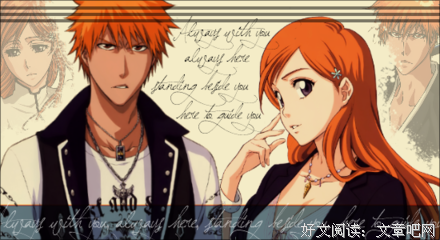远在汉之前,已有个惯例:君要臣死,不必亲自加诛。
刑不上大夫,那么上头责罚你,暗示你死,允许你自由选死法,已算是大体面了。
像夫差赐死伍子胥,是派使者送剑过去,逼他*。只是伍子胥气不忿,*前说要亲眼看越国灭吴,夫差大怒,又亲自过去斩了伍子胥首级,处理了他尸体。
这便是*与加诛的区别:你老实*,就不祸害你尸体,许还留你全尸;你不识相,就让你死无全尸。
后来勾践要文种*,也只是赐剑,连声责罚都没有,但文种就懂了:*吧,也没多说,省得还要尸体受罪。
范蠡更聪明,早就溜了。
吕不韦独揽大权,到嫪毐出事,吕不韦自己遭流放时,嬴政给他敕书:
“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
乍看只是两句反问,但在诏书里,这是很严格的口吻了。吕不韦便明白了,不劳秦王动手,服毒*。
哪位会问了:伍子胥和文种若不*,吕不韦若不服毒,是什么下场?
商鞅嫪毐荆轲,那都是体解车裂——反正就是分尸。
到汉时,这套不劳君王动手、自己领会*的制度已经成型。因为汉时重儒,《礼记》成篇;又汉文帝废肉刑,身体侵害少了一点。刑不上大夫嘛,大家彼此留面子。
比如汉文帝要杀薄昭,然而薄昭是太后母家血统,没法直接杀,薄昭又不肯*;汉文帝便让大臣们穿了丧服去给他哭丧,逼薄昭*。
后来孙权要杀陆逊,是派人去责骂,所谓:
“累遣中使责让逊,逊愤恚致卒”
——孙权不停派人去骂陆逊,意思很明白:你怎么还不死?你怎么还不死??你怎么还不死???
所以陆逊所谓愤怒而死,意思也明白得很了。
比较优雅的赐*,像《三国志》里,陈寿要给曹魏留脸面,说荀彧“以忧薨”,忧虑而死,曹操谥了他个敬候。
“明年,太祖遂为魏公矣”
这个“遂”字,用得很巧妙:于是、就、顺心如意。荀彧忧死,曹操顺心如意当了魏公。
“至濡须,彧病留寿春,操馈之食,发视,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
看,如果你学薄昭般不肯死,催命使者会不停上门来逼你。
你如果如荀彧般,看见空盒子就乖乖*了,连史书上都会给你留面子,君臣之间不失体面,还有谥号呢。
当然,催命的不止是使者。李广因为出征失道,眼看要被卫青责罚,即将下狱面对刀笔吏,于是*。
哪位会问:刀笔吏有多可怕?比死还可怕?
如果不及时*,要面对酷吏审判了,会怎么办呢?
汉景帝时,周亚夫为丞相,汉景帝已经看他不顺眼了。逮住个机会,说周亚夫儿子为了给他陪葬买盔甲、苛待雇工。
汉景帝先遣使询问,周亚夫拒绝回答——如果这时周亚夫及时*,情况会好些。可惜他是个直性子。
于是汉景帝让廷尉以谋反罪审案:一个丞相当了阶下囚,当然没那么舒服了。
廷尉:你买盔甲是要谋反吧!
周亚夫:我买盔甲是为了陪葬!
廷尉:你在活着时不谋反,死了也要在地下谋反!
但在狱中,没有白绫鸩酒长剑,要*没那么方便了:于是绝食五天,吐血而死。
他一个军人世家出来的太尉,真正在军营战功赫赫,平吴楚七国时账下大乱都不动如山的将军,到这时都撑不下去了。这时要死,没有白绫和长剑用来自裁,只好绝食饿死。那是漫长而痛苦的死法,但他确实没得选。
这还是汉景帝,“文景之治”的汉景帝。到武帝朝,酷吏横生,张汤和他的徒子徒孙们手法华丽多样,庄青翟这路*,又没有周亚夫坚强,所以一被责罚,立刻干脆*了:
能自由选择死法,比绝食吐血饿死之类好多了。
当然,除了*,还有许多优待。
李秀成投降曾国藩后,写数万字自供书。赵烈文记述道:李秀成被曾国藩斩首前,还说
“中堂厚德,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生图报。”
被斩首还感恩?只因为太平天国其他诸位被擒,那都是凌迟。所以天京城破前,太平天国许多重要干部都及时地病死了——其实是*。
而李秀成之死,是被曾国藩“免凌迟。其首传示各省,而棺殓其躯,亦幸矣”。
喏,所以赐死也分等级排列的:
暗示*最优雅,参考荀彧。
逼*很留面子,参考薄昭。
赐*是相对体面的,参考文种。
斥责令*稍微吓人点,参考吕不韦和陆逊。
廷尉逼令*已经很痛苦了,参考周亚夫。
你无法*,必须处刑了,就很痛苦;曹操恨吕布,所以先勒死,再斩首,让他尸体受两茬罪。
最痛苦的自然是车裂与凌迟。所以吕不韦赶紧*免得车裂,李秀成感激曾国藩免得凌迟。
现代人自然觉得,古代人被责让就*,真是奇怪:那是因为不了解,古代的残忍统治者有多少暴力,可以对一个人及其亲族的肉体施展。
毕竟千古艰难唯一死。能让那些人精们主动*,甚至到后来明清被赐*还有谢恩的,那自然是:
有比让你*,更残忍的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