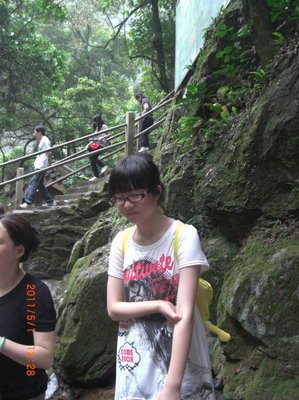剑男:与己书
我不再是那个踏浪的游子
也不是那个踏青的少年
我不再回到任何一个春天
如果要回去,我要拆掉它的院墙
铺得有多么奢侈,花开得有
多么恣肆,看树有多么庄重
风有多么轻佻——
如果允许我奔跑
在上面种花、种草、种树
即使明知是徒劳,我也要
用尽毕生的力气把他们赶到了天上
(2015)
魏天无:不应当停止想望,
不应当泯灭“一意孤行”
倘若说,在20世纪末至本世纪的最初十年间,诗人剑男书写乡村的诗作是华兹华斯意义上的“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是寄居在城市庞大而空荡的躯壳里,因心灵无所依托而回首往昔乡村生活的结晶,那么,他的近作中的回忆/回溯则是在不断返身乡村现场的所思所想所感;乡村的现实激发他的想象和联想,这现实也让他既以山中人也以局外人的双重视角来观察和思索,并因此进入对自我生命历程的反思。现代文学艺术是对人的现实存在的勘察,为此需要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空中逡巡;现代诗在这种勘察中追问自我的价值和意义:既是古典、现代哲学意味上的“我是谁?”,也是后现代哲学意味上的“谁是我?”。因此,“藉意”这样一个源自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并在里尔克手上发扬光大的诗观,在深受20世纪80年代大学校园文化和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熏染的诗人身上再度复活,是自然而然的。“藉意”的核心是藉由描绘外在世界来反映诗人的内心世界。[1]只是现在,这个外在世界虽然依旧动荡不安、魂不守舍,但在诗人的文本中,幕阜山以它风云际会中的沧海桑田,以它孤寂落寞中的坚忍倔强,以它的无言无语、不喜不悲,让人低首,让人羞愧,也让人感发,让人心生要守住一个更其卑微、渺小的自我的执念。
《与己书》(2015)肯定不是诗人反思自我的开始,但它包孕着反思的基本指向:“不再是”“不是”。它依然偏重于直抒胸臆,带有诗人早期诗作的唯美气息和理想主义情怀。诗中出现的物象并不具有特殊地域色彩,也没有诗人后来诗作中对物象的具体称名。它们可以出现在任何一首诗中,并且在任何一首诗中,踏浪与踏青,院墙与栅栏,花与风与树,蓝天与白云与羊群,其寓意都不会随语境起太大变化。然而,正是靠着这些可为任何人所用的寻常物象,诗人却构建起独具个人色彩的梦幻世界。其中最动人的,是“我”诚恳的、坚执得有些决绝的语调;在诗作末尾,诗人让“你”——我们——随“我”的目光去看蓝天,这“有人”中包容着现在的“我”对未来道路的期许,也涵括着“你”对超脱世俗的梦想的追求。不应当停止这种想望,不应当泯灭这种“明知是徒劳”的“一意孤行”——诗人是对着自己说的,那个“你”也不妨理解为“我”的投影,但肯定无意中轻轻拨动了许多读者的心弦。
[1] 关于“藉意”,参见唐际明《“窗”在里尔克作品中的诗学含义》,《上海文化》2016年11月号。
节选自魏天无《新世纪诗歌中的乡村伦理与诗学伦理——以剑男的诗歌写作为例》,《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4期
图片除诗人肖像外,为魏天无手机摄影,拍摄地依次为:甘肃山丹军马场、甘肃张掖平湖大峡谷、青海南部至四川途中
真无观:与他者比邻而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