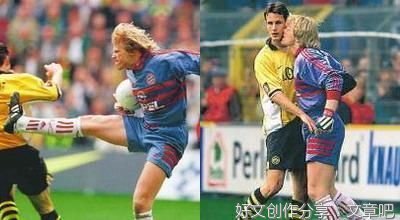
《阿尔伯特·卡恩的理想国:黑白时代的彩色世界史》是一本由(英)大卫·奥库夫纳著作,金城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68.00,页数:35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阿尔伯特·卡恩的理想国:黑白时代的彩色世界史》读后感(一):阴影下的色彩
卡恩的摄影师们为重要的历史节点所记录下的影像,让历史栩栩如生。希腊总理和凯末尔的肖像让人觉得没有距离感,而背后是巴尔干的哀恸。战争魅惑又真实的场景,躲在树洞中的难民,牲畜车厢里的人们,忧惧不止在当时的人群中散布,也透过纸背感染着我们……“地平线蓝”出现前招摇的红裤,伦敦胜利大游行的全景图比所有繁琐的会议更令人印象深刻。
作为“环球档案”赞助者的卡恩有非凡的眼界——采集者不需要盲从他的指导,摄影师可记录下那些真正吸引他们目光的内容。卡恩务实、乐观、开明,他实践理想主义的方式之一是执着地记录世界上第一批彩色影像,构筑理解的桥梁,提醒人们全球化所带来的破坏性,亦质疑生产力的进步最终究竟为何服务。而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其一生都伴随着战争的阴影。
卡恩的资料提醒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印象:与如今富饶的欧洲不同——在北欧和意大利,当时许多地区经历着长期人口流失带来的凋敝,让一个真实的欧洲从新闻,从文学作品,从当今回望的想象里走出来,对于我们加深理解大有帮助。不同文明之间的人们看似因服饰和外貌有着鲜明区别,但又亲切地统属于生活这一主题之下。
老照片本身的魅力并不需要更多言语,所有的影像都带着灰蓝色调,又比点彩油画更真实细腻。在无数迷人繁复的民族服饰中,你还是会被维罗纳教堂地下室沉思的小姑娘吸引。还有一位又帅又美的加拿大女牛仔……即便是今天人们也会盛赞她的时尚。
古迹爱好者会看到Alberobello的锥形屋100年前的状态,历史名村圣埃米利永村庄的农民,吴哥窟的彩色全景,锡耶纳主广场,还有未被机动车占领的纽约,但多数图像都带着沉重的历史背景——一战中被炮火轰炸过的兰斯大教堂,失序带来的震撼超出人们的想象力。可以把这本书当作珍贵的缩微全球史,图像超越反复诠释的文字,直达人心。
《阿尔伯特·卡恩的理想国:黑白时代的彩色世界史》读后感(二):旧世界的新色彩(代译序)
彩色摄影技术问世之前,直观再现旧世界色彩的唯一媒介便只有绘画。
彩色摄影时代的帷幕在1907年甫一拉开,犹太裔法国银行家阿尔伯特·卡恩(1860-1940)便启动了他那吉诃德式的壮举:创建一个名为“星球档案”的影像资料库,试图用照片为地球上的人类生活留下一份真实具象的彩色记录。而这一雄心勃勃的努力背后,寄寓着一个更为雄心勃勃的、空想乌托邦式的愿望——通过他资助的环球旅行者所带回的影像作品,来增进各个国家与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用彩色照片这一社会教化工具,来推广传播国际主义与和平主义理念,以此预防和阻止各民族间的冲突纷争。
卡恩的设想固然美好,但遗憾的是,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他的图谋不出所料地落空了:从童年直至离世,他一生都伴随着战争的阴影,尤其是他生命的后半程,也即二十世纪上半叶,一战二战都是人类恐怖编年史上最惨烈的篇章。
无论如何,卡恩的付出是有意义的。虽然他的个人理想被现实无情地碾碎,但他的“星球档案”影像资料库却为所有后人留下了一份难能可贵的遗产,让我们看到那个“黑白”旧世界的新色彩。
一百年前的地球人类生活形态,与一千年前的相比,或许并无质的改变,依旧是“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人”;那时的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仍然在承受着社会创痛与经济窘困的双重煎熬。
但如今的爱尔兰人,早已不再是穷得只剩下“奶和屁股”,而北欧瑞典丹麦的民众们则享受着可谓是这个星球上最高的生活水准;连“脏得令人厌恶”的远东中国也在物质意义上庶几完成了现代化。所以,眼下这个以高速运输与实时通讯为显著特征的商品化消费时代,与一百年前相比,早已是天壤之别。
而上世纪初环球旅行之艰辛及费用之高,也与今日芸芸众生“看世界”的休闲海外游是完全迥异的概念。
我们因此要更加感激卡恩那不可救药的“天真”。正是由于他的孤注一掷与狂热,那个如今看来已经感觉无限遥远、模糊和陌生的旧世界,才得以系统地展露她当初的真彩形貌。
卡恩离群索居、不婚不娶、倾尽个人财产,只是为了给各国的年轻学者提供经费,资助他们去海外旅行,增广见闻,更好地体验和认识各地文化的差异性、多样性。他聘任专业摄影师远赴亚非欧美几大洲的每个角落去采访拍摄,所诉求的,依旧是对不同人类群体各自生存方式的理解与尊重。卡恩如此慷慨解囊,将这一义举延续长达二十多年,并且在金融危机导致其财富严重缩水乃至破产之后,仍苦苦坚持,而支撑他的动机或信念始终是那样单纯、朴素——用宽容去化解民族种群之间的对立分歧,用善意去消弭文化体系之间的嫌隙龃龉。
这是一位顽固偏执得令人肃然起敬的理想主义者,因其理想的“幼稚”而越发可敬。卡恩在他的时代积聚起不可思议的资本,然后又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散尽千金,写就了独特的人生传奇篇章。
如果说,人活着就是个体生命与身外世界建立关联的一个持续过程,那么,通过对二十世纪初叶全球各地人类存在图景(包括人文环境、民俗风情、日常经验、苦难与战争)的彩色化呈现,卡恩无疑是与当年人力物力条件下所能及的一个最广泛的世界建立起了一份令人感慨玩味的深刻关系。
安德鲁·卡内基曾有言,“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这位美国钢铁大王、“公益之父”也践行了自己这一掷地有声的高格调宣言,临终前将全部家当捐出——尽管有人数远为更多的富豪们宁愿选择耻辱。而晚于卡内基二十一年死去的阿尔伯特·卡恩,则在辞世之际的十年前便提早摆脱了这一耻辱。
英国著名脑神经学家、作家奥利佛·萨克斯(Oliver Sacks,1933-2015)被《纽约时报》誉为“医学桂冠诗人”。在一篇名为《我的一生》的短文中,他曾颇为感伤煽情地写道:过去的十年间,我的同龄人陆续离世。我这一代人正在消失。每当他们有人走了,我就会有一种自己的一部分被撕裂的感觉。当我们走了,没有人会再像我们这样。这个世界上也永远不会有人能像其他人一样。当人们死了,他们无法被取代。他们留下了不能被弥补的缺口,因为这是命运——遗传和神经的命运——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找自己的路,过自己的日子,最后结束自己的一生。
一百年前,当卡恩审视“星球档案”中他的同代人影像时,心中泛起的,大概也是与萨克斯同样的悲悯情怀。
能够去感知、关爱、珍视和怜悯,便是人道。虽然,这人道的荆棘之路常常沦于迷乱与荒芜。
即使在西方世界,知道卡恩的人也并不多,更不必说是在东方。卡恩曾于1909年1月来过中国,但只是短暂逗留。好在,几年后他派往中国、蒙古和越南的摄影师为我们留下了聚焦于这一区域的珍贵彩色影像,而且数量品质都相当可观。
现在,让我们来欢迎卡恩重返中国——以一本图册的形式。
译者
2015年11月
《阿尔伯特·卡恩的理想国:黑白时代的彩色世界史》读后感(三):时间的质地
已于2020年7月发表于中国科学报文化版
二十世纪上半叶是近现代历史的重要关口。技术的发展、政治和社会的革新将文明拔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进步并未带来幸福,两次世界大战相继发生,将整个世界拖入了一个集体噩梦,人类不得不以一种悲剧性的方式进入现代。今人回顾那段历史的时候,往往将哈布斯堡王朝的崩溃,东方与西方的碰撞,以及大战的阴云置于核心位置,但这种基于传统断代方式的“后知之明”,拉大了我们与先辈的距离,对于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并无实质帮助。要想获得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我们必须要选择一个个人视角进入历史,而这个将眼睛借给我们的人,必须同时具有特殊性和典型性,他的身份、阶层、知识水平、道德准则更决定了他的视野,和他希望呈现给我们的世界。
最近出版的《黑白时代的彩色世界史:阿尔伯特·卡恩的理想国》便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为宝贵的审视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的视角。这本书可以说是一部宏大的集体摄影作品,它将二十世纪初的各块大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平等地摆在同一个层面,从新闻报道到家庭纪事,从公共领域到私人领域,均有涉猎,将一个立体的世纪之交呈现在纸上。
文明的琥珀
这本二十一世纪出版的图书,其内容的基础是一个二十世纪初的,即书中所呈现的那个年代的文化项目。阿尔伯特·卡恩便是这个项目的策划人和赞助人。卡恩出生于1860年,在项目开始实行的1907年,正值中年的他兼有多重身份: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甚至可算是当时欧洲最为成功的商人之一;他是一个知识分子,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著名法国哲学亨利·柏格森是他一生的朋友;同时,他也是在欧洲备受歧视的犹太人中的一员。身份的多重性使他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格外敏感,或许在他看来,这是巴别塔倒塌之后,人类所面临的唯一问题。因此,当他有了财富与地位之后,他便致力于教育各国家、各民族的人们学会理解和欣赏不同文化、不同语言和不同生活方式的他者。在他看来,人类能够认识的唯一真理,就是并不存在唯一的真理,只有在接受并包容了差异之后,在多元的背景下,一个真正的大同世界才会到来。
1907年,卢米埃尔兄弟发明了玻璃干板彩色正片工艺,这标志着摄影进入了彩色时代,但那个时代,彩色摄影仍然极少被应用。阿尔伯特·卡恩作为塔尖阶层的一员,才能成为最早见证和尝试这个光影魔术的人之一。在他看来,彩色照片和黑白照片的区别是巨大的。相纸呈现了与眼中所见一致的色彩,这意味着真正的再现,意味着没有失真的视觉传达成为可能,意味着相距遥远的人们能够感受一样的风景,这对他来说极具启发性。
作为一名国际主义者,或者说世界主义者,卡恩笃信媒介的力量,他认为,如果想要在平等和理解的基础上融合这个四分五裂的世界,有关传播的问题至关重要。于是,他组织了一批摄影记者奔赴全世界各个大洲,在五十多个国家长期驻地拍摄。这一计划从1908年开始,共实行了二十多年,直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因为卡恩的破产而终止。
这一前无古人的壮举为全人类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其中包括超过72000张照片和120个小时的电影胶卷。这些不可替代的影像资料就像一些精美的琥珀,将一个业已逝去的世界封存在里面,向我们展示了人类文明的重要一页。
“星球档案”
以彩色摄影技术为整个世界立传,这只是阿尔伯特·卡恩用以构造他的理想国的整体计划的一个部分,或者说,一个步骤。而相对于他浩如烟海的影像收藏,《黑白时代的彩色世界史》一书中收录的摄影作品又只能算是九牛一毛。一本书的容量实在是微不足道,但正因如此,作为读者的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历史”究竟是什么。对于这个我们总是津津乐道的词汇,我们即使不是一无所知,也不过只握住了一粒尘埃而已。人之所以狭隘,原因大多在于将自己的一点所见错当作整体全局。其实,历史如宇宙般浩瀚,哪怕只是一个瞬间的切片,也是无限。也许,在启动项目的时候,卡恩也产生了这样的时空联想,因此,他将他的计划命名为“星球档案”。
可以说,卡恩的宏大构思实质上是一个梦想,他倾尽所有,所为的并非实现它,而是不断地去接近它,行动本身的意义甚至要重于结果。在这样的前提下,他显然不能够对摄影师的工作提过多要求、做过多干预。因此,这些照片所呈现的内容极为芜杂,在题材和审美取向方向均存在差异。然而,这正与阿尔伯特·卡恩的以包容差异为主旨的世界主义理想相吻合。
翻开《黑白时代的彩色世界史》一书,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中国、印度、日本和土耳其的人像摄影;能看到在希土战争中被摧毁的古城士麦那;能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法国士兵,也能看到他们的敌人——德国士兵;能看到印度土邦君主的奢华宴会;能看到自家门前睡着的法国小女孩;能看到伦敦的大街和挪威的小村;能看到发生在1923年的一起凶杀案的现场;能看到1912年的某天清晨,巴黎街头卖花小贩的装满鲜花的推车。
所有这些图像,或严肃,或轻松,或关乎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或仅仅记录了普通人的一个平凡的瞬间,但每一张都不可替代,因为其中的每一人每一物都曾真实存在,都是历史的一部分。
时间的质地
阅读《黑白时代的彩色世界史》的感受十分特殊,那是一种混合了愉快的惆怅——这或许是最佳的阅读效果了。而造成这种感受的主要原因是遍布全书的沧桑感。作为一本历史摄影集,《黑白时代的彩色世界史》至少在两个层面给人以这种独特而强烈的时空体验。
其一,自然就是作品本身。这些作品的拍摄初衷本身就是践行文化传播的使命,因此,每一幅作品都像一张玻片,保留了最为鲜明的时代特征。另外,在摄影技术刚刚兴起的时代,摄影师们秉持着承袭自古典绘画的艺术理念,与后来的新闻摄影或商业摄影有明显不同。因此,这些作品大多有着近似于油画或水粉画的质地。
第二,这本书的背景以及阿尔伯特·卡恩的个人经历从侧面给这些照片增加了人文色彩,使之更具震撼力。这让它不仅具有特殊的文献价值,更在一个世纪之后,为一个伟大而无名的人文主义者奏响了一曲动人的挽歌。
因此,《黑白时代的彩色世界史:阿尔伯特·卡恩的理想国》这本书及其背后的故事值得被我们珍视,它提醒我们,赋予历史色彩的不仅仅是技术的发展,更是理想主义的坚持。那些执拗地为梦想而奋进的堂吉诃德们,也许生前潦倒,但历史终究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为他们加冕。
《阿尔伯特·卡恩的理想国:黑白时代的彩色世界史》读后感(四):用镜头缔造世界和平
书评人:林建军
《阿尔伯特·卡恩的理想国:黑白时代的彩色世界史》
熟悉艺术史的朋友都知道,相机的出现改变了艺术史的走向。画得“像”让位于画得“传神”,务求毫厘不差的肖像留影,被交给了技术不断进步的相机。印象派、抽象派、野兽派趁机兴起。不过,与此同时,用《阿尔伯特·卡恩的理想国:黑白时代的彩色世界史》 作者大卫·奥库夫纳的话说:“在同样的时段,同一处地方,另外一场革命也正在展开。”
那是1907年的夏天。毕加索的《亚维侬的少女》问世。这幅人物肖像作品动态感强烈,极富戏剧性;画面中,身处风月场所的五位少女嬉戏笑闹,尽管“画得不怎么像”,但少女们挑逗嬉闹,极尽其韵。作者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指责。而同年的6 月10 日,在巴黎《插画》(L’Illustration )周报的办公室,发明家奥古斯特(Auguste)与路易·卢米埃尔(Louis Lumière)两兄弟第一次向公众展示了被他们称为“玻璃干板彩色正片”(autochrome)的摄影成像工艺。
这一技术的原料非常简单:土豆。基于一种主要由土豆淀粉制成的微粒体复合物。通过在平面玻璃板上涂抹双层经过染色的土豆淀粉涂层,并在中间加入全色性乳剂和碳粉,利用常规的玻璃板成像相机,便可以拍出色彩真实的照片。这让“创作彩色图片”这件事,变得异常便捷和容易——挎上一台相机,可以走遍大江南北。艺术家不用再让当地人长时间摆出姿势,便能画出《塔希提少女》或《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哪里去》。咔嚓一下,便可以记录当地最真实的生活劳作瞬间。卢米埃尔兄弟的发明,不但在摄影艺术上开启了彩色照片的时代,还为“走出去,看世界”的人类本能,提供了既便宜家常、完成度又极高的解决方案。对此,美国摄影师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兹(Alfred Stieglitz)预言道:“整个世界很快将疯狂地沉迷于彩色。对此番狂热风潮,卢米埃尔兄弟功不可没。”
斯蒂格里兹并非意识到玻璃干板彩色正片那令人兴奋的美好前景的唯一一人。法国银行家阿尔伯特·卡恩也意识到,摄影正跨过了一道门槛,门槛后是一个充满创造可能性的新世界。更重要的是,这些摄影技术也许能帮他实现珍藏已久的政治理念。卡恩是一位国际主义者,他相信世界不只是凯旋门和香榭丽舍大街这一种模样——当年高更出走时也许也这样想。此外,卡恩还是和平主义者,他希望找到预防和阻止各民族间冲突纷争的途径。很多年来,他每周都在巴黎近郊举办聚会,邀约欧洲政界、商界、文化界与学术界的杰出精英人士共聚一处,商讨“天下”大事。
卡恩相信,如果人们能够理解,这个世界上和你不一样的人,也有权利好好活着,也许这世间会平和许多。他希望,通过交流,能够让人们对多元文化有更多的共情,意识到那些语言、肤色和习俗不同的人们,其实和自己一样有寻常的喜怒哀乐。那些黄种人、棕色人种和黑人,和“高贵”的欧洲人一样,每天吃喝拉撒,也会生老病死。他们也有着文化消遣和市场交易,有着婚丧嫁娶和长幼人伦。这一切与站在“世界文明与话语权顶端”的白人没什么两样。那么,这些世界尽头的“非我族类”,也许就不该被轻易妖魔化为“他者”,就不该如此随便地成为枪炮奴役的对象。
彩色摄影技术的发明,让卡恩和平主义的想法得以成为现实。这位投资南非黄金和宝石矿山成功、欧洲屈指可数的富豪,此时已经对跨国银行结算、发行国际公债没有那么热心了。从1908年开始,他倾注了大量的资产和心血,派遣大量摄影师去世界各地,采用当时最先进的彩色摄影技术,拍摄了72000余枚彩色照片,记录了二十世纪初叶,50多个国家的民众,在时代变迁的浪潮席卷下的日常劳动、娱乐、传统仪式。其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各地的民族文化、生活发生急剧变化。卡恩的摄影师们帮助他实现了建立地球史料馆,保留此时此刻世界面貌的愿望,更在有意无意间参与并记录下了各个年代的代表性事件,捕捉了无数宝贵而不可再现的瞬间。
法国兰斯,1917年4月1日卡恩影像档案中最感人的场景之一:这位踩单车的传令兵停在兰斯的皇家广场上进食午餐。尽管同盟国在西线战场搭建了有固定线路的电话网络,但在敌方的炮火轰击下,这个电话通讯系统总是屡屡中断。有很多场战役,跑腿的或踩单车的传令兵才是最快速最可靠的通信方式,可将讯息
镜头下,巴尔干地区新国家和新政权不断涌现,并且正在掀起数次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军人和原来的“殖民地伙伴”在西线战场并肩作战。1918年的停战协议签订后,巴黎到处是狂欢喧闹的庆祝活动,而摄影师们也置身其中。整个1920年代,亚洲与中东地区的人民为自主自治而战。卡恩的摄影师们也用照片记录下了那些国家缔造者为建立现代政权而进行的努力:穆斯塔法·凯末尔和叙利亚领导人费萨尔埃米尔都出现在他们的镜头中。在这个时期,储量巨大的成片油田被发现,一夜之间改变了中东地区的经济与战略地位。照片中,英国首相阿瑟·鲍尔福因支持创立一个新的犹太人家园,在访问巴勒斯坦时,激起了当地民众的强烈反应。同一时期,伊朗的军事政变将新的国王推上政坛不久,卡恩的摄影师便造访了该国,记录了那位国王富有深意的表情。第三次英阿战争之后的几年间,摄影师们也深入阿富汗,用影像捕捉当地的现实生活。
不仅如此,卡恩的摄影师们还在继续向东方开进,他们用镜头记录了日本天皇去世后举国哀悼的悲伤时刻,还有印度大君举办佳节狂欢派对时那生机勃勃、流光溢彩的壮丽场面。在亚洲,卡恩的摄影师们所定格的许多影像为一个正在消失的世界留下了纪实档案。他自己也身体力行,甚至于1909年1月来到中国。此时,慈禧太后刚去世,溥仪登基,醇亲王执政。在23天的时间里,卡恩游历了中国多个地方。摄影师的镜头记录下了帝制被推翻前的中国,这也是记录中国最早的一批彩色照片。当时,全球范围内,在欧洲文明的影响下,各地的传统与文化都持续地遭到了毫不留情的侵蚀。一切生产方式、文化语言、宗教礼俗和服饰习惯都在西方“文明”洗礼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现代化”,趋于同化。用作者奥库夫纳的话说:“这份影像档案,其中至少一部分的意图便是,抢在世界上那些易受伤害的脆弱文化永远消失之前,用图像记录下它们那最富生命力的、生动鲜明的重要特色。”
不过别忘了,卡恩的摄影师们绝不是在收集异国风情、温情脉脉而小确幸的世外桃源,他们造访过的那些国家中,对那里的很多人来说,生活是残酷的,是贫乏、穷困和痛苦的集大成者。用作家A·N·威尔逊(Wilson)的话说,“这一段历史时期中,人类彼此屠杀,而且伤亡之多,史上为最”。卡恩热切地关注时事新闻,肯定也意识到了暴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存在。实际上,很可能是他青少年期的战乱经历与他对世界各地动荡风波的认知。正如杰伊·温特所推测的,“或许是好望角地区那利润极为丰厚的矿产开采提炼行业背后所伴随的种族剥削与压榨,也或许是日俄战争那血流成河的场面,让卡恩对未来产生了忧虑恐慌:如果生产力的进步得不到引导约束,不为和平目标服务,会怎样?或者,他是否在1890年代遭受了‘道德上的危机’,良知的谴责让他去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活信念与人生使命?”
总之,无论是因为其财富来源导致的负罪感的冲击,或者是对基于世界多样性的和平主义所持的信仰或热忱,卡恩的摄像师们在二十多年内从未停止过奔忙。当然,这一项目代价高昂,需要无数的财力物力。不过,巨大的费用并未让卡恩气馁畏缩。他预计过,将会有充足的经济手段来无限期地维持这一事业。然而,风云变幻让他的计划遭到了致命的重击。1929年刚开始之际,卡恩还掌管着一个令人羡慕的金融帝国,特别是以政府间贷款业务的熟练操作而知名。但是,到了那一年的年底,华尔街股市崩溃,这位欧洲最成功的银行家也陷入危机。而他的“地球史料馆”计划也遭到毁灭性打击。失意的他(作为一名犹太人)于1941年底,在德军占领下的巴黎黯然去世,唯一留在他身边的,是这一批庞大的映像收藏,历经近百年在这部《阿尔伯特·卡恩的理想国:黑白时代的彩色世界史》中与你相见。
本文转载自:凤凰网 http://feng.ifeng.com/c/7y9irRBLQN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