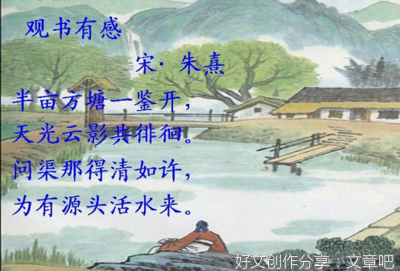
《观书辨音》是一本由徐冲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8,页数:3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观书辨音》读后感(一):再論苻堅“璽已送晉,不可得也”
我曾撰一小文(《苻堅“璽已送晉,不可得也”再議——兼與徐冲先生商榷》 ),指出《晉書·苻堅載記》中“璽已送晉,不可得也”指的是此時傳國璽早已送回東晉朝廷,苻堅手上並無,自然無從將其交給姚萇,徐沖老師將這句解讀為書寫東晉正統性的結果當是有所偏差的。其實《晉書·與服志》早已交代清楚:“及懷帝沒胡,傳國璽沒於劉聰,後又沒於石勒。及石季龍死,胡亂,穆帝世乃還江南。”傳國璽歸於東晉乃是永和八年(352年),事在姚萇逼迫苻堅求璽(384年)三十多年前,此後再未流落北方,因而苻堅此語確實不是表示他自己已經派人將傳國璽送到東晉,這一記載確實不足以反映苻堅對東晉正統性的認可。 但是,想要將傳國璽歸還東晉這樣的說法卻並非毫無根據,《通鑒》晉紀十二太興元年(318年)條有“準自號大將軍、漢天王,稱制,置百官。謂安定胡嵩曰:“自古無胡人爲天子者,今以傳國璽付汝,還如晉家。”劉聰亂政,權臣靳準殺死劉粲,自號大將軍、漢天王,稱制,置百官,但是卻認為自古以來並無胡人為天子之事,想要將傳國璽交還給東晉朝廷,他認為自己可以為王,但斷然不足以當皇帝、天子。 兩晉時期,“夷狄不足為君”“無胡人為天子”這樣的說法非常流行,對胡人政權的建立者有一定影響。中國自古以來都有鮮明華夷之分,若胡人真的稱帝,其實面臨著士大夫階層的激烈反對,難得民心,可能會導致各路人馬的攻訐,曹操當年不面臨民族問題,但依然認為不當慕虛名而處實禍,實際上此時胡人政權的大多數領導者也是這樣的想法,當一個王就可以享受幾近於天子的地位,也不用面臨這麼大的輿論壓力,不如上書稱臣於晉,或許還能擁有在相當廣大區域內專斷之權的合法性,何樂而不為呢,靳準想要送還傳國璽回東晉,其實是一種轉嫁矛盾的避禍之法。 那麼,苻堅所謂“璽已送晉”事,很可能是後世歷史書寫者為了強調東晉正統性,而將此事附於苻堅身上,乃至全然不顧苻堅並無傳國璽的基本事實。但,即便苻堅真的有傳國璽,也真的把傳國璽送到了東晉,大概也應當是類似於靳準那樣的心思。傳國璽並不一定意味著正統性,只有被天下公認的人獲得它才能作為合法性的依據,而未被公認的人貿然依其發號施令,實際上是遭致禍端的危險品。
《观书辨音》读后感(二):关于书写的一点想法
五胡这个肯定没有定论【废话,有定论作者绝对会写出来】,暂时也没有实锤。
杂七杂八的观点里,有拿张祚那条来说明五胡仅是刘石五主,这个就比较好玩。
胡,羯,氐,羌,胡因为和后面三个分开表述,所以不是慕容氏,姚氏等等,却可以是石氏?
xswl
不巧的是,作者本人似乎也,被这种思路牵引了。
五胡次序,无汝羌名。到底指什么,我无意复读,讲书写的书,我们就看看书写。
基本上所有解释这个的学者,对连带的传国玺和后面的记载几乎都没有引起重视,也就根本无法联系不到这段书写原本可能的指向。
很明显这个东西,它就是一开始称帝的“胡”们,捏造的一个天命,亦即解释权在这些称帝的胡手里。他们的依凭是什么呢?正是传国玺。
冉闵灭石氏,姚弋仲绝望,慕容儁封奉玺君,称历运在己,这已经很能说明“五胡次序”与传国玺的某种关联。
所以姚苌先求传国玺,旨在复现慕容儁故事,而苻坚才以“无汝羌名”“玺已送晋”回答,是为了绝姚苌之望。【有冉闵慕容永的例子,东晋结盟前秦顺个玺什么的,也是有可能的】
接下来的书写,再有尹纬说禅让之事。这段记载,与前求传国玺为一体,正是书写者的原意。
苻坚对五胡次序的解释,以及姚苌退而求次的要求禅让。都说明,通过对前燕所存“传国玺”的继承,苻坚本人【或者说此时的前秦政权】是在五胡次序里的。
五胡次序出现之时,慕容儁苻坚未必存世,这个是以结果论,恰好是一种后见之明。
所以,当晋宋之际,旧时诸胡纷纷退场谢幕之时,这种“天命”为敌对方所用,反而宣称其命数将终,也就不足为怪了。
一点浅见
《观书辨音》读后感(三):书写的历史也需“辨”
昨日读完《观书辨音:历史书写与魏晋精英的政治文化》,徐冲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10月1版1印,16开平装318页,定价78元。本书为“博雅史学论丛”系列丛书之一。
所谓“观书辨音”者,“书”为史书,即史料。中国是历史源远流长的大国,史料纷繁,古人也以作史为好,以求青史留名。这对后来者既是好事,可免史料不足之苦,也是苦事,史料众多,同一事件同段时间说法不一而足,不同史书不同作者,受限于史家之个人史观,同时史家作为社会人,不能在社会真空中写作,尚需叠加是时之官方史观,以及情势下内外力量之博弈,才造就了一卷史册所展示出来的“书的史观”。所谓“辨音”者,就是需要后人进行史料的综合分析、判断,方能辨识出史家通过史书所发出的独有的“声音”。正如本书作者所言,“在研究......历史时,将...佚文作为史料库,视自身研究需要加以援引或辩驳,......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其结论的准确性。”(p4) 这个论断,对于许多史学研究来说,可谓是一针见血之论,也是后来者需时刻警惕之事了。
本书分为三大部分,《“献帝三书”》篇、《续汉书.百官志》篇和《劝伐河北》篇。主要集中在对历史书写进行讨论,与所读的前一本《叙述观点与历史建构——两晋史家的“三国”前期想象》可谓是选取了不同阶段的历史文本进行解读,方法论也较为相近,不过优势在于考据更为精当,若说不足,则由于文本跨度较大,内容较散,本来也是作者集不同时期的论文所作而成。于政治史而言,作者把荀彧当作汉魏转换时期的核心人物看待,认为荀彧使命的开始和终结,标志着汉魏时代的转换,这虽然不是新论,但是依然是解读很多汉魏史的不可违阙的一点。其实,从袁、曹两阵营对待流亡的献帝的策略可以看出,双方都有重要人物看出献帝的重要性。袁营中沮授、曹营中荀彧都提出过迎献帝的主张,不管是“奉天子以讨不臣”还是实际操作中“挟天子以令诸侯”,正统问题始终是汉末群雄所不能回避的,也就是说要解决“我是谁”的问题。但是袁氏阵营中迎接献帝的策略当受到质疑后(以后怎么对待皇帝:远之则怨,臣之则不愿),作为主要主张者的沮授也拿不出具体的应对方案,而荀彧作为心怀汉室的曹营核心人物,则只需要“奉天子”就足够了,至于未来权力如何更替,在当下可能无人思考那么复杂悠远。历史就是这么曲折蜿蜒,谁也不能一下子看到一个清晰的未来。所以袁营之人未能想出全盘计划而不行动,曹营却是先行动再筹划后续步奏,棋差一着,就满盘皆输了。当然,这是与本书主题无关的一点余论了。
本书正文之外,尚有三条附录,其中《“禅让”与魏晋王权的历史特质》一文甚有启发,尤其是对陈寿《三国志》中出现的一个特别的板块“开国群雄传”进行了精辟的解读,认为这是“通过标示新王权的“驱除”之所在,来最大化创业之主相对于旧王权的“功臣”身份,以正当化“自臣而君”的身份转换过程”。这一论断可谓卓识。稍显遗憾的是,似乎本文未曾关注卫广来先生的《汉魏晋皇权嬗代》一书,稍显遗憾。
最后有趣的是徐冲老师的后记,除了常规的致谢导师、家人以外,也把研究汉魏晋隋唐的大部分专家都鸣谢了一遍,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名人济济一堂,难怪有朋友说这就是徐老师的朋友圈了。哈哈哈。
值得一读。
《观书辨音》读后感(四):关于五胡部分的一点杂感
今讀徐冲先生新作《“五胡”新詮》,其在文章第一部分對《晉書·苻堅載記》中苻堅與姚萇對話的內容進行了史料批判,他認為:這個故事本質上是圍繞“姚萇向苻堅求傳國璽遭拒”這一主題而展開的。姚萇所言與苻堅所答,都共同服務於這一主題,最終的指向是“璽已送晉,不可得也”。如所周知,傳國璽在當時爲正統之象徵。真僞姑且不論,將傳國璽送至東晉的行爲顯然意味着對東晉正統性的認可。换言之,這一故事在渲染苻堅威武不屈形象的同時,也達到了書寫東晉正統性的效果。反過來自然也否定了前秦以及後秦的正統性,至少是將前秦的正統性置於東晉之下。 然則徐氏錯誤分析了苻堅“璽已送晉,不可得也”的真實含義,因為傳國璽早已在永和八年(公元352年)八月便由冉閔之子交給都護戴施,並由其送於晉穆帝,自此之後並未流到北方,苻堅從未擁有過此傳國璽。 傳國璽便是所謂以和氏璧鑄成的天子之璽,《漢官儀》云:“子嬰上始皇璽,因服御之,代代傳受,號曰漢傳國璽也。”衛宏曰:“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后乃出以投地,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時,仍帶璽紱,杜吳殺莽,不知取璽,公賓就斬莽首,並取璽。更始將李松送上更始。赤眉至高陵,更始奉璽上赤眉。建武三年,盆子奉以上光武。孫堅從桂陽入雒討董卓,軍於城南,見井中有五色光,軍人莫敢汲,堅乃浚得璽。袁術有僭盜意,乃拘堅妻求之。術得璽,舉以向肘。魏武謂之曰:‘我在,不聽汝乃至此。’”時璆得而獻之。”後魏文帝受漢獻帝禪,司馬炎在此後又受魏禪,此傳國璽傳承有序,《宋書·禮志》載:“晉懷帝沒胡,傳國璽沒於劉聰,後又屬石勒。及石勒弟石虎死,胡亂,晉穆帝代,乃還天府。”《晉書·元帝紀》有“劉聰故將王騰、馬忠等誅靳準,送傳國璽於劉曜。”《晉書·穆帝紀》載“冉閔子智以鄴降,督護戴施獲其傳國璽,送之,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百僚畢賀。” 以上諸條勾勒出傳國璽自曹魏到劉宋以來的流傳過程,未見任何其流落到苻堅處之記載,因而並不存在苻堅敗亡前將傳國璽送到東晉一事,苻堅只是表示傳國璽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經送到了東晉,他這裡並沒有傳國璽,姚萇自然無從得到。此處苻堅絕對沒有承認東晉正統性的意思,這段記載恐怕也本無服務於政治正統性而刻意構建苻堅送璽自我貶低而承認東晉的歷史書寫成分在。徐氏在其文的第一部分勾勒出《晉書·苻堅載記》出自《十六國春秋》,而《十六國春秋》的資料來源於兩位入劉宋士人所撰寫的前秦史著作這一線索,十分高明,然對苻堅此語的分析,卻未免有些求之過深了。 徐冲先生認為:晉宋之際以降建康精英所使用的“五胡”稱謂,具有相當一致的修辭特徵,即往往與“僭襲”“遞襲”“代起”等措辭連用。顯示這裏的“五胡”並非泛指匈奴、羯、鮮卑、氐、羌諸異族人群,而是特指其中曾在華北建立王朝帝業者。 按,與“五胡”連用的詞彙並不一定指向在華北建立王朝者,因為在中國古代傳統士大夫眼中,中原地區是國家的核心區,也是正統之所寄,所謂“內諸夏而外夷狄”也,《陳書·高祖本紀》云:“五胡荐食,競謀諸夏”,《魏書·天象志》有“自五胡蹂躪生人,力正諸夏,百有餘年”,五胡與“諸夏”鮮明區分開來,所指也就是少數民族族群。凡是少數民族進入中原,破壞中原地區的日常秩序,則皆被視為悖逆和僭越,《南齊書·曹虎傳》云:“七狄交侵,五胡代起,顧瞻中原”,此七狄、五胡皆與覬覦中原這一華夏核心區息息相關,而未必皆與建立王朝相關。《晉書·馮素弗傳》史臣曰:“自五胡縱慝,九域淪胥,帝里神州,遂混之於荒裔;鴻名寶位,咸假之於雜種。嘗謂戎狄凶嚚,未窺道德,欺天擅命,抑乃其常。而馮跋出自中州,有殊醜類,因鮮卑之昏虐,亦盜名於海隅。”五胡之縱匿,其結果是“帝里神州,遂混之於荒裔”,因而五胡的行為是將夷狄之風氣帶入中原地區也,在華夏士大夫眼裡,少數民族風俗對中原傳統文化的侵染是非常可怕的。《宋書·索虜傳》史臣曰:“元康以後,風雅雕喪,五胡遞襲,翦覆諸華。”這說的是少數民族一個接一個侵襲華夏之核心區——中原,《晉書·儒林傳》有:“憲章弛廢,名敎穨毁,五胡乘間而競逐”之感歎,五胡之間往往是並存且互相競爭的,他們有著共同的目標就是侵佔中原,而並非皆是為了建立王朝,所謂夷狄的侵入,導致了士大夫最珍視的價值——名教倫理的進一步淪喪,“五胡”所指代的大體就是侵入中原的少數民族族群,未必一定指代五個具體的王朝或者民族,而苻堅對姚萇所謂的“五胡次序,無汝羌名。”大體是對姚萇身份地位表達蔑視,未必意味著羌族便不在五胡序列之中。 除了以上一點淺見,我認為討論五胡具體指代的一個可行方法是找出史籍中這一時期被稱為“胡”的主要是哪些民族或政權,以及被重點提及的是哪些民族或政權。如《晉書·劉曜載記》:“置左右賢王已下,皆以胡、羯、鮮卑、氐、羌豪桀爲之。”《晉書·張祚傳》:“戎狄亂華,胡、羯、氐、羌咸懷竊璽。”鮮卑人段匹磾自謂“我雖胡夷”,《晉書·傅玄傳》有“羌胡擾邊”,《晉書·元帝紀》有“逆胡劉曜”,姚萇等皆被稱為“氐胡”,石勒等被稱為“胡羯”。據我統計東晉十六國史料,出現次數最多的被稱為“胡”的其實就是我們傳統認識的匈奴、鮮卑、羯、氐、羌這五個民族,因而宋元以來人判斷的“五胡”指代,大體是沒有問題的。 在對五胡具體指代的研究中,還是要盡量避免以單一史料中的“五胡”指代作為判斷標準,因為單一史料未必能代表一時期之整體觀念。依我淺見,“五胡”一般泛指東晉時期試圖侵犯並佔據中原的少數民族群體(其後建立了政權或者王朝),《晉書·后妃傳》有“四海未一,五胡叛逆”等為其例也;而這些少數民族群體,又以匈奴、鮮卑、羯、氐、羌最為強大、有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