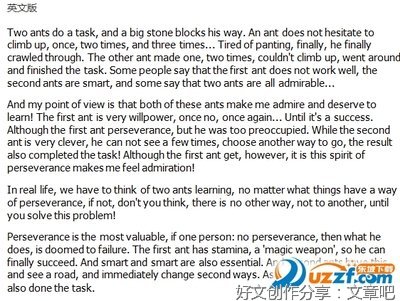
《蚂蚁社会》是一本由[德]尼尔斯·韦贝尔著作,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8,页数:4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蚂蚁社会》读后感(一):人类进化的目的地就是蚂蚁社会?
在人类过往的历史中,蚂蚁曾多次作为主角出现在东西方的寓言故事中,或者出现在流传已久的俗语之中作为象征性的事物而存在。那么蚂蚁是在什么时候开始作为社会性群体出现在人类的学者的视线之内呢?在这之后,人类通过观察研究又从蚂蚁社会之中得到了多少人类发展的启示呢?打开尼尔斯•韦贝尔的这本《蚂蚁社会》,我们能看到如本书副标题所言的壮观景况——一段引人入胜的历史。
本书讲述了近百年来世界各国学者对蚂蚁的社会性进行的各方面研究与思考,同时列举了不少乌托邦社会的著名小说,还介绍了几部专门描写蚂蚁社会的小说,期间数次提及迪士尼皮克斯等动画制作公司出品的关于蚂蚁的动画作品。书中内容是围绕蚂蚁展开,涵盖了从科学研究到影视动画的方方面面,包罗万象,作者将事物串联在一起从而得到新的发现的能力堪称一绝。 蚂蚁在地球上已经生活了几百万年了,比人类更为古老,那为什么我们只有近百年来才对蚂蚁这类昆虫的社会性研究渐入佳境。其实从古老的寓言及俗语中我们能看出来,人类从很久以前就开始观察我们脚下的蝼蚁,从而得出无数的经验教训。但那些观察发现,都仅仅是将蚂蚁作为个体来看待,而未能发现蚂蚁的社会性。本书便是从人类发现蚂蚁的社会性行为开始讲述。 那为何人类会突然发现蚂蚁的社会性行为,而之前又未能发现。在于过往的学者的研究方向过于单一,昆虫学家仅仅是对昆虫的分类、外观等进行研究,那时的主要研究方向在于发现新的物种,社会学家则主要研究人类社会,对昆虫又没有研究。直到百年前某个时期,学者们的知识面得到了扩展,昆虫学家开始对社会学有了了解,就开展发现蚂蚁的社会性行为。 有些事情真是不研究不知道,一研究就有惊天发现。原来蚂蚁、蜜蜂这些昆虫拥有社会性行为,而且他们的社会性行为有着高度的自主文明。书中写到,最初学者们通过研究,将蚂蚁社会和蜜蜂社会分别比作共和制和君主制,蚂蚁们是分工明确集体参与,但没有像蜂群那样的蜂王的存在。这些只是那时的学者研究的局限性以致产生这样的认识,作者表明,蚂蚁社会其实并不想那时的学者研究的那样属于共和制,当然也不是君主制。这一点在作者之后的研究发现之中得到了很好地阐述。 在本书第五章《社会即蚁丘》中,这一章可以说是本书的核心所在,通过近来的研究,或者是人类终于开始谦逊了,或者说在赫胥黎等作家的作品中我们隐约看到了人类的未来。总之,蚂蚁作为比我们人类存在更久,进化时间更久的生物,他们的社会已经发展到了终极形态了。一个具有群体智慧、集体意识、心灵感应的动态平衡社会,我们人类正是在向着蚂蚁社会进化。 我们人类在向着蚂蚁社会进化,这事儿听起来挺可怕的。在本书开头,作者借动画片《恶搞之家》中盖茨之口说出了“人就是蚂蚁”。这句看起来不怎么礼貌的话语其实代表了一种超前的思想,人类进化的最终目的地乌托邦就是蚂蚁社会这样的存在。当然,首先是人类没有自我毁灭。书中借着《蚁丘》《蚂蚁编年史》等小说为我们展现了蚂蚁社会的动态平衡生存状态,让我们真切看到了蚂蚁社会的高度发达。 也许我们不应该,至少不能泯灭人性,但现在社会的发展却似乎在向着这个方向发展,人似乎不再作为个体而存在,而是作为人群这样的群体社会而存在,这样的未来究竟是利是弊,就让我们看看比我们更古老种族的社会现状吧。
《蚂蚁社会》读后感(二):《蚂蚁社会》:蚂蚁和人类社会到底有什么样的异同呢?
蚂蚁与人类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为什么从古到今很多哲学家、文人、学者把蚂蚁与人类放在一起做比较呢? 在动物界,单个蚂蚁是微不足道的,是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的,但是蚁群却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蚁群并不仅仅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有着具体的社会分工,有着良好的沟通技巧,也有着非常多的协同合作。蚁后、雄蚁、工蚁、保育蚁各种蚂蚁具体而明确,而蚁穴更是功能齐全,就是一种完美的协作体系,而这种体系是由完全没有任何智力的蚂蚁所搭建,这就是匪夷所思的。 整个蚁群也像极了人类的社会,学者用蚁群来比喻人类社会由来已久,研究蚁群对于人类社会的借鉴意义也是非常明显的。德国学者尼尔斯•韦贝尔的这本著作《蚂蚁社会》就是在尽数前人用蚂蚁、用蚁群来构建的关系和我们的社会关系进行的论述和探讨。
现在已经无法具体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蚁群和人类社会建立起了固定联系,但这种联系却是由来已久了。蚁群也不是唯一被选择来类比人类社会的存在,和蚁群非常接近的是蜂群。蜂群虽然也有着各种协作关系,但相对单一,远无法体现出人类的复杂性。特别是在蚁群密切合作的时候,看似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的,遇水架桥,遇山开路,像极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我们在大自然之中,就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蚂蚁,可以克服任何的障碍,完成看似对于他们单个个体完全无法完成的任务,这不也就是我们人类所拥有的状态吗?
《蚂蚁社会》还试图论述从蚁群的形态探讨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而这本书也就更多的是分析前人的研究结果并形成自己的观点。蚁群最早也被应用到了政治论述之中,卡尔•施米特这样一位政治思想家就借用动物来论述社会的结构,即所谓“政治象征”。在他的论述之中,曾出现了很多的动物形象,但最终却落在了社会性昆虫之上,落在了“白蚁的国家”这样一个群体之中。即在“自然科学的思维”看来,社会性昆虫在建设和维持其国家秩序时,同人类社群有着同样的难题,既个体明显是自然的,也就是说不可避免的利己主义本能甚或“个体的顽固性”能否及如何转化为全体的福利。 在这段论述之中,施米特就用“白蚁之国”论述着人类的社会。人类和昆虫蚂蚁是一样的,它们都是作为政治动物生活在社会中。必然存在于生存与支持系统之下。如果把蚁群比喻成一个国家,那么一个个蚂蚁,就是单个的个体。而单个的个体必须服从于整个群体关系,否则他的生存必然受到挑战。但个体之中必然有着各种各样的特殊存在。作为蚁后的统治者,成为人类社会的超级个人;作为雄蚁的闲散人员,在人类社会也是大量存在的;作为工蚁的形象,像极了大量的劳苦大众,还有这其他种种。白蚁之国像极了曾经的人类社会。
《蚂蚁社会》并非简单的这样类比,大量的学者,大量的作家用蚂蚁来论证这种类比,而在这本论著之中,这些观点研究就汇聚于此,材料庞大而具体。这就是一部关于蚂蚁和人类类比这种最常见论述的“百科全书”,这有着大量的前人智慧结晶,当然也有着作者自己的精心研究。这本书虽然不好读,但确非常有趣而实际。
《蚂蚁社会》读后感(三):《蚂蚁社会》——蚂蚁与人类有着怎样的联系?
蚂蚁,是一个神奇的物种,以其令人叹为观止的组织性在这个星球上繁衍生息不绝。虽然可能我们每个人都看到过蚂蚁,但我们中很少有人去认真地分析、了解蚂蚁社会的结构,蚂蚁对于我们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的。 《蚂蚁社会》是德国锡根大学现代德国文学研究主席教授尼尔斯•韦贝尔的全新力作,作者带领广大读者从政治学、社会学、昆虫学、文学与电影评论中去找寻蚂蚁与人类的关系,从蚂蚁身上寻找文明的前景。
“人像蚂蚁”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比喻,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时常被拿来和蚁群的组织形式作对比。蚂蚁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动物,无论是他们的个体数量还是他们的适应能力,都是其他动物无法相比的,在历史的进程里,我们也随着研究者们的发现,不断刷新着对蚂蚁的认识。在这本书中,作者将历史、文学、社会学和研究蚂蚁本身的昆虫学紧密地结合起来,我们不断发掘对蚂蚁的认知,事实上也是在探寻对于我们自身的认知。
蚂蚁与人之间的类比在很久以前就出现了,在古希腊罗马时代,蚂蚁就被拿来和人做比较。蚂蚁被赋予了政治性和社会性,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发自天性地”要成为一种“建立国家的生物”,这是人类的本质属性——一种“政治动物”。他认为蚂蚁也是一种政治动物,在他看来蚂蚁和人类一样,生活在城市及国家中,他们相互合作,没有“城邦”就无法生存。人类和蚂蚁作为物种,始终都生活在一个社会中,政治动物形成集合体,它们“一直都是社会性的生活着”。
对蚂蚁的研究对于描述社会有着怎样的贡献呢?蚂蚁所被人们给予足够的关注,人们在对蚂蚁作为社会性昆虫的观察的基础上去分析人类作为社会性存在的特征。蚂蚁被赋予了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对于蚂蚁社会的分析助于我们了解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我们会发现,社会性的蚂蚁和文明的人类的进化都处于群体选择和劳动分工这个同样的原则之内。
人类的社会秩序有着怎样的特征?我们仿佛总能从对蚂蚁社会的分析中找到一丝线索,让我们深入去思考我们是谁,我们身处于怎样的社会秩序之中。
《蚂蚁社会》读后感(四):奇特的“人与蚂蚁”
每天站在高楼上 看着地上的小蚂蚁 他们的头很大 他们的腿很细 他们拿着苹果手机 他们穿着耐克阿迪 上班就要迟到了 他们很着急 2013年9月郝云《活着》专辑发行,“人是蚂蚁”这样的比喻惊艳到我,成年人的苦痛与辛酸浓缩为人是蚂蚁这样的比喻之时,便感觉一切都是微不足道。回想起学生时代常常背诵的俗语与诗句“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蚂蚁搬家,蛇过道,大雨要来到”、“仰蜂黏落絮,行蚁上枯梨”……如此微不足道的蚂蚁何以引来古人如此之关注呢?
带着好奇,我便走进了中西方先哲眼中的蚂蚁,了解着蚂蚁的故事。想当年,它,可是与1一年前的恐龙是一个时代。而且蚂蚁不但常见而且种类繁多,目前世界上已知的蚂蚁约有9000种,估计全部种类应有12000-15000种,而中国至少有600种以上。智人消灭了所有巨型动物却消灭不了微不足道的蝼蚁,这绝对是昆虫发展史的奇迹了。 我国古代很早就有关于蚂蚁的文字记录,成书于汉代初期的《尔雅》中就有蚍蜉、蚁、打蚁、飞蚁等字,但这里所指的蚁有的与白蚁相混。据考证,直至南宋罗愿著《尔雅翼》(公元1174年)时,才把蚂蚁和白蚁真正分开叙述。在公元前123年前后成书的《淮南子》就有蚁生活史的记述。其后《酉阳杂俎》、《太平御览》、《六收故》和《本草纲目》等历代文献,都记述了古人对蚂蚁的观察和认识。最经典的关于蚂蚁的案例莫过于张良利用蚂蚁灭霸王的案例了。 楚汉相争之际,汉高祖刘邦的谋士张良用饴糖作诱饵,使蚂蚁闻糖而聚,组成了霸王自刎乌江6个大字,霸王见此以为天意,吓得丧魂落魄,不由仰天长叹:“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乃挥剑自杀而死。汉家天下,蚂蚁助成的故事从此流传开来。而张良正是利用蚂蚁嗜甜这一习性,智取刚愎自用的霸王,可谓兵法妙用,棋高一着定江山。 不同的文化体系中“蚂蚁”的作用和意义便开始发生变化,在西方文明史中“蚂蚁”对人类的意义可以上升到“人就是蚂蚁”这样的高度,不信各位请看尼尔斯·韦贝尔(德国锡根大学现代德国文学研究主席)在《蚂蚁社会》这本书中怎么写的。
“数百年来,每当需要解读人类社会的时候,到处都可以听到蚂蚁的故事。每当设计一个社会的形象时,每当研究怎样从一个物种的大量个体中生成一个社群、一个集体、一个组织、一个国家或一个群体的问题时,每当在乌合大众之中指明社会秩序的模型时——就很有可能会参考蚂蚁社会。几乎没有另一种形象、另一种政治性动物、另一种集体象征,如此持续也因此简洁地代表着人类社会。” 从昆虫学到社会学,人从动物再到社会性的人都在这一概念中囊括。作者通过大量研究,将维吉尔《农事诗》中关于蚂蚁的描写与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进行对比,动物性的世界到社会性的世界逐步推导,蚂蚁的社会世界也逐步明晰,莱辛、于贝尔、林奈等学者也加入这一讨论和研究之中,作者分五步走将这些串成历史脉络带领读者深入。 1、认识史及科学技术研究的领域; 2、“人就是蚂蚁”这个概念的起源和历史; 3、蚂蚁形象的明证性; 4、蚂蚁是政治性动物; 5、社会学和昆虫学之间的交互; 因此书涵盖丰富,概念逻辑推理严密,我只能带领眼前的你读到这里了,“人与蚂蚁”的关系真正内涵恐还得眼前的你去延伸了。
《蚂蚁社会》读后感(五):蚂蚁,群体的社会
蚂蚁作为一种群体动物,已经得到了广泛关注。在计算机算法中的蚁群算法,其灵感就来源于蚂蚁在寻找食物过程中发现路径的行为。它是一种用来寻找优化路径的概率型算法具有分布计算、信息正反馈和启发式搜索的特征,是群体智能算法的一种。蚂蚁社会的影响力已经远超出了生物学的范畴。近日,德国锡根大学教授尼尔斯·韦尔贝著的《蚂蚁社会:一段引人入胜的历史》一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就系统地介绍了蚂蚁社会的各种内涵,包括而不限于社会学、生物学、文学、历史学,从文本、电影等多方面阐述研究了蚂蚁社会的种种。
蚂蚁社会无疑是十分完善的。它具有自身完整的结构,而这个社会中的每只蚂蚁几乎没有自主意识,完全服务于蚁群利益,整个蚁群作为一个整体存在,共同组成一个“超个体”。这近乎是一种完美的状态。
蚁群的核心就是蚂蚁社会的创建者、整群蚂蚁的母亲——蚁后。每个蚁巢有一只或多只蚁后,是专职的繁殖机器。蚁后在蚁巢中养尊处优,不事劳作,唯一使命就是在交配后开始挖洞创造繁殖新的蚁群。蚁群中数量最多的,是维持蚁群运转的普通劳动者——工蚁。工蚁们纪律严明,秩序井然。从事不同“职务”的工蚁,破茧而出后的体型、模样都有所差别。在部分蚂蚁中,还有一类特殊的工蚁——兵蚁。它们就是纯粹的战斗机器,靠工蚁供养。在蚂蚁的社会,每只蚂蚁都作为工具存在,具有自己的使命。
在本书中,引用了《利维坦》的观点,霍布斯认为蚂蚁只受各自的欲望和判断指挥,共同利益与个体利益没有分歧;它们根据天性会为自己的个体利益打算,这样也就有助于公共利益。它们不像人类一样能运用理智,它们见不到,同时也不认为自己能见到公共事物管理中的任何缺点。当它们安闲时,就不感到受了同伴的冒犯。蚂蚁社会的协同一致是自然的。从这种意义上讲,蚂蚁社会比人类社会更完善。
在书中浓墨重彩提到,也更加形象地借用了蚂蚁社会理念的就是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美丽的新世界》。在这部小说中,赫胥黎构建了一个可怕的未来。美丽新世界是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受着控制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由于社会与生物控制技术的发展,人类已经沦为垄断基因公司和政治人物手中的玩偶。这种统治甚至从基因和胎儿阶段就开始了。这是一个有阶级、有社会分工的社会,人类经基因控制孵化,被分为 “阿尔法(α)”、“贝塔(β)”、“伽玛(γ)”、“德尔塔(δ)”、“厄普西隆(ε)”五种“种姓”或社会阶层。,分别从事劳心、劳力、创造、统治等不同性质的社会活动。人们习惯于自己从事的任何工作,视恶劣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与极高的工作强度为幸福。正如蚂蚁社会的蚁后、雄蚁、工蚁一样。这种残酷社会已经渗透到了现实,这是最可怕的地方。
此外,在本书中还介绍了其他许多文本,比如有关蚂蚁的寓言、《蚁丘》等等,这些都极大地拓展了本书的边界,更加引发读者的思考。这本书确实可以让我们学到很多,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社会学好书。
《蚂蚁社会》读后感(六):《蚂蚁社会》在群体里是该利己,还是该利人
随着电视剧《乔家的儿女》热播,人们对于自私老父亲乔祖望的种种行为深感愤然,而对于哥哥一成的遭遇却是既同情又惋惜。他给了弟妹们家的温暖,但自己的小家却是一片狼藉,失去孩子,与前妻离婚,没有积蓄,最后还得了重病。
在利他或利己中,自私的人贪得无厌,丧失创造无能;无私的人不堪重负,艰难前行,这些都不是人生好的状态。《蚂蚁社会》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视角,那就是集体均等的贡献精神,在这里没有人混吃等死,也没有人累得要死,所以同类都尽职尽责,弱小的个体团结在一起共同创造出伟大的奇迹。
作者尼尔斯•韦贝尔是德国锡根大学现代德国文学研究主席、教授。曾在欧洲多所大学任教。他的研究重点包括社会性昆虫、社会自描写、文学及其媒介,文学的地缘政治等。
小的时候,我家里养蜜蜂,看着它们每天忙来忙去,使我很疑惑,是什么样的领导者管理这么多蜜蜂。
父亲告诉我,蜜蜂家族人员都各司其职,没有管理者。蜂王和雄蜂负责繁殖下一代,工蜂负责所有的劳动工作,如采粉、酿蜜、筑巢、饲喂幼虫、清洁环境、保卫蜂群等,它们每天兢兢业业在干着自己分内的事情,在春暖花开的季节把短暂的生命活出最绚烂。
公平的社会,谁都不争不抢,安分守己干好自己的事情,只有分工不同,没有好坏之分,社会就会一片和谐。每个个体累加起来的能力,对社会的贡献将会无限大。
《乔家的儿女》里二强单纯软弱,三丽敏感善良,四美自私任性,还有各种作妖的老父亲乔祖望,他们不管谁有事都想着找大哥。
其实他们的大哥也是和他们一样的普通人,也有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日子要过。因为从小一成就有担当,把照顾弟弟妹妹们当成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他们早就习惯了大哥无所不能的角色,虽然他们也爱这个大哥,但是他们的能力范围只能看见自己的困难,却很难看见一成的诸多不容易。
如果当初一成为他们少做一点,让他们每个人都锻炼出拥有独当一面的能力,在他有困难的时候,也能有人和他一起分担,也不用在自己伤痛只能独自一个人默默地舔舐。
人的有些能力是天生的,有些能力是后天磨砺中学习获得的。有人替你负重前行,有人就会心安理得地觉得生活如此简单。
一旦暴风雨来袭,除非保护一直都在,不然没有抵御能力的一定最先被打倒。如果不能给爱的人一辈子的保护,就要让他学会独立对抗一切的能力。
昨天看了一个视频,一个刚出生没多久的小狮子孤零零地蹲在一边,它又饿又渴,看着远处的兄弟姐妹在吃妈妈奶,它也好想过去吃,但是每当它走过去想吃奶时,狮妈妈就用爪子打翻它或者走开,反正就是不让它吃到。
小狮子只好可怜巴巴地找个地方睡去,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当它醒来,发现狮妈妈带着兄弟姐妹已经离开,抛弃它独自一个孤零零地在那儿。
它知道自己要想活下来,就得去找到自己的妈妈,于是它挣扎着站起来,脚步踉跄地朝前走。在一个山坡上找到狮妈妈时,它非常高兴,可是狮妈妈对它的到来感到十分厌烦。
原来它的腿已经受伤,狮妈妈只能把自己有限的奶水留给更健康的狮宝宝们,因为它们在这样的环境下存活下来的几率更大。
自然界的淘汰法则,看着让人觉得残酷和冰冷,但是现实生活中我们会发现,父母越是溺爱的孩子能力越差,父母狠命使唤和压榨的孩子往往能力更强。
结果是一个能力低下,一个心理留下大面积阴影。无论是选择利己,还是利他,每一个极端的背后,都是一个失败的案例。
无论是蚂蚁还是蜜蜂,他们讲究团队协作各尽所能,因为它们知道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小动物尚且明白的道理,人自认为是自然界最聪明的高等动物,有时候却只在自己眼前所见的范围内尔虞我诈,你争我夺,过分地追求名利会迷失人的双眼。
《蚂蚁社会》透过动物们的社会秩序,让我们看清小我的价值与生活的本质。在社会里,无论是利己,还是利人都要张弛有度,否则过犹不及。
图片来源网络,侵权必删
作者:豆浆 喜欢读书、写评,希望能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欢迎关注˜∽
《蚂蚁社会》读后感(七):蚂蚁、人与社会
正如尼尔斯·韦贝尔在《蚂蚁社会》中所说,人们喜欢以蚂蚁这样的生物来类比人类。维吉尔在《农事诗》称蚂蚁一起劳作,一起休息,然后与其他带有浪漫倾向的人们如艺术家莱辛与政治家克鲁泡特金齐声赞美蚂蚁是完全的利他主义,并把它们看作是人类应该学习的对象或应该达成的理想。这显然是一种非常幼稚的错觉。我们现在知道蚂蚁不是什么道德标兵,而是进化过程中生存与繁衍竞争的获胜者。你从昆虫学家那里了解到,不仅蚂蚁之间存在各种对抗,有些蚂蚁还蓄奴;如果这些吹嘘蚂蚁的人肯去先观察一下自然自身,或许他们就不会这么妄加议论了;但是,你知道,艺术家或政治家并不擅长这个,所以从他们那里很少能够听到真理。
在福楼拜的小说里,你会读到有人称“蚂蚁证明了君主制”这样的说法,其逻辑是,蚂蚁采取了蚁后统治其他蚂蚁的君主制,既然“大自然”的设定就是这种制度,那么人类采用君主制就是自然而合理的。你或许想到,这个人这是把自己的脑袋放在了休谟的断头台上——自然本身“是”什么,并不等于就“应该”是什么,所有把“是”什么就说成“应该”如此的人,如我反复所说,在逻辑上都犯了通常所谓的自然主义谬误。当然,不该苛求艺术家能讲出什么哲理。如果你了解过蜜蜂或蚂蚁,你会如凯文·凯利、托马西·西利一样发现它们的“民主性”,经常根据民主投票来做出决策。当然,实际上,在西利的《蜜蜂的民主》中你会发现,实际上这种“民主”表决,更多是一种技术上的优秀的决策手段,而不是道德上的“民主”美德。
人们早早就发现,单个的蚂蚁非常笨蛋,什么都不懂;但是,一窝蚂蚁却如赫伯特·西蒙所说,展示出了智慧,能够完成复杂的工作。人的原生智能会发出疑问:谁在指导与控制蚂蚁的行动?在《星河战队》中,你会看到编剧人为造了一个指挥着无数虫子行为的司令官的角色,用这种幼稚的设想迎合了原生智能孱弱的理解力。我们现在知道,不需要有一个指挥中心,就像库尔茨班在《人人都是伪君子》以及其他许多人所说的人的大脑那样;就像大脑由许多模块构成,蚂蚁或蜜蜂也可以充当一个个功能单元,所有这些单元就像大脑的模块一样,能够组合成一个完整的算法,从而能够完成某种功能,实现某种目标。作为生命算法,蚂蚁与人类一样目标都是生存与繁衍。
人类生命算法与蚂蚁生命算法存在一个显著的差异。人类的生存繁衍算法,是通过男女两人来完成生存、生殖与抚养后代的工作,构成一个完整的算法,而蚂蚁则是由蚁后通过与雄蚁的交合受精之后,产下大量的后代,然后由这些后代来完成生存与抚养后代的工作,构成一个完整的算法。对人类来说,算法的主体甚至只维持短短的时间,因而正如Helen Fisher在The Anatomy of Love中说,人类最初是系列一夫一妻制,男女两人相识、结合,女方怀孕,然后共同养孩子到能独立存活,然后两人分开,继续寻找下一个对象,重复这个过程。这就是为什么爱情往往难以终生维持的原因。这就可以理解为何布伦姆等人在《亲密关系》中说,婚姻关系的是否稳定并非是来自两人感情的深厚程度,而是来自是否有更优秀的第三者的出现。在人类对应的算法中,个体的功能实际上就是努力生存,以及与性伴侣繁衍与抚养后代。
蚂蚁则不是这样,对于蚂蚁来说,生存与繁衍的工作需要许许多多的个体集体完成,单个的个体蚂蚁,在这个集体中扮演一个工具单元,或者是工蚁中的一个,或者是兵蚁,或者是蚁后,或者在适当的时候改变自己的角色,就像棋盘上的一枚棋子。如果某些角色不能完成自己的功能,比如蚁后不产卵,或者工蚁不干活,那么整个集体就无法实现生存与繁衍的目标。这就是人类对应的生命算法与蚂蚁对应的算法之间的差别。一个常见的疑问是,单个的蚂蚁为何不抚养自己的后代?你或许听说过汉密尔顿的inclusive fitness理论,有时候也被等同于kin selection,这个理论通常用来解释为何个体会为了其他个体牺牲自己的利益。有些人误以为存在一个反例,韦贝尔提到,给蜜蜂群一个与它们无血缘关系的蜂后,它们也会无私地去抚育这个蚁后的后代。其错误之处是没有看到自然算法打造的“智能”并不完美,有些时候会出错,就像我们在自然界看到狼妈妈收养了羊崽子的例子。
许多人在蚂蚁身上看到了许多让他们心动的景象。前面提到,一些人看到蚂蚁忙忙碌碌,不像人类那样单个个体都是自私自利,而是为集体服务,于是感慨蚂蚁高尚的道德品质,并且批评人类的恶劣。你或许意识到,除了前面提到的这种对蚂蚁的浪漫美化的错误,也不懂什么才是“道德”。如前所述,蚂蚁作为一种进化算法的产品,必然只是“关心”如何能实现自身对应的算法所设定的生存与繁衍的目标,无论这种手段是善的还是恶的,仅仅只看“技术上”的有效性;或许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一些人误以为,人类有理性,所以知道善恶。但是,不妨让我们问一下,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伦理价值,人类思想史上有诸多争论与错误的观点,似乎从未有人给出正确的结论。价值的基本来源与标准,我已经在《价值与自由》中给出,或许可以从此终结争论。
这些人在蚂蚁身上所看到的利她行为,在算法中只是作为一种实现生存与繁衍的手段,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总是可以引用理查德·道金斯的观点,即这些表面上的利她,实际上是一种隐蔽的自私。我经常引用被德吕舍尔在《温暖的巢穴》以及日常的常识中常被称作“伟大”的父母对子女的“爱”与“牺牲”,这实际上是算法为了实现繁衍的设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父母只是对自己的孩子才有这种“爱与牺牲”,不仅对别人的孩子没有,甚至对收养的孩子也有所不同。但是这种“爱”也并非真正的爱,不仅是说,在其他生命如鸟类或动物那里,你会看到一窝后代中最弱小的个体被鸟妈妈或动物妈妈吃掉或丢出巢穴的现象,在人类身上你也可以看到父母更关注孩子如何成功与结婚生子,而不是孩子主观上的幸福与否。如果你说存在反例,那么我们又回到了前面谈及的蜜蜂“反例”——人类的智能更复杂,导致人类的行为更容易出错,比如人类发明避孕套来避开生殖,或者某些个体的“道德”模块的发达使得她们能够对她人做出真正的利她行为,以及一些人通过理性超越了自身的原生智能。表象纷繁,需要足够的理解力才能看到本质,否则就会出现误解。
另一些人在蚂蚁身上看到另一种“价值”,如梅特林克、恩斯特·云格尔、卡尔·埃舍里希,以为一个个的蚂蚁或蜜蜂,把自己投身于集体之中,通过相互协作,构成一个强大的超级有机体——她们以为,这种蜂巢精神或蚁窝精神,克服了个体自私性,“公共利益优于个人利益”,服务于集体或国家这个“崇高的目标”。这相当于引入了一个价值标准,即把集体或国家的利益看作价值的核心概念。但是,问题是,为什么集体或国家的利益是核心概念?施密特与埃舍里希所在的时代,欧洲正面临或陷入战争之中,所以二位当时内心隐秘的动机必然是感觉作为一个群体受到了威胁,希望他们所在的德国变得强盛,而且大概不仅仅是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是最好征服整个世界。或许这也正是希特勒的想法,或说E. O. Wilson在《蚁丘》里的想法——不管怎样,这种想法的来源是进化在人的原生智能中设定的一种本能。
如前所述,算法本身只是一个方案;生命算法也只是在技术上用于完成既定的目标,因而自然选择本身不讲善恶,只是选择那些能够奏效的手段,在人类身上也是如此。人类看上去也是一种群居动物,通过相互合作来提高生存与繁衍能力,因此人类发展出一种合作本能。我反复提到过合作的威力,就像简单系统的复合,能够通过增加复杂性带来新属性或现象的涌现,就像单个蚂蚁的愚笨与群体蚂蚁表现出智慧所展示的那样,拥有发达智力的人类所创造出的文明,正如罗伯特·赖特、马特·里德利以及她们的前辈如曼德维尔与亚当·斯密所发现的那样,是通过人类的分工合作而实现的。马丁·诺瓦克以为创新不是通过竞争,而是通过合作产生的,这是一种选择性失明,虽然说任何发现或发明往往需要像Mercier和Sperber所说的那样需要头脑之间的交流,或者用流行的说法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是驱动人获得成就的动机实际上难道不是来自竞争吗?
从算法上说,个体通过合作能够得到更多的进化利益,比如说一个人无法猎取一头猛犸象,但是一群人却能。这就使得个体之间拥有了一种“共同利益”,无论是否有直接的基因关系或亲缘关系,就像囚徒困境或R. Axelrod所说的那样。于是,人类就进化出一种“集体”本能,使得个体能够像蚂蚁那样在集体构成的整体中扮演一种功能性的单元角色,并且对集体进行维护。正是这种集体本能,使得施密特与埃舍里希以及其他许多人提出国家理论,以国家为至高目标。在战乱的时代,这种本能发作的尤其强烈,这些时代的一些思想者也就越会强调“国家”的思想,包括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当然,你或许会意识到,人的这种集体本能不仅在国家层面上抱团,在民族、种族、地区、语言、肤色上,在兴趣爱好上,比如喜欢某个明星或球队,同样也会触发这种集体本能;此外,人的这种本能会随着情景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利益的计算在变化。你或许会发现,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会在不同的场景或事件中改变了她们的看法,这一点都不奇怪。
施密特与埃舍里希这些人,由于这种集体本能的发作,看到蚂蚁作为工具或功能单元,构成一个团体为总体目标而服务,就像零件组合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机器那样,于是认为人也应该像蚂蚁那样,去除自身的个体性,为集体利益服务,以“国家”为崇高目标。那么他们就应该回答以下这些问题:增进集体利益的目的是什么?让个体为国家服务是为了什么?答案或许是为了国家的强大,文化的繁荣,那么问题就变成了让国家强大是为了什么,文化繁荣是为了什么?你会在威尔逊的书里读到一些答案,什么“进化的优势”,什么“蚁群的成功”之类。这就类似高尔顿貌似符合道德实际上是践踏道德的“优生学”那一套,他说,我们为何不主动加快、帮助自然进化呢?能让他无话可答的依然是“为何要加快、帮助进化”这个问题,如前面所提到,这是一种源自原生智能的错误,逻辑上的自然主义谬误;自然设计我们要搞生存竞争,更要在跟她人的竞争中繁衍成功,结果这些人就误把自然设定的这种本能冲动,真当成是最高的价值和自己的终生目标了,这是要让进化与基因即使睡着了也笑醒。
如何才能让人类形成像蚂蚁那样的超级有机体,一个大“我”?一些人设想了一种心灵感应,通过某种脑波,就像1920年的《北美评论》所说,“一个人知道了什么,所有人都立刻知道了”,克服语言表述的障碍,让人与人之间实现瞬间的绝对的沟通与交流,达成所有人同一个头脑,同一个意志,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卢梭所谓的“全体意志”,我的意志就是全体人的意志,全体人的意志就是我的意志。不难看出这个想法的幼稚之处。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的想法与意志是一样的吗?如果想法与意志各不相同,在这些相互冲突的想法与意志之中,最终让谁的想法与意志成为全体人的想法与意志?有些人如帕累托与威尔逊一样相信大众需要精英的领导,那么想必是精英的想法与意志灌输给大众了;有些人或许引入某种纯技术手段,就像西利在蜜蜂身上观察到的所谓“群体智慧”的决策方式。这就又回到了关于价值的疑问,所谓的精英领导,或者是群体决策,目标还是进化利益本能所决定的“集体利益”、“集体成功”或“集体繁荣”之类,就像水流如果有思想,把流入海洋看作自己要追求的崇高目标一样。正如我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这些错误的观点实际上都是有害的。我在《价值与自由》中已经提及,真正的价值在于个体而不是任何集体,包括国家;等人类认识到这一点,就会减少许多因为无知而犯下的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