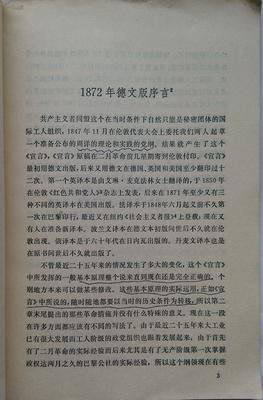
《若非此时,何时?》是一本由[意大利] 普里莫·莱维著作,三辉图书/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页数:31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若非此时,何时?》读后感(一):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UxOTc4Mw==&mid=402627429&idx=2&sn=ca014e5ac602711a083cc6612c008d3d&scene=0#wechat_redirect
《若非此时,何时?》读后感(二):精神上的领带
莱维是奥斯维辛的幸存者,这一经历几乎构成了他写作的全部基础。回到家乡都灵之后,他即迫不及待的开始关于奥斯维辛的写作,三个月完成了《活在奥斯维辛》。他跟其他迫切想要忘却却又时刻受着折磨的幸存者不同,他怀着一种见证者的使命感,主动迎接这些记忆,不断的思考,不断的记录。
一旦作品牵涉到奥斯维辛这个词,我们即会自然而然的预先感到一种不可承受的沉重。但莱维的作品不同,他把自己放在一个合格的讲故事的人的位置上,表现出的是冷静与节制。《若非此时,何时》是莱维唯一一部虚构小说作品。描写的是奥斯维辛之外的故事。相比奥斯维辛里密集的苦难,在这部作品里,有着不断升起的希望,难能可贵的个性与自由。
他们是被抛在森林,沼泽,田野里的一群人。他们的村子,田地,家庭都不复存在,他们受到其他所有民族的厌恶。他们是一群寻根的犹太人。因着空间的广大,他们有机会失落,有机会迷茫,有机会痛苦,也有机会展现自己饱满的个性。列昂尼德性情古怪激烈,脆弱。门德尔是个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却又时刻在行动的钟表匠。基大力作为武工队的首领,写过诗,喜欢拉小提琴。琳虽然外表安静,但内心潜藏着巨大的能量。每一个人的身心虽然都被战争拖累挤压,但每一个人都有着某种程度的自由。就算是在失事的飞机里生活的乌兹别克人,在井下生活了三年的什慕列克,他们过的也是属于自己的生活。
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的精神上一直隐隐有着某种追求,这种追求让他们在压抑痛苦的生存环境下免于彻底的麻木,失落。他们朝着遥远的巴勒斯坦的目标,从俄罗斯一直走到意大利,而被营救出来的集中营幸存者却毫无生机,只愿原地等待。他们在为黑罗柯尔报仇之后,还能立即懊悔血债不应血偿,应以正义偿还。他们虽然落魄狼狈,衣衫不整,但就像基大利在埃德克身上感受到的一样,我们在他们身上也看到了精神上的领带。
从俄罗斯到意大利,战争结束了,但他们寻找安宁的征途还远未结束。不过这是一个孕育着希望的故事。他们必将如结尾的新生儿一般找到他们想要的新的生活。
《若非此时,何时?》读后感(三):给为尊严战斗人们的赞歌 给为尊严战斗人们的赞歌
被书名吸引的我买下了《若非此时,何时?》,然后惊奇地发现这是一本写战争的书,然后延伸到作者,普利莫·莱维,奥斯维辛集中营囚犯幸存者。不禁被作者的身世感到震惊。“我若不为自己,谁会为我?我若只为自己,我是什么?若非此时,何时?”三个问句震撼人心,道出了书中为尊严而战的犹太人以及武工队!
作者以门德尔为主线展开了一个个故事,从列昂尼德到到基大利武工队……门德尔的名字意思为“安慰者”,却自诩从未安慰过谁,他向列昂尼德袒露了自己所有的经历,而列昂尼德闪烁其词的经历透出的是苏联集权体制下犹太人的艰难处境,而他最终选择战斗,只希望从村里的大屠杀中不再想起丽芙柯的脸,不再想起自己的妻子,能面对眼前的一切。而作者塑造列昂尼德这个形象无非是为了反衬门德尔的形象……而列昂尼德的死更像是为了他自己的尊严,为了琳。
战争从未停止,就像基大利在一次战斗中所说:“你们已经打了五年战争,我们呢,已经打了三千年。”身为犹太人,他们经历了无数次前线与作战,要面对太多的凶险与恶意,一个犹太女孩,没有死于集中营与战争,却死于和平时期德国人的挑衅与谋杀,这是一个最为悲伤的寓言,或许战争真的结束了,但是也许之后会有另外一场战争,或许没有硝烟的种族偏见的战争一直不会平息,而这种战争无疑更加磨折人们的心志,取而代之的是空虚、疲乏与绝望,甚至是连绵的战火。
武工队的所有人几乎都有惨痛的经历,他们一路西行,出生入死,近观这支自发组成的队伍,既非目标统一纪律严明的组织,亦非自由散漫溃不成军的群体,他们有自相矛盾之处,在时局磨砺中竟也凝为团队。最初他们赚弃老弱妇孺无所贡献,后来体恤兼爱相互照顾;最初领队者一言九鼎享受独裁,后来群策群力趋于民主;最初他们行动激进,必要闹出点大动静,后来学会审时度势顾全大局……虽然他们同是犹太人,但却来自不同国家,甚至有不同的信仰,而让他们走到一起的是什么?是未来和希望!
书中的最后提到了新的生命的诞生,以及第一枚原子弹在广岛投放的新闻,昭示的是未来、生命与和平。尽管《若非此时,何时?》是普利莫·莱维的长篇虚构作品,但却展示了他真实的内心想法,以冷静透彻的态度来完成此书。而“如果我不为我,那么谁来为我?如果我只为我,那么我是什么?若非此时,何时?”这贯穿故事始终的句子便带有一种决绝、舍我其谁的力量,就像武工队队员那不屈服的勇气一样。带给人们属于他们的尊严!
《若非此时,何时?》读后感(四):只有勇敢,才有希望
《若非此时,何时?》展示了一个在二战中不同犹太人的故事。与往往被纳粹屠杀犹太人的事件中,作者让我们看到了犹太人的另一面,他们的勇敢。只有勇敢地抗争,才会有生的希望。
作者意大利犹太裔大师普里莫•莱维,他曾经历过二战,在1944年还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他的作品都以二战、集中营生活为主,作为对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一种回忆,一种证据,代表作《被淹没和被拯救的》、《再度觉醒》等。相比记录纳粹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暴行,本书与其他作品不同,主要讲述了犹太人勇敢地抗争,用微弱地武装战争为二战献出自己的力量。他们渴望着安全,世界的和平,但是他们知道只有自己勇敢,才能不被纳粹屠杀,生命才有希望。
故事的背景发生在1943年,正是二战的转折点,1943年7月西西里岛战役,同盟国打败了纳粹德国,从此打开了欧洲的大门,同年斯大林开始反攻。书中的人物代表着战争中不同的角色,无论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唯一的目的都是与纳粹战斗,打败他们,争取胜利,换取生命的存在。
主人公门德尔,代表着逃出集中营的“幸运者”,他看到了集中营纳粹的暴行,犹太人的屠杀,他一心寻找着武装部队,只有加入武装部队,去战斗,才有可能不被屠杀,他与列昂尼德结伴而行。列昂尼德是苏联制度下的犹太人,他曾经是军人,在他的话语中也让人看到了在苏联的犹太人生活也十分艰难。他脾气有些古怪,一心向往和平,不想再参与战争,但是因为环境,他必须加入武装。他从出场的阴郁,到讲述父亲的纳粹遭遇,也许是因为厌倦战争,也许是他心中没有了希望,最后他自杀而终。
长途跋涉地寻觅,门德尔与列昂尼德找到了朵夫,小型的武装队,在这里门德尔看到了希望,同时朵夫又是一位英雄,他从火车勇敢地跳下,摔折了腿,但是依然为了抗战而坚定地活着,一直勇往直前。最大的武装队长应属基大利,带领着众多的犹太人与德国纳粹战斗,破坏德国军事。“若非此时,何时?”的口号也由基大利在黑暗的卡车中笑喊出。
书中不得不提到的人是她,琳,代表着战争中女性勇敢、硬朗的一面,巾帼不让须眉。琳,俄罗斯犹太人,先后在车尼哥夫和基辅上学,本打算成为教师。可是在二战中的俄罗斯,犹太人被拒绝上大学,甚至污蔑她,被封锁在聚居区的琳结识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朋友们,在武工队的帮助下学会使用武器,与战争战斗。她知道只有勇敢地抗争,才会有希望。
文章的最后用了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以及原子弹的报道作为结局,也许这正是作者给予新和平,新希望的象征。
《若非此时,何时?》读后感(五):幸存者的逃亡
这不是一个记录屠杀的故事,莱维说。这个故事是关于一群人,战争的幸存者,在战事残局的时刻逃匿在波兰乡间,带着犹太人的身份原罪,提防着所有的敌意。他们战斗、躲藏、劳作、逃亡,辗转于各个势力之间,被各个势力扣押过,彼此之间应是最可靠的联系但也不乏复杂的纠葛。不是来自普通的爱恨情仇,而是历经地狱边缘的生死之后无法摆脱的怀疑和不安,连保持沉默都是危险。,和一般描述二战中犹太人被关押和处决的故事不同,这个故事里面的犹太人是有着战斗的坚韧和洒脱,书名即来自如此的战斗檄文般的歌词“我若不为自己,谁会为我?若非这条路,哪条路?若非此时,何时?”。而同时与这样的战斗力相映衬得,是以门德尔作为叙述的主声部,一个前钟表匠、炮兵、俘虏,他在逃亡中顺应着安排而逃避自我选择,拖曳着过往阴影,“平静而不快乐。平静地不快乐”。这个描述让我心头一震。记忆堵塞着他,同时又在远离他,他不知该往何处去,即使战争结束,可是他的生命力早已经结束了。
战争的恐怖和悲怆不全是来自于枪炮相见时的血肉横飞,也发生在当我们目随着这一路人穿越疮痍的土地、听见来自普通百姓毫不掩饰的敌意。故事里面对于波兰人的描述难以决断,他们同时是加害者(对犹太人)和被害者(俄罗斯和德国),敌人是个永远存在但身份却不定的对象。在我们看来故事的主人公们是无辜者,然若书写故事的人是波兰人,那么为了生存而做出的选择又怎么能铁齿咬定就是错。终归是战争的残忍,心怀恶意的一小群人把更多大众变成暂时的恶魔,世界变成非人间。
好在这个逃亡的故事并非全然悲剧。最后旅程停留在一个中继站,大家暂时地安定下来。那是在意大利,作者的国度,关于意大利莱维的描述不乏诙谐,他说意大利人不喜欢法律他们喜欢犯法,他们做弥撒也诅咒,比起讨厌外国人他们对彼此更有敌意。
莱维的书是关于二战里面最不容错过的选择。见证者、幸存者和作家集于一身是多么罕见而又幸运的事情——幸运更多是对于除他以外的人而言,这使得我们可以读到非常优秀的故事和记录,深刻、真实而克制,并带着文字的优美和来自个性的诙谐。这本书里面提到了幸存者愧疚,莱维可能一直在试图用他的笔来使自己平静,但他最后还是从家中窗口跳了下去。我想起多尔的记忆墙里面的一个故事,一个集中营幸存的老太太在死后加入一直等着自己的童年伙伴的鬼魂,大家终于可以安然离去。莱维最后也获得这样的释然了吗?
《若非此时,何时?》读后感(六):困顿中踟蹰前行
在所有作家所描述的所有战争的场面中,我们体会过太多的痛苦与无望,那些或直接面对或间接讲述的杀戮与摧毁,刺激着读者每一根脆弱的神经,难得读到如《若非此时,何时?》一般平静淡漠的战争小说,却在读的过程中感觉到一种更加沉重的压力。
作者选取了一个巧妙的角度,绕过正面交火的战场,去到战场广阔后方一片片支离破碎的土地上,那里还生活着各种各样的人,波兰人、俄罗斯人、犹太人,或者是难民、战士、流寇,也可能是老人、鳏夫、孩子,他们因为不同的目的组成了一个个不同的群体,流动着、变化着也向前着,在这里生存显然占据着最主要的地位,但同时,还有另一种关乎人类感情的东西——尊严以及对于民族的情感——在若隐若现,且与生存交缠向前,偶尔甚至占据上风,所以才有了基大利的小提琴乐曲,铁道沿线电缆塔上的南瓜,才有浪漫神秘的“沼泽共和国”,以及在战争中结成的深情厚谊,整本书最令人感动纠结之处就是创作武工队队歌的马丁与德国士兵的故事,对于艺术的热爱,彼此的惺惺相惜,却一次又一次被敌对关系所斩断,读来令人心痛愤懑,但是毕竟那首乐曲终于得到流传,“如果我不为我,那么谁来为我?如果我只为我,那么我算什么?若非此时,何时?”这贯穿故事始终的句子带有一种决绝、舍我其谁的力量,就像武工队队员那不屈服的勇气一样。
似乎普里莫•莱维下定了决心想要在自己的书里回避战争,尽管门德尔以被毁灭的村庄开始这个故事,他们间或也会加入一场战斗,但是在这里,却能感觉到战争远远不是主角,人类所形成的偏见与约定俗成才是,就像基大利在一次战斗中所说:“你们已经打了五年战争,我们呢,已经打了三千年。”身为犹太人,他们经历了无数次前线与作战,要面对太多的凶险与恶意,一个犹太女孩,没有死于集中营与战争,却死于和平时期德国人的挑衅与谋杀,这是一个最为悲伤的寓言,或许战争真的结束了,但是也许之后会有另外一场战争,或许没有硝烟的种族偏见的战争一直不会平息,而这种战争无疑更加磨折人们的心志,取而代之的是空虚、疲乏与绝望,甚至是连绵的战火。
作者用近乎平静的语气以及高超的技巧,让人难以相信这仅是一段虚构的故事,整个故事如此浪漫凄楚,却又真实的可怕,故事的结尾,伴随着原子弹的爆炸,在战争中孕育的婴儿终于来到这个世间,这似乎带有明显的寓意与希望,生命就像种子,即使再艰难的困境,再痛苦的折磨,再漫长无止境的战争,依然无法抵挡生的力量,对于生命的渴望,以及对于彼此的拯救。
《若非此时,何时?》读后感(七):《若非此时,何时?》
quot;If am not for myself, who will be for me? If am for myself alone, what am I? If not now, when." 我若不为自己,谁会为我?我若只为自己,我是什么?若非此时,何时?
这句话出自犹太教拉比的教义,就字面而言,这句话其实可以用到很多地方,作者却将最后一句“若非此时,何时”选为书名,当断断续续一个多月终于读完后,突然觉得没有什么比这个名字更贴切了。
这个故事的开始,是两个说着意地绪语的意大利犹太小伙子在逃亡中的相遇,Mendel,一个修表匠,一个被打散的炮兵,他的妻子和全村的人都被屠杀后埋在大坑里;Leonid,一个学过记账坐过监狱,被训练成伞兵又好容易从德国劳动营逃出的战俘。他们两,只是为了生存结成了同伴。这一段,作者以Mendel的口吻这样描述“那是债主的眼睛,或是自觉有所亏欠的人都眼睛。可是,又有谁不觉得自己有所亏欠呢”
他们一路流离,其间有加入各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武装力量,他们的伙伴很多根本不懂打仗的章法,只是要做点什么证明自己,他们参加一次次或有计划或无心遭遇的战斗,Leonid死去,很多人死去,只有少数人,包括Mendel走到了最后。
怎么说呢,当你读完,你不会认为它是一部虚构的故事,因为质感太真实,它和其他很多有关二战,有关犹太武工队,有关集中营,有关犹太人homeland梦的纪实作品一样,就是活生生的历史;
原来那些千千万万被战争机器碾压的个体、他们渺小的生与死、那些令人窒息的绝望,竟然可以用这样平淡的语气、这样简单的文字一笔笔写来,看似不施铅华却又会让人更觉其中的凌厉。比起其他很多二战回忆录,这本书几乎可以说是不动声色的,没有强烈的情感宣泄。死亡,就像自然的花开花谢,可以在一路走来的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发生在这些犹太武工队员任何一个人身上,其他的人,还是会头也不回的继续走,哪怕他们从意大利到波兰到德国的一路游击抵抗完全无法左右战争的结局,更多的只是一种不屈服的姿态而已,这才是可悲可叹之处。
很多年前,我曾经很着迷有关二战的纪录片,女性思维看战争纪录片免不了还是有看故事的嫌疑,何况多数二战片关注的是欧洲战场,对太平洋战场的比重相对小了很多。我的注意力并没有集中在各方政治军事力量的此消彼长,而更多感兴趣的是那些被采访的铁血风云人物以及战争亲历者的讲述。这些年过去,很多细节都已渐渐记不清楚了。最近几年,也本能的只愿读些轻松的东西。
本书作者Primo Levi,是奥斯威辛幸存者以及意大利国宝级作家,但却以另外一种方式处理了这种以生俱来的沉重,我给四星。
《若非此时,何时?》读后感(八):若非这条路,哪条路?
若非这条路,哪条路?
——读《若非此时,何时?》
文/唐斯婷
“我若不为自己,谁会为我?
若非这条路,哪条路?若非此时,何时?”
……
这是普里莫·莱维在小说中描写关于二战时犹太武工队里传唱的一首歌歌词。作者在后记中引用《先贤书》的一些格言,例如《塔木德》的话:“我若不为自己,谁会为我?我若只为自己,我是什么?若非此时,何时?”沉思良久,多少人心中的一盏灯灭了又亮起来?
读完一本书,我已不太喜欢复述作者所写的内容,尤其此小说还是全世界都知道的犹太人二战时的苦难史。我想起自己读这本书的初衷,更多是想了解,经历过磨难、屈辱、受过死亡威胁的人,他们是如何凭着自己的意志生存下来,生存下来后,他们又要度过多少心里的难关,才有可能治愈内心的创伤。最近有同学推荐看钱钢的一篇报告文学《我和我的唐山》,作者写到一个被压在废墟中三天后才得救的幸存者的感受:“‘我一到阴天,一到天黑,人就说不出的难受。胸口堵得慌,透不过气来,只想喘,只想往外跑……’她不止一次这样跑到屋外,哪怕屋外飘着雪花,刮着寒风,任丈夫怎样劝也劝不回来。她害怕!”他说这位妇女只要看到天阴,那些绝望恐怖的感觉就会找到她,令她窒息。这些令人难以接受的画面,一旦发生,如何面对?实际上,是迫于无奈地面对,然后等待命运的眷顾。经历集中营的普里莫·莱维在接受访问时说到,跟他一样幸存下来的人,有很多人都想彻底遗忘那些日子,可现实是,他们时刻受着折磨。如果幸福是属于无灾无难的人,那他们早就没有了幸福的权利。
小说中,基大利带领的由犹太人组成的武工队,在深林,遇到了一位三年前在聚居区走出来的波兰籍犹太人。这位犹太人的处境让我印象深刻,他的名字叫什慕列克,三年前,近一百人躲在井下的一个地洞,到最后,只剩他一人活着并继续住在此。武工队的犹太人同样历尽艰险,仍难以置信,这里居然能住人,他们都以为他是老头,实际只是三十七岁的年轻人。
作为一位幸存者,普里奥·莱维并没有把文字放置在沉重的基调上,而是别开生面,写他们顽强的求生意志,把他们刻画成不易打败却容易被刺痛的一群人。文字也没有流露出仇恨情绪,作者在一次采访中说道:“怪物的确存在,但他们在数量上太少而无法构成真正的危险。更大的危险来自于普通人,那些不提出问题,而直接相信和执行的公务员们。我们必须对那些试图通过诡辩而不是道理来说服我们的人抱有怀疑之心,必须对那些所谓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抱有怀疑之心。”
用“历史的俘虏”来形容一群悲惨的人,并不意味着把人的罪恶遗忘,因为内心的魔鬼,随时会跃出栏栅,疯狂地轰炸无辜的人。作者没有被围困在循环的罪恶之中,他更关注的是叙述的平和感,展示的画面已超出自己的亲身体验。罪恶存在人的意识之中,有时候,沉默也会成为帮凶。所以,普里莫·莱维说:“在世界的任何角落,只要你开始否认人类的基本自由和人们之间的平等,你就开始向集中营体系迈进。而这是一条难以止步的道路。”
2016年2月25日
《若非此时,何时?》读后感(九):人生必须透过黑暗,才能看到光明
意大利作家普利莫•莱维的小说《若非此时,何时?》,是其唯一一部长篇虚构作品,但其中创作出来的人物和事件却有着真实的历史背景。
《若非此时,何时?》讲述了在华沙犹太人起义之后的波兰,莱维通过对两位掉队的犹太士兵门德尔和列昂尼德引述出犹太人武工队,这些人或从集中营中幸存,或从战场走失,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生存,且是有尊严的活着。
小说中每一个人男人或女人背后都有着不同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似熔化的铅块一样令人感到灼热,随着对这些人物了解的深入又令人渐觉其沉重。仿佛亲眼目睹他们那憔悴却坚定的脸上流露出对战争胜利的肯定,他们知道战争终将以德国战败而结束,但他们不知道犹太人的未来在哪里。
对这些人们的刻画铺陈出届时犹太人的生存境遇与内心真实状况。种族屠杀带来的伤害、波兰人对犹太人所表现出的冷漠,武工队在敌后的活跃,此间种种共同影射出一幅背负沉重希望缓慢而行的意象。
如果莱维笔下一切关于奥斯维辛的回忆是为人们提供一个真实而残酷的视角,以了解奥斯维辛集中营之中纳粹的极恶罪行。那这部小说便书写了犹太人对自身的证明,他们的民族长久以来都遭受着人们的歧视,在流离颠沛的日子里忍受着世人的欺辱,故事之中人们的奋斗关乎尊严,同时也是对自身的过去与未来的证明。
正如莱维在书中所说那样,“跟所有的墙壁一样,缺乏理解的墙壁也有两面。因缺乏理解而生困窘,因困窘而生敌意。”尽管在这部作品之中莱维无意探究犹太人长久以来遭受歧视的原因,但他在书中却表现出了对此问题深刻的理解。
“惊恐不安,像被追猎的野兽。”波兰人仅从犹太人的眼睛便可断定他们的身份,莱维的这句话概括了犹太人的内心,他们眼神之中流露出的惊恐,已经延续了数千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不经历磨难,但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犹太人一样,他们坚定的追随着大卫之星的光芒,坚守着与上帝所订的约,却又数以千年的过着流亡的生活。他们的民族长久以来都遭受着人们的歧视,他们有着过去,却看不到未来,他们难以回到心中的家与国。自从罗马人将犹太民族驱逐出以色列的土地后,千百年来犹太民族便如荒野的游荡的野兽般逃匿流散于世界各地,人们在政治和宗教领域上的歧见令她的儿女一直饱受来自各方的迫害,但他们凭借超凡的忍耐与坚如磐石的信仰在绝境中存活,在羞辱中前行。
“如果吾等得知所有受害者的真相,吾等将无法生存。”一如莱维所说,作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174517”这个囚犯编号却已然在其生命中成为了一个永远无法磨灭的印记,尽管在他的回忆录中透彻而冷静的叙述着纳粹的罪行,自我意识的恢复与苦难记忆郁结内心永远得不到释怀,但在这部小说之中难得一见的看到了作者以一种积极、满怀希望的态度去重塑过往和期盼未来。
“不是为了死者,而是为了生者,为了相信祈祷的生者。”或许这就是莱维著书的目的,不是为了纪念昔日英勇的战士,而是要让后人永远的保持着对自身尊严的肯定,对自由的渴望,对命运的不曲。小说最后,战争结束之后武工队员都不知自身的去从,但伴随着战争中爱情孕育出的新生命的出现,一切似乎都显得不重要了。
《若非此时,何时?》读后感(十):最坏的时代,为生命著书
二战疮痍过后,该用怎样的文字记录历史?集中营幸存者将纳粹令人发指的罪行大白天下,记者为战场归来的士兵、为经历动荡的老弱妇孺立传,研究者们深入分析各个阵营的立场、代表人物的心理。战争过后,不是只有胜利者和失败者;生命,亦不是只有活着和死去两种状态,这或许是普里莫·莱维在战后放下化学家的本行,一心写作的原因:为战斗者著书。
身为奥斯维辛的幸存者,莱维目睹了集中营里惨无人道的生活,以此为素材撰写的回忆录不仅令莱维跻身意大利国宝级作家,更让他在奥斯维辛的代号174517成为时代的烙印。但莱维还看到了集中营以外的世界,那些不同处境下同样在战斗的人们——他们不是英雄,没有做出决定性的贡献,可是谁也无法否认他们的斗争,无法忽视生命的力量。《若非此时,何时?》这部小说即是脱胎于此。偏安一隅照料弱小、背井离乡寻求和平、未被收编涉险奋战,这些鲜活的生命绽放在动荡土地的夹缝中,纳粹将他们视若草芥,世人不理解他们,莱维却向他们致敬:“无论寥寥数人或人数众多,他们都在这场力量悬殊的奋斗里重新找到了尊严和自由。”
小说中的犹太人武工队一路西行,出生入死,主人公门德尔是中坚力量。近观这支自发组成的队伍,既非目标统一纪律严明的组织,亦非自由散漫溃不成军的群体,他们有自相矛盾之处,在时局磨砺中竟也凝为团队。最初他们赚弃老弱妇孺无所贡献,后来体恤兼爱相互照顾;最初领队者一言九鼎享受独裁,后来群策群力趋于民主;最初他们行动激进,必要闹出点大动静,后来学会审时度势顾全大局……
书中不时出现对信仰的讨论,也是小说得名的出处,《塔木德》有言:“我若不为自己,谁会为我?我若只为自己,我是什么?若非此时,何时?”武工队成员不忍放弃信仰的教条,然而在现实面前,信仰显得乏力,不足以应对所有问题,难免心生动摇,此时又该如何妥协或是折中?譬如杀人,有了报复、反击作借口,是否就合情合理?即使对方是杀害同胞的德国人,也未必能杀之后快。面对手无寸铁的德国妇孺,如何能不想起自己的妻儿?以纳粹的逻辑“十命抵一命”,如何能结束以血洗血的战争?在为无辜被杀的妇女报仇后,门德尔自省,血债血偿离和平日远,可又无法否认情绪得到了释放。他们必须硬起心肠才能生存下去,又不可避免本能的悲悯。
其实这并不矛盾,因为他们先为生命而战,证明作为人的身份,其次才是信仰。俄罗斯人遇到波兰人,互为异己,直到发现双方奋起抗争的原因是一致的。俄罗斯犹太人说:“唯有通过杀德国人,我才能说服其他德国人我是一个人。”波兰人说:“因为我们是波兰人。我们要让全世界看到我们的存在。如果有必要,我们以死证明我们的存在。”莱维总结道:“每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犹太人,波兰人是德国人和俄罗斯人的犹太人。”倘若连作为一个人的身份都无法得到承认,那要如何立身,子孙们要如何立身?遑论争取其他权利。相比之下,为了信仰而战反倒飘忽,就像和平后不再胜任修钟表的门德尔,“射击令手指僵硬、迟钝,眼睛习惯于透过瞄准器看向远处”,“他没有听到从那应许之地传来的任何召唤……责任不是财富”。
信息闭塞、忍饥挨饿、武器难寻、跋山涉水,绝望中支撑着武工队员的希望即是证明身为人的价值。他们不是天生好斗,和平将至,琴瑟友之,却还是要大声疾呼,自己是武工队员,不是流民。这难道不是二战中一幅壮美的风景吗?最坏的时代,平凡的生命进发出无比的坚韧,不甘民族湮灭,不甘人生淡漠,尽管世界还给他们的只是今非昔比的陌生。
至少莱维看到了,而他也在以他的方式争取生而为人的证明。索尔·贝娄说:“再也没有人死于心碎,一种叫做麻木的特效药治好了这种鬼病。”莱维偏偏最痛恨这种能换来安宁的“特效药”,集中营里小心翼翼走在灰色地带的往事令他黯然,集中营外的生命气息令他动容。莱维为这番喜悦助澜,随后似也得到救赎,自戕是他无奈的归途。
——乙未年读普里莫·莱维《若非此时,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