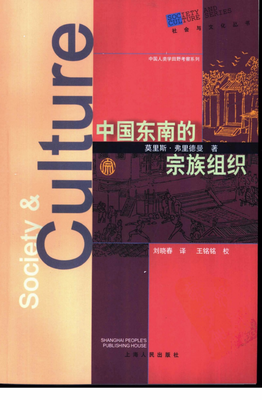
《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是一本由【英】莫里斯・弗里德曼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4.00元,页数:19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精选点评:
●不是很有说服力,概念不明晰,材料不足以支撑观点。
●翻译得太烂啦,很多句子要逐字推断原文=v=
●弗里德曼在20世纪采取文献综述法对中国东南宗族的研究,由于翻译问题,很多语句并不顺畅,资料不够充足。
●外国人写的中国研究,一些观点蛮有意思,更多是对已有研究的再研究
●看的是电子版,有时间再研究下。
●其实人家不是专门搞中国研究的嘛~
●跟日本鬼子的精致入微比起来,英美鬼子究竟粗枝大叶了些,难怪冈部达味有自信当着费正清的面说,美国的中国研究是天文学的一部分……只能用望远镜对自己实际没有接触过的事情进行观测,然后从中得出针尖大小的观测结果。
●我觉得有点无趣啊
●这样一本书竟然能在宗族研究领域获得这么大的声望,真是汉学界的奇迹!
●宗族之外还有什么
《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读后感(一):关于宗族,你我了解有多少
中国谱牒中记载的历史人物,一般可以追溯到明朝中央政府大力提倡民间宗族建设而大规模生效的万历年间。但要分别出世系之间的联宗关系。在福建就有大小几个家庭组建成一个继承式家族,再从继承式家族出发,联宗成一个继承式的宗族。依附式宗族,有着从最基层组织不断向较高层行政单位发展的趋势。也就是说,依附式宗族的联宗会从村——乡——社——里——县的地缘发展关系。
明清的著名历史人物的世系由于时代关系,也多不可信,或争议不断。明朝万历年间以前的历史人物的世系,也大多出自伪造。永乐年间的科举考试名录也多为虚构。福建方姓更将方孝孺加以引进,杜撰出方孝孺的子孙避乱入闽的史实,无不令人啼笑皆非。如明末的袁崇焕,朱三太子为代表的朱明皇室后裔,福建的郑成功后裔、郑成功日本胞弟以及后裔、施琅后裔,黄道周后裔等等都是满纸荒唐言,谁解其中味?
民族英雄和前政权的后人怎么都是清朝的孝子贤孙呢?就英雄本身,袁崇焕生前本无子,朱三太子被清政府追杀到雍正年间,郑成功子孙在北京附近断子绝孙,郑成功日本胞弟无从考证,施琅的祠堂在小刀会起义都被摧毁,黄道周连徒弟都被清军捕杀,怎么会有所谓的袁崇焕堂弟和他的清初官员子孙,朱元璋的清初知府和清末举人出身的知县子孙,郑成功的清末举人的子孙,黄道周的清初总兵子孙呢?就继承方面而言,即使是真实的世系,这群主持或参与宗族组织活动的子孙,连祖先事业就没继往开来;而就个人而言,一群没有所谓的祖先所秉持的民族气节,趋炎附势卑躬屈膝地生儿育女,怎能算是民族英雄的子孙?
从袁世凯在痴心妄想皇帝梦开始,就存在着。1916年,距离明朝灭亡的1644年,三百年不到,袁世凯的幕僚就想拉袁崇焕到袁世凯的祖先谱系。经官方和半官方大造舆论,杜撰袁世凯是袁崇焕的第十几代子孙,既然有详细的世代,就当有传承世系的人物。
此外,还有至少两位著名辛亥革命先驱,也是如此这般演绎。如前文所述,孙中山的南明志士祖先,是被罗香林给客家学研究造势而歪打正着的牵强附会。史坚如也不例外。不知是他自称还是被称,说是史可法的后代。史可法和袁崇焕一样,生前均没有留下子嗣。况且史可法是河南人,而史坚如是广东人。史可法就义在江苏,清政府都有扬州十日,史可法的河南宗族怎能脱身于清政府的视线。
如此这般去述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发起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正式取代清朝统治,并自己改元称帝;史坚如参加辛亥革命,不畏强权死得其所------,种种这些,都和他们自身的家仇国恨有关,完成的是他们民族英雄祖先的未尽事业?更令人愤慨的是,历史伟人和民族志士的救国救民的出于或是出发点之一竟是为祖先报仇雪恨?!虽为给他们贴金,在当时的中国,也许有些作用。但是从历史角度是不尊重历史,对辛亥革命起到了贬低先驱和革命事业的不良影响!
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朱熹,以及闽学人物,甚至清初的李光地、刘墉、林则徐,也免不了被拉去签字画押。诸多姓氏谱牒也都可以找寻到他们的芳名。历史上的朱姓和孔姓一样,均以朱熹和孔丘为中心,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纷纷牵强附会,杜撰与之的承接关系。朱熹世系原本就仅能追溯到孙辈。而且此孙据说是朱熹长子英年早逝几年后,由其寡妇儿媳生育的,朱熹在世时就被揭发为朱老夫子所谓。朱熹更是当街左拥右抱两尼姑招摇过市。无论如何,朱熹子孙的血统即有争议问题。历代封建政权,多有打着优待帮助其统治的历史人物子孙的政策,以此来笼络人心。也就有了婺源朱姓自称为朱熹之后,朱熹生活过的尤溪和建阳朱姓相互呼应。由于古代朝鲜信仰儒教,于是就有朱熹后人迁徙韩国的虚构史实。也有了所谓的世界各地的朱熹子孙。连接的谱牒均为伪造。
《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读后感(二):校译癖 | 族谱是宗族的宪章Charters
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是在钱航先生发表在《史林》2000年第三期的文章上。钱氏对这句话的翻译是:
quot;族谱对世系群的发展和结构具有影响,并成为世系群的宪章",原话是"Genealogie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e of the lineages for which they constituted the charters".
这个是弗里德曼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今天看见笔记里写了这样没头没尾一句,怕是自己出现了幻觉,就去找原文,不过彼时我没有看过英文原版,只看过2000年出版的中译本。发现咋找不到呢?去对了一下中文版发现,中译版翻译是这样的:
quot;…在下文中我们有必要考察族谱与他们制定契约的宗族发展和宗族结构之间的关联。"(在第6页)
然后发现实际上钱氏引的是后半句。整句刘志伟先生也曾经提到过,但是因为和前文联系很紧,所以应该整体理解,乃是这样一句话:
In fact we know that the truly Chinese population of the region goes back much further; by T'ang times the south-east was a real part of the Empire. It is therefore a problem to decide why the lineage system as we know it in modern times should not extend back conceptually to the full depth of Chinese settlement in the area. This problem, because of the historical question involved, lies out side the scope of this essay, but we shall later need to examine the bearing of written genealogie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e of the lineages for which they constituted the charters. (在58英文版第一章第7-8页,但我建议还是看一下再引)
整理一下语序大概是written genealogies constituted the charters of lineages,in the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e of the lineges, and we need to examine the bearing later. (整理的不对请方家指教)
好了。如果下次有人不清楚这句话的出处、页码和context,可以到网上搜一搜,保不齐我这篇跳将出来,就节省了一个小时破案时间。又有人问我你写这个有什么用,有什么问题意识。听好杠精,本探就是一个烧砖的,砖块烧好,愿意拿去垒厕所,就去垒厕所,愿意拿去垒长城,就去垒长城。虽然自己学艺不精,但是还是要时刻不忘为人民服务。
《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读后感(三):强宗族,弱个体
《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一书将关注点放在分布在中国福建、广东两个省的宗族组织上,认为宗族组织内部因资源分配的不平均和流动的可能性形成了分化。本书也是围绕着宗族组织这个分化社会中的单系亲属组织和集权政治体系来进行探讨。
这种在中国东南部的以父系继嗣为主的单系亲属组织一般会形成村落。在宗族组织中,因资源不均分配和自由流动会导致宗族社区发生分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一是政治——权力层面:在宗族组织中,权力一是经由先赋型权力产生,宗族、宗支的首领以及各房的家长之所以能拥有权力,是因为他们辈分最高、在同辈中年龄最大;但是为了防止宗族组织中出现辈分大年龄小的特殊情况,村落里同时还会出现一位以年龄为标准而出现的村落首领。村落首领可能是宗族体系首领中的某一人,也有可能只是宗族体系里的普通人。二是自致型权力,这种权力的产生方式也分两种,第一种是通过‘正规’模式,即通过读书获取国家考试的资格;第二种是通过‘非正规模式’,即是运用本身的经济实力来捐一个学衔。
二是经济——财富方面:除了因为政治权力带来的财富以外,财富来源多样化。对于宗族成员中的个人而言,财富可能来自于男耕女织的传统型小农经济模式;也可能来自于当地的商业化,当地有地区生产适合市场销路的稻米和丝织品,还有一些靠近通商口岸的地区生产糖和茶叶作为收入来源;也可能来自于某个人的本领或技术,例如技术性劳动者、非技术性劳动者等。而将视角放到宗族这个整体中,就能发现在中国东南部的宗族组织中存在着一个与中国其他地区不同的现象:土地的共同拥有在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宗族和村落共同拥有土地,土地按不同归属可分为村田、族田、房支田等,田地上所获取的收入用于各种不同的开支。族田由成员轮值,轮值成员承担节庆和礼仪的开支。强宗大族拥有的土地要比弱小的宗族拥有的公共土地多。
三是社会——声望层面:在宗族中,声望有可能是来自祖先的恩惠,若祖先曾在过去有所作为,在宗族的祠堂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其后代若也能在宗族层次上得到对其祖先崇拜的认可,那死者荣耀就可能使生者更加煊赫,提高了他在宗族里的声望。有可能来自当代宗族成员自己的个人努力,比如在政治上取得权力或在经济上获取财富,反过来成功的人们也可能在宗族中提升他祖先的地位,这是一种延迟的互惠。
这三者之间是相互联系,也可以相互转化。政治权力可以获得经济财富,提升社会声望;经济财富可以用来获取政治权力,也可以用来提升社会声望;而社会声望可以更有利于宗族成员在政治权力和经济财富的分层。虽然宗族底层成员有了能够通过自身努力来向上流动的机会,但是先天上就有其局限性,无论是教育观念、能得到的教育资源还是可利用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所要付出的机会成本等方面,都难以获得与宗族组织上层成员同等的资源,更难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
社会分层产生了如下影响:1.使宗族内部分化,宗族分化在横向上可能会形成几个不同的宗支,宗支又可能分化为几个房支,房支又可能分化成几个复合体,复合体可能又分化成几个家庭。在纵向上可能就形成了宗族成员在宗族内部的不同地位。宗族、宗支的首领和宗族中地位较高的人组成宗族委员会,成为宗族权力的中心。2.祭祀方面发生了变化,有地位的人在四代之后的家祭之后得以进入祠堂,享受祠祭,而无甚地位的人则可能在四代的家祭之后,被人遗忘。
从宗族内部的角度看,处于宗族权力中心的人们控制宗族财产并且征集其宗族税收,宗族管理者成为了国家和土地拥有者之间的财政中间人。由于宗族内部和政府机关缺乏对宗族管理者的监督,同时也就产生了宗族共同利益的腐败问题,处于宗族底层的农民可能受到其控制土地的同宗的不公的对待,公共财产除了完成对税收、宗教、世俗费用和教育津贴支付之后剩余财产归那些人所有,宗族内部强势成员还可能对其他成员的控制超出了简单的经济剥削的界限。
从宗族对外的角度看,宗族会与其他宗族进行联姻,也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与其他宗族发生对抗,甚至产生挑衅国家权威的行为。
《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读后感(四):中国东南宗族组织 读书笔记
一、作者简介及写作背景
《中国东南宗族组织》的作者是莫里斯.弗里德曼,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伦敦,其父母是东欧犹太民族的移民。弗里德曼在二战爆发之后曾加入军队,在印度作战。二战后,出于人种学上的兴趣,进入伦敦大学的人类学系学习,并且把他的研究调查点放在了新加坡的华侨社会中,同时先后在印尼、香港、以及新加坡做过田野考察工作。在完成人类学的课程学习后,回到了母校任教,接着转入牛津大学教书。直至他的心脏病发作,才导致他的不幸离世。
这一书的写作背景是弗里德曼在1949—1954年完成了对新加坡华人社会以及印尼和香港的田野调查。尤其是在1957年他出版了《新加坡的华人家庭与婚姻》一书之后,对着田野调查的实证材料,他发现了另外的兴趣点:中国的基层管理结构——宗族。但鉴于当时的政治因素以及敏感的时代背景下,作者无法亲身到中国的东南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因此只能结合大量的对中国基层社会记叙的文献材料,以这样的方式来“想象”出一个接近于真实的中国传统的社会组织形态。这些文献材料的其中主要包括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翼》、《义序的宗族研究》,以及胡先缙、陈翰笙等人的著作,对中国实地考察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文字材料,以及另外一些关于中国的地方志和历史文献等。
尽管这一书在田野上第一手的资料不够充分,但作者的人类学功力弥补了这一点,他充分地发挥了社会学、人类学的建构思维,首次提出了不同的宗族模式,以至于后来的学者在研究宗族的问题上都不能避免地讨论他提出的“非对称性”的宗族分支结构模型、Z型、A型及M型的宗族规模模型。比如科大卫老师写的《皇帝与祖宗》——“ 在他这两本书出版之前,宗族研究只局限于谱牒的文字规条;而在他两本书出版之后,宗族研究遂进入了这些文字规条所赖以产生的社区。”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宗族与乡村政治结构:对南方宗族的研究则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中国之宗族与社会》。”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讲,弗里德曼的这本《中国东南》可以说是把中国的宗族正式地研究考察成了一套供分析宗族问题的理论框架,正式地把中国的宗族问题引进了人类学研究的领域。
二、本书概要
在《中国东南》这本书里面有15个章节,作者主要是围绕着宗族及内部结构、村落生活、家庭与家户、宗族内部的等级制度及权力分配、祖先崇拜与宗族结构及宗族模式等6个方面进行展开描述,以下的内容主要是围绕上面的6方面进行简单描述。
宗族及内部结构:在作者考察的文献资料里,东南地区的两省——广东与福建的宗族和村落是明显地重叠交织在一起的,以致许多村落只有单姓宗族。而且作者考察后认为——我国东南地区的宗族更像是政治与地方的组织,而不是一种表面上的亲属关系的组织。作者还发现一些特有的宗族现象——宗族之内一般都会有相关的族规或规范。比如说: 同姓之间不能婚配,这不仅是因为同姓之间的婚姻风俗规范,而且加上因为与官方的法律相违反了。于是面对这种情况,宗族内部人员之间产生了 “五服”之分。
村落生活:中国东南地区的宗族组织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重视类似于族产、庙产等公共财产的收益,而且宗族内部的分配是存在着不平等的关系。作者通过考察有关福建和广东村落地区的文献材料,发现宗族内部大都是通过经济优势或者政治性的资本——官员,用强势的经济实力对弱势的群体进行控制或者剥削,宗族与宗族之间的剥削大致也是这样,大的强势的宗族对其他弱小宗族的剥削情况并不罕见。
家庭与家户:在福建和广东地区的村落,人们大多还是传统的父系社会,所以嫁出去的女性大都是“从夫居”的形式。但作者发现不同地区的家庭或家户又会有不同的划分标准。库尔伯以广东省凤凰村为例,区分了自然家庭和经济家庭; 兰女士将福建的农民家庭分成配偶家庭、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 而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也对华北地区的农村进行了“家”、“灶”、“院”等的分类。
宗族内部的等级制度及权力分配:关于继嗣群体的等级,弗里德曼以林耀华在其论文中构建的等级为起点——个人、婚姻群体、基本家庭、联合家庭、户、小支、大支、房、宗族,弗里德曼在此基础上批判性地认为——根据家庭的数目,产生出一个家庭的复合体,而具有威望的家长成为复合体的首领,首领的主要功能在于参加祠堂举行的会议,他们在复合体的祖先崇拜仪式中是主要的祭拜者。因此,复合体的首领存在的作用,不仅在于经济上,也在于政治上、外交上以及宗教上。
祖先崇拜与宗族结构及宗族模式:弗里德曼还通过前人的材料细致考察了东南地区汉人宗族的结构。并在这基础上认为宗族内部模式主要是根据祖先崇拜的仪式以及宗族的规模而界定的,一端是家户——家庭和扩大的家庭,另一端是宗族和房支。家祭中的祖先一般限定在五服之内,甚至只有新去世的直系亲属,是一种单纯的对亲属的纪念仪式,祖先被视为对其有贡献的个体。而在集体性的祭祀当中的祖先则被当做宗族中的裂变群体单位来祭祀,被认为是远祖或者是非个人化的祖先。
三、个人看法
关于这本《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的看法主要还是源自于我所在的乡村地区——两广地区的某个小山村来结合论述。同样的我生长的村落也是一个单姓村庄或者是单姓宗族,主要是以“*”姓为主。虽说是单姓宗族,但所在的村落中并不止一间祠堂,人们划分成为宗族的依据标准似乎也是不一样的,而且人们是依据祠堂的不同而构建一种不同的群体认同感。鉴于这样的情况,我尝试结合我当地的实际情况,以弗里德曼式的人类学视角来论述我在阅读《中国东南》一书而产生的几个问题。
第一点,宗族的功能到底有什么?弗里德曼在这本书里面也讲过——“在农民之间这种组织是一种地方组织,而不是一种亲属组织……东南地区的宗族当然是一种地方与政治组织”以及后来他提出来的“宗族其实是一个法人代表”。而在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中也提到“宗族在典章、仪式及组织方面的特征使它成为了权力文化网络中一种典型结构……并操纵着传统的政治机制。”所以在学者研究的范式里,宗族的功能不止是地方武装组织,还有是国家与地方社会联结的政治组织,更是某种实质上的控股机构。把眼光放到我的熟悉的小村庄上,宗族对于边远山区的人们来讲,最实际的作用可以说是具有地方军事化程度的武装组织。人们把居住的地方建筑建成了类似于福建土楼式的四合院,而且在其建筑四周的角落武装成了一个碉堡楼,正门口装上了用木材做的防盗门等等。以上描述的种种迹象,都在告诉我们,处于边远地区的宗族组织更像是科大卫在《皇帝与祖宗》里所说的——一种地方军事化力量的武装组织,但说到底这种军事化组织还是在围绕着宗族间共同的利益而存在的。
这也牵扯出第二个问题——既然宗族存在的最大作用是地方武装组织,那么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跟西方社会中的什么地区组织是相同或相似的呢?我们身边的地方宗族在一方面来看,从经济学的视角或者是从利益的角度来看是一种控产机构的合作形式;但从另一角度来阐述,宗族还是一个管理人的组织或者是机构,而且从地区范围来讲宗族还是一个地方上小范围的组织,管理的人数都不会超出2000人。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与希腊小国城邦自治的直接民主的管理模式是非常相似的。但相对于希腊雅典时期的直接民主——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内,所有公民都亲身参与一切治理或曰治理活动。宗族内部的管理模式更像是一种直接民主倾向的管理,它还没有完全程度的直接民主,由于宗族的管理者往往是有财富、有威望——政治资本的长者,但同时村民可以因为是宗族成员的身份而拥有部分或完整的话语权以及相对特权。所以说宗族更像是“初级版”的直接民主管理。
第三个问题,是宗族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以来才会大量发展起来的地方组织,一直发展到现在它在我们当中仍有它自身存在的价值跟合法性,但在未来的时间维度里,现代宗族存在的合法性又是在哪里?会不会走向灭亡?在未来走向灭亡的理由又是什么?在这里我们可以大胆而又合理的做出自己的猜想或是假设——宗族最终会走向灭亡的趋势。我尤其赞成赵思渊的论文《微型宗族组织的衰落过程研究》——在这一案例中,人口损失是宗族衰落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来说,由于时代的全球化趋势越来越强烈,人口流动与人口迁移也越来越频繁。这就造成了村庄尤其是边远山区里的宗族组织的人群在不断减少,而且由于现代科学知识的兴起与冲击,宗族的那套仪式以及构建而成的理论体系被现代知识体系斥之为“封建迷信”。所以反观当下的村庄里的宗族仪式大都是一些年老的长辈在主持着,而年轻人相对少了宗族的参与感。加上城乡之间的遥远的距离,会使得一些风俗节日也很少人参加或者说少了很多节日的仪式感,以上的种种因素都是极为不利于宗族的构建或者合法性的存在,同时也是造成宗族最终走向衰落的趋势。
参考文献
[1]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M].刘小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香)科大卫著.皇帝和祖宗 华南的国家与宗族[K]. 卜永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11.
[3](美)杜赞奇著.文化、权力与国家[G].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4]钱杭.莫里斯·弗里德曼与《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J].史林, 2000.
[5]杨春宇,胡鸿保.弗里德曼及其汉人社会的人类学研究———兼评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J].开放时代,2001,(11).
[6]韩水法.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天津社会科学学报,2011,03,23.
[7]赵思渊.微型宗族组织的衰落过程研究——歙县驼岗萧江氏的世系演变与祀产经营(1869—1928).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05,10.
《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读后感(五):钱杭:莫里斯•弗利德曼与《东南部中国的宗族组织
一
有关莫里斯·弗利德曼的生平、履历、业绩和他的学问背景,笔者已在《莫里斯·弗利德曼与〈中国宗族与社会:福建与广东〉》[1] 一文中做了较全面的介绍。出版于1958年的《东南部中国的中国组织》(以下简称《东南》)一书,是莫里斯·弗利德曼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社会人类学方法,以一种整体构想的形式来重新理解旧中国社会的初次尝试;而1966年出版的《中国的宗族与社会》(以下简称《中国宗族》),则是遵循着《东南》一书所提出的框架,在实践中对新出现的问题的进一步探索。两书在结构上密切关连,相辅相成。如果勉为区分的话,《东南》一书通过系统整理作者所定义的“中国学的人类学”(Sinological Anthropology)的学术史,率先在以中国宗族为对象的研究中推出了“世系群”(lineage)分析模型的构想,奠定了以社会人类学为理论指针的中国宗族研究的学术基础;而《中国宗族》一书则是通过分析1958年以来新收集的实例,实践并完善了这一分析模型。笔者是先读1966年的《中国宗族》,再读1958年的《东南》;读毕发现,这个阅读顺序完全应该倒过来。这不仅因为两书的写作顺序本来如此,后书构成了前书的基础,而且因为《东南》一书中讨论的许多问题已被《中国宗族》所忽略,或曰超越。而恰恰是这些问题,可以带给研究者许多新的启发。
《东南》全书内容非常丰富,本文所及仅是其中三个断片,可说是对“新启发”的断想。
二、宗族与“世系群”(lineage)
从一开始,弗利德曼就用“世系群”一词来对译中国的“宗族”;但同时,弗利德曼又从来没有认为世系群就是宗族。这似乎不符合逻辑。然而这正是弗利德曼在理论上的精确和高明之处。他知道,世系群是一个来源于非洲研究的社会人类学的分析概念,它主要是指这样一种亲族集团:以共同的祖先为中介,成员之间能够明确寻找到单系的系谱关系———父系或母系。一般情况下,它是一个实行外婚制的,拥有共同财产和独自的运营组织的团体。其内部也根据同样的原理形成分支。现代社会人类学著作对单系集团又作了进一步的区分,即分为能具体、清晰地寻找到系谱关系的世系群(实体性组织),和在这之上的、系谱关系模糊的、互相的联结仅仅依靠关于祖先的神话性传承的clan(习惯上译为“氏族”的虚拟性组织)。总之,世系群是单系亲族组织,但这单系组织的性质却并不确定,可以是父系,也可以是母系;可以是实体,也可以是虚拟;而中国的宗族毫无疑问肯定是父系实体性组织,这就使宗族只有在特定的前提下才能被称为世系群之一种。弗利德曼在需要精确的时候,比如在第四章《男系单位的层次》(The Hierarchy of Agnatic Units)中,对“宗族”直接使用汉语拼音tsung-tsu,就反映了他在理论上的深沉。
弗利德曼对这两个术语的处理方式逐渐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已故社会人类学家王崧兴认为,“宗族”是中国社会、文化中的一个民俗语汇,而“世系群”则是来自英语的人类学术语,将两者直接对应显然不妥,原因是:
民 由于民俗语汇没有如专门用语那样的严格定义,因此容易引起各种问题。以lineage为例。中文译文为“世系群”,但也常用民俗语汇译为“宗族”。然而中国社会中的“宗族”未必与人类学术语lineage的定义完全一致,把宗族作为专门用语显然会发生很多困惑。[2]
王崧兴发生“困惑”感觉是对的,但“困惑”之所以发生,并非因为宗族这一“民俗语汇”没有“严格定义”;恰恰相反,宗族自古有严格定义,详见《尔雅·释亲》“宗族”章、班固《白虎通德论》卷八“宗族”章。宗族与世系群的区别,从根本上说,前者是客观实体,后者是分析原则。两者的联接必须依靠理论说明作为中介,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不知是不是有意地想避开这类“困惑”,有些学者尝试着走了一步偏棋。如日本学者田中真砂子在研究“单系世系群”时,就曾经把lineage改译为“系族”。原文是:
基于与一个始祖或一组始祖(一般情况下采取“始祖—配偶”联接的形式)之间共同的系谱关系而形成的、被人们自觉认识到的亲族集团,称为继嗣集团(descent group)。在社会人类学著作中,虽然分别将其中可以明确寻找到与特定始祖关系的集团,称为“系族”(lineage),而将无法加以确定的集团,称为“氏族”(clan),然而在实际过程中将两者清晰地区分常常难以做到。在同时存在氏族和系族的社会中,系族往往是氏族的一个分支;但是还有仅存在氏族的社会和仅存在系族的社会,甚至还有两者都不存在的社会。[3]
这一译法至今尚未在国际人类学界获得认真回应。笔者以为,既然lineage是对实行单系世系原则的亲族组织的一种描述方法,那么将此术语所泛指的亲族团体称之为“系族”,也未尝不可,至少可以避免弗利德曼以来人们已经感觉到的问题,不与作为中国“民俗语汇”的“宗族”的原意相混淆。当然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宗族与世系群在对译上出现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只有Chinese lineage(即“中国世系群”)一词,直译为“宗族”才较为恰当。
80年代以后,国际人类学界对世系群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和批评。有些批评相当著名,常常被人们引用。如J. Goody在其编著的《东洋的、古代的、原始的:欧亚大陆前近代社会中各种婚姻和家族制度》[4] 一书中警告说,lineage概念具有狭窄僵硬的普遍弊病;被它所忽略的重要问题中,有亲族、婚姻和人口学动态之间的关系,对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关联也没有加以彻底的探索。此外,对居于世系群之下的层次,如以“家”为中心的生产和再生产集团、财产和习惯、家户、家族、农商工经营联合体、居住集团等等问题注意不够,对地域和地区的偏差也有忽略的倾向。Goody指出,一般来说,莫里斯·弗利德曼的分析模型没有表现出他具有很深的文化偏见,但由于他对东南亚华侨中亲族关系的强大程度,有一些先入为主的看法,因此就偏向于从世系群的观点来解释一切。
这一批评似乎有些不着边际。“世系群”是社会人类学众多分析概念中的一个,其逻辑前提和有用性基础,建立在一个经过严格限制的学术范围之内。若要超出它的规定,研究“它所忽略的重要问题”,尽管研究就是了,与它本身的“狭窄僵硬”何干?弗利德曼对世系群理论的把握无疑是有缺陷的,但缺陷不是他涉及的研究领域不够宽,而恰恰是他没有更为集中地研究对于世系群术语来说属于最本质规定的“世系”问题,反而过多地关心世系群外在的功能问题。从类似的批评看来,弗利德曼的许多批评者本身也未必对世系群与宗族的区别有比弗利德曼更清醒的认识。
在弗利德曼之后,有学者认为应该对中国社会中实际存在的各类世系集团作出不同的区分,即⑴注重共有族产的广东“股份公司”(corporation)型世系群;⑵其族产仅限于仪礼目的的长江流域的中等规模集团;⑶华北地区程度较低的公司型继嗣集团,等等。弗利德曼的好友A.Wolf也将中国南方的世系群组织区分为三种类型,⑴拥有族产的corporation型世系群;⑵只具备祠堂、祖坟的世系群;⑶虽然编纂了族谱,但没有显示出公司类型的世系群。[5] 诸如此类的细致划分,当然有相应的实证资料作支持,在理论上也有一定的意义;但从根本上说来,也不过是世系群功能主义研究策略的进一步发挥;既没有最大限度地弥补弗利德曼的缺陷,也没有把宗族与世系群的关系整理得更加清楚一些。
三、族谱是宗族的“宪章”(charters)
这是弗利德曼在第一章《福建、广东地区的村落及世系群》(Village and Lineage in Fukien and Kwangtung)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原文是:
族谱对世系群的发展和结构具有影响,并成为世系群的宪章。(Genealogie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e of the lineages for which they constituted the charters.)
这种“宪章”性质,主要表现在族谱与宗族之间的具体关系上。弗利德曼在第八章《世系群内部的权力分配》(The Differention of Power within the Lineage)中,分析了以下三个层次。
一,族谱明确了世系群成员的范围。每隔一至二代,就将积累的婚姻、出生和死亡的材料加入已有的内容之中。当然,这里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有的宗族规定,在把出生情况加入新修订的族谱时,需要征收一定数量的费用,这就使得世系群成员资料的完整性,受到外在经济条件的制约而大受影响。
二,族谱记录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宗族的现实要求。弗利德曼以中国学者胡先晋研究江西谭姓宗族的成果说明,由于宗族内各分支的不均衡发展,导致出现人数和财力方面实力不等的分支;一旦发生这种结果,宗族管理者就会综合平衡各方利益,在世系群内部进行重新编组。比如由于谭姓宗族在成员数量和财富方面出现了不均衡的发展,于是,就先将一个超过所有分支规模的最大分支(房)分解成五份,随后再将其余各房合并为两个部分。通过引进防止一房独大、一房垄断的新制度,使全族各分支的力量获得了新的均衡。谭姓宗族的族谱忠实地记录了这一过程,使之成为一个体现了宗族规范的范例,供谭姓后人参照。在《中国宗族》一书的第四章《世系群间的关系》(Relations between Lineages)中,弗利德曼重申了这个观点:“大规模的族谱是作为潜在的世系集团的一部宪章,因此它向我们揭示了这一集团结构上的重要关系。”
三,族谱本身也有一套独立的规则,有时表现得相当程式化,弗利德曼将这一特征称为“编纂族谱的方式缺乏可塑性”。这就使得族谱往往滞后于宗族内部发生的变化。族谱作为历史资料的可贵性和保守性,就集中地表现在这一点上。
弗利德曼关于族谱是宗族“宪章”的阐述,具有深刻而“辩证”的意义。族谱不是普及读物;族谱既不是为学者生产的,也不是为现在许多试图开发族谱的“价值”、将族谱纳入某种文化产业的经营者、策划者生产的。族谱的印刷数量受到严格控制,族谱保存者的资格和收藏条件也有严格规定。一般族人最关心的是有没有族谱和自己上没上族谱,至于族谱上具体写什么,怎么写,他们并不十分在乎。普通宗族成员对本族历史的了解,主要是基于世代相传且高度简化的口头传承,很少是通过阅读谱中广博繁琐且不无庞杂的考证、转述和世系表而获得。除非遇到特别严重的纠纷,需要援引族谱中的某些记载来加以证实,族谱在宗族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功能相当有限,可以说基本上是奉为神明,束之高阁。为人津津乐道的所谓族谱教化、惩戒功能,大部分是研究者后来赋予它的。族谱中的这部分内容,大多体现了族谱编撰者们世代相传的理想,仅在很有限的程度上简略地记录了宗族的实际生活状态和所遵循的规范,而并不是相反;宗族日常生活的组织和运转,靠的是既定的世系规则和共同的经济利益,不需要依靠族谱的道德说教。对于普通族人来说,谱牒内容的重要性,远远不及谱牒编撰活动所体现的宗族一体化以及其他象征意义。
学者们现在所看到的族谱,无论就其文本形式,还是就其精神实质而言,都已经脱离了它原来的生存状态。在这一意义上,研究者手中的族谱,已不再是有生命的、与当事人的实际利益联系在一起的东西,而是成了局外人用以观察当事人生活及其环境的工具之一。我们之所以不应轻视族谱,也不应过于夸大族谱地位的基本原因,就在于“工具”和“工具所指”之间的这种距离。对于研究者来说,保持适当的“距离感”不仅非常必要,而且符合事物的本来性质。首先,不要对族谱的编撰抱过高的要求。族谱本不为我们而生产,是否适合“我们的需要”,即为一“假问题”。其次,不要不切实际地夸大族谱的地位。族谱作为宗族“宪章”的性质,决定了族谱作为了解中国宗族生活状态工具之一的特殊地位和局限性。当前有一波将族谱和正史、方志一起,列为所谓中国史学“三大支柱”的热闹宣传,真不知从何说起。且不说这里遗漏了考古、文物、小学、训诂、历法、口述等构筑史学大厦的重镇,就连四部中的经部、集部、子部都未顾及。轻信和传播此类外行话的根本原因,一是没有翻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是对族谱的本来性质缺乏应有的了解。
四、 宗族间的械斗
在第十三章《世系群之间以及跨越世系群的关系》(Relations between and across Lineages)中,弗利德曼表达了对华南地区频繁发生的宗族械斗事件的浓厚兴趣。他根据福建总督1817年向皇帝报告南部蔡、王二氏械斗案、广东总督1828年的报告、刘兴唐对福建亲族组织械斗的详尽记录、陈盛韶的《问俗录》、《泉州府志》所载敕令等公、私文献,全面描述了闽、广地区居民不讲法律,祠堂间发生冲突时举族闹事,动刀动枪,大打出手的热闹场面。如引证刘兴唐的记载,说漳、泉二州人士傲慢而好喧哗,为小事而聚族械斗。在有些地方,械斗又是结拜弟兄和流氓集团活动的结果。但在农村,械斗主要是在世系群之间发生的。赢家要讲和,输家不肯罢休,于是寻机再打。再引陈盛韶《问俗录》中关于福建、广东两省交界处械斗之后的惨状:
携家带口的族内善良人总是最大的受害者。有了一次械斗,富裕者丧失财富;两次械斗后,富裕者变得贫穷;三次械斗后,贫穷者变成乞丐,不久就完全败亡了。(按,此据英文转译。)
弗利德曼综合各类资料,详细介绍了械斗对农村社会秩序和原有生活格局的破坏。其中有作为械斗经费的“丁亩钱”的摊派;各类强制性的捐款;漳州人、泉州人可以抗国税,但不敢抗族内捐款。械斗还会形成超出暴力区域的同盟关系。在诏安县,有势力的世系群把许多弱小的世系群连接在自己的周围,形成更强大的地域集团。他又详细介绍了成书于18世纪的《觉书》中关于械斗发生的原因、械斗前的动员、对参加者的许诺、对死伤者以及须承担法律责任者的安排和对家属的保证等等记载。如引述1836年广州近郊的械斗报告:
两个集团集中了战斗部队,两个村庄的全体村民互相列队对峙。在人数和势力的较量中,互相追击,对立持续2~3天。但是当战斗结束后,两者又象以前一样,恢复到自己的工作中。然而,有时出现死了一个人或更多的人的情况,特别是有一次乱斗中死了4人,伤了20人以上;这时,尽快消除事件,就成了双方共同的利益,绝不向政府报告出现杀人事件。如果出现了法律诉讼,搜查不可避免时,虽然知道在中国对杀人者有严格的法律,但诉讼的嫌疑犯仍不是孤立无援的。当地有一种对付此类事件的奇妙的准备,即所谓“献身者集团”(A band of devoted man)。
这是关于械斗具体经过和善后处理的一个颇具典型性的案例。
有关宗族械斗破坏地方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情况,从来就受到人们的重视,至今仍是证明宗族落后性最强有力的证据之一。就弗利德曼所收集的资料本身而言,其实都是常见的东西;值得读者高度注意的,是他对械斗问题的理论思考。他在对官方报告和民间文献的械斗资料进行了分类比较后,发现“械斗绝不是一种偶发的行为”,而有其结构性原因;也就是说,宗族间频繁发生的械斗在某种意义上是解决农村各种矛盾的一个平衡器。弗利德曼有一段相当精彩的论述:
我们绝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整个东南中国经常处于武装敌对状态之中。但是,福建、广东地域化的世系群之间的相互关系体系,无疑显示了一项证据,即依靠武力来解决各世系群间的矛盾,显然超出通过国家司法机关解决的程度。另一方面,证据虽然详细并不够明确,却已足以证实,交战者双方对导致特定械斗的过程,以及所需的必要的天数和死伤者的人数,都有一个默然的了解。至少在两者实力大致相当时,在一次交锋中,如果追溯过去历代械斗的情况来看,双方伤亡人员的总数,基本保持平衡。
弗利德曼对械斗发生客观上的平衡作用设定了一个前提条件,即“在两者实力大致相当时”;并指出“在双方实力不平衡的时候,械斗的结果将导致大族对小族的欺压。”这是他的思维严密之处。但实际上,大量的历史调查已经证明,一次械斗以后,导致械斗的最尖锐的矛盾---族间血仇、宿怨等---就会得到一定的缓解;而其缓解的程度恰与械斗的烈度成正比,所谓“打得越凶,解决得越彻底”。械斗的发动,常常就是走向和解谈判和诉诸司法程序的第一步;甚至是呼唤外界可以进行干预的一个信号。作为交战双方,一旦在各自一方出现一定数量的死伤者以后,可以预料战斗就会中止。国家并不是与冲突有关的唯一的第三者,还有他们的近邻,因此械斗绝不会升级为全面的战争。正如弗利德曼在《中国宗族》一书第四章《世系群间的关系》(Relations brtween Lineages)中所补充的那样:
东南中国连续的争斗最好应该被看做是“宿仇”(vendetta)间战斗的一种方式。由于具有代代相传的敌意,一个集团与别的集团形成对立的局面,发展到现在也有可能拿起武器相互进行杀戮。但是,他们也都有准备,一旦骚乱过后就接受仲裁。……世系群在关于女性的问题上尤其是相互依存的。一旦面对共同的危机,它们会协力合作。但是它们的利害又是多样性的,在政治上以及经济上都会发生冲突。这时,集团就互相拿起了武器。或者被杀,或者被抓住当作苦力被卖掉。但是,械斗并不是以灭绝为目的、以公然的服从为目的的“战争”。……世系群拿起武器,是一个制度的一部分。
当然,这并不是说宗族间或村落间的械斗所带来的社会性破坏不值得批评,而是指出这样一个事实:社会矛盾是客观存在,矛盾的解决依靠自我调节和司法管理;如果械斗频繁而普遍地发生,则说明社会矛盾的调控机制麻木了,迟钝了。在这种情况下,械斗不仅属于社会矛盾自我调节的范畴,而且还是促使调控机制重返正常化的推进力量。
弗利德曼关于宗族械斗问题的研究成果,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如能引起学者的广泛注意,将有利于推动社会史研究的进展。
(原载《史林》2000年第3期)
--------------------------------------------------------------------------------
[1] 《史林》,1999年第3期。
[2] 王崧兴:《关于人类学语汇的对译问题》,《中国文化人类学文献解题》,末成道男编,东京大学出版会,1995年。附录之五《人类学语汇英、中、日文对照表》序。
[3]《事典·家族》,比较家族史学会编,弘文堂,1996年1月。又参见日文版D.米切尔《新社会学辞典》,页68,lineage条。下田直春监译,新泉社,1987年。
[4] The Oriental, the Ancient and the Primitive: Systems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in the Pre-industrial Societies of Eurrasia, 199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 A. P. Wolf, The Origins and Explanation of Variation in the Chinese Kinship System. MS. 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