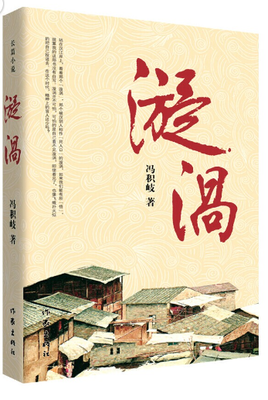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是一本由雷海宗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页数:26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精选点评:
●中国四千年的历史可分为两大周。第一周,由最初至西元383年的淝水之战,大致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外来的血统与文化没有重要的地位。第一周的中国可称为古典的中国。第二周,由西元383年至今日,是北方各族胡族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地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不管在血统上或文化上,都起了大的变化。第二周的中国已不是当初纯华夏族的古典中国,而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一个综合的中国。
●近几月来,心思总不能完全集中,也不知是什么原因,通读了一遍,印象不深
●于文可观,于史则庸
●“于文可观,于史则庸”。
●由于时代原因有些地方感觉过于激烈了,总体是本很有趣的小书
●文字从领会中流出,我只是看这个真切与否,流派之是非吾不论,多见多识自然分别而统摄之。
●太好看了
●居然有几处很明显的错误,商务的编校质量也不敢相信了。殷周年代断代一篇,最觉眼界大开。
●被高估了
●观点有不少新奇独到之处。有此大师,实乃我开之幸。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读后感(一):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李金铮说:“那是一个容易出大师的时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成书于抗战爆发前后,作者有感于国家的贫弱,努力从历史上找原因和解决的办法,再加上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史观的影响,才写出了这本书,提出了“无兵的文化”的命题。今日看来,很显粗糙。但是这一理论毕竟自成一体,还颇有影响,姑且当做一种历史哲学的观点去看吧。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读后感(二):名不虚传
最早听说雷海宗源于社科院的陈乐民,上大学时读过他有关欧洲文化的书,其中极力推荐雷海宗的《西洋文化史纲》,后来购得此书,一看全属大纲性质,虽规模宏大,竟难卒读。后来刘仲敬在访谈中也推荐他的《中国文化和中国的兵》,读完之后才感觉雷海宗果然名不虚传,他浸淫西方史学理论匪浅,于论述中国历史也显露出卓有个性的历史哲学观,书中《中国历史的两周》一篇流露出对中国文化复兴的殷切期望。《雅乐与新声》《古今华北的农事与气候》两文尤其可见雷海宗的考证功力,此为治史学的基本功。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读后感(三):另一视角看兵制
颇有争议的一本小册子,读来酣畅淋漓。反对者则给戴上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短暂军事化思潮的代表,雷海宗先生等“战国策派”也一度被打为右派而湮没于历史洪流之中。套用公司治理的框架,可能更好理解其观点。关键不在于兵制孰优孰劣,而在于其背后的形成机理:
1. 秦汉以上,列国皆小国,持天子“特许经营权”,诸侯国即贵族家族企业。家即是国,国即为家,家国统一,经营权和所有权一致,故贵族人人皆兵,里里外外自家人打理,理所当然,亦足以应对。贵族尚武,习礼乐射御书数,文武兼修,实是早期家族企业家精神所必须。文士与武人尚未分工,亦未职业化,士人兼具家国情怀和侠士精神,并非先秦中国天然为礼乐之邦,亦非彼时人生而为君子,实际是大家族治小国之产物。
2.秦汉以下,大一统,家天下,贵族没落,皇帝作为升级版的国君,面临治大国的新命题,需要职业经理人和雇员帮助打理,尤其地广而人稀,需扩充军队守边戍疆、内征外伐。然大国格局下,家国概念开始背离:家为乡土,具体而现实,国为天下,抽象而空洞。保家有动力,卫国少激励,风险收益不对等,平民百姓不愿从军。故如汉武帝不得不等发囚犯、亡命之徒、恶少年等乌合之众充行伍,士兵逐渐职业化,且愈来愈吸收底层人群。文士与武人两种身份分化。因不再受礼乐传承与家国情怀所牵绊,武人由上流阶层组成之社会中坚沦为由末流阶层组成的社会不稳定因子。从军民合一到军民分离再到军民对立,实际是皇权集中治大国之产物。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读后感(四):消极两千年
中国政治自春秋以降,没有贵族,只有流民游士,没有德行,只有机会权术。
雷海宗先生还是太天真了。其天真之处表现在: 一、他写了“世袭以外的大位继承法”一文。给中国乃至世界上其他共和国家之政治实权领袖的更替承袭提供参考? 二、恢复战国以上文武并重的文化。尤其强调每个国民,尤其是处在社会领袖地位的人,必须文武兼备。非如此,不能有光明磊落的人格,不能创造光明磊落的文化,社会不能有光明磊落的风气! 中国文化第三周(第三周纯属雷先生不切实际的妄想)的崭新生命力的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武德”。要抛弃文德的劣根性。 由军民不分,经军民分立,到军民不两立...... 兼文武的社会是一个比较光明坦白的社会,这是武德的特征。中国两千多年来社会上下的卑鄙黑暗恐怕都是畸形发展的重文德的产物。偏重文德使人文弱,文弱的个人和文弱的社会难以有坦白光明的风度,只知使用心计,虚伪,欺诈的风气支配一切。中国兵制的破裂和整个文化的不健全其实是同一回事。只有振兴武德,叫良民当兵(而不是只让贫民、流民、外族、囚徒当兵),尤其是一般的所谓的“士大夫”都人人知兵,人人当兵,才能使中国自立自强。 P88:
一切宪法的歧义与政体的花样不过都是门面与装饰品而已。换句话说,政治社会生活总逃不出多数平民为少数特权阶级所统治或全体人民为一人所统治的两种方式。 P89——91: 没有真正阶级分别的民众必定是一盘散沙,团结力日减以至于消灭。命定论变成人心普遍的信仰,富贵贫贱都听天命,算命看相升到哲学的地位。这样的民族是最自私自利、最不进取的。别人的痛苦与自己无关。团体的利害更无人顾及,一切都由命去摆布。 皇帝制的离心力日盛,向心力日衰,所以皇帝必须把自己神话来加强他的维系力。因此皇帝、皇室的庙布满各地是震慑人心的一个巧妙办法。经过西汉二百年的训练,一般人民对于皇帝的态度真与敬鬼神的心理相同。皇帝的崇拜根深蒂固,经过长期的锻炼,单一的连锁已成纯钢,内在的势力绝无可能把它折断。若无外力的强烈压迫,这种皇帝制是永久不变的。 多数人如果反对皇帝制,他必难成功。但这些消极的人民也都默认。所以皇帝制可说是皇帝的积极建设与人民的消极拥护所造成的。
P105: 「士大夫与流氓」 乱世士大夫的行为几乎都是误国误民的,主要表现在三点: 一、无谓的结党误国。东汉末的党祸,宋代的新旧党争,明末的结党是三个最明显的例子。三例都是在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下的结党营私行为。起初的动机无论是否纯粹,到后来都变成了意气之争与权力的竞争。大家都宁可误国,也不肯牺牲自己的意见与颜面,当然不肯放弃自己的私利。
二、清淡。最典型的就是魏晋时代的清静无为主义。胡人已经把凉州、并州、幽州(略等于今天甘肃、山西、河北三省)大部殖民化,中国的内政与民生也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一些负政治责任的人与很多在野的人仍在谈玄,这可说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行为。
三、作汉奸。作汉奸当然不必需要士大夫,但第一等的汉奸却只有士大夫才有资格去作。比如洪承畴是进士出身。 在太平时代,流氓不能与士大夫严重对抗,并且往往为士大夫所利用:大则为国家的武官或捕快。小则为士大夫个人的保镖。由流氓团体的立场来看,这是同类相残的举动,可说是士大夫“以夷制夷”伎俩成功的表现。 但遇到乱世,士大夫所依靠的皇帝与组织失去效用,流氓集团就可临时得势。天下大乱,大则各地割据的土皇帝一部为流氓头目出身,小则土匪遍地,各地人民以及士大夫都要受到流氓地痞的威胁与侵凌。人民除了正式为宫廷纳税外,还要法外与土匪纳保护费,否则身家财产都难保障。士大夫为自保起见,往往被迫加入流氓团体,为匪徒奔走,正如太平时代士大夫的利用流氓一样。 一二流的流氓头目如汉高祖与明太祖都是历史上有名的这类人物。他们成事最少一部分须靠士大夫的帮助,成事之后更需要靠士大夫的力量去保守成业,天下的权力于是无形中又由流氓转移到了士大夫的手里。
作者提出了中国文化二周乃至三周的论点,大致是说,第一周,由最初至西元383年的淝水之战,大致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外来的血统与文化没有重要的地位。第一周的中国可称为古典的中国。第二周,由西元383年至今日,是北方五胡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地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不管在血统上或文化上,都起了大的变化。第二周的中国已不是当初纯华夏的古典中国,而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一个被入侵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