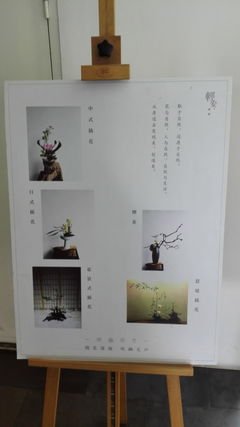
《汪曾祺全集(2)》是一本由汪曾祺著作,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无盘)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54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汪曾祺全集(2)》精选点评:
●下载在手机里,每次上下班的地铁看一点,一流的小说家,犀利而温和
●自然清新有爱
●汪老的文笔清新有韵致,寥寥几笔,人物 环境跃然纸上。故事的结尾多是“没有了”,旁观者的叙事,冷静而悲凉。
●老汪小说真是写得太霸道了,写人写物活灵活现,我都找不着词汇来赞美了,这本水平比较平均,不像一,好的特别好,但是有几篇比较差的,我想特别说说那篇【薛大娘】老汪赞美这个拉皮条的女人身心健康,舒舒展展无拘无束,他未必真这么想,只是出了自己胸中一口恶气,他被压迫太久了,写东西畏畏缩缩,好在手中笔没折断,所以他讴歌自由,赞美任何情况下的无拘束,就算是做坏事情也罢,一个自由的人有自由的做坏事的权力,老汪要自由,这个必须有,有这样才华的家伙不应该被任何名义借口下的桎梏所束缚,真喜欢他的短篇啊
●当代作家难有可比拟者
●高中时逃掉的数学课
●汪老爷子的文笔永远氤氲着江南水乡的雾气,一颗长不大的童心,平平淡淡,自自在在,而撩人心弦。
●当代大陆短篇第一人。
●最喜欢汪老的文字,无论小说还是食评都很接地气,一边写人,一边写人文,一边写事,也一边写风俗,信手拈来,其味入骨,值得反复咀嚼。
●清新明快
《汪曾祺全集(2)》读后感(一):遇见汪曾祺
他的文章很通透!这是我第一次的读他文章的感觉,那时候我高一。我不喜欢读散文类的一些文章,但是他的文章是意外啊!他的散文能给我对生活和自己的一些折射,无论写景,人,还是美食。
《汪曾祺全集(2)》读后感(二):我所敬仰的汪曾祺(前言)
我,看过的书按说不少了,说那啥一点,也算个文学爱好者。喜欢的作家、作品很多,从古代的『三国』、『水浒』、『浮生六记』、李白、曹操;到现代当代的贾平凹、方方、迟莉、鲁迅、金庸、史铁生;再到回龙观网上的韦小宝宝、告别的年代上的稻草人、列农……可是仔细想想,谁的作品能让我百读不厌,能让我彻底折服,永远仰视才见,能改变我的文笔风格,能改变我的人生观世界观?
谁,这个银到底是谁??
没错,汪曾祺。
我喜欢叫他老妖精,或者老家伙,老东西,最恭敬的叫法是老头儿,这个老头。为何我如此不敬?非也非也。
老家伙写过一篇关于他父亲的文字:『多年父子成兄弟』。呵呵,和我家里差不多,父子间开玩笑,下棋,打闹,互相损,互相吹捧——除去外人在场,我对我爹的称呼永远是“你”,而不是“您”。嘟猫除了叫我爸爸,称呼也是:你,脏猪爸爸,棒爸爸,不棒的爸爸;称妈妈“小胖儿”……
我对老汪的崇拜和欣赏,老汪自己的文字风格、形象,让我觉得他象个不拘小节的长辈、随和散淡的哥们儿,说是老妖精,其实,他是一个真人。
我慧眼识老妖其实很早很早。我不太确切的记忆中是在『东方少年』还是什么中学生的杂志上看到这样一段文字:
“牛鞭者,牛鸡巴是也。这东西好吃!”——我就想,靠,***文艺作品还可以这样写啊!寥寥几字,全是大白话,却让人流着哈喇子想着:牛鸡巴好吃!——不过很久以后真吃了感觉一般,莫非那天是斗牛士死了?
等到上了大学,才在一家小书店里发现一本汪曾祺的作品集,如获至宝,买来反复的看,反复的看,十分不过瘾。
我至今记得,那天狮子带着他那时的小女朋友,拎着八卷『汪曾祺全集』,一路笑着走进展春园小区。我想这是人间至乐之一,所以屁颠屁颠的亲自下楼来迎接。
从此,老东西的淡黄色书在枕边长伴,很多文章是怎么看都不厌,越看越喜欢,越看越认真,逐字逐句,着了魔一样,直到现在……
《汪曾祺全集(2)》读后感(三):Journal of Reading -- 留白
1987年秋天, 美国加洲San Luis Obispo一家叫<New Times>的报纸发起了一场写作竞赛, 名为"Fifty-Five Fiction", 就是用不多于55个字写一篇小说. 历年的获奖作品多以极赋讽刺的幽默小品为主. 2001年美国的畅销书<The Writer's Block>里, 作者收入了一篇"55-Fiction"的获奖作品, Jeff Whitmore写的"Bedtime Story", 以此作为一个例子来提醒写作者, 经济的使用语言在文学写作中有可能会获得异忽寻常的效果.
edtime Story
quot;Careful, honey, it's loaded," he said, re-entering the bedroom.
Her back rested against the headboard. "This for your wife?"
quot;No. Too chancy. I'm hiring a professional."
quot;How about me?"
He smirked. "Cute. But who'd be dumb enough to hire a lady hit man?"
he wet her lips, sighting along the barrel.
quot;Your wife."
“小心,亲爱的,上过堂了” 他边说边回到卧室。
她倚着床头。“为你妻子准备的?”
“不,那样太危险。我雇了个专业的。”
“你看我怎么样?”
他假笑道“不错。但是谁会傻到去找一个女杀手?”
她添湿了她的嘴唇,眼睛顺着枪管瞄过去。
“你妻子。”
这篇"小小说"总共53个字, 6句对白, 3个动作, 2个表情. 从头至尾读下来, 用不了30秒. 但就在这30秒之内, 你将会经历一个心被刹那间揪起, 然后顿生悬疑, 随之感到恐怖, 既而永远也无法释然的心理变化. 随着卧室里两个人看似舒散的对话, 你一句我一句之间, 弦被越拉越紧. 直到小说进行到第51个字的时候, 高潮来临. 镜头最终聚焦在女人两眼之间的枪管上. 镜头下方是她正在添湿她的嘴唇.
惊悚, 悬疑, 谋杀, 背叛, 复仇, 性感.... 这好象也是好莱坞的杀手锏. 但这篇小说聪明就聪明在它到最后也没有把早已张紧的弦给你松开. Jeff Whitmore写了53个字, 每个都不浪费. 如果他足够愚蠢的话, 本可以再加上一声, 或是两声枪鸣. 可惜他很聪明. 他知道, 如若再添一笔, 他就不是作家了.
换句话说, 即使是一篇短如五十来字的故事, 好的作家, 也会留一手. 其实, 故事的"好"与"坏", 往往不在其曲折, 也不在其篇幅, 而就取决于讲故事的人会不会给你留那么一手, 给你一个阖卷沉思的余地.
在中国, 这就叫留白. 在我读到过的很有限很有限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里, 能像中国园林, 戏曲和字画一样把留白留出意境来的作家, 一是老舍, 一是汪曾祺. 张大春的<小说稗类>里, 曾经提到过老舍的一个短篇<断魂枪>. 在我看来, 张大春提到的小说中的"速度感", 在这个例子里面也就是一种"留白", 也即是老舍留的一手. 小说最后那疾驰而过的六十四枪, 和末尾那句"微微一笑, '不传!不传!'", 实在是大境界. 相形之下, Jeff Whitmore之流充其量只是个狡猾的写手而已.
汪曾祺则是另一个很会留白的作家. 也许和他谙熟中国字画和京戏有关, 他的小说总是开始的不紧不慢, 发展的不疾不驰, 晃晃悠悠的看到一半, 似乎连情节都找不到; 但突然间寥寥挥上几笔, 就是一个高潮, 仿佛就点石成金了. 他的小说往往把高潮都安排在最后, 而且不会给你写尽, 就好比一大段特写蒙太奇过后镜头缓缓的拉开, 远处的山, 水, 芦苇, 群燕依次入画, 渐渐的形成一幅泼墨山水. 他的小说<受戒>里, 主人公明海在受戒之后被小英子接上回家的船. 路途之上, 小英子从寺里的方丈问到方丈的小老婆. 她不紧不慢的问, 不紧不慢的划. 这时----
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
“你说话呀!”
明子说:“嗯。”
“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
明子大声地说:“要!”
“你喊什么!”
明子小小声说:“要——!”
“快点划!”
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
(完)
正所谓意广象圆, 象有限而意无边. 说实话, 这片芦花荡远比端着手枪用舌头舔唇的女孩要性感, 要美许多.
20 September 2005, Melbourne.
《汪曾祺全集(2)》读后感(四):重写?47、82两版《职业》之差异何以发生?
对比汪曾祺47和82年版本的《职业》,我们就可发现不论是从内容、主题还是形式上,这两个版本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同时,我们不该仅仅放入一个历时的框架中思考,认为82年的《职业》是在47年基础上的更加完善的作品,就像是艺术作品除去精雕细琢除去冗余一样。而是透过47年之作,重新审视82年作品中的症候点,那些文本中本应出现却没有出现的话语。(为方便起见,下文的47年与82年的《职业》简化为47、82)
在内容上,47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 着重于 “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 这一职业,第二部分装年灯的工人们。而82,则删去了47年第二部分的内容,只留下第一部分,然而问题出现了,一个只留存有“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这一种职业的作品,何以被命名为《职业》,而非“卖煎饼的孩子”之类的名字呢?面对这种困境,在47的文本中被压抑、被放之边缘的因素——收旧衣烂衫的女人形象得以出现,被放之到作品最显眼的开头,同时伴随着卖化风丹、卖杨梅等具有当地民俗特点的职业出现。
由此,我们看见了一组二元对立,即具有民俗特点的职业与普遍的非民俗的职业(工人)的对立。简单来看,47年是将两者并置的,可以说,民俗特色 这一因素并没有被“问题化”,被放置到核心的位置。而82年则是对后者的排斥与“抹杀”,只留下想表现的当地民俗职业,然而正如拉康的镜像对体的概念所表明的,主体的建构不论在何时都需要他者的存在,特色化的当地化的特点恰恰得依靠与普遍的职业的对比,才更能确立自身的地位,而82年的排斥与抹杀恰恰是一种狂妄的自以为是的主体意识,更是无法直面他者,对他者的恐惧,毫无疑问,在47年中出现的那个普遍的职业——(装年灯的)工人,不也是传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的必备要素吗?这个何曾不是82年汪曾祺自身的恐惧呢,对那10年以及10年的符号的恐惧呢?82“自大的主体意识”同样是主体的危机——它无法直面他者的恐怖,在47中尚不成为问题的民俗主体,必须在82年被放之到核心的位置以应对主体的危机,从而想象性地建立文本内与外 的“稳定“主体。
然而,47的文本中,却早已“预示”了“民俗”的悖论——抬起头看见的年灯不同样具有当地特色吗?而这种特色维持、存续 却依靠的是普遍的平凡的工人。
在情感方面,47与82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47中第一部分的主角“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的孩子,虽写他成长之迅速老道,并没有任何描写孩子身世之苦难,只有写其乐观与活泼。而82年中则似乎加入了更多“人道主义”的情怀,叙述了孩子身世的悲惨“他是个孤儿,父亲死得早,母亲给人家洗衣服。”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这更多表现了汪曾祺的同情悲悯之意,而更应该说,这种做法乃是服务于更进一步的 (个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在47中的职业是群体化的,而那个男孩只是作为该职业的现实例证,一种“具体的普遍性”,而82的职业是个体化的,收旧衣烂衫的、化风丹、卖杨梅的关联的不是职业群体,而是想象的“个体”,也因此对男孩(那个具体的角色)有更多的着墨,其苦难身世(其实也是一笔带过)不是服务于一种同理心,而是为了使角色更加“现实化”、“个体化”,随后迎来的便是孩子对马匹吆喝的生动场景与欢快奔去外婆家的情形,即出现的是一种美学化的生活,苦难的背景是以反讽的姿态出现的——一个这样经历的孩子,虽然很小便从事着这种职业,却仍然快活地“享受生活”。(一种倒错的“生活宣言”,不正要浮现了吗——纵使我们遭遇了多少危机、苦难与矛盾,但我们的生活却仍然有美好之处,让我们热爱生活吧!)
如果说,47是暗含着一定的职业生活审美化,那么82具有的是强烈的(个人)日常生活审美化,更进一步说,对于82而言,日常生活恰在不断倾轧职业生活,那个“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虽然是孩子的符号身份,他却只有在观看马儿、在去外婆家吃饭的路上、在喊出“捏着鼻子吹洋号”而非“卖椒盐饼子西洋糕”(即在非职业工作)时才愉悦、快活,也只有这时的画面才被审美化。
在此,我们更进一步遭遇了职业与民俗关系的悖论,当某种职业成为民俗生活的一部分,一个代表性的符号,而符号主体却只有在非职业时刻才能脱离、忘却苦难,能够“享受快乐”,那么汪曾祺们 对由此种职业构成的民俗生活大加赞美、夸耀,高喊着“保卫我们的民俗风情”,除了狂妄、自以为是外,还剩下些什么呢(笑)
此外,我们来看形式层面,82与47在形式层面最明显的区别 就在于对“声音”的描写,82将声音置在了核心的位置,包括“收旧衣烂衫的、卖化风丹、卖杨梅”等众多声音,而47对声音的描写则少得多。更进一步的特点是47的声音都是群体性的,是职业群体的声音,如“收旧衣烂衫的是女人多”(女性群体),而82的声音是个体化的,收旧衣烂衫的、化风丹、卖杨梅的关联的不是职业群体,而是想象的“个体”,如文本中这样写道“‘有旧衣烂衫我来卖’……这是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
47的声音是“无人称”的,它没有特定的言说者,也没有特定的接收人,就像爱伦坡的信一样,总是已经在此处的。而82的声音却非常不同,它既有特定的言说者(具体的个体),也有特定的接收人——第一人称的“我”。47中虽也出现第一人称的“我”,却是漂浮不定的,(除了观看外)没有与角色产生任何互动,少有的书写主观感受(在第二部分)也不具有个人化的特点,更像是大家都常有的举措。而82则不同,出现了大量的第一人称的个人感受如“我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脆的嗓子”、“这位xx,想必是板桥的人了”,也有与角色的互动“我去看一个朋友,依门看着”,毫无疑问,与47年相比,第一人称的“我”被个人化了,被主体化了。同时,我们不能仅仅将形式看作单纯的形式本身,恰恰相反,这种形式仍然与内容(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对个人日常生活的审美,正是通过这样特征明显的主体视角,才能得以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