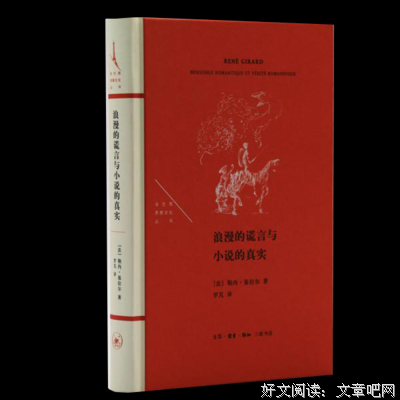
《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是一本由(法)勒内.基拉尔著作,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8.80,页数:3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精选点评:
●好久没看五星书了吧!特棒!相逢恨晚!
●可能是翻译的问题,读不下去
●翻译有些不大不小的错误
●很有意思
●还是高中时候读的书。。。重读一遍。。。
●欲望的三角结构,让人看到的是人世的恐怖,人人都活在这样的世界之下。普鲁斯特《重现的时光》,在他看来还是有所欠缺。但我无疑还是相信,这部作品是人世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文本的结尾某种忏悔性的效果,意味着一种升华。但一些文本失去这种效果并不意味着它没有教育意义,它仅仅是使那种被展示更加明显,用更讽刺的手法让人舍弃这样的生活,伟大如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他提到加缪的《堕落者》,并将之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提并论,当然是他的《地下室手记》这部作品。并坦言,若加缪不是因意外(车祸)而死去,他的文学会发生转向。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在说,加缪会朝着陀思妥耶夫斯基靠近。另外,昆德拉给我的小提示,所谓的法国上流社会,觉得加缪是个粗俗的人。这到底是验证了普鲁斯特还是勒内基拉尔呢?等你告诉我。
●深刻的偏见之典型,对我当时的阶段几乎致命
●接受推荐,非常优秀。稍微懂一点法语更好。从如此经典的著作中发掘出不为人知的秘密,才是我们应该努力的。
●没怎么读懂,不明觉厉,以后阅读量够了再读吧。
●内容:基于欲望摹仿论对现代小说文学所作的历史哲学解释。最终立场是批判人本主义,揄扬基督教。 翻译:中译本根据法文本译出,整体很好,个别地方存在误译。英译本在法文本的基础上变动了部分内容,所以还需参考英译本。
《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读后感(一):三角欲望
勒内吉拉尔是人类学家,借助人类学的理论对文学作品进行评价确实是独辟蹊径,也打开了文学批评的一条新道路。本书奠定了吉拉尔理论的基石,通过分析大量案例揭示了“欲望”促使人不断地对“介体”进行模仿的行为,对立都是虚无的、无意义的,越是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就越容易导致盲目,而欲望的终点是死亡,一切虚无都将在这里获得救赎,这是文学不朽的主题,并非窠臼。
这本书读过之后会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很多行为,关注自己的欲望到底是出自于“自发”还是“竞争”,毕竟,由于介体带来的欲望客体,本身并没有什么重要。会持续关注吉拉尔的集大成理论《替罪羊》。
《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读后感(二):基拉尔的“摹仿性欲望”
08年我第一次读此书,觉得相见恨晚,那时我正迷于拉康,但同时又觉得这书隐隐缺了些什么,当时我说不清。现在重读此书,我终于可以写些东西了。
基拉尔认为欲望常常都不是自发的,他说:“如今,已经没有人相信所谓的自发欲望。”(p285)他说欲望需要一个“介体”, 他反对没有中介的二分法,提倡主体-介体-客体三角关系的三分法,“主观性和客观性,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个人主义与科学主义,唯心主义和实证主义……都掩盖了介体的存在”(p15)
由此引出了基拉尔思想体系的基本假设——“摹仿性欲望”,即认为人永远不是自身欲望的根源,欲望永远源自被摹仿的他者。他认为摹仿性欲望会像传染病一样横扫一切,很像是拉康的“欲望就是他者的欲望”的翻牌。
在主体-介体-客体的三角欲望前提下,他又细分了“内中介” 和“外中介”。 内中介即主体与介体或多或少彼此渗透的“内中介” ,外中介即介体与主体彼此不接触的“外中介” (p9)外中介指介体在人心之外,非内在。
在基拉尔心目中,《堂吉诃德》和《包法利夫人》代表了“外中介”类的小说。相比“外中介”他更推崇“内中介”,“介体和主体间的距离越小,他们的差异就越小;他们的见识愈准确,仇恨就愈强烈。主体在他者身上谴责的欲望,永远正好是主体自己的欲望,但是他对此浑然无知。仇恨是个人主义的,它不由分说地维持自我和他者间虚幻的绝对差异,实际上没有任何东西把二者分开。”(p77-78)他说:“现代性的深刻真实存在于内中介中。”(p97)
我觉得“外中介”是个不必要的假设,因为“外中介”对人来说就是客体。是人没有“中介”。他也说,(在“外中介”下)“追求客体,归根结蒂就是追求介体”(p10)。而且,如果他能把“内中介”再细分为知识与信念,那么理论上将是很有用的。
为了贯彻后现代反对人的自主性的信条,在书中他抨击“浪漫主义”的写作以“人的自主性”掩饰“介体”的作用。这样说的时候他可能心中想得是《浮士德》。就算是“欲望就是他者的欲望”,可是以时间考察的话,十年前埋下的念头现在浮现了,算自己的还是算他人的?所以,他无法说清普鲁斯特的第二时间和第三时间。他说的“双重中介”(也就是相互影响的意思)是对的,可如何分清人我呢。
清算人的自主性终究会走向虚无。所以他说:“形而上”(精神的)欲望的真实乃是死亡(p297),又一个拉康的语言。他反复提到 “羨慕、嫉妒和软弱的仇恨(p14)为什么软弱?因为拒斥真实。
其实,用黑格尔的眼光来看,“内中介”就是反思。“内中介”的普及就是现代公共理性的成长。
基拉尔试图用“摹仿性欲望”来解释政治,在我看来软弱无力。说到贵族问题他也是错的。
《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读后感(三):摹仿理论
十分佩服基拉尔文本细读的功夫。。因为都是欲望理论,所以私下跟拉康做比较。拉康的自我建立在与他者幻想的同一的基础上,而基拉尔的自我建立在他者的对立和竞争上。但我发现拿这两种理论来做对比其实有点不妥,因为拉康面向的是精神分析,基拉尔主要用来分析小说。而且在欲望三角的许多细枝末节上,二者都十分不同。我觉得应该拿这一理论跟基拉尔经常吐槽的浪漫主义比较才比较妥当。基拉尔吐槽新小说我也很赞同,小说本来就不是科学实验,不用细分到最小单位的原子,小说描写的是关系,虽然文字务虚,但虚幻的土壤里就是能结出真果实。给我启发最大的是,基拉尔的欲望理论描写的是现代人,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发展是有一条时间轴的,通过这个我们可以勾勒出人类从传统到现代的精神演变历程,而且基拉尔还细致描写了我不理解的孤独问题。
基拉尔的主论点:自我的欲望就是他人的欲望。事实上也是现代性批判的核心观点之一,也就是,主体是被建构的,不管是被他者,还是被意识形态,还是被权力关系。但基拉尔具体的理论还是与这一主流有所偏离。
首先,就我目前了解到的,现代性的主体理论可以适用于任何时间的任何人,而基拉尔的被建构的自我,就如我上面所说,是有时间性的,在传统社会,人原本是有其本质的,到了现代社会,由于差异的缩小,信仰衰落等问题,人们丧失了自我,变得虚无。
其次,基拉尔由构建自我的欲望更像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点,而像拉康的主体,福柯的驯服的肉体,都是被一个覆盖一切的面所包围,这个面在拉康那里是象征秩序,在福柯那里是权力关系。它们决定了知识的生产以及接纳,其作用更像是意识形态,决定人们如何去思想,如何去行动。而基拉尔的自我还有喘息的余地,因此还“有救”,这条救赎的道路就是克服虚无主义,保持谦卑。虚无主义的一大问题就是自负,他谁都否定,就是不否定他自己,因此只有否定自己,才能获得“真实”,获得重生。这个地方对于我来说很有启发性。
它与其他人的主体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基拉尔认为我身上所包含的他人的欲望,是虚假的,虚无的。但是,据我目前有限的学识水平所了解到的,拉康的“虚拟的现实”中,包含着“现实的虚拟”,也就是说虚中其实带着“真”,福柯的权力关系也认为人的主体性是人们主动构建的,或许与福柯最大的不同在于,在福柯眼中,主体性、人的本质这个概念是步入现代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创造的(步入现代后才有的,以前的人根本不在意人有没有本质,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概念)这是一种新型的权力支配关系,建构这个概念,如何用这个概念来驾驭公民,即使有部分人就获得人的主体性进行反抗,那也是反方向加强了这一观念。这么看来,其实基拉尔的谦卑的和解道路也被解构掉了,因为人本来就没有本质/主体这一说,那么人为什么要与他人和解呢?虽是如此,基拉尔的“死亡与再生”的和解方法还是让我眼前一亮。
受虐癖和施虐癖一章也写得极好,可无限次重读。
这本书还有许许多多让人耳目一新的地方,他对浪漫主义,存在主义的局限也抓得很准。总之,基拉尔的摹仿理论建构得有血有肉,令人信服。
《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读后感(四):生日自度: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
哦。我已经这么老了。我这么老了所以连生日也懒得过了,这么老了还是头一次,独自一人过生日。她在火车上,越走越远。
1、《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是朱文的一个长篇。朱文是当今中国最牛的小说家,之一,但,《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是他最糟的作品。之一。我一向不爱对人对事下判断,但有时候判断自己会蹦出来,既然出来了,我就随它去,不管它断得对不对,因为它也许根本就不是我的本意。
2、很多年前我无意间读了一本法国人勒内•基拉尔写的小说评论《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深受影响,影响之深,我至今没能探底,——或者说是不敢深究。
3、——如果要你独自一人,去一座孤岛,只准带上一本书,你会带上哪一本?
——就是它,《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这本三百页的小书简直要说是浩瀚,每段话都像一个超链接,点开是一片新天地。首先是它的评论对象好:塞万提斯、福楼拜、斯丹达尔、普鲁斯特、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么多看上去互不相干的大部头,基拉尔用奇妙的手法一一串起来了。更重要的是,它非常适合独自一人在岛上看,看它的时间越长,功夫越深,我也许就能彻底看穿自己的一切欲望。
4、基拉尔认为,人永远不是自身欲望的根源,欲望源自被模仿的第三者,我们瞄准他人的欲望目标,亦步亦趋地模仿他人的欲望,因为这些“他人”象征了某种我们竭力追求而不得的完美和充实。
5、我想起来了,我看《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并不是全然无意。在看到它之前,它的名字我就有印象,因为米兰•昆德拉曾经在一个脚注里轻描淡写地说,《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是他所知道的最好的小说评论。还有一个例子也许更能说明问题。胡安•鲁尔福的中篇《佩德罗•巴拉莫》,我几度拿起又几度放下,实在读不出什么好来,直到有一天看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访谈,他说他能把《佩德罗•巴拉莫》倒背如流,说胡安•鲁尔福的全集虽然只有三百页,却“像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一样浩瀚”。我再度捧起胡安•鲁尔福,从此走南闯北贴身携带,跟《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一起。
6、——爱一个人,需要理由么?
——这不是需不需要的问题。牛小说家和牛小说如是说。
7、虚荣。
攀附。
羡慕。
嫉妒。
赶时髦。
充满仇恨的偶像崇拜。
卖弄风情。
冷漠。
8、她说:讨厌。我是人,不是一本书。
9、她说:网上说了,不要招惹浪子,文学青年,中年男子。你倒三样都占全了。
我说:你才文学青年呢。就算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也不是文学青年,我是文学青年的敌人。我打心眼儿里瞧不上文学青年。那时候我学重工业,每次路过宣传栏,看见文学社的活动布告,就觉得他们又在勾引女同学,我替他们感到害臊。那时候我们学校有个文学青年牛皮哄哄的,他叫朱文。
10、我说:我只是一个读书人。
11、上网后,人们的性别、年龄、身份等等差异变得模糊了,世界仿佛一下子平等起来。这种平等扩大了人的欲望,但同时又从各个方面限制着人的力量,使人们感到痛苦和疲惫,于是,我们看到了使劲折腾的人,哗众取宠的人,故作惊世骇俗之举的人,时刻挥舞道德正义大棒的人。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他人的模仿对象,自己却懵然不知,每个人都在模仿他人,同时又极力掩盖掉模仿的痕迹,最糟的是,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模仿的是谁,是否值得我们模仿。欲望在网上涌动,象火炬一样传递,通过连续不断的正反馈,变成汹涌的激情。
12、SNS,尤其是真人实名的SNS会给世界带来一些什么变化呢?如果说现实世界中的欲望俱为虚幻,那么当更为虚幻的网络欲望进入我们的现实生活,我们应该如何去判断,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
《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读后感(五):揭开谎言背后的真相
《浪漫的谎言和小说的真实》是勒内•基拉尔1961年的作品,题目完美地诠释了作品的主题:浪漫主义空洞的谎言与小说对现实世界真实的揭示。该论著与另一本早期著作《地下室批评》共同构成了基拉尔思想体系的重大假设——“摹仿的欲望”,即宣扬人永远不是自身欲望的根源,欲望永远源自被摹仿的第三者,源自一个既是楷模又是对手的介体。我们已经提到,在《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中,基拉尔清晰地分析了几位重要作家:塞万提斯,福楼拜,司汤达,普鲁斯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关于人类行为的重要角度。从塞万提斯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了福楼拜,司汤达,普鲁斯特,这一过程也显示了人类与世界,人与神之间关系的逐渐恶化。基拉尔的这本著作,正是希望通过文学证实自己的这一假设——人的规律将我们引入一个地狱般的三角中,“人只希望他人所希望的东西”。“这种特殊的关系解释了人与人之间持久的竞争,并揭示了人际关系中充满永久的暴力。” 好像文学走到了理论的前面,用小说家的直观发现了这一隐藏的真实:司汤达的虚荣心;普鲁斯特的攀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充满仇恨的向往;塞万提斯的英雄主义。文学中存在许多不同的案例,都能让我们从中看到摹仿的想象,并受其控制。
堂吉诃德作为三角欲望的牺牲品,抛弃了个人的基本特征,对传说中的阿马迪斯的骑士生活进行摹仿。就像福楼拜的主人公,为自己树立一个“模式”, “摹仿他们想变成的那个人,身上所有能够摹仿的地方。” 在司汤达的作品里,我们也同样看到了三角欲望,司汤达作品中的虚荣这个词表示的就是各种“模拟”或“摹仿”行为。虚荣人不向心底找寻欲望,而是向他人借,“介体”就是虚荣人的竞争者。前两者的介体外在于主人公的世界,好像是永远无法追求到的“理想”;司汤达的小说里,介体则内在于主人公的世界。“一旦介体之感知产生影响,现实就失去意义,判断被麻痹。”福楼拜有这样的过程——包法利主义;司汤达——伪善、自负;普鲁斯特——附庸风雅;陀思妥耶夫斯基——隐蔽的人。根据他者的欲望产生了一种三角关系:主体-介体-客体。这个三角的顶端是介体衰退为一个越来越钝的角,从塞万提斯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欲望主体与介体之间的形而上距离变小的过程。由此,基拉尔将小说分为了两个大类——介体与主体彼此不接触的“外中介”,和主体与介体或多或少彼此渗透的“内中介”。这种区分,尤其是“外中介”类的小说,会让我们很容易发现此类小说的雷同,正如《堂吉诃德》和《包法利夫人》的近似广为人知一样。只是在“内中介”那里,主人公因为与介体的靠近而百般遮掩摹仿的欲望,在这种遮掩中,产生了更多的情感,比如仇恨、嫉妒和羡慕。德国哲学家舍勒 认为,羡慕、嫉妒、争强好胜这些词都是仇恨的根源。塞万提斯、福楼拜、司汤达,他们都在伟大的小说中揭示了欲望的真实内容。在此处,基拉尔对小说又做了一种区分:“我们用‘浪漫的’这个词指那些反映了介体存在却没有揭示介体的作品,用‘小说的’这个词形容那些揭示了介体存在的作品。”基拉尔的这个区分呼应了该论著的题目,但对做这一区分的目的,基拉尔好像并没有言明。
基拉尔揭示出欲望的结果成了通过吸收介体的存在而创造我们的他者(形而上学的欲望)。当主人公占有了他所欲望的东西之后,他总是会失望(什么!那个东西不是这样的?)。如果他承认了自己的欲望,他就成为自己的介体-主宰者的奴隶。自虐者(masochist)知道客体一旦被拥有就失去了所有兴趣,便寻求障碍去保证自己失败。我们可以在这几位作家的结论中找到答案——主人公放弃形而上的欲望,用他自己的自上而下的超越取代了介体。在一部作品中,掩饰介体的出现,就是跌入了浪漫的谎言,就是相信他自身欲望的自发性,让人相信其真实性。相反,小说的真实,尤其是伟大小说家,在作品中的所提出的根本问题,是揭示介体的出现,揭穿谎言。这是一种个人与世界,人与神的和解。比如对于普鲁斯特来说,重现时光就是重新寻找真正的在他者的目光中发现真实的印象;也是揭示这种作为陌生信念的他者的信念。重现时光就是收集大部分人将自己的存在流逝的真理,是重新认识我们总是在复制的他者、在他们眼中显现本原,就好像是在我们自己的眼中显现。重现时光就是放弃自己的骄傲。
在完成了对这几部小说的批评研究之后,基拉尔又继续编纂了关于普鲁斯特的批评文集《普鲁斯特批评论文集》 ,同时他还在《从小说的经验到俄狄浦斯神话》(De l’expérience romanesque au mythe oedipien)中探讨了从《让•桑徳伊》开始,普鲁斯特艺术起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