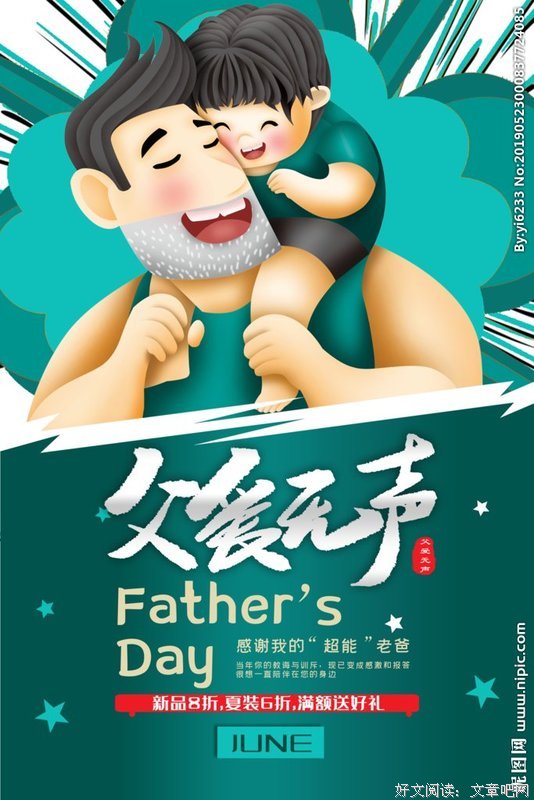
《无声》是一部由柯贞年执导,陳姸霏 / 刘子铨 / 刘冠廷主演的一部剧情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影评,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无声》影评(一):《無聲》短評
4.5/5 好看到頭皮發麻…今年最需要被看到的國片就是這部,格局比《熔爐》小,但是闡述「霸凌」這個主題上也更加生猛有力,影片從旁觀者的視角進入被霸凌者的世界,在從被霸凌者的視角移轉到霸凌者的內心,深入原委細探源頭,學校的檯面下處理、老師的漠視、同學的隱忍,縱容著霸凌的發生,最終成為惡性循環,影片切入角度跟《熔爐》有很大的不同,格局上弱化了社會輿論視角,強化了校園整體本身,但這不代表它的議題被消弱,相反地它帶來的反思,更能從學生的視角被展現出來。 學生選角真是棒透了,每個都好會演,尤其從韓國過來拍片的金玄彬,入圍男配角的確夠格,沒有入圍金馬獎最佳劇情片實在可惜,但柯貞年導演第一部劇情長片就已經展現熟捻的敘事功力,整部片在聲音的設計上也感覺出下了不少功夫,結尾也收的恰如其分,霸凌是再次週而復始,還是就在此終結?沒看過北影版本,但是院線版明顯收的剛剛好,今年第一部想二刷的國片,實在太喜歡了。
《无声》影评(二):2020北影開幕片- 無聲
3.5 我真的超級超級無敵愛柯貞年導演的「天黑請閉眼」,喜歡她對於整體驚悚程度的掌握和對於青少年之間的情誼以及勾心鬥角的描寫,這次拍了「無聲」這部片,取材自真實事件,野心當隨之增大,探討的議題也更顯嚴肅以及社會性,但是,我真的要說,有幸能在台北電影節看世界首映而且親耳聽柯貞年導演講述她自己的作品成果,我真的超級滿足了,當然這次,表現也沒有讓我失望。本身就是一個喜歡看極具社會性批判以及描寫社會那股不管是權力鬥爭以及弱勢群體的心靈痛楚的電影的人,我對這次敢用聾人學校為背景去帶出聾人所處在那無法為自己發聲所遭受的不管是心理上甚至是身理上的壓抑以及對於社會上階級對下階級或是下階級對上階級的勾結以及無奈,感到十分的敬佩以及震撼。雖然在第二幕劇開始落入許多這類型電影常顯示的艱澀生疏感,但是還是一句話,這部電影需要被看到,需要被大眾認真看待,也許這部電影無法真正解決社會上這類型的問題,但是,能再次為弱勢群體或是更明確地說,為真正正在因此等問題所苦的人發聲,可以說是多一次幫別人發聲的機會,多一次能讓多人能夠看見並且正視此等問題的機會,況且,以一部國片來說,這部片可以說是又再跨出了一大步。 當然,請進戲院感受盧律銘配樂造成的音響炸裂,這很重要,所以再講3遍。 請進戲院感受盧律銘配樂造成的音響炸裂。 請進戲院感受盧律銘配樂造成的音響炸裂。 請進戲院感受盧律銘配樂造成的音響炸裂。 還有,請注意聽郭禮杞和李東煥的環境音,真的超級棒。
《无声》影评(三):揭露真相過程是痛苦的,但「不說」更令人絕望
專訪入圍金馬8獎項《無聲》導演 柯貞年
看不到、聽不見、說不出,哪一種最令人膽戰心驚?以聾人世界為題材、金馬獎熱門片《無聲》導演細述自己首部長片,自癒癒人的心路歷程。 與怪物戰鬥的人,應當小心自己不要成為怪物。」這是德國哲學家尼采說過的話。這句話,也是7年級導演柯貞年最新作品所關注的核心。
《無聲》是她首部長片,這部以現實題材、聾人世界所改編的電影,被台北電影節選為開幕片,且一舉入圍今年金馬獎最佳新導演、最佳新演員、最佳原著劇本等8大獎項,備受關注。業界甚至有這樣說法:「去年有《返校》,今年有《無聲》。」顯見其突出。
對柯貞年來說,拍攝此題材,是一段「憤青」過渡到「文青」、自我解鎖的轉變過程。
「雖然談到性侵,且受害者和加害者都是發生在封閉環境(聽覺障礙)中的孩子,但真正想探討的是上下階級、男女⋯⋯不對等權力關係。」柯貞年從成名作、講訴校園霸凌劇集《天黑請閉眼》到噤語或者說不出話的《無聲》,彷彿校園、霸凌等字眼成了這位導演說故事的關鍵詞,但她的企圖是穿越衝突張力的表象,探討背後深層、非僅限於善惡對立二元所講述的複雜關係。
柯貞年從在南部接觸到的2位聾人朋友溯源。一位是從小就在啟聰學校上學,高中畢業就到工廠上班,21歲的他一天工作12小時。他在聽不見的世界裡用文字、手語溝通交流,在同溫層裡溝通沒有障礙,但一進入「一般」世界,溝通會有理解的落差,加上這個孩子個性內向,常吃悶虧,這一切都看在柯貞年眼中。
另一位來自中產階級家庭,父母都是聽人(聽得見的人),3個孩子有聽力障礙,但不妨礙孩子學習,其中一個孩子還是高雄女中的高材生。因為母親從小用口語教他們,一個詞背了2、3百遍,聲音總會刻進骨子裡,所以與一般人溝通即使不透過手語也沒問題。
「我很心疼那位21歲年輕人,如果家境好一點,就有多一點時間練習口語。但轉念一想,我是不是也是站在另一個角度產生這樣的理解?」她從21歲聾人男孩身上學習到的是,儘管在社會價值中歸屬於「弱勢」,但他依然樂天知命,在柯貞年取材拍攝過程中熱心提供許多幫助。男孩是快樂的,不需要他人的同情眼光,但通常一般人會自以為「我是為你好」,而造成不對等的視角。
她說:「(拍攝過程期間是)學習放下自以為是的成見,就算自己認為善意,有時卻是一種傷害。」正如同電影對白中,女主角被欺負後卻對著男主角說:「沒關係,你跟他們一起欺負我就好了。」男主角自以為要保護女主角,成了加害者,然而,卻埋下加害者可能變成受害者的伏筆。惡,不斷循環重演!
「從田野調查到拍片,是段反省與改變的過程,更希望大家用更多同理心去看待這個社會,不是只看見存在的惡,而是惡背後的改變。」取代批判控訴,柯貞年用溫柔、理解觀看世界。
「我內心當然有自己的想法,但電影不一定要有一個批判結論,善惡也並非一定對立,答案要留給觀眾去思考。壞人會有無可奈何的揪心境況,好人也會做出一些錯的事,可能下一刻就成為大家口中的壞人。所以你認為世界上有好壞嗎?世界上究竟什麼是比較好的?」柯貞年反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