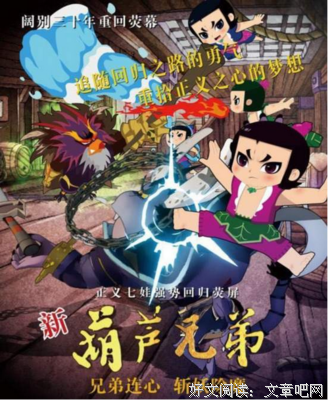《兄弟》是一部由Aslaug Holm执导,纪录片主演的一部挪威类型的电影,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观众的影评,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兄弟》影评(一):挪威兄弟有点烦
如果说照片记录下的是永恒的瞬间,那么影像则是这些瞬间的集合。人的一生,都将经历数不胜数的事件,然而我们终将忘却这其中的全部。可是在某一个时刻,我们不禁会问:哎,我小时候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吗?然后我们又不禁感叹:不太记得了……
纯粹的揣测给不了任何准确的答案,最多让我们在记忆的海洋中抓取一些模糊的片段,就像昨天晚上做的一场梦,细节什么的,全然消逝不见了。
所以,看完这部将近2个小时的影像,我觉得这位母亲的拍摄计划是值得的。从大儿子出生,一直到小儿子也长大,它勾连起了一个家庭的成长史,甚至连祖辈的故事都被纳入。我看到了两兄弟延续了父亲对足球的热爱,也看到了大儿子对独立梦想的追寻,从父亲的羽翼下尝试逃离,却又在父亲回望的目光中颤颤巍巍;我看到了两兄弟之间争吵打闹,也看到他们之间的温情相拥;我更加看到母爱的伟大,她端着一部摄像机,完成了引导儿子解读生命终极并反过来向他们学习的过程。一个梦想有多大?一个想法有多大?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当那些答案出自两个十几岁孩子的口中,我能感受到生命的厚重。不知道他们是应激表达还是向着录音机读完一段已经写好的结论,但这三个问题,我想,两兄弟的母亲自有答案。
我们还记得多少孩童时代的小事?那一年我几岁?为什么会记住这件事?当我们自问,却说不清楚答案。如果我问这两兄弟,你们怎么会想到成为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他们的答案来自哪里?是足球俱乐部、父亲、同窗,还是墙上挂着的那张利物浦全家福?
影像的作用,不仅帮助我们回忆过往,它还有一个极其重要但又容易被忽略的功能,那就是提供拍摄者的视角。两个孩子的母亲,将大自然的声像代入到成长的经历之中,仿佛为一个个事件涂上了情感的色泽。两个儿子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母亲。他们未必读得懂母亲,但他们终将不会忘却,在伴随他们成长的路途中,还有着蓝蓝的天空白白的云、摇曳的稻草悠悠的风。
我们总能读到诸如“壮丽的史诗”这样的论断。可是,为何一定要宏大?为何一定要波澜壮阔?这部影片,平淡得就像流淌过指尖的溪流与两兄弟泛舟的湖面,没有一丝涟漪。但它却给了我一次次的会心微笑与心灵触动。这种感受或许就来自于它的平凡。继《一个人的西藏》之后,我再一次感受到了浓浓的乐感与诗意,那往复闪现的薰衣草群、简陋的白木屋、借风鼓动的床单以及简单的配乐,都是那么简简单单,可是每一个观者的内心到最后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不是吗?
母亲最后说,但我知道,这美好的一切终将过去,一个时代结束了。我想,这又何尝不是生命的意义?放下一段故事、一段过往,才能更好地开启一段更新的故事、更好的人生。
《兄弟》影评(二):看完后自己的一点感悟。
看完后自己的一点感悟。
1.一开始看片的时候觉得这个主意真不错啊,等自己以后有宝宝了也时刻拿摄像机记录他们的日常起居,年复一年,用摄像跟着宝宝一起长大,以后等宝宝长大了一起回放观看一定很有趣。但看到最后又决定还是放弃这种做法吧,一个人每天都会有很多新的记忆也会忘记很多。经过岁月而遗忘的那些事情,虽然可能也非常有意义,但终究有其被遗忘的原因。即使因为摄像被记录下来,回看时候的心境也不会与发生事实的当下相一致。那么多年后的自己看着多年前不记得的那个自己,也像是在看着别人的故事一样,如身世外。
当然那些被遗忘的记忆并非没有任何意义,但它们会以不露声色的方式,360度全方位无死角地影响到个人,就像是每一餐被吃下去的蔬菜、水果、米饭,成为一种养分,使你成长为和别人不同的那个人。
所以最终的最终,一切被记忆住的记忆,才是自然雨刷后需要被沉淀下来的记忆吧,就像是珍珠,玉,奇观景象下的石头。
2.片中一个情节,妈妈过44岁生日,儿子问妈妈你怕吗?妈妈说怕,怕死。非常非常非常感同身受并且28岁的自己跟着一起害怕到了影片结束还没有缓过劲来。
怎么办啊,我也好害怕,即使现在的我只有28岁。好像20年前的我,已经在害怕这件事了。甚至印象深刻某一个大雨夜,还在读小学的我为了“人终有一死”这个无法改变的事实而辗转反侧到失眠。
然而20年过去了,一想到这件事我还是害怕得不得了。怕自己离开让爱的人伤心,也怕爱的人离开,自己欲绝。
这件事真的是我到现在都无法想通的一道难题,也因为害怕从未与人沟通过,好想知道大家都是靠怎样的意志力让自己尽量积极生活起来的,我没法太积极,一直以来也只能够,“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
《兄弟》影评(三):每个人都是一部电影,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拍一部好电影。
每个人都是一部电影,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拍一部好电影。
其实不然,身边的人与物都可以是电影素材,生活就是天然的布景,无需刻意去布置,生活本身已经足够丰满与色彩。
结婚、生子、坚持梦想,不可思议?似乎觉得梦想这神圣不可侵犯的产物怎能在轻浮平俗的油盐米醋日子里产生?然而,油盐米醋正是生活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是生活的根基。
用十年的时间去拍一部100分钟的电影,很难想象背后艰辛。成长与衰老不会停止,坚持随时可能被打击和劝退。重要的是如何突破种种一直走下来,语言不足于表达一切,作品会说话。
卢卡斯说:“我觉得从我出生的时候拍摄就一直存在。”何止十年,或许早在兄弟俩出生之前母亲的梦想已经在孕育。她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小心翼翼、一砖一瓦地筑梦。孩子的出生令她看到梦想的雏形,于是她抓住最美好的时机,通过摄像头与两个儿子交流,有时候孩子们会反抗,于是她学会什么时候放下摄像机。
躺在午后柔软的草地上,或者在静静地海湾划船,有时思考,有时对谈。
结束。另一个开始。
《兄弟》影评(四):专访导演亚丝拉琪·霍尔姆
亚丝拉琪·霍尔姆拍了二十年电影了,成为两个儿子的母亲之后,她意识到这才是真正与生命有关的——她的儿子,他们的生活、成长和烦恼,她问自己,“在生命之初我们是谁,然后我们又成为了谁”——于是就有了《兄弟》这部纪录片。
他们一家四口都来了,先是受邀参加了极地光影电影展,然后去广州的一座老祠堂里面放映他们的片子,最后到深圳与观众见面,结束工作后他们计划去香港的海边度假。
在广州长大后马库斯(哥哥)和卢卡斯(弟弟)兄弟俩变得腼腆多了,尽管早就习惯了妈妈拿摄影机对着他们,记录他们的生活,但在记者的镜头面前,他们还是颇为害羞,不太说话,倒是妈妈和爸爸十分热情,轮流抢麦回答记者的问题。他们一个是导演,一个是制片,都已经在电影行业从事过多年,成立了电影制作公司,主要拍摄纪录片,获得过多次国际电影节的大奖。
霍尔姆一家生活在挪威奥斯陆一座安静的小镇上,已经几乎想不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兄弟俩发现妈妈总是扛着一台摄影机跟在他们周围,拍摄他们起床、上学、踢足球、吵架、玩乐队、旅游…… 问他们关于生命、成长和梦想的问题,卢卡斯抱怨道,“好像从出生开始妈妈就在拍我们了。”
《兄弟》不仅仅是一部家庭录像带式的作品,它更加凝缩,也更有普世性,讲述着这一个家庭,也讲述着无数其他家庭的故事,“我寻找庸常生活中的诗意”,亚丝拉琪说。
“捕捉时间,这样我们才不会忘记”
巴塞电影:最初为什么会想到要拍这部纪录片?
亚丝拉琪(导演/妈妈):在开始拍这个项目之前,我已经从事电影制作很多年了,超过20年。当我成为一个母亲的时候,觉得这很令人激动。因为我意识到,这才真正是与生命有关的。两兄弟都充满了生命力,卢卡斯很富有诗意,他说出口的话常常那么美好;而马库斯则那么勇敢、常常给他的弟弟很多挑战。
于是我就想,如果我拍一部片子来讨论‘在生命之初我们是谁,然后我们又成为了谁’,那会怎么样?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一开始想要拍这部片子的原因。
亚丝拉琪:一开始不会,那时候他们还很小,卢卡斯才5岁,马库斯才8岁。当时我问他们,如果妈妈拍一部以你们为主角的影片,你们会觉得怎么样?马库斯说,哇,那应该会很有趣,不过也会很辛苦吧。他很有智慧,他预见到了接下来会发生的事。
所以一开始大家都很有热情,都对这个项目感到很激动。抗议是后来开始的。
巴塞电影:除了影片中展示的,一共还有多长的素材?
亚丝拉琪:我一共拍了8年,所以自然有很多素材。尽管我没有每天都拍,每天都拍那会让人筋疲力尽的,我大概是拍一周,停两个月,然后再拍一周,所以最后结束拍摄以后,我大概有450个小时的素材。真的很多。
巴塞电影:剪辑花了多长时间?
亚丝拉琪:也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过程,花了将近3年。
巴塞电影:如何在众多素材中进行选择的?
亚丝拉琪:我觉得是挑选那些和我的家庭有关、同时又对人类共通的东西有所讨论的部分。所以每个画面都应该有些更大的东西在里面。有点像透过一个小小的雨滴,来看这个世界。我寻找庸常生活中的诗意,就像雪花落下来的感觉——在你小时候,那是非常美好的一种感觉。我也尝试去捕捉时间,我认为时间是影片中的第三主角——时间在流逝。当我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那艘船在海上驶过的画面代表了我最初的想法。因为我觉得时间流逝得好快,我得捕捉到这些美好的片刻,这样我们才不会忘记。
“在那种情境下我需要尊重他们”
巴塞电影:你在影片中所处的身份非常特殊,创作者和母亲的身份是否存在某些矛盾的地方?
亚丝拉琪:在一开始,我只想像到了那些美好的时刻能够被记录下来。当我开始着手拍摄之后我才发现,要同时当一个母亲和一个导演兼摄影师是非常困难的。但我觉得能够透过一个孩子崭新的眼光来观察这个世界是一个很棒的机会,所以我不想去干涉太多,我只想要捕捉记录下那些情境和瞬间。
但过程中我同时也发现,我是个母亲,我也身处在那个情境中,当事件发生,或有矛盾产生,或者他们跌倒了之类的,我就作为妈妈被拽进了情境里,我就必须要应对这个情境。于是我才明白,我作为镜头背后的那个角色,也应该成为影片的一部分。所以尽管我最初并没有这样计划,但在过程中我意识到,我的声音也是很重要的,因为那是母亲的视角,是我眼中的画面,尽管记录下的是儿子们的生活,但要了解到这是我眼中的他们,我的视角注定是相对主观的。所以即使我一开始的想法是让两兄弟自己讲他们的故事,但后来我认为同时让我的声音也存在,会是更诚实的讲述。
巴塞电影:在兄弟俩看来,这部影片是否展现了真实的自己?
马库斯(哥哥):我个人觉得确实拍出了我们真实的一面。因为我们并没有在表演,这就是纪录片和虚构电影的区别。所以我认为,也许有些片段是经过提炼的,但最终呈现的结果是真实的而不是虚构的。
巴塞电影:爸爸作为制作人,如何看待自己在影片中的身份,对这部影片最初有什么想法?
图勒(制片/爸爸):我最早的期望是能因为这部片子来到中国。(笑)没有,那只是个额外的奖赏。我只是给亚丝拉琪提供制作上的帮助。最初的四年,我都并没有想要成为电影画面中的一部分,我只是想作为制片人参与这电影,当然我是主角们的爸爸。几年以后,他们说服了我,我也出现在影片中会更自然。于是作为他们的足球教练,我同意了参与“出演”。
影片中有一些片段,作为父亲的我并不喜欢,但是作为制片人的我很喜欢。因为它们是展现了矛盾冲突的片段,在电影中你需要冲突,冲突是电影的燃料。
而且我也知道,每一部电影都需要一个坏人。
巴塞电影:拍摄过程中最困难最矛盾的是哪一次?
亚丝拉琪:我一开始拍摄他们与外部世界互动的时候,尤其是在学校,就意识到这会有困难。因为我既是导演又是妈妈。我记得在一开始的时候,有一次我在拍马库斯,他当时有点伤心,站在学校院子里哭泣,我在镜头后面,感到无法继续拍摄,因为太沉重了。我应该回到母亲的身份。所以我放下了摄影机。接着我又问我自己,如果每次这种情况我都要放下摄影机,电影就拍不出来了。所以我必须得把这种两难带进电影里。
因为我的确既是母亲也是电影制作者。我同时也认为,展示这种矛盾会让电影更真实。而且我觉得他们俩在镜头前的那种抗拒表现也是一种成长过程的自然呈现——因为即使我没有拿着摄影机,他们的抗拒也依然会存在。
我感觉他们是非常坚强的两个,如果他们没有这么坚强,我不可能完成这部片子。
图勒:电影中有一些场景呈现了她作为母亲的角色和作为导演的角色之间的冲突。例如卢卡斯在厨房里故意打翻水桶,让水流了一地。因为哥哥不允许他偷拿厨房里的饼干吃,他很生气。(作为妈妈)正常的反应会是放下摄影机,把地上的水抹干。但她没有那么做。因为她当下依然是个导演,她得到了一个电影场景——如果她放下摄影机,就失去这个场景,或者说失去这个场景的后半部分了。于是她继续拍摄,然后事后你再让制片人去确认保险条款。
亚丝拉琪:我必须说,当时卢卡斯不开心地对我说,只要我还在拿摄影机拍着,他就不想跟我说话。我就问他,如果我把摄影机放下呢,他说,可以,那样他就愿意对话。于是我放下了摄影机。
后来我再查看当时拍下的素材,我松了一口气,因为我看到自己确实终止了拍摄。因为我觉得那种情境下我当然需要尊重他们。而且我终于有一个好机会可以告诉他们我为什么要拍这部电影。
过程中有很多挑战,需要去平衡很多东西。但同时也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对生命、对我们是谁,有一些好的表达。
电影里有两三处是男孩们表现出抗拒这部电影的拍摄。一处是厨房的那场戏,还有一处是亚丝拉琪在拍马库斯对着镜子梳头发,他说,把摄影机关了。最后一幕,他对他妈妈说,你必须停止拍摄了,你已经有了足够的素材了。对这部电影而言,让人们看到兄弟俩对持续了多年的拍摄有自然的抗拒,是很重要的。同时,在你小时候,你会拥有自己越来越强烈的想法,自己的立场,以及对你的父母越来越有了抗拒的心态,这也是这部影片一个重要的部分。
“如果片子由兄弟俩来剪辑?”
巴塞电影:拍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但没有保留在最后的成片中的?
图勒:马库斯和他的朋友欧德纳,也就是乐队中的鼓手,他也在电影里, 他们躺在床上有一段大约10分钟的对话,谈论他们长大以后不能吸毒。他们当时大概10岁,对话非常棒,但是太长了,那样会占掉电影太大块的时间。
他们当时在谈论梦想和未来,提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想法。马库斯说,“我永远都不会抽烟的——也许会尝试一点点,就一点点的毒品,但绝对不抽烟”。欧德纳说,“哦不,那毒品也不行,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尝试毒品”。这段对话很有意思,因为他们当时只有10岁,就有这么智慧的想法了。他们对于长大应该怎么做有非常清晰的认知。
我们之前还有一个版本,时长两个半小时,好像是2012年。那是比电影结束拍摄还要早两年半的时候。后来我们把电影剪短了40分钟。我们拍了更长,电影却剪得更短、也更好了。所以剪辑的时机,是做一部好电影的关键。
巴塞电影:如果由兄弟俩来剪辑,电影会否很不同?
卢卡斯(弟弟): 我想如果是我们来剪的话,电影一定没有现在这么好,但确实会很不同。可能会有更多的动作、和冲突,少一些这种安静的、平和的画面。
图勒: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扔球的画面?
卢卡斯:对,我想不会(笑)。
马库斯:我同意卢卡斯说的。因为我妈妈用了一些特效来展现时间的流逝, 我一开始没有理解为什么她要重复呈现划船的画面那么多次,但我对跳水的那场戏有共鸣,如果是我来剪辑的话,应该会把跳水的戏放在前面,也许不是最开头,但会放一部分在开头,然后一部分在中段。而划船的场景,我一开始没有理解,后来看过电影几遍之后才明白,它是用来代表时间的场景,所以它才在电影中出现了一遍又一遍。 每到夏天我们都会重复这个场景,她挑选出来表现了我们的成长。你可以很清楚看出每次换一艘新船,我们都长大了一点点。然后你看到故事随之发展。总而言之如果我来剪辑,会剪进更多冲突性强的画面,但电影不是仅仅建立在冲突上的。
图勒:但你并没有看过剩下的素材,那些原始素材。
马库斯:对。
巴塞电影:为什么兄弟俩不想看看剩下的素材呢?
亚丝拉琪:我早早就做了这个决定。因为我直觉认为,在拍摄过程中不应该给他们看这些原始素材。因为我如果给他们看了,他们也许就会开始评估自己在画面中的表现,也许他们会想,我这样看起来不太好,下次我应该表现更好,然后也许就开始摆拍和表演了。那样会伤害这部电影。同时我也觉得,制作这部电影是我的责任,如果他们介入其中,就会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他们会时时想着这部电影,那样我就破坏了他们生活的日常性。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好决定——他们可以结束了两个小时的拍摄就出去玩,完全不需要再记挂电影的事。
我还听说《少年时代》的导演理查德·林克莱特,也是这么做的。当然,那是一部虚构电影,他也不让他的演员们看任何一点拍摄素材,在拍摄的12年间——也许是出于相同的理由吧。
巴塞电影:人们会经常拿《少年时代》同你们的电影相比较吗?
亚丝拉琪:会。我也理解为什么。其实我觉得挺有趣的。在我一开始拍摄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少年时代》这片子。直到导演林克莱特结束了拍摄,也就是知道2014年8月份 的时候,我才听说这部片,原来几乎是同一个时期,在德州有个导演,跟我在挪威拍的片子是同一个主题:时间流逝,孩子成长。所以我告诉图勒,我们应该看看那部片子。于是我们就去看了,当时是我进入剪辑的最后阶段,当我看到那部片子的时候,我觉得它棒极了,我很爱这个电影,也感受到与导演林克莱特之间的一种联系——他尝试着去捕捉当下,同时也想保留下我们生命中一个更长的时间线——也许是因为我们在现代生活中缺失了这个,它是某种想要弄清楚对我们是谁,我们从谁哪里来,以及我们将会成为谁的渴望;我也感觉到,他的电影在围绕着他的团队打转。
巴塞电影:划船的场景是否承载了一些导演特别的想要表达的东西?
亚丝拉琪:我是受到了安德烈·塔可夫斯基,那位俄罗斯导演的影响。他拍了《镜子》。他谈到过作为一位艺术家,你就像一个摆渡人,连结过去和未来。这让我觉得很受启发,在这部电影里我就感觉到自己像一个摆渡人,因为我就在船的中间,试图连结起过去——也就是我的家族故事,和未来——也就是两个小男孩。
这给了我一个进入故事的视角,因此划船场景部分对这电影而言很重要,对我也是。我觉得这部电影有很多个层次,一方面这个故事很容易跟随,但同时如果你多看几遍,又可以发现一些新的东西。我在故事底下还是有一些想法希望去表达的。有趣的是,我跟人们聊天的时候,他们会问我问题,其中很多是关于电影中不太明显的部分,但是他们抓住了。所以我觉得很有趣,人们能够领会你藏在电影里的东西。
巴塞电影:(问俩兄弟)看过电影之后有没有更新了对自己的认识?
卢卡斯:可能就是发现我小时候很无赖吧。
巴塞电影:马库斯最喜欢的足球俱乐部依然是利物浦吗?
马库斯:依然是利物浦。
巴塞电影:光是看着两兄弟小时候的样子,觉得可以预测他们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吗?
亚丝拉琪: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我通过成为母亲,学到了很多。在此之前,我总觉得我可以把他们培养成“好人”,我以为父母的影响在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当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但在我成为母亲后,我发现在我介入之前,他们就已经完整了。他们很坚强,也有他们自己的个性等等。所以我理解到,不论是马库斯还是卢卡斯,他们都是他们自己,都是不同的。
所以我觉得是可能的,从一开始就看清一个人究竟是谁。所以也许关键是在于后来他们如何在世界上展开自己的旅程——也许这才是我们作为父母可以帮助他们的:去发现他们是谁,去成为他们最好的自己。那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很多的挑战,和很多情况要去应对。我很仰慕我们天生的这些伟大的禀赋,就像我在马库斯、卢卡斯身上看到的那样,我现在看到的他们还是和当年相同的两个人,这很有趣。
——————————————————
本文首发巴塞电影APP,拒绝任何形式转载、引用、洗稿
合作、约稿、勾搭请私信~~
《兄弟》影评(五):剪辑成长
8.0分。
以潜水开始,又以潜水结束,形成一个闭环,一段解锁成长的历程,寓意着由害怕转向勇敢,寓意着向前与抉择,虽然这个起点与终点与终点在时间上重合,却展示出两种不同的人生可能,也只有介入了他们的成长才能更深刻体悟时间以及选择的美妙,或者可以说这是电影语言(剪辑)的美妙。
他们的成长令我最感兴趣的还是童年生活中参杂的哲学话题,这对于我来说是多么不可思议,跟孩子谈死亡、谈存在主义。蛮向往生活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
除了家庭记录影像本身存在的意义之外,影片构图确实不错,尤其是在岛上。与我的观影预期契合,也正好与我买相机的初衷契合。
《兄弟》影评(六):因为真实所以可爱
参加了挪威领事馆举办的活动,见到了电影里的两个少年、导演(妈妈)、制片人(爸爸)。
片子可以很长也可以很短的题材,要抓住主线不是容易的事,抓住主线的同时还要引起共鸣则更难。导演说因为5岁的卢卡斯开始问一些哲学问题才开始的拍摄想法,而这些哲学问题(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就是贯穿全片的主线。
在电影开始的时候我是不抱期待的,结果影片里那些细节带来的笑点,那些穿插的上几代人的影像,使得整个电影呈现得很丰富。关于勇敢、关于梦想、关于传承...每一点电影都只是呈现而不给你答案。这些本就是没有答案的话题,能带来一些思考就已经足够。
画面很美,因为真实所以可爱。
《兄弟》影评(七):时间的女儿
近期看过最满意的电影。一直觉得每个人的人生经历就是是最好的电影剧本。也曾想过会一直有一台摄影机,记录着你的一切。中间有一段美好的让我掉下了眼泪。很久没有看过这种直击心灵的电影了。你有太多东西思考的时候,记忆就会趁你不注意溜走。这些影像或许会让你想起那些瞬间。从蛛丝马迹中知晓如何成长为如今的模样。
《兄弟》影评(八):我的妈妈是一台摄影机,这很棒
很少能看到像《兄弟》这样干净又迷人的纪录片。
挪威女导演亚丝拉琪·霍尔姆(Aslaug Holm)在自己的小儿子卢卡斯5岁那年,拿起了摄影机,开始拍摄这部关于她两个孩子马库斯和卢卡斯的家庭纪录片。“很庞大的工程啊,差不多十年后等到电影完工了,再看自己小时候一定很有趣”8岁大的马库斯语重心长地说,的确如此,她一拍就是十年,因此被人称作是纪录片版的《少年时代》。
画面很美,没能在大屏幕上观看这部片子,遗憾得想哭。主要的取景地有两处,一个就是导演和儿子居住的城镇,另一处则是风景宜人的挪威郊外,他们一家在那里的海边有一座红色的小木屋。影片一开始,就是两个小正太光着膀子在木屋的门口准备比赛跳水,海面被风吹过,起了一片深蓝色的涟漪。
“跳啊,卢卡斯。”哥哥率先跳进海里,在水中喊道。
卢卡斯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穿上衣服,跑回家去了。
“你真是个懦夫。”哥哥说。
他们所在的地方,是一个长满了狗尾巴草的海滨半岛,开着大片大片紫色的花,天气好的时候,兄弟俩会划着一艘小木船出海,母亲就在另一艘船上远远地拍他们。
霍尔姆有一次问儿子,“你知道为什么妈妈一直在拍摄吗?”
儿子回答说:“因为,你想让我记住你,在你死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纪录片里每个人说的话,都像是诗一样,也许只是单纯琐碎的日常对话,但在镜头的缓慢变换和音乐的配合下,孩子们那些突如其来的话语显得充满诗意——充满了一个母亲爱的诗意。
妈妈拍摄自己的孩子,已经可以想象这部纪录片拍摄过程的与众不同之处。苏珊·桑塔格在《关于他人的苦难》一书中已经指出影像工作者的矛盾之处,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1993年自由记者凯文·卡特在大闹饥荒的苏丹拍下了一个即将饿死的小女孩和在她身后虎视眈眈的兀鹰的照片——一方面是作为摄影师的专业素养让凯文·卡特守在原地,试图拍出最震撼的画面;另一方面则是作为一个人的凯文·卡特,应不应该放下相机去救助那个将死的女孩。
假设凯文·卡特正是他照片中女孩的妈妈,那么这个问题便不成问题了,在《兄弟》一片中也正是如此,虽然大多数时候,霍尔姆都是采用旁观、不干预的态度,对两个儿子的小打小闹保持客观包容,但在某些关键时刻,她不可能不挺身而出。
小儿子卢卡斯在小学课堂上被老师骂了,“我要回家”,他说着推门跑出了教室。
“你不能这样做,卢卡斯,那样的话我们就得去见校长了”妈妈说。
“我厌倦了在这儿带着,我很烦了!臭不要脸的老师!不要脸,不要脸!”
摄影机没关,但也没对准人物,非常晃,我们看到的是学校走廊的墙壁和地板,然后听到妈妈在镜头背后叹了一口气:“你不能在每次事情变得有些困难了就逃跑。”
“我当然可以,我可以!我可以直接退学!”卢卡斯说着,镜头更晃了一点…… 观看这样的片段让人感到非常亲切,妈妈手中的摄影机并不是冰冷的,那个装着胶片的镜头就是妈妈的眼睛,有时它会陷入焦虑,一下子变得不知道该拍什么好了;有时为了去帮助受伤的儿子,霍尔姆会曳着摄影机飞快地冲上前去;有时,自然地,她会把一切都拍得很美,再配上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悠扬音乐,美到不真实了,但那种“不真实”,何尝不是一个母亲眼里的真实呢?
吉田喜重曾说小津安二郎镜头下的景象是一种“无记名的、暧昧的景象”,因为我们无法判断观看者究竟是谁。与之相反,《兄弟》中的观看者很难不被察觉,甚至,霍尔姆还时不时让自己本人也出现在屏幕中,显得比瓦尔达出现在《阿涅斯的海滩》中还要理所应当。(瓦尔达是法国新浪潮电影的教母,《阿涅斯的海滩》是她于2008年拍摄的一部自传体纪录片)
另一个让人惊讶的时刻,发生在大儿子马库斯的青春期阶段,他开始玩乐队了,喜欢Green Day,也似乎开始接触到女孩子的问题了。有一天,他突然说他想把头发染成黑色,虽然爸爸十分不赞同,但霍尔姆还是陪着儿子去了理发店,马库斯不仅染了头,还在耳朵上打了个耳洞。镜头里的马库斯坐在理发店的椅子上,强装镇定,等到耳洞打好之后,他朝镜子看了看,害羞又兴奋地傻笑,以及回家路上遇到爸爸的那一刻的不知所措。
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几乎忘记了镜头和镜头后面的妈妈的在场,然而仔细一想,几乎可以无比真实地感受到妈妈在儿子人生中这一次小小的“长大”的瞬间,作为一个观察者,在镜头后面露出的有点无奈的笑容。
其实他们都过着极为平凡的生活,哥哥马库斯从小喜欢踢球,他梦想着进入利物浦球队,长大一些后又爱上了音乐;弟弟卢卡斯非常害羞,身体没有哥哥强壮,踢球也不如哥哥,常常闹脾气,经常让妈妈头疼。
更多时候,他们只是在做着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在妈妈的镜头下,寒暑交替,景色变换,时间慢慢流逝,空气中的灰尘都像有了生命。
她拍了十年,有时候孩子会对母亲发飙,“我讨厌你一直拍摄,你都拍了十年了,还是完不成它。”
时间是影片的一个重要的主题,“时间永不终止,它一直走啊走啊,即使其他一切都终止了,时间还会走,时间只是不停地走啊走啊,我们都不知道最后的最后会发生什么。”小儿子卢卡斯说。
“每一年都像是一阵风,吹拂而过,38,39,40,41,42,43,44,妈妈四十四岁了”大儿子马库斯在日记里写道。
“我记录下我们的时光,可它依旧很快溜走”霍尔姆说,影片中有许多叶子从树上掉落的画面,让我想起了好莱坞之父D·W·格里菲斯曾说过的一句话,他说:“电影就是一片树叶被风吹下来。” 电影对于时间的流逝有一种细腻的感知,一次镜头运动,一次剪辑,也许就是一个月、一年甚至十年过去了。在这之中,也许有某种残酷的东西存在着。
对于一个母亲来说。
《兄弟》影评(九):看完这部片,我太嫉妒他们的生活了
在遥远的挪威,有一位母亲。
花了整整十年拍摄两个儿子的纪录片。
由于文化和教育观念差异,两兄弟和我们的成长路径大不相同。
但他们,看起来更快乐。
看完派爷忍不住在想。
我们长这么大的过程中,是不是有哪一块出了毛病?
《奥斯陆少年有点烦》
《兄弟》影评(十):我的妈妈是一台摄影机,那很棒
很少能看到像《兄弟Brødre》这样干净又迷人的纪录片。
挪威女导演亚丝拉琪·霍尔姆(Aslaug Holm)在自己的小儿子卢卡斯5岁那年,拿起了摄影机,开始拍摄这部关于她两个孩子马库斯和卢卡斯的家庭纪录片。
“很庞大的工程啊,差不多十年后等到电影完工了,再看自己小时候一定很有趣”8岁大的马库斯语重心长地说,的确如此,她一拍就是十年,因此被人称作是纪录片版的《少年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