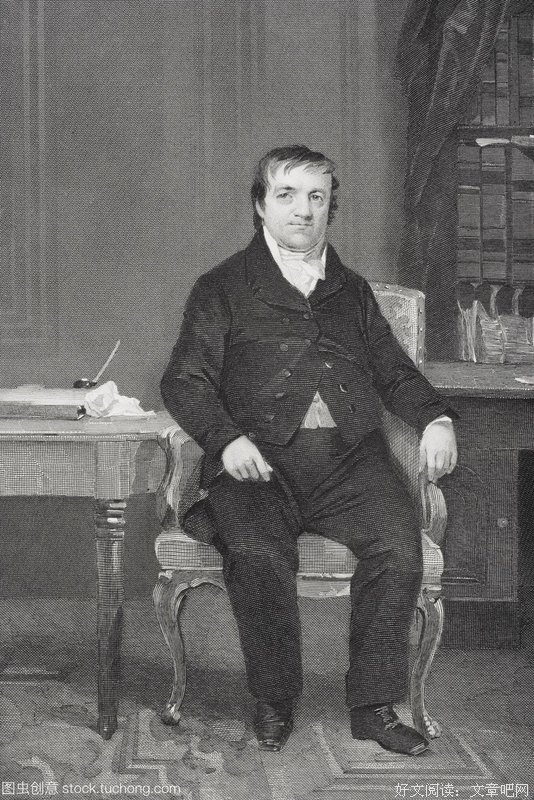《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是一本由[英]大卫·米切尔著作,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48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读后感(一):还行
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
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
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
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eeeeeeeeeeeeeeeeee
《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读后感(二):渐入佳境之作
在我最初看德佐特的千秋时,我认为这部作品在构思和气势上都远远不如幽灵代笔和云图,少了很多小创意,加之又是一部历史小说,还是我不太熟悉的十九世纪前夜的日本,开始的情节进展不紧不慢,大量的描写冲淡了情节,几乎没有悬念可言。
但看到第二部的时候发现此书就像书中写下围棋一样,在慢慢布局,而且开始有意思起来,人物的形象在选择中丰满。无论是德佐特、蓝场川织斗、绪川左宇卫门还是榎本都开始在行动中展现了各自的特性。
第三部开始,织斗被隐藏,德佐特和城山在邪恶面前展示了无畏和牺牲精神,最终榎本被杀,这让我想到了这部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村上春树《1Q84》的仿作,但仿写的如此成功,可敬可叹!
很多画面,放下此书后还栩栩如生的印在我的脑海中。译作非常成功!敬佩之至!
幽灵代笔是时空延续的变化,云图是生命在轮回中的变化,德佐特的千秋则是在一个历史点上诸多人性的展现,善与恶、世俗和宗教、东方和西方、爱情和错失,等等。
爱情无法改变命运,但知识也许可以。蓝场川小姐用从荷兰人那里传来的助产知识,挽救了城山奉行大人小妾和孩子的生命,也因此挽救了自己日趋悲惨的运命。
邪恶的大反派榎本,用当时日本人前所未见的先进手持火器,抵住绪川宇左卫门的心窝,如同所有的反派话唠大BOSS,喋喋不休,享受着猎物的恐惧,直至枪口瞄准宇左卫门的额头。
奇迹不会为男配角出现。大BOSS的演讲欲,要在最终的决战中才会让正义联盟觅到胜机。
绪川桑为了营救他深爱的蓝场川小姐,被峡河藩大名、不知火山神社最高住持榎本用前膛装弹击锤手枪发射的弹丸击杀。
绪川最后的念头是“为我报仇”。报仇的希望,寄托在他的情敌、不远万里来日本做生意的离岛荷兰特区书记官、红发德佐特身上。
城山奉行大人收到德佐特保存的致命卷轴,为了正义和公理,邀请榎本大人手谈并在茶中下毒。这是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城山大人甘愿和榎本大人同归于尽,榎本大人的残念,则在于整个日本,无人能理解他在下一盘更大的棋……
大卫 米切尔在本书中抛弃了初级工程文学概念,采取了传统的顺序时间轴描写手法,这一转变,在《绿野黑天鹅》中已有表征。故事内涵的丰富性,让《雅各布 德佐特的千秋》并不需要如同《云图》那样炫技般繁复的架构,内在的情节张力更为深邃含蓄。
这也许是更高层次的工程文学。把西方和东方在全球化殖民进程中的文化侵蚀和交融刻画的丝丝入扣,而无论西方和东方,人性的复杂性也许并无不同。
然而,无可言说却一生萦绕于怀的,依然是那场在险恶异国咫尺天涯的爱情。当德佐特回到荷兰,弥留之际,他依稀看到,相距万里如隔千秋蓝场川小姐的身影……
《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读后感(四):大卫·米切尔的万变与不变
在这个影像化的时代,当《黑客帝国》的导演把某部小说以大手笔铺陈在银幕上,被改编成电影的原作自然红得发紫。大卫·米切尔的《云图》就是这部传说之作,六分钟长的预告片通过网络被不断复制,不管有没有看过书,人人都睁大了眼。
我早就是米切尔的拥趸,从《幽灵代笔》到《云图》,他的故事一向有挑战极限的姿态,背景一变再变,一部小说里塞着迥异的时代、国家和种族,层叠如俄罗斯套盒。不免对他的新书怀了期待,《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仅看书名,莫非是时光在千年尺度流转的又一则传奇?
这一次米切尔没有炫技,他用了极其传统的手法,巨细无遗地勾勒主人公及其环境:德佐特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办事员,随船来到长崎的出岛,闭关锁国的日本惟一一处允许外国人停留通商的人造岛屿。题名的“千秋”指的便是日本。出岛是投机者的天堂,德佐特生性耿直,试图厘清公司内部的种种舞弊行为,树敌颇多。能算得上朋友的只有长驻当地的医生马里纳斯,以及日本政府的年轻翻译绪川。一七九九年的日本正处于严惩基督教的封闭状态,德佐特在这片行动不自由的陌生土地上,外有职场倾轧,内在则是年轻的煎熬。他思念未婚妻,却又不由自主地爱上一个不可能的对象,织斗是日本医生的女儿,卓绝的助产士,脸有烫伤,兰心惠质。
如果就这么絮絮叨叨地描写一场两百年前的跨文化恋情,实在无趣。好在剧情从第二部开始转折。织斗在父亲亡故后被送入隐僻的寺庙,等着她的是不为人知的邪恶寺规。享有大名身份的住持在出岛享有显赫地位,据说还能伸手取走蝴蝶的灵气。织斗试图逃跑,曾与她有过未遂婚约的绪川也从别的渠道获知寺内的秘密,决定抛下现有的身份地位,前去营救。临行前,绪川把秘密交托给德佐特。既是情敌又是朋友的两个男人,抛开他们的国籍、身份和思维模式,内里很有几分相像。米切尔似乎在曲折地传递一种可能:那些懂得爱的人,正直的人,为他人不惜牺牲自己的人,本质是同一的。
只要熬过前半部太过细节的描写,你很难不被三个年轻人的命运所牵引。织斗枉有技能和知识,被母亲卖给寺院;绪川作为养子,按养父母的意愿过了几十年缺乏自由的生活,因无法坐视织斗身陷囹圄,甘愿以身犯险;德佐特花了两百个夜晚研习日语,读懂了绪川留下的卷轴,但作为外国人,他的话无法传到当权者的耳中。抉择和困局之间,一艘突然出现的英国船用炮弹击碎了出岛的宁静,德佐特在荷兰公司名存实亡的时刻站了出来,自嘲地以“出岛总统”之名捍卫心中的信条……
德佐特站在瞭望塔上面对炮火的场景是如此熟稔,并不是哪本书里有同样的设定。在这一刻,《千秋》历史小说的外壳簌簌掉落,露出米切尔式的炙热内核。正如《幽灵代笔》或《云图》,他的故事关注的总是那些“以卵击石”的人。他们没有权势和力量,有时甚至没有姓名,惟有抉择的时刻彰显他们带着脆弱的明净。“人的心灵也有它自己的心灵……心灵的心灵也会发挥它自己的意志,也会用它自己的声音说话。”无论是跳跃纵横的科幻连环作,还是工笔长卷式的《千秋》,心灵的声音从文字构筑的世界漏出来,直抵读者的耳际。米切尔的魅力在于此,炫技式的写法不过是心灵之声的通道。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位最传统的作家,惩恶扬善式的,只是不那么说教。
《千秋》起源于米切尔在日本教书期间的一次旅行,出岛博物馆给了他灵感,当时写下的笔记一放就是十年。真正重要的题材,作家会留到成熟之后再写。米切尔选择重拾旧梦,用了四年时间写出他的第五本书,有理由相信,其中蕴含了太多沉淀,所以前半部才充溢着过长过久的铺垫,而后半部的痛快和怅然,果然是熟透的故事如好酒,余味悠长。掩卷之后不免担心,作家用前影视时代的节奏推进的浩大叙事,究竟有几个读者能耐心追随呢?
《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读后感(五):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
为唯一与外界通商的口岸,并且只与荷兰通商。荷兰在出岛设
而被囚禁。现任馆长福斯滕博斯奉命彻查与前任馆长相关的渎
职行为,具体交由办事员雅各布.德佐特办理。雅各布因此而
了馆长。前任副馆长范克利夫因擅于随风转舵,而继续被任命
为副馆长。
篇集属违禁品。但出岛三级翻译绪川宇左卫门在例行检查中替
兰的未婚妻,但他对出岛医生马里纳斯的学生--助产士蓝场川
馆长福斯滕博斯收集完同僚的罪证后,在返回向总督复命前,
要求雅各布和副馆长范克利夫在他本人做假账的帐表上签字,
损公肥私。被任命为馆长的范克利夫痛快的签了字,但被任命
。取而代之的是副馆长费歇尔。
。织斗曾逃出过不知火神社,但又被抓回。这个神社以一种半
炼。由神社逃出的一个名叫而立的僧侣,带出了写有神社信条
的卷轴。在山上的老药草师家避难,并诉说一切,于当夜死掉
。老药草师因与织斗有几面交情,将卷轴交予绪川,希望他能
帮助织斗逃离苦海。深爱织斗的绪川,密谋营救她。行动前,
被榎本杀害。
1800年10月,一艘英国护卫舰由前任馆长斯尼特克带领来到出
岛,想强取铜或其他货物,并绑架了范克利夫馆长和费歇尔副
舰因此炮轰出岛,给予震慑,但雅各布和马里纳斯医生坚守瞭
望塔,没有丝毫畏惧。在即将对瞭望塔进行致命打击的最后一
刻,英国护卫舰船长看到了雅各布的一头红发,想起了自己死
希望能将罪首榎本绳之以法。奉行大人因防卫失策,被下令自
裁。他邀请了榎本当他的介错人。奉行在自裁前的酒里下了毒
。
1811年,医生马里纳斯的葬礼上,雅各布重遇织斗。此时,雅
各布已有了一个十岁的儿子,妻子病逝。织斗在京都重新做起
却了一桩心愿。
,他的儿子只能留在日本。回国后,雅各布再婚并有了孩子。
在他临终前,他似乎看到织斗来到他的床榻前,并在他的额头
上印下一吻,正像他多年前想对她做的那样。
以上是内容概要。米切尔的这本书精彩在后面,前面很多无谓的啰嗦,但总体感觉还是不错的。
《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读后感(六):一眼有多久
阅读需要契机。你会看哪些作家的哪些作品,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范围。如今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何中学时代会看诸如《青年近卫军》之类的前苏联小说,看过主人公的名字全都记不全,只知道看到一长串名字是甲,那一串名字是乙,如是。看过的不一定喜欢,喜欢的也许在未来,阅读内容和所获感知如同人与人直接的缘分,总归是在认识的人中寻找气场相合、俩俩相吸的对象。
读《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是借了电影《云图》上映的契机。这部电影原著改编的小说很得体地把不易表达的部分略去,加入了补充情节,令阅读原著的艰涩感消减,理解更加清晰。即使知道结局会失败依然做出努力,并坚信此刻的努力会在后世发挥影响——这种信念不仅撑起“云图六重奏”的宏大历史建构,而且在大卫•米切尔的其他作品中也有此隐喻。看过电影后,我买来《云图》和《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一般刚看完电影会先看同名书籍,但我却被后者的名字所吸引。
初看便觉是场繁复的思索之旅。首先,故事在一个并不熟悉的历史背景下发生,十九世纪前夜、1799年的日本长崎湾出岛,日本锁国时期唯一的贸易港口,封闭的天花板被历史进步的洪流钻开一个小孔,荷兰东印度公司借通商之机投下科技与文明的阳光;其次,有令人想拨开迷雾一探究竟的设定,峡河藩主榎本用庵堂作掩饰,利用封闭社会对日本女性的禁锢,骗取她们的信任,让她们生育婴孩,再以此当作自己的“收成”;最令人沉醉的,是雅各布对助产士蓝场川织斗的爱意,他们接触不多,也在传统和新知的碰撞下受到压抑,却令雅各布到老年弥留之际,还将角落的灯影凝结成她的身姿。
大卫•米切尔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道,这是一本历史小说,与之前的“炫技”小说不同,是自己的作品里他目前最喜欢的。我对宏大叙事下的人物命运向来没有抵抗力,再加上一眼即获得的爱情,穿越千秋也不会褪色的力量,使我对此书非常喜欢。
书的开篇一章进展缓慢,以真实历史为基础,但跳出来在描绘那个时代的特殊景象,西方贸易扩张下的腐败和无序,东方文化的保守和抗拒,二者不可避免的冲突和阵痛表现得淋漓尽致。譬如对于蓝场川织斗的人物设定——一个日本女人学习西方医学并做得非常出色,本国人对她的所作所为指指点点,荷兰商人们也忽略她的能力,只知嘲笑她烫伤的脸。这正印证了黎明前的最黑暗阶段,任何新鲜的事物,都要在恐惧中不断接受,在讥讽中坚持到底。
对于时代的描绘也不是单纯叙述,那只是背景,是在为一份正直、一份斗志和一份爱意的呼之欲出垫好温床。以结构出新的米切尔说他想远离框架的复杂,回归于人,展现“人生的混沌”,但始终做不到。因为“最好的小说让你关心一个人,你担心在他们身上会发生坏的事情,然后你不断地读下去,希望这些坏事情不会发生。有时候一本书变得很复杂是因为我希望把太多的东西放进去,它们必须要有一个复杂的结构,才不会变得无聊。”但他也直言,“小说的骨架里面,仍然是跳动着的人的心灵”,这与作品的结构是否复杂并没有直接关系,什么都不妨碍人物、人性与人生的刻画,只要饱含情感来讲述。
这片千秋在当事人的内心和历史的星河里都留下了不会磨灭的痕迹,特别是雅各布遇上蓝场川小姐后的情绪和念想,充满了神迹,语言半知半解下的初次见面,一眼仿佛能够万年。此后,他们在共同的朋友马里纳斯医生处有过几次碰面,但单独交流甚少。蓝场川被榎本抓去幽禁,被解救后他们再次见面,雅各布也没有直抒其意。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医生的葬礼上,聊天内容透露出他们对于彼此的交集记忆深刻,却没有涉及到爱情。直到蓝场川用荷兰语说“长阶已尽,我们就此分别吧”,美好又遗憾的氛围达到最浓。爱的一眼有多久?纠缠一生从未终结。科技与文明开启了一个国家的新气象,出乎意料的异国经历改变了人的命运,持续久远的爱虽藏在心的角落,但不用晒出就有声声回响。
《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读后感(七):转帖:新京报近日对大卫米切尔的访谈
大卫·米切尔 幸运的是保持“杂食性”思考
2012年08月18日 星期六 新京报分享:
去年年底,《书评周刊》邀请100位名家为读者推荐新年好书,《寻路中国》的作者彼得·海斯勒推荐了一本《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那时候,几乎没有中国读者知道这本书。而半年之后,不但这本书有了中译本,因为《云图》即将拍成电影,作者大卫·米切尔也成了一时的红人。从北京到上海,大卫·米切尔先后与徐则臣、李洱、苏童等中国作家对谈,媒体约访不断,简直有了一点明星的感觉,回想两年前《云图》刚刚推出中文版时的冷清,让人不得不感慨文学在娱乐时代的命运。关于这一点,大卫·米切尔本人也给出了一个事例,电影《云图》的片花两周前出来,在这之前,这本书在美国亚马逊网站上大概排在2400名左右的,片花一出来,就在当天晚上,它一下子就跳到了第六名——无论如何,对作家来说这当然都是一件好事。但相比于人们的热烈讨论,文学本身永远是更重要的,我们在两年前已经谈论过大卫·米切尔的作品了,所以这一次,我们不说八卦,只讨论文学本身。
大卫·米切尔 英国作家,欧美文学界公认的新一代小说大师。1969年生于英格兰伍斯特郡,作品博采村上春树、奥斯特、卡尔维诺、博尔赫斯诸大师作品之所长,自成一派。代表作《云图》(2004)获英国国家图书奖最佳小说奖,同时入围布克奖、星云奖、克拉克奖决选;新作《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2010)获得英联邦作家奖。2007年,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世界10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摄影/新京报记者 孙纯霞
【如果我想的话,我可以成为“新颖”先生,或者“创新”先生,或者“后现代”先生】
大卫·米切尔常常被归类为“后现代作家”,他小说中的结构游戏有时候会让人望而却步。不过他最喜爱的新著《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是一部历史小说,而之前那本《绿野黑天鹅》则是传统的半自传体。看上去,玩儿过结构游戏之后,他“回归了”。
新京报:在与中国作家徐则臣的对谈中,你说过,小说有五元素:情节、人物、主题、形式和结构。你说到,前四种已经很难有创新,而结构则仍有不少创新的空间。这是你喜欢在小说设置复杂结构的原因吗?
米切尔:嗯,对于情节和人物来说,好像是这样,又好像不是。你很难做很戏剧化的、很激进的创新,或者说作家很难去“创造”些什么。我想我的意思是,你很难去创造什么。当然,世界在改变,作家要对这些改变做出反应,你还可以找到创新点。二十年前,互联网并不存在,你不能去写一本关于互联网的小说。现在,互联网存在了,你当然可以写一本关于此的小说。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创新,而不是创造,它是对变化的一种反应。而对于结构来说,还是有“创造”的空间。
新京报:似乎对于一个新作者来说,当你开始写小说的时候,你总会有一种冲动要去“创造”些什么,去写别人没写过的那种小说,好像你的第一本小说也是这样。但你的第四本小说《绿野黑天鹅》就比较传统了,它是一个半自传体的故事,读起来倒像是别人的第一本小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写作轨迹?
米切尔:对我来说这好像是一种很有逻辑的发展。我的前三本书——其中第二本还没有被翻译成中文——都是很新颖、很“炫”的,也许很“创新”。我觉得我已经向我自己证明了,如果我想的话,我可以成为“新颖”先生,或者“创新”先生,或者“后现代”先生,我可以成为这样的小说家。尤其是通过《云图》,我证明了这一点,或者向我自己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这个我做过了,下一步是什么?我不想重复我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写同样的小说。
我的《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是一本历史小说,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新的领域。因为我一开始就是写那种新颖的、奇怪的小说,一旦我写过了这样的小说,对我来说新颖的、奇怪的反倒是像《绿野黑天鹅》这样比较传统的小说。所以,它成了我的新前沿,是我没有做过的事情,但是在很多方面,它看起来确实像是一本小说处女作。但我希望它比很多人的处女作小说要好,因为在这之前我已经用三本书教会我自己怎么写小说了。
新京报:那么在你所有的小说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一本?
米切尔:最近的那一本,《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如果我的下一本书没有比上一本书好,我就不会把它交给我的编辑,因为那说明我在退步,而不是在进步。我也许是错的,但我必须相信这一点。但是,说真的,真正让我激动的是我的下一本书。我不在乎我已经写过的那些书,我感兴趣的永远是我的下一本书。当然,书一旦出版,我要在采访中谈论它们,但我的心永远在下一本书上面。
【对我放松一点要求,如果你一开始就不犯错误,你就不能超越错误】
《幽灵代笔》和《云图》都进行了结构试验,前者可能显得有点用力过猛,不过大卫·米切尔说那是27岁时的他能写出的最好东西了。他骄傲于自己的新书比少作更好,至于其中的经验,很简单,用他最喜欢的词语来形容,保持“杂食性”地思考就好。
新京报:不少人曾将你与保罗·奥斯特和村上春树做比较,你认同这种比较吗?你的写作是否曾受过他们的影响?
米切尔:我试着不去想这些。我是否受过他们的影响?嗯……我不觉得。我想影响是,你读了什么,它让你很佩服,然后你想去模仿它。我想保罗·奥斯特和村上春树都是很好的作家,他们写出了非常漂亮的作品,他们的作品位于最好的之列。我想我读到任何东西,那些让我觉得“哦那很聪明,你怎么做到的,让我想想”、“哦那很漂亮”的东西,我就会去思考它,然后或许会去使用它或是改一改再把它放在自己的小说里面,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但我想这不是你的问题是吗?我想你的问题是我最喜欢的作家是谁?
新京报:哦,那也是我的问题之一。
米切尔:我的神是俄国作家安东·契诃夫。他真是无比伟大。我爱极了他的小说,我会一遍又一遍地去读它们。是的,俄国作家确实是伟大,我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俄国人真的是很好的作家。还有Bulgakov,我不知道他是否被介绍到了中国;他不是很有名,但他写过一本完美的小说叫做《大师与玛格丽特》。
新京报:哦,中文叫布尔加科夫。我读过那本小说,不过还有一小部分没有读完。坦白说我并没有完全被折服——我不知道是因为翻译还是什么。
米切尔:你很诚实。我觉得英文翻译好极了。我现在还经常想着那本小说。在这本书中,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叙事——上世纪30年代的俄国,和一世纪的巴基斯坦,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但是融合得那么好。书中有很多幻想的成分,但它不是孩子气的,而是美丽的。这是我喜欢它的原因。还有狄更斯,我一直喜欢狄更斯,他写过一些垃圾,但大多数都非常好。几乎所有人都会写一些垃圾,这是正常的。嗯……所有人都会写垃圾,但如果他们幸运的话,这些东西不会被发表——不要在太年轻、太早的时候发表作品。我想如果你在21岁、22岁的时候就发表了作品,在当时你会感觉良好,在后来它会带来问题。
新京报:之前我提到,作家在写第一本小说时总是会很用力地去写“新颖”的东西,但有时他们会用力过猛。在你的《幽灵代笔》中,你似乎在试验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叙事,但是结果似乎不是很平均。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而言,其中有一些非常出色的故事和章节,但也有些章节读起来似乎缺乏深度。
米切尔:对我放松一点要求。我写那本书的时候才二十六七岁,在你看来不算小了,但对于一个作家的生命来说,其实还是一个婴儿。对于其他艺术家来说,毁掉少作要容易得多。如果你是一个画家,只要拿起一把刀子,它就没有了。但对作家来说,你的作品印出来了,发表了,流传了,它就成了你永远都不能改变的东西。你会成长。如果你一开始就不犯错误,你就不能超越错误,而且你的错误是你的老师。不幸的是,身为作家,它们是非常“公众”的老师,你不能改变它们,所有人都知道它们。但是,我又确实不能为它们感到遗憾。在我27岁的时候,它确实是我可能写出的最好的书了。现在我42岁了,我可以写得更好,感谢上帝!我都不敢读我以前的作品的英文版,我会想,天呐,看看那些东西!那么的自我,那么多比喻!每页纸一个比喻,你为什么要放十个比喻、五个比喻?那么多的“好像”,“就像”……你就直接说那个东西是什么好了,为什么要用比喻?但是,如果我没有那么做过,我就不会知道这一点。我很高兴我的早期作品要比后期作品更不平均,如果是相反,如果我的早期作品是更好的,我就会担心,就会沮丧。幸运的是,对于作家来说,如果你保持思考,保持“杂食性”地思考——这是我最喜欢的词——如果你可以“杂食性”地思考,那么你就会不断地成长和进步。
【你必须忽视坏评论、怀疑好评论】
大卫·米切尔在英国是畅销作家,在美国却可能不是,当然现在有了电影《云图》,在美国他也可以算作畅销作家了。于是,他和读者的关系,他和评论家的关系,也就成了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像面对这场有点刁钻的访谈一样。
新京报:评论家好像很喜欢那本书。你从评论家那里学到过什么吗?
米切尔:只有百分之三的评论家会深入地思考你的书,并且爱文学胜过爱他们自己,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去写作。当我读他们的文章,我觉得他们是温和的导师,他们想帮助我。但是这些人的数量并不多,事实上,不是百分之三,而是整个世界上只有三个人。对于其他的,你最好都不要去读他们,包括正面评论和负面评论。他们是平静心灵的野餐会上的黄蜂——这是他们的角色。如果你想写作,他们会在旁边嗡嗡,你最好是好的坏的都不听。那些写坏评论的人更像是平静心灵的野餐会上的狙击手,他们开枪打你。但是就算是那些写你好的评论家也会妨碍你集中注意力,而且你也不能听信他们——所以你必须忽视坏评论、怀疑好评论,这就是我和评论家的关系。
新京报:但很多时候读者很容易受评论影响。你和读者的关系是怎样的?你觉得读者会帮助你成为更好的作家吗?
米切尔:如果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你,那么他们是比较容易受评论影响,但如果他们已经读过你的作品了,那么读者和作家的关系就变得更直接,就不再需要评论的裁判所来当中介。如果你可以连续写五六本书并生存下去,那么你会建立一个读者群,他们会去买你的书,而不会去等报纸书评出来。我想互联网、社交网络也让这个关系变得更直接,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好的力量。至于我和读者的关系,他们养活我,我想这会让我变成一个更好的作家。事实上,我也不太考虑这个事情,我只是很高兴我有这些读者。当我偶而从我在爱尔兰海边小镇那个僻静的洞穴出来,当我去文学节、读书会上见他们的时候,我喜欢从他们身上汲取能量——就像两天前在三联书店时那样,我确实没有料到当天会有那么多人去,我不知道在中国有没有人听说过我,但那天在地板上都坐满了人。倒不是说我为自己感到高兴,我是为我的书感到高兴,我很高兴我的孩子们找到了好朋友,这是我和读者的关系。同样地,就像你和评论家的关系一样,你最好不要经常去想它,不然你会开始为读者写作。然后你会碰到这个问题:哪些读者?一个北京的22岁的学生,还是犹他州盐湖城的一个极端主义的摩门教徒?事实上,我是在为我和我妻子写作,如果我妻子喜欢我的书,那就行了。
【小说的骨架里面,是跳动着的人的心灵】
这是一场紧张的,甚至有点咄咄逼人的对话,所以我们有必要给作家留出反击的空间。他说,你在22岁的时候只想证明自己一定是对的,但生活终将教会你成长与和解。所以,如果你觉得《幽灵代笔》不够成熟,请试试《云图》,或者《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大部分时候,你总会喜欢其中一部的,不喜欢,也没有关系。
新京报:我喜欢读作家谈写作的文章。我想马尔克斯和雷蒙德·卡佛都说过,推动他们去写一个故事的往往是一个形象。对你来说,什么是促使你去写一本小说的动因?
米切尔:一本特定的书,还是笼统地说?
新京报:哪个问题你更愿意回答?
米切尔: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不同的,那我两个问题都回答吧。总的来说,我写作是因为如果不写,我会不快乐。非常简单。然后你又会说,为什么我写了这本书,而不是那本书?这取决于我碰到怎样的种子。有时候它是一个形象,但也有其他的种子,有时候是一次相遇,一次会面,也可以是一个句子。这儿有一个好句子——“死者在假期的生活”——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句子吗?
新京报:是呀,你会把它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米切尔:正是!它可以怎么成长?它可以是关于还没有出生的死者的哀痛?它可以是关于吸血鬼,葬礼?它可以是关于一个死了女儿的人,他需要承受从前从没有承受过的悲痛?它可以有很多的方向,它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种子,有很多可能性。是的,对我来说这个动因有时候是形象,但不总是。
新京报:我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你创作小说的过程,人们通常觉得这个过程很神秘。
米切尔:很简单,你有了一个种子,决定写它。你决定写它是因为你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它。然后你需要一个世界,你需要时间、地点、人物。人物是非常重要的,你需要创造一个人物形象,他可能是你认识的某个人,可能是一个像弗兰肯斯坦一样的魔鬼,他可能融合你从这个人身上提取出的某种素质,和那个人的脸,以及另外一个人的某段历史——让他成为一个复合型的人。然后你需要把这个人送上一段旅程,它可能是一段物理上的旅程,也可能是一段心理上的旅程。他们必须有什么不对劲,必须要有某些性格上的缺陷给他们带来痛苦。他们需要处于痛苦当中——这是小说的来源。他们需要“需要”什么东西,需要有让他们无法得到这些东西的障碍;也许他们得到了他们需要的东西,但最后发现这不是他们想要的。就像许多个世纪之前亚里士多德说的,戏剧来自冲突,所以需要有障碍。如果这个障碍是另外一个人,那么将会有争吵,冲突。所以,这就是从事我们这个行当用到的工具,这就是你创造一个故事的方法——也许它会变得很复杂,也许它会拥有不同的视角,也许它会有很长的时间跨度,也许它只是很长,呵呵。
新京报:我记得你在一个访谈中说你希望以后远离复杂性,因为小说是关于人,关于“人生的混沌”的。
米切尔:是的,我确实说过我希望远离复杂性,但是我经常做不到。小说是关于人的,难道不是吗?最好的小说让你关心一个人,你担心在他们身上会发生坏的事情,然后你不断地读下去,希望这些坏事情不会发生。有时候一本书变得很复杂是因为我希望把太多的东西放进去,它们必须要有一个复杂的结构,才不会变得无聊。但在小说的骨架里面,仍然是跳动着的人的心灵。你必须记住这一点,不然你的作品就会变得生硬、变得毫无生命力。
新京报:很多作家谈到,在他们的写作生涯中有过一些顿悟。比如卡佛说过,在写完《大教堂》以后,他作为小说家才真正成熟了。你有过这样的顿悟吗?
米切尔:在此“顿悟”有两个涵义,一个是关于你的作品的顿悟,一个是关于人生、关于宇宙的顿悟。你指哪一个意思呢?
新京报:两个都是。
米切尔:是啊,上帝啊,它们无处不在!而且它们是好东西。往往是在你回头去看你从前的作品的时候,你会得到这些顿悟。你会想,天呐,那真是太糟糕了——这是一个顿悟。因为你现在知道为什么它很糟糕,那意味着你以后不会犯同样的错误,那意味着比起你有这个顿悟以前你是一个更好的作家了。谢谢!——越多这样的顿悟越好。当你意识到形容词不是你的朋友,当你明白一页纸一个比喻足够了,当你决定至多五页纸一个感叹号的时候——这些是极好的顿悟。而关于人生的顿悟?我想是同样的道理。而且不光是对于作家,对于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比如当你意识到友善比正确更重要的时候。比如,如果你的妻子很爱一部电影,而你觉得那是一部很糟糕的电影,不要和她争论,就说,我很高兴你喜欢这部电影,我没你这么强烈的感觉,但我很高兴你喜欢它。在我22岁的时候,我肯定必须要为此大肆争论一番,我必须证明我是对的,这部电影是一堆垃圾。但我们在生活中得到了学习和成长,如果我们幸运地远离了灾祸活下去,我们需要尽可能多的这种顿悟,它们会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快乐,它们是我们的朋友。
【记者手记】
好运气的大卫·米切尔
对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一周之前,大卫·米切尔可能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相信在上海书展之后,随着密集的媒体轰炸,这个名字将会不再陌生。几乎可以预见,到了明年一月,当《云图》搬上银幕之时,大卫·米切尔这个名字将会变得家喻户晓,他将毫无悬念地成为一个国际性作家。在我们的时代,没有比好莱坞更强大的造星机器了。
当然,米切尔的好运不是从最近才开始的。1999年,30岁的大卫·米切尔发表了小说处女作《幽灵代笔》,获得了当年的约翰·卢威连·莱斯文学奖。2004年的《云图》则获得了当年的英国国家图书奖。可以说,米切尔的写作事业是异常顺利的,顺利到足以令绝大多数作家羡慕嫉妒恨。
米切尔的小说最为人称道的是它们的结构,这也是国外评论家经常大做文章的地方。作家苏童将他的写作比作乐高玩具。在《幽灵代笔》中,米切尔讲述了九个不同地方的九个故事,涉及人物众多,跨越诸多年代。这些故事中,有带着村上春树式淡淡的虚无和惆怅的小品,也有讲述国际名画大盗爱欲情仇的类型小说,甚至还有以一个四川老妇人的视角讲述的浓缩版中国近代史。这些故事大抵可以看作独立的篇章,虽然不同章节中的人物命运出现了交叉与勾连。米切尔自己说这部小说想要讲的是命运,但是,关于命运的什么道理?读完小说后我并没有答案。
我接触到的大卫·米切尔是一个和善、谦逊、坦诚而健谈的人。与前辈立足于英国本土社会生活的作家相比,米切尔似乎要更为“国际化”,而更少本土化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不是很典型的英国作家。在他的五本书中,只有第四本《绿野黑天鹅》是设定在英国的故事,这部半自传体的小说讲述了一个有点结巴的13岁的小男孩在一年当中的遭遇。作为一名严肃作家,他还没有涉及他所成长的社会中更为广阔的生活疆域。又或许,这对于米切尔这一辈的英国作家——或者不论哪里的作家来说——才是更合理的一种取向。在这样的时代,对于小说家来说,他的工作是变得更容易,还是更困难了呢?我很遗憾在访谈中我没有问到这个问题,对此我自己也没有答案。不过,所幸的是,小说这种艺术形式依然充满无数的可能性,可以容纳和完成无限的思考。正如米切尔所说,只要你保持“杂食性”地思考,你就会不断地成长和进步。
C12-C13版/新京报记者 吴永熹
本次访谈获得了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艺述英国”活动的支持,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