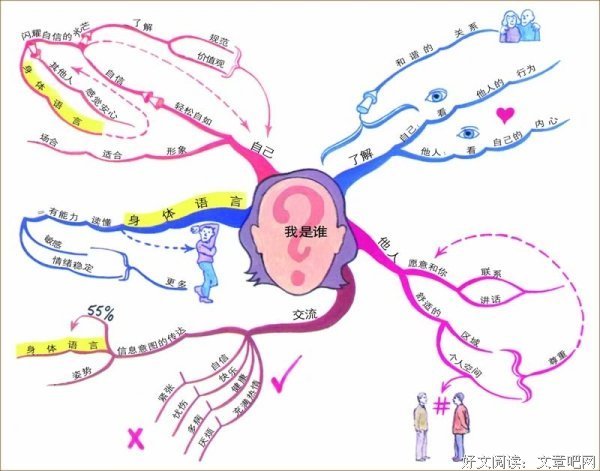《乡村与城市》是一本由[英]雷蒙•威廉斯著作,三辉图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页数:46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乡村与城市》读后感(一):这个男人来自乡村
2007年,美国上映了一部电影《这个男人来自地球》,影片主人公欧德曼说他是一位生活了14000多年的穴居人,这件事太过荒谬,来自哈佛的同事们只权当是个找故事漏洞的智力游戏,因此,要求他描述一下他所生活过的远古时代。随后,他对自己漫长童年的回忆很快被渊博的考古学教授驳斥为全是书上的东西。他从容地说,当然是书上的东西,我只有在读到关于那些时代的书籍时才能回忆并认识那时的处境。这听上去很可笑,但仔细一想,我们对生活世界的认识并非仅仅源自经验,文本亦同样参与到建构我们认识的过程之中,有时甚至会让我们对本真的经验失却了信心。
有个出生于威尔士乡村的男人也提到了同样的尴尬处境,他叫雷蒙·威廉斯,他在其著作《乡村与城市》中说:“来到城市之后,我才从市民、学者那里了解到有关乡村生活、乡村文学真正意义的说法。”换句话说,在剑桥三一学院教会他乡村是什么样子以前,他并不知道该如何描述承载自己童年记忆,以及祖祖辈辈耕耘其中的乡村,难怪他会说,“一想到这,我就感到有一种讽刺的意味。”可这就是他一生的写照,正如他的自传体小说《边界乡村》所显示的那样,他像个边缘人一直游走在城市与乡村的边界上。伊格尔顿就曾说:“就仪表谈吐而言,威廉斯不像教授倒像个乡下人,他待人热情淳朴,显然同中产阶级上流人士们的那种优雅而随意的做派格格不入。”然而,正是童年时所经历的乡村生活仿佛一道暗涌的激流不停地质问着他的生命:纸上的乡村都不是真的。《乡村与城市》就是这种矛盾的体现,有时你会看见颇有利维斯风范的威廉斯旁征博引,在各种文本间细细地考究,似乎在重温那“伟大的传统”;可有时你也会看见“我的祖父”“我的外祖父”“我的父亲”等等带着私人烙印的叙述者,携着人生经历突然现身于这样一本煌煌学术著作中的某个角落。这种吊诡和突兀在读者仿佛是白璧微瑕,可深究了,却是他此书的核心——文本与经验的战争。
如今的社会并未比威廉斯所揭露的那个时代更好一些,都市人仍然会将自己湮没在“怀旧”之中,也许是在怀念逝者如斯的韶华,也许是在憎恶形同陌路的自我。他们想回到童年,回到乡村,回归田园诗般的大自然。可读完《乡村与城市》,我仿佛被眼袋深凸、眼神深邃的威廉斯当头棒喝,心中只得兀自深吼一句:醒醒吧!哪里有什么可以归去的乡间和家园,以前没有,现在更没有!文学中所谓“黄金时代”、所谓“快乐的英格兰”、所谓“田园传统”从来都只是吟游的诗人们臆造的美好,这些维吉尔们来了又走了,偶尔眨巴眨巴眼睛,便发现了所谓的美,可他们眼中除了感谢造物主的眼泪,就只有吲哚花朵的蜜蜂、咕咕吟唱的斑鸠,天上掉下“好奇的桃子”,酒杯中斟满馥郁的埃尔酒,即便诗人不小心跌倒了,也一定是躺在花丛缠绕的绿茵之上。面对这些,威廉斯说,一切都是阐释和视角的问题。转过头去,换个视角,你就能撞见赤裸裸一丝不挂的真实。他所亲身经历以及从亲人口中得知的乡村应该是克雷布笔下的那般模样,没有泉水叮咚,没有羊羔嬉闹,没有红雀啁啾,也没有快乐田野,真正存在的是汗水、尘土、令人窒息的烟雾,以及受尽主人责骂的打谷工人。可诗人们不停地歌咏,让田园和乡村成为邪恶城市的对立面,成了天真纯朴的代言人。一旦人们看惯了城市里商人的虚伪、资本家的残忍,就能义无反顾地“还乡”,就像托马斯·哈代笔下的克莱姆·约布赖特,看破纸醉金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在真正艰难生存的乡下人眼里,没有比这更矫揉造作的了。
威廉斯如数家珍,一倾而下,从古希腊到英国,从诗歌到小说。古典时期的田园诗中尚且既能看见田园生活的乐趣,也能瞥见农事劳作的心酸,但从文艺复兴开始直到新古典主义,田园意象被不停地打磨成精致的瓷盘画,人人如奥林匹亚诸神,尽情演奏、嬉戏,食物们仿佛都是迫不及待地跳入宾客的餐盘之中供人享用。他们看不见挥汗如雨的农奴,也瞧不见负轭犁田的老牛。英国乡村宅邸的新贵们,肆意地模仿普桑笔下的风景,企图将周遭的山山水水打造成“风景如画”(picturesque)的样子。威廉斯却一针见血,小说中夜夜笙歌的乡村大宅背后隐藏的却是“圈地运动”和“农业资本主义”的残酷。在让人如痴如醉的文学之外还有一段被人遗忘的残酷历史,此时的威廉斯显露出马克思信徒的光环,振聋发聩地说,“阿卡迪亚”般的乡间庭院所依赖的是一套完善的剥削体系,乡间新贵的猎场之外满是找不到食物、流离失所的佃农们,他们被迫成为盗猎者,因为饥饿让他们不得不去“无耻地侵占”这些大爷们的私人财产。贫穷成了一种罪恶,在济贫法之后,流浪的穷人被扔进了监狱或教养院,享受着与疯人一般的待遇。即便是被雇佣的农户,也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他们努力劳作被看作是天经地义,因为雇主们会赏赐给他们的食物,也免去了他们的牢狱之灾。也正是因此,地主与上帝共享着同一个尊贵的名号“Lord”。这种看似荒谬的逻辑所还原的正是一个历史上的乡村。他真正想告诉我们的是,古老英格兰的所谓“自然经济”并没有与城市里的资本主义有任何本质上的不同,但更可怕的是,这种残酷的现状却被桂冠诗人以及文化精英们尊奉为失去的传统。他们住在城市的繁华之中,敲着烟斗,端着红酒,偶尔一声长吁短叹:世风不古,田园何在?
乡村被一堆堆精雕细刻的文本所遮蔽,海德格尔眼中能涌现真理的诗歌到头来只是赤裸裸的欺骗和隐瞒,也许正如克雷布所说:“诗中不再有真相,尽管表示不屑吧。”充满着贫困、饥馑以及苦难的归园田居让人想起普桑的一幅名作《阿卡迪亚的牧人》,在优美静谧的田园景观中,潇洒飘逸的古希腊式牧人围绕着一块神秘的石碑,上面铭刻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死神箴言:“阿卡迪亚亦有我在(Et in Arcadia ego)”。无论你是厌恶工业革命后烟囱的肆虐,还是憎恶资本家双手沾满鲜血,都别企图逃跑,更别想去乡村寻觅安慰和希望。城市固然不能是文明的代名词,乡村也并非纯朴的栖息地。资本主义的魔爪素来所向披靡,威廉斯打碎的不只是我们不愿从中醒来的迷梦,更是牢牢桎梏着我们的思想枷锁。如果你非要像奥威尔笔下的乔治那样“上来透口气”,那结果只能是被窒息在绝望之中,因为故乡倏已逝,迷途哪可返。乡村从来都不会比城市更美好,天使和恶魔都同时盘旋在两者的上空。他希望我们知道如果资本主义就是原罪,那么我们应当像“鲜血还是面包”运动那样去与资本主义体系抗争,去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解决问题之前必须得让人知道:这儿的确有个问题!
【本文已发表于《上海证券报》2014年4月某日(忘了),标题被更改为“醒醒吧 今天哪里还有可归隐的乡间田园”,此处公开的为本人原稿】
《乡村与城市》读后感(二):想象的田园
文 李华芳 原载 《东方早报》
我之前讲了很多城市的好处。城市之间的比较遵循的是制度竞争的逻辑,简单来说就是包容性的制度最终会胜出,因为实行包容性制度的城市更鼓励自由选择。而自由选择激励创新,最终使得该城市在与其他城市的竞争中胜出。这个城市层面的好处比较容易理解,反倒是有不少意见心心念念农村的好处,认为我说的城乡之间要选入城去的说法过于简单粗暴,并不能说服人。其理由也简单,因为农村有城市不可企及的好处。
对田园生活的浪漫想象不是目前北上广深里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专有的,事实上,这也不是新生事物。最近读到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威廉斯的《乡村与城市》一书,就对16-20世纪英国文学作品中对乡村的浪漫想象给予当头棒喝,基本破除了这种想象中的农村的好处。雷蒙·威廉斯是二战后英国极有名望的思想家。在《乡村与城市》一书中,他批评了缅怀英国旧日乡村的一些观念,例如“快乐的英格兰”、“黄金时代”以及“消逝的农村经济”等等。威廉斯指出不管是历史事实,还是不少作家的作品,其实都指出了昔日英国农村充满了苦难。我在这里不想卷入威廉斯讨论的资本主义的恶劣后果。我想指出的是对农村浪漫生活的想象是站不住脚的。威廉斯通过对文学作品的分析,至少有一点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指出了对田园生活浪漫想象的文学作品其实并不多,而大部分作品其实是揭示乡村的困境。这一事实即便不能说明农村的确要悲惨得多,也多少表明从公众认知上来讲,田园是悲惨的代名词,而不是“高品质”的浪漫生活的同义词。
一种反驳意见认为现在有城里人的确想住到农村去,可能是被污染吓怕了,或者是受不了城市的喧嚣了,以至于冒着小产权房得不到有效法律保护的情况下,依旧购买了农村的房子住下来享受“田园生活”。如此一来,怎么还算是“想象”田园呢?不得不承认这类现象的确存在,但当我们谈及一种现象的时候,不妨找一找同样存在的与此矛盾的另一面事实,那就是千方百计要进城去的农村人口远远多于想要享受田园的城市人口。在双向流动的过程中,从农村到城市是更为重要的一面,而从城市到农村的流动,毕竟是少数。在这些少数的流动人群里,的确有些人已经有能力实现浪漫生活,但这不同于农村本身就能给他们提供浪漫,相反,是他们去农村创造了浪漫。事实上,他们在想到要夜宵、要卡拉OK、要午夜场电影的时候,“有能力”回到城市,这和单纯生活在农村的农户“没有能力进城落户”有本质的区别。
城市的发展其实已经某种程度上内化了这种“想象的浪漫”,或者说在某些场合刻意营造出“田园风格”。例如建筑和内部装修采用田园风格等,当然无法全部复制农村的生活,但这种“想象中的田园”的确通过城市更为丰富的选择得到了部分满足。简单来说,如果预算足够,同样有可能在城市里买到带后院的房子,并且将后院布置成乡村风格。
但反过来的那种农村对城市的向往可能是更加强烈的。这不仅是指农村现在有大量建筑的风格是跟风城市,而且也指装修上的亦步亦趋。实际上,没有什么能阻挡农村人民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以至于当他们无法真正“进城落户”的时候,就从身边可见的一切里模仿城市。村落保护、遗迹传承这一类的故事,只有在政府资金支持或者之前出去到城市打拼的富人回乡捐资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
而最近三十年的中国,正是这种从乡村到城市巨变的典型例子。我出生在浙江舟山的金塘岛的一个小村子里,这个小村子叫做擂鼓岙。在我上完小学后,我家从擂鼓岙搬了出来,但当时在擂鼓岙里面的至少还有四十几户人家。今年暑期特意回去老家看了看,所剩不过5户人家,而且全是老人,已经习惯了岙里面的生活,不乐意住儿孙们在城里的新屋。但和这些老人们一起聊天,所感叹的却是这三十年来打破生产队进入改革开放给自己家庭带来的“好处”。当然也有留恋,那就是人越来越少,除了寿终正寝的,就只剩下他们这些老人了。偶尔能热闹一下的,也只有春节和清明了。老人们感叹的是这些农耕时代的节日似乎越来越传不下去了。我倒对此并不担心,文明的演化当然也和经济水平紧密相关,节日的形式和内容都会随着时代变迁而有所变化,但经济水平上去了,对传统的传承反而是有助益的。前几年擂鼓岙修宗祠,各家开始搞家谱,当然是因为有钱了。要是在生产队挣工分,怕是谁也没有那闲心的。
我得说正是城里头扎扎实实有各种选择的自由,或者按照擂鼓岙老一辈人的说法“机会多”,吸引了这几十户岙里面的人家跟着改革热潮,外出打工进而落脚城市,切切实实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回头去看,你当然怀念儿时的乐趣,但你也不愿意停留在那过去的时光。因为那种想象的田园背后,正如威廉斯所言,是“悲惨”的现实。打补丁的裤子、两三年才有双新鞋子、客人来了才买鱼肉、过年才有零食,那没礼物的童年对照今天儿童的处境,如果还有什么人因为想象的田园里能捉知了捉泥鳅而愿意返回田园,那只能是“有闲阶层”。但实话说,我不认为这些有闲阶层真能抵抗村里夏天的蚊子。
“想象的田园”架不住真实的数据,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下一代教育问题。2013年5月中国国家审计署公布了《1185个县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情况专项审计调查结果》,其中提到在重点核实的52个县农村1155所学校,辍学人数由2006年的3963人上升至2011年的8352人,增加了1.1倍。这还是在国家普及义务教育,增加财政支出,并且农村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情况下发生的。农村中小学的凋敝却是不争的事实。造成辍学率提高的因素当然有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依旧是“钱”。一旦当农村家庭感觉到无法负担子女的教育,孩子辍学就几乎是很“自然而然”的结果。因为农村人口大量进城,导致农村人口减少,促使国家对农村中小学布局做出调整,集中教育资源到稍微中心一点的“镇”。这样一来,如果学生不住校,就要花费很大的交通费用;如果住校,就要花费很大的住宿费用。总之,孩子教育花费上去了,这对于收入增长没有那么快的农村家庭来说,就造成了沉重的负担。所以“想象的田园”是靠不住的,孩子的教育问题就会阻止城市里有能力的人做出隐居田园的决定。
当然在义务教育以及高等教育上的回报,在中国依旧是非常高的。李小瑛等2010年在《世界经济文汇》发表文章测算了教育的私人回报,从1989年的6.4%上升到2006年的13%,这表明“读书无用论”是站不住脚的。同时,进大学也依旧是农村孩子进城的一个重要途径。所以出路是摆在那里的,别被“读书无用论”迷惑,也别被“想象的田园”迷惑,农村的孩子还是要读书、进城去。■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乡村与城市》读后感(三):《乡村与城市》第一章翻译讨论
原先觉得翻译得不太容易读,但是比照了一下原文,感到译者已经尽力了......由于要开读书会,抽空去对比了一下第一章的原文和翻译。
【第1页】
第19行:把“but nothing like identity”译作“但二者绝对不是完全相同的”,疑似将identity看成identical。或许应该是“但身份上完全不同”。
第23行:“in Britain as clearly as anywhere”应当是在英国有区别,在别的任何地方也有这样的区别,而不是“英国和其他地方的村庄也有区别”。
【第2页】
第10行:原文有“and this in a society which had already become the first predominantly urban-dwelling people in the long history of human settlements.”译文里只有“在人类漫长的定居史上,英国成为第一个主要在都市居住的民族。”首先“urban”译为“都市…的”有一点小问题,似乎metropolitan才能说是都市。另外前后这个衔接“and this in a society”省略不太合适,要强调的正是农业比例如此低的情况下还有这么多人住城市里,更加进一步体现出威廉斯对于农业衰退的不满。还有一个小地方,这一段中Britain和England都混为“英国”,但我也没看出来威廉斯是不是真的要强调英格兰。
第16行:把“attitude”和“idea”都译成了“态度”,或许后一个说成是“观念”会好一些,但两者意思可以相通。
第17、18行:原文是两个相同的predominantly,但是一个译成“绝对”,一个译成“主要”,似乎应当统一一下。个人感觉应当是找一个程度在上述两个词之间的词。
【第3页】
第4行:把visit译成“参观”,从字典角度来说没什么问题…但总是给我一种去看奇葩的感觉…威廉斯可能更多地是体验和感受,译成造访怎么样… 不过这一点有点太抠了。
第8行:explicitly译成“详尽”,这个词应当既译出详细,又译出明确、清晰的意思,“详尽”似乎只能顾到一面。
第12行:我倾向于认为这一章当中的experience都译成“体验”而不是“经验”,因为威廉斯强调的更多是一种非结构的感受,而不是成形的“经验”,特别是这里的“切身”之后跟着“体验”很舒服…不过这一点也有点太抠。
第17行:headscarf是“头巾”而不是“围巾”。之后这句话似乎有点歧义,我的理解是这辆蓝色的公共汽车载的是女人们,她们在不用管孩子的时间可以坐车去收获… 是这样吗…
第22行:land译成田地有些奇怪,还是土地吧,另外这一句当中漏掉一个插入语not far up the road没有译出来。
第25行:这里一个on the Welsh border没有译出来就比上一条更加严重一点,因为威廉斯出生在边境地区这件事在后文有比较重要的影响。
【第4页】
第11行:这里有一个“巷子”并不是错误,但是英文都是lane,前后都译成“小路”了,最好统一。
第25行:“四段路”有歧义,读着感觉是四种不同的路连接在一起,而实际上则是四条并行的路。
【第5页】
第2行:这个car感到应该是汽车而不是马车。在OED上可以查到它可以是汽车或者(火车)车厢,虽然有chariot的意思但那是用来打仗的 … 之后也提到商贩们开卡车,所以看似应该是开汽车。
第13行:去地图上查一下Brynarw在哪里就知道它是在威尔士西南部而不是英国西南部,另外处于“英国西南方”的地方肯定不在英国,所以是“部”。同样在下一行这是威尔士的东部而不是英国的。这句话的意思似乎分析有误,不是说“我在西南部”或者“我在东部”,而是“我朝西南方向看”或者“我朝东看”。求证一下地图,基本意思应该是“我”在家里,现在往西南看过去看到了Brynarw那里,往东看过去能看到剑桥的光。
第14行:“白马在吃草”虽然挺符合逻辑的,但似乎从原文读不出白马在干什么。
第16行:“晚上我刚…”这里我倾向于认为first的意思是第一次,“刚”的话就感觉作者有点傻,每天晚上看到都以为着火了。
第17行:“我在窗前坐的地方”,漏了一个动词“写”,他在窗前写作呢。
第19行:“晚上睡觉前,我走到屋外,注视着明亮的天空”有一点奇怪,毕竟睡觉的时候一般是晚上,晚上不会有“明亮的天空”。“look at that glow in the sky” 更像是看着天空中那一点发亮的地方。这有点太抠了。
【第6页】
第3行:dome翻译成“圆顶”没有什么意见,但诗里同一个词翻成了教堂,最好能够统一。
第19行:my own people翻成了“我的家人”,不过如果一眼望下去一块块色彩斑斓的田地全是自己家人开垦的也是不太容易。感觉威廉斯指的是“我自己那样的人”,也就是乡村的农民。
第21行:有漏掉了lines received and lines made这一个插入语的翻译。
【第8页】
科贝特这段话在这一页上的最后一句:原文是The land just about here does seem to be really bad. 所以应该确实是挺贫瘠的,而不是“看起来并不差”。另外这段话最后有一个“上面字写得很大”,原文用的形容词是conspicuous,可以认为是比较清晰但不一定是大。
【第9页】
第7-9行:词语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原文是两个运动,而不是翻译中的四个。似乎应当是“通过一个家庭和一个民族的历史在时间上运动,通过关系和决策组成的网络在情感与观念中运动”。
《乡村与城市》读后感(四):被诟病的怀旧
(一)怀旧情绪的产生
逆着城市街道的喧嚷,似乎可以回溯到一个过往,那里静谧而安详。资本供养的浮华让人迷醉,在这之后总有一些人被耳边的喧闹惊醒,他们开始寻觅往昔——一个自然的、未被破坏的、纯真而充满温情的时代。一些人想要退居这里,来逃避似乎是独属于城市的冷漠、贪婪、剥削与猜疑,或是把“过去的好日子”作为一种手杖,来敲打现在,产生了这种被称为“怀旧”的情绪。
怀旧着的人们把自己的情感投射予乡村,于是,乡村的一般意象成为有关过去的,而城市的一般意象是关乎未来的。“如果把这些形象孤立来看,就被发现一个未被定义的现在。‘现在’被体验为一种张力,在此张力之中,人们用乡村和城市的对比来证实本能冲动之间的一种无法解释的分裂和冲突。”
怀旧一部分是来自于身处于无序之中的人们,对稳定秩序的深切渴望,此外,也来自于对时空概念的混淆和意识形态的控制。田园诗中对田园牧歌的歌颂被选择性地留存了下来,把同属于一个时间维度之上的苦难与赞美分割为不同时间维度上的当下、未来与往昔,而在这样的分割之后,前者代表着残酷而后者代表着乌托邦式的完美。“先有一些诗歌,它们赞美乡村背景中那些谦卑、高尚的人物,或多或少都有意识地域城市和宫廷的财富和野心形成对比。然后又出现了一些诗歌,它们将这种道德对比进一步发展为一种历史对比”,从而由反思走向怀旧。而逝去的往昔,常常也因为故乡和童年的逝去,和自然的被破坏,而承载着怀旧的感慨,“纯真、安全、宁静和富足都首先印刻在一片特殊的风景上,然后被强有力的扩展至一个特殊的乡村往昔”,人们“在自然的静谧中入睡,就像贴着母亲的胸脯睡去”。而怀旧者的田园想象恰好契合了所谓的意识形态——曾经的田野上,农民是被“保护”的,“不过是像牲畜和溪流那样受到保护,以便他们能够付出更多的劳力,生产更多的食物,抛洒更多的鲜血”,而“正义被他们所操控,为他们说话”。
(二)怀旧合法性的消除
然而在雷蒙•威廉斯的分析中,城乡之间并不存在这样的对比。其一,并不存在一个“自然的”和“道德的”经济,石油公司做的事情、采矿公司做的事情,就是地主做过的事情。新田园诗中写出来的,不过是一种消费慈善——似乎所有在劳动上的不慈善,都能够通过后继的宴席而得到救赎。其二,这种“自然经济”和后来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并非截然不同,而是存在着割舍不断的暧昧关系,后者是在前者之中孕育产生的。在封建时代晚期,地主阶级本身已经发生了改变,他们广泛涉足各类商业活动,依靠租金和资本投资的利润生活,逐渐演变成新式的资本家地主。他们的商业行为导致了大范围的圈地运动,征收苛刻的地租和圈占土地的过程巩固了他们对土地的控制。其三,所谓“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对立不过是表面现象。城镇既是乡村的映像,也是乡村的代理者,多数城镇都是作为农业秩序本身的一个方面发展起来的:在简单的层面上作为市场,而在更高的层面上,作为金融、行政管理和二次生产的中心。乡村中进行的对人和自然的剥削,在城市里被集中变成了利润——商人、律师、宫廷宠臣积累的财富——又渗入了乡村,进一步加强了农业剥削的力度。
剥削和压迫替代了的,是剥削和压迫本身(见对圈地、公地、社群、济贫法的分析)。在这样的分析之后,威廉斯有理由否定了怀旧的情绪,在看过了前资本主义——那基于当下而定义的往昔——之后,“难道我还敢让这些真实的不幸藏在诗意的骄傲那华而不实的陷阱之中?”我们需要的,是辨析人们所经历变化的真正过程,而将这些经历了、经历着变化的人们作为真正的整体生命,而不是观察对象,来感受他们的感觉。
此外,我以为,在《威塞克斯和边境区》一章中,哈代笔下还乡者的形象是类似于奥德赛式的。姚伯带着还乡的理想——“不是劝人悔改,而是劝人高尚”——然而,“他在忠诚的驱使下在旧群体眼中没有任何意义”。在复杂的压力之下,“还乡变得没有价值,唯一可能公然做出的行为也会显得很不正当。”他成了一名劳工,使他最初的事业更加困难,只有“他工作的单调性抚慰了他,这种单调本身就是一种乐趣”。
(三)劳动分工、专门化与分裂
在质疑了田园主义的怀旧情绪之后,威廉斯同样抨击了生机勃勃的城市工业主义——他们对乡村社会的蔑视和对城市工业化的信心一样强烈,被关于“进步”的想象迷惑了双眼而看不到前方的深渊。资本主义作为既定的趋势,在乡村和城市中制造着城市和乡村的,也是是人与人之间的疏离,田园怀旧和城市工业都无法弥合这样的断裂和伤痛,对此,威廉斯首先找到了这种断裂的现代性根源——“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分裂和对立在现代有了新的形势:劳动分工和专门化的顶点”。
“劳动分工和专门化的存在先于资本主义,但却在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了一个惊人的程度。”这种分裂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裂、管理和操作的分裂、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分裂”,它们渗透在生活中并形成了各种症状:“在社会各个阶级的思想和做法中;在对工作和教育的传统定义中;在对居住场所的分配中;在有关日、星期、年、一生这样的时间安排中”。因此,在这种种分裂中找寻联系,就需要“克服劳动分工的问题”,“只有拒绝划分,我们才能够克服这种划分”。
(四)被诟病的怀旧
威廉斯打碎怀旧想象的关键逻辑是:怀旧者所想象的往昔同样充斥着压迫与剥削,不存在一个“快乐的往昔”,因而,怀旧是对生存于往昔世界的人们之艰苦的漠视,进而,是一种不尊重。
我以为,这里存在一些问题:在弥合断裂的过程中,是否用力过了头,把由往昔到当下,进而到未来这个时间历程上发生的变化完全夷平了。退一步说,即便城乡之间“贪婪-纯真”的对立真的是一个谎言,那么,“怀旧”所指涉的那一个“乌托邦”是否有其存在的必要?
我以为答案是肯定的。《上海摩登》的作者李欧梵很喜欢用“想象”这个词,这其中的“想象”至少包含两种意思:第一个是“文化感觉”。我不由得想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一句话,“当一个隐喻形成,爱情就降临了”,在“想象”和“隐喻”的层面上(这里把两者直接等同可能有不恰当之处),是“感觉”的世界,那是客观现实之外,主观性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第二个涉及到关于民族国家的构想,以及这种构想如何成为可能。“这样一个景观也止于景观,是想象的,先于民族构建和制度化而行”,更重要的问题是,“‘想象性社区’的民族何以可能?”
这样说来,“怀旧”可以是一种个人化的“文化感觉”,有其存在的权利;同时,它也可以关乎一个“民族国家的构想”,先于制度,而设计一个更好的未来。因而,虽然想象终究不是现实,想象的美好和现实的苦痛可能残忍地同属于一副客观的图景,粗暴地抹杀怀旧的必要性也是需要商榷的。
威廉斯似乎把反思和怀旧对立在天秤的两端,然而,我们需要反思,也需要怀旧。反思式怀旧在天秤的一端,衡量着的是沉甸甸的未来。
《乡村与城市》读后感(五):pre稿|观点 危机 边界 成长
(二十分钟左右pre的讲稿,作者和背景介绍部分不是我,我负责泛泛地梳理书本内容,然而实际梳理的效果不尽如人意。除了我自己lazy,pre前六个小时刚开始写讲稿之外,这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威廉斯本人在这本书里呈现的精分倾向。读的时候总是很感动,但这种感动是碎片化的,无法形成脉络,甚至内部无法自洽。最终挑了几个我觉得重要的点,强行把它们串连起来,可是,在威廉斯那里真的存在这种关联吗?
(可能存在,只是我太菜了没发觉吧orz
视角与方法
乡村和城市不仅是两种人类的居住方式,也是不断变化的历史现实。而有关乡村与城市的观点和它们的变化发展则被威廉斯视作另一种历史现实。
威廉斯指出,人们在历史上总是对这些居住形式倾注了强烈的情感,并将这些情感概括化为具体的观点和意象。这些观点和意象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一方面保存着某些传统,一方面又在其内部发生着细微的变化。把它们放到具体的经济社会背景中考察,我们就能发现某些永恒的需求和变化的结构。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这些观点的出现是为了阐释怎样的经历?为什么在某个时期会产生或再次产生某种形式?
而这就需要对观点和意象进行历史性的、批判性的追溯。
关于农村的观点
农村在文学作品中的意象总是与一种快乐的往昔联系在一起。
早在公元前9世纪,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就在诗歌中描绘了一个远离灾祸和悲哀的黄金时代。这一意象对后世文学创作中“乡村”的形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典田园诗歌在歌颂乡村生活的纯净与美好时,保留了劳作和乡村生活的社会条件之间的联系,而文艺复兴则删除了这些生活张力,而留下了被精心挑选的田园意象;到16、17世纪的新田园诗那里,乡村和乡村经济被进一步地神秘化,脱离了现实的劳动生产,而成为一种自然的、宗教性的生活方式与经济结构。
除了快乐的“黄金时代”之外,16、17世纪英国的诗歌和小说还塑造了乡村意象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纯真。乡村被认为拥有一种与当时的城镇相比更为稳定的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在具体的文本中则表现为老实、忠诚的乡下人形象。
而随着农业资本主义秩序在农村的建立,小说和戏剧中开始出现经济利益和其他价值观念之间的选择,一种平衡物质利益与自我满足的价值观被安放在对乡村及其成员的描写中。而这一阶段的诗歌也把关注点从理想化的往昔转移到失落的现实上,穷苦的劳动者进入诗人的视野,使诗歌充满对惨淡现实的叹惋。需要注意的是,即便诗人发出的是对惨淡现实的叹惋,这种情感依然以对美好往昔的怀念为基础和最终导向,所有现实的苦难都被归结为世风沦丧或是纯粹的时间推移,是美好往昔被破坏的结果。
18、19世纪工业主义和城市的扩张,使城市中的物质主义与乡村的“自然”传统形成鲜明反差,城市里的人们对机械文明的反抗让人的身体在乡村文学中得到了前所未有强调。农业、自然和生命的意象被投射到人的身体上,农民和乡村劳工的劳动生活成为了自然节律的象征。因此,劳作的乡村变成了肉体和精神重生的地方。
在农村这个文学意象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威廉斯始终强调的是其背后的经济剥削关系。“黄金时代”的神话通过把乡村经济神秘化和宗教化,掩盖了地产和农产品的生产过程,而它们作为上帝的恩赐赠与地主阶级。乡村的“纯真”印象也来自于农村统治阶级与城镇居民的互动,稳定的社会秩序本质是一种稳定的统治秩序。随后的改良与反思更是直接来自于农业资本主义秩序在农村建立后的农村社会关系的变化。再往后的乡村意象,就典型的是城市居民对机械文明的反抗。
关于城市的观点
城市作为一种居住方式,并且作为一种越来越占主导的居住方式,比起遥远而充满怀旧色彩的乡村,对于生活在里面的人们和写作者来说,是更为实际的存在。这并不是说人们对城市的观念和意象更贴近“真实”,而是说城市意象的建立会更多地与人们对周遭环境的体验、对自我与他人的认知产生关联。因此,城市的意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同人物的意象构成的。
首先是暴民。18世纪,英国的高雅文学把都市定义为秩序和自由的中心时,又会强调都市中存在一个更为黑暗的现实。在这一现实中,城市里的下层阶级被视为不稳定和不安全的因素,被视为一群随时会被煽动起来挑战社会秩序的“乌合之众”,他们实际上也给城市带来了暴力和脏乱。威廉斯指出,狄更斯的作品反映了一种对城市下层阶级的同情与批判混合的矛盾态度,而在后狄更斯时代,这一态度被简化和扩大为对城市中绝大部分人的排斥和对极少数人的认同。因此,“暴民”是一个边界模糊的概念,它本质上是城市中孤立的个体对其他同样孤立的陌生人的集体想象。
因此,陌生人的形象也是城市意象的重要部分。艾略特在诗中这么写道:“虽然我们不曾在这里,我过去也是一模一样,知道我是自己但同时又是另一个人——而他的一张脸正在形成;但这些话足够促进他们已开始了的相认。”“我”的另一张脸,就是面对陌生人的脸,他之所以能与另一张陌生人的脸相认是因为他们是相同的:都是面对陌生人的脸。因此,对个体而言,陌生人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陌生公共空间里自我呈现和这个自我呈现在一个去人格化的他者之上的投射,这一自我呈现,本身也如另一张脸一样是去人格化的。而同时,他们又“顺着共同的风,相互太为陌生,因而不会误解”,在去人格化的同时又生发出一种机械化的同情,而这恰恰回到了狄更斯作品中的那种混杂着同情与拒斥的复杂态度。
艾略特诗中的“我”在遇到那个陌生人时,正漫步在城市黎明前黑暗的沥青道路上。与陌生人的相遇、对陌生人的感知,是以独自在寂静城市中漫步为背景的。威廉斯指出,从一开始,对现代城市新特性的感知就与一个人独自在城市街头漫步的形象联系在一起。在布莱克的诗中,他“独占着街道”、“独占着泰晤士河”,他切断了与他看到的事物之外一切的联系,而把自己交付给偶然发生的未知,他深陷于人群之中,体会的却是想象的真实。城市的活生生的一切都存在与漫步者的思想中,历史存在于迷失中,存在于人们之间关联的迷失中。
危机与焦虑
文学作品中关于乡村与城市的观点和它们的意象在威廉斯这里被视作一种社会危机面前的反应,而他也在本书中试图通过对这些观点和意象的考察,来了解这些社会危机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和影响。
事实上,威廉斯对每一种被归类的乡村和城市意象的解读中都大量地提到“危机”,如果我们对它们加以分类的话,这些危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类:
首先是农村和农村经验的危机。对农业资本主义下的金钱秩序的批判与鄙夷往往附着于对前资本主义世界的向往上,而由于其不可挽回,这种情感继而转向书本和记忆的世界里,并使人在现实世界里不是闭塞的,就是冷漠的,他们向往的往昔成为了封建性质的制度、阶层和道德的庇护。在城市和工业主义的扩张下,乡村生活方式被新兴工业体系发展到喧嚣所遮蔽,英国乡村成为了为工业发展承受最终冲击和付出最终代价的地方。农业生产没有缩小,而乡村中的贫民却被剥夺了土地和收入来源,不得不靠离开家庭或是依附他人生活。
另一方面的是城市中的危机。工业和农业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城市和乡村的分裂带来了其他一系列的分裂: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管理和操作、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并随着城市作为一种支配形式的全球化扩张而带来更多世界性的问题。
但是,这些“危机”是在哪些群体眼中,是在何种意义上被称为“危机”的,威廉斯却没有交代。
事实上,不管是在乡村还是城市,从农业资本主义秩序建立以来都有一个不断扩大和内部分化的中间阶层。他们过去处于封建领主和农奴之间,处于大地主和无地劳工之间,如今更多地处于城市精英阶层与下层劳动人民之间,却都承受着严峻的经济压力。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无法稳固下来,不仅在阶层体系内部面临不确定性,也面临着社会结构本身的不确定性,他们的内心始终是不安和焦虑的。
在这个意义上,“危机”其实是对变化了的现实和正在变化的现实的免疫性反应,抛开对农业与工业、乡村与城市的划分,威廉斯认为的“危机”广泛并永久地存在于社会越来越强的流动性中,而它也不再指涉农村的人口增长、粮食不足、贫困或是城市的治安问题、住房问题等具体的社会矛盾,而成为了威廉斯所谓的“情感结构”中的一部分。
流动性与情感结构
边界区的概念与流动性是密不可分的。边界的存在使流动成为可能,而威廉斯在本书中呈现的流动性,也恰恰集中在各种意义上的边界区。
乡村的一般意象是一个有关过去的意象,而城市的一般意象是有关未来的形象。如果我们将这些形象孤立来看,就会发展一个未被定义的现在。威廉斯认为,“现在”被体验为一种张力,但这个“现在”不是抽象的、绝对的存在,而历史地指向了工业革命以来被体验的时间。“现在”的张力可以被解释为人类社会本能冲突的分裂,但事实上,乡村是一个怀旧的意象,却比城市带有更多规范性和理想性的要求,劳伦斯等人的假想和现代科幻小说中的社会结构中闪烁着“黄金时代”的影子。相反地,城市生活在成为普遍而连续的生活经验之后,也被加入到“美好往昔”的回忆中。这是一种时间上的边界区。
空间上的城乡边界区则更为清楚地呈现了流动性特征。边界区的社会结构不同于传统的农村社会结构,一定距离之外的市场力量深深根植在其中,而不是表现为“外部城市、内部乡村”。曾经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如今成为了离开旧社群而进入新社群的人,他们被自己的历史困在教育和阶级关系的普遍危机中。这一点不管是在哈代那里还是在劳伦斯那里都是显而易见的。
哈代在生活和自己的写作中的地位是特别的,他是从边沿乡村成长起来的建筑师,与有教养的人士联系在一起,同时也通过自己的家庭与乡村的小雇主、商人和手艺人联系在一起。他既不是地主也不是佃户,不是商人也不是劳工,而是一个对自己的实际关系感到不确定的观察者、记录者。他叙写乡村劳动人民的故事,他的读者却是城市里的陌生人。这种边界区的成长经历和写作视角,使哈代个人“即根植于这个世界,又充满流动性”。而这种成长经历,这种生命状态,这种对自我与社会关系的认知,总能让我们想到雷蒙威廉斯自己。
童年与成长
被个人历史围困住的不仅是哈代、劳伦斯或者威廉斯,事实上,童年与成长的矛盾可能成为每一个当代成年人的困扰。“曾经亲密的、有趣的、接受了的、熟悉的、内心体验到的一切都变成了分开的、可辨明的、吹毛求疵的、不断变化的、从外部进行观察的东西。”这个过程发生在每一个人,不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的生命中,也发生在整个社会变迁的过程中。
童年的观点和童年的记忆常常被转化成对往昔乡村生活的怀恋,而随着城市的生活方式成为更多人的童年故事,对旧的城市社区的怀恋也同样具有真实的情感意义。在某种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和社会关系模式通过教导、加深印象以及主动给予的方式使那些外部感觉和行为模式显得正常和牢不可破时,童年的经验和回忆则是对这种社会畸变的反映。
美好的往昔无法挽回,儿童视角长成被健全的成人意识才能真正对畸变的社会做出抵抗。成人的塑造就在于正视那个导致异化、分离和外部化的社会过程,这也正是威廉斯在本书中做出的努力。
《乡村与城市》读后感(六):乡村与城市的二重性
文 朱晓剑 原载《都市时报》
乡村与城市在我的印象中,几乎是呈两极化的状态存在着,同时,它也反映了当下的社会状况存在着二重性。既有美好的一面,又有落后的因素。在英国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的《乡村与城市》里,它所描绘的英国乡村与城市的景象,也许对我们的当下是一种暗喻,并给以启示。
在文学样本里,乡村在不同的体裁中亮相,其所呈现的姿态是多种多样的。作为城市的参照物,乡村的魅力同样诱人。作者追溯英国乡村的衰落是从圈地运动开始,归结为工业化的后果。不过,作家、诗人对乡村的文学想象与书写是“把那些‘过去的好日子’当作一种手杖,来敲打现在”。
雷蒙·威廉斯在书中就乡村与城市进行条分缕析。比如第一章具有前言的性质,概括了历史上人们围绕“乡村”和“城市”所形成的各种观念,指出英国经验对于研究“乡村”和“城市”关系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作者以英国文学中根深蒂固的乡村怀旧为起点,回顾了十六至二十世纪多部英国文学作品(包括诗歌、戏剧、小说、散文、随笔等)中对于“乡村”和“城市”的描写以及有关“乡村”和“城市”观点的发展变化,并将之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发展过程联系起来,揭示出“乡村”和“城市”对立的实质及其所反映的现代大都市和工业化生活方式的危机。这种社会的分野实质上是从城市的建立和乡村就有了不同,作者将此归结为资本主义的危害,却也还是带着意识形态去观察。
在书中,雷蒙·威廉斯就乡村与城市的种种观念进行地批判,他集中驳斥了部分学者所坚持的“消逝的农村经济”、“快乐的英格兰”、“黄金时代”等缅怀旧日农村的错误观念,指出这些观念只是作者的想象,无论是历史事实,还是部分作家的作品,都显示出昔日的英国农村充满了苦难,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既不等同于落后和愚昧,也不是充满欢乐的故园;同理,城市虽然是在新的生产方式确立后兴盛起来的,但城市并不必然代表了进步,城市也面临太多的问题。因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城市无法拯救乡村,乡村也拯救不了城市。
有意思的是,雷蒙·威廉斯认为,城市与乡村的这种矛盾与张力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遇到的一场全面而重的危机。作为20世纪中叶英语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所表达的情绪客观而又带有深邃的思想,事实上,城市化、工业化对乡村生活来说,几乎是天敌。不过,现代化的后遗症猛看是消除乡村与城市的差距,但因经济的支撑,这种差距不是变小而是变大了。倘若因此而抵抗资本主义,是否能使现代生活得以拯救,这也还是一个疑问。
诚然,在英国文学中,乡村与城市的话题带来的是对社会问题的思索,完美的世界似乎总没有最好的方式,人类对此做出的种种探索是在寻求答案,但问题的复杂性则让这种可能性变小。乌托邦看上去很美好,在实践中却不能长期存在下去,这背后的原因是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可能。今天的中国在经济发展上的突飞猛进,让人想起资本主义在英国发展的初期的景象,它们之间既类似又有联系,从这里或许我们可以观察到乡村与城市的变迁,以及社会思潮的运动。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对新兴事物的兴趣到底是迎接,还是抵抗,也影响着社会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看乡村与城市的变迁,就更耐人寻味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