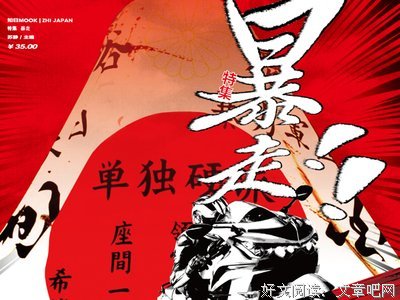《知日·暴走》是一本由苏静 等编著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1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知日·暴走》读后感(一):此处请下车推行
《幽游白书》是我最爱的漫画,没有之一。不过,和主角光环加身的幽助又或是万人迷的藏马君,我更偏爱头脑简单的桑原和真。
大概那是我第一次直观的接触到飞机头和特攻服,“健康第一”的刺绣印在桑原背后,充满喜感。
直到后来看过《湘南纯爱组》和《GTO麻辣教师》才明白所谓“暴走族”和桑原没有半毛钱关系。暴走族除了飞机头、特攻服,最重要是胯下的那匹坐骑——HONDA、铃木、川崎、雅马哈、哈雷……
《知日》从第一期奈良美智到现在,一直游走在雅致和清新风格间,《暴走》是属于血脉贲张的一本异类。热血和怀旧共存的机车史,让我们这些整天只知道爱玛、绿源电动车的小伙伴们都燃了起来。
合上杂志,有一种想要马上登陆Chiphell论坛大喝一声“我要收一辆二手杜卡迪(或者川崎Ninja)”的冲动。很可惜,这股即将四射满溢的小宇宙立刻被今天刚刚收到的一则不确定新闻当头浇灭——《北京要求制定征收拥堵费政策》,在天朝的土地上,拥挤的城市早已出卖了所有可供暴走的土壤,面对着汹涌的小绵羊电瓶车车潮,就算是日本的暴走族也要默默推车流泪吧。
翻看着异国民俗,在噤若寒蝉的字典里寻找“暴走”,其实也不是没有——
想当年,作为追风少年攒了大半年工资拼了一辆捷安特ATX690,一个月不到被偷,我的确“暴走”过!!!
《知日·暴走》读后感(二):有文化的暴走《知日 暴走》
有文化的暴走《知日 暴走》
最近看了几本《知日》,感觉书越办越漂亮,我也越来越喜欢了,可是当这一本拿到手里的时候,我才发现,这日本的暴走和我们中国说的暴走并不是一回事。我们的暴走就是长时间的走路,一般是在乡间,或者在城市内,很多人一起走,而日本的暴走原来是摩托车暴走。马上就有点泄气,对摩托车我可不了解,要知道是摩托车的话我是不会买这本书的。
不过既然买了就看看吧,可是没承想,越看越有味道。原来摩托车竟然也可以做得很有文化。在我的眼里,那些开摩托车的暴走团,充满了暴力,嚣张,野蛮,不可理喻,在心理很排斥。看了这期内容后发现,日本的摩托车暴走开始也是这样的,只是越往后就越变得有文化了起来。
书里的几个人物打动了我,他们真的太痴迷摩托车了,都痴迷出文化来了。怎么个有文化了呢?一位是木村信也,他自己手工制作摩托车,创造了自己的品牌,不过真是慢工出细活,半年才能做出一辆,不过那手艺,做的不是摩托车,是艺术品摩托车,对于摩托车我真不懂,但是最后的几张图片是他用摩托车剩下的配件改造的几个小作品,足够艺术了。
第二位是打田念(是禾字旁加个念),这是一位摩托车车手,喜欢驾驶越野摩托,开着摩托周游世界,去过非洲和蒙古。
第三位是东本昌平,是位喜欢摩托车的插画家,甚至不承认自己是插画家,只是痴迷摩托车,他开始给摩托车杂志画漫画,后来成名后出版了一份杂志,就叫《东本昌平RIDE》,每期封面是一款主打摩托车,里面的内容都由他决定,就这么一本以一个人为主的杂志竟然已经出版了二十年!赶上郑渊洁的《童话大王》了。
和往期的《知日》不同的是,这期的主打内容几乎占据了书的绝大多数,除了暴走外几乎没几页了。剩下都是关于摩托车暴走的内容,从开摩托车的人,到给摩托车拍照的人,有暴走族的着装,还有关于摩托车的漫画,和漫画杂志,有日本十条最有名的摩托车道的介绍,有各种摩托车品牌,有摩托车的广告,有摩托车暴走的装备,有相关的图书和电影,摩托车的头盔都成了一个专题,真是太全面了。
日本竟然有一百条有名的摩托车道,在介绍十佳摩托车道里面有一条道路最打动我,那就是千里滨海滨观光道,那根本就不是一条路,在那条海滩上摩托车竟然可以在沙滩上骑行,那里的沙滩特别特殊,沙子密度特别大,不但摩托车不能陷进去,就是车轮后面都不扬沙,轮子上都看不到沙子,太神奇了。在那海边上自由地开着摩托车,简直酷毙了,看得我都想成为暴走一族了。
《知日·暴走》读后感(三):充满罗曼蒂克的暴走族
以前听说暴走族都是在日本小说里面,我只是靠想象。这次我真的看到了有人会剃掉自己的眉毛,体验还蛮惊讶的,至于帅嘛,谈不上。
我读杂志喜欢看图片,因为我并没有把杂志当做一个速食的读物,而是当做一个休闲工具,知日作为一个地域文化介绍性的杂志,显然比较成功,也受到了许多文艺青年的追捧。不过这期书评,我不想过多的套用我以前下书评的风格,还是写写感受吧。
每个正常国家的青年都有自己热衷的事情,暴走族就是这样一群人。狂热的感觉不亚于摇滚,刺激程度亦然。在之前,我一直感觉摩托车相比于汽车或是死飞来说,感觉差一些,因为汽车可以靠引擎驱动感觉,死飞可以靠直面速度驱动感觉,但是后来仔细的想象,发现原来摩托车兼顾这两种快感。
想象一下,夜幕降临,一阵轰鸣的引擎声鞭挞着黑夜,然后一群机车载着一群年轻的人奔向远方,的确就像一群“幽灵”。感觉就像在草原上骑着宝马驰骋一般,总之快感来自于自由和宣泄。日本同样也是经历战争惩罚的国家,暂且不论战争的对与错,战争中总会有一些无辜的人受害。这种青年的暴走就像摇滚一样,源于宣泄。而且据说暴走族的影响在日本非常之大,工藤静香、滨崎步甚至饭岛爱都曾经是暴走族中一员。
接着想象一下,染发,机车服上面还写着亡命天涯的浪子的格言,引擎轰鸣加上机车带来的速度享受,男男女女聚集在一起,那感觉简直是酷毙了。
或许你没接触过摩托车,但是多少少年都会想到暴走这种念头,就像田村卡夫卡。现在中国不是流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么,给一个青年一个洒热血的机会,那必然是要惊天地泣鬼神,如果我从小生活在日本,会不会也成为一个暴走族!
小团体的社会认知力
文/渔歌
温和的读者大多不爱“暴走”、“相扑”、“黑道”这类的字眼。拿到这本书之前,就开始担心,我是否能够沉下心来欣赏这本关于青春热血与暴力的书,因为我实在是女汉子的外表,小女子的心啊!
然而在日本,类似于暴走族这样的边缘社会团体,总是会被社会投以关注的目光,时间久了,不仅冠之以名字,而且还投之以相应的法规制度。
虽然如今“暴走”已经成为历史,但仍有一部分人,在以另外一种形式继续着暴走的精神。比如吉永祐之,作为一名曾经的暴走族,他转换了看待暴走的眼光,投之以对青春的赞意,夺得了年少者们的亲耐。在他的相机里面,留存的影像并不是、也没有暴走的风驰电掣的机鸣声,而是面对暴走带来的内心成分、外部变化以及暴走的社会认知文化。
另一方面,也许暴走同如今中国的夜车和骑行有点关系。我十分不懂机车文化。但就我知道的朋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喜爱骑车的。他们向往一辆华丽而且高性能的自行车。许多人给自己规定骑行任务,更新骑行设备。骑行成了结交朋友、游览各地风景的好途径。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出于异常的孤独期,骑行外出或许意味着,那些独生子女可以将安静的家庭生活转换成充满“速度与激情”的飞奔。
当然,半夜出来飙车赌博的年轻人大有人在。缺钱、缺爱、缺关注应该是他们的内在动力。而外在的,飙车确实可以带来年轻力的释放,使他们更加自信。暴走是否就是这样的一些人?一群“年轻力”释放者!诚然,暴走的坏影响是有目共睹的,首先是噪音,其次是危险,最重要的是年轻人可能在暴走的同时滋生暴力倾向。这些应该早已被日本的民众所体察了。
本书中还专门列举了一些日本摩托车的生产商。日本果真是一个科技和人结合的非常紧密的国家,而且经常是由于一群人对一项新的产品产生迷恋才衍生出一个“族”,于是“暴走”就是摩托与年轻人的结合,文化便也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这或许是冷血机器的幸运吧………遇上这样一群热血青年!
《知日·暴走》读后感(五):有一种感觉叫做逆风过耳 ——《知日·暴走》,有关年轻时的幻想
有一种感觉叫做逆风过耳
——《知日·暴走》,有关年轻时的幻想
尽管我们想要拼命否认,但是90年代的香港古惑仔老片、00s初的关于新武侠的热潮甚至是后来我们已经在各个片源论坛寻找自己想要看的电影把电脑当成电视的今天,某些形象已经成为我们的价值观中的一部分——摩托车、皮衣、头盔或者干脆大喇喇的爆炸头,在轰鸣的排气管道突突声中,《麻辣教师GTO》式的帅气暴走团体模样,构成我们年轻时坏坏的向往与幻想。
很难说这一期知日对于我们这样的怪乖宅种族读者的意义,显然我们不是那种能够“说走就走的旅行”的孩纸,更何况就连前几天网购的巨大的吃货包裹也是老爸下去拿上来的;我们在书本上看到这种肆意迷茫着、寻找热血速度激情飞驰的世界的灵魂们,很大程度上与我们截然不同的。当然也可以说,正是这种巨大的不同让这样的阅读变得有吸引力——我们总是在寻找与我们不相同的事物。
于80年代狂热到今天迷茫的中国而言,“暴走”、机车、不良少年的形象依旧是某种写在纸上的故事;人们过于现实,摩托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是一种价格相对较为合理的交通工具,他们穿行在老街、小巷、甚至是田野——代言人是广东春节跨省返乡的民工之类的形象。
印象中最后一次坐那种较为帅气的摩托是在老家的海岛,10级狂风吹拂过脸颊,逆风骑行,一种割裂一般的疼痛,没戴头盔吹走了我显然已经支撑不住的头箍,强大阻力撕扯着我的头皮,风灌进我的衣服,狼狈的是我,而叼着一根烟的姑父用一种轻易而潇洒的姿态,让过耳的呼啸声变成了80迈的关于自由的歌。
后来我想,也许暴走的场景比较适合于这样的地方,背后是蓝天,一支烟,一条公路,一骑本田。制造世界上最多摩托的日本作为拥有最多百年老店的念旧的国度,注定是能够产生一种风格的,透过那些经典的动画和日剧甚至小说,他们勾勒出的别样的画面,影响了一代代的本国甚至他国的青少年。
他们是“失落的十年”,垮掉的一代的风格,让他们夹有了一种破坏的欲望;他们是守护自我信仰的一群少年,披上夸张的战袍,讲着只有他们明白的黑话,遵守属于夜晚的规矩;他们是轻柔而幼稚的,简单地说好恶,然后为逆风过耳的感觉而疾驰在危险的山道或者进行热血战斗;他们是理想主义的,不为金钱,而为证明自己的存在。
也许我们烧掉的就是这样一群人的勇气。我们会知道开发区的某个工厂里面制造着YAMAHA的琴、建设×路的某框螺钉会变成HONDA上面的一个标准配件,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报出这江边潮水的汹涌澎湃,以及逐浪的冒险。
我们少了年轻。
封面上的暴走后面两个惊叹号和血红色的封面,就像是燃烧着的少年的精魂,而打开这本mook,我们想要释放的,或许就是这样一种狂热吧。
关于一种感觉。
逆风过耳。
y 林怿
2013年9月11日22:15:23
写于御庭园
《知日·暴走》读后感(六):乱咬的青春
1
“有谁愿意自己的孩子不结婚,盼着他长大了成为僧人”几年前,爸妈天天催着我结婚,我一句他们一句,话赶话往往会赶到这个地方,词穷无法再继续下去,父母没话说的时候常这样说。那时候我还没结婚,天天上班下班,整天闷屋子里看书或者坐板凳上用耳机听音乐,像个嫁不出去的老闺女,孩子大了不结婚,父母让人问起了都觉得挂不住脸。
那段时间我生活觉得很不如意,提起结婚,张口便是“人为什么一定要结婚”,闭口便是“别人怎么样我难道就一定要怎么样吗”,和弟弟现在的口气如出一辙。一晃几年过去,角色转换,常被催婚的变成了弟弟,我结婚后,便不再是孩子了,家人不再说什么。为什么没有父母会希望自己孩子长大了成为僧人,我有时候这样琢磨,也许没有人希望否定生命延续的道理,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后却要去否定他出生这件事,仿佛父母让他来到这个世界是一件错误的,被否定被谴责埋怨的事情,“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我这样想。否定自己生活的方式,否定自己既定的生活做法,否定拒绝婚姻这事是被当成一件大事的,子女是要肩负起种族延续,生活方式、生活价值延续的道理,我们希望孩子要靠谱,希望自己的邻居安分靠谱,希望自己的周围人靠谱。
2
青春,一个很大的词,正慢慢变得苍白矫情的词,前段时间我在家睡前翻书的时候,在书中翻出了这样一个道理:“青春多么残酷,当你真正长大时,它就不见了,而它笼罩你的时候,你却因为生涩而处处表现得像个傻子”,这种一石二鸟的箴言,往往阐释一个二律背反的道理,你在或不在总有概括议论你的办法,认为青春像个傻子或者对着月亮乱咬的疯狗,都有道理。
我也不认为我以前和现在的生活符合什么,或靠近一种如何的秩序,像在暴走族纪录片《永别了!speed Tribes》,这样一种完成时的标题,找到叙述相机架设的角度,我并不因此找到能够查看自己的角度,我还没能符合“真正长大的”的过程,仍旧像个傻子。
只是这几个月来,我越读越喜欢上了知日系列。这是非虚构的,结合了采访、记录探索和科普的功效,每期一个小专题,穿插图片、文字,打开了一扇了解日本种种生活现象的窗口。这两天翻读《知日•暴走》,书中大多曾经这样方式生活的人已经进入了中年,结婚生子。可能一个人对自己孩子的期望值正对应了自己生活的价值观,想起我在父亲期望值越来越少的同时慢慢长大,像一条成反比函数关系的曲线。我想到父亲慢慢不再劝诫我怎样生活,也不再表现出任何强烈的希冀,我工作后他出钱买房,每天来装修,直到最后把钥匙交给我,我买车后给我还车钱,他似乎更希望好的东西已经出现在我的身上,虽然并不明确知道那好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前天,我回家吃晚饭时,告诉爸妈,我的一个书评被某杂志采用得了五十元稿费,这也是我看书阅读这一行为换来的第一笔钱,虽然我此时已经二十八岁。父亲并没有说什么,只是说“不管想干什么,你都上上心”。记得我读高中的时候,他那么反对我业余的阅读的不务正业,而现在体制中人站起了似乎认同我,他又觉得这事满意了。我就这样在家庭和个人之见的游走,小心地琢磨着父母对我态度的转变。
3
《知日•暴走》采访羽月时,谈到对他将来孩子有着怎样的期望,冒号的后面,他回答的是,希望孩子将来可以成为僧人吧,尽可能地希望他在精神的世界里成长。就这样,我终于看到了有人这样希望自己的孩子,没有什么语气,像说一个别人的世界和人生,压低了某种对自己青春生活的失望和悔恨。
我从书中抬头,把这个问题丢给了旁边的妻子,“要是我们的孩子长大了信基督教,你觉得怎么样” 她的回答却有点让我意外,她说“只管我们的孩子如何,再下一辈我就管不了了”,显然她以定了基督教不允许结婚,等价于了和尚。但无论如何想,我仍然觉得“希望自己孩子将来成为僧人”,是一个夹杂失望成分的句子,正如“我希望能让我自己一个人清净地坐一会”一样的语气。暴走族在度过了自己暴走的青春之后,不再希望孩子像自己一样成为暴走族,不希望下一代这样重复承受青春的惩罚。
写到此处,我想起了庄子里面的一句:“厉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视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丑陋的人夜半生孩子,赶紧拿火来照看,心里十分急,唯恐生下的孩子像自己。暴走族在自己成长后,终于站到了自己生活的对面去评价自己的青春,认为那样的生活也是丑陋的,这样对自己过去的否定构成了暴走族当下的生活。
乱咬的疯狗一样的青春正是暴走的,至少我没有看到过一只疯狗的突然掉头会有什么理由可言。愈是反对,愈是否定,生活便愈是有意义,也许有一天下午,我从午睡中醒来走进中年,坐在餐桌前,面对纸张的采访,或者有一天,我坐在地头上,抽着烟袋,像爷爷当年那样看着眼前的庄稼,过去生活的否定,不断累积成为现在。(玟涛 2013年9月14日)
《知日·暴走》读后感(七):我差点误会了这是一本关于情绪控制的书
“知日”系列现在越出越深入了,如果以前的森女、犬、日本禅,我还能凭字面上的意思去理解这本书要讲什么,但这本暴走,就不是那么容易让人理解了。
暴走一词如果你打开百度百科,你会发现,第一个解释是一种“动漫术语”,指的是“在情绪暴发之下诉诸于暴力”。而且这一解释至少是比较普遍的,当我拿到本书时,我老婆说樱木花道才是暴走族。不过,很显然,这本书,谈论的是另一类暴走——机车男。(http://baike.baidu.com/view/9783.htm#sub5037715)
根据本书的普及知识,所谓暴走族,就是机车男,他们的标志包括了特攻队服、各种团队标志和胯下的铁马,而年龄都在19岁左右的叛逆期,一旦年岁过大了,就不得不退出暴走族。这使我想起了另一个神话,哈雷和那些大男孩。
在《荒野大飚客》(wild hogs)中,几个中年男子由于中年危机,于是利用假期,重新披上皮衣,跨上哈雷,开始了回忆之路。哈雷在美国无意是一种文化象征,而这种文化并没有随着时代的过去而过去,即便你看到跨在哈雷上的已经垂垂老矣。
而在日本,暴走族不过是一群厌恶了传统教条的日本人,他们或许等到年纪大了,又做回传统的日本人,或许就直接由此进入黑帮——当然,在日本,黑帮也不过是经营的一种模式。说白了,你可以说,暴走族不过是一群开了一会小差的日本人。
而自从80年代的黄金时代过去,暴走族也越来越少。这里,我特别关注的,其实还是商业对文化的侵入。虽然暴走族只是亚文化,但是到了后期,商业逐渐入侵,人们关注的不再是反抗,而是兜风和舒适性。本书还花了不少篇幅介绍那些曾经的的卢、赤兔,可是我发现读者很容易产生暴走族最不喜欢看到的一幕,迷恋器物,比如某网友直接高呼,要在chiphell这样的悬浮论坛上嚷嚷买一辆机车。
君子不器,孔子这句话解释的版本太多。我也借此说说,一个人不是因为穿什么就是什么,而是你想成为什么,才会有什么,你不能骑个机车就说你暴走了,这点,我反而喜欢那个自制机车的大叔。
《知日·暴走》读后感(八):嚎叫的间隔年
题记:意识形态分离了我们,而梦想和痛苦使我们走到了一起。——Eugene Ionesco
《知日》书刊出了那么多期,我唯一的遗憾是没拥有森女。错过了《森女》,我只有暴走。这也是我为什么要读《暴走》,而且我确实暴走了,在《we own it》的单曲循环中我完成了视听的暴走。
《知日·暴走》,在说日本暴走!的姿态。暴走族,崇尚暴力(暴)速度(走)的群体。暴走族,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与无趣,也没有传说的那么不良与无道。他们可是有组织有精神有文化有追求的少年。暴走的装备摩托车,衣服,剃眉,发型,刺青,装饰,以及暴走团体,都是很有传统与讲究的。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暴走族的。在书里,你会看见不一样的知性暴走。
有人说,暴走只有速度与激情,燃烧掉机油一切都又哑然无声,恢复到苍白的茫然。这样的青春期过得相当昏暗啊!也许这比不上那些大人啊,一把年纪了还在厕所偷摸的玩飞车或者在床上苦憋的闪烁吧。当我们青春的不能再青春,当我们热血的不能再热血,我们有做自己的勇气和自由。因为人的一生,青春就一次。那还不赶紧暴走。他们骑的不仅仅是机车,而是燃烧自己的灵魂。所以才要不停的加速骑下去,直到青春的尽头。
十几岁孩子的心灵都很脆弱,但是大人不明白。少年们把机车当朋友,而大人们把朋友当玩具。大人说,世界上是有规则这种东西存在的!那么暴走的少年们,会说规则就是为了让人打破而存在。大人和暴走族都生活在一个世界,但是生存在不同的平行空间。
暴走的少年们献出一切的东西,只为机车而活。他们只忠于自己,这就是他选择的生活。不是报社党,而是站在世界的中心大声说自己罢了。一个小火点便能灼烧他们的灵魂,骑着机车的他们和一起飙车的兄弟,也将瞬间点燃黑夜。只有死亡和时间才能停止飞速的机车,既然没有什么好怕的了,只剩下咆哮着去嚎叫吧。在夜色的轰鸣声中,他们体内黑色野兽在嚎叫。你不可能听得到,悠闲的活着没有獠牙的现在的你,不可能了解他们的心情的。
这个嚎叫的瞬间,只属于暴走的他们。既然有可能瞬间毁了自己的人生,所以才更加把握人生中不能错过的激情时刻了。这是一场速度的游戏,如风般的穿过万物,霎时间拥有着许多的感官。光想想,就让我血脉喷张。所以有时候,他们宁愿摔的粉身碎骨,也绝不放慢速度。
他们在暴走中自由了,但他们还没离开。20岁的间隔年,暴走族卸下机车,重新回归社会,开始不动声色的生活下去。也许他们曾经弱小,通过速度的暴力洗礼,现在长大成熟了。
暴走族曾经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存活着,但是他们的时代不会终结。这个时代也许不需要暴走族,但暴走的精神永远不会丢弃。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即使有一天“禁摩”或者“无摩”的时代到来,但灵魂的机车也绝不能丢弃。而且,暴走的生活想要长久,靠的不是长度,也不是速度,而是能再战几回合。
我很喜欢这种暴走精神。我更愿意把车不离身的暴走族称为机车党。如果根据能量守恒定律,男人没有机车过,那么可是会变得很机车的哦。暴走,不应以速度约束,而应以灵魂来约束。“飙车族算什么!我们可是早已习惯在人生这条路上狂飙了呢!”
《知日·暴走》读后感(九):日本青年文化:暴走族
暴走族一词最初是从《龙樱》这部片子里认识的,那时面对责难,阿部宽大叔一脸正气地申明自己是暴走族,不是XX族(两个什么区别,一个是机车迷,一个是黑社会?)。难怪,一个几乎是“坏孩子”印象的暴走族,经过努力居然通过入了日本司法考试,所以,由他辅导的差生孩子们也能考入东大,更震憾,更青春、热血、励志。真是很经典的片子,推荐。
这一辑暴走族,让我从字面上的暴走族更深入了解了日本的机车文化,真是很有个性的一群人。暴走族少年往往被诟病为学业失败者,不良少年或者未来的黑帮成员。始于20世纪50年代,随着日本机车工业的不断崛起而不断发展。当时被媒体定义为:崇尚暴力(暴)、速度(走)的一群人。早期的“霹雳族”少年群体,多是来自底层贫困家庭,怀着各种愤懑和不满聚集成帮派,四处游荡滋事。特点:骑着改装过消音器的摩托车,身着各种夸张的特攻服,挥着各咱旗帜,成群结队呼啸而过,嚣张跋扈。
在摄影师吉永佑之的暴走亲历中,记录了这些年少轻狂,青春燥动的少年们。他采用棚拍手法,记录下静止状态中的摩托车与人,摩托车,人物三者的关系。这些照片也让人看到叛逆形象外,暴走族们对机车的珍视及暴走族成员不同的精神状态。我其实没有阿部宽那种要分得很清楚的暴走族的概念,从文中照片来看,暴走族可以算是游手好闲的不良少年,还未进黑道的前期吧。文中说:“暴走族和黑社会不一样。黑社会是一个行业,是生意,而暴走族是正值青春的年轻人的纯粹的表达。”可认为是正解。如果你是机车爱好者,还可以看看日本机车爱好者定制改装的摩托车,以及各种摩托车大赛情况、机车漫画以及摩托车旅行者可骑行的传说中的“百名道”。
文中“武士之魂,骑士之心”一篇中分享了许多漂亮帅气的机车照片,由这些机车也引发了制造业本田、雅马哈、铃木、川崎的梦想。这些机车的宣传海报,有许多罕见的上个世纪的海报。这些海报资料非常不错,赞!
《知日·暴走》读后感(十):暴走族边缘的热点
知日-智,介绍日报文化的杂志,书的印刷质量很赞,这期红白黑的总色调让人有热血沸腾的感觉。这是我了解知日的第二本杂志,上一本是断舍离,那个主题还是比较贴近生活。而这期介绍的是相关摩托车的系列特辑。因为最初不了解暴走族,开始的第一反应让我最初认为是介绍一种暴走户外运动。
而实际上开篇就是日本特有的次文化、亚文化暴走族专访,其实这也是一种日本70年代文化的追忆,很配那冲击力又略带沧桑感的封面,只是与现实的感觉有所差异,改装的摩托车,神功特工队的特攻服,反叛、另类,非合法的一种形象在书中展现的是一段日本尘封的历史感。
暴走族首领、拍摄暴走族的摄影师、导演系列采访以及摩托车相关的一系列深层文化都有所涉猎,信息量非常大,但因为国内的禁摩让这些对我都很有距离感。
暴走族曾经也是日本的热点话题,但总体看还是比较边缘化的一部分,在日本也是少年青春叛逆以及犯罪等等的标志。在这本杂志介绍中尽量以最客观的形式描述,但是依然是大众文化中的小众。
杂志的另外一半介绍的是暴走族的相关电影、漫画,摩托车品牌、广告、杂志以及在日报举报的摩托车赛事的介绍。人文部分还有机车改装高手以及赛车手的专访。日本工业文化和漫画产业的繁荣以及璀璨。
最关注的是《日本十名道 暴走!》这篇(这篇跟我预想还有点挨边吧),推荐了百名道中10条尤为受欢迎的路线,分布于日本各地,同时也各具特色和看点的骑行。
最近我这里在举办旅游博览会,会场上也有哈雷摩托车的展示,依然炫酷闪亮,不菲的价格也让人晕眩(38万一辆),但他们似乎只成为一种符号的姿态默默的摆在角落中。
遥想当年也曾经骑过摩托在轰轰嗡鸣中飞速游走,但现在这也只变成一种回忆。暴走族在日本已逐步衰退,不知道摩托车在中国的发展如何,也许会逐步变成发烧友和体育赛事的专供产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