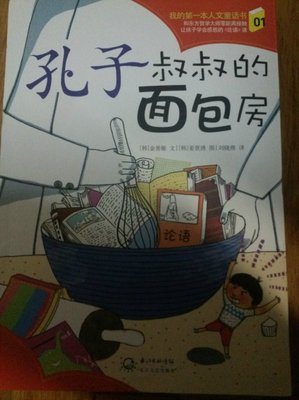
《面包屑山》是一本由[美国] 伊丽娜·戈罗霍娃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页数:31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面包屑山》读后感(一):当年扔鸡蛋的少年,今天在干嘛
几年之前,砍柴师兄回校做小范围交流。有人问他,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怎么看?乐观一些还是悲观一些?师兄回答问题的时候说了这句话,“那些当年朝使馆扔鸡蛋的少年,今天在做什么?”他指的是1999年,我驻南联盟的使馆被美国人的炸弹袭击了,政府大力炒作,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不少爱国青年走上街头,焚烧美国国旗,向美国使领馆投掷鸡蛋。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些青年回头再看当年的行为,或许会觉得幼稚可笑。认为自己当年被忽悠了,成了被利用的棋子。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对前途那么担忧,因为人心总是自然觉醒,哪怕曾经因为信息的缺失等原因被蒙蔽一时,但人对自由的向往不会变,总会走向好的一面。
人心不死。即便是在管制最为严厉,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总是能自己想出过下去的办法,甚至为将来的改变做好准备。比如,城里人可以到乡村去改善生活,去野外采蘑菇作为辅食。比如学生可以立志学好英语,哪怕不知何时有机会去英国看大本钟。在家里餐桌上食物最为紧张的时代,作者祖母将面包撕碎成小块儿,堆成山状,这样的面包看起来也算丰厚,每个人拿一小点慢慢咀嚼,挨过最难熬的时光。
或许这就是选定面包屑山作为这本自传体小说题目的原因。生活艰难,但人总有办法渡过。此外,人们总是想挑战现有制度的荒谬,即便环境险恶,人人不说,但大家心知肚明。小说里的一个细节是,当演员的二姐,天天咒骂戏剧审查部门的无知和愚笨,即便眼下的她无可奈何,但如果哪天真的有力量对此进行改变,这些长期累积的不满就一定可以化为劈开那迂腐桎梏的利斧。
旧的体制在1989年瞬间解体,曾经封闭的、意识形态化的帝国,逐渐走向开放。这或是曾经大部分人想要的结果,只是没有料到会来的这样快——正是人心所向。因为自由、开放、个体权力等等价值是普世性的,和国家制度没有关系。任何对诸如此类价值的限制都是反人性的,得不到人民支持。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始终推行限制政策的政府和政党最终将被人民所抛弃。
面包屑山,让人看到希望。诚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M库切所言,“作者展现了那个年代中所有的艰难,也发现了其中被压制与藏匿的诗意。” 这样的时代,即便寒冷,却也有点滴烛火,给人温暖。而人人心里都燃起这点火,就不至于在暗夜里因找不到方向而迷失、绝望。
《面包屑山》读后感(二):全民铸造乌托邦幻象的执迷与诡谲
肩负一家老小温饱的母亲难为无米之炊,只得把面包掰碎了堆成“盘中山”,用来哄骗饿得嗷嗷直叫的孩子,换取一时一刻的太平和幸福……这幕情形虽发生在苏联早期,有着集体饥饿记忆的一代中国人想必也会心有戚戚:比起前胸贴后背的肚子,更值得回味的可能是对面包屑堆成的空中楼阁,保持一种你知我知、心照不宣却从不说破的心态,或说默契也罢。这种诡异的默契感贯穿回忆录《面包屑山》始终,作者伊丽娜•戈罗霍娃拨开后斯大林时代的重重迷雾,以一种尖刻、嘲讽的文字,记录下一个全民铸造乌托邦谎言的国度的世态人心。
伊丽娜•戈罗霍娃出生和成长于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彼时苏联社会“解冻”和“上冻”暗战正酣。苏共二十大就斯大林问题所作的报告属“秘密”,其影响却不可能不渗透到社会层面。不过,也正因其“秘密”,对单一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反思就不可能做到公开透彻,这些东西仍然以国家名义,牢牢钳制着苏联公民的思想和行动。这种二元化的价值取向,势必营造出一个说一套做一套的社会。伊丽娜就读的小学,就陷入了这样的混乱:老师以少先队英雄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揭发地主父亲、“大义灭亲”的先进事迹,弘扬共产主义道德观,伊丽娜和小伙伴们是何反应呢?
“我不能断定,告自己父亲的密,致使他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去服劳役,算不算是一种英勇的行为,即使这种行为使一些人避免了挨饿。不过,对老师赞扬帕夫利克•莫罗佐夫警觉勇敢的话,我并没有去反驳,其他的同学也没有。我们大家都知道,无需争论。对写进历史课本的东西,无需争辩。你假装认同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是个真正的英雄,就应该得到一枚勋章,就像我们在幼儿园时假装咀嚼面包和变了味的黄油一样。”
也就是说,“对写进历史课本的东西”,或者一切以官方口径宣传的东西,大家暗自谐谑、调侃、嘲弄,就是不公开说破之。在《面包屑山》中,伊丽娜向我们披露了从家庭到社会各个层面的“假装”:有四十年党龄的父亲斥责《真理报》既无信息也无真理,却仍“假装”认真贯彻学习其精神(随书附照一张);母亲衷心希望弟弟们不要在战争中当炮灰,仍“假装”祝愿他们英勇杀敌为国捐躯;伊丽娜在外国客人面前“假装”自己熟稔“特效”、“星球大战”和“派克大衣”;她执教的学生家长“假装”雇佣家教的“教育黑市”不存在;高干子弟“假装”自己的好成绩好工作与父母无关,后者则谦虚地表示自己是人民群众的一员……
“假装”的心理机制来源于高层规划的乌托邦理想与现实发生冲撞的不可协调性,这种理想通常打着看似崇高实则狭隘的旗号强加于人。它不承认人之为人的个性、本质乃至弱点,而齐以一种含糊笼统的集体价值观。因之,苏联的外事部门可以信誓旦旦地宣称苏联消灭了失业,却无视商店门口常年大排长龙,而排队的人们根本不知道店里在卖什么;他们告诉你性爱和妓女在苏联业已绝迹,因为它们是腐朽堕落的西方资本主义才能产生的东西。彼时苏联文艺领域稍有松动,根据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作品改编的电影《榆树下的欲望》易名《榆树下的恋情》搬上苏联银幕,伊丽娜精确地捕捉到其中蕴藏的猫腻:“难道爱情和欲望有相同的含义吗?或者说——一个更大的可能性——在翻译中间的这一改变是蓄意而为的,是要把肉体的、性欲的东西转变成灵魂的和崇高的?”
审查、删除、偷换概念、以及擅作阐释的牵强附会,与上文说到的人们听之任之、见惯不怪的“假装”,构成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对权力的恐惧。《面包屑山》不同反响的一个地方,就在于作者揭橥国家编织的谎言并没有蒙蔽住老百姓,可能国家本身也并不意在把谎言编织得滴水不漏,而是老百姓如何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通过“假装”悉心维护并让自己生活在谎言之中,由此,权力最大化地使人们心甘情愿地维系权力本身。另一方面,此书也说明“谎言灌输千遍就会成为真理”这一政治学上的教条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倒是证成了“真理灌输千遍也会变成谎言”。官方宣传的诸多历史观、价值观、道德观,由于片面化的灌输、重复,以至成了抽象而不具实质意义的陈词滥调,无论真实与否,老百姓一律打上一个问号。伊丽娜自己就体会到,官方注了意识形态水分的套话、大话,是如何使前者意欲表达的真相、真理失色和变味的:她是从父亲的假牙(健康的牙齿因营养不良而全部烂掉)而不是书本上的知识,才确认“大饥荒”并非子虚乌有而是确有其事的。
后来用脚投票移民美国的伊丽娜见识到美国的另一面,坐标自然有所调整。不过她对美国自由、平等,特别是“说真话”的想象,则一点也不差,正如她实话实说地告诉大家,她嫁给美国人就是为了移民。本书写得无不激烈和愤怒,不过正因作者不作保留的诚实而尤显可信,其中甚至也包括作者对母亲不依不饶的谴责。伊丽娜实在无法想象如母亲这样一个年轻时敢给斯大林写信要求筹建地区产科医院的女性,到头来为何会变成既有“秩序”最忠实、最顽固的捍卫者。其实我们稍作联系就可以明白,母亲在战争中失去两任丈夫,被别人监视也被迫监视别人,其担负一身一家的心事何其沉重!无疑,在母亲身上,伊丽娜看到了祖国的影子,那制造了无数“面包屑山”、并“假装”生活太平幸福的存在,她对之既恨又爱。
《面包屑山》读后感(三):“茧”
看完伊丽娜•戈罗霍娃《面包屑山》(23.3万字),一部很有可读性、让人满意的作品。
作为个人自传,戈罗霍娃细致而微地讲述了自己身上从小到大发生的故事,直至获得机会嫁给一个美国人,从而离开这个看不到希望的“黑心的国家”、“丢脸的国家”。读着这本书,心里不由地涌上了一种对于世界的观感:“茧”——茧,要么是一种桎梏,要么是一个迷梦,不假以时日或者不发生戏剧性乃至颠覆性的变化,桎梏就无法挣脱,迷梦也无法醒来。本书何尝不是写了一个个的“茧”呢!苏联,就是一个巨大的茧,它桎梏俄罗斯人民近70年,如果不是最终解体,这个大茧的桎梏将继续存在,那是比恶梦更加可怕的存在;另一方面,童年也像一个“茧”,生活在里面的人,都是活在一个大梦里,是怎么喊怎么摇也不会醒的,“茧”里面的生活和行为逻辑与成人世界完全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只有当我们走出童年,回头望去,才能确切地知道童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曾经生活在“苏联茧”和“童年茧”之中的小女孩,写出的是个人的成长史和心路历程,也是苏联存在期间一些老百姓生活状况的可靠还原,一切都十分清晰。
本书故事情节真实生动,语言细腻流畅,情感暗流涌动,还有着打动人心的睿智和坦然态度。作者笔下的一切都充满了画面感、环境感。当她描写童年生活时,口气就是一个有着认真、执着、好奇劲头的小女孩,还带着一点小小的叛逆、一些些敏感和紧张感;而一旦长大,内心的各种看法、主见,就以柔韧的面貌出现了,而且蓬勃生长。人们会看到,生活在那样的国家、那样的年代,年轻人的内心有多么纠结;而作者在苏联解体前脱离苏联的过程,读来在平静之中又给人脱离险境的惊心动魄的感觉。以上这一切,都由丰富的细节来支撑。这再次证明,细节决定作品的成败,令人难忘、有说服力的作品(小说、纪实作品等),必须由无数精微的细节来支撑,就如同生命要由细胞来支撑其存在一样。这样的写作,无端地就很吸引人,正如库切所说:“引人入胜的阅读”。在这些生动细节的推动下,一切都在我们的注视之中展开,一切都以现在进行时发展着,非常鲜活。那些童年往事,挑动着读者的脑细胞,激活了读者自己的童年记忆;而那些社会主义国家里特有的现象,更让我们觉得似曾相识。阅读这本书,有种很真切的感觉:好像跟作者一起亲历过这种生活。
生长在冷战时期的苏联,虽然黑暗的斯大林时代已经过去,最严酷的政治环境已在解冻,但社会生活仍然是肃杀的、没有生机的,而且势必仍会遇到书中写到的那些折磨人的、让人倒尽胃口的现象:物资奇缺、谨言慎行、口是心非、种种禁忌、道德洁癖、对自己国家和制度的过度粉饰、对资本主义的肆意丑化和诋毁、对各种事情的蛮横甚至扭曲人性的做法、官僚作派、权力(特权)至上、不正之风、甚至包括态度恶劣的公务员和服务员……这些,对中国人来说太熟悉了。我们不由地发现,中国曾亦步亦趋地跟在苏联后面走了太久。原来,苏联对于中国人生活的影响是如此之深!比“苏联茧”更大的那个“茧”,应该叫做“意识形态茧”。所有那些不良现象,似乎都是从这个巨大的“意识形态茧”里衍生出来的(不得不这样说)。有意思的是,身处这个“意识形态茧”中的人,一旦到了上高中的年龄,就难以继续受到蒙蔽而“有种种的怀疑和愤世嫉俗”。当内心的信仰完全瓦解后,“假装”的老把戏仍会继续表演下去,对此作者总结得很经典:“他们对我们说谎,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也清楚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但是他们就这样一直说谎说下去,我们就这样一直假装相信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所谓“信仰”,总是、也仅仅是被用来作为正统身份的界定和实用主义(个人前途)的敲门砖。司空见惯的人格分裂的常态无疑加速了整个社会虚伪化的进程。然而,大家都还在不由自主地精心维护着这个巨大的“茧”。可悲又无奈。
在这种国情下,只要有机会,一些女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嫁给外国人,投奔新生。作者的一些同学,嫁给芬兰人也好,嫁给德国人也好,反正只要离开苏联就好;在作者嫁给美国人之后,她的姐姐也嫁到了美国,母亲也选择到美国定居,一家人都走出了“苏联茧”,冲破了“意识形态茧”,在美国团聚,过上了内心安宁、物质有保障的幸福生活。通过这些亲身经历,作者仿佛在告诉人们:一个国家,如果不重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甚至为维护统治而剥夺、侵害人民权利、压制个人幸福,那么,人民就会从内心背弃这个国家。这还让人想到:后来苏联的解体,也可以看作是人民不需要它了,作为一个国家,它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作者脱离苏联有其偶然性,而苏联的解体则有其必然性。人心向背,就像天理那么自然。
回过头来再说一下书名《面包屑山》。书名抽取了苏联饥荒时期一个极小的意象:由一片面包和一块方糖碾碎堆成的山形碎屑——外婆以此哄骗饥饿的孩子,让孩子以为食物变多了,变成了一顿盛宴。读完全书,作者用“面包屑山”来作书名提领故事的目的或可作如下解读,犹如一个忠告:如果最基本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饥渴与不满就将持续存在,哄骗则不可能永远继续,“面包屑山”的把戏也就难以一直玩下去,长此以往,终有一天,人们可能会见到戏剧性或者颠覆性局面的出现。
《面包屑山》读后感(四):深信不疑的谎言
提到小时候深信不疑的几件事情,恐怕除了在屋子里打伞长不高以外,也就是红旗是用烈士的鲜血染红的,而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红领巾的供应渠道是独家的,必须到大队辅导员那边买。有一次,我弄丢了红领巾,又不想被批评,爸爸从柜子里翻了一块红布头,给我做了一条。倒霉的是,这块红布红得不正,有点偏紫,爸爸说没关系。事实证明,不是没有关系。第二天,我们班的大队委就很敏锐地发现,要么是染红我红领巾的烈士可能患有血液病,要么我的红领巾是冒牌货。显然,她对烈士健康的信心要高于对我人品的评价,便向老师报告了我这种可耻的行为。事情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不记得了,只记得那条红领巾我再也没有戴过。
这件事情给我留下的痕迹是对权威的敬畏与自我羞愧,显然,错在我而非别人,更非道理,错在我。
当我把这件事情告诉《面包屑山》的作者伊丽娜本人的时候,她说,她很震惊,她希望我把这件事情写下来。我说算了,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况且,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写作的……况且,她在《面包屑山》里替我们写了很多。比如,不谙世事时候,我也曾经给男孩子递过写了真心祝福的贺卡,虽然没有人检举我,但是没有人会觉得这是一份值得珍惜的情感,我觉得很失落;比如,我的信件没有伊丽娜的日记本藏得好,因而经常被父母翻阅,受到斥责,告诉我,父母翻翻女儿的信件是很正常和正确的;比如,我幼儿园的老师曾经像珀尔亚阿姨那样打过包票,我将来一事无成……
我和伊丽娜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她的母亲会从一个敢于给斯大林写信申请医疗经费,违抗院长命令,用部队医院的医疗资源救活了被炸伤的男孩的鲜活的姑娘,变成了一个难见笑容,深信生活的精髓在于“秩序”的女人。伊丽娜说,她觉得她母亲显然是个缺乏情感,内心用福尔马林擦拭的女人。我说,或许你错了,或许她内心曾经如你这般地丰肥,她的情感也如你的一样激越。她曾经结过三次婚,对于前两个她从战场上捧回来的丈夫,她都爱得那么真,像所有感性的女孩一样,爱得愿意当即托付,虽然她得到的都是辜负。而最终接受她托付的却并非她之所爱,可事实证明,真正有用的是顺从,是接受,是适应,于是她安心地躺了下去,不再挣扎。就如我们俩生活的环境一样,换取安心安全的托付未必是你心之所信,但是却可以慵懒地放弃努力,每天回家和家人团聚,没有人会半夜敲门。况且,明察与抗争的后果,我们已经见过足够的例子。伊丽娜说,或许你是对的,很多事情不能怪母亲。
我喜欢伊丽娜,不单是因为我们都有天蝎座的近乎刻薄的洞察,对于很多小时候的事情无法憨憨地释怀,非要讲出来讨个说法,还在于,她在丑陋的一大坨中挑出的宝石,让我泪流满面。我始终记得在《面包屑山》的第二章中有这么一件事情:初春的时候,河流的冰面变薄了,浮冰稍有撞击便会引爆封冻在河里的炸弹,把鱼儿炸飞。孩子们会涉水捞鱼,从而可能引爆更多炸弹。4月的一天,一个女人把一个失去知觉的男孩抱来伊丽娜母亲所在的部队医院,同一颗炸弹刚刚炸死了这个女人的孩子母亲违法规定,毫不犹豫地给孩子做了手术,我想,那个女人把儿子的尸体留在了冰冷的河岸上抱起儿子的朋友时,应该也没有犹豫。伊丽娜明白这种在那个时代,没有人会关注的英勇,是多么的珍贵,她明白,谁才是英雄。
我们很多人的成长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倒不是我们真的受过什么苦,而是在我们没有思辨能力的时候,认真地学习了一整套的价值观,等长大心智成熟以后,发现这一套价值观是错的,然后重新开始校准,调整,甚至要推倒重来,这便是痛苦所在。当然,大多数人并不在意,或许一生都不会发现其中的奥秘,也便不会有什么痛苦,但是有的人却在其他人选择用双手蒙住眼睛塞住耳朵的时候,挥舞双臂驱散雾瘴,奋力地攀爬到云翳的顶端,一览世界的风景,比所有虚构的仙境都要美丽。这是一条辛苦的道路,当然,也更体面。
我告诉伊丽娜,我想在封面上画一个女孩,梳着两根辫子,所有的一切都是黑白的,没有色彩,只有她脖子上的红领巾是红色的,我希望是血红血红的。伊丽娜说,好,我觉得很好。
《面包屑山》读后感(五):假装的生活
我不知这是否算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它更像是作者伊丽娜•戈罗霍娃的回忆录,在中间插了几页关于她生活的真实照片可以佐证这点。这使得我们对作品的真实性不容怀疑,更重要的是叙事的语调不像当代英美文学凸显在场感,而是充满了一种尖刻、嘲讽的回顾感,例如她在文中写到“1920年,粮食配给又再度紧张起来,饥饿的阴霾笼罩着整个国家,这以后六十年的恐怖和不祥已依稀闪现在地平线上”。小说里时常出现时间网络交错状,作者站在现在时的位置,回看1920母亲生活的年代,但同时又带入接下来六十年的阴霾。
作者的笔触不像一部忠实记录的摄像机,而像是一部显微镜,它放大了这个国家的谎言,和旨在将苏联建成乌托邦国度下的真实:父子之间的出卖,异性间的检举,对入侵阿富汗的合理化表达,对英美的丑化。这是一个少女在成长中隐约感受到的,在意识形态摇摆中,撕裂的缝隙里露出的真实一角。她从出生就开始接受谎言的灌输,在幼儿园时身边充斥着诸如“把你的汤喝掉,否则,你会死掉的”、“如果不把你的奶喝完,你就会生病”,伊丽娜“几乎就相信她说的是真的了”,但随着她的成长,随着不断渗透进来的文学作品、戏剧、来访的外国人和自身敏锐的洞察力,她逐步拨开迷雾,看清这个国家的真相。直到最后,她选择离开这里。
“面包屑山”这个意象表面是外祖母对孩子的关爱,而更深的却是一个国家面对饥饿的恐慌感以及掩饰真相的谎言。在食品供给匮乏的年代,外祖母把面包和方糖碾成碎屑,形成两座小山,无知的孩子被这个谎言唬住,用一个小时一粒一粒把它们放进嘴里,而年长的孩子,通过交换眼神,了解真相。全书选择这个意象作为题目,将家庭内部环境与国家外部灾难并置,两者却形成了一个合谋的关系,造成了一种反讽的效果。
童年时,伊丽娜就懂得在乌托邦世界里生活的唯一法则就是“学会假装”,她把它称为一种“把戏”,“父母工作时候玩,姐姐在学校玩,我们所有人都装着在做着什么事情,而看着我们的人也假装他们在深切地关注着我们,好像不知道我们是在做戏。”才几岁的孩子就开始熟练地运用着生活的法则,偶尔也用“假装”的策略给童年生活增添一点乐趣。可悲的是当面对和自己幸福有关的婚姻选择时,主人公依然在假装,“我知道如何能装得很像,我愿意装出我们是一对恩爱夫妻的样子。”,“假装”是小时候就被外祖母灌输了“谁也触摸不到你的内心”的教诲,是一辈子需要练习的生存术。如果说成年以后发现自己童年时所受的教育,无法形成对真实世界有效认知,一切价值观需要重新建立是一场悲剧,那《面包屑山》的悲剧在于主人公从小就隐约感觉到这一切的不对劲,随着生活的艰难不断验证着乌托邦世界的虚幻,她缺乏幸福的童年,却也收获了冲破屏障的勇气。
同样是描写集权统治下的乌托邦世界的《1984》,是突然发现真相的人不断挣脱的故事,充满着撞击的力量。而《面包屑山》则是不断被驯化的故事;是这个国家的人安于现状,心甘情愿接受洗脑的故事,就好像主人公的玩伴妮娜,最终选择安于现状生儿育女;是不停撕破真相的主人公,和生存在谎言之下的身边人愈发格格不入的故事。它有多种读解方式,于是读起来有一种错位的感觉,尤其是在全书的中段,伊丽娜不断和体制周旋着,她嘲讽却不得不遵守。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的她,却只能就读大学夜读部,而全日制的名额让给了工人阶级子女,对这一切伊丽娜并没有明确的反抗,只是暗自策划着要离开这里,她把可能爆发的力量自行消解掉。《1984》的主人公发现真相后,开始察觉到一切都不对劲,而《面包屑山》的主人公,一点点在撕开谎言的口子,向真相张望。随着父亲假牙代表的饥荒真相,英国少年带来的关于另一国度的真相,《榆树下的恋情》关于欲望的真相,还有那些被奉为民族英雄的作家们的生活真相被揭露,伊丽娜开始学会对谎言免疫,她形容随处可见的《真理报》是最不可能找到真相的地方,久而久之,对那些歪曲真相的文章有了免疫力。
在全书里,伊丽娜的成长和母亲的选择,成了两条相反的曲线,曾经勇敢写信给斯大林要求增加产房的母亲,曾经和部队上司顶撞执意要救平民少年的母亲,曾经经历了三次婚姻却依然坚强的母亲,是伊丽娜眼里被谎言驯服的最好注解。母亲变成了一个不苟言笑的女人,坚决服从社会的秩序,用福尔马林刺鼻的气味熏陶着女儿进入严谨的科学世界。伊丽娜想离开国家的心跟想离开母亲的心一样坚定,因为在她看来“这个国家让我觉得那么像我的母亲。他们两个,我的母亲和我的祖国,几乎是同样的年龄。他们都喜欢秩序,专横,总是在提防着什么;他们都平淡乏味,,无论是我母亲还是我的祖国都不懂得人生命中重要的东西:戏剧的魔法、英语语言的力量、爱情。他们就像是7月份上下班高峰期的公共汽车,你在里面不能呼吸,不能移动,不能挤到车门那里下车。”关于国家和母亲的类比,也显示出伊丽娜缺乏一位真正作家对人性深处的体察,自传体回忆录尽管真实还原了细节,却由于先入为主的偏见,而使得人物脸谱化。母亲年轻时的勇敢和对爱情的执着,正表明了她对生活的掌控力,在面对大女儿学习表演的事情上,她最后也开明地同意了,作为一个失去丈夫的知识女性,她更需要在谎言的社会里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冷酷和顺从规则是她套上的面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