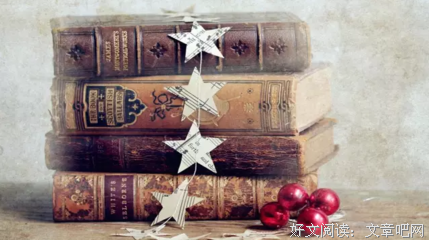《别想摆脱书》是一本由(法)卡里埃尔 / (意)艾柯 / (法) 让–菲利浦·德·托纳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9.80元,页数:41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以轮子来譬喻书,是意大利符号学家安贝托•艾柯的说法。他的意思是,书如同轮子般,一经造出,已然非常完善,“书多方证明了自身,我们看不出还有什么比书更适于实现书的用途。也许书的组成部分将有所演变,也许书不再是纸质的书。但书终将是书。”这是《别想摆脱书:艾柯、卡里埃尔对话录》开篇即言明的,为了回答这次会谈的起因:数字阅读是否会导致书的消失?艾柯和卡里埃尔(法国电影编剧、评论家,《大鼻子情圣》《布拉格之恋》《屋顶上的轻骑兵》《白昼美人》等,都是其名下作品)以极短的篇幅即解决掉这个问题,这篇对话录获得如此的前提,方得以充分展开。而两位学者的会谈,可谓是跑题复跑题,神聊书之上下四方、纵横古今,或许正是以这种方式,恰可切中“别想摆脱书”的主题。
作为纸质书的衷心热爱者,艾柯和卡里埃尔没有放过对新生媒介弊端的指摘。艾柯说第一次看光盘播映时惊诧万分,“所有人都为这次革新而倾倒不已,它似乎解决了我们这些图像和档案专业人员长期以来遇到的所有难题”,但,制造奇迹产品的美国工厂若干年后就关闭了。卡里埃尔也说,有位职业是电影编剧的朋友,在地下室放了十八台电脑,就为了可以看从前的影片。新媒介推出,都声称自己是永久性载体,可其昙花一现的程度让我们看得眼花缭乱。前些天我还看到一则微博,讲有位仁兄多年前自豪地讲,留给儿子最有价值的财富就是上万张影碟,如今再看,大家只能苦笑了,难道也要在地下室里给未成年的孩子保存老式播放器么?技术的日新月异,未必会增加载体的可靠性,且“没有电,一切都会消失,无可弥补”。从多层意义上考量,纸质书作为书存在的一种形式,未必没有独特的优势在,即使数量会减少,但完全被取代也要有具足够说服力的载体出现才可能。
艾柯和卡里埃尔的神聊中,出乎意料出现了“愚蠢颂”,与他们智者的身份构成吊诡的反差。理由何在?“为什么只关注智慧、杰作和精神丰碑的历史?在我们看来,福楼拜所珍视的人类的愚蠢要普遍得多,这是显而易见的。愚蠢更丰富多产,更具启发性,在某种意义上,更公正。”两位学人在这个话题上达成了共识,卡里埃尔编写过《愚蠢辞典》,艾柯在《丑的历史》等多种著作中频繁涉及。缘何如此,因为他们深刻认知着人类既具有万物之灵长的优胜之处,同时亦有犯下愚行的劣根性,两者的结合,方构成完整的一体,“当我们决定谈论愚蠢,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在向人类这一半天才、半愚昧的造物致敬”。
如何谈论没有读过的书,这是许多读书人都会犯难的事情。还好,艾柯和卡里埃尔为我们预备了多种答案。艾柯会说,“您知道,我不读书,我写书”,另有,“不。这些只不过是我下周要读的书。我读的书都在大学里”。当然,这些或具挑衅性,或为笑谈,但其隐藏着一个事实,几乎没有人能够读完自己所拥有的所有的书。艾柯就问,有谁真的读了《芬尼根的守灵》,“是说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我想,只有译这本书的译者能够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吧。有一个有趣的比喻,“(藏书)类似于酒窖,没必要把里面的葡萄酒全喝了”,即意味着,我们的藏书未必是读过的书,而是一些我们会读或可能读的书(艾柯语)。如此的阐释,大约可以解除许多读书人对家中日益增多却无暇读完的书的负疚感吧。
同样,读书人都会或早或晚地遭遇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很棘手,却必须面对:死后藏书怎么办?卡里埃尔说,自己可以想象,太太和女儿将卖掉家里全部或部分的藏书,用来付清遗产税等等。而艾柯也认为孩子们似乎对自己的藏书不感兴趣,“我儿子很高兴我收藏有乔伊斯初版的《尤利西斯》,我女儿常常翻看16世纪马蒂奥利的植物图册。不过仅此而已”。藏书是一种孤独而隐秘的激情,只有自己能够承受,乏人可以分享,即使最亲近的亲人。于是,书籍的流散就难以避免了,卡里埃尔想得很开,他认为旧书重返市场,彼此分散,到别的地方,给别的人带来喜悦,激发别的收藏激情;而艾柯宁愿自己的藏书捐赠给公立图书馆,或通过拍卖行整体出售,以保持完整性。揆诸我们国内,鲁迅的藏书大约是结局最好的了,有专职博物馆完整保存,还可供研究用,并不断有成果出版,是为书籍寿命的自然延长;而许多人的藏书未必有如此优厚的待遇,或者完全流失,或者进入图书馆被打散,在书的海洋里失去踪迹,即使如巴金这般名人,捐赠的图书不也被人发现流落到旧书市场,几乎是种悲哀了。
艾柯与卡里埃尔谈论着关于书的自家心事,且旁征博引的几乎均为西方纵贯千年的各类典籍,但我们并未感到事不关己的隔膜,因为书有着语言文字的相异,爱书的心思却消泯了地域的界限。他们诉说忧虑,坚定自信,谈古论今,大跑野马,处处都敲打着我们的敏感之处,印证与解答着某些存在已久的问题。不论如何,我们信服着那句关于书与轮子的譬喻,或许时代会改变,或许表现形态亦不免发生变化,但其本质的无法超越,已然存在,且将恒久地持续下去。
《别想摆脱书》读后感(二):接下来,继续疯一样的买书吧。
艾柯的书都是很有趣的,比如《美的历史》《无限的清单》。这书《别想摆脱书》是他与一位同样爱好藏书的电影导演的对话录。话题都是关于藏书和书的历史。对于喜欢藏书和阅读的朋友来说,这是一本必须推荐的精品。我个人强烈推荐。这两位重量级的人物谈到了关于书的不为我们所关注的内容。比如:在人类的历史上,书除了是被保存的集体记忆,也是用来被遗忘的。还有我很关心的藏书的问题。如果有人问:你藏的书都看过吗?我要怎么回答呢?本书给了我们一个巧妙的回答,也说明了藏书不一定都要看过,也不一定都看完。另外,目前电子书发展快速,那么电子书会不会取代纸书呢?两位高手也有讨论。首先不论是电子书还是纸书,阅读并没有改变。而相对电子书,纸书更有优势。还谈到关于书与火的历史,那是很有趣的一段。
总之,别想用什么科技产品在短时间内取代书, 书不会退出历史舞台。这正是我这个爱书人希望的样子,借由本书,两高手给了我依靠。接下来,继续疯一样的买书吧。
《别想摆脱书》读后感(三):你家里的这些书都读过吗?
电子书大势之下,立志做藏书家的人不免叹气,可供把玩收藏的书籍越来越少,不是入了各种图书馆,就是被商人拍在手里当黄金使。普通人进这个圈子毫无前途,玩单反说不定还能泡个美女。
我可没有雄心要做藏书家。藏书家是要有资本的,经济实力首先要雄厚,如果不是,那么至少专业上必须十分懂行,版本目录学必须精通,八卦掌故必须背熟,见到好书被别人抢走必须沉得住气。最后,还必须有“藏书穷一生”的觉悟。
我只愿做个普通读者,然而,即便如此,也会遇到有人问出这样令你尴尬的问题:你家里的这些书都读过吗?
一般情况下,我都老实回答,没有,很多没读过。这时假如我偷看提问者的脸部表情,一定会发现他努力藏着但终于藏不住的笑意,仿佛是说,我就知道,谅你也不可能看完。得到这个答案,他心安理得并且感到安全,原来对面这个人不过是拿书充门面,买书不读,呵-呵。如果他性格阴暗一点,说不定还要在往后的谈话中“不小心”的数落你几句:真浪费!
对此,你能说什么呢?反正我是无力辩解。
然而,有人早就想好了对付这种不识趣者的法子,比如你可以这么回答,“比这还多,先生,比这还多。”你这么一说,对方除了哑口无言,料也没有第二选择了。或者你也可以夸口,“不,这些只是不过是我下周要读的书。”或者来个干脆的反问,“我一本都没读过。不然我留着它们干吗?”
这几面盾牌由“意大利国宝级的学者和作家”安贝托·艾柯打造,据说屡试不爽。艾柯本人拥有五万册藏书,是回答此类问题的不二人选。而这几句妙语,是在他与让-克洛德•卡里埃尔——法国国家电影学院创始人,西班牙电影大师布努埃尔的御用编剧——的对话录《别想摆脱书》里发现的。
面对不读书的人,要怎样说明藏书和读书之间的关系呢?卡里埃尔说,我们的藏书并不一定是由已经读过或将要读的书组成,它们应该是一些我们会读的书,或者我们可能读的书。即便最终可能没有读。这就类似藏酒不一定都要喝掉。
这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可能”。就像你知道你所生活的城市拥有一家舒适又有品位的书店会增加你的幸福指数,即便不经常去逛,但拥有了这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本身便能使你感受到一种丰富人生的美好之味。
《别想摆脱书》的两位谈话者都是藏书家,但是本书却不仅仅谈论藏书,而是由藏书引出一系列的话题,虽然看似散漫,但实际上有迹可循。在如今技术发达的互联网环境下,藏书的处境如何?书作为一种载体是否受到挑战?书籍的革命迫在眉睫?在漫长的历史中,一些书成为经典,而另一些则不,这仅仅因为作品本身吗?政治、宗教对书籍的迫害以及无知人类对于书籍的无声过滤,哪一种更为严重?
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如今的技术会不会让我们疏远书籍?要知道,我们已经能够明确的感受,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新的工具正在颠覆并使我们远离书籍所限定的思维习惯。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赞颂的印刷术时代下的思考方式已经离我们远去。
艾柯发现,“我们不再活在一个平和的现在之中,我们只是没完没了地为未来努力做准备”。我们处于永恒的变化和不安定之中,这到底是灾难还是好事?还没有人能下定论。
但是,艾柯和卡里埃尔都对书籍抱有强大的信心。我们的知识和文化素养很大程度上依靠记忆,在计算机比人可靠的世界里,背诵乘法表可能没有多大意义。但是,如何从自己的工具中抽取最好的部分,如何管理自己的记忆,仍然是一个不可替代的需要自身培养的技能。商铺黄页、百科全书可以被技术接替,但包含思想的书籍无可替代,艾柯不止一次提到一个关于书籍的比喻,他说,书就像轮子,一旦造好就没有改善的余地。
其次,我对这本书里的两个议题充满兴趣,一个是过滤,一个是愚蠢。这是相关的两件事。先来看看过滤,在人类的历史中,一些书籍浮出水面,直到现在我们仍在阅读,但另一些却早已湮灭于时间之海,为什么是这些还不是那些,是谁在选择?
他们得出了一个有意思结论,“我们对于过去的认识,归功于傻子、呆子和敌人”。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很多我们如今保存下来的残篇断简,很有可能只是因为当时的人没有发现它的价值,而加以忽略,就像如果有人问为什么西班牙人只摧毁了一部分前哥伦布时期建筑而保留了其他的?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没有看见。书籍一直遭受着宗教和政治的压迫,焚书事件不只中国独有,而在各种劫难中幸免于难,或许只是因为它被用作垫桌脚,或者被敌人重点批评而得以寄存。
这无疑是一种讽刺,随之而来的问题,如果不想被时间、文化和各种人为以及自然的灾害所湮没,有没有什么办法?
艾柯和他的小伙伴给出了两大法则。第一,如果一个作家想要避免被过滤,那么他最好联合、参与某个小群体,而不要保持孤立。就像木心总是强调天才总是一群一群的降生,孤立的天才不可想象。七星社的诗人,龙萨、杜·贝莱和马洛是知交。法国莫里哀、拉辛、高乃依和布瓦洛彼此相识。俄罗斯小说家们也互相往来,甚至和法国同行都保持书信往来,比如屠格涅夫和福楼拜。
第二,想要穿越历史,恒长久远,必须艰涩难懂。因为如此,才能经得起更多的解释和关于解释的解释,才能和这些解释一起形成力量对抗时间的侵蚀。杰作并非生来就是杰作,一部杰作要成为“杰作”,必须为人所知,吸收各种因它而起的解释,而这些解释最终将会成为它的一部分。伟大的作品往往通过读者而互相影响。
说道愚蠢,艾柯又有一大发现,一个让我脸红的发现,他说,从前的愚蠢没有爆发,不为人知,今天的愚蠢却肆意横行。如今人人都想发声(看看我),而没有人聆听,人人都是作者,但读者少的可怜,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别想摆脱书》读后感(四):假书亦是书
关于书的看法,最近真是遇到一本好书,是一本关于书的书。每次迫不及待去读,是急于听两位对书籍有真知灼见的大师聊天。那感觉特别像时下流行的对谈类节目,每章围绕一个关于书的命题,但内容也不拘泥,随想随说,金句频出,让人领略到卓越思想碰撞的美妙,于爱书人士来说十分过瘾。他们讨论了许多与书有关的问题,有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有些却连想都没想过。比如书籍经典形象的对立面们——虚妄、愚蠢、过滤、虚假等等,这些负面的标签并非与书籍无关。在人们习惯性将书作为智慧、光明、正确、未来的代表时,负面标签亦如影随形。有了这样的认识,对书籍的理解才更为立体丰富,才能对书籍获得更深的感知。人们对书籍以及对读书的担忧从未消失过,但两位大师却没有那么担心——谁会在轮子被发明后又去担心它的消失?书籍的地位不该被放低,但也绝不能过分抬高。这些年我也反思此事,它或许像打球玩牌一样,只是个人的兴趣而已。书不能让别人为你让路,却又能让你看到更多可选择的路,而决定与迈步,又能受书籍多少影响呢?
《别想摆脱书》读后感(五):别想摆脱书
这本书记录的是两位文学大家的对话。先马克一下这两位大人物的信息:
安贝托艾柯(Umberto Eco),享誉世界的哲学家、符号学家、文艺批评家和小说家,二十世纪最后一位百科全书式学者,少有的将精深学术与玄奥著作变成畅销书的作家,作品被翻译成三十五种文字之多。
让-克洛德卡里埃尔(Jean-Claude Carrière),法国电影泰斗、国家电影学院创始人、著名作家,《布拉格之恋》、《铁皮鼓》、《大鼻子情圣》等八十多部经典电影剧本的创作者,电影大师布努埃尔最青睐的编剧,龚古尔文学奖得主。
其实这本书真的很难写书评,我读完的时候很激动,刚好那天文答应过来了,就赶紧跟她推荐,又列举了书中的几个活脱脱的读书例子给她,我想,我能做的,其实也就只有摘录其中一些片段出来而已。读书的时候我不断地用荧光色的标签做记号,十几处最最精彩的都标识出来,这是一本肯定会重读的书,才有了这样的举动。我暗思索了几天,也找不到合适的角度来写这篇书评,班门弄斧的事情实不能为啊。读完这本书,我接着就看《莎士比亚书店》,才知道比起来这本还是比较亲切,起码也是我们当代的人物说当代的事情,而《莎士比亚书店》年代有点远,其中提到的很多作家和作品虽然也有知道的,但大部分是一头雾水。
本书讨论的话题目录分为13个,每个话题都有非常独特的观点,又与爱读书的人息息相关,篇幅不算太长,文章翻译也好,容易阅读。书评如果没写,我觉得就像没有了解这本书似的,才不得不逼着自己动手动脑。这次难度系高,我就依照之前的策略,根据我的标记写几个体会吧:
一,书的这个载体之意义。
这两位大师都是珍藏本的收集爱好者,他们有自己的一个专题或者说是爱好,根据这个标准来收集古书。虽然收集的书籍是不同的,但他们有共通点,就是喜欢搜罗那些与“谬论”、“虚假”相关的书。他们的观点是,尽管这些书是“错”的,但站在这个角度,它们也确实告诉我们一些过去的事。 这里面有一个例子,关于某些古老民族文化的消声灭迹,本身已经没有任何可以考据的真实文献存在,但是通过他们的敌人的记录,我们却可以从某个方面了解这些讯息。
书的这种阅读载体,在新科技时代的影响下,已经面临巨大的危机。电子书,电子浏览器的迅速普及以及它们的方便携带,已经使得书籍出版遭遇前所未有的打击。但书真的会因此就消失吗?两位作者认为,即使有可能存在未来的阅读载体不是书本,也无法让书籍灭亡。因为科技依靠的是电源,但书本的实实在在的阅读方式在只点煤油灯的情况下也可以实现,是它的优势。
二 、面对科技带来的威胁阅读习惯如何更改?
现今我们想知道某个词语的意义,或者某句话的出处,不再需要查阅大量的百科全书,只需要简单通过网络,比如维基百科,百度等搜索引擎就可以轻易获得。但这些信息没有经过严密的审核(也很难做到这点),所以如果说互联网上大量的信息一半真实一半虚假的话,我们作为人的这个角色,还需要有一个自我审查的功能需要开发。自发过滤筛选信息,化为已用。“知识塞满我们的脑袋,却不总是有用。认识则是把一种知识转化为生活经验。也许我们可以把不断更新知识这个任务交给机器,而把精力集中在认识之上。”(P81)
三、经典作品的经典之处
尽管这个世界上经典的作品数之不尽,但随着时代的更迭,有很多被前人备受推崇的作品却在今时今日遭受忽视,相反,某些被不待见的作品却在现今受到追捧。这是因为每个作品都无法脱离创作它的那个环境所影响。只有当某个时代某个环境与作品所在时代的背景有交集的时候,才能让读者得到共鸣。这其中不乏某些作品是经久不衰, 得到所有年代读者的青睐。比如书中提及的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我们的人生道路、个人经历、生活的时代、获得的信息,甚至我们的家庭变故、子女的问题,所有这一切都会影响我们对古代作品的阅读。”(P181),………"一本伟大的书的权威性、通俗性和现实性就在于此:我们打开书,它向我们讲述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从这一刻起真正地活着,我们的记忆获得补充,与书相系。”(P182)
四 、中国
本书提及中国文化的次数颇多,多得有点让我吃惊。特别是由于卡里埃尔,由于工作的关系他多次来到中国,在某些敏感时期也来到这里,并与当地的文化人频繁接触,有所了解。这里面有这么一段话:”有些人就是不可能接受世界的本来面目。他们没法重建世界,只好竭力重写世界。“
这确实是一本爱读书的人必须读一读的书,读书不是为了考取功名,不是为了打发时间,”为阅读而读,正如为生活而活。“(P315)